-

 CNAS L23010
CNAS L23010

 国家高新企业 | ISO9001认证 | 肠道健康精准检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 专精特新企业
国家高新企业 | ISO9001认证 | 肠道健康精准检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 专精特新企业 二级病原微生物安全实验室
二级病原微生物安全实验室- 联系电话:+13336028502
- +400-161-1580
- service@guheinfo.com


谷禾健康

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 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其特征是社交沟通和行为障碍,经常伴有兴趣或活动受限和重复的模式。遗传和环境都与自闭症有关。
近年来,多种类型的研究都将肠道菌群与自闭症的病因联系起来。前面我们的文章有提到,肠道微生物群影响宿主健康的许多方面,包括免疫系统控制、肠道激素调节和神经传递。它会改变摄入的药物及其代谢、毒素清除以及多种影响宿主的物质的产生。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肠-脑轴”的相互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大脑。
近期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可以通过中间细胞因子和代谢物诱发神经炎症。炎症偏差是肠道微生物群影响自闭症患者肠脑轴的潜在病因候选者。
神经炎症因素会导致肠道屏障完整性丧失、小胶质细胞激活和神经递质失调,从而导致自闭症。它强调了神经炎症中间体与自闭症患者肠道微生物群改变相关的潜在作用。具体而言,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钙卫蛋白、S100B、RANTES、嗜酸细胞趋化因子等细胞因子以及一些代谢物和微小RNA已被视为病因生物标志物。
了解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微生物群和神经炎症生物标志物的变化,是理解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病因、诊断、预后和治疗的基础背景。目前,自闭症谱系障碍的诊断是基于临床症状的,这可能会导致延误。基于与肠道微生物群相关的神经炎症过程的生物标志物可能是一种更客观精确可行的自闭症谱系障碍检测方法。
本文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神经炎症生物标志物在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发病机制和潜在诊断试验中的作用,还概述了益生菌及其他营养干预措施用作自闭症儿童的治疗策略及孕妇的饮食建议。
深入了解自闭症的复杂病理机制,结合生物标志物监测、肠道菌群管理和营养干预,或将为受影响的个体及其家庭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干预措施。
近 20 年前,有人提出了肠道菌群与自闭症之间的潜在关联。尽管自闭症的确切病因尚不完全清楚,但现有文献表明,自闭症患者存在肠道菌群失调和神经炎症。
自闭症的肠道菌群
总体而言,自闭症人群表现出菌群失调的迹象,与健康对照组相比,下列菌群和许多其他微生物的丰度有所不同:
拟杆菌门 / 厚壁菌门
普雷沃氏菌
梭菌属
乳杆菌属
双歧杆菌属
粪杆菌属
链球菌属
肠杆菌科
疣微菌属
梭杆菌门
大肠杆菌
肠球菌属
阿克曼菌属
考拉杆菌属
肠道菌群失调的识别与炎症途径
最近也有研究指出,自闭症儿童的肠道菌群失调和炎症可通过宿主粪便 DNA 特异性甲基化来识别。患有菌群失调的自闭症患者的炎症和免疫途径显著丰富,包括IL-2、IL-6 和 IL-12 的产生以及 Toll 样受体 (TLR3) 信号通路的激活。
多项研究一致证实了早期的发现,即菌群失调在各种神经退行性和神经精神疾病中会引起神经炎症。
自闭症儿童微生物组改变的潜在影响

doi.org/10.1016/j.bbr.2024.115177
菌群失调:免疫信号通路中断与自闭症严重程度
NLRP3炎症小体、1型干扰素和NF-κB信号通路等免疫信号通路的中断是菌群失调可能导致的后果之一。Th17/Tregs比例发生改变,巨噬细胞极化、TNF-α、IL-1β、IL-18、IL-6 失衡也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炎症和免疫失调已被证明与自闭症的发展和/或严重程度有关。先前对自闭症病例的研究表明,TNF-α、干扰素-γ、IL-2、IL-4、IL-5、IL-6、IL-8、IL-17、IL-10 等炎症标志物的水平升高。
神经炎症生物标志物与微生物交替和自闭症行为的关联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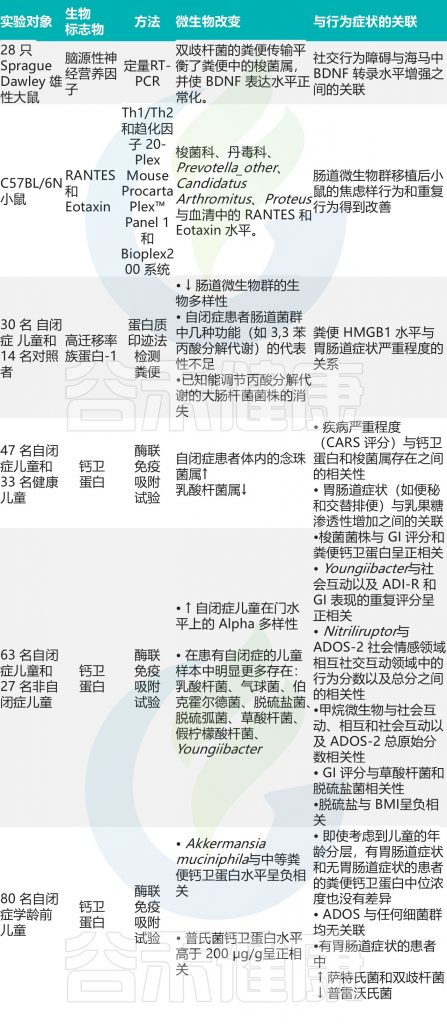

doi.org/10.1007/s10753-024-02061-y
关于自闭症患者肠道微生物组成和代谢物与炎症,这三个因素之间的确切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总体而言,肠道菌群似乎通过炎症在自闭症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些研究已将蛋白质和肽类生物标志物作为自闭症早期诊断的研究对象。S100 钙结合蛋白 β 亚基 (S100B) 在星形胶质细胞和其他神经外细胞(包括EGC)中表达。
注:EGC,enteric glial cells,肠神经胶质细胞,EGC是肠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调节肠道稳态、参与维持肠黏膜屏障功能,调控炎症反应,在消化及非消化系统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S100B对神经元的影响取决于浓度
浓度在几纳摩尔剂量下可产生营养作用,在微摩尔水平下可产生毒性。
S100B 促进神经炎症
细胞外蛋白 S100B 与促炎细胞因子协同作用,在较高浓度下可作为细胞因子,从而显著促进神经炎症。
自闭症 S100B 显著升高
尽管存在争议,但多项研究发现与健康人相比,自闭症患者的 S100B 显著升高,支持该因素在 ASD 的病因和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外周 S100B 浓度升高的来源可能是受损的神经元或 EGC。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血浆 S100B 水平与粪便钙卫蛋白浓度(胃肠道炎症状态的客观标志物)之间的相关性表明,不仅脑星形胶质细胞,还有 EGC 也可能参与自闭症的病理生理学。
肠道微生物群与S100B的相互作用
有一种假说认为,自闭症患者肠道胶质细胞衍生的 S100B 表达的改变可能是由微生物群改变、肠道屏障破坏甚至致病菌引起的,这些因素共同诱发肠道炎症并将 EGC 转化为反应性 EGC。
另一项小鼠体内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随着 S100B 水平或口服给药而增加。
厚壁菌门(包括乳杆菌)和拟杆菌门(包括Barnesiella和丁酸杆菌属)均受 S100B 水平的影响。然而,在一组自闭症儿童中观察到拟杆菌门水平较高,而厚壁菌门水平较低。可以考虑研究 S100B 作为自闭症诊断和治疗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BDN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是神经生长因子家族(神经营养因子)的蛋白质成员。BDNF 在突触前位点(调节神经递质释放)和突触后位点(增强离子通道功能)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它通常会影响神经可塑性,从而影响行为相关疾病。
BDNF与自闭症病理生理学的关联
多种神经系统疾病都存在 BDNF 水平异常,包括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甚至自闭症。最近的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自闭症患者的 BDNF 水平发生了改变,这表明 BDNF 可能在自闭症病理生理学中发挥作用。
与重度自闭症相比,轻度表型患者的 BDNF 水平相对较高,强调了该因子可能具有保护作用。自闭症患者脑内抗凋亡信号通路中 BDNF 的下调是自闭症病理生理的可能机制之一。
作为神经保护剂的 BDNF 表达减少可能是由炎症因子(包括 IL-1β 和 TNF)升高引起的;因此,它可能在神经炎症中起负调节作用。
肠道菌群与BDNF的相互影响
自闭症患者肠道菌群失调可能通过免疫失调和释放穿过血脑屏障的炎症因子(如 IL-1β)导致这种炎症状态。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了解自闭症患者肠道微生物改变的诱导和改变,是否可以通过 BDNF 水平进行监测和控制。
受激活、正常 T 细胞表达和分泌的调节,RANTES(CCL5)和嗜酸细胞趋化因子(CCL11)是由多种细胞释放的促炎趋化因子,包括血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上皮细胞、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
详情展开如下:
RANTES
RANTES是一种重要的趋化因子,属于CC亚家族的β趋化因子。它由多种细胞类型表达和分泌,包括T细胞、单核细胞、NK细胞、上皮细胞和血小板等。
RANTES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与其特异性受体结合来诱导白细胞向炎症部位迁移,从而在炎症反应中起关键作用。
这些受体包括CCR1、CCR3、CCR4和CCR5。RANTES不仅能够促进T细胞的活化和增殖,还能调节Th1/Th2细胞效应平衡。
嗜酸细胞趋化因子
嗜酸细胞趋化因子是一类属于CC趋化因子家族的小细胞因子,主要作用是选择性地募集嗜酸性粒细胞。
这些因子在多种组织中表达,并通过与特定受体结合来诱导嗜酸性粒细胞向特定位置迁移。主要包括CCL11、CCL24和CCL26。
不仅在过敏性疾病如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参与了其他炎症反应和肿瘤的发展。
RANTES和嗜酸细胞趋化因子在自闭症中的神经炎症作用
自闭症儿童的血浆中 RANTES和嗜酸细胞趋化因子水平明显较高。由于RANTES和嗜酸细胞趋化因子充当促炎介质,它们的升高意味着两者都在 自闭症中发挥神经炎症作用。
尽管Shen等人报告 RANTES 或嗜酸细胞趋化因子与自闭症的行为模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但Han 等人和 Hu 等人分别发现 RANTES 和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与自闭症相关。此外,其他研究表明这两个因素的增加都与自闭症相关。
肠道菌群诱导RANTES介导的炎症
早期研究发现,NOD 样受体家族含有吡啶结构域的 6-肠道菌群轴以及随后的 IL-6 和 TNF 释放是肠道菌群失调与 RANTES 介导的免疫失调之间的可能联系。
关于基因编码的表达,已发现肠道菌群可以操纵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的表达水平。在这方面,接受抗生素治疗的小鼠的微生物组发生了改变,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升高,小胶质细胞结构不同。
小胶质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常驻免疫细胞,是抵御病原体和损伤的第一道防线。它们不断探测大脑环境,寻找感染、损伤或疾病的迹象。小胶质细胞对全身炎症信号特别敏感。TNF-α和IL-6等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升高可激活小胶质细胞,使其从静息状态转变为活化状态。
激活的小胶质细胞可以吞噬细胞碎片、死细胞和病原体,并释放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来协调免疫反应。它们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发挥双重作用:促进炎症以抵御威胁,并在威胁过去后促进组织修复和炎症消退。慢性小胶质细胞活化与神经炎症有关。
粪菌移植与行为改善
此外,研究发现,小鼠的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水平在粪菌移植后发生了变化。关于肠道微生物群与自闭症的关系,在自闭症小鼠中,通过肠道微生物群移植,研究人员观察到焦虑样行为和重复性行为得到改善,而 RANTES 和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的水平得到改善。
这些结果表明,RANTES 和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在中枢神经系统突触传递和发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的水平与小鼠的微生物群结构有关。
特定菌群与趋化因子水平呈负相关
研究发现,梭菌科、丹毒丝菌科、普氏菌科、CandidatusArthromitus、变形杆菌属与 RANTES 和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的水平呈负相关。
通过益生菌改善
体内外用和口服益生菌治疗已报告与RANTES有关的菌株,包括副干酪乳杆菌SGL04、植物乳杆菌SGL07、发酵乳杆菌SGL10、短乳杆菌 SGL12裂解物以及鼠李糖乳杆菌GG有关。
同样,含有嗜酸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 GG和双歧杆菌的益生菌也改变了动物体内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基因的表达。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的重要发现表明肠道菌群通过 RANTES和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的炎症因子在自闭症发病机制和严重程度中的潜在机制。
细胞因子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M-CSF) 驱动髓系造血细胞生物学的许多方面,包括存活、增殖、分化和功能活动。它还通过树突状细胞和 T 细胞功能影响免疫系统。GM-CSF 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慢性炎症,并作为神经元生长因子刺激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分化。
GM-CSF在自闭症中的复杂作用
一些早期研究认为自闭症患者的 GM-CSF 水平较低,但随后的研究在自闭症患者大脑中发现 GM-CSF 水平较高。
研究发现,在同时出现胃肠道症状的自闭症儿童中,GM-CSF-IL-1α、TNF-α 和干扰素-α 的水平较高。自闭症中 GM-CSF 水平的变化可能表明炎症过程可能与发育和神经免疫障碍有关。
Takada 等人的共培养实验结果首次表明,GM-CSF 诱导的巨噬细胞可抑制自闭症个体神经元的树突状生长。这种现象是通过促炎细胞因子IL-1α和TNF-α的分泌介导的,并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行为影响。
肠道菌群与GM-CSF的关联
有趣的是,GM-CSF 水平随着肠道菌群的变化而变化,且主要与 IL-17a有关,IL-17a 是一种与 自闭症患者行为症状严重程度相关的细胞因子。
不同种类的肠道细菌与 GM-CSF 有关,包括副拟杆菌、普氏菌、链球菌、梭菌、罗伊氏乳杆菌、卷曲乳杆菌、粪肠球菌、布劳特氏菌、丁酸单胞菌、罗斯氏菌、Anaerotruncus、Blautia。一项重要发现表明,肠道菌群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可能会改变 GM-CSF 水平。
一项研究表明,使用含有长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的益生菌可增加神经免疫因子 GM-CSF。
总之,肠道菌群改变导致 GM-CSF 神经炎症因子的变化,为了解自闭症患者发病机制提供了思路。
高迁移率族蛋白 1 (HMGB-1) 是 HMGB 蛋白家族中最丰富的成员之一,具有许多潜在作用。作为核蛋白,它在DNA调控活动中起关键作用。作为一种细胞外因子,它在免疫细胞对炎症作出反应时主动释放,也会被坏死或受损细胞被动释放。
HMGB-1的多功能性和在炎症中的作用
HMGB1 具有多种膜受体,称为病原体识别受体,其中 TLR4、TLR9 和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 (RAGE) 是主要受体。通过与这些受体的相互作用,HMGB1可促进细胞炎症。HMGB1 可以穿过血脑屏障,促进神经突生长和细胞迁移,或介导损伤后的神经炎症。
HMGB-1与自闭症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已知自闭症患者血浆中的HMGB-1水平会升高,并且与自闭症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另一种有效的炎症分子——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与自闭症儿童的症状严重程度有关,而 HMGB1 水平与之相关。
肠道功能障碍与HMGB-1水平的联系
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的 HMGB1 水平较高与胃肠道功能障碍较高有关,这可能意味着肠道是发病机制的一部分。
类似的研究表明,粪便中的HMGB1水平与自闭症儿童的胃肠道体征严重程度相关,这与自闭症相关的菌群失调有关。伴有肠道炎症的微生物群失调可导致单核细胞的激活,上调 HMGB1 的排泄,从而形成促炎反馈回路。
扩展阅读:炎症回路和肠道微生物
HMGB-1与自闭症行为表现的关联
较高水平的 HMGB1 和 TLR4 也与小鼠的自闭症样行为有关,可能是通过激活 HMGB1/TLR4 信号级联实现的。
自闭症儿童血清中 TLR4 水平升高,并且与他们的多动评分呈正相关。这进一步强调了炎症因子在自闭症行为表现中的作用。
HMGB-1在神经炎症中的作用机制
HMGB1/RAGE/TLR4 轴的激活会导致白细胞浸润到神经细胞中,从而引起持续的中枢神经系统炎症。有研究表明,神经炎症与自闭症的发生密切相关,其机制是激活炎症小体系统。此外,HMGB1 可以与内源性分泌性 RAGE 结合,导致血浆 RAGE 水平下降。这可能通过干扰神经肽催产素从外周到大脑的运输,导致自闭症的病理生理。
益生菌和肠道菌群改变对自闭症患者 HMGB1 水平的影响可以强化这一想法,并可以进一步研究。HMGB1 可能通过神经炎症在自闭症发病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可以指导治疗策略。然而,它是自闭症病理生理学中一个非常潜在的因素,尚未明确阐明,需要更多研究。
骨桥蛋白 (OPN) 是一种可溶性促炎细胞因子,在自身免疫性神经炎性疾病中发挥着明确的作用,同时也是控制骨组织生物矿化的非胶原骨基质的组成部分。
OPN的功能多样,根据其位置和环境,OPN 参与局部炎症、细胞粘附、免疫反应、趋化性和防止细胞凋亡。
OPN在免疫调节中的作用
Heilmann 等人认为 OPN 可以在急性炎症期间激活免疫系统、减少组织损伤并刺激粘膜修复,同时在慢性情况下促进 Th1 反应并增强炎症。
OPN与神经系统疾病的关系
OPN 与多发性硬化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心理疾病的发病机制有关。CD11c + 细胞表达分泌性磷蛋白1 及其编码蛋白 OPN 与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障碍和常见神经病变有关。
注:CD11c+ 是一种在多种免疫细胞上表达的分子,主要与树突状细胞(DCs)相关。CD11c+ 标记物在免疫系统中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例如,在炎症性关节炎模型中,CD11c+ 树突状细胞的存在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OPN在自闭症研究中的发现
有研究发现血清中 OPN 水平升高与病情严重程度有关,表明 OPN 在神经炎症和大脑特异性自身抗体的产生中的作用。他们的发现可以支持 OPN 是自闭症机制中重要神经炎症因子的观点。
在代谢紊乱中,人们讨论了 OPN 与肠道微生物群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然而,OPN 与肠道微生物群在神经系统疾病(尤其是自闭症患者)中的作用尚未得到研究,这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潜在目标。
钙卫蛋白是一种与钙结合的蛋白质,主要存在于中性粒细胞中,中性粒细胞是一种白细胞,在炎症和细胞损伤时会增加。
粪便中的钙卫蛋白可以指示肠道炎症,并可作为生物标志物。
钙卫蛋白与自闭症
考虑到肠道炎症在自闭症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许多研究已经研究了自闭症患者中钙卫蛋白水平的关联,但结果并不一致。
一些报告显示,自闭症患者及其亲属的钙卫蛋白水平可能高于对照组。
钙卫蛋白与炎症及自闭症的关联
钙卫蛋白水平也与巨噬细胞炎症蛋白 1β 的较高表达呈中等相关性,而巨噬细胞炎症蛋白 1β 与自闭症诊断观察计划的沟通分量表和总分相关,表明它可能在微生物-神经元串扰中发挥作用。不太可能的是,一些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和对照组之间的钙卫蛋白水平没有统计学上显著差异,因此,有和没有胃肠道症状的自闭症患者的钙卫蛋白水平没有明显变化。
钙卫蛋白水平与肠道菌群的关系
Laghi 等人的研究表明,钙卫蛋白水平较高与肠道中普雷沃氏菌较多和阿克曼氏菌减少有关,表明这些细菌可能分别具有炎症或保护作用。
益生菌疗法对自闭症患者的影响
Santocchi 等人发现益生菌疗法(包括 多种链球菌、双歧杆菌、乳杆菌)对自闭症患者的适应功能有有利影响,但对有或无胃肠道症状的钙卫蛋白水平没有明显影响。这表明益生菌对自闭症患者的影响比减少肠道炎症更为复杂,钙卫蛋白作为可能的神经炎症介质的作用应得到进一步研究。
总体而言,钙卫蛋白研究的异质性可能是由于试验个体的多样性、所用方法的准确性以及对微生物群改变和钙卫蛋白的同时研究不足造成的。但我们仍然可理解宿主微生物群失调和炎症诱导的钙卫蛋白会触发导致自闭症方面的神经炎症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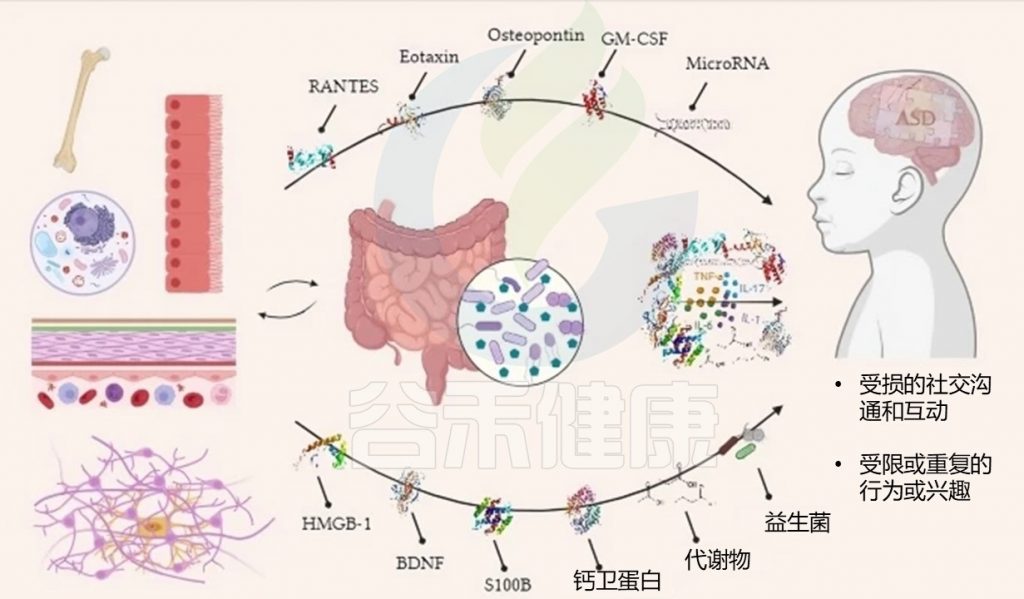
doi.org/10.1007/s10753-024-02061-y
在自闭症患者中,许多肠道微生物衍生的代谢物尤为突出,例如复合多糖或代谢氨基酸,它们可以作为神经递质。其中几种代谢物最近被讨论作为自闭症的早期诊断生物标志物。
特定菌群与短链脂肪酸的生产
肠道微生物通过一组重要的代谢物来调节宿主的生理机能,这些代谢物是短链脂肪酸,主要构成乙酸盐 (AA)、丁酸盐 (BTA) 、丙酸盐 (PPA)。
自闭症患者短链脂肪酸研究不一致
与某些研究不同,其他研究报告称自闭症患者的 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水平高于对照组。这些肠道菌群相关的短链脂肪酸在宿主的炎症反应中表现出相互冲突的促炎和抗炎作用,可能是由于结合受体和局部浓度的差异。一些动物研究表明,补充微生物代谢物乙酸盐和丁酸盐可以逆转社会行为表型。
相反,在大鼠脑室内注射丙酸盐会诱发自闭症样症状,包括反应性神经胶质增生。丙酸盐可通过调节自闭症中的 PTEN/AKT 通路导致神经胶质增生、神经回路紊乱和神经炎症反应。
短链脂肪酸在自闭症和肠道微生物群中的意义

doi.org/10.1016/j.bbr.2024.115177
由于关于自闭症患者短链脂肪酸水平的发现数据不一致且尚待研究,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短链脂肪酸在自闭症病理生理学中的潜在作用。它们可能被视为自闭症患者神经炎症生物标志物和肠道微生物群改变的指标。
COX1 和 COX2
脂质是大脑的主要成分,脂质代谢物是大脑发育和体内平衡的调节分子。作为脂质介质的主要脂质代谢物是前列腺素 (PG) 和白三烯 (LT),它们分别由花生四烯酸 (AA) 和其他不饱和脂肪酸在环氧合酶 (COX) 和脂氧合酶 (LOX) 的代谢下代谢。
已知 PGE2 信号在大脑形态形成中发挥作用,COX2/PEG2 信号受损与 MIA 模型中的自闭症发病机制有关。COX 通路涉及两种限速酶,COX-1 和 COX-2。
用于诱导 MIA 的内毒素和 MIA 模型中产生的炎症介质(IL-1β、IL-6、TNF-α、IFN、AA)均可诱导 COX-2。此外,有证据表明 COX-2 介导 N-甲基-D 天冬氨酸 (NMDA) 神经毒性。
COX2 和 自闭症
先前的研究使用自闭症患者的外周血单核细胞作为小胶质细胞的替代品,观察到在先天免疫刺激下上述细胞因子的产生增加。这种增加发生在有微生物感染后行为症状和认知功能波动史的自闭症患者中。有趣的是,自闭症患者血浆中的 COX-2 和 PGE2 升高,同时 α-突触核蛋白水平降低。因此,阻断 COX-2 可能有助于减轻自闭症患者的神经炎症和随后的神经元损伤。另一方面,脑中 COX-2 的上调可能具有神经保护作用,部分调节脑血流。
关于 COX-2 抑制剂在 ASD 患者中的临床试验数据很少。只有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研究了 COX-2 抑制剂塞来昔布对 ASD 患者行为症状的疗效。
该试验将塞来昔布作为利培酮的辅助治疗,持续 10 周;使用异常行为检查表 (ABC) 评估行为症状。发现ABC分量表的易怒、嗜睡和刻板行为有显著改善。
当使用塞来昔布控制病毒性流感等综合征引起的 自闭症行为症状恶化时,也经常观察到 COX2 抑制剂塞来昔布减轻行为症状。吡格列酮具有多种抗炎作用,包括抑制小胶质细胞上 COX-2 的表达。吡格列酮对创伤性脑损伤有有益作用。
综上所述,COX-2抑制剂可能对有COX2激活迹象的自闭症患者有益,尤其是在急性和/或亚急性期。
自闭症患者中犬尿氨酸代谢产物的变化
例如,自闭症的患者尿液中神经毒性色氨酸代谢物的浓度增加。有报道称,自闭症患者中犬尿氨酸代谢物的靶分子 NMDAR 亚基的多态性 ,以及其他色氨酸代谢物的水平改变。
据报道,大约三分之一的自闭症患者具有高循环 5-HT 水平,这主要反映了肠道产生并储存在血小板中的 5-HT。5-HT 水平的变化可能与肠道 5-HT 代谢的变化和/或肝脏和肺部 5-HT 清除率的变化有关。然而,高血清素血症和特征性 ASD 行为症状之间的关联尚未得到一致证实。
同样,抑制 5-羟色胺再摄取转运蛋白 (SERT) 作用的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SSRI) 对 自闭症患者并没有普遍有益的作用。这些发现表明,其中存在复杂的潜在机制。
有趣的是,对主要致病成分和生物内表型(包括血液中 5-羟色胺水平)的分析发现,与自闭症患者的免疫功能障碍有关。在同一研究人群中,免疫成分对表型变异的贡献最大;这些结果支持免疫激活对自闭症受试者血清素代谢的影响。
色氨酸影响大脑功能的 4 种不同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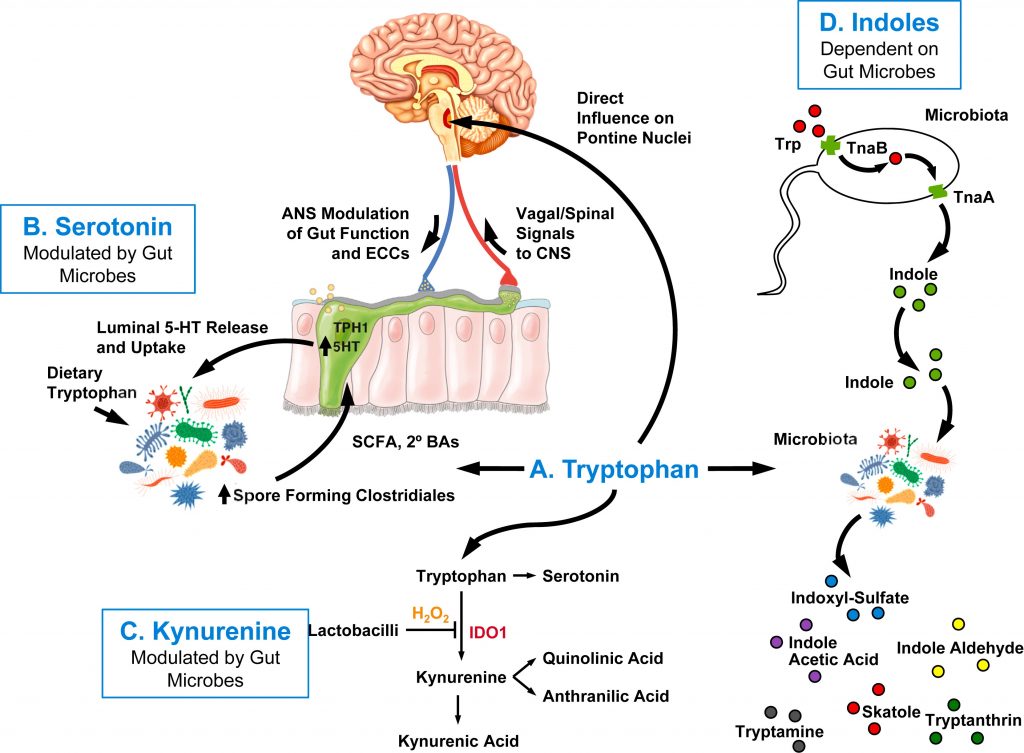
doi.org/10.1016/j.biopsych.2023.10.018
色氨酸[A]、血清素[B] 、犬尿氨酸[C]、吲哚[D]。其中三种途径依赖于肠道微生物代谢,而另一种途径中,色氨酸通过体循环到达缝核,无需微生物修饰。
自闭症与血清素代谢物研究的总结
SERT多态性与自闭症
米诺环素对色氨酸代谢的影响
当色氨酸代谢物的复杂稳态受损时,米诺环素可能对特定情况有效,从而导致犬尿氨酸代谢物的毒性作用恶化。将米诺环素用作自闭症患者的治疗选择需要谨慎选择自闭症患者。
miRNA 在神经系统中的作用
超过 60% 的人类基因受微小 RNA (miRNA) 控制,微小 RNA 是一种小型非编码 RNA,长度约为 18 到 24 个核苷酸,可作为表观遗传调控因子。miRNA 可改变大脑的可塑性和神经元的发育,其失调会导致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包括自闭症。miRNA 已充分证实其可调控多种细胞和生理过程,包括造血、免疫反应、炎症。此外,miRNA 还受宿主-微生物群相互作用的影响,并在菌群失调和诱发炎症中发挥关键作用。
miR-146a 是自闭症中失调最严重的miRNA
一项深入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中存在过度表达的 miRNA,它们可能通过失调的炎症基因在神经发育受损中发挥作用。
此外,一些研究还发现,miRNA 通过与调节炎症小体表达的 3′-UTR 基因相互作用直接或间接激活炎症小体。具体而言,动物研究表明 miR-146a 的增加或减少可能是自闭症的潜在原因。
一项产后临床研究比较了自闭症和健康对照者的 miRNA,证实 miR-146a 是自闭症中失调最严重的 miRNA。
miR-146a 和 miR-155 在自闭症中的作用
另一项使用体外模型和死后人脑组织的研究也发现,早在儿童时期即可在自闭症患者脑中检测到 miR-146a 过表达。肠道菌群-宿主相互作用的变化可能诱导 miR-146a,从而促进神经炎症途径。值得注意的是,miR-146a 诱导的核因子 κB 增强了肠-脑轴的炎症信号通路。
研究表明,脆弱拟杆菌、鼠李糖乳杆菌 GG、嗜酸乳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大肠杆菌Nissle 1917与 miR-146a 表达相关。
另一项研究表明,miR-146a 对某些炎症细胞因子表达至关重要,其在大脑中的缺失会导致 miR-155整体补偿性上调。蛋白质羰基化增强和半胱氨酸硫醇水平降低是氧化应激介质激增导致神经炎症通量升高的额外指标。
miR-146a和miR-155如何与慢性炎症相关?
多项研究已将 miR-146a 和 miR-155 与慢性炎症所指的各种病理状况联系起来。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肠道毒素(如 LPS)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并进入体循环,可能激活 NF-kB-miRNA-146a-miRNA-155 信号通路。该通路会将来自微生物组的致病信号传递到大脑,这可能会扰乱先天免疫反应并导致神经炎症。
肠道菌群失调也可能改变 miR-155
一项研究增加了证据表明,自闭症儿童的杏仁核、额叶皮质和小脑中的 miR-155 表达增加。miRNA-155 参与细菌脂多糖对 TLR 的激活、肿瘤坏死因子-α 和 IL-6 的激活以及对树突状细胞上细胞因子信号传导抑制因子 1 的调节。这些活动,加上微生物群失调的变化,可以使 miRNA-155 成为肠脑轴和自闭症神经炎症机制中的候选角色。
早期研究发现,发酵乳杆菌、唾液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GG、嗜酸乳杆菌、德氏乳杆菌、双歧杆菌和大肠杆菌 Nissle 1917 等益生菌可以改变 miR-155的水平。
miR-181在自闭症中的潜在影响
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的 miR-181 上调,预计会影响自闭症相关的神经连接蛋白 1基因。神经炎症和免疫失调是与 miR-181 家族相关的众多生理过程中的两种。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可以调节小鼠的 miR-181。还有研究显示,鼠李糖乳杆菌和德氏乳杆菌益生菌会影响炎症疾病中 miR-181a 的表达。此外,来自肠道菌群的代谢物可能影响不同状态下的 miR-181表达。总之,这些证据强化了 miR 介导肠道微生物群可能通过自闭症中的神经炎症过程发挥作用的论点。
生酮饮食对miRNA及自闭症的影响
一项小型介入性随访研究,分析七名儿童包括在生酮饮食之前和生酮饮食 4 个月之后收集的血液和粪便样本。经过 4 个月的随访发现,生酮饮食 导致促炎细胞因子(IL-12p70 和 IL-1b)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的血浆水平下降。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肠道中丁酸激酶表达的增加以及血浆中 BDNF 相关 miRNA 水平的变化。这些队列研究结果表明,生酮饮食可能通过减少炎症、逆转肠道微生物群失调以及影响与大脑活动相关的 BDNF 通路对自闭症社交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生酮饮食诱导的神经炎症变化的拟议间接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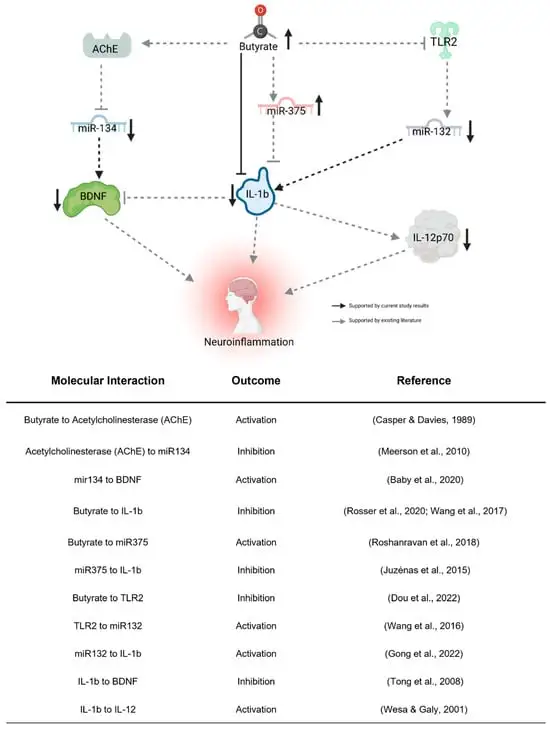
doi.org/10.3390/nu16101401
益生菌可以通过各种机制影响宿主的健康。据最近的研究,它们可以作为治疗工具,通过恢复肠道菌群的健康平衡、调节组织中的神经递质水平以及减少肠道炎症来治疗自闭症。
动物模型显示,益生菌显著改变了大鼠的社交和情感行为以及血液中 IL-6、IL-17a 和 IL-10 等细胞因子的水平。另一方面,只有少数试验从炎症调节和免疫系统调节方面评估了益生菌对自闭症的影响。
益生菌在炎症和自闭症管理中的作用试验

doi.org/10.1007/s10753-024-02061-y
有研究评估了婴儿双歧杆菌与牛初乳产品联合用于自闭症儿童的情况。一些患者出现胃肠道症状和异常行为的频率较低,可能是由于TNF-α和 IL-13 减少所致。
益生菌对自闭症儿童炎症标志物和症状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粪便中TNF-α水平与自闭症严重程度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表明胃肠道炎症和通透性可能通过炎症途径参与自闭症。他们可以通过补充益生菌(包括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和 链球菌)显著降低自闭症儿童粪便中的TNF-α水平。
在患有胃肠道问题的自闭症儿童亚组中,益生菌治疗组的一些胃肠道症状、适应性功能和感觉状况比安慰剂治疗组有较大改善。
益生菌混合物的应用
目前尚无针对自闭症核心缺陷的药物。因此,迫切需要为自闭症患者开发新的药理学方法。总体而言,这些发现表明益生菌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治疗方法,因为它们对自闭症症状有有益的影响。考虑到免疫系统功能障碍与行为异常之间存在关联,以及肠道微生物群可能通过炎症介质对 自闭症产生影响,建议在益生菌给药期间检查神经炎症变量,并确定改变这些变量的最有效配方。
无麸质和无酪蛋白饮食
研究发现,单纯的无麸质饮食对自闭症儿童的症状、行为或智力能力没有显著影响。
当无麸质饮食结合其他干预措施(如维生素、矿物质、必需脂肪酸、肉碱、硫酸镁浴、消化酶和无酪蛋白、无大豆饮食)时,观察到在非言语智力能力和自闭症症状方面有显著改善。
改良的生酮无麸质饮食
一项研究评估了补充MCT的改良生酮无麸质饮食对自闭症症状的影响,为期3个月的干预导致自闭症核心特征显著改善。
低FODMAP饮食
一项实施低FODMAP饮食的研究在自闭症儿童中未发现行为问题的显著差异。
适合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饮食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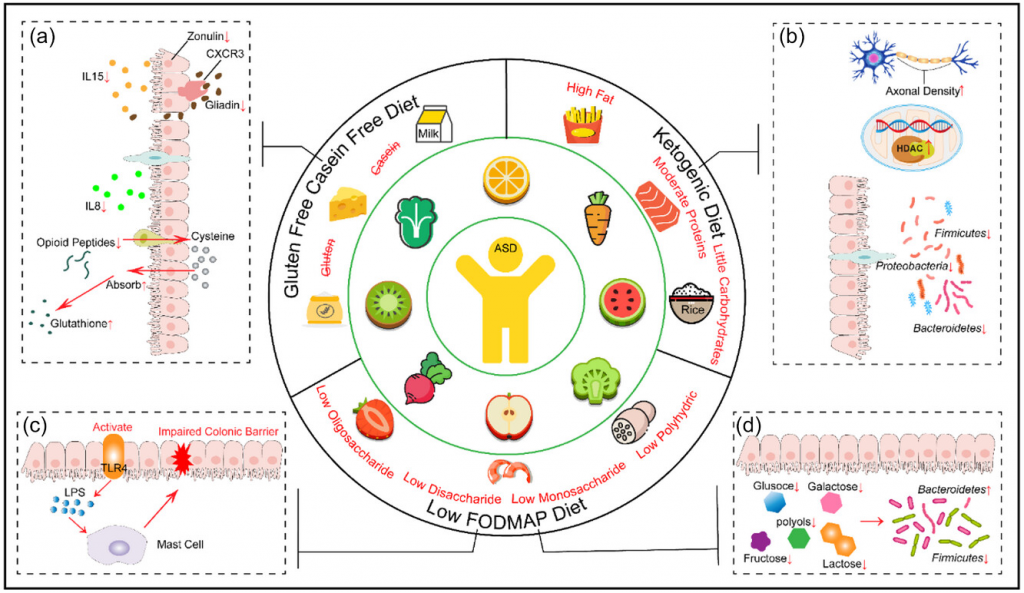
doi.org/10.1002/fft2.380
a)无麸质/无酪蛋白(GFCF)饮食可以使肠黏膜组织正常化,恢复肠上皮细胞对半胱氨酸的吸收,提高谷胱甘肽水平,增加甲基供体,防止甲基化抑制;
b)生酮饮食(KD)可以优化肠道菌群结构,降低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和变形菌的丰度,调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活性,增加脑神经元轴突的密度;
c、d)低发酵寡糖-双糖-单糖-多元醇(FODMAP)饮食可以通过激活toll样受体修复受损的结肠屏障,同时调节肠道菌群以恢复肠道稳态。
必需脂肪酸补充
多项研究调查了ω-3脂肪酸补充对自闭症症状、发展年龄和营养状况的影响。综合分析显示,ω-3脂肪酸补充显著改善了干预组的刻板行为、多动、社交沟通、非言语智力能力、发展和营养状况。
肉碱
肉碱补充在自闭症患者的一年营养计划中显示出改善非言语智力能力和症状的效果。
萝卜硫素
萝卜硫素是一种存在于十字花科蔬菜中的膳食异硫氰酸酯,是一种营养保健食品。几项研究探索了萝卜硫素在自闭症治疗中的潜力,报告显示在行为和生化标志物方面有所改善。
多项研究调查了维生素补充对自闭症患者症状严重程度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维生素A
维生素A补充对自闭症症状有显著缓解作用,特别是通过增加血清中的维生素A水平来改善社交响应性。
维生素D
维生素D补充在减少多动、减轻易怒方面有效,并可能与ω-3联合使用时进一步改善自闭症症状。
矿物质
锌的补充被认为可以增强自闭症患者的认知-运动功能。
肌肽
肌肽补充对自闭症儿童的睡眠障碍有积极作用,但对自闭症症状的严重程度影响不大。
益生元
一项针对 30 名自闭症儿童的为期 6 周的研究表明,益生元干预显著减轻了胃肠道不适并改善了排便,但对睡眠或胃肠道症状没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韦荣球菌科和双歧杆菌减少,拟杆菌属和普拉梭菌增加。
一项为期 12 周的小规模试点研究针对 8 名患有 自闭症和胃肠道合并症的儿童,发现益生元补充剂可显著减少异常行为(嗜睡、多动、刻板行为和易怒)并改善胃肠道症状,这可能是由于肿瘤坏死因子α 和IL-13 的产生减少所致。

doi.org/10.1016/j.rasd.2024.102352
近期研究表明,孕妇饮食中某些营养素含量高与患自闭症的风险增加有关。
在这些饮食因素中,孕妇饮食中水果和蔬菜上的农药残留可能是导致胎儿神经发育异常的重要暴露因素。
孕妇蛋白质营养不良和高咖啡因摄入量均与胎儿发育受限和后代患自闭症的风险增加有关。
每日盐的摄入量也可能是一个条件性危险因素。具体而言,盐摄入量增加对身体免疫系统和肠道微生物群有显著影响,导致肠道稳态失衡和炎症的发生,进一步通过菌-肠-脑轴导致神经发育异常。
母亲怀孕期间不良的饮食模式会增加后代患自闭症的风险。例如,高能量、高密度饮食和西式饮食均可导致自闭症发病率增加。
与这些不良饮食因素相反,怀孕期间摄入足够的维生素和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与后代自闭症发病率较低相关。
此外,增加孕妇膳食中的锌含量可以预防与自闭症相关的社交缺陷和焦虑症状。除了避免上述与孕期不良饮食有关的潜在风险因素外,患有糖尿病、肥胖或高血压等潜在风险的孕妇应特别注意每日膳食摄入量。
肥胖孕妇的饮食建议
基于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母亲肥胖和怀孕期间体重大幅增加均与后代患自闭症的风险增加有关。
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会导致肠道中的短链脂肪酸水平异常。高膳食纤维干预和短链脂肪酸疗法可以缓解由此产生的后代的认知和社交功能障碍。高纤维饮食可能减少突触损伤和小胶质细胞缺陷,降低后代神经发育障碍风险。所有母亲无论胖瘦,都应在怀孕期间避免高脂肪饮食,以降低后代患精神疾病的风险。
动物研究表明,母鼠的高脂饮食选择性地促使雄性子代脑内免疫细胞过度消耗5-HT,从而导致神经系统异常。
孕期高脂、高糖饮食可能导致炎症介导的神经发育障碍,增加自闭症风险。肥胖女性在孕期应限制脂肪和糖摄入,增加膳食纤维摄入,以降低后代精神疾病风险。
糖尿病孕妇的饮食建议
众多研究发现母亲孕期患糖尿病与子代罹患自闭症风险增高显著相关。
短暂性高血糖可能引发持续性表观遗传改变和紧密连接蛋白表达抑制,伴随活性氧产生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表达的抑制。动物研究显示,高血糖可诱导子代杏仁核中活性氧产生和SOD表达抑制,诱导自闭症样表型。
母亲糖尿病介导的氧化应激可能导致消化道功能障碍、肠道通透性增加、肠道微生物组成改变和神经元基因表达抑制,最终导致后代出现自闭症表型。母亲糖尿病可能抑制造血干细胞SOD表达、诱导炎性细胞因子,导致子代自闭症患者免疫功能紊乱。
妊娠期糖尿病女性应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适量摄入具有抗糖尿病作用的食物,如洋葱和苦瓜。传统植物,如葱属、苦瓜属和荆芥属植物,含有抗糖尿病功效成分,可能有助于控制血糖。
维生素B6和维生素D的补充对降低后代罹患自闭症风险和改善糖尿病相关并发症有益。矿物质如锌和铬有助于保护糖尿病患者免于产生胰岛素抵抗。
妊娠高血压孕妇的饮食建议
妊娠期高血压与后代神经发育障碍和自闭症风险增加有关。
DASH饮食是一种有效的降低血压的饮食干预措施,通过增加粗粮、蔬菜、蛋白质、纤维素、钙和钾的摄入,并限制食盐摄入,可以显著降低血压。高质量的DASH饮食还与降低后代焦虑、行为缺陷和神经发育障碍的风险相关。
补钙和增加膳食钾的摄入也有助于预防妊娠高血压。此外,高血压的发病与肠道菌群有关,通过增加南美油藤的摄入量,可以缓解高血压。
类风湿性关节炎孕妇饮食建议
母亲类风湿性关节炎也与后代患自闭症的风险增加有关,可能通过炎症或免疫机制导致自闭症的发展。目前尚无特定的饮食模式来预防这种风险,但食用具有抗炎症或自身免疫反应的食物,如含有酚类和三萜类化合物的水果和蔬菜,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替代方案。
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探索孕期饮食与菌群和炎症之间的联系,并开发有效的预防策略。
扩展阅读:深度解析 | 炎症,肠道菌群以及抗炎饮食
鉴于自闭症病理生理的复杂性和不明确性,近年来人们对炎症机制和免疫失调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自闭症中的失调途径在病因上也可以追溯到肠道微生物群失调。
这些变化可能通过释放的代谢物、BDNF的神经信号通路和神经炎症生物标志物(包括 S100B、HMGB-1、OPN、miRNA、RANTES、嗜酸细胞趋化因子和 GM-CSF)与自闭症症状和严重程度有关。
本文强调了介质作为触发机制和桥梁作用,一方面是肠道微生物群失调引起的炎症,另一方面是自闭症中枢神经系统神经炎症过程。益生菌作为恢复自闭症微生物群的适用治疗选择,表明肠道微生物群的相关性和潜在的有益影响。
然而,考虑到微生物群改变类型、神经炎症介质的巧合、干预时间长度以及自闭症年龄和症状等个体差异,评估个体肠道菌群状况以及不同益生菌及其他配方的功效对于自闭症的干预至关重要。
随着对微生物群与自闭症关系的深入理解,一个多维度的临床视角逐渐显现。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微生物群的变化、相关的代谢产物、神经炎症介质以及它们与自闭症患者中枢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在临床上描绘出自闭症的发展轨迹,这些研究的整合可能有助于我们构建一个综合的框架,用于自闭症的早期识别、干预和长期管理。
主要参考文献
Zarimeidani F, Rahmati R, Mostafavi M, Darvishi M, Khodadadi S, Mohammadi M, Shamlou F, Bakhtiyari S, Alipourfard I. Gut Microbiota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Neuroinflammatory Mediated Mechanism of Pathogenesis? Inflammation. 2024 Aug 2.
Yu R, Hafeez R, Ibrahim M, Alonazi WB, Li B.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gut microbiota in childre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Behav Brain Res. 2024 Aug 2;473:115177.
Allan NP, Yamamoto BY, Kunihiro BP, Nunokawa CKL, Rubas NC, Wells RK, Umeda L, Phankitnirundorn K, Torres A, Peres R, Takahashi E, Maunakea AK. Ketogenic Diet Induced Shifts in the Gut Microbiome Associate with Changes to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Brain-Related miRNA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Nutrients. 2024 May 7;16(10):1401.
Li, Wentian, et al. “Dietary nutrients that potentially mitigat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dietar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ldren and pregnant women.” Food Frontiers 5.3 (2024): 920-946.
Aldegheri, Luana, et al. “Impact of Human Milk Oligosaccharides and Probiotics on Gut Microbiome and Mood in Autism: A Case Report.” Microorganisms 12.8 (2024): 1625.
Ross FC, Mayer DE, Gupta A, Gill CIR, Del Rio D, Cryan JF, Lavelle A, Ross RP, Stanton C, Mayer EA. Existing and Future Strategies to Manipulate the Gut Microbiota With Diet as a Potential Adjuvant Treatment f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Biol Psychiatry. 2024 Feb 15;95(4):348-360.
Kim J.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Eating Problems: The Imbalance of Gut Microbiota and the Gut-Brain Axis Hypothesis. Soa Chongsonyon Chongsin Uihak. 2024 Jan 1;35(1):51-56.
Camberos-Barraza, J.; Guadrón-Llanos, A.M.; De la Herrán-Arita, A.K. The Gut Microbiome-Neuroglia Axis: Implications for Brain Health, Inflammation, and Disease. Neuroglia 2024, 5, 254-273.
Jyonouchi 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a possible role of anti-inflammatory treatments: experience in the pediatric allergy/immunology clinic. Front Psychiatry. 2024 Jun 24;15:1333717.

谷禾健康

饮食在塑造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功能和多样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各种饮食对肠道内微生物群落的稳定性、功能性和多样性有着深远的影响。了解不同饮食对微生物群的深远影响至关重要,改善代谢和肠道健康,预防和减缓由饮食不当引起的特定饮食相关疾病的发生。
在生命早期,分娩方式、喂养、饮食和环境等因素会塑造肠道微生物群。在成年期,虽然微生物群趋于相对稳定,但外界因素,尤其是饮食,会大大影响其组成和功能。营养素、微生物群和免疫系统之间的这种复杂相互作用是维持体内平衡和防御外部病原体的重要调节机制。
精准营养承认每个人对饮食的代谢反应会有所不同,因此针对人群健康的广泛饮食指南在个人层面上并不理想。一些大规模研究已开始将微生物组概念纳入精准营养,发现纳入肠道微生物组组成的预测模型远远优于仅基于宿主、饮食和身体活动因素的预测模型。
比如从控制体重来说,我们常常关注卡路里的摄入与消耗,却可能忽略了肠道菌群层面的理解。不同人群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高纤维饮食可以促进产生短链脂肪酸的肠道细菌的生长,这些短链脂肪酸不仅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还可能通过调节食欲和能量代谢等方式来帮助控制体重。
鉴于测序和机器学习等方面技术的最新进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饮食及其对微生物群影响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常见整个饮食方式(如地中海饮食、高纤维饮食、植物性饮食、高蛋白饮食、生酮饮食、西方饮食、间歇性禁食、热量限制饮食等)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机制,还包括生命早期和成年期肠道微生物群相关的饮食相关慢性疾病,临床实践中用于缓解或预防疾病进展的特定饮食等。
微生物组研究成果的迅速扩展使多种长期营养原则变得复杂,同时也为干预提供了新的机会。更深入地了解饮食、宿主和微生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为开发精准营养和基于微生物组的疗法提供新的视角。
饮食对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有相当大的有益或负面影响。
下图是常见饮食方式对肠道菌群的影响,这在后面我们会详细展开阐述。
全膳食的常量营养素组成及其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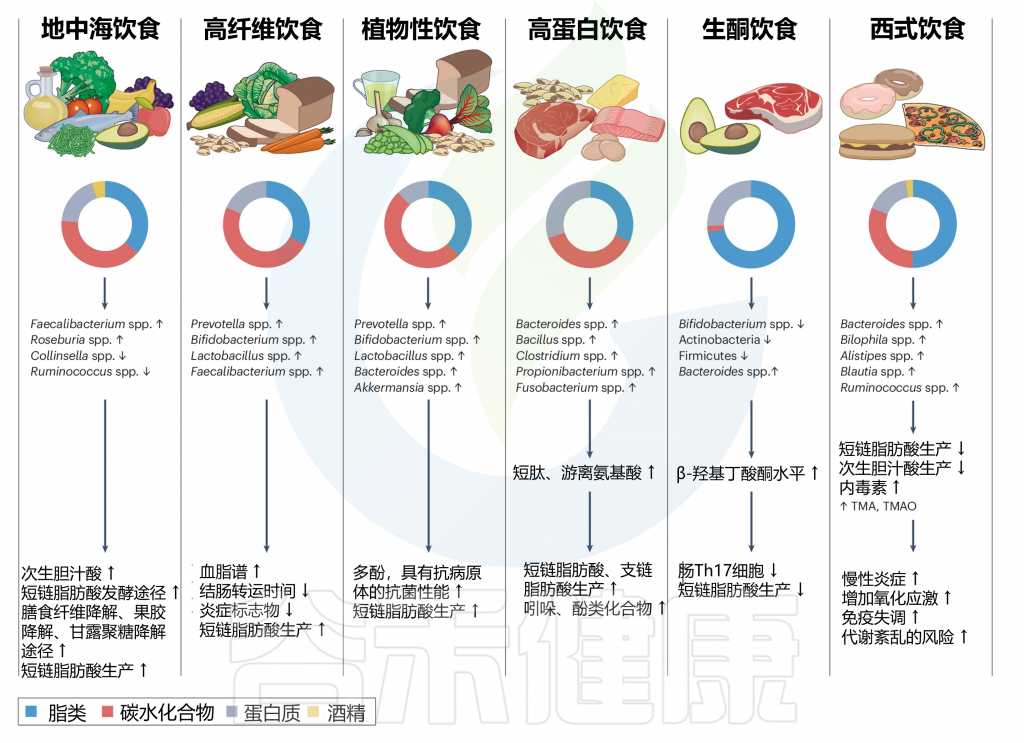
doi.org/10.1038/s41579-024-01068-4
当膳食纤维到达肠道时,会经过肠道微生物群的发酵,产生如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等短链脂肪酸(SCFA)。这些短链脂肪酸随后进入门脉循环,对宿主健康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
激活GPCRs
短链脂肪酸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GPCRs 41和43,这是它们发挥作用的初步机制。
触发肠道激素分泌
激活的受体进一步触发胰高血糖素样肽(GLP)和肽YY(PYY)等肠道激素的分泌。
注:GLP1和PYY在调节食欲、减缓胃排空和促进饱腹感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增强肠道屏障功能
SCFAs通过增加粘液分泌和降低肠腔pH值来增强肠道屏障功能,保护肠道内壁,防止有害病原体进入血液。
抗炎与免疫调节作用
SCFAs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作用,有助于维持整体肠道健康,并降低胃肠道疾病的风险。
肠道微生物群对纤维的分解及其对屏障功能和免疫力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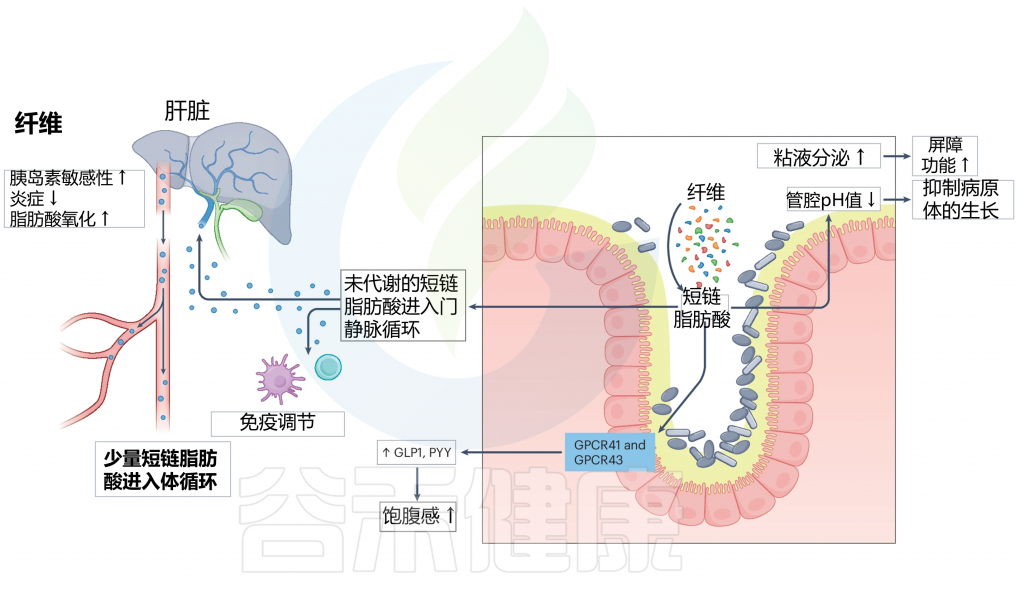
doi.org/10.1038/s41579-024-01068-4
在肠道中,膳食蛋白质经过肠道微生物群的代谢,这与拟杆菌属的增加有关。这导致产生各种代谢产物,包括短链脂肪酸、支链脂肪酸(BCFAs)和吲哚。
支链脂肪酸可以激活 GPCR41 和 GPCR43,从而触发 GLP1 和 PYY 等肠道激素的分泌。此外,BCFAs 可以增加粘液分泌并降低腔内 pH 值,从而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并保护肠道内壁。
肠道微生物群对蛋白质的代谢以及SCFA和吲哚对人类健康的后续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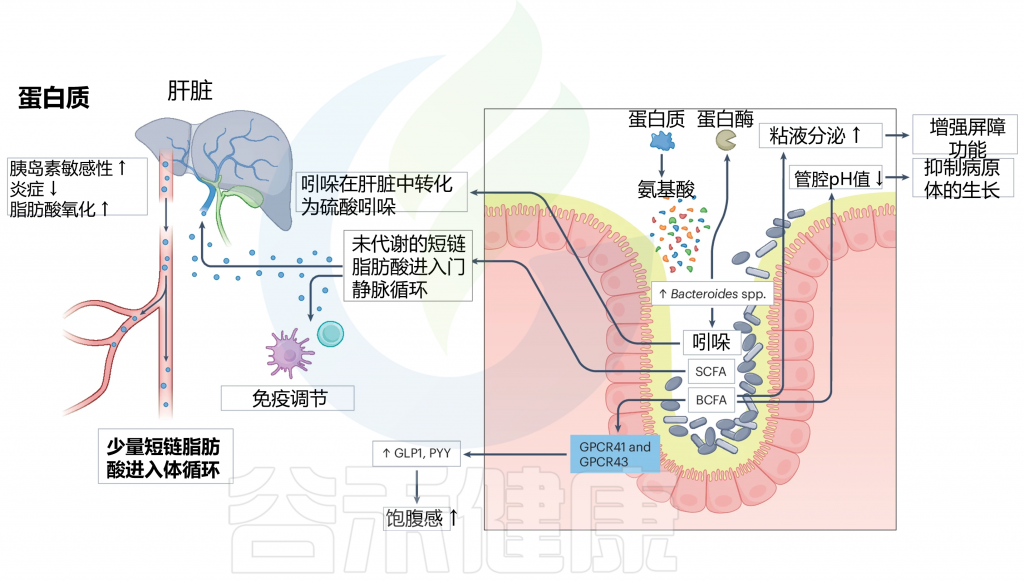
doi.org/10.1038/s41579-024-01068-4
SCFAs、BCFAs、GLP1 和 PYY 等肠道激素、粘液分泌和腔内 pH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包括改善胃肠功能、调节食欲、减少炎症、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和脂肪酸氧化,从而促进整体肠道健康。
当膳食PUFAs到达肠道时,它们会被肠道微生物群代谢。这一过程增加了特定细菌的丰度,如双歧杆菌属和产丁酸菌。因此,产生了各种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例如丁酸盐。
PUFAs可以减少促炎的肠杆菌属(Enterobacterium)的丰度,从而减少炎症并改善肠道屏障功能。这可能导致内毒素和IL-17的产生减少,进而减少炎症并改善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由PUFA代谢产生的未代谢SCFAs进入系统循环,在其中发挥免疫调节作用。它们可以通过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炎症和改善肠道渗漏症内毒素血症来增强抵抗肥胖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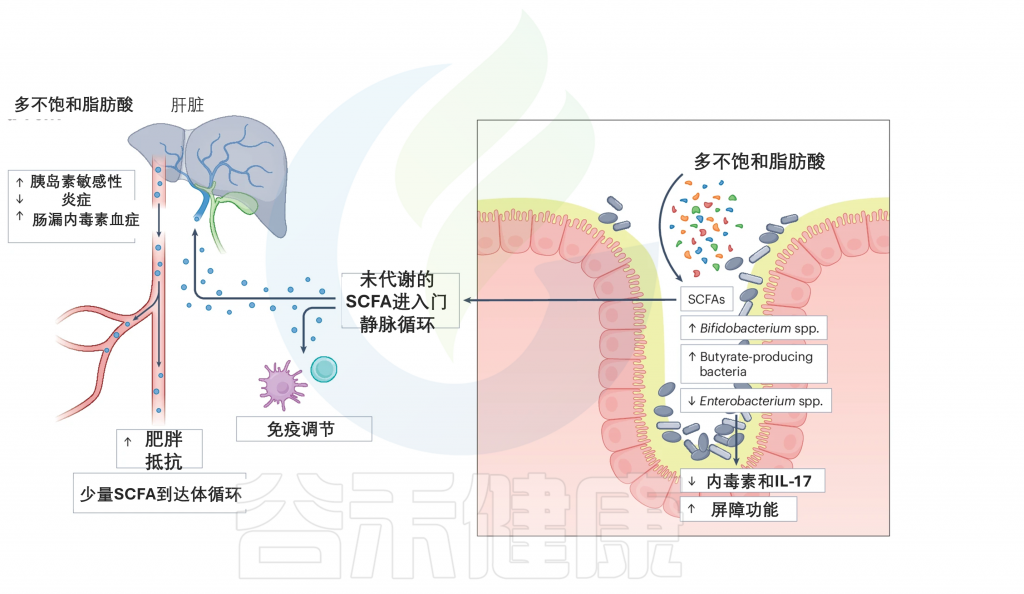
doi.org/10.1038/s41579-024-01068-4
多酚类物质被肠道细菌代谢,因此被分解成生物活性微生物代谢产物。多酚已被证明可以增加肠道腔中有益细菌的丰度,如双歧杆菌、Akkermansia、乳酸杆菌属。这些细菌在维持肠道屏障功能、调节免疫系统、促进肠道稳态和抑制病原菌生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多酚在肠道内表现出显著的抗炎和抗氧化作用。多酚代谢的副产物,缺乏酚类的代谢产物,在系统循环中被吸收,在那里它们发挥显著的免疫调节作用。例如,这些代谢产物已被证明可以通过减少炎症和氧化应激,以及改善内皮功能,从而改善肺部、大脑和心脏功能,增加周围血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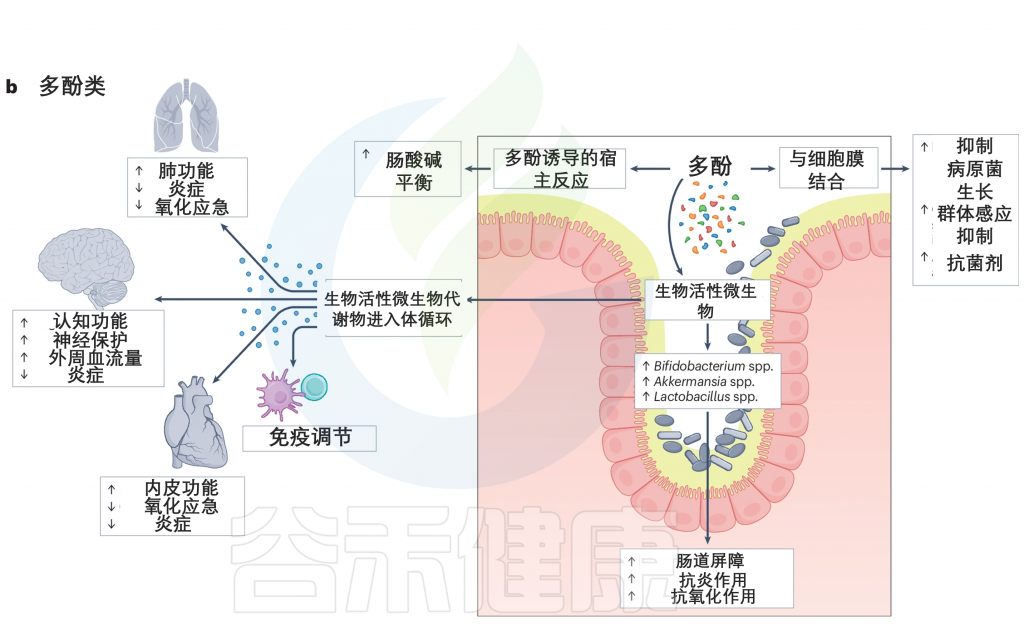
doi.org/10.1038/s41579-024-01068-4
肠道微生物组的差异性影响
不同肠道微生物群对宿主能量状态的贡献存在差异,与肥胖相关的肠道微生物组特征可能会加剧宿主的表型。
遗传性肥胖小鼠及其瘦弱的同窝小鼠在肠道微生物组成上存在差异,从ob/ob供体获得的肠道微生物群受体增加的体脂,比从遗传性瘦弱供体获得的微生物群受体多。
将适应高脂高糖(HFHS)饮食的小鼠肠道微生物群与适应低脂高植物多糖饮食的小鼠肠道微生物群进行移植,一致地增强了接受控制饲料的无菌受体小鼠的脂肪积累。
这些研究表明,无论是由遗传还是饮食驱动的肥胖表型,都可以通过肠道微生物群传播。
肠道微生物组与营养不良
患有夸希奥科病(kwashiorkor)的儿童的肠道微生物群表现出发育不良的特征,并通过在无菌小鼠中定植后与健康对照相比,损害了营养吸收,从而在因果上对营养不良有所贡献。
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也已被证明有助于极低热量饮食(VLCDs)和Roux-en-Y胃旁路手术后的快速减重。
例如,对超重或肥胖的绝经后妇女进行每天800千卡的极低热量饮食,导致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和改善的代谢表型,如体重减轻和减少的脂肪量,这些变化可以在接受了节食前后肠道微生物群的无菌小鼠受体中重现。
肠道微生物组的能量缓冲作用
与低消化性饮食相关的更高营养流入结肠可以以一种增强其对宿主能量状态贡献的方式改变肠道微生物群,表现为接受低消化性饮食条件的微生物群的无菌小鼠受体体重增加和脂肪量更多。
在这个宿主-微生物组生态共生的例子中,宿主的营养吸收较低被肠道微生物群衍生的代谢产物及其下游效应所部分缓冲,例如增加宿主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能量缓冲在能量受限条件下可能有助于宿主的代谢健康,但在能量过剩条件下也可能妨碍体重管理。
肠道微生物组的环境和饮食依赖性
肠道微生物群对宿主能量平衡的贡献可能依赖于环境和饮食背景,即使不通过饮食操纵宿主能量平衡也是如此。
来自肥胖不一致的人类双胞胎的无菌小鼠受体通常模仿了它们供体的代谢表型,但是当差异性定植的受体动物共同饲养时,来自瘦弱供体的微生物群侵入了来自肥胖供体的微生物群,结果是两者都保持了瘦弱。
当共同饲养的受体动物被喂食高脂肪和低水果蔬菜的饮食时,与瘦弱相关的微生物群的传播性被破坏了。
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强调了饮食对宿主-微生物组代谢相互作用的影响有时可能难以追踪。
肠道微生物通过其代谢产物影响健康
短链脂肪酸可以被各种宿主组织转化为ATP,其中:
SCFAs具有多样的信号功能,影响能量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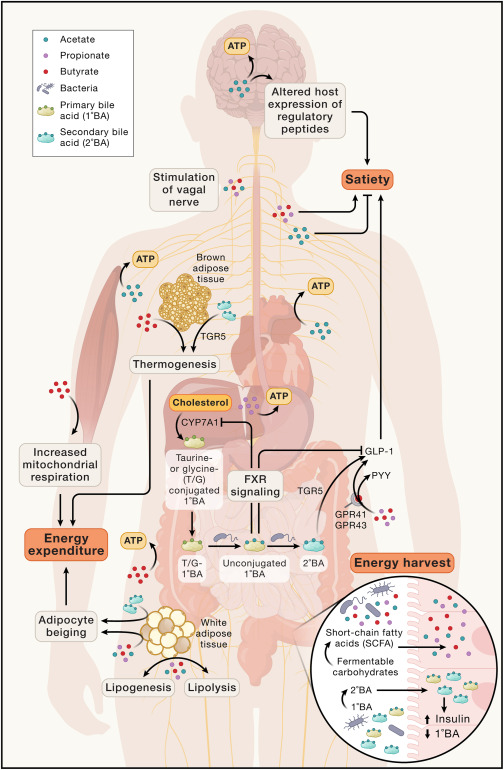
doi.org/10.1038/s41579-024-01068-4
SCFA通过各种方法影响能量摄入,包括乙酸盐穿过血脑屏障,介导调节性神经肽的表达,丙酸盐和丁酸盐结合肠内分泌L细胞中的GPR41和GPR43受体,刺激GLP-1和PYY的释放,以及通过迷走神经的肠脑信号传导,乙酸盐与SCFA混合物可能不同地介导这些信号传导。
SCFA通过促进棕色脂肪组织的产热、白色脂肪组织的米色和骨骼肌的线粒体呼吸来影响能量消耗。SCFA还可以影响脂肪生成和脂肪分解的动力学,据报道,丁酸盐促进脂肪分解,而乙酸盐和丙酸盐促进脂肪生成。
此外,肠道微生物组可以使宿主肝脏分泌的牛磺酸或甘氨酸结合的初级胆汁酸(T/G-1°BA)脱偶联和脱羟基,产生调节宿主能量代谢各个方面的非偶联初级胆汁酸和次级胆汁酸。未结合的初级胆汁酸通过法尼醇X受体(FXR)发出信号,抑制CYP7A1,CYP7A1是初级胆汁酸合成的限速步骤,对饮食脂肪吸收具有潜在的下游影响。次级胆汁酸激活TGR5,促进棕色脂肪组织的产热、白色脂肪组织的米色和胰腺β细胞的胰岛素产生。
肠道微生物胆汁酸代谢也可能通过对厌食素GLP-1的对比作用来影响能量摄入,2°BA激活的TGR5信号促进L细胞分泌GLP-1,1°BA活化的FXR信号在小鼠中显示出抑制GLP-1活性。这些多效性效应强调了对SCFA和胆汁酸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从能量收获的载体转变为能够对宿主能量状态产生净积极和净消极影响的代谢调节因子.
地中海饮食(MD)强调摄入大量未加工的全植物性食品、橄榄油、乳制品、适量家禽和鱼类,以及少量红肉。
降低癌症死亡率及糖尿病风险
一项对美国25,315名女性的前瞻性研究显示,那些坚持地中海饮食模式的人在25年的随访期间全因死亡率降低了23%。这项研究还显示,较高的地中海饮食摄入量与20年随访期间未来2型糖尿病风险降低30%相关。地中海饮食模式可能还对癌症有保护作用。实际上,高度遵守这种饮食与普通人群中的癌症死亡率降低、癌症幸存者的全因死亡率降低,以及降低发展结直肠癌、头颈癌、呼吸、胃、肝和膀胱癌风险有关。
增加产丁酸菌
两项干预研究将地中海饮食与特定分类特征联系起来,增加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Roseburia丰度,减少Ruminococcus gnavus、Collinsella aerofaciens、Ruminococcus torques丰度。这些因饮食而导致的微生物组变化与短链脂肪酸产量的增加和代谢副产物(如乙醇、对甲酚和二氧化碳)产量的减少有关。
地中海饮食与特定功能途径有关
之前研究用宏基因组测序分析了307名男性长期饮食信息的微生物组数据。结果显示,地中海饮食与36条功能途径有关,这些途径大多类似于植物性饮食,具有丰富的微生物功能,用于SCFA发酵和膳食纤维降解。对地中海饮食的坚持显示出与特定功能途径的正相关,如用于果胶分解的d-果糖醛酸降解途径和用于半纤维素分解的甘露聚糖降解途径。地中海饮食的坚持和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在P. copri水平较低的个体中更为明显。
地中海饮食plus版——更积极的变化相关
最近,DIRECT-PLUS研究包括294名肥胖或血脂异常的参与者,发现与地中海饮食相比,绿色地中海饮食与更显著的组成变化相关。绿色地中海饮食是地中海饮食的增强版,它增加了植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减少了红肉的摄入,并且每天还摄入富含多酚的绿茶和Mankai水生植物。
这种饮食在微生物组成和多样性上产生了更大的变化,包括增加普雷沃特氏菌的丰度和支链氨基酸降解酶(异亮氨酸降解),减少双歧杆菌和支链氨基酸生物合成酶(缬氨酸和异亮氨酸生物合成)。这些变化与体重和心代谢指标的积极变化相关联。
膳食纤维对人类健康至关重要,它有助于降低长期体重增加,低纤维摄入量会增加患2型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
高纤维饮食会改变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包括显著增加乳酸杆菌属和双歧杆菌属的丰度。
断奶后饮食变化,引起代谢复杂多糖的菌增加
不同的膳食纤维组分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各不相同。例如,母乳喂养的婴儿表现出更高丰度的适应于利用人乳寡糖(HMOs——母乳中大量存在的不可消化的益生元糖类)的双歧杆菌。断奶后,肠道微生物组成会发生明显变化,这主要归因于饮食组成的改变。这导致能代谢更复杂多糖的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的扩张。
超重个体:改善菌群预防代谢疾病
在超重的个体中,阿拉伯木聚糖低聚糖的干预增加了普雷沃氏菌和直肠真杆菌(Eubacterium rectale)的丰度,伴随着代谢组学特征的有利变化,可能有助于预防代谢性疾病。
全谷物和小麦麸皮:双歧杆菌、乳杆菌↑↑
在31名志愿者中补充全谷物和小麦麸皮,导致双歧杆菌属和乳酸杆菌属的水平增加。全谷物消费者中的增加更为明显;两组都经历了总胆固醇的降低。
燕麦:厚壁菌门↑ 拟杆菌门↓ 心血管疾病风险↓
来自燕麦的高分子量β-葡聚糖减少了厚壁菌门,增加了拟杆菌门,并伴随着心血管疾病风险标志物的减少。
抗性淀粉:影响短链脂肪酸产生
以IV型抗性淀粉形式的膳食纤维对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以及丁酸盐或丙酸盐的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简单碳水化合物在小肠中吸收,而复杂碳水化合物如膳食纤维则经历结肠微生物发酵,从而产生短链脂肪酸。人类只产生非常有限的用于碳水化合物降解的碳水化合物活性酶(CAZymes),因此依赖于肠道微生物群间接代谢几种膳食纤维。低纤维的饮食与肠道微生物群中减少的CAZyme储备相关。
短链脂肪酸的健康益处
包括前面文中提到过的,通过GPCRs传递信号,以及刺激肠道内分泌细胞分泌饱腹感激素(GLP-1和肽YY)。这影响了食欲调节,并调节了调节性T细胞的功能,以及脂质和葡萄糖代谢,在调节宿主能量代谢和结肠稳态中发挥关键作用。
丁酸盐作为结肠细胞的能量来源,通过肠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介导抗炎特性,并增强粘液产生,这突出了其在优化肠道吸收和肠道屏障功能中的作用。
短链脂肪酸与GPCRs及其他细胞的作用和互动不仅限于肠道,还扩展到外周组织、器官和免疫细胞。在小鼠模型中的报告表明,SCFAs和高纤维饮食可能在降低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哮喘和压力的风险,减少脂肪酸合成和脂肪分解方面发挥作用,从而减轻体重并增强神经认知发展。SCFA的吸收导致肠腔pH值降低,这抑制了对pH敏感的病原体如梭菌纲和肠杆菌科的生长,并增加了营养素吸收。
全谷物中的不可溶纤维影响肠道传输速率和细菌发酵
两项随机对照交叉试验涉及50名超重或有代谢综合征风险的个体,表明全谷物饮食增加了粪便中的丁酸盐和己酸盐,改善了血脂水平,减少了炎症标志物,并与精制谷物饮食相比改善了体重减轻。产短链脂肪酸的菌与结肠传输时间显示出负相关关系。这进一步有助于调节肠道微生物组成和多样性,从而缓解各种肠道疾病,如肠易激综合症、炎症性肠病、结直肠癌和胃癌以及便秘。
微生物群与人类健康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了采取整体方法和更大规模的人类研究的必要性,以便深入认识饮食碳水化合物、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和疾病易感性之间复杂的关系。
植物性饮食富含多酚类、宿主可消化和不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并发挥益生元和后生元的双重效应。素食饮食导致形成独特的细菌环境,这一点从细菌功能能力的转变中得到证实。
素食者:拟杆菌↑ 普雷沃氏菌属↑
例如,素食者表现出低肉碱降解但增加氮同化。与杂食者饮食相比,这些饮食促进了拟杆菌门和普雷沃氏菌属的丰度,尽管由于微生物个体差异和研究方法的不一致性,研究结果有时会出现矛盾。
某些属或种的对比水平可以归因于饮食快速与逐渐转变对微生物造成的压力、健康与不健康饮食成分的存在,以及各种生物活性化合物的来源。例如:
植物性饮食的这些特性使其在预防和管理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和某些癌症方面显示出潜力。然而,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充分理解植物性饮食对肠道微生物组的具体影响,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宿主的健康和疾病风险。
多酚类物质的吸收:少量在小肠,大量在结肠
多酚类物质,分为类黄酮和非类黄酮,是植物的次级代谢产物,存在于水果、蔬菜、谷物、葡萄酒、茶、咖啡等食物中。
少量的多酚类物质(5%~10%)在小肠中被吸收,主要是那些具有单体和二体结构的多酚。吸收后,苷元在肠细胞内经历生物转化,然后在肝细胞内继续转化。这些代谢产物通过循环系统运输到肾脏和肝脏等器官,并最终随尿液排出。
大部分多酚类物质(90%-95%)在回肠和结肠中与肠道微生物发生作用,它们促进双歧杆菌、Akkermansia、乳杆菌等物种的丰度,从而提供显著的抗炎和抗病原体特性,以及心血管保护作用。
最近一项涉及超过2万名成年人的随机对照试验表明,食用富含多酚的可可提取物减少了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然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并没有减少。
多酚类物质的抗菌和抗病原体特性
多酚类物质可以通过几种机制抑制细菌生长,包括结合并改变细胞膜的功能特性。它们还展现出对食源性病原体的抗菌活性,并以剂量依赖性方式作为群体感应抑制剂和抗菌剂。
肠道微生物群代谢多酚
肠道微生物群双向调节并代谢多酚类物质,将它们转化为更具生物活性的微生物代谢产物,并提高其相对于原始化合物的吸收。
代谢产物的健康益处
研究表明,食用生物活性微生物代谢产物对人类健康有益处。例如:
多酚类物质对肠道微生物群的调节
多酚类物质可以通过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影响各种微生物酶的功能,调节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包括短链脂肪酸、TMAO、多巴胺、脂多糖、胆汁酸。
这最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引起多酚类物质诱导的宿主反应,例如,作为调节肠道酸碱平衡的调节器。多酚类物质对肠道微生物群的调节已被证明支持肺功能、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和肠道屏障完整性的稳态。
植物和动物源食物类型不同,对菌群影响有差异
植物和动物源性食物中蛋白质和脂肪类型的不同导致了肠道微生物组成和代谢组的差异。例如,基于动物的饮食导致耐胆汁细菌种类的丰度增加,如Alistipes、Bilophila,同时减少了厚壁菌门的丰度,降低了支链氨基酸(BCAAs)的水平,并增加了SCFAs和二甲基硫化物。
其他植物化合物,如纤维、萜类和类胡萝卜素,也已显示出健康益处。个体在从饮食多酚中产生酚类衍生代谢产物的量上的差异归因于每个人肠道微生物组的独特组成。
因此,分析多酚代谢产物可以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方法,以更深入了解生物活性化合物效应,并为理解个体间的显著多样性提供全面的认识。
每日蛋白质摄入量超过1.5克/千克体重的饮食通常被认为是高蛋白饮食。这种饮食通常用于运动员或为超重人群减肥时所推荐。
蛋白质的消化和吸收
饮食中的蛋白质主要由宿主的蛋白酶分解,但每天有12-18克的蛋白质可到达大肠并被微生物群代谢。
不同类型的复杂蛋白质具有不同程度的可消化性,以及不同的氨基酸组成。
参与蛋白质分解的菌群
一些细菌物种参与蛋白质分解,并在高蛋白饮食者的肠道微生物群中富集,主要是拟杆菌属、芽孢杆菌属(Bacillus)、梭菌属(Clostridium)、Phocaeicola、丙酸杆菌属(Propionibacterium)、梭杆菌属(Fusobacterium)、乳杆菌属、链球菌属。
其他细菌可以直接利用氨基酸,并从蛋白质分解中受益,形成交叉喂养的相互作用。
蛋白质分解细菌使用多种酶
蛋白质分解细菌使用多种外肽酶、蛋白酶(包括金属、丝氨酸、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苏氨酸、谷氨酸和天冬酰胺蛋白酶)和内肽酶来释放短肽和游离氨基酸。
氨基酸代谢产生短链脂肪酸
大多数氨基酸被发酵成短链脂肪酸:
部分发酵产物可能带来的健康危害
其他发酵产物包括可能的炎症化合物,如来自芳香族氨基酸(例如色氨酸)的吲哚和酚类化合物,以及氨、胺、有机酸和气体(即由含硫氨基酸半胱氨酸和甲硫氨酸产生的硫化氢,以及二氧化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最终产物中的一些可能与疾病有关。吲哚和吲哚相关化合物可以到达肝脏并转化为硫酸吲哚酚,这是一种对肾脏有害的有毒代谢产物,并参与内皮功能障碍。此外,硫化氢可能具有致突变性,并可能在炎症中发挥作用,增加结肠癌的风险。
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化合物、适量蛋白质和高脂肪的饮食模式,模拟了禁食期间的代谢反应,这种状态下循环酮体水平升高。
注:酮体是脂肪酸衍生的分子,当葡萄糖可用性受限时作为替代能量来源。这些酮体(KBs)包括β-羟基丁酸(βHB)、乙酰乙酸和丙酮,主要在肝脏中产生。
生酮饮食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治疗癫痫的饮食疗法,并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种饮食在治疗阿尔茨海默症、肥胖症、癌症等各种疾病方面的益处。
注:传统的长链甘油三酯生酮饮食遵循脂肪(克)与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总和的4:1比例。变体包括中链甘油三酯生酮饮食、改良阿特金斯饮食和低血糖指数治疗,每种方法都有稍微不同的宏观营养素比例。
在人类中,诱导生酮状态需要严格限制碳水化合物摄入(5%–10%千卡/天),适量蛋白质摄入(30%–35%),和高脂肪摄入(55%–60%)。
生酮饮食的潜在风险和副作用
生酮饮食(利于拟杆菌门) ≠ 高脂饮食(利于厚壁菌门)
典型的高脂饮食通常会增加厚壁菌门的丰度并减少拟杆菌门;然而,生酮饮食的效果不同。
——超重成年人
在涉及17名超重成年人的研究中,为期4周的生酮饮食显示在人肠道中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和厚壁菌门的大量减少。具体来说,有益的双歧杆菌的19种物种减少了,而拟杆菌门丰度增加。这些变化部分是通过宿主产生酮体诱导的。
——癫痫儿童
在涉及12名严重癫痫儿童的为期3个月的研究中,遵循生酮饮食的儿童显示健康促进和消耗纤维的双歧杆菌属、直肠真杆菌(E. rectale)和Dialister属的丰度大幅减少。相反,儿童显示拟杆菌属和大肠杆菌属的丰度增加,后者部分归因于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的增加。
生酮饮食对肠道微生物组的影响
临床前研究也表明,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在响应生酮饮食时发生了显著变化,最明显的是:
酮体βHB↑ 双歧杆菌↓
一项分析生酮饮食对肠道微生物组组成的变化的潜在机制的研究报告了在人类和鼠类受试者中,双歧杆菌属和酮体β-羟基丁酸(βHB)之间的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随着βHB水平的增加,双歧杆菌属的水平会降低。
来自人类、啮齿动物和细胞培养的数据支持β-羟基丁酸抑制NLRP3炎症体的能力。高水平的酮体可以降低血压并增加血管功能。循环酮体水平的增加还可以减少心脏炎症和心力衰竭的可能性。酮体也可能通过刺激胰岛素受体,通过诱导AMP激活蛋白激酶(AMPK)和下调mTOR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高水平的酮体可能减少食欲,从而使体重减轻。
生酮饮食→双歧杆菌↓→减少诱导Th17→促炎降低
将生酮饮食者的粪便微生物群移植到无菌小鼠中,研究揭示了肠道TH17细胞的变化。
注:Th17细胞是一种辅助性T细胞亚群,其主要特征是能够产生多种促炎细胞因子,如IL-17、IL-21和IL-22等。
双歧杆菌属对肠道TH17细胞的有强烈诱导作用,而生酮饮食改变肠道菌群(双歧杆菌降低)也减少了诱导Th17的能力,可能导致这些细胞的促炎性降低,从而影响肠道和脂肪组织的炎症状态,
然而,由于有益的肠道微生物群的减少和促炎性及病原性肠道细菌的促进,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了解生酮饮食对宿主健康的长期影响。
西方饮食的特点是高热量含量,富含动物蛋白、饱和脂肪、简单糖和超加工食品,同时纤维、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不足。
西方饮食:多样性下降,拟杆菌为主
与其他饮食相比,西方饮食与肠道微生物组多样性的显著降低有关,其肠道特征转向以拟杆菌属为主的肠道特征。其他丰富的物种属于Ruminococcus、Faecalibacterium、双歧杆菌属、Alistipes、Blautia、Bilophila。
由于纤维摄入较少和不同的微生物组成,相关的微生物群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较少。
红肉中胆碱→TMAO→多种慢病相关
红肉中的特定化合物,如胆碱和肉碱,也可以被肠道微生物群转化为三甲胺,然后在肝脏中转化为与慢性疾病相关的三甲胺-N-氧化物(TMAO)。
加工食品和添加剂的影响
加工食品包含各种添加剂、防腐剂和乳化剂,能够直接或间接与肠道微生物群相互作用。
非营养性人造甜味剂,如低热量或饮食食品和饮料中的糖精、三氯蔗糖和阿斯巴甜,对微生物组多样性和组成的潜在长期影响尚不清楚。
其他添加剂,如卡拉胶(一种从红海藻中提取的增稠剂或凝胶剂,存在于许多加工食品中,如乳制品),已知会促进肠道炎症和破坏粘液层,导致肠道微生物组的变化。
人工食品色素,如糖果和烘焙产品中的Allura Red AC,赋予颜色并通过与肠道细菌的相互作用改变硫的稳态。
一些防腐剂,如加工肉类中的硝酸钠,也可以调节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而乳化剂,如羧甲基纤维素(一种存在于酱汁中的增稠剂)和聚山梨醇酯-80(一种存在于酱汁和烘焙食品中的乳化剂和稳定剂),直接冲击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和功能。
详见我们之前的文章:
你的焦虑可能与食品添加剂有关,警惕食品添加剂引起的微生物群变化
糖,功能糖,代糖,如何从健康角度看这些肠道菌群的“甜蜜伙伴”
总体而言,西方饮食与慢性炎症的激增有关,导致与饮食相关的疾病,包括肥胖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
过去50年中,一种受到极大关注的饮食疗法是日常热量限制(CR),它被定义为在保持充足营养的同时,将饮食摄入量减少至低于维持体重所需的能量水平。观察性、临床前和临床试验的发现表明,CR可能将寿命延长1-5年,同时改善生活质量。
最严格的CR随机试验来自国家老龄化研究所资助的CALERIE(减少能量摄入长期效应综合评估)联盟。CALERIE研究包括CALERIE第一阶段(三项为期6至12个月的CR小规模试点研究)和CALERIE第二阶段(一项大型、多中心、为期2年的CR随机试验)。
注:这些研究招募了体重正常且健康状况良好的成年人。每项试验中实施的CR程度不同,但通常涉及日常能量摄入量减少10%至30%,同时确保其他关键营养素的充足摄入。
CR的健康益处
CALERIE研究的发现显示,短期和长期CR都可以减少体重、皮下脂肪、内脏脂肪和肝内脂肪含量。
CR减少了微生物表达的酶
这些酶能够使脂多糖A生物合成,从而限制了脂多糖(LPS)的产生,并以药理学上已知能刺激脂肪细胞褐化和减少内脏脂肪的方式抑制了LPS-TLR4途径。
将经过CR调节的与对照肠道微生物群移植到未经处理的无菌小鼠中,导致体重和体脂肪的增加减少,胰岛素敏感性提高,UCP1+(即褐/产热)脂肪细胞增加,这表明CR诱导的肠道微生物组变化在这些效应中起到了因果作用。
Dorea弱预测了CR诱导的体重减轻
人类的CR研究报道了肠道微生物组组成和功能的多种变化,但据所知,还没有研究表明这些变化是代谢益处的基础。
最近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比较了147名超重或肥胖成年人中12周间歇性与持续性CR的效果,发现体重减轻与细菌相对丰度、群落α多样性或循环微生物代谢产物(例如短链脂肪酸)的变化之间没有关联。尽管如此,基线微生物组组成——特别是Dorea的相对丰度——弱预测了CR诱导的体重减轻。
超重人群日常热量限制后相关菌群变化
同样,一项涉及80名超重或肥胖成年人进行14周CR的前瞻性研究发现,体重减轻5%或以上与Collinsella和Christensenellaceae的丰度正相关,与大肠杆菌/志贺菌属、克雷伯菌属、巨球形菌属(Megasphaera)、Sellimonas、乳杆菌属的丰度负相关。
微生物组特征与特定代谢健康标志物之间的关联
如Akkermansia和Christensenellaceae与基于HOMA-IR的胰岛素敏感性之间的关系。需要额外的功能研究来测试这些微生物组特征与代谢反应之间的联系是因果关系还是其他生理状态的共线性结果。
解决开始和维持饮食模式重大转变挑战的一个潜在解决方案来自于一组数据,即间歇性禁食可以导致显著的体重减轻。
最常见的间歇性禁食形式是时间限制性进食(TRE),它涉及将进食窗口限制在4-10小时内,并在一天剩余的14-20小时内禁食。
TRE的做法
在进食窗口期间,个人不需要计算卡路里或以任何方式监测食物摄入,这种简单性可能解释了近期TRE受欢迎度的上升。在禁食窗口期间,个人被鼓励大量饮水,也可以消费无能量饮料,如不加添加剂的茶和咖啡。当肥胖成年人将进食窗口限制在每天4-10小时时,他们通常会将能量摄入减少200-550千卡/天,这种能量限制程度与日常CR(热量限制)相当。
TRE的减重效果
随机对照试验显示,TRE在降低体重和改善一些心血管健康标志物方面是有效的。体重通常在2-12个月的TRE后减少3%-5%,减少主要来自脂肪质量和内脏脂肪质量的减少,而不是瘦体重。
然而,并非所有关于人类TRE的研究都报告了体重减轻。有研究表明,3个月的8小时TRE(下午12点至晚上8点的进食窗口)对肥胖成年人的体重与无干预对照组相比没有影响。
注:然而,这项研究是在自由生活的参与者中进行的,他们在试验期间与研究团队的接触很少。
当进食窗口较早时,降血压效果才较为明显
即使实现了减重,也不是所有受试者都表现出代谢改善。血压通常在2-12个月的TRE后降低5-10毫米汞柱,但这些效果通常只有在进食窗口设在一天中较早的时候(即下午2点前)才会被注意到。早期进食窗口可能通过促进钠尿(通过肾脏在尿液中排泄钠)来降低血压,因为当盐分摄入转移到一天中较早的时候,由昼夜节律系统调节的钠排泄会增加。TRE似乎并不影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或甘油三酯水平。循环炎症标志物,如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也不受TRE影响,尽管数据有限。
TRE改善血糖效果明显(早点吃,进食时间短)
临床试验发现,TRE在改善前驱糖尿病和肥胖个体的空腹胰岛素和胰岛素敏感性方面表现出相当一致的效果。TRE还改善了葡萄糖耐受性并减少了血清葡萄糖波动。这些改善更常见于早期进食窗口(即在下午3点前吃完所有食物)和较短的进食窗口(4-6小时)。
在2型糖尿病成人中,TRE改善了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每日CR相当,并且没有增加低血糖的风险。
TRE如何改善糖调节?
来自人类试验的数据显示,身体在TRE期间经历了代谢转换。
肠道微生物群发挥作用
在小鼠中,时间限制性喂养(TRF)通过恢复肠道细菌相对丰度的昼夜变化,减轻高脂高糖(HFHS)饮食的影响。
这些变化在远端小肠(回肠)最为明显,并与促胰高血糖素基因Gcg的表达增加和GLP-1的血浆水平升高相对应。
经抗生素处理和无菌小鼠的研究支持肠道微生物群在昼夜GLP-1释放中发挥因果作用,但具体的微生物效应因子仍不清楚。
一个概念验证来自于肠道共生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的研究,它分泌一种84kDa的蛋白质(P9),足以通过与细胞间粘附分子2(ICAM-2)相互作用诱导GLP-1的分泌。
需要更多的工作来理解参与TRE的糖调节和其他有益效应的微生物群的全范围,以及它们的临床相关性。
TREplus版:肠道菌群变化更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一项临床研究比较了CR与能量匹配的TRE加蛋白质plus(定义为每天四次均匀间隔的餐食;TRE-P)方案在超重或肥胖成年人中的效果,发现TRE-P与肠道微生物组组成的更显著变化相关,包括之前与减重和蛋白质消费有关的类群的丰富,如Christensenellaceae。此外,在TRE-P干预期间,体重减轻高与低的参与者之间观察到肠道微生物组组成和功能能力的差异,但这些微生物组变化是否对TRE-P诱导的代谢改善有因果贡献仍不清楚。
母乳是大量生物活性化合物的来源,包括人乳寡糖(HMOs)、免疫球蛋白G(IgGs)、免疫细胞和微小RNA(miRNA),其中一些可以影响婴儿的肠道微生物群。与配方奶相比,母乳喂养会导致粪便钙保护素和β-防御素2等炎症标志物水平更高,这反映了随着促炎血清细胞因子减少,免疫成熟的过程。
双歧杆菌和拟杆菌利用HMOs,因此占主导地位
HMOs被双歧杆菌属(包括Bifidobacterium breve、Bifidobacterium bifidum、B. longum、B. infantis、Bifidobacterium pseudocatenulatum)以及拟杆菌属物种利用,导致这些物种在母乳喂养的婴儿肠道中占主导地位。
这可能会改变宿主中微生物与代谢产物之间的关系,如降低的肌苷水平与长双歧杆菌丰度增加之间的相关性所证明的,这表明其可能在婴儿的免疫和神经发育中发挥作用。
HMOs作为益生元发挥作用
乳铁蛋白和溶菌酶具有抗菌特性,能够调节对感染的保护。
肠道中由HMO利用形成的SCFAs被宿主用作能量来源。
非母乳喂养的肠道菌群
非纯母乳喂养的配方奶喂养婴儿拥有更高丰度的链球菌属、肠球菌属、韦荣球菌、梭菌属,并表现出在更多碳水化合物代谢途径上的功能能力差异,这证明了饮食对肠道微生物组的重要性。
较短的母乳喂养时间,菌群多样化
较短的母乳喂养持续时间与早期生活中高度多样化且类似成人的微生物组成相关联。
母乳中的HMOs调节婴儿肠道微生物群,并提供若干健康益处,如长期保护免受过敏、特应性皮炎和肥胖的影响,以及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同样,引入辅食会导致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这些变化促进了碳水化合物的利用、维生素的合成和外源性物质的降解,结果是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中的微生物水平增加。
最近的研究报道,涉及脂肪和糖摄入的孕妇饮食干预改变了婴儿肠道微生物组的功能,而另一项研究则报告没有关联。
小鼠实验:母亲孕期低纤维饮食,幼鼠呼吸感染的严重程度增强
最近的研究显示,在怀孕期间接受低纤维饮食的小鼠在后代中经历了延迟的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扩增的扰动,导致呼吸感染的严重程度增强。同样,在无纤维饮食的小鼠中,幼崽中的比例较低的Akkermansia muciniphila、固有淋巴细胞和TH17细胞,而缺乏AKK菌属且被喂食纤维的小鼠显示出减少的固有和适应性RORγt‐阳性免疫细胞亚群。
小鼠实验:富含发酵食品,减少新生儿结肠炎症
另一项在母猪和小鼠上进行的研究表明,富含发酵食品的母亲饮食影响了新生儿肠道微生物群的发展,并通过p38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和c-Jun氨基末端激酶激活的caspase 3的磷酸化减少了结肠炎症。母亲饮食对婴儿长期健康影响的程度需要进一步研究。
肠道微生物群在调节宿主代谢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微生物组成的某些变化和多样性的减少与多种代谢性疾病发病率的上升有关。
肥胖与肠道菌群有关
利用无菌啮齿动物模型,研究人员已经建立了肠道微生物群与肥胖之间的联系。将肥胖小鼠的肠道微生物群定植到无菌小鼠体内,导致体重和胰岛素抵抗显著增加,而当无菌小鼠被喂食西式饮食时,肥胖的发展则不存在,这突显了肠道微生物群在肥胖中的作用。然而,其他几项同意微生物群在能量稳态中的作用的研究未能显示其在肥胖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指出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索这种复杂的关系。
2型糖尿病和肥胖的个体的肠道菌群特征
患有2型糖尿病和肥胖的个体通常表现出产丁酸菌减少,乙酸盐及促炎物种增加,这些与胰岛素抵抗性升高有关。在肥胖小鼠上进行的研究支持肠道微生物群在2型糖尿病中的作用。双歧杆菌属、拟杆菌属、Faecalibacterium、Akkermansia与2型糖尿病负相关,其中双歧杆菌增加了胰高血糖素样肽-2(GLP-2)的水平,从而改善肠道通透性并减少代谢性内毒素血症。
注:二甲双胍,一种常见的2型糖尿病药物,与肠道微生物群相互作用,可能通过调节葡萄糖稳态和短链脂肪酸的产生来介导其抗糖尿病效应。
饮食、肠道微生物组、代谢性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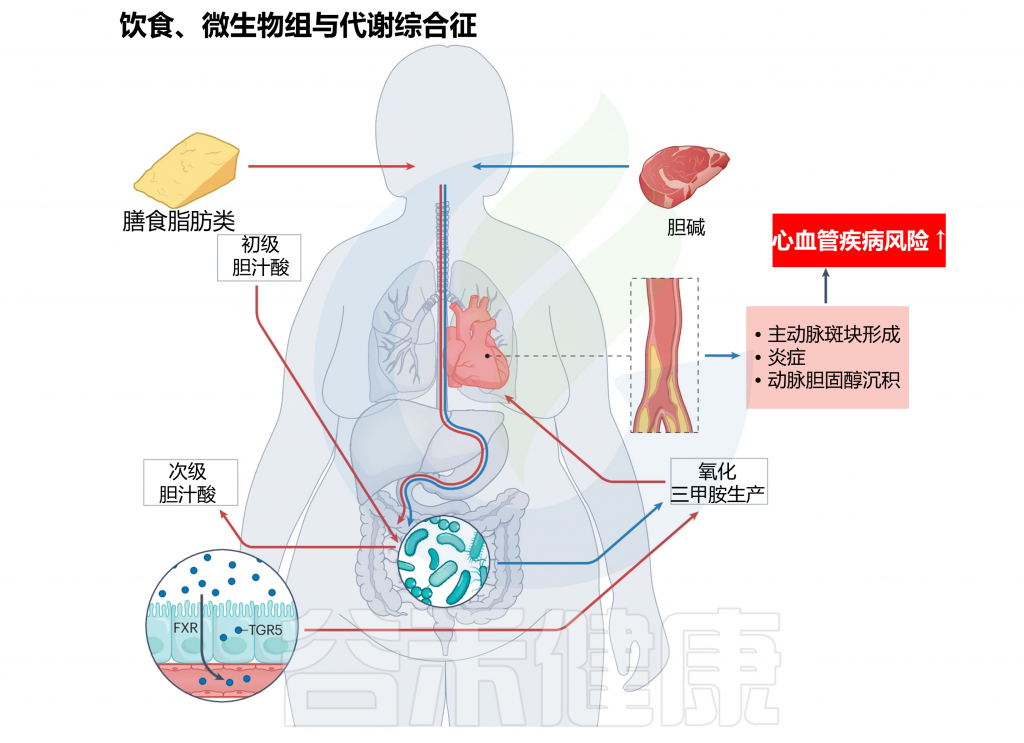
doi.org/10.1038/s41579-024-01068-4
注:红色箭头表示饮食脂肪可以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对宿主健康产生下游影响,最终导致CVD风险。此外,蓝色箭头显示了主要存在于动物产品中的胆碱如何引起CVD风险。
心血管代谢疾病的个体的肠道菌群变化
特征是增加的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物种和减少的拟杆菌属以及抗炎的F. prausnitzii。肠道微生物群的这些变化与更具炎症性和较少发酵性的肠道环境有关。
TMAO
三甲胺-N-氧化物(TMAO),一种由肠道细菌从饮食化合物产生的代谢产物,与动脉硬化、血小板聚集和血栓形成有关。
在小鼠和人类的研究表明,饮食因素影响TMAO水平,某些情况下抗生素降低了TMAO,而杂食饮食增加了它。TMAO水平升高与心力衰竭患者的高死亡率相关。然而,结果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表明某些饮食成分如左旋肉碱和富含TMAO的食物可能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这引发了关于饮食、微生物组和宿主遗传学在动脉粥样硬化发展中复杂相互作用的问题。
增加的饮食脂肪可以影响FXR和TGR5等胆汁酸受体的激活,它们在脂质和葡萄糖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途径的调节失常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展。
由于微生物组改变导致的能量稳态的微小变化可能具有长期效应,在代谢性疾病中发挥作用,既是因果因素也是促成因素。此外,它们可以作为使用微生物组靶向治疗改善这些状况的目标。
饮食在肠道疾病的病理生理学中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炎症性肠病、肠易激综合症和结肠癌。
肠易激综合征
过敏、食物不耐受、微生物群组成的转变、轻度粘膜炎症和肠道通透性的增加可能促成了肠易激综合症的表现。
研究发现,类似于病原性肠易激综合症的人类微生物组表现出拟杆菌门的丰度减少,以及厚壁菌门和与氨基酸及碳水化合物代谢相关的基因丰度增加。
饮食成分与炎症性肠病风险
饮食也可以改变炎症性肠病(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的肠道微生物群落组成,影响短链脂肪酸和纤维等物质的代谢,这反过来又可能促成疾病的发生。
动物蛋白、乳制品、碳水化合物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等食物成分与发生炎症性肠病的风险有关。
动物蛋白与炎症性肠病的机制
一个将炎症性肠病与动物蛋白联系起来的机制涉及小肠中的氨基酸和血红素吸收不良,导致产生酚类和氢气等有害副产物。这通过抑制丁酸盐的产生和减少肠道屏障中的二硫键,促成了炎症性肠病的发病机制。
高脂肪饮食也与炎症性肠病强烈相关
在实验模型中,高脂肪饮食可以破坏肠细胞间的结合蛋白功能,从而改变粘液层的组成和肠道微生物群。
持续且控制不当的炎症性肠病,以及由于不良饮食模式(如西方饮食)导致的慢性胃肠道炎症,是影响结肠炎相关结直肠癌风险的主要外部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免疫反应、肠道组织平衡和肠道微生物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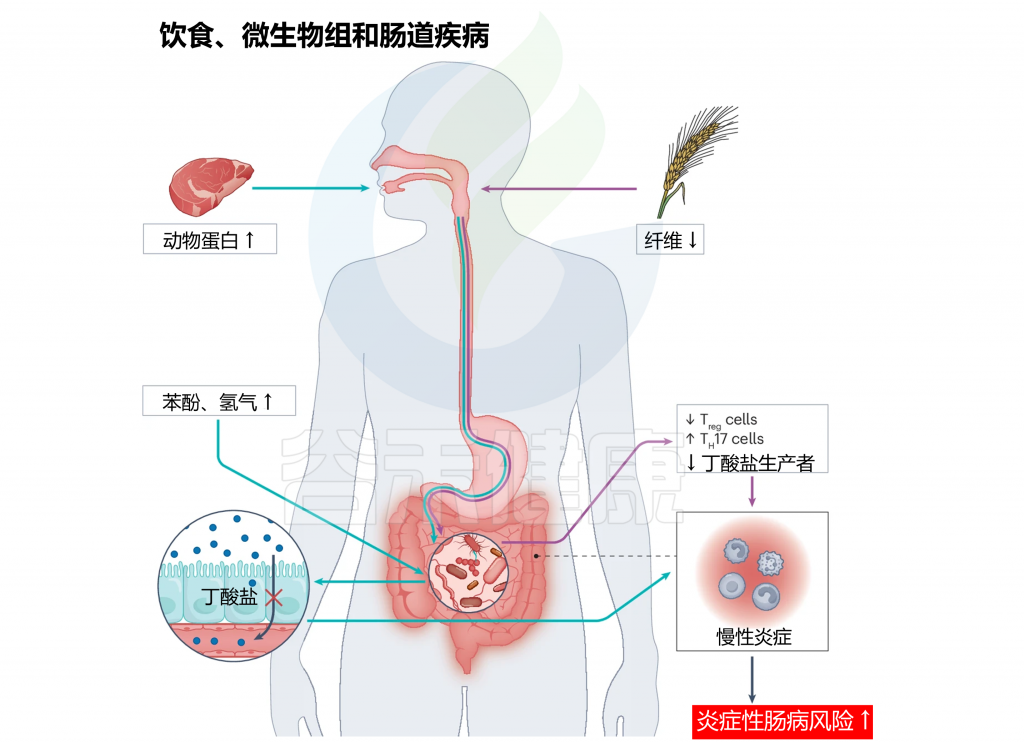
doi.org/10.1038/s41579-024-01068-4
注:增加的动物蛋白(绿色箭头)和低纤维(紫色箭头)饮食可能对生理功能和宿主健康产生下游影响。
增加红肉消费可导致胆碱水平升高,由于血红素吸收不良,在小肠中产生更多的氢气和苯酚。这反过来可以减少胃肠道中的丁酸盐生产,导致炎症增加。同样,饮食中纤维摄入减少可能通过增加TH17的产生,同时减少Treg和短链脂肪酸产生,对肠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种不平衡最终导致胃肠道内慢性炎症加剧。肠道内长期的慢性炎症可能大幅增加发展成炎症性肠病的风险。
饮食在散发性结直肠癌中的作用
研究发现,低纤维、高脂肪饮食与Fusobacterium nucleatum有关。拟杆菌属通过激活E-钙粘蛋白-β-链球蛋白信号、表观遗传变化和改变肿瘤微环境等机制与结直肠癌有关,从而促进恶性转变。同样,诸如产毒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等致癌细菌被假设通过直接与结肠上皮细胞相互作用和改变局部微生物群组成来触发结直肠癌的发病。
人类肠道是真菌和病毒群的栖息地,分别称为肠道真菌组和病毒组。尽管这些群落只占肠道中总微生物的0.1%-1%,但它们都受到饮食的影响。
婴儿肠道真菌组中,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是优势物种,断奶后被其他酵母属(丝孢酵母属Cystofilobasidium、曲霉属Ascomycota、单孢子酵母属Monographella)取代。
城市居民的肠道真菌组成包括酿酒酵母和较少的产短链脂肪酸菌,农村居民则有更多样化的真菌物种。
念珠菌属(Candida species)与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饮食相关,与富含蛋白质的饮食负相关。
母乳喂养和配方奶喂养婴儿的肠道病毒组组成差异由肠道微生物群变化和母乳垂直传递病毒引起。
高脂饮食与Siphoviridae病毒丰度减少和Microviridae噬菌体丰度增加有关。
无麸质饮食则与相反的变化有关,Siphoviridae在Microviridae之上,占主导地位。
肥胖和1型及2型糖尿病患者的病毒组成也发生变化,高脂饮食喂养小鼠的粪便病毒移植降低肥胖风险。
肠道耐药组,赋予微生物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所有基因或遗传物质的集合,随着细菌微生物组和病毒组的变化而变化。
一些研究报告γ-变形菌纲(Gammaproteobacteria)属拥有丰富的抗生素抗性基因(ARG)储备。
配方奶喂养的婴儿ARG负荷更高,与细菌组成有关。
纯素和鱼素食饮食个体肠道中的微生物组成不同,但他们的耐药组档案并没有显著差异,表明耐药组主要由抗微生物药物暴露而非饮食塑造,可能的例外是含有特定防腐剂的食物。
需要进行详细的饮食干预研究,以了解饮食是否可以减少ARG的负担。
地中海饮食在缓解和管理多种疾病方面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包括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炎症性肠病、肠易激综合症、认知能力下降和抑郁症。此外,对这种饮食的调整,如MIND饮食,已成功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并减缓认知能力下降。同样,DASH(阻止高血压的饮食方法)饮食已证明在治疗高血压方面有效。
特定的碳水化合物饮食在临床实践中用于治疗炎症性肠病的症状。特定的碳水化合物饮食在儿童和成人队列中已证明其有效性,并已与改善的临床参数和炎症标志物相关联。然而,使用这种饮食时必须保持营养控制,以避免营养不足和体重下降。
对于肠易激综合症的治疗,通常使用低发酵性低聚糖、二糖、单糖和多元醇(低FODMAP)饮食,有50%~80%的患者有积极的临床反应。
在41名患者中进行的为期四周的低FODMAP饮食研究显示,从类似病原性肠易激综合症的肠道微生物组向健康相关的肠道微生物组发生了组成和功能上的转变。
同样,研究表明,坚持低FODMAP饮食,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adolescentis)方面表现出显著降低,这种细菌会破坏肠道屏障功能并改变紧密连接的完整性,从而支持低FODMAP饮食的积极效应是通过肠道微生物群介导的假设。
无麸质饮食目前是治疗乳糜泻的方法,研究已证实这种饮食在缓解胃肠道症状方面的有效性。采用这种饮食方案与肠道微生物组成和肠道微生物途径的改变有关。
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乳糜泻患者的小RNA和宏基因组测序数据,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无麸质饮食改变了miRNA和微生物群落的轮廓。该研究还揭示了乳糜泻患者中的miRNA-细菌关系和特定的分子模式,表明可能存在用于监测无麸质饮食依从性和评估肠道炎症状态的生物标志物。
对于慢性肾病的管理,推荐采用低蛋白饮食,目的是减缓进入终末期肾病的进展,并推迟对肾脏替代治疗的需求。
综述表明,极低蛋白饮食可能有效减少4期或5期肾病的发生。然而,仅采用低蛋白饮食并未影响终末期肾病的发展。
此外,五篇文章的系统综述和元分析发现,低蛋白饮食增加了拟杆菌科、乳酸菌科、咽峡链球菌Streptococcus anginosus的丰度,同时减少了Roseburia faecis和Bacteroides eggerthii的丰度。但是,在没有微生物多样性和丰富度的整体构成变化的情况下,这些主要在物种和科水平上的变化似乎不足以影响代谢或临床结果。
用于管理2型糖尿病的血糖指数饮食,因其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及其在影响疾病发展和严重程度方面的潜在作用而受到关注。
这种饮食包括消耗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化合物(例如,豆类、燕麦和小麦),促进血糖水平逐渐且持续上升。尽管关于这种饮食对肠道微生物群影响的研究有限,但小鼠研究表明,它与因摄入大麦而增加的乳酸杆菌属、普雷沃特氏菌属和纤维降解S24-7细菌的丰度有关,或因摄入全谷物燕麦而增加的双歧杆菌属和乳酸杆菌-肠球菌属(Lactobacillus-Enterococcus)有关。
肠道微生物组在人体生理学中的中心作用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健康的看法,并日益渗透到营养研究和建议中。
目前,全球饮食指南普遍达成共识,但不幸的是,这种均质性也延伸到了微生物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例如美国和南非)明确考虑了饮食-微生物组相互作用。
很多文章已经讨论了肠道微生物组知识如何与当前的营养指南相结合,为包含微生物组的精准营养提供了机会,并广泛考虑了将微生物组科学纳入研究、教育、政策和公共卫生沟通的更广泛问题。
几乎所有方面的人类营养最终都需要根据饮食-微生物组相互作用对人类健康的直接和间接后果重新评估。
这里强调微生物组知识挑战营养科学的三个原则:
宿主卡路里≠宿主-微生物组卡路里
由美国化学家威尔伯·奥林·阿特沃特(Wilbur Olin Atwater)在19世纪末提出的阿特沃特系统,用于估算食物中各种营养成分的热量值,反映了食物中的平均化学能量减去粪便、尿液、分泌物和气体中排泄的平均分数。
阿特沃特系统估算热量含量的方法存在三个关键疏漏:
1、食物基质效应
没有捕捉到更广泛食物基质的效果,如植物性宏观营养素在细胞壁或亚细胞结构中的封装。
2、饮食诱导的热生成
没有捕捉到消化的代谢成本,这基于宏观营养素含量、餐食的可口性和食物加工而变化。
3、宿主与微生物组的卡路里区分
只在很小程度上区分了对人类可利用的卡路里和对肠道微生物组可利用的卡路里。
营养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合理地关注那些被吸收进入人体组织的饮食成分,因为这些成分有潜力直接影响健康。然而,大量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组对饮食消化性很敏感,并且饮食引起的肠道微生物组的变化可以在不同情况下因果地塑造宿主的健康和疾病,这日益凸显了未吸收营养素的重要性。
未吸收营养素的重要性
与被吸收的营养素不同,未吸收的营养素可靠地到达结肠中最密集的微生物群落。此外,随着消化液在胃肠道内向下推进,未吸收的营养素会因为被吸收的营养素和水分的消失而浓缩。因此,可以预期,未吸收的营养素在塑造肠道微生物组及其对健康和疾病的下游影响方面,可能比被吸收的营养素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饮食与肠道微生物组的相互作用
目前研究主要关注食物入口时的状态,而未充分考虑小肠末端的消化残余物。
虽然历史上对回肠消化性的描述依赖于体外模型或复杂的体内模型,例如插管动物、回肠造口术后的人类患者、健康人体中的侵入性鼻-回肠或结肠插管,以及在血浆中检测同位素标记的营养素,但受微生物组启发的新方法可能证明是有希望的。
深入理解饮食-微生物组相互作用的新视角
例如,基于DNA的饮食底物表征——一种称为DNA metabarcoding的技术,可能与基于DNA的微生物组分析相结合,研究特定排泄样本中直接的饮食-微生物组相互作用。可以在动物模型中或使用新的可吞咽装置在人体中执行对饮食和微生物组信号的双重表征,这些装置能够在由pH变化确定的胃肠道间隔处采样消化液。
许多食品物质已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基于动物毒理学试验和/或过去在人类中广泛使用且未产生已知有害影响的基础上,被授予“通常认为安全”(GRAS)的认定。
潜在健康影响
然而,GRAS评估通常并未考虑这些物质对肠道微生物组的影响,或者通过微生物组介导的间接健康效应的潜力。
专注于宿主组织的危险通过发现乳化剂如卵磷脂和人造甜味剂如糖精等GRAS物质在饮食相关水平下可能通过影响肠道微生物组诱导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得到了说明。
牛磺胆酸可能通过菌群与肠道病理的关联
GRAS化合物牛磺胆酸及其化学成分,GRAS化合物牛磺酸和胆酸,可能与肠道微生物组相互作用,促进肠道病理。具体来说,由Bilophila wadsworthia细菌在牛磺胆酸的脱结合过程中释放的牛磺酸产生遗传毒性的硫化氢,同时释放的胆酸作为微生物产生促炎的次级胆汁酸脱氧胆酸的基质。因此,补充牛磺胆酸的饮食导致了B. wadsworthia的增长和易感基因型(IL-10−/−)小鼠中结肠炎的发展。
肠道微生物组可能转化为更有害的形式:杂环胺的肠肝循环
此外,肠道微生物组可能使用其广泛的酶库将饮食化合物或宿主代谢产物转化为更具有害的形式。例如,细菌β-葡萄糖醛酸酶有助于致癌的杂环胺(如IQ,2-氨基-3-甲基咪唑[4,5-F]喹啉)的肠肝循环,这些物质通过肝脏的葡萄糖醛酸化被解毒。
在暴露于IQ时,常规小鼠比无菌小鼠显示出更多的DNA加合物和DNA损伤。单核子大肠杆菌携带功能性与非功能性uidA基因(编码β-葡萄糖醛酸酶)的大鼠表现出增加的结肠遗传毒性,与这种化合物排泄的多个峰值相结合,这与肠肝循环一致。
三聚氰胺污染+肠道微生物组→肾脏病理
肠道微生物组还与由饮食污染物三聚氰胺引起的肾脏病理有关,三聚氰胺是一种用于许多食品制备工具的塑料添加剂。体外和体内实验表明,存在于一些婴儿肠道中的克雷伯菌可以将三聚氰胺转化为三聚氰酸,三聚氰酸现在已知与三聚氰胺形成不溶性的肾脏聚集体。
有益效应
另一方面,肠道微生物组对未吸收的饮食化合物的生物转化可能有助于有益效应,这些效应如果只关注饮食对宿主的直接影响则可能被忽视。
对抗乳腺癌的保护作用
例如,植物衍生的饮食木脂素(如全谷物、种子、豆类和坚果中发现的)的肠道微生物生物转化被认为是它们对抗乳腺癌的保护作用的基础。一组肠道细菌类群(例如,Eggerthella lenta、Blautia producta、Gordonibacter pamelaeae和Lactonifactor longoviformis)将饮食木脂素松香转化为具有抗癌作用的雌激素模拟物enterodiol和enterolactone。
因此,与无菌动物相比,在化学诱导乳腺癌时,能够从饮食木脂素前体产生enterodiol和enterolactone的细菌群落定植的无菌大鼠显示出较少的肿瘤数量和较小的肿瘤大小。
扩展阅读:
肠道菌群有助于饮食解毒改变疾病风险
例如,肠道细菌Oxalobacter formigenes参与草酸盐的分解,草酸盐是一种螯合饮食毒素,通过结合游离金属阳离子,有助于肾结石和肾衰竭。缺乏O. formigenes与高草酸尿症的风险增加有关,其在大鼠中的施用以剂量依赖性的方式减少了饮食诱导的高草酸尿症。
在探索肠道微生物群与饮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微小的生态系统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调节能量平衡到影响免疫功能,从塑造情绪到预防疾病,肠道微生物群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当然,饮食也只是众多生活方式因素之一,例如身体活动、环境暴露和睡眠,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宿主的能量平衡和肠道微生物群。此外,药物的广泛使用已经显著改变了饮食干预的背景。例如,GLP-1 激动剂延迟胃排空,这对消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包括肠道微生物代谢可用底物的变化。
即使仅考虑饮食,现在也非常清楚,肠道微生物影响宿主代谢的多种途径,加上关键的饮食和微生物组相关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次级胆汁酸等)的多效性作用,使预测特定饮食或微生物组特征的代谢影响变得复杂。
实现基于微生物组的精准营养方法需要对人类进行实验研究,以测量整个生物体水平的综合影响,涵盖地理、性别、种族和年龄等各种因素,以及更大规模的横断面研究,针对饮食成分、肠道微生物组结构和功能以及宿主健康之间的特定联系。
这些数据将受益于机器学习的快速发展并将人工智能与实施精准医疗方面的结合起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数据的积累,肠道菌群检测有望成为精准营养和个性化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健康,预防疾病,并提升生活质量。
主要参考文献
Carmody RN, Varady K, Turnbaugh PJ. Digesting the complex metabolic effects of diet on the host and microbiome. Cell. 2024 Jul 25;187(15):3857-3876.
Ross FC, Patangia D, Grimaud G, Lavelle A, Dempsey EM, Ross RP, Stanton C. The interplay between diet and the gut microbiome: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and disease. Nat Rev Microbiol. 2024 Jul 15.
Ahmad S, Moorthy MV, Lee IM, Ridker PM, Manson JE, Buring JE, Demler OV, Mora S. Mediterranean Diet Adherence and Risk of All-Cause Mortality in Women. JAMA Netw Open. 2024 May 1;7(5):e2414322.
McEvoy CT, Jennings A, Steves CJ, Macgregor A, Spector T, Cassidy A. Diet patterns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a UK Female Twin Registry (TwinsUK). Alzheimers Res Ther. 2024 Jan 23;16(1):17.
Link VM, Subramanian P, Cheung F, Han KL, Stacy A, Chi L, Sellers BA, Koroleva G, Courville AB, Mistry S, Burns A, Apps R, Hall KD, Belkaid Y. Differential peripheral immune signatures elicited by vegan versus ketogenic diets in humans. Nat Med. 2024 Feb;30(2):560-572.
Staudacher HM, Mahoney S, Canale K, Opie RS, Loughman A, So D, Beswick L, Hair C, Jacka FN. Clinical trial: A Mediterranean diet is feasible and improves gastrointestin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24 Feb;59(4):492-503.

谷禾健康

营养不良的微生物 Malnourished Microbes
儿童营养不良是全球主要的健康负担,营养干预措施只能部分解决这一问题。儿童营养不良的慢性和急性形式均以多种生物系统紊乱为特征,包括新陈代谢、免疫和内分泌系统。
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肠道微生物组在调节这些影响早期生命生长的途径中的作用。观察性研究报告了营养不良儿童肠道微生物组的变化,而临床前研究表明,这可能引发肠病,改变宿主代谢,并破坏免疫介导的针对肠道病原体的抵抗力,这些都会导致早期生命生长不良。
肠道微生物组在健康和疾病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饮食是其组成、多样性和功能的主要驱动因素。鉴于婴儿和儿童肠道微生物组的动态发育,解决两个主要问题至关重要:
a) 饮食能否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多样性或功能
b) 这种修改是否会影响功能/临床结果,包括免疫功能、认知发展和整体健康?
本文汇编了临床前和临床研究的证据,包括生命早期肠道微生物组影响宿主代谢、免疫、肠道功能、内分泌调节和其他导致儿童营养不良的途径的新兴病理生理学途径。
我们综合了儿童青少年的营养、营养干预措施和肠道微生物群之间联系的最新研究,该年龄段儿童是一个生长阶段,对疾病的易感性各不相同。还讨论了营养素如何单独或组合如何影响肠道微生物组的机制。
同时综合并讨论了新兴的微生物组导向疗法,并考虑未来的研究方向,以确定和针对儿童营养不良的微生物组治疗目标。
2013年发表在《柳叶刀》上文章统计,儿童营养不良导致全球儿童死亡人数的 45%,并对健康产生终生影响。全世界超过五分之一的5岁以下儿童至少表现出一种形式的慢性或急性营养不良。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发育迟缓、消瘦的定义。
发育迟缓[定义为年龄别身长 Z 得分 (LAZ) < −2],影响着全球 22% 的儿童,与认知发展较差、终身综合能力下降以及成年后慢性病风险增加有关。
消瘦[定义为身高体重 Z 得分 (WHZ) < –2] 影响着全世界近 7% 的儿童,除了长期认知和健康缺陷不佳之外,还与高死亡率相关。
▸ 目前的治疗方法无法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营养疗法不足以完全恢复生长缺陷和营养不良的相关病理生理后果。标准生命早期营养补充剂仅可将发育迟缓降低 12-14%。
而严重消瘦后会出现高死亡率、再入院和长期生长缺陷。因此,存在与儿童营养不良相关的隐藏的病理生理学负担,目前的治疗方法无法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 儿童营养不良与多个生命早期生物系统紊乱有关
发育迟缓和消瘦儿童的肠道功能受到环境肠道功能障碍(EED)的影响。这种肠道病理学损害营养吸收,并可能导致全身炎症,从而损害早期生命生长。
在营养不良的儿童中宿主免疫力广泛缺陷,导致抵抗感染能力受损,特别是病原体密集的环境。
营养良好和营养不良的儿童之间存在激素差异,尤其是与生长 [生长激素 (GH) 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IGF-1)] 和食欲调节(瘦素和生长素释放肽)相关的荷尔蒙差异。
营养不良时宿主代谢发生改变,氨基酸、脂质和能量代谢受到干扰。这些受到干扰的生理系统表明,儿童营养不良背后存在复杂的病理生理学,涉及相互关联的生物系统。
▸ 微生物群影响生命早期的生长发育
生命早期接触微生物也可能导致儿童营养不良中这些扰动途径。肠道病原体携带量高与线性生长和体重生长下降以及 EED 相关,而腹泻和呼吸道感染也与儿童营养不良密切相关。
除了病原体之外,共生肠道微生物群也会影响早期生命的生长。生命早期复杂微生物组的组装对于免疫训练、对病原体的定植抵抗、母乳寡糖(HMO) 和其他营养物质的代谢、肠道结构和内分泌信号传导至关重要。
因此,儿童时期肠道微生物组的破坏可能会损害这些有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途径。
▸ 儿童在出生时就获得了一些的微生物组
除了环境获得的微生物外,这些微生物组主要源自母体肠道、阴道、口腔和皮肤微生物组。
在纯母乳喂养的儿童中,最初的婴儿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仍然很低,主要由大肠杆菌、双歧杆菌和拟杆菌组成物种。
在接下来2-3 年里,肠道微生物群会经历一种模式化的组装,这种组装主要是由纯母乳喂养和随后的补充食品的引入所形成的,这导致肠道微生物群的快速扩张和多样化。
▸ 许多环境因素会影响微生物,从而影响生长
包括地理位置、分娩方式、抗生素暴露、胎龄以及其他母亲和家庭因素。这些微生物群在出生后在胃肠道内的积累,除了肠道结构和对病原体的定植抵抗力之外,还推动了免疫、代谢和内分泌途径的成熟,这些都有助于儿童的正常生长。
如果微生物演替因营养不足、卫生或抗生素暴露而受到干扰,这些生长决定途径可能会受到损害。很少有研究纵向研究在营养匮乏的环境中保持良好营养的儿童与消瘦或发育迟缓的儿童的肠道微生物群的演替和组装情况。
因此,这种依赖高收入环境的微生物组数据库的现象,限制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个体所产生的营养不良微生物组的解释性(这也是构建本地数据库和谷禾长期追踪重点人群纵向数据的主要原因),这些国家的肠道微生物组特征不太明确。
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横断面和短期纵向研究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揭示了微生物组的差异,这些差异将营养不良与健康生长区分开来。
▸ 发育迟缓——多因素驱动
“发育迟缓”是一种慢性营养不良的形式,由多种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驱动。高达30%的发育迟缓发生在子宫内,这可以通过出生体重对发育迟缓风险的强烈影响来证明。
之后一系列环境因素有助于产后线性生长。很少有研究纵向研究健康婴儿与发育不良婴儿肠道微生物组的获取和组装情况。
▸ 横断面研究:肠道菌群特征破坏导致发育迟缓
对马拉维和孟加拉国队列的二次分析发现,微生物组多样性减少和Acidaminococcus(氨基酸球菌)丰度增加分别与发育迟缓严重程度和未来线性生长缺陷相关。
其他一些小型横断面研究已经发现,在一系列中低收入国家队列中,发育不良儿童与健康儿童的粪便微生物组组成存在不同差异。来自中非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的一项更大规模的多点横断面分析发现,发育不良儿童的粪便微生物群中大肠杆菌/志贺氏菌和弯曲杆菌种类丰富,而产生丁酸的种类较少。
▸ 发育迟缓的儿童:小肠细菌过度生长
在发育迟缓的儿童中观察到小肠细菌过度生长的比率较高,其特征是十二指肠中口咽微生物的富集。发现一群来自孟加拉国的发育迟缓儿童的小肠细菌载量与 LAZ 之间呈负相关。韦荣球菌属、链球菌属和Rothia mucilaginosa的十二指肠丰度也与 LAZ 呈负相关。
▸ 肠道菌群的功能潜力——预测儿童生长的指标
对 335 名津巴布韦农村的 1 至 18 个月大儿童的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和功能发育的跟踪发现,肠道微生物组的功能宏基因组组成(而非分类组成),可以预测孩子已达到的线性生长和未来的生长速度,其中 B 族维生素和核苷酸生物合成途径是最具预测性的特征之一。这些数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组的功能潜力是儿童生长的更强大的指标。
来自马拉维的一个纵向队列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即 16S 测序无法识别成分多样性、成熟度或物种丰度与 LAZ 之间的关联。秘鲁对 6-24 个月大的儿童(作为营养不良和肠道疾病队列的一部分)进行的一项纵向研究表明,成分多样性与线性生长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仅针对出生时发育迟缓的儿童。
该研究组另外一项研究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组可能介导腹泻和弯曲杆菌感染对线性生长的影响。除了肠道微生物组细菌成分的影响之外,发育迟缓婴儿与非发育迟缓婴儿中噬菌体(可以调节微生物组组成的病毒)的丰度也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发育不良儿童的肠道微生物群与营养良好的儿童不同。然而,这因地理群体而异。因此,目前不存在一致的发育迟缓的组成或功能微生物组特征。
▸ 儿童口腔微生物组与发育迟缓有关
发育迟缓的儿童在十二指肠和粪便中表现出更丰富的口咽微生物,包括唾液乳杆菌,这表明胃肠道的隔室化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儿童中肠道菌群变化,并通过减少营养吸收而导致生长不良或口腔微生物在其生态位之外的炎症作用。
▸ 怀孕期间母亲的口腔微生物组预测儿童营养不良
牙周炎是一种口腔生态失调疾病,会导致局部免疫反应功能失调,并与低出生体重呈负相关。在怀孕期间的母亲口腔中,Actinomyces naeslundii(内氏放线菌)的相对丰度与出生体重和妊娠持续时间呈负相关,而Lactobacillus casei(干酪乳杆菌)则呈正相关,两者都强烈预测儿童营养不良。
▸ 早产的阴道微生物组,与新生儿低出生体重和随后的发育迟缓密切相关
高度多样化、缺乏乳杆菌的阴道微生物群与西方地区的早产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新生儿 LAZ 的减少密切相关。阴道微生物组的改变很可能与早产的经典感染触发因素同时发生,包括绒毛膜羊膜炎、细菌性阴道病和泌尿生殖感染,从而导致泌尿生殖环境炎症,这些共同可能限制胎儿生长或引发早产。
▸ 消瘦及其分类:营养不良形式的反映
消瘦是营养不良的一种形式,可以反映慢性营养缺乏和急性疾病,通常与发育迟缓同时发生。
消瘦可分为中度[中度急性营养不良(MAM)]或重度[严重急性营养不良(SAM)],取决于 WHZ 阈值、中上臂围 (MUAC) 和/或水肿的存在。
▸ 水肿性SAM、非水肿性SAM、复杂SAM
SAM 还以两种主要形式存在:
如果出现急性感染、食欲不振、休克或水肿(也称为复杂 SAM)。
患有水肿性和非水肿性 SAM 的儿童具有不同的临床结果,其中非水肿性 SAM 儿童在某些情况下接受 SAM 住院治疗后表现出更高的死亡率和再入院率。
尽管治疗 SAM 的营养疗法有所改进,但需要住院治疗的复杂 SAM 的死亡率在 10% 至 40% 之间,而生长缺陷可能会持续长达7年,此外,日后认知缺陷和慢性病风险也会增加。
▸ 在SAM 儿童肠道中肠道微生物组具有影响力
患有 SAM 的儿童肠道微生物多样性降低,肠杆菌科细菌增多,而与健康生长一致的双胞胎相比,SAM不一致的双胞胎肠道病毒组受到干扰。
▸ 年龄微生物群Z评分——微生物群成熟度指标
2014 年,孟加拉国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创建了微生物群成熟度指标,称为年龄微生物群Z评分(MAZ),该评分在 SAM 儿童中显着降低,并且与术后营养恢复的人体测量指标高度相关。这项研究和最近的后续研究使得所谓的微生物组生态群得以细化,该生态群由 15 种细菌类群组成,这些细菌类群在不同地理环境中在生命的头 2 年中表现出一致的共变,可用作微生物群落的指标。
不成熟的微生物组发育并衡量MAM 或 SAM 后微生物组的恢复程度。根据 MAZ 的评估,标准治疗性往往只能暂时恢复微生物组的成熟度,表明 MAZ 可能有潜力作为未来 MAM/SAM 复发的指标,或者针对肠道微生物组的营养疗法可能有助于营养恢复。
事实上,这些微生物群成熟度指标为 MAM 中新的微生物群导向营养干预措施提供了信息,在试点研究中,与标准治疗食品相比,这些干预措施在更大程度上改善了营养恢复。
▸ 在水肿性SAM 和非水肿性 SAM 儿童差异
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他们营养恢复的差异。与水肿性SAM儿童相比,非水肿性 SAM 儿童的α多样性显著降低,并且与普雷沃氏菌科(Prevotellaceae)、毛螺菌科 (Lachnospiraceae) 、瘤胃菌科(Ruminoccoaceae)相对丰度的减少有关。
总的来说,与健康成长的儿童相比,SAM 儿童的微生物组始终不成熟且多样性降低。这种失调的微生物组可能是急性营养状态以及与治疗相关的合并症和抗生素治疗的结果。
如上所述,越来越多的人类观察研究证据表明,营养良好和营养不良的儿童之间的微生物组组成存在差异。
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已开始揭示,生命早期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可能导致儿童生长不良的病理生理机制。其中包括肠道微生物组对免疫、新陈代谢、肠道功能和内分泌信号传导等途径的影响(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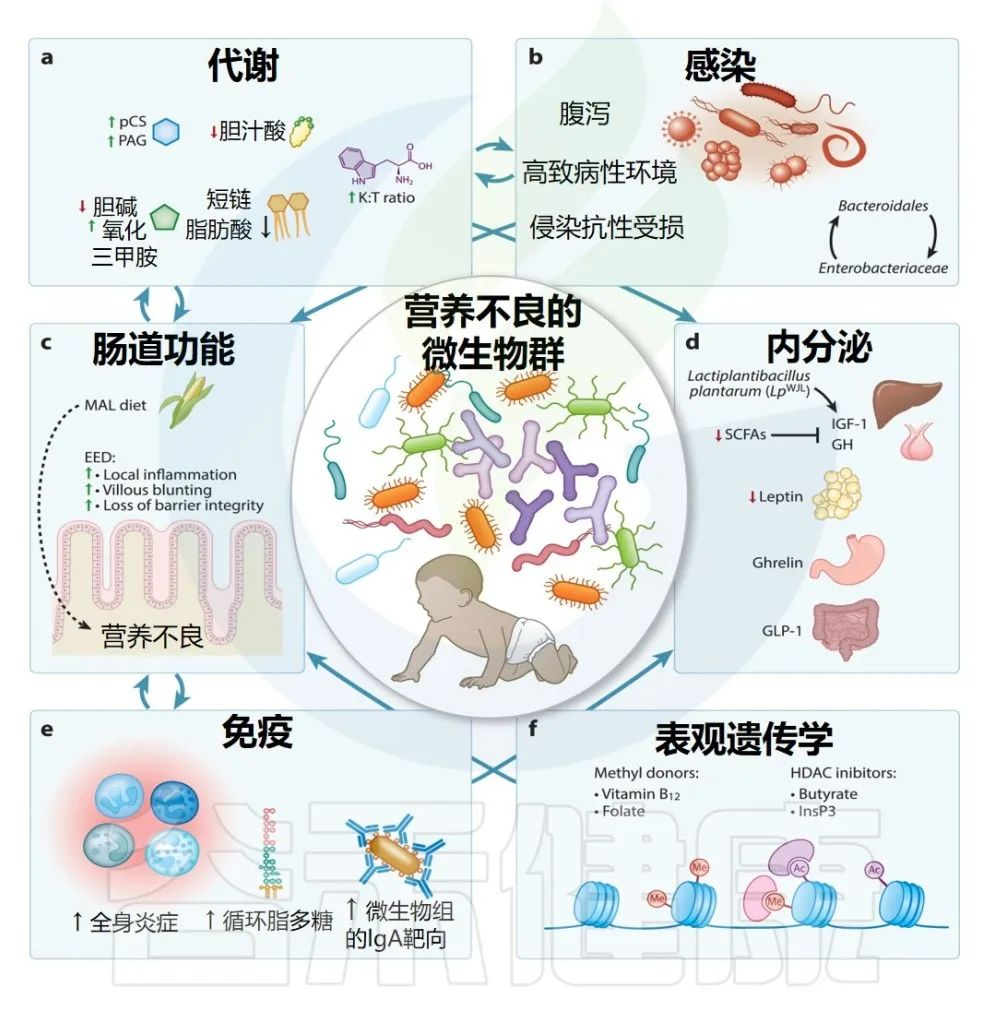
doi.org/10.1146/annurev-nutr-061121-091234
下面我们逐一来了解营养不良的微生物群带来的多方面影响。
共生肠道微生物群的存在,对于生命早期肠道屏障的正常结构、功能和转录发育至关重要。临床前研究的大量证据表明,无菌小鼠幼崽表现出肠道屏障成熟延迟,这与自发性结肠炎、更容易肠道感染和营养吸收不良有关。
生命早期长期接触肠道病原体会破坏肠道结构和功能。环境肠道功能障碍(EED)是一种胃肠道现象,在营养匮乏的环境中很常见,并且经常在营养不良的儿童中观察到(我们以前也专门写过儿童EED的文章)。
▸ 什么是环境肠道功能障碍(EED)?
EED 通常是亚临床的,局限于小肠,其特征是肠道通透性增加、绒毛萎缩和变钝、粘膜屏障变化、吸收不良、局部炎症和隐窝伸长。屏障功能的丧失还导致微生物及其产物(最常研究的是脂多糖)从肠道转移到体循环中,从而刺激全身炎症。据推测,营养吸收不良、肠道炎症和慢性全身炎症的结合会阻碍儿童的健康成长。
▸ 环境肠道功能障碍(EED)与什么相关?
EED 通常归因于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WASH) 较差的环境中长期接触肠道病原体。然而,在此类环境中改善怀孕期间和早期生活中的 WASH 的大型随机试验未能减少幼儿 EED 的常见生物标志物,这可能是由于同时未能减少其肠道病原体携带。
除了病原体携带之外,共生微生物组的破坏也可能导致 EED。对611 名儿童( 6、18 和 30 个月大)大型分析发现,微生物群多样性/成熟度与 EED 的三种生物标志物之间存在负相关:
表明肠道微生物群的不成熟可能会导致肠道炎症和屏障功能障碍。特定菌群的丰度升高,包括Megasphaera、Mitsuokella、Sutterella也与 EED 有关。
注:REG1B,Regenerating family member 1 beta 是一种蛋白质,它是一种由胰腺细胞产生的蛋白质,在胰岛细胞再生和胰岛功能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
REG1B在胰腺细胞再生过程中被表达,且参与了胰岛细胞增殖和分化,对胰岛细胞的生长和修复有促进作用,在胰岛素分泌和血糖调节中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
EED 动物模型有助于深入了解可能驱动该疾病表型的机制。一些模型能够通过应用低蛋白饮食和 LPS 或吲哚美辛等肠道损伤来复制 EED 的某些方面。
注:吲哚美辛:用于治疗关节炎,癌性疼痛,痛风,滑囊炎、肌腱炎及肩周炎等非关节软组织炎症;可用于高热的对症解热,恶性肿瘤引起的发热或其他难以控制的发热。
▸ 肠道微生物对 EED 的潜在贡献
利用异常微生物状态和改变的营养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新模型已经成功地概括了几种 EED 表型。例如,肠道生理学和微生物组通过血管紧张素 I 转换 2 酶 (ACE2) 的表达联系起来。
注:ACE2是一种在分化上皮细胞的管腔表面表达的蛋白质。
与野生型小鼠相比,缺乏 ACE2 的小鼠在受到DSS攻击时,表现出类似 EED 的病理学、氨基酸代谢紊乱和肠道微生物组紊乱。DSS 攻击期间的 EED 表型可以在从 ACE2 缺陷小鼠进行粪便移植后转移到野生型动物中,这表明微生物群被破坏。
注:DSS,右旋糖酐硫酸钠,一种破坏肠上皮屏障并导致结肠炎的刺激物
膳食色氨酸及其代谢物烟酰胺可以通过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点 (mTOR) 活性刺激抗菌肽的产生,从而挽救 ACE2 缺陷小鼠的表型,从而维持微生物组稳态。
▸ 微生物结合营养物质影响EED
低蛋白、低脂肪饮食会导致小鼠小肠微生物群遭到破坏,其特点是小肠内物种丰富度升高,此外拟杆菌门和变形菌门也会扩张。
将营养不良的饮食与拟杆菌和大肠杆菌结合起来作者产生了 EED 的表型,包括肠道通透性、绒毛和隐窝萎缩增加、空肠细胞因子 (IL-6 和 MCP-1)释放到腔内增加,以及细菌对小肠上皮细胞的粘附增加。这种表型依赖于微生物组的改变和营养不良的饮食,这表明 EED 表型是复杂的微生物与营养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
总体表明,肠道微生物群破坏在营养不良相关肠道功能障碍的病理学中具有潜在的因果作用。
▸ 腹泻和有症状的呼吸道感染与发育迟缓和消瘦有关
关于腹泻和儿童营养不良的大型多中心研究的有力证据表明,肠道病原体的高负担与生命早期生长不良有关。
健康且多样化的肠道微生物群通过生态位排除提供针对肠道病原体的定植抵抗力。因此,受损的肠道微生物组可能为病原体定植提供了环境。
肠道微生物组也可能介导远处部位的感染易感性,包括肺部。因此,生命早期健康肠道微生物组可能有助于在卫生条件差的环境中抵抗病原体的定植,从而防止感染负担和相关的生长不良。
▸ 发育迟缓:肠道菌群多样性减少——预示腹泻发病率的增加
来自秘鲁的发育不良儿童在生命的前两年表现出肠道微生物组多样化轨迹受损。在此期间,发育迟缓的儿童的微生物多样性显着减少,腹泻后多样性的恢复也较慢。因此,肠道微生物组的组装受损可能会加剧感染-发育迟缓的循环。
来自同一队列的一项研究发现,弯曲杆菌的携带与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有关。此外,肠道微生物组内与弯曲杆菌携带相关的物种与 LAZ 的减少独立相关,这表明肠道微生物组组成受损会促进病原体定植和并发生长缺陷。
▸ 营养不良:微生物组对病原体定植产生影响
与营养良好的小鼠相比,由营养不良饮食和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引起的 EED 小鼠模型对感染的敏感性更高,这表明与营养不良相关的微生物群破坏可能会导致病原体定植和感染负担。
蓝氏贾第鞭毛虫感染后生长缺陷的易感性也取决于动物模型中的肠道微生物组。人类研究报告称,贾第鞭毛虫和相关的肠侵袭性病原体,除了那些涉及粘膜破坏的病原体外,对全身炎症、肠道炎症和生长受损具有最深远的影响。
在小鼠中,贾第鞭毛虫与小肠中的肠杆菌科细菌相互作用,以限制蛋白质营养不良期间的生长,这种作用在用没有抗贾第鞭毛虫活性的抗菌药物治疗后消失,表明失调的微生物群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表明特定的病原体或病原体依赖于共生肠道微生物群的成员来定殖和增殖。这在人类发育迟缓研究中很明显,即肠杆菌科细菌和拟杆菌目细菌之间的交叉喂养与儿童发育迟缓有关。
▸ 在体外,肠杆菌科和拟杆菌目之间协同生长
特别是在蛋白质和铁含量低的营养不良条件下。在这种情况下拟杆菌属利用饮食和粘蛋白衍生的糖和肠杆菌科细菌提高铁的生物利用度,铁是特定病原体增殖所必需的微量营养素。
拟杆菌科和肠杆菌科在营养不良的儿童中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在营养良好的儿童中则没有。另一种拟杆菌属的脆弱拟杆菌,还依赖周围的微生物群来诱导小鼠的生长效应。含有bft毒素的脆弱拟杆菌的产肠毒素菌株会导致无菌小鼠体重减轻和能量代谢受损,这些小鼠被来自发育迟缓儿童的微生物群定植,但对于那些被来自营养良好儿童的微生物群定植的小鼠则不会。
这些数据表明,病原体和感染对儿童营养不良的影响可能依赖于共生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在儿童营养不良患病率高的环境中减少病原体负担的策略除了考虑病原体负担外,还必须考虑共生微生物群。
营养不良儿童的宿主蛋白质、脂肪和能量代谢紊乱早已有报道。然而,肠道微生物组的代谢能力大大扩展了哺乳动物宿主的生物转化能力,扩大了可加工底物的多样性,并增加了宿主接触的分子范围。
许多微生物衍生的代谢物可以在肠道和肠壁中发挥局部作用,并且在吸收后还可以影响周围组织中的宿主过程。因此,儿童早期肠道微生物组的变化可能会通过改变提供给儿童的代谢副产物和宿主代谢途径本身来影响代谢表型,从而影响生长。
▸ 成熟度与微生物代谢
与用于绘制儿童微生物组成熟度的MAZ评分类似,代谢成熟度模型,称为年龄表组 Z 评分 (PAZ),是根据秘鲁、坦桑尼亚和孟加拉国儿童的尿液样本构建的,并用于追踪生化年龄及其与生长的关系。用于计算 PAZ 的八种代谢物中的三种——对甲酚硫酸盐 (pCS)、苯乙酰谷氨酰胺 (PAG) 和马尿酸,与肠道微生物代谢相关。
有趣的是,与未生长受限的婴儿相比,生长受限的婴儿早在出生后 3 个月就出现生化不成熟(即,其生化年龄低于实际年龄)。这凸显了微生物群在宿主整体代谢能力发展及其对生长的后续影响中的重要性。
健康肠道微生物群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发酵宿主无法消化的膳食底物。在母乳喂养期间,这主要涉及HMO的微生物消化。患有发育不良婴儿的母亲的母乳中 HMO 含量明显较低,结构相似的牛乳低聚糖可以恢复营养不良模型中小鼠的生长。
然而,这种效果取决于微生物群,因此补充乳寡糖后,无菌小鼠的生长不会恢复。断奶后,肠道微生物群转向不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抗性淀粉、粘蛋白和蛋白质的代谢。
▸ 糖分解产生短链脂肪酸,满足能量需求
糖分解活性(即碳水化合物的分解)的主要最终产物是短链脂肪酸。这些都有助于宿主日常的能量需求。丁酸盐是结肠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提供其所需能量的 80%,而乙酸盐在肌肉等全身区域代谢,丙酸盐在肝脏中用于产生 ATP。
这种微生物活动提供了一种从饮食中释放能量的机制,可用于支持生长。此外,短链脂肪酸还具有其他有益作用,例如降低结肠 pH 值以增强对潜在病原体的定植抵抗力并提高矿物质吸收。此外,丁酸盐已被证明可以通过增加 AMP 激活蛋白激酶 (AMPK) 活性和紧密连接蛋白的组装来促进肠道屏障的发育。
▸ 营养不良:从碳水化合物发酵和短链脂肪酸生产转向蛋白水解代谢
例如,与营养良好的儿童相比,印度尼西亚中度营养不良儿童的粪便丙酸盐和丁酸盐含量较低,粪便 pH 值较高。
在营养不良的猪模型中,肠道微生物组产生的丁酸盐较少,并且与肝脏脂肪酸代谢(β-氧化)减少有因果关系。同样,在对巴西东北部儿童进行的代谢组学研究中,发育不良的婴儿排出了更多由微生物降解氨基酸而产生的微生物-宿主共代谢物。
其中包括 pCS 和 PAG,它们分别源自酪氨酸和苯丙氨酸的微生物分解。营养不良病原体相关的EED导致肠道吸收不良可能会推动这一观察。这增加了小肠中氨基酸的可用性,从而导致发育不良儿童中的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并增加到达结肠进行细菌代谢的氨基酸。
▸ 营养不良:微生物群与发育中的宿主竞争氨基酸
有趣的是,虽然 SCFA 促进上皮屏障完整性,但 pCS 被发现会损害它,可能导致营养不良个体中观察到的肠漏表型。
此外,pCS由艰难梭菌和其他病原体产生,限制肠道微生物群的生物多样性。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婴儿中观察到的微生物群失调。另外两种氨基酸代谢物,吲哚乳酸和N-乙酰谷氨酸,分别源自色氨酸和谷氨酸代谢,在来自孟加拉国的一组儿童中,它们与 2-24 个月龄之间的线性和体重生长指标呈正相关。长双歧杆菌也与生长呈正相关,它编码了参与这些化合物生产的大部分微生物代谢途径,这些化合物可能有助于支持早期生命的生长。
▸ 膳食胆碱的微生物分解增加还导致蛋白质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
在蛋白质缺乏的小鼠模型中,尿胆碱减少,而胆碱代谢的微生物产物三甲胺和二甲胺增加。
同样,在马拉维儿童中,血清中三甲胺-N-氧化物(TMAO)与胆碱的比率与线性生长障碍呈正相关。
胆碱和甜菜碱排泄量降低与巴西婴儿发育迟缓有关。胆碱的可用性不仅对于肌肉获得很重要,对于S-腺苷甲硫氨酸 (SAMe)的生成也是必要的,而 S-腺苷甲硫氨酸 (SAMe) 是 DNA 甲基化和发育的关键。
重要的是,胆碱是骨骼肌的必需营养素以及神经发育和大脑功能。胆汁酸是宿主肝脏和肠道微生物群组合代谢产生的代谢物的一个例子,在消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初级胆汁酸,例如胆酸和鹅去氧胆酸,在肝脏中合成,然后通常与甘氨酸或牛磺酸结合,并分泌到胆汁中。释放到肠道后,一小部分胆汁酸可以到达结肠,在那里微生物群将它们分解并转化为次级胆汁酸,例如脱氧胆酸。这些修饰的胆汁酸可以通过粪便排出或再循环回肝脏。
与没有 EED 的儿童相比,患有 EED 的儿童的血清总胆汁酸含量较低,其中牛磺鹅去氧胆酸、牛磺鼠胆酸和甘氨酰去氧胆酸存在特定差异。除了消化之外,胆汁酸在代谢调节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充当全身表达的受体(例如 FXR、PXR、VDR 和 TGR5)的配体,胆汁酸可以调节多种宿主途径和功能的表达,例如能量稳态、葡萄糖和脂质代谢。
▸ 这些细菌相关代谢物还具有抗菌特性,既能抑制又能促进特定病原体的生长
例如,胆汁酸代谢的变化,特别是细菌胆汁盐水解酶活性,被认为是隐孢子虫卵囊排泄的重要触发因素。此外,观察到未患阿米巴病的儿童粪便中次级胆汁酸、脱氧胆酸的含量较低。研究表明,给小鼠注射这种胆汁酸足以增加粒细胞-单核细胞祖细胞的数量,并提供针对阿米巴病的保护。这表明胆汁酸可能在预防营养不良环境中常见的不同肠道感染和对这些感染的易感性方面发挥潜在作用。
▸ 从微生物代谢,到宿主代谢的改变
除了微生物代谢的改变外,在营养不良的儿童中还观察到宿主代谢的改变,这可能部分是由菌群失调引起的。例如,从发育迟缓儿童的小肠中分离出的口腔微生物在体外和体内模型中会损害脂质吸收,从而提供小肠微生物组和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在营养不良中的潜在因果作用。
肠道屏障功能的丧失会导致微生物群及其产物(包括脂多糖)从肠道进入体循环的易位增加。LPS 易位可导致慢性全身炎症,从而通过吲哚胺 2,3-双加氧酶诱导激活色氨酸-犬尿氨酸途径。事实上,秘鲁和坦桑尼亚儿童的血浆犬尿氨酸与色氨酸 (K:T) 比率与血浆 LPS 和 LPS 结合蛋白 (LBP) 相关,并且还与线性增长缺陷相关。
扩展阅读:
犬尿氨酸途径的激活可以抑制炎症并促进耐受性,但可能会失调色氨酸途径,而色氨酸途径对于血清素的产生以及 NAD +和烟酰胺的生成非常重要,而后者是生长的关键。免疫耐受性的增加也可能对增强对病原体的有效反应产生影响,这也可能受到色氨酸剥夺的影响,并可能导致此类感染在营养不良的肠道中持续存在。
儿童营养不良与内分泌信号中断有关,包括介导食欲和能量代谢的瘦素和生长素释放肽,以及共同构成生长轴的GH 和IGF-1 。
发育迟缓儿童与非发育迟缓儿童相比,在童年后期血浆 IGF-1 较低以及生命的前 18 个月,一种与慢性炎症相关的现象。
▸ 瘦素水平低可预测SAM儿童的死亡率
新数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组直接和间接影响肠道局部激素的产生,例如胰高血糖素样肽-1 (GLP-1),并通过介导瘦素、生长素释放肽和 IGF-1 的产生来系统地进行,每一个都调节新陈代谢和营养状况。
▸ 微生物组→产生SCFA→GLP-1 的产生→抑制胰高血糖素原的表达
GLP-1 是一种肠道源性激素,负责刺激胰岛素分泌、减少胃排空和增加饱腹感,从而影响新陈代谢和营养状况。
在没有微生物组的情况下,在无菌小鼠中,GLP-1 的产生在一种假设的适应性机制中升高,当微生物组被破坏或不存在时,GLP-1 的产生会增加营养物质的吸收,而 SCFA 给药可以逆转这种效应。
▸ 微生物衍生的SCFA也会影响 IGF-1 的产生
IGF-1 在肝脏和脂肪组织中产生,影响骨形成、骨量和骨骼生长,尤其是在生命早期。当无菌小鼠被微生物定植时,血浆中血清 IGF-1 的浓度会增加。
同样,抗生素的使用会降低 IGF-1 浓度,而补充 SCFA 可恢复抗生素治疗期间 IGF-1 的浓度。不产生短链脂肪酸的细菌种类也可以通过刺激生长轴来刺激实验动物的生长。植物乳杆菌的特定菌株可恢复果蝇和小鼠的线性生长、股骨长度、IGF-1 产生和活性以及外周组织对 GH 的敏感性。
植物乳杆菌WJL ( Lp WJL ) 菌株对 IGF-1 产生和生长的活性取决于肠上皮细胞中含有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的蛋白 2 (NOD2) 的刺激。
▸ 肠道共生细菌还可以防止感染时的肌肉萎缩
共生大肠杆菌在骨骼肌中维持 IGF-1 信号传导,独立于宿主代谢、热量吸收或炎症,从而防止肠道或肺部感染后肌肉萎缩。
▸ 与饱腹感和新陈代谢有关的激素与特定共生菌群丰度相关
在动物模型中,双歧杆菌和乳酸菌丰度与瘦素浓度呈正相关,而生长素释放肽则与拟杆菌和普雷沃氏菌丰度呈正相关。
在营养不良模型中,生长素释放肽水平还与双歧杆菌、乳酸菌和球状球菌-直肠真杆菌呈负相关。一项针对 6 至 24 个月大的冈比亚儿童( n = 60)的横断面观察队列研究发现,严重营养不良儿童的肠道微生物群与代谢激素浓度之间存在许多密切相关性,使用网络分析模拟肠道微生物组和激素相互作用。埃希氏菌/志贺氏菌通过其与生长素释放肽和生长素释放肽受体的相互作用,在区分健康对照和营养不良患者方面具有高度预测性,而粘膜乳杆菌与瘦素/瘦素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对营养不良和营养良好的儿童具有高度区分性。肠杆菌科细菌和 IGF-1 的相互作用也区分了 MAM 和 SAM。
这些相互作用可能是双向的,瘦素可以刺激粘蛋白的产生并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而特定的产生脂多糖的肠杆菌科细菌的炎症活性可能会损害 IGF-1 和 GH 信号传导。
微生物群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与宿主免疫系统保持着相互的、动态的沟通,而这种沟通会因营养不良而被破坏。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营养不良的儿童在免疫学上与营养充足的同龄人不同,胸腺较小,免疫细胞组成和分布在质量和数量上不同,全身和肠道环境中的促炎介质长期升高,以及由不利因素驱动的免疫基因上的表观遗传标记。
产前和产后暴露。迄今为止,大多数营养不良儿童的免疫表型都是在感染和病原体携带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然而,新出现的数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组内共生和条件致病微生物的多样性可能会驱动营养不良儿童的独特免疫表型,而与病原体无关。
▸ 营养不良引起的肠道炎症的特征——EED生物标志物
例如钙卫蛋白和髓过氧化物酶,这些生物标志物是由肠道组织中微生物激活的先天免疫细胞产生的,这些细胞可能会被破坏的肠道微生物组激活。
EED 动物模型表明,营养缺乏的小鼠与营养充足的小鼠相比,肠道菌群失调会导致小肠上皮内淋巴细胞数量增加和促炎细胞因子分泌增加。尽管空肠免疫激活增加,但营养缺乏的动物在肠道内抑制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能力较差,导致细菌传播到脾脏和肝脏,并导致肝脏分泌促炎介质。
▸ 儿童营养不良还与慢性全身炎症有关
尽管反复出现症状的感染可以引发全身炎症表型,但小鼠模型表明,在没有明显感染的情况下,肠道微生物群和/或其成分系统性扩散到功能失调的肠道屏障进入循环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如 EED 中观察到的那样。
与营养充足的幼鼠相比,断奶后采用缺乏蛋白质、铁、锌的饮食的健康小鼠出现了微生物群失调和体重减轻,这与向结肠给药时未能含有脂多糖有关;全身、盲肠和结肠(但不包括回肠)促炎细胞因子升高;在没有感染的情况下,LPS 攻击后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增多。
在该模型中,通过针对革兰氏阴性(LPS 阳性)而非革兰氏阳性(LPS 阴性)共生体的抗生素治疗,使体重增加和促炎性免疫反应的差异正常化。
该模型中抗生素治疗效果的选择性支持了对革兰氏阴性微生物群成分的播散性促炎性免疫反应的作用,这些微生物群成分从肠道转移到循环系统中,从而导致营养不良的体重和身高缺陷。
由微生物易位驱动的慢性全身炎症可能影响人体测量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抑制生长因子信号传导和骨/骨骼肌生长。来自动物研究的证据表明,依赖于微生物群代谢的唾液酸化HMO会增加成骨细胞驱动的骨形成,并且该过程是由 Th2 极化免疫反应介导的,即增加大肠中的嗜酸性粒细胞募集和嗜酸细胞趋化因子浓度。
中低收入国家儿科队列研究一致的证据表明,炎症介质也与IGF-1呈负相关。
注:前面讲过,营养良好和营养不良的儿童之间存在激素差异,尤其是与生长[生长激素 (GH) 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IGF-1)] 和食欲调节(瘦素和生长素释放肽)相关的激素差异。
包括 sCD14、补体蛋白 2、巨噬细胞炎症蛋白 1B 和 LBP 在内的炎症介质与SAM入院后康复儿童的体重和/或 MUAC 增加呈负相关。
▸ 炎症介质对生长的直接影响
无菌小鼠持续过度表达促炎细胞因子 IL-6 和循环 IGF-1 减少,生长速度较慢,并且比非无菌同窝小鼠小 30-50%,这种表型可以通过给予 IL-6 来部分挽救。
研究发现,IL-1β 和TNFα 与 IL-6 一起下调人肝细胞中生长激素受体 (GHR) 的表达、通过细胞因子信号传导抑制因子 3 (SOCS3) 产生的 GH 信号传导以及 IGF-1 的产生体外细胞系和小鼠肝脏体内细胞系。
▸ 微生物群:或将使炎症驱动的生长缺陷正常化
在一项以豆类为基础的治疗性营养的临床试验中,已经探索了将微生物群作为使炎症驱动的生长缺陷正常化的一种手段的潜力,该营养旨在增强营养不良的孟加拉国儿童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和成熟度。
与之前的观察结果一致,30 名 SAM 儿童在基线时可以通过血浆蛋白质组与 21 名健康儿童区分开来,该血浆蛋白质组与较低的骨化和成骨细胞分化以及较高的急性期炎症反应有关,包括 C 反应蛋白 (CRP)、IL- 6、促炎核因子 kappa B (NF-κB) 信号通路中的中间蛋白。干预后,尽管证据表明总体肠道病原体携带或绝对粪便微生物群多样性存在差异,但 WHZ 和微生物群成熟度有所增加;这些变化与血浆蛋白质组向健康生长和减少炎症特征的转变有关,表明肠道微生物组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可以减少营养不良相关的炎症。
菌群失调引起肠道和全身炎症的能力也可能取决于抗体介导的肠道微生物组成的控制。肠道中的分泌性免疫球蛋白,特别是免疫球蛋白 A (IgA),选择性地结合微生物组成分,从而调节微生物组组成。
扩展阅读:
▸ 发育不良:IgA靶向的细菌比例更高
研究发现,与来自马达加斯加和中非共和国的非发育迟缓对照儿童相比,发育不良儿童的粪便中 IgA 所靶向的细菌比例更高。除了 IgA 靶向肠道微生物群的数量差异外,IgA 还靶向健康儿童与 SAM 儿童不同的肠道微生物子集。其中 IgA 倾向于靶向SAM 儿童中的肠杆菌科细菌,同时针对健康儿童中更广泛的共生生物。
从患有 SAM 的儿童身上提取的IgA +微生物群在移植到小鼠体内时会诱发类似 EED 的病理学和全身炎症,这种效应依赖于营养不良的饮食。
在另一个模型中,给小鼠喂食低蛋白、低脂肪饮食,并进行或不进行细菌灌胃来模拟 EED,这些小鼠的 IgA 对乳杆菌属的靶向作用受损。尽管空肠中乳酸杆菌的相对丰度、粪便 IgA 总量以及 IgA 目标细菌总数的百分比与营养良好的对照组相似。
这些差异是由于乳杆菌碳水化合物代谢对饮食变化的适应,而不是 IgA 丰度或亲合力的差异。总的来说,这些观察结果强调了肠道屏障处免疫-微生物群相互作用的可塑性,有证据表明,微生物群和组织驻留免疫细胞的适应可能会损害 EED 中微生物及其抗原的免疫介导遏制,从而导致生长缓慢。
▸ 营养不良儿童的口服疫苗反应受损并反映营养不良中存在的一些免疫缺陷
小鼠模型为营养不良时微生物组失调如何损害口服疫苗的免疫原性提供了一些线索。然而,这些范式需要在人类队列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在针对产肠毒素大肠杆菌(ETEC)进行初免加强口服疫苗接种后,由于饮食缺乏和大肠杆菌粘附定植而诱导出现 EED 样表型的小鼠,其小肠中的疫苗特异性 CD4 + T 细胞较低,且疫苗水平较低-相对于饲喂营养充足饮食的小鼠和饲喂营养不足或充足饮食的未定植小鼠的特异性 IgA。这些差异取决于微生物群,因为 ETEC 定植小鼠的小肠疫苗特异性 T 细胞数量在广谱抗生素治疗 3 周后恢复正常。
EED 表型中疫苗反应受损是由于微生物群依赖性 RORγT + FOXP3 +Treg 的扩张,这些细胞能够抑制小肠中的疫苗反应;小肠中疫苗特异性 CD4 + T 细胞增殖和 IgA 丰度得到恢复,并且在有条件地消耗 Tregs 后体重增加百分比增加。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为微生物群靶向疗法如何恢复营养不良儿童受损的免疫表型(包括受损的疫苗反应)提供了概念证明,但也强调了固有的免疫和微生物异质性,在设计转化研究和人群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许多研究开始探索食物或食物成分对整个童年时期肠道微生物组的影响。
纳入的试验采用了涉及天然食品的干预措施;微量营养素补充或强化;食品成分,例如牛乳脂肪球膜(MFGM);以及特殊配方食品,例如早期限量配方食品(ELF)、即用治疗食品、即用补充食品(RUSF)和脂类营养补充剂(LNS)。
母乳
纯母乳喂养的婴儿往往含有较高比例的双歧杆菌和乳酸菌属。与配方奶喂养的婴儿相比,他们的肠道微生物组往往含有更高丰度的潜在致病菌,例如变形菌门成员。
双歧杆菌属丰度更高对婴儿健康有益,而肠球菌属的比例较高与不良的健康结果相关。
从瓶子中挤出的母乳,与潜在病原体的富集和双歧杆菌的消耗相关。
▸ 母乳是一种复杂的基质,有助于双歧杆菌定植
母乳含有许多成分,包括乳糖、400 多种不同的脂肪酸、蛋白质(乳清)、核苷酸、维生素、矿物质、乳脂肪球 (MFG) 、HMO等。
HMO 可以与牛奶中的其他化合物(例如糖复合物)结合,形成母乳聚糖 (HMG),其完整地到达婴儿结肠并驱动细菌定植,特别是双歧杆菌的定植。
HMG 逃脱肠道消化并转运到结肠,进入那里常驻双歧杆菌的发酵循环,使这些物种能够增殖并在 HMO 的双歧杆菌效应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婴儿双歧杆菌(ATCC 15697) 、短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和双歧双歧杆菌(PRL2010) 在婴儿期占主导地位,是更健康肠道微生物组的标志。
▸ 母乳本身也含有细菌
在几组哺乳期妇女中,发现母乳样本最常见有葡萄球菌、链球菌和假单胞菌,其他分类单元因女性和环境而异;这些细菌可能有助于在婴儿肠道中播种。
配方奶
▸ 配方奶与对肠道微生物群的潜在负面影响有关
a ) pH 值的变化,导致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等细菌过度生长,从而破坏肠道完整性,可能是由于蛋白质类型和含量的差异
b ) 牛乳中缺乏母乳中存在的游离氨基酸和某些生物活性化合物。
食用牛奶配方奶粉的婴儿往往具有较高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和丰富的厚壁菌门、梭状芽胞杆菌、肠球菌属、肠杆菌科和拟杆菌属和双歧杆菌属的丰度较低。
在配方奶喂养的婴儿中存在的双歧杆菌属中,有更多的青春双歧杆菌和假链状双歧杆菌,这两种细菌都与成人肠道微生物群有关。
▸ MFGM 对肠道菌群的影响:嗜血杆菌水平较低
MFGM (牛乳脂肪球膜)因其在婴儿肠道成熟、免疫以及大脑结构和功能中的潜在作用而受到关注。MFGM 源自乳腺上皮,包含 60% 蛋白质和 40% 脂质,使 MFG 稳定为乳液。为了复制母乳,婴儿配方奶粉中添加了牛 MFGM。
在 2 至 6 个月龄期间,MFGM 配方奶粉组的几种氨基酸及其分解产物的含量较低,乳酸和琥珀酸的含量也较低。12 个月时,MFGM 组的婴儿嗜血杆菌水平较低与接受标准配方奶粉的婴儿相比,该属含有多种病原体。
然而,与母乳喂养(非随机)参考组相比,MFGM 配方奶粉组的微生物群与标准配方奶粉组的微生物群更相似,因此,将 MFGM 和标准组的结果汇总进行分析,并与来自 MFGM 配方奶粉组的结果进行比较。
▸ ELF:改善健康的同时,尽量不破坏肠道菌群
母乳和婴儿配方奶粉中乳清蛋白和酪蛋白的含量各不相同。婴儿配方奶粉中牛奶的比例较高,较难消化。水解牛奶可以提高其消化率,水解牛奶用于早期限量配方食品(ELF),用于纯母乳喂养的新生儿作为干预措施,以增加肠内摄入量并避免并发症,例如胆红素血症或脱水。
与纯母乳喂养相比,ELF 不会导致α 多样性或群落结构出现显着差异,也不会导致乳杆菌丰度降低或更高丰度的梭状芽胞杆菌。这些发现表明,ELF 可能有助于改善体重大幅减轻的新生儿的健康,同时不会对肠道微生物群产生不利影响。
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包括简单的单糖和二糖以及复杂的寡糖和多糖,例如淀粉和纤维素。简单的糖在小肠 (SI) 中被消化和吸收,而复杂的或非血糖碳水化合物在到达结肠之前仍未被消化。
后者已被证明可以通过聚糖的降解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特别是以纤维和寡糖的形式。
关于单糖对肠道微生物群影响的研究有限,因为它们通常不会到达大肠;更常见的是针对人工甜味剂影响的研究或高糖、高脂肪的西方饮食的组合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
注:单糖,如葡萄糖、半乳糖和果糖;二糖,例如乳糖、蔗糖、麦芽糖和海藻糖;和糖醇(多元醇)
▸ 果糖
一项小鼠研究中,果糖可以逃避肠道吸收并到达结肠,从而降低多形拟杆菌的丰度。
在一项针对 12-19 岁青少年的队列研究中,高果糖摄入量与真杆菌和链球菌含量降低有关,而这些细菌被认为有利于碳水化合物代谢。这些研究的结果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在随机试验中检查单糖对人类肠道微生物组的影响是有益的,这些试验尚未在儿童中进行。
▸ 复杂碳水化合物
包括寡糖、多糖和膳食纤维,可以起到益生元的作用,被定义为“被宿主微生物选择性利用并赋予健康益处的底物”。这些分子不会被人类消化,而是被完整地运送到结肠,在那里微生物可能会代谢和发酵它们。
碳水化合物益生元包括HMO、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甘露低聚糖、低聚木糖和膳食纤维,例如不溶性纤维,包括纤维素和半纤维素,例如β-葡聚糖(来自燕麦)。碳水化合物益生元还包括可溶性纤维,例如果胶和菊粉,两者都是微生物发酵罐的底物,包括长双歧杆菌亚种、婴儿杆菌、拟杆菌、拟杆菌、乳杆菌和普氏粪杆菌。
▸ 益生元通过直接机制发挥作用
简而言之,结构与宿主聚糖相似的碳水化合物分子可以直接阻断与宿主细胞的粘附;β-葡聚糖可以与吞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上的受体结合,引发中性粒细胞的吞噬作用;
菊粉型果聚糖可以通过 Toll 样受体、C 型凝集素受体和半乳糖凝集素作为肠道树突状细胞的受体,诱导抗炎细胞因子。
▸ 益生元可以间接地选择有益共生细菌的增殖
其代谢副产物可以直接影响肠道环境或宿主基因表达。例如,与潜在致病性大肠杆菌和梭菌相比,双歧杆菌属、拟杆菌和厚壁菌门中的物种将到达结肠的未消化碳水化合物发酵成微生物副产物,宿主或其他共生细菌可以将其用作底物。
▸ 麸皮添加:微生物群的变化因基线饮食差异而异
麸皮(小麦、燕麦和大米等谷物的外皮)是益生元可溶性纤维以及其他营养素(如植物化学物质、脂肪酸和酚类物质)的主要来源。
在一项试验中,生活在尼加拉瓜 ( n = 47) 和马里 ( n = 48)的 6 个月大婴儿每天补充米糠(每天 1-5 克),添加到断奶食品中,或者不进行干预 6 个月。
不同国家的基线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通过非度量多维尺度(NMDS)绘制的布雷-柯蒂斯差异来测量)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 8 个月和 12 个月龄时微生物对米糠补充剂的反应越来越明显;例如,马里样本在两个时间点的群落结构差异(NMDS 图上的分离)更为明显。对米糠摄入量敏感的属也因国家而异:在尼加拉瓜,8 个月和 12 个月龄时,双歧杆菌属、乳杆菌和韦荣球菌的相对丰度增加,而在马里乳杆菌在 8 个月和 12 个月大时,对米糠的反应丰度有所增加。
这些反应性类群被公认为碳水化合物消化者。这项研究在比较这些人群时的一个局限性是,整个马里队列都是纯母乳喂养和阴道分娩,而尼加拉瓜样本包括配方奶喂养和大多数剖腹产婴儿;这些基线饮食差异可能导致了微生物对米糠的不同反应。
引入补充食品,包括低聚糖的植物性食物来源,例如大豆和其他豆类、水果和蔬菜,帮助婴儿肠道微生物群多样化并增加其丰富度,使其达到类似成人的组成。
▸ 蜂蜜:双歧双歧杆菌有变化
蜂蜜是单糖(即葡萄糖、果糖、蔗糖和麦芽糖)以及益生元低聚果糖的来源。
在早产儿肠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埃及早产儿 ( n = 40) 连续 14 天食用添加到牛奶配方奶粉中的 5、10、15 或 0 克医用级三叶草蜂蜜。从定量实时聚合酶链反应 (qRT-PCR) 结果来看,双歧双歧杆菌似乎以剂量依赖性方式对蜂蜜做出反应,而乳酸杆菌种不会。10g 组的计数最高,5g、15g 和 0g 组变化不大;这可能与这些细菌的底物代谢差异有关。
一些局限性包括样本量小(每组仅 10 名婴儿)、通过 qRT-PCR 定量特定细菌(相对于整个细菌群落的下一代测序)、干预持续时间短以及研究结果的适用性(考虑到不推荐蜂蜜)对于 12 个月以下的儿童,因为担心它可能含有导致婴儿肉毒杆菌中毒的细菌。
然而,作为一项试点研究,这些发现为进一步研究蜂蜜和单糖对老年人群肠道微生物组的潜在影响提供了支持。除了豆类外,没有其他试验研究过碳水化合物在天然食品中的作用,包括天然存在的益生元,对足月婴儿或年龄较大的儿童或青少年人群的作用。
脂 肪
脂肪酸,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 (MUFA)、多不饱和脂肪酸 (PUFA)(例如亚麻酸 ω-3 和亚油酸 ω-6 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 (SFA),构成脂质分子的一部分,例如甘油三酯、磷脂、胆固醇和植物甾醇。
膳食脂肪在整个胃肠道中被分解。大多数甘油三酯的消化和吸收发生在小肠(特别是十二指肠)中,并且依赖于胰脂肪酶、肝脏中的胆汁盐和胆囊中的胆汁。
初级胆汁盐,包括胆酸盐和鹅脱氧胆酸盐,是由胆固醇合成的;共生微生物群从初级胆汁盐合成次级胆汁盐、脱氧胆酸盐和石胆酸盐,这些盐进一步被细菌用作底物或被肝细胞修饰。大约 7% 的游离脂肪酸完好无损地到达结肠,它们可能会影响体内的微生物群。食物通常含有短链、中链和长链脂肪酸的混合物。
脂肪酸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机制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并且关于 SFA、MUFA 和 PUFA 对人类肠道微生物组的影响存在相互矛盾的证据。
▸ 促炎:饱和脂肪酸、ω-6 多不饱和脂肪酸; 抗炎:ω-6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
一些研究表明,SFAs 和 ω-6 PUFA 会促进炎症和氧化应激,而 ω-3 PUFA 和 MUFA 则具有积极作用,例如增加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属。由于膳食脂肪的代谢需要氧气,因此脂肪不太可能成为厌氧肠道细菌的能量来源。然而,较高的脂肪摄入量可能会取代饮食中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因此,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可能是由于饮食替代或较低的碳水化合物底物可用性,而不是较高的脂肪摄入量。膳食脂肪可能对细胞膜有杀菌作用,导致细菌丰度降低。此外,膳食脂肪可以诱导细菌增加胆汁酸代谢,以应对增加的脂肪。
一项研究旨在分析鱼和红花油的混合物对接受小肠肠造口术的早产儿(n = 16)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即在腹壁上开一个开口,以便在出生后进行肠内喂养)因炎症性疾病而需要进行腹部手术,例如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NEC),与标准护理相比这是早产儿的常见病症。
与标准营养疗法相比,干预措施持续 9 周,结果增加了微生物α 多样性,降低了潜在致病菌(肠杆菌科、梭状芽胞杆菌)的丰度,并丰富了碳水化合物代谢的预测基因功能。
总之,这些研究表明,ω-3 LCPUFA 干预可能会改善婴儿肠道微生物群多样性、组成和预测功能,特别是患 NEC 的早产儿,但母亲在怀孕期间摄入 LCPUFA 不会影响婴儿肠道微生物组。
蛋白质
膳食蛋白质由形成肽的氨基酸 (AA) 组成,肽是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氨基酸对于骨骼肌功能、生长、健康、发育和生存至关重要,可以为宿主和肠道微生物群提供能量,而肠道微生物群可以改变宿主对氨基酸的生物利用度。
膳食蛋白质的消化从胃开始,蛋白酶将蛋白质切割成大肽。小肠中的肽酶分解这些肽,以便随后由肠上皮细胞和腔细菌进行转运和分解代谢。
增加蛋白质摄入量通常会导致结肠消化率降低和可发酵底物增加。细菌将游离氨基酸转化为多肽有助于肠道中氨基酸的代谢和生物利用度,而 L-谷氨酰胺等氨基酸的可用性可以调节必需和非必需氨基酸的小肠细菌代谢。
结肠细菌,特别是拟杆菌、梭状芽胞杆菌和大肠菌,将摄入的蛋白质和来自宿主酶、粘蛋白和脱落的肠细胞的内源蛋白质转化,产生副产物,例如较短的肽、AA、脂肪酸(例如 SCFA)和气体例如氨和硫化氢。
整个肠道的蛋白水解活性各不相同:例如,体外实验发现,与回肠微生物群相比,结肠微生物群可以更有效地降解结肠中的牛血清白蛋白,具体取决于 pH 水平、碳水化合物可用性和肠道模型保留时间。
▸ 较高的蛋白质摄入量:促进潜在致病菌
较高的蛋白质摄入量(例如西方饮食中的蛋白质)被认为会增加 pH 值,从而减少双歧杆菌等严格厌氧菌的生长。并促进蛋白质发酵,潜在致病性兼性厌氧细菌。
这些细菌,例如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可以通过形成降解产物(例如三甲胺氧化物以及芳香族和支链氨基酸)来破坏肠道屏障和免疫系统;这些副产品与胰岛素抵抗和 2 型糖尿病有关。除了摄入水平之外,蛋白质来源、浓度和 AA 组成也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
▸ 蛋白质来源会导致微生物组成和功能的变化
由于植物细胞壁的原因,豆类等植物蛋白不能被宿主酶完全消化,导致它们作为微生物发酵的益生元运输到结肠。
难解析出植物蛋白来源中的蛋白质、纤维或其他化学物质的个体效应,但总的来说,这些蛋白质来源往往与细菌组成的有益变化有关,包括乳酸菌的生长和更大的微生物多样性。
进行了两项试验,利用 V4 区的 16S 测序来检查植物性蛋白质来源(包括豇豆、黄豌豆和普通豆)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
一项试验比较了烤豇豆粉(25% 蛋白质,21% 纤维)、烤普通豆粉(25% 蛋白质,28% 纤维)和挤压煮熟的玉米大豆混合 (CSB) 面粉(13% 蛋白质,8% 纤维) ,6 个月大的儿童每天服用 6 个月,豇豆导致双歧杆菌属的比例更高。
与普通豆和 CSB 相比, 9 至 12 个月期间普雷沃氏菌丰度较低,6 至 9 个月期间埃希氏菌/志贺氏菌丰度较低;这是出乎意料的,因为与普通豆相比,豇豆的纤维含量较低。
另一项针对儿童(6-10 岁)的研究检查了四种不同剂量的补充微量营养素的豆类蛋白质(黄豌豆)(即 6、8、10 或 12 克),连续 1 个月每天食用两次,在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中发现了 9 个有区别的类群,其中许多与植物多糖发酵和 SCFA 生产有关——对应于肠道微生物组的变化。
三个类群(普雷沃菌属、颤旋菌属、普氏镰刀菌)与儿童线性生长的增加显着相关,并且所有类群的相对丰度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最低蛋白质剂量组(6 g)和最高蛋白质剂量组(12 g)。这些结果强调了豆类对肠道微生物群的潜在剂量反应效应,并确定了与功能结果(例如儿童线性生长)相关的分类群以进一步研究。
与植物蛋白相比,动物来源的蛋白质在近端肠道更容易消化,因此运输到结肠的蛋白质较少,导致结肠微生物群调节减少,并可能抑制病原体。
维生素A
维生素A是一类具有全反式视黄醇生物活性的类视黄醇化合物,包括视黄醛(视黄醛)、视黄酸、视黄酯(主要是棕榈酸视黄酯)和类胡萝卜素化合物,如β-胡萝卜素、α-胡萝卜素和β-胡萝卜素。
▸ 维生素 A 的功能
维生素 A 对于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性和受损粘膜上皮的再生至关重要,特别是肠上皮细胞的正常增殖和产生粘液的杯状细胞分化,这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定植和粘附。
膳食维生素 A 可以作为植物来源的维生素 A 原(类胡萝卜素)或动物来源的预制维生素 A(视黄酯)形式食用。
▸ 维生素 A在体内的加工
消化从咀嚼开始,包括通过胆汁盐和胰脂肪酶的胃作用,胆汁盐和胰脂肪酶在肠腔中从膳食脂质形成混合胶束以供吸收。虽然预先形成的维生素 A 来源更容易被宿主肠细胞吸收以运输至储存或循环,但维生素 A 原类胡萝卜素必须进一步加工才能转化为类视黄醇并被宿主使用。
▸ β-胡萝卜素的吸收
根据食物基质的不同,大约 5-50% 的 β-胡萝卜素被吸收。例如,膳食脂质的存在会增加小肠中类胡萝卜素的吸收;如果β-胡萝卜素被纤维吸附,它可以绕过上肠的吸收并被转运到结肠。结肠微生物群可以消化纤维,释放β-胡萝卜素供结肠细胞吸收。在结肠粘膜中发现了类胡萝卜素,主要是在升结肠中。
一项研究发现,大肠杆菌表达一种与 β-胡萝卜素单加氧酶 1 同源的耐盐酶,使大肠杆菌能够积累 β-胡萝卜素;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这种β-胡萝卜素被裂解形成视网膜以供进一步使用。
▸ 维生素A与普通拟杆菌:此消彼长
在一项针对小鼠的研究中,普通拟杆菌(Bacteroides vulgatus)先前被证明是一种生长歧视类群,随维生素 A 补充而丰度降低,并因维生素 A 缺乏而丰度增加,可能与胆汁酸代谢的改变有关。作者报告说,这些变化是由于普通双歧杆菌视黄醇流出系统的破坏以及随后对视黄醇和胆汁辅助敏感性的影响造成的。
▸ 肠道共生菌与视黄酸代谢
另一项针对小鼠的研究发现,粘膜树突状细胞 (DC) 对肠道共生婴儿双歧杆菌进行摄取,导致其从维生素 A 向视黄酸的转化增加,并且具有更高数量的具有耐受性的粘膜 DC,例如抑制 1 型 T 辅助细胞(Th1) 和 Th17 细胞。这种效果也随着宿主视黄酸状态的不同而变化。然而,还需要对人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啮齿类动物的类胡萝卜素代谢效率比人类高得多,并且没有其他动物模型能够完全代表人类类胡萝卜素代谢。
最近的一项研究检查了补充维生素 A 对新生儿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结果发现对细菌组成(包括大双歧杆菌属)有积极的以及性别特异性的影响。
与安慰剂相比,入组时单剂量 50,000 国际单位剂量不会改变α-多样性,但在 6-15 周龄时对雄性产生双歧效应,但对雌性没有影响;作者推测,这可能有助于解释本研究中男性死亡率低于女性的原因。
维生素E
维生素 E 主要通过 α-生育酚活性发挥抗氧化剂的作用。
α-生育酚可来源于坚果、植物油、乳制品、奶酪和鸡蛋,也可以作为酯化 α-生育酚的补充剂形式食用。
作为自由基清除剂,α-生育酚可破坏细胞膜和血浆脂蛋白中的自由基链,以维持 LCPUFA 的完整性。维生素E与膳食脂质一起被吸收到肠道细胞中,融入乳糜微粒中,分泌到淋巴系统中,并转运到肝脏,然后被极低密度脂蛋白吸收并分泌到与α-生育酚转移蛋白结合的血液中; 然而,其吸收和贩运的许多细节基本上不为人所知。
经过额外的代谢步骤后,未结合的维生素 E 异构体通过粪便和尿液排出体外。维生素 E 与铁一起,与氧化电位降低有关;因此,维生素 E 被认为可以改善铁相关炎症的影响,改善肠道微生物群的结果。
一项针对美国缺铁 6 个月大婴儿的研究发现,每天两次服用 18 毫克维生素 E 和 15 毫克元素铁,持续 2 个月,并不会导致细菌多样性的变化,但确实会导致相对细菌多样性的变化出现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维生素 E 与铁的结合导致拟杆菌门(尤其是拟杆菌科)数量减少,而厚壁菌门(尤其是毛螺菌科)和罗氏菌属(Roseburia)数量增加。Roseburia产生丁酸盐,可以刺激结肠血流。
铁
铁是人体内最丰富的微量营养素,对于人体的氧运输、氧化还原反应、新陈代谢和电子传递链机制以及许多细菌的新陈代谢和毒力功能至关重要。
膳食血红素铁 (10%) 和非血红素铁 (90%) 的摄取和吸收存在不同的机制。牛肉是血红素铁的来源;美国的一项对测序研究使用牛肉作为干预措施。从 16S测序数据来看,以牛肉作为补充食品的群体中双歧杆菌属没有下降。与基线相比,4 周后细菌种类丰富度更高;4 个月后,放线菌和 XIVa 族梭菌(丁酸盐生产者)的丰度增加,并且与铁强化婴儿谷物相比,拟杆菌门较低。
差异可能是由于肉类中铁的生物利用度较高,以及未吸收的铁进入结肠,以及铁强化谷物类中存在植酸盐。
▸ 铁的生物利用度
铁的生物利用度随着植酸盐和多酚的存在而降低,而抗坏血酸(维生素 C)则提高铁的生物利用度。胃酸和蛋白水解可能会从食物基质中释放非血红素铁,需要更多的消化才能释放血红素和铁蛋白。一些细菌可以通过特殊机制获取食物中的铁源,例如解没食子链球菌或路邓葡萄球菌降解多酚单宁酸。
营养干预措施对肠道菌群影响的潜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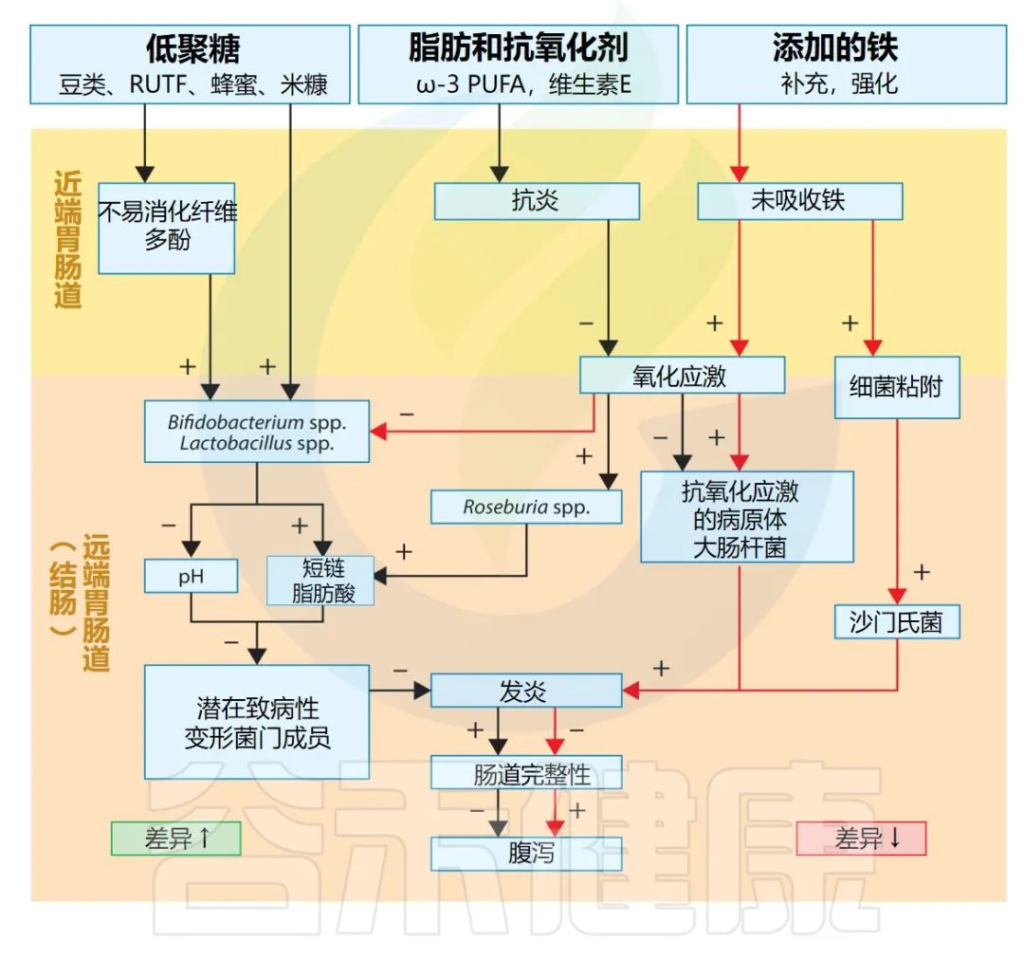
doi.org/10.1146/annurev-nutr-021020-025755
▸ 未吸收的铁被认为会刺激肠道中细菌病原体的生长和毒力
例如大肠杆菌,而宿主铁的状态会影响细菌免疫防御和宿主炎症反应,包括乳杆菌科和伯氏疏螺旋体在内的一些细菌不依赖铁生长,而是利用锰。
链球菌属可以使用铁或锰,具体取决于可用性。大肠杆菌使用 Feo 摄取系统来摄取二价铁,而三价铁在摄取之前首先被细胞外还原酶还原为二价铁,或者被摄取为柠檬酸铁或与细菌铁载体结合。
▸ 感染期间可用铁量的变化向毒力基因发送信号
低铁会导致铁载体抑制和毒素上调,而较高的铁可用性会诱导细菌粘附到肠上皮细胞,如肠沙门氏菌的情况鼠伤寒血清型。缺铁还会减少肠道细菌(包括Roseburia 、直肠真杆菌和梭状芽胞杆菌IV 族成员)等产生的短链脂肪酸。
在易缺铁的人群中,婴儿和幼儿最常需要口服铁剂治疗,例如补充剂,尽管他们的肠道微生物群仍在成熟。
▸ 铁干预措施对腹泻:负面影响
多项研究表明铁干预措施对腹泻等胃肠道症状有负面影响以及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例如较高的肠杆菌科和较低的乳杆菌科和双歧杆菌属。
▸ 铁补充剂,取决于基线铁或贫血状态
为了帮助抵消铁的这些影响,儿童随机试验检查了铁与维生素 E 等抗氧化剂结合使用的效果或冻干覆盆子作为抗氧化剂来源。例如,在加拿大一项研究中,与仅接受铁强化谷物的婴儿相比,接受含冻干覆盆子的电解铁强化米粉的婴儿在2 -4周后肠道微生物组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有所增加。
然而,接受冻干覆盆子的组活性氧并没有显着减少,与胃肠道中过量铁相关的炎症过程的引发剂;这可能是由于冻干覆盆子的消耗量很小,或者与新鲜覆盆子中的抗氧化剂含量相比可能较低,而新鲜覆盆子没有被任何群体食用。
在未来的研究中,考虑其他抗氧化剂来源(例如新鲜浆果或提取物)和不同剂量的这些抗氧化剂来源,以及对大量贫血婴儿的研究或铁充足,将有助于建立铁和抗氧化剂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
▸ 使用铁剂联合干预的随机试验
包括叶酸, 锌和多种微量营养素(MMN),无论是片剂的形式还是作为微量营养素粉(MNP)的一部分。铁的形式包括硫酸亚铁、富马酸亚铁、NaFeEDTA 和电解铁,它们可能对儿童肠道微生物群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他变量包括给药剂量、基线铁和贫血状况、抗氧化剂和其他微量营养素等辅助干预措施以及研究环境。
大多数检查 MNP 的研究都是在肯尼亚针对开始添加辅食的 6 个月大婴儿进行的;MNP 与玉米粥一起服用 3 至 4 个月。MNP 的微量营养素成分各不相同,但都含有维生素 A、叶酸和维生素 C,并且除了一种还含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铜、碘、硒和锌。
根据靶向 qRT-PCR 结果,MNP ( MixMe ) 加上 2.5 mg NaFeEDTA 4 个月,导致大肠杆菌/志贺氏菌丰度增加,以及肠杆菌科:双歧杆菌属比例增加。与单独使用相同MNP产生的丰度相比,10个月大时的比例增加。
在一项比较 MNP(Sprinkles)加 12.5 毫克富马酸亚铁与单独使用相同 MNP 的试验中,以及当含铁组组合并与仅使用 MNP 的组进行比较时,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果。
在另一项试验中,与单独使用相同的 MNP 相比,MNP 中的铁含量(2.5 mg NaFeEDTA 和 2.5 mg富马酸亚铁)对微生物组组成有显着影响,包括较低丰度的有益菌(如乳杆菌属和双歧杆菌属)以及较高比例的梭菌目,而拟杆菌门在各组之间保持相似。在一项辅助研究中,抗生素治疗并没有抵消铁的作用,铁仍然导致肠杆菌科细菌的增加。
最后,在另一项试验中,与单独的 MNP 相比,含铁的 MNP(12.5 毫克富马酸亚铁)在多样性或相对丰度方面没有组间差异。然而,接受含铁 MNP 的组梭状芽胞杆菌增加,双歧杆菌减少,而仅接受 MNP 的组大肠杆菌减少。
尽管 MNP 配方和 16S 测序区域存在差异,但这些研究一致发现铁会导致有益细菌减少和可能有害细菌增加,这为铁对肠道微生物组的影响提供了多种证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检查铁在其他环境中对肠道微生物组的影响。
▸ 铁强化和补充剂: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在科特迪瓦 6-14 岁儿童中(n = 60),铁强化饼干(20 毫克电解铁)不会导致微生物多样性发生变化,肠杆菌科细菌增加,乳杆菌属细菌减少,并且双歧杆菌属没有差异。6个月后这些发现与之前对婴儿进行的研究一致。
在南非进行的另一项针对 6-11 岁儿童的研究中,与安慰剂组(两组均服用维生素 C)相比,饮用含 50 毫克硫酸亚铁的饮料会导致组内相对含量存在差异;然而,尽管铁剂量较高,但没有发现组间差异。这些发现可能是由于肠道病原体负担和卫生设施的差异造成的,包括优质水和卫生设施、饮食质量和感染负担。
▸ 存在于全食物基质中的铁可能有利于铁的吸收
如LNS,不会产生与铁相关的负面影响,例如增加潜在致病菌、炎症和腹泻等胃肠道疾病症状。
LNS由植物油、花生、奶粉、糖、维生素和矿物质组成,食用量约为54g小袋,或在少量的情况下,食用量为20g(~6g脂肪),以帮助解决大量营养素和能量不足问题,并满足微量营养素需求。
已经进行了三项随机试验来检验直接给予婴儿 LNS 的影响或在怀孕期间给予母亲,然后给予婴儿。在同一队列的两项研究中,6 个月大的儿童接受基于牛奶蛋白的 LNS、基于大豆蛋白的 LNS、CSB 或 12 个月内不接受干预。通过 16S rRNA V4 区域测序评估肠道微生物群,双歧杆菌属的定植率或计数没有差异。与未接受营养补充剂的对照组相比,接受 LNS 和 CSB 补充剂的组中发现了金黄色葡萄球菌或其他肠道细菌。
在另一项试验中,将 SQ-LNS(20 克铁)给予孕妇(妊娠 <29 周),然后给予 6 至 18 个月大的婴儿;对照组包括给怀孕期间和哺乳期前 6 个月的母亲服用含有 20 毫克铁的 MMN,或者给怀孕期间的母亲服用标准护理铁和叶酸(含有 60 毫克铁)加上安慰剂哺乳期的前 6 个月。
12 个月时,与任一对照组相比,SQ-LNS 组的婴儿肠道微生物α 多样性和均匀度更高,而β 多样性没有差异或观察年龄微生物群 z 评分 (MAZ)。
然而,由于干预组之间干预的类型、数量、接受者和给药方案存在差异(只有 SQ-LNS 组中的婴儿接受直接补充),因此很难确定任何一种特定的营养素或干预类型可能会造成这些影响。总之,这些发现表明,怀孕和哺乳期间补充铁可能不会影响新生儿和婴儿的微生物组。
锌
微量矿物质锌在体内发挥催化、结构和调节作用,包括肠道健康和免疫健康,并已广泛用于治疗严重腹泻。
锌的吸收主要发生在人体的小肠中,受到食品中含锌物质是否存在以及食品加工方法的影响。例如,植物性锌来源(如种子、根和块茎)中的植酸盐会抑制锌的吸收,而铁等其他微量营养素会竞争性地抑制锌的吸收,而谷物的发酵可以提高锌的吸收。
此外,由于存在组氨酸等氨基酸增强锌的溶解度,动物源产品中的锌更容易被利用。过量的锌,包括未吸收的膳食锌和内源性锌,以受控机制通过粪便排出体外,以维持体内平衡。由于体内没有锌的储存,低锌饮食后可能会迅速出现锌缺乏症。
▸ 共生菌和病原菌在肠道中的定植和功能可能受到锌的调节
锌对于许多细菌(例如毒力因子)至关重要,并因其抗菌作用而用于动物生产。
在大肠杆菌中,锌受到严格调控,并在 300 多种蛋白质中发挥结构和催化作用,并且许多细菌拥有重金属外排系统或进行特定重金属质粒的基因转移。乳酸杆菌等细菌对膳食锌的抗性也不同。
关于锌和肠道微生物群的研究主要在动物模型中进行;这些研究的作者发现了细菌组成的差异,特别是乳杆菌属、梭菌属和肠杆菌科。
一项针对患有继发于肺炎的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 2-36 个月大儿童的研究,检查了锌补充剂与益生菌的作用,为期 14 天,与单独益生菌相比,双歧杆菌属的计数没有显着差异。与基线相比,每个干预组中大肠杆菌减少。
另一项针对 6 个月大儿童食用铁和锌强化或仅铁强化谷物的研究发现,锌可以抵消铁强化对肠道微生物群的潜在不利影响。
上面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组在生命早期生长中的作用,为儿童营养不良的营养和药物治疗提供了新的目标。
目前预防发育迟缓和消瘦的营养策略并不能完全解决短期和长期生长缺陷或相关的临床结果。6-24 个月龄小剂量脂质营养补充剂可将发育迟缓发生率降低12%,将严重发育迟缓发生率降低 17%。
使用即用型治疗食品 (RUTF) 对 SAM 进行社区管理可显着改善营养恢复;然而,复杂的 SAM 后仍然存在高死亡率和长期生长缺陷。
总的来说,目前的治疗方法通过抗生素解决感染负担,并通过单糖、脂质和微量营养素恢复宿主营养;然而,这些治疗方法并不专门针对肠道微生物组,而肠道微生物组可能有助于改善生长。
事实上,目前对复杂 SAM 的建议(包括在所有情况下进行抗生素治疗)可能会损害肠道微生物组的恢复。而越来越多的试验报告了针对微生物群的干预措施对儿童营养不良的临床有益效果。
益生菌
少数益生菌试验报告了在营养不良负担较高的环境中益生菌对儿童生长的不同影响。对 795 名 SAM 儿童进行的一项大型随机临床试验发现,尽管观察到门诊死亡率有降低的趋势,但多物种益生菌和益生元联合治疗对营养恢复、死亡率或相关临床症状没有影响。较小规模的试验表明,其他益生菌种类对 SAM 和其他形式的营养不良具有潜在益处。
长双歧杆菌亚种由于婴儿益生菌与资源匮乏环境中的生长呈正相关,因此它具有作为促进生长的潜在益生菌的巨大潜力。在孟加拉国开展的一项 SAM 儿童试验,在临床稳定和急性期管理后,将 62 名参与者随机分为婴儿双歧杆菌益生菌(婴儿双歧杆菌 EVC001)、益生菌和纯化 HMO(乳-N-新四糖)或安慰剂,为期4周在医院。
在开始治疗 8 周后的研究终点,益生菌组的年龄别体重 Z 评分 (WAZ) 和 MUAC 显着更高。鼠李糖乳杆菌GG (LGG) 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组合的试验。SAM 治疗期间的乳酸菌和 LGG 也证明了感染发生率和门诊腹泻减少的证据。
由于患有复杂 SAM 的儿童的临床不稳定和高死亡率,特定益生菌用作 SAM 标准治疗的潜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本、可持续性和安全性。
此外,需要合理选择益生菌,以确定那些能够适当定植于营养不良儿童受损肠道的益生菌,并针对可以改善生长恢复的特定途径。
来自动物研究的进一步数据可能有助于为未来合适益生菌的临床试验提供信息,例如针对内分泌生长途径的益生菌。
即食治疗性食品(RUTF)
针对肠道微生物群的改良营养疗法有潜力成为儿童营养不良的可持续且经济有效的疗法。SAM 的证据表明,RUTF 喂养后微生物组成熟度的恢复是短暂的,并且往往在治疗后 3-4 个月恢复到不成熟状态。
因此,针对 SAM 恢复中肠道微生物组和预防发育迟缓的改良补充食品可能有助于促进生长。
一项试点试验评估了在 SAM 治疗期间向 F75 和 F100 治疗奶中添加可微生物发酵的碳水化合物菊粉或豇豆粉,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对营养恢复没有改善作用;然而,补充营养可以防止住院治疗期间物种多样性的暂时丧失,这部分是由抗生素治疗引起的。
豇豆辅助喂养可以显着减少有发育迟缓风险的儿童的一些 LAZ 缺陷;然而,它仅引起肠道微生物组组成的适度变化,包括双歧杆菌增加和大肠杆菌/志贺氏菌减少,表明对生长的有益影响可能与肠道微生物组无关。
来自孟加拉国的一个队列的研究,与标准 RUTF 疗法相比,微生物群导向的补充食品 (MDCF) 对 MAM 恢复儿童生长的影响显着增强。通过合理设计由当地可用的、文化上可接受的食物组成的补充食品组合 (MDCF-2),该组合可促进人源化动物模型中早期生命肠道微生物组的成熟。
这些有希望的数据表明,与目前的疗法相比,针对微生物群的补充食品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儿童营养不良后的生长恢复。从长远来看,这些小但显着更大的生长改善是否与持续的生长改善、认知益处或感染和慢性病风险的降低相对应,目前尚不清楚。
来自高收入环境的临床试验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针对微生物群的治疗在各种感染、胃肠道和代谢疾病中的功效。
由于世界上超过五分之一的儿童发育迟缓或消瘦,旨在进一步表征导致儿童营养不良的微生物介导的病理生理途径的研究对于为更好的治疗提供信息至关重要。
儿童营养不良涉及许多生理系统的紊乱,包括代谢、免疫和内分泌系统,其中许多系统与肠道微生物组密切相关,因此可能适合针对微生物组的干预措施。
未来潜在的微生物组靶向疗法将补充针对宿主营养需求和感染负担的现有疗法。此外,必须根据国家或地区的具体要求调整这些干预措施,以制定具有成本效益且本国或本地区上可接受的可持续干预措施。
Tips
在这篇文章中综合了营养干预试验的现有证据,这些试验测试了多种饮食干预措施对婴儿和儿童微生物组相关结果的影响,并讨论了来自实验室和动物研究的支持证据,以及来自人类研究的观察数据,旨在指导未来的研究并增强可解释性,为饮食相关政策提供信息。
可比性较差,因为纳入的研究在干预类型和持续时间上有所不同,是在有或没有既往疾病的不同儿科人群中进行的,并且是在可能影响基线微生物组成的各种环境中进行的。
虽然调查婴儿微生物群的研究发现,母亲在怀孕期间的饮食变化几乎没有影响儿童肠道微生物群。但是通过单独检查研究而不是包括整个全球背景,很难将研究偏差与真实的生物现象分开。可以使用 Qiita 等工具尝试进行此类分析,前提是研究数据与符合标准的样本元数据是公开的,以促进未来分析中的跨研究可比性。
在进行 16S rRNA 测序的 19 项研究中,只有两项对 16S V4 区域进行测序的试验可用于 Qiita 的进一步分析。作者将这两个试验人群的肠道微生物群与 2012 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微生物组队列研究的亚组进行了比较。
在 2012 年的研究中发现,马拉维出生的婴儿和美国出生的婴儿之间存在显着的微生物分离,但在纳入最近的两项试验时,缺乏数据来深入研究营养干预措施的效果与2012年的研究对比。
尽管微生物组生物信息学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且研究的人群类型和健康状况的广度不断扩大,但在营养和肠道微生物组领域,特别是儿童,仍需要解决许多研究空白和问题。
为了解决基于发现的差距,未来的研究人员将需要:
a)识别饮食细分成分响应微生物群并确定它们是否影响宿主的生理结果;
b)与最适合现实世界应用的特定膳食成分相比,了解全食干预措施的作用;
c)提高复制性和再现性,例如在不同人群中使用相同的饮食干预措施,以及在同一人群中测试不同的饮食干预措施;
d)确定食品加工和准备的作用,了解熟食或生食如何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烹饪的影响最近已被研究,但仍是一个研究不足的领域);
e)考虑到依从性的差异,设计和使用饮食干预措施,这需要大量的队列和长时间的随访;
f)将研究结果和序列数据整合到一个数据库中,用于对类似处理的序列进行汇总分析并了解全局现象,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偏差。
介入/治疗差距
未来的研究应解决以下五个介入和治疗差距。
首先,需要解决稳定性和可塑性问题。虽然短期饮食变化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群,但长期饮食模式与更稳定的微生物群构象相关,并且很难改变。仍有待确定的是哪种饮食模式具有最大或最小的可塑性,以及这种可塑性是否也取决于基线微生物种群和过去的饮食模式。
第二个差距是干预研究中针对不同人群的营养素和食物研究不足。尽管本次综述确定了几项微量营养素粉 (MNP) 试验,而关于补充个别维生素、矿物质和天然食品的试验相对较少,但仍然需要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重复研究中对 MNP 进行调查。
第三,应进行纵向、长期的人体研究。需要对 2-18 岁婴儿、青春期、成年早期和晚年等人群进行长期喂养研究,以了解衰老微生物群的动态。
第四,解决精准营养健康问题。
第五,未来健康建议应考虑大局。建议食物和饮食(生活方式)改变需要全面的方法和来自营养师和营养科学家、心理学家、医生和生物统计学家的多方面团队的支持。
小编寄语
中国在医疗和队列研究方面的发展仍有待提升。正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目前还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队列研究,尤其是能够改变临床指南的里程碑试验”。
举例来说,美国的弗明汉心脏研究和英国的UK Biobank人群队列都对临床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弗明汉心脏研究自1948年开始,最初只有5200名参与者,但经过70年的发展,参与者数量增加到15000人,产生了3698篇文章。这项研究改变了几乎所有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危险因素的认知。
另外,英国的UK Biobank人群队列从2006年开始策划,至今已发表超过3000篇文章。该队列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逾越的临床队列研究之一。
因此,谷禾也愿意和期待与各大医疗机构合作构建大型研究队列,尤其是关于青少年儿童的。通过对这些队列进行全面多组学以及生活营养指标的调查分析,将为我国医疗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和突破,为改善人们的健康水平做出重要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Jones HJ, Bourke CD, Swann JR, Robertson RC. Malnourished Microbes: Host-Microbiome Interactions in Child Undernutrition. Annu Rev Nutr. 2023 Aug 21;43:327-353.
Acosta A, De Burga R, Chavez C, Flores J, Olortegui M, et al. 2017.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and illness, enteropathogens and dietary intakes in the first 2 years of life: findings from the MAL-ED birth cohort study. BMJ Glob. Health 2(4):e000370
Alves da Silva AV, de Castro Oliveira SB, Di Rienzi SC, Brown-Steinke K, Dehan LM, et al. 2019. Murine methyl donor deficiency impairs early growth in association with dysmorphic small intestinal crypts and reduced gut microbial community diversity. Curr. Dev. Nutr. 3(1):nzy070
Mehta S, Huey SL, McDonald D, Knight R, Finkelstein JL.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s and the Gut Microbiome in Children. Annu Rev Nutr. 2021 Oct 11;41:479-510.
Amadi B, Fagbemi AO, Kelly P, Mwiya M, Torrente F, et al. 2009. Reduced production of sulfated glycosaminoglycans occurs in Zambian children with kwashiorkor but not marasmus. Am. J. Clin. Nutr. 89(2):592–600
Amadi B, Zyambo K, Chandwe K, Besa E, Mulenga C, et al. 2021. Adaptation of the small intestine to microbial enteropathogens in Zambian children with stunting. Nat. Microbiol. 6(4):445–54
Ansaldo E, Farley TK, Belkaid Y. 2021. Control of immunity by the microbiota. Annu. Rev. Immunol. 39:449–79
Attia S, Versloot CJ, Voskuijl W, van Vliet SJ, Di Giovanni V, et al. 2016. Mortality in children with complicated severe acute malnutrition is related to intestinal and systemic inflammation: an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 Am. J. Clin. Nutr. 104:1441–49
Barratt MJ, Nuzhat S, Ahsan K, Frese SA, Arzamasov AA, et al. 2022. Bifidobacterium infantis treatment promotes weight gain in Bangladeshi infants with severe acute malnutrition. Sci. Transl. Med. 14(640):eabk1107
Bartelt LA, Bolick DT, Mayneris-Perxachs J, Kolling GL, Medlock GL, et al. 2017. Cross-modulation of pathogen-specific pathways enhances malnutrition during enteric co-infection with Giardia lamblia and enteroaggregative Escherichia coli. PLOS Pathog. 13(7):e1006471
Bartz S, Mody A, Hornik C, Bain J, Muehlbauer M, et al. 2014. Severe acute malnutrition in childhood: hormonal and metabolic status at presentation, response to treatment, and predictors of mortality.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99(6):2128–37
Bhattacharjee A, Burr AHP, Overacre-Delgoffe AE, Tometich JT, Yang D, et al. 2021. Environmental enteric dysfunction induces regulatory T cells that inhibit local CD4+ T cell responses and impair oral vaccine efficacy. Immunity 54(8):1745–57.e7
Black RE, Victora CG, Walker SP, Bhutta ZA, Christian P, et al. 2013. Maternal and child undernutrition and overweight in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Lancet 382(9890):427–51
Bourdon C, Lelijveld N, Thompson D, Dalvi PS, Gonzales GB, et al. 2019. Metabolomics in plasma of Malawian children 7 years after surviving severe acute malnutrition: “ChroSAM” a cohort study. EBioMedicine 45:464–72
Aakko J, Grzeskowiak L, Asukas T, Paivansade E, Lehto KM, et al. 2017. Lipid-based nutrient supplements do not affect gut Bifidobacterium microbiota in Malawian infants: a randomized trial. J. Pediatr. Gastroenterol. Nutr. 64:610–15
Aly H, Said RN, Wali IE, Elwakkad A, Soliman Y, et al. 2017. Medically graded honey supplementation formula to preterm infants as a prebiotic: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Pediatr. Gastroenterol. Nutr. 64:966–70
Amarri S, Benatti F, Callegari ML, Shahkhalili Y, Chauffard F, et al. 2006. Changes of gut microbiota and immune markers during the complementary feeding period in healthy breast-fed infants. J. Pediatr. Gastroenterol. Nutr. 42:488–95
Andrews SC, Robinson AK, Rodriguez-Quinones F. 2003. Bacterial iron homeostasis. FEMS Microbiol. Rev. 27:215–37
Arimond M, Zeilani M, Jungjohann S, Brown KH, Ashorn P, et al. 2015. Considerations in developing lipid-based nutrient supplements for prevention of undernutrition: experie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Lipid-Based Nutrient Supplements (iLiNS) Project. Matern. Child Nutr. 11:31–61
Arrieta MC, Stiemsma LT, Amenyogbe N, Brown EM, Finlay B. 2014. The intestinal microbiome in early life: health and disease. Front. Immunol. 5:427
Black RE, Victora CG, Walker SP, Bhutta ZA, Christian P, de Onis M, Ezzati M, Grantham-McGregor S, Katz J, Martorell R, Uauy R; Maternal and Child Nutrition Study Group. Maternal and child undernutrition and overweight in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Lancet. 2013 Aug 3;382(9890):427-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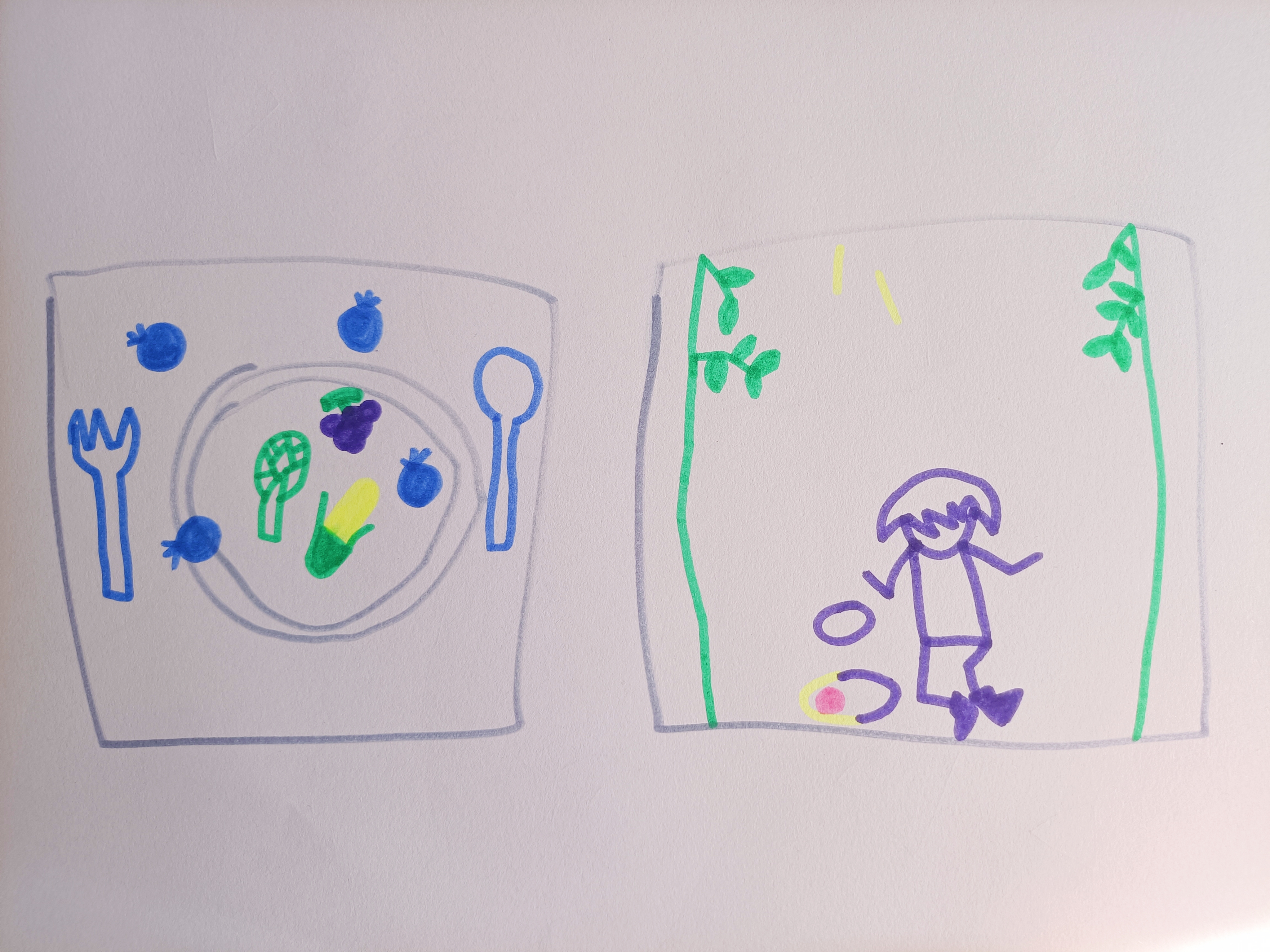
谷禾健康
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很多人的一种常态,因此导致2型糖尿病 、肥胖、心血管疾病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上升。
★ 代谢性疾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库,2019年,代谢风险(即高体重指数 (BMI)、高血糖、高血压和高胆固醇)占全球总健康损失的近 20%。调查发现,2019年,高血压导致了近五分之一的死亡(近1100万人),其次是高血糖(650万人死亡)、高BMI(500万人)和高胆固醇(440万人)。
这些疾病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巨大影响,不过定期和适当水平的体育锻炼可以起到预防作用。
最新的研究发现,运动与饮食结合:通过肠道微生物群的相互作用能够更好地预防和调节代谢性疾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定期进行体育锻炼和饮食干预可以将妊娠糖尿病的患病率降低30%,将死亡风险降低20%至30%。
•运动与肠道微生物
肠道微生物在宿主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参与影响健康的各种相互作用。
运动促进的微生物群结构和状态的变化在促进有益代谢物的产生、刺激/调节免疫系统、保护宿主免受病原体定植以及控制脂质积累和胰岛素信号。
规律的运动是对肠道的刺激性应激源,可促进有益反应并改善肠道屏障的完整性。
•饮食与肠道微生物
饮食对于塑造微生物群落或代谢物很重要。
微生物群暴露于健康的膳食成分,如膳食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多酚,它们可以产生有益的代谢物,特别是短链脂肪酸和色氨酸代谢物。
这些代谢物参与维持肠粘膜完整性,还介导宿主免疫和稳态反应。相反,不健康的饮食,如高脂饮食,会增加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从而导致全身慢性炎症和脂多糖易位,从而增加代谢疾病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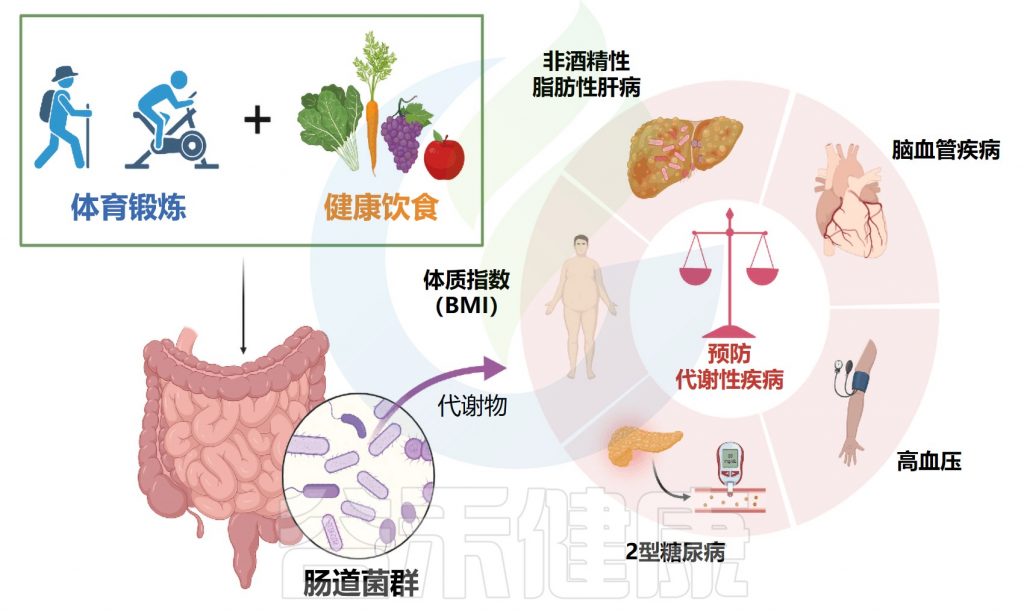

本文讲述了肠道微生物与代谢性疾病的关联,主要包括肥胖、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非酒精性脂肪肝。
我们还提到了体育锻炼、饮食成分和饮食模式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并介绍了通过体育锻炼和饮食相结合来预防代谢性疾病的一些研究和相关机制,这可能为预防代谢性疾病提供一条新途径。
▸ 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被定义为有计划、结构化和重复的体育活动的一个子集,旨在改善或保持身体健康。
注意:定期锻炼是指每周5天,每次至少30分钟的中等强度体育锻炼,或每周3天,至少20分钟的高强度体育锻炼。
★运动与炎症及代谢疾病有关
研究表明,习惯性运动会抑制基础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但过度运动会引发多种促炎介质的产生。合理和适度的体育锻炼可以减少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增加体育锻炼相关并发症的风险。
事实上,定期运动会独立影响肠道功能和微生物组特征,进而对预防代谢疾病具有有益作用。
体育锻炼对肠道菌群和宿主健康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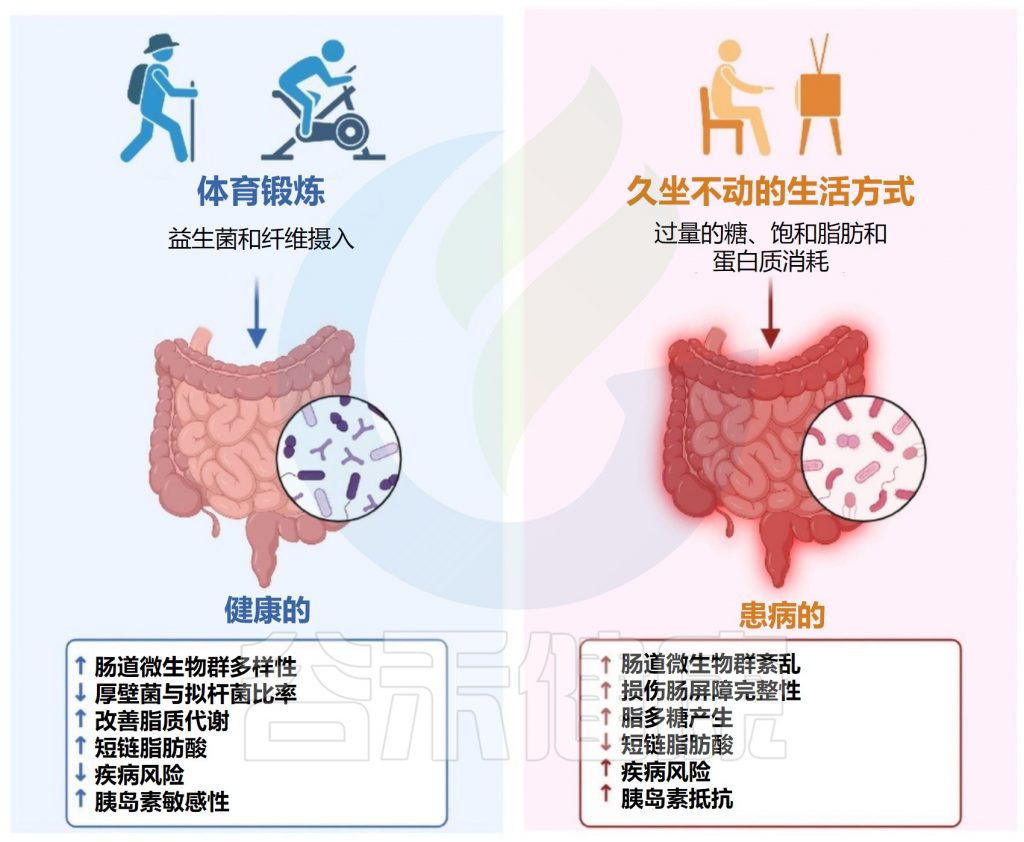

编辑
Zhang L,et al.Nutrients.2022
肠道菌群受性别、遗传、年龄和种族(即不可改变的因素)和可改变的因素(如宿主健康、身体活动、饮食和最终的抗生素治疗)的调节。研究表明,运动对微生物群有独特的影响。
体育锻炼与肠道菌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调节有关;体育锻炼在塑造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和调节其分布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证明。如下表所示:
运动对微生物群与代谢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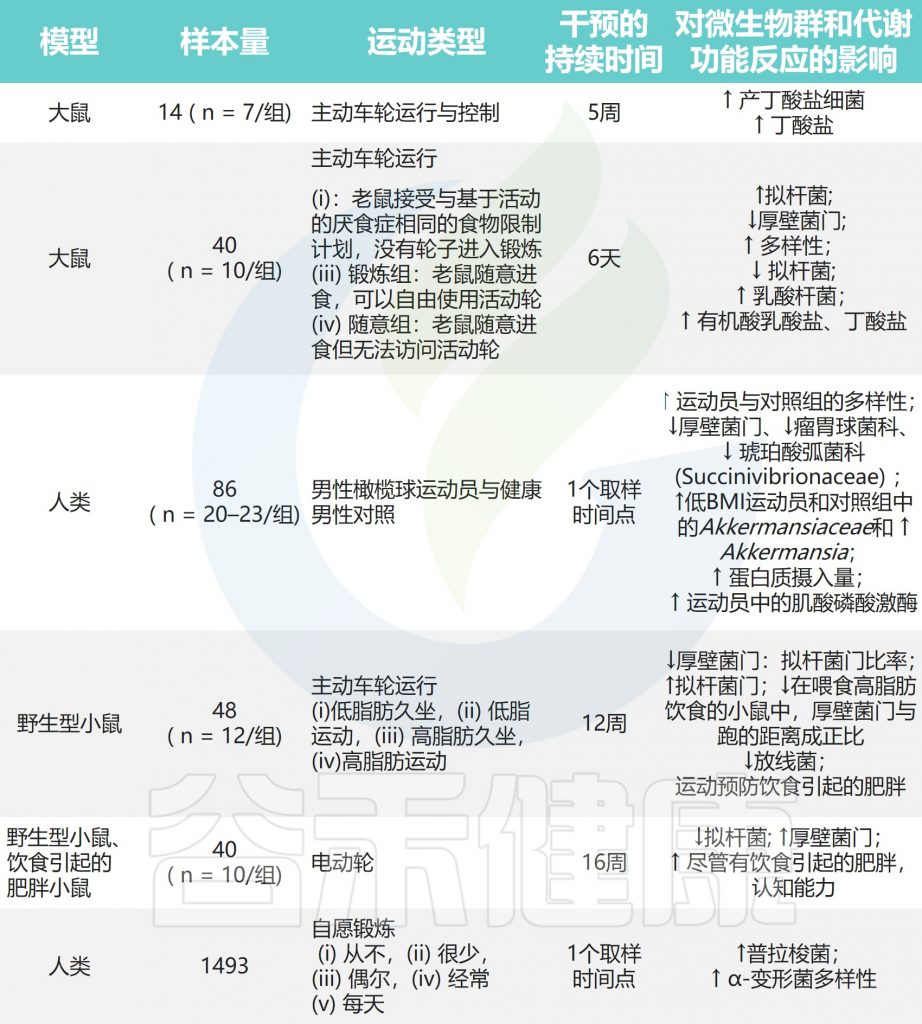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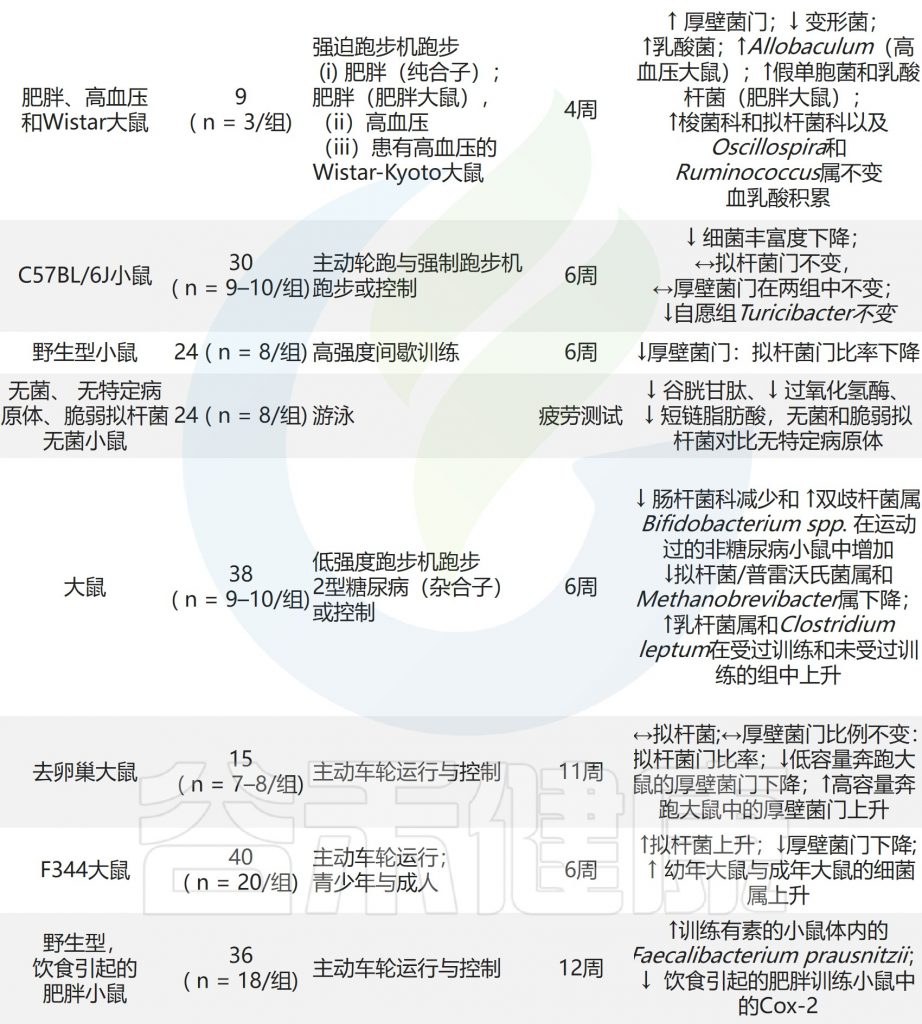






Donati Zeppa S,et al.Nutrients.2019
•改变原因
体育锻炼引起的肠道菌群改变是由于肠道转运时间 、胆汁酸谱的改变、通过AMPK激活产生短链脂肪酸 、Toll样受体 (TLRs) 信号通路、免疫球蛋白 A (IgA)、B和CD4+T细胞的数量,最后到体重减轻。
AMPK即AMP依赖的蛋白激酶,是生物能量代谢调节的关键分子。它表达于各种代谢相关的器官中,能被机体各种刺激激活,包括细胞压力、运动和很多激素及能影响细胞代谢的物质。
•体重与菌群变化显著相关
在一项分析运动活跃和久坐的40岁以下女性的研究中,几种细菌类群的变化与体重指数 (BMI) 显著相关。即使所有参与者的微生物群组成在运动后的一段时间内发生变化,具有已知抗炎特性和产生短链脂肪酸能力的物种在瘦受试者中更高。
✦运动促进新陈代谢
在运动条件下,肠道微生物的变化会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进而影响宿主的新陈代谢。来自美国肠道计划的数据表明,进行适度运动(从不运动到每天运动)重塑了微生物组成和功能的变化,促进了老年人尤其是超重老年人更健康的肠道环境。
在动物身上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进行体育锻炼的小鼠通常表现出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乳酸杆菌和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丰度增加。
这些结果可能反映了运动更高的新陈代谢,因为阿克曼菌比例增加通常与更健康的新陈代谢特征相关。
✦对肠道屏障、免疫系统有积极作用
此外,运动可能会对肠道粘液层产生积极影响,肠道粘液层是粘膜相关细菌(如嗜粘蛋白-阿克曼氏菌)的重要基质。适度运动还可以减轻慢性应激诱导的小鼠肠道屏障损伤,减少细菌移位并维持肠道通透性。
罗氏菌属(R.hominis)和普拉梭菌(F.prausnitzii)产生的丁酸盐对健康有益,对肠道功能和脂质代谢有积极影响。普拉梭菌还产生具有抗炎作用的代谢物。
粪球菌属(Coprococcus)属是一种产丁酸盐的属,在经常运动的女性中更为丰富,促进了一些与运动相关的健康影响。
•瘦的人群产丁酸盐菌群丰度较高
在另一项比较瘦和肥胖成年人在饮食控制下参加为期六周的监督耐力运动计划的研究中,仅在瘦受试者中发现产生丁酸盐的分类群增加。
此外,瘦成人的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增加,而肥胖成人则减少,而拟杆菌属(Bacteroides)有相反的趋势,证实了体重的影响。
注意:在体重、饮食和年龄正常化后,有氧适能水平较高的个体中产丁酸盐类群的丰度更高。
研究表明,这些微生物是已知的丁酸盐生产者,对促进肠道屏障完整性、调节宿主免疫系统和脂质代谢具有有益作用。
✦肠道微生物影响运动表现
在运动期间和之后,大量的乳酸会释放到血液中。乳酸在耐力表现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被用作多种器官和组织的燃料。这些器官和组织“学习”使用乳酸作为底物的次数越多,性能提高的越多。
最近证明,全身性乳酸可以穿过肠道屏障进入肠腔,然后可以被韦荣氏球菌属(Veillonella)转化为丙酸。
有报道说,肠道微生物群中的韦荣球菌丰度增加,其甲基丙二酰辅酶A在运动后过度表达。
•提高抗氧化活性
此外,他们证明在老鼠身上,韦荣氏球菌属(Veillonella)接种改善了跑步性能,通过结肠内输注给予丙酸盐也改善了这种性能。
在一项关于小鼠耐力游泳时间的研究中,证明了肠道微生物群的表现和抗氧化活性之间的关系,表明“肠道微生物群的状态可能对运动表现及其与运动员抗氧化酶系统相关的潜在作用至关重要”。
因此,这些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对短链脂肪酸产生的调节会影响运动过程中的能量代谢,从而有助于运动诱导的适应。这些微生物群发酵产物也可用作肝脏和肌肉细胞的能量来源,通过长期维持血糖来提高耐力表现。
✦运动频率不同体内菌群不同
已发现运动员微生物组包含不同的微生物组成,这些微生物主要由韦荣氏球菌(Veillonella)、拟杆菌属(Bacteroides)、普雷沃氏菌属(Prevotella)、甲烷杆菌(Methanobacteriaceae)和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所组成。
参与能量和碳水化合物代谢的分类群的丰度,如普雷沃氏菌和史密森甲烷杆菌,被发现在职业自行车手中明显高于业余自行车手,并且与训练频率相关。
在超重的成年人中,遵循富含纤维和全谷物的饮食六周后,普雷沃氏菌的丰度可预测体重减轻,这表明应在个性化营养策略中考虑肠型以对抗肥胖。短链脂肪酸的产生,尤其是丁酸,是肠道健康的重要标志,在人类运动后会增加。
✦经常运动肠道菌群多样有助于促进健康
职业橄榄球运动员的肠道微生物表现出更大的α多样性和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比率的下降. 与久坐不动的女性相比,进行常规运动量的女性显示出更多的促进健康的分类群,例如
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罗氏菌属(Roseburia hominis)↑↑↑
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 ↑↑↑
这些物种与促进健康的作用有关。先前已在运动员的微生物群中描述了高丰度的阿克曼菌,而低水平与炎症性肠病患者的代谢紊乱(肥胖、代谢综合征和 II 型糖尿病)有关。
•增加有益菌丰度预防疾病
检查了20名业余跑步者在半程马拉松比赛前后的粪便代谢物和微生物群。
根据α多样性分析,多样性几乎没有差异,但是,某些微生物群成员的丰度在跑步前后显示出差异。在门水平上,跑步后检测到在人体肠道中的功能未知的Lentisphaerae和Acidobacteria。
在物种水平上,Coriobacteriaceae和Succinivibrionaceae显著增加。
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参与胆汁盐和类固醇激素的代谢以及人体肠道中膳食多酚的激活。Coriobacteriaceae与15种代谢物呈正相关,表明Coriobacteriaceae的代谢可能是运动预防疾病和改善健康结果的潜在机制。
这些增加的代谢物表明,跑步促进了微生物群衍生的新陈代谢。
•减少致病菌,具有抗炎作用
在属水平上,半程马拉松跑减少了粪便中Ezakiella、Romboutsia和放线杆菌(Actinobacillus)的丰度,但增加了粪球菌(Coprococcus)和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放线杆菌属会导致几种不同的动物疾病,例如牛的放线菌病、新生马驹的烈性败血症和人类牙周病。
因此,对这种潜在病原体的抑制表明运动具有抗炎作用。还需注意,戊糖磷酸途径是一种与糖酵解平行并涉及葡萄糖氧化的代谢途径,是半程马拉松跑后最丰富的途径。这些发现强调了运动促进健康益处的微生物群衍生机制。
✦不同运动类型菌群组成不同
为了研究特定运动类型和运动员饮食对肠道微生物群的长期影响。比较了15名久坐不动的健康男性(作为对照组)、15名健美运动员和15名长跑运动员的粪便微生物群特征、膳食摄入量和身体成分。
运动类型与运动员饮食模式相关(即,健美运动员:高蛋白、高脂肪和低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饮食;长跑运动员:低碳水化合物和低膳食纤维饮食)。
虽然运动员类型在肠道微生物群α和β多样性方面没有差异,但它与几种细菌的相对丰度显著相关。例如,在属水平上,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萨特氏菌(Sutterella)、Clostridium、嗜血杆菌、艾森氏菌属最高,而双歧杆菌和副双歧杆菌在健美运动员中最低。
在物种水平上,广泛用作益生菌的肠道有益菌(青春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清酒乳杆菌)和产生短链脂肪酸的有益菌(经黏液真杆菌属、霍氏真杆菌(Eubacterium hallii))在健美运动员中最低,在对照组中最高。
在长跑运动员中,蛋白质摄入量与多样性呈负相关,而在健美运动员中,脂肪摄入量与双歧杆菌呈负相关。这些差异可能与运动中的的营养状况有关。
✦不同生理状态下运动效果不同
此外,体育锻炼所产生的变化似乎取决于个人的生理状态。例如,无论是肥胖-高血压大鼠还是正常大鼠,规律的强迫运动都会对微生物群丰富度产生不同的影响。高脂肪饮食后运动对大鼠微生物群的改变与正常饮食的大鼠不同,糖尿病小鼠产生的改变也不同于对照小鼠。
•幼年运动对微生物群影响更显著
最后,据观察,与成年大鼠相比,运动对幼年大鼠的微生物群产生更有效的改变。在这些研究运动训练对肠道微生物组影响的小鼠研究中,一个共同发现是α多样性增加。使用基于小鼠的模型的其他几项研究也表明,与久坐不动的动物相比,运动的动物的α多样性增加。
高强度运动对肠道微生物不利
需要注意的是,高强度运动可能会对肠道功能产生有害影响。总共70%的运动员在剧烈运动后可能会出现腹痛、恶心和腹泻。
长时间运动还会导致微生物多样性减少,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数量增加。过度运动会诱发增加肠道通透性的压力,这可能导致细菌及其有毒产物(包括微生物群衍生的脂多糖)进入血液并激活全身炎症。易位的脂多糖激活 TLR,促进NF-kB通路激活和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最终导致内毒素血症。
运动强度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各种运动形式,以及运动的持续时间。同时,要针对不同人群制定不同的干预方案;目的在于激励久坐不动的人摆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小结
运动会改变参与代谢模式的分子的转换,并刺激神经内分泌激素的释放,这些激素直接或通过免疫系统间接与肠道相互作用。
总之,运动的强度、时间和类型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因为它还与受试者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和训练状态有关。已经证明,低水平但持续进行的身体活动可以增加微生物群的多样性,改善受试者的代谢特征和免疫反应,而急性剧烈运动可能会对运动员的微生物群及其总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
碳水化合物是由碳、氢和氧三种元素组成,自然界存在最多、具有广谱化学结构和生物功能的有机化合物。
不同种类的水果、蔬菜和全麦谷物是膳食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基因组中,只有不到20种糖苷酶被鉴定为参与消化膳食碳水化合物的酶。
唾液淀粉酶首先在口腔内将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分解为单糖,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可通过胰淀粉酶、蔗糖酶、麦芽糖酶、半乳糖酶和乳糖酶等降解消化。复杂的不易消化的膳食碳水化合物驱使我们的肠道微生物进化出碳水化合物活性酶库,以便有效地竞争营养。
✦不同的碳水化合物对肠道影响不同
宿主的肠道不断被动态排列的碳水化合物淹没。而不同的碳水化合物对肠道的影响各不相同。
•简单的碳水化合物导致宿主代谢紊乱
已经注意到,简单的碳水化合物(例如蔗糖、果糖)会引起微生物群快速重塑,从而导致宿主代谢紊乱。
✦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对健康有利
复杂的碳水化合物,特别是某些微生物群可接触的多糖和膳食纤维,为在该栖息地竞争的密集微生物群提供食物,对肠道微生物生态学和健康产生重大影响。
多糖含量高的饮食与上调的肠道微生物群落多样性有关,并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生长,例如阿克曼氏菌、双歧杆菌和乳杆菌。同时,肠道微生物可以使用中间寡糖来生成对宿主有益的短链脂肪酸。
•增强肠道屏障
例如,铁皮石斛多糖 (DOPs) 不易消化和吸收,但会促进肠道微生物产生更多的丁酸,主要由Parabacteroides sp. HGS0025产生,从而介导肠道健康和免疫功能的改善。
铁皮石斛多糖干预还可以通过作用于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来促进粘蛋白合成,从而增强肠道屏障功能。
•参与抗炎保护
五味子的其他多糖还逆转了肠道微生物生态失调并上调了丁酸和丙酸的产生,这可能参与了抗炎保护机制。
膳食蛋白质是另一种关键的常量营养素,人们每天必须摄入一定量蛋白质,以获得氨基酸和一定量的氮元素,用于合成组织蛋白质。
★ 蛋白质摄入过高或过低都不健康
它还可以调节微生物组成和代谢产物的产生。蛋白质摄入量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遵循U形曲线,其中较低的蛋白质摄入量与营养不良状态相关,而高于可耐受限度的摄入量与营养过剩疾病相关。
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普通成人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0.83g/kg。
✦影响肠道环境
膳食蛋白质消化的产物是氨基酸。肠道微生物降解的氨基酸代谢物包括短链脂肪酸、支链脂肪酸、吲哚、酚、硫醇、硫化物、氨和胺。这些代谢产物参与与宿主健康和疾病相关的各种生理功能。
一方面,蛋白质降解提供必需的游离氨基酸作为结肠细胞的替代能源. 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会释放出有毒的代谢副产物,如氨、硫化物和酚类,它们对局部肠道环境有害。
研究表明,适度限制日粮蛋白质可以塑造微生物群组成和多样性的和谐平衡,并改善成年猪的肠道屏障功能。
▸ 高蛋白饮食
•高蛋白饮食导致菌群减少和一些疾病
高蛋白饮食者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瘤胃球菌科(Ruminococcaceae)和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的丰度减少。
此外,蛋白质,尤其是红肉和加工肉类中的蛋白质,是左旋肉碱和胆碱的来源,可被肠道微生物代谢并产生三甲胺 (TMA),随后被氧化为三甲胺N-氧化物 (TMAO)。高TMAO浓度与心血管疾病或死亡风险增加相关。
•经常运动蛋白质需求大
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员可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来支持骨代谢,保持足够的蛋白质合成和能量代谢,以及在强化/长时间的运动程序中保持足够的免疫功能和肠道完整性。
研究建议接受过耐力和力量训练的运动员的蛋白质摄入量为1.2-1.7克每公斤体重/天。
注:缺乏蛋白质可能导致女运动员月经失调。
膳食脂肪是指我们每日所吃各种食物含油脂的总和。来自植物和动物的膳食脂肪是人类生长发育的能量储备来源。
▸ 消化过程
脂肪首先被口腔中的舌脂肪酶和胃脂肪酶消化。接下来被胰脂肪酶水解成游离脂肪酸(FFA);大部分游离脂肪酸被小肠吸收,少数会通过胃肠道并直接改变肠道微生物成分。
✦膳食脂肪导致肠道微生物改变
与橄榄油或红花油相比,以棕榈油为基础的饮食可能会导致体重增加,对微生物群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并增加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的比例。
•高脂饮食减少了有益菌和短链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降低拟杆菌属、普雷沃氏菌属、乳酸菌属和双歧杆菌属。与低脂饮食相比,食用高脂饮食也显著减少了短链脂肪酸的释放。
✦高脂饮食不利于健康
•高脂饮食易导致结肠癌
膳食脂肪引起的肠道微生物群成分变化也可以调节微生物衍生的次级胆汁酸 (BA) 的产生。高脂饮食引发增强的胆汁酸放电,导致初级胆汁酸的结肠浓度增加。然而,5%到10%的胆汁酸没有被重吸收,而是被大肠中的微生物转化为次级胆汁酸,这对人体有害并会促进结肠癌发生。
•高脂饮食易导致炎症
此外,在高脂饮食小鼠中观察到的微生物群失调引起脂多糖从肠腔进入体循环,从而激活宿主促炎信号通路,然后引发低度全身炎症。
▸ 定义
膳食纤维的定义一直存在争议,一般将膳食纤维定义为具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单元的可食用碳水化合物聚合物,对内源性消化酶有抵抗力,因此在小肠中既不水解也不吸收。
✦膳食纤维的作用
•重要能量来源
膳食纤维是盲肠和结肠微生物群的重要能量来源。特定肠道条件下的厌氧菌会激活其由关键酶和代谢途径组成的机制,这些机制可以代谢复杂的碳水化合物,从而导致产生短链脂肪酸等代谢物。
•影响微生物多样性
值得注意的是,限制膳食纤维不仅会导致微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短链脂肪酸的产生,还会改变肠道微生物的代谢以利用不太有利的底物,这可能对宿主有害。
Q1
什么是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是主要由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组成的有机产物。短链脂肪酸在调节宿主代谢、免疫系统和细胞增殖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短链脂肪酸在盲肠和近端结肠中浓度很高,它们被用作结肠细胞的能量来源(尤其是丁酸盐),但也可以通过门静脉输送到外周循环,作用于肝脏和外周组织。尽管短链脂肪酸在外周循环中的水平很低,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它们在宿主体内充当信号分子并调节不同的生物过程。
✦高纤维饮食有助于降低危害
为人类志愿者提供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不仅显著减少了总短链脂肪酸和丁酸盐的产生,还导致氨基酸发酵产生的潜在有害代谢物增加,包括支链脂肪酸、氨、胺、N-亚硝基化合物、酚类化合物、硫化物、吲哚化合物和氢气硫化物。这些代谢物的细胞毒性和促炎特性导致慢性疾病的发展,尤其是结直肠癌。
考虑到糖酵解发酵和蛋白水解发酵之间的权衡,高纤维饮食可能会抑制蛋白质发酵,抵消肉类和脂肪的许多不利影响,从而降低这些食物成分的危害。
稳定的肠道微生物群落受多种必需成分的影响,例如维生素、矿物质和多酚。
✦维生素
维生素是维持正常生理功能所需的少量辅助因子。人类无法合成大多数维生素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求,因此必须从外部获取。
•改变肠道微生物丰度和多样性
值得注意的是,肠道微生物有能力调节各种维生素的合成和代谢输出。随后,维生素还可以显著改变肠道微生物的丰度和多样性。
例如,维生素A可以上调对健康有益的微生物群,包括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和阿克曼氏菌。
✦矿物质
与维生素一样,矿物质是微量营养素,它们在宿主新陈代谢和与肠道微生物群进行积极互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影响肠道菌群和慢性疾病
已经证明,镁缺乏与慢性病发病率增加有关,并且镁缺乏小鼠体内的双歧杆菌含量会降低四天。不过,如果长期缺镁(21 天),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丰度会增加。
需要进行更多临床试验来确定缺镁和补充镁对避免不良反应的影响。
✦多酚
多酚是广泛存在于植物性食物中的一大类化合物,其中一些与肠道健康有关。
•抑制有害菌,促进益生菌
例如茶多酚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害细菌的生长,并刺激或促进双歧杆菌和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等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调节肠道微生物
类黄酮可以影响和重塑肠道菌群的组成,发挥益生元和杀菌作用,尽管证据尚不确凿,它们的全身抗炎作用可能至少部分与微生物群的调节有关。
多酚的“益生元样”作用已经通过对人类肠道微生物群的体外研究以及临床前和临床试验中的体内观察到,在这些试验中,补充多酚和富含多酚的食物被证明可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
多酚有利于生长的其他有益物种包括:
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
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罗氏菌属(Roseburia spp)
✦多酚人体利用度较低
不幸的是,许多天然多酚,如浓缩或可水解的单宁和糖基化多酚衍生物(与葡萄糖、半乳糖、鼠李糖、核酮糖、阿拉伯吡喃糖等糖结合)的特点是人体肠道吸收率低。口服生物利用度的降低严重限制了这些化合物的潜在有益作用。
•经肠道微生物作用更容易吸收
有趣的是,这些通常在饮食中保持无活性的多酚在肠道微生物群去除糖部分后被生物转化为活性化合物。这些代谢物可以保留母体化合物的抗氧化和多效活性,同时还表现出增加的肠道吸收和更好的生物利用度。
因此,类黄酮通过微生物群的生物转化,可以更容易地到达血液并在全身水平发挥其生物学相关作用。
总的来说,微生物群和多酚之间的相互积极的相互作用可能会促进人们的健康。
除了个别营养素,饮食模式对肠道微生物群的代谢活动也有显著影响。
世界范围内的饮食习惯多种多样,包括西式饮食、地中海饮食、生酮饮食、间歇性禁食等。
饮食模式对肠道微生物群介导的健康的影响


Zhang L,et al.Nutrients.2022
▸ 西式饮食
西式饮食,是一种以高含量精加工糖和碳水化合物、高含量饱和脂肪酸、高含量动物蛋白以及低含量膳食纤维为特征的一种现代饮食方式。
•西式饮食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稳态
在西方饮食中,大部分能量由非细胞营养素提供,这些营养素更容易被微生物和人体细胞消化。易于获取的非细胞营养素的数量增加会影响pH值、肠道微生物群成分和新陈代谢的变化,从而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稳态的调节和维持。
•易导致炎症
另一方面,高脂饮食的消耗也增加了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从而导致全身性慢性炎症和脂多糖易位。
不同饮食对肠道菌群和宿主生理功能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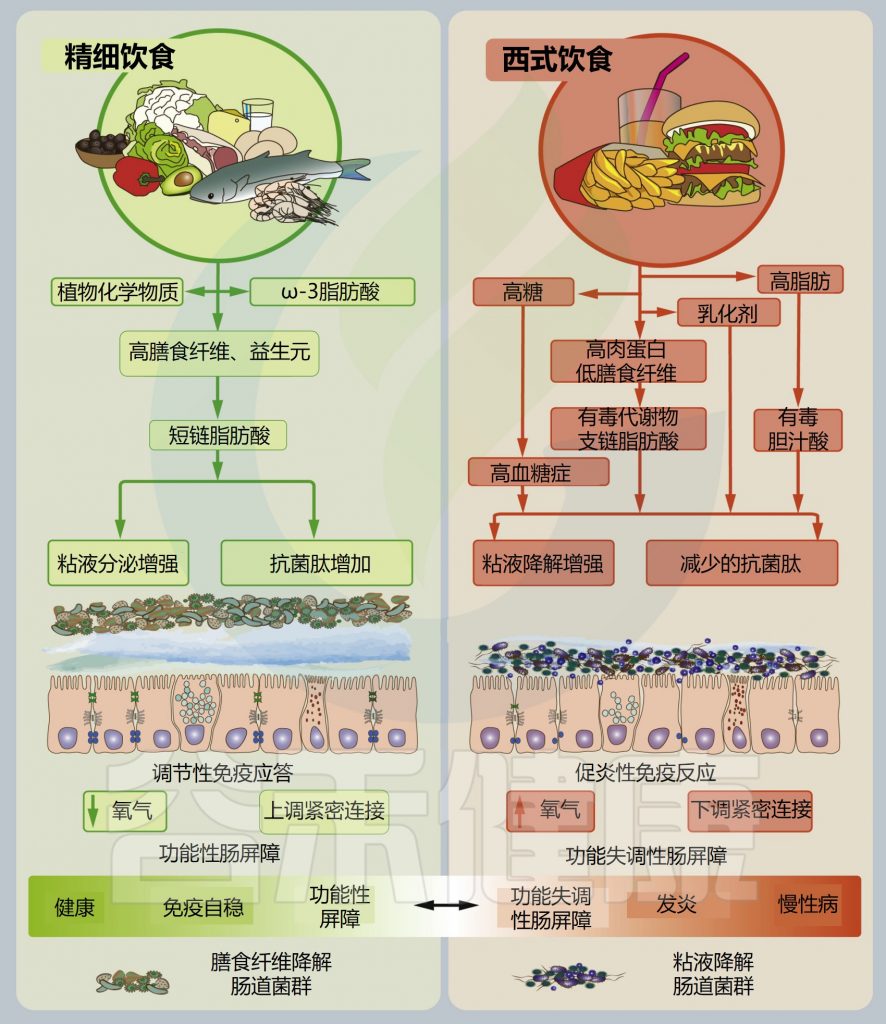

Makki K,et al.Cell Host Microbe.2018
▸ 地中海饮食
“地中海式饮食”是指有利于健康的,简单、清淡以及富含营养的饮食。这种特殊的饮食结构强调多吃蔬菜、水果、鱼、海鲜、豆类、坚果类食物,其次才是谷类,并且烹饪时要用植物油(含不饱和脂肪酸)来代替动物油(含饱和脂肪酸)。
•降低免疫性疾病风险
与西方饮食不同,地中海饮食被认为是全球最健康的饮食模式之一。更好地坚持地中海饮食与总死亡率的显著降低以及免疫系统失调、心血管疾病、认知能力下降和癌症的风险降低有关 。
•改善微生物群组成
此外,地中海饮食改变了微生物群的组成,有利于有益细菌,例如狄氏副拟杆菌(Parabacteroides distasonis)、多形拟杆菌(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和青春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adolescentis),并抑制病原体的生长,恢复可能有益的微生物。
▸ 生酮饮食
生酮饮食是一种高脂肪、充足蛋白质和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
身体通过限制碳水化合物的可用性来燃烧脂肪而不是碳水化合物来获取卡路里。研究表明,生酮饮食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有好有坏。
•有营养不足的风险
一方面,生酮饮食营养不足的风险更大,并且由于缺乏纤维、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和铁,可能无法维持健康的微生物群。
•缓解结肠炎
另一方面,研究表明,随着阿克曼氏菌丰度的急剧增加,生酮饮食在DSS诱导的接受者中赋予微生物群益处并缓解结肠炎和产丁酸的罗氏菌属(Roseburia) ; 此外,在喂食生酮饮食的小鼠中发现大肠杆菌(Escherichia)/志贺氏菌(Shigella)的丰度减少。
▸ 间歇性禁食
间歇性禁食是一种类似于热量限制的饮食干预,包括各种操纵进餐时间以改善身体成分和整体健康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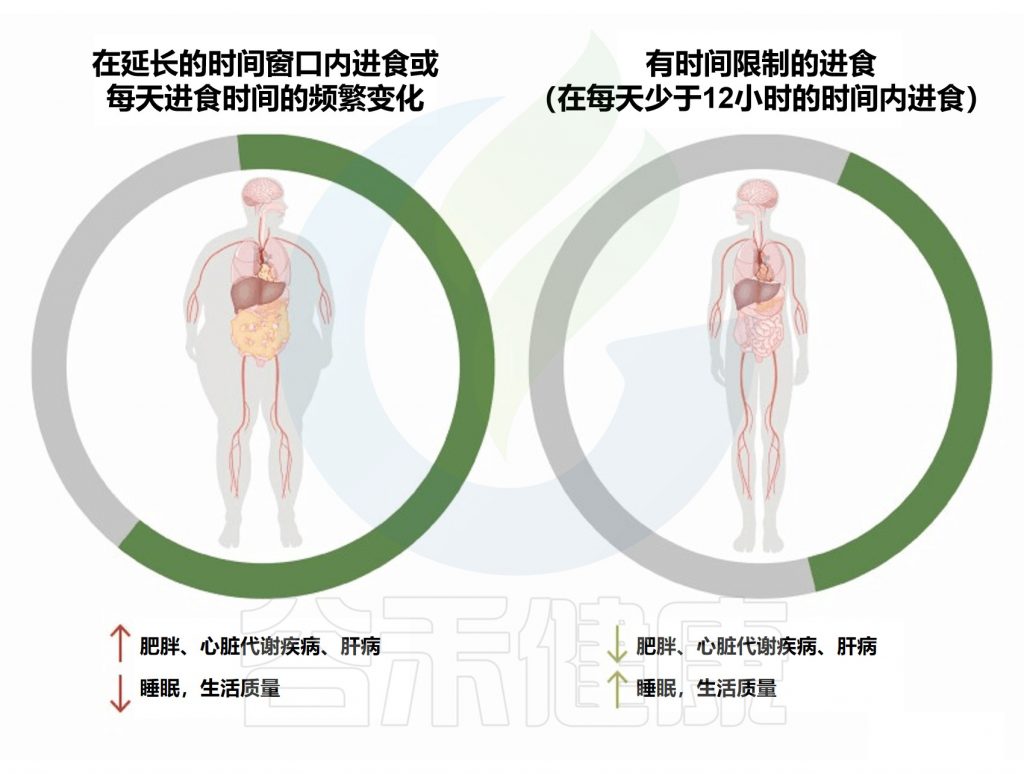

Chow LS,et al.Endocr Rev.2022
•缓解慢性疾病
研究发现间歇性禁食在动物模型中对广泛的慢性疾病(包括肝病、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脑功能)以及体重减轻具有强大的疾病缓解功效。
•增加肠道微生物丰富度
间歇性禁食似乎对肠道微生物群有积极影响。临床前研究一致表明,间歇性禁食有助于增加肠道微生物的丰富度,丰富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和乳杆菌(Lactobacillus),减少假定的促炎类群脱硫弧菌属(Desulfovibrio)和Turicibacter,并增强抗氧化微生物代谢途径。
建议
我们应该合理搭配膳食,尽量做到高纤维低脂肪的摄入,并保证一定量的碳水和蛋白质,以及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有助于降低代谢性疾病风险,恢复肠道环境,提升健康水平。
遗传变异被认为是代谢疾病的主要驱动因素,但这些变异的遗传概率相当有限。最近肠道微生物群被怀疑是驱动代谢疾病的另一个因素。
与健康个体相比,大多数患有肥胖、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人群肠道微生物多样性降低。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如果被外部因素改变,会导致肠道微生物与宿主之间的共生关系发生巨大变化,这对于代谢疾病的发展至关重要。
肥胖是指一定程度的明显超重与脂肪层过厚,是体内脂肪,尤其是甘油三酯积聚过多而导致的一种状态。由于食物摄入过多或机体代谢的改变而导致体内脂肪积聚过多造成体重过度增长并引起人体病理、生理改变或潜伏。
✦肥胖个体的微生物能量获取显著增加
通过行为改变(例如高脂饮食和抗生素的使用)改变肠道微生物可能是肥胖大流行的强大驱动力。
关于肠道微生物群在介导肥胖发病机制中作用,基于动物模型的发现。肥胖的微生物群导致从饮食中获取的能量显著增加。
据观察,与接受瘦捐赠者微生物群的小鼠相比,将肥胖捐赠者的微生物群引入无菌 (GF) 小鼠会导致能量获取能力增加。同样,可转移的肥胖相关微生物群比“瘦微生物群”定植更有助于全身脂肪的积累。
✦菌群丰度发生变化
肠道微生物成分在肥胖和瘦弱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人体研究观察到,与非超重个体相比,超重个体的微生物群的特征是拟杆菌(Bacteroides)的丰度较低,而厚壁菌门(Phylum Firmicutes)的丰度较高 。
在属水平上,一项宏基因组关联研究揭示了多形拟杆菌(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在肥胖个体中的不足。
有趣的是,用B. thetaiotaomicron灌胃可以减轻饮食引起的小鼠体重增加和肥胖,这意味着益生菌或微生物化合物可能是未来潜在的抗肥胖方式。
2型糖尿病也被认为受到肠道微生物成分和功能失调的影响。
✦肠道微生物丰度与2型糖尿病相关
临床报告表明,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乳杆菌(Lactobacillus)和产丁酸细菌 (例如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的相对丰度与2型糖尿病呈负相关,而梭菌属(Clostridium spp)、瘤胃球菌属(Ruminococcus)、梭杆菌属(Fusobacterium)和经黏液真杆菌属(Blautia)与2型糖尿病呈正相关。
•肠道屏障受损影响2型糖尿病
肠道微生物的失调可能通过破坏紧密连接蛋白 (TJP) 损害肠道屏障,随后导致粘膜渗漏和代谢性内毒素血症,这是胰岛素抵抗和2型糖尿病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此外,肠道微生物可能参与葡萄糖调节。一项研究表明,与未接受结肠切除术的患者相比,接受全结肠切除术的患者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因此,营造一个良好的肠道稳态有助于预防2型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是心脏血管和脑血管疾病的统称,泛指由于高脂血症、血液黏稠、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等所导致的心脏、大脑及全身组织发生的缺血性或出血性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特别是50岁以上中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病,具有高患病率、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
肥胖、2型糖尿病、血脂异常、高血压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吸烟、缺乏运动和不良饮食习惯等,都涉及心血管疾病的病理过程和危险因素。
✦肠道微生物影响心血管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都与肠道微生物有关,基因组测序和宏基因组分析也揭示了心血管疾病表型与特定微生物类群变化或肠道微生物丰富度和多样性之间的关联。
早期研究表明,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检测到细菌 DNA(主要是Chryseomonas),其特征与疾病状态相关的分类群相匹配.
•肠道菌群丰度发生变化
此外,宏基因组分析表明,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组与健康个体不同,这主要表现为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 spp.)和肠杆菌属(Enterobacteriaceae spp.)的丰度升高。以及拟杆菌属(Bacteroides spp.)、普氏菌属(Prevotella copri)和Alistipes shahii的丰度下降。
•肠道微生物作用机制
在机制层面,肠道微生物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与炎症、肠道屏障功能和代谢物的调节有关。肠道微生物群中与生态失调相关的变化会损害肠道屏障,导致循环脂多糖水平升高,而脂多糖可通过 Toll 样受体 (TLR)-MyD88信号通路激活炎症信号,从而释放促炎细胞因子,从而在宿主中协调炎症状态。
先前的研究表明,心力衰竭患者的肠道完整性受损,血液中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与症状严重程度和较差的预后相关。在依赖代谢的途径中,肠道微生物裂解一些含三甲胺的化合物产生三甲胺,三甲胺可被黄素单加氧酶进一步氧化成氧化三甲胺。氧化三甲胺激活 MAPK、NF-κB 信号通路,促进炎症基因表达,从而影响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脂质代谢并增加甘油三酯,降低高密度脂蛋白。
非酒精性脂肪肝是一种与肥胖有关的疾病,通常被认为是代谢综合征的肝脏表现。
多项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强调了肠道微生物群在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尽管对因果关系还不确定。
✦微生物多样性较低
简而言之,与健康受试者相比,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多样性较低,Anaerobacter、链球菌(Streptococcus)、大肠杆菌(Escherichia)和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的物种丰度增加,普雷沃氏菌(Prevotella)、颤螺菌属(Oscillibacter)和Alistipes spp的丰度较低。
注:肠道微生物群影响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机制可能是在肠-肝轴方面。
✦影响其他疾病
除了肠道微生物群失调外,非酒精性脂肪肝还与胆汁酸的肠肝循环、肠道微生物群介导的肠粘膜炎症和相关的粘膜免疫功能损伤有关。
高热量饮食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导致肥胖的发病率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能量摄入超过能量消耗造成的。
大量流行病学证据表明,肥胖是诱发其他代谢性疾病(包括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危险因素。
代谢性疾病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这一疾病主要是日积月累的不良习惯引起的,那么有什么可以预防或是降低这类疾病发病率的方法呢?
✦运动加饮食效果更好
确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是改善代谢性疾病的重要途径。前文已有讲到运动和饮食都会调节肠道微生物并改善代谢性疾病。
事实上,当一项计划包括饮食和体育锻炼时,与单独锻炼或饮食相比,会有更有效的改变。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和功能也受到饮食和体育锻炼的影响。
锻炼与饮食结合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预防代谢性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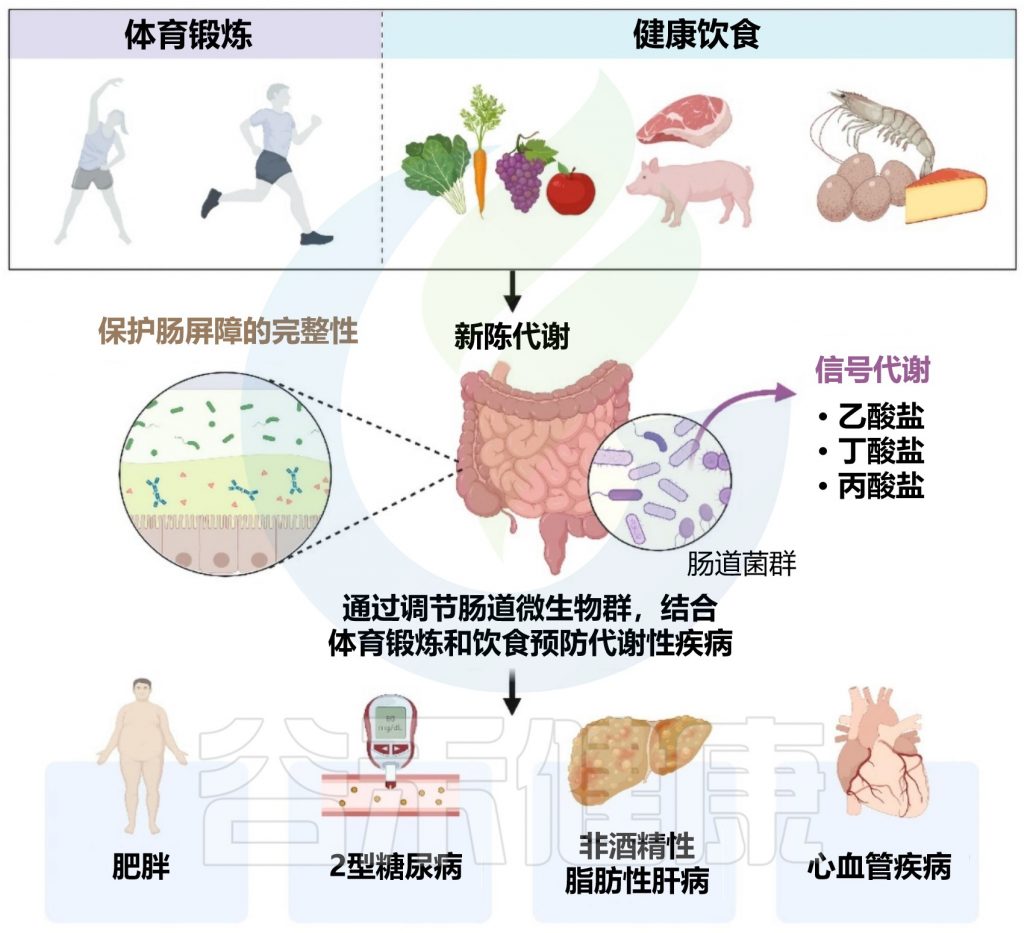

Zhang L,et al.Nutrients.2022
在这里,我们总结了一些动物和人类通过饮食加运动干预改善代谢性疾病的研究。
饮食诱导期间重复运动增加了免疫和代谢能力
在饮食诱导的肥胖期间,重复运动增加了小鼠远端肠道微生物群的α多样性和代谢能力。
适度运动和低脂饮食对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的体重减轻和巨噬细胞免疫能力具有有益影响。
运动搭配低碳饮食减少了脂肪以及预防糖尿病
此外,一项为期6个月的随机干预计划表明,有氧运动和低碳水饮食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可以通过改变肠道微生物群成分来减少肝脏脂肪和预防糖尿病。
低碳饮食加运动改善了心脏代谢
一项针对超重/肥胖中国女性表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与运动训练相结合会增加产生短链脂肪酸的经黏液真杆菌属(Blautia)并减少与2型糖尿病相关的Alistipes属,导致显著的体重减轻,并改善血压、胰岛素敏感性和心肺健康,这表明低碳水饮食和运动干预可能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在心脏代谢健康中发挥作用。
✦降低肝脏脂肪含量
最近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表明,与运动或单独饮食干预相比,饮食加运动干预可以显著降低肝脏脂肪含量并增加关键微生物的多样性和稳定性,这为制定饮食加运动干预策略提供了更有效的途径用于预防非酒精性脂肪肝。
✦有效控制血糖
在禁食状态下锻炼会产生有利的代谢适应,伴随着稳定的血糖浓度和升高的血液游离脂肪酸浓度,这可能更有效地改善胰岛素抵抗个体的胰岛素敏感性和控制血糖。
✦保护肠道屏障
肠道屏障是一种选择性的物理和免疫屏障,可促进营养、水和电解质吸收进入循环,同时阻止有害病原体和有毒管腔物质的转移。
如前所述,代谢疾病可能长期存在和加重的病理生理状态之一是肠道稳态失调释放内毒素,造成肠道渗漏,从而在宿主中诱发慢性低度炎症状态。
饮食和运动可以调节参与维持上皮膜完整性的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从而改善肠道通透性并降低慢性病风险。
从肠道微生物的角度来看,体育锻炼和饮食相结合可以缓和肠道屏障功能障碍,保持粘液厚度和肠道通透性。
✦影响代谢物的利用
饮食和运动的结合也会影响肠道微生物如何利用和合成代谢物。
肠道微生物和相应的代谢物以不同的方式与宿主协同作用,影响肠道稳态并为代谢性疾病提供保护性干预。具体而言,短链脂肪酸是微生物发酵或肠道中膳食多糖转化的主要终产物之一。而运动是短链脂肪酸的有效调节剂,对丁酸盐浓度具有特殊影响。
短链脂肪酸是肠上皮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参与维持肠粘膜完整性,改善糖脂代谢,控制能量消耗,调节免疫系统和炎症反应。在动物模型中,补充短链脂肪酸已被证明可以通过增加能量消耗和葡萄糖耐量来改善代谢,并且可能有助于延迟或减轻糖尿病并导致体重减轻。
益生菌、益生元等已被提议作为预防代谢性疾病的有效手段。
益生菌、益生元等对代谢性疾病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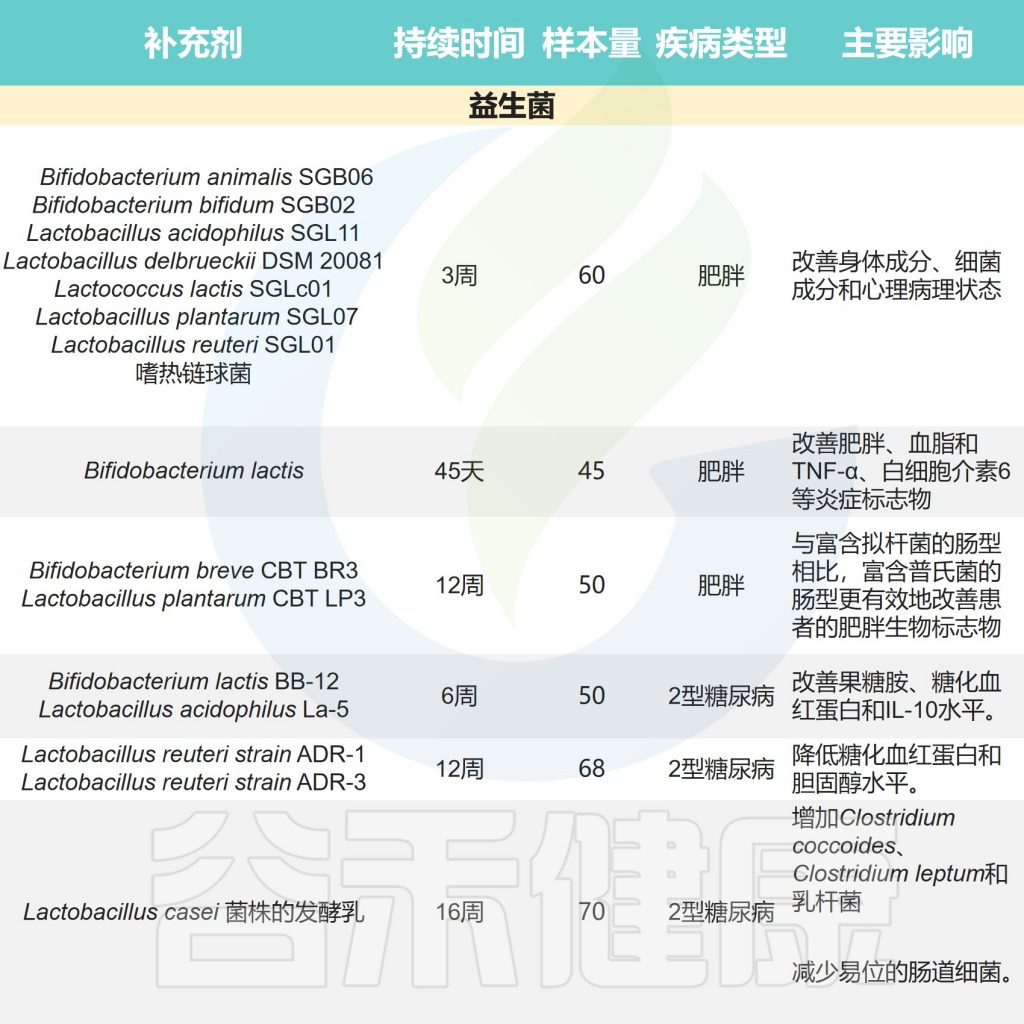



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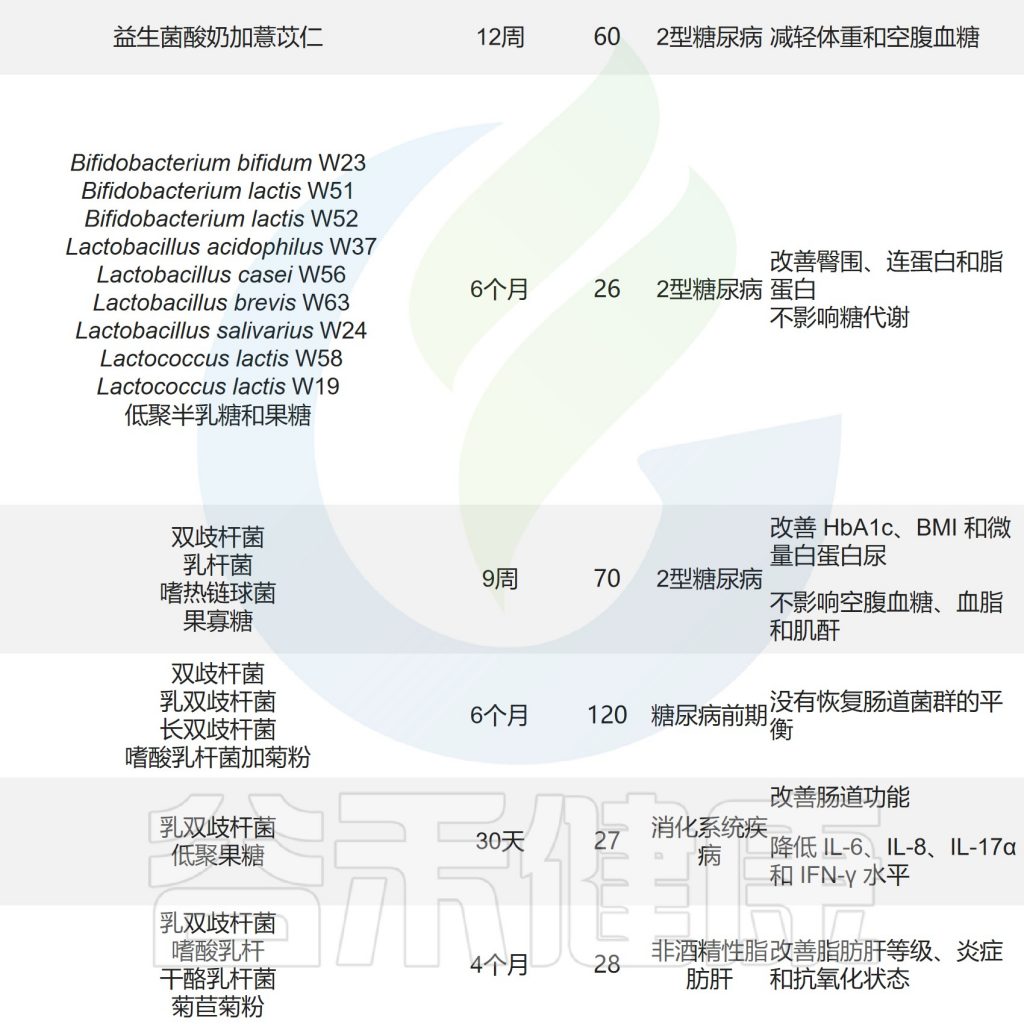
Li HY, et al.Nutrients.2021
✦调节肠道菌群
含有Bifidobacterium lactis LMG P-28149和Lactobacillus rhamnosus LMG S-28148的益生菌混合物可以调节肥胖相关肠道菌群的组成,恢复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和Rikenellaceae的丰度,同时降低乳杆菌科的丰度。
✦改善代谢功能、减轻炎症
肠道微生物群被认为是肥胖和2型糖尿病代谢炎症的触发因素,罗伊氏乳杆菌(Lactobacillus reuteri)的给药可以通过抑制有害细菌(如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的生长和改善TLR1-中的连四硫酸盐代谢来改善代谢功能有肠道炎症的缺陷小鼠。
此外,摄入干酪乳杆菌(Lactobacillus casei)可通过减少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来预防围产期大鼠代谢相关性高血压比率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ACE) 的表达,同时增加阿克曼菌和乳杆菌的丰度。
✦合生元有效改善肥胖
合生元被认为是预防肥胖的新领域,与单独的益生菌相比,omega-3脂肪酸与含有双歧杆菌、乳杆菌、乳球菌和丙酸杆菌的活益生菌混合物显示出更显著的肝脂肪变性和脂质积累减少。
此外,结合地衣芽孢杆菌和低聚木糖的口服补充剂可以更有效地改善肥胖大鼠的体重增加和脂质代谢,同时降低脱硫弧菌科和瘤胃球菌科的丰度。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PMO 08与奇亚籽的混合物显示出对肥胖小鼠的协同抗肥胖作用,并为植物乳杆菌的生长创造了更有利的肠道微环境。
小结
益生菌(如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益生元(如菊粉低聚果糖和其他多糖)、合生元(由益生菌菌株和益生元食品组成)等的干预可以使对代谢功能有重要影响。
主要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组成、调节肠道微生物代谢物、改善肠道屏障功能这三个机制。
健康的饮食与体育锻炼相结合,可促进有益代谢物的产生并缓和肠屏障功能障碍,从而保护宿主免受入侵微生物的侵害,有助于维持体内平衡和预防代谢性疾病。
然而,虽然传统上这两种干预措施都被接受和实施,但很少有深入研究关注基于微生物群的策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肠道微生物是否可以作为对饮食和运动干预做出反应的代谢疾病的重要预测因子。
主要参考文献
Zhang L, Liu Y, Sun Y, Zhang X. Combined Physical Exercise and Diet: Regulation of Gut Microbiota to Prevent and Treat of Metabolic Disease: A Review. Nutrients. 2022 Nov 11;14(22):4774. doi:10.3390/nu14224774. PMID: 36432462; PMCID: PMC9699229.
Donati Zeppa S, Agostini D, Gervasi M, Annibalini G, Amatori S, Ferrini F, Sisti D, Piccoli G, Barbieri E, Sestili P, Stocchi V. Mutual Interactions among Exercise, Sport Supplements and Microbiota. Nutrients. 2019 Dec 20;12(1):17. doi: 10.3390/nu12010017. PMID: 31861755; PMCID: PMC7019274.
Makki K, Deehan EC, Walter J, Bäckhed F. The Impact of Dietary Fiber on Gut Microbiota in Host Health and Disease. Cell Host Microbe. 2018 Jun 13;23(6):705-715. doi: 10.1016/j.chom.2018.05.012. PMID: 29902436.
Allen JM, Mailing LJ, Niemiro GM, Moore R, Cook MD, White BA, Holscher HD, Woods JA. Exercise Alters 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 in Lean and Obese Humans. Med Sci Sports Exerc. 2018 Apr;50(4):747-757. doi: 10.1249/MSS.0000000000001495. PMID: 29166320.
Mohr AE, Jäger R, Carpenter KC, Kerksick CM, Purpura M, Townsend JR, West NP, Black K, Gleeson M, Pyne DB, Wells SD, Arent SM, Kreider RB, Campbell BI, Bannock L, Scheiman J, Wissent CJ, Pane M, Kalman DS, Pugh JN, Ortega-Santos CP, Ter Haar JA, Arciero PJ, Antonio J. The athletic gut microbiota. J Int Soc Sports Nutr. 2020 May 12;17(1):24. doi: 10.1186/s12970-020-00353-w. PMID: 32398103; PMCID: PMC7218537.
Manoogian ENC, Chow LS, Taub PR, Laferrère B, Panda S. Time-restricted Eating for the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Metabolic Diseases. Endocr Rev. 2022 Mar 9;43(2):405-436. doi: 10.1210/endrev/bnab027. PMID: 34550357; PMCID: PMC8905332.
Li HY, Zhou DD, Gan RY, Huang SY, Zhao CN, Shang A, Xu XY, Li HB.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Probiotics, Prebiotics, Synbiotics, and Postbiotics on Metabolic Diseases Targeting Gut Microbiota: A Narrative Review. Nutrients. 2021 Sep 15;13(9):3211. doi: 10.3390/nu13093211. PMID: 34579087; PMCID: PMC8470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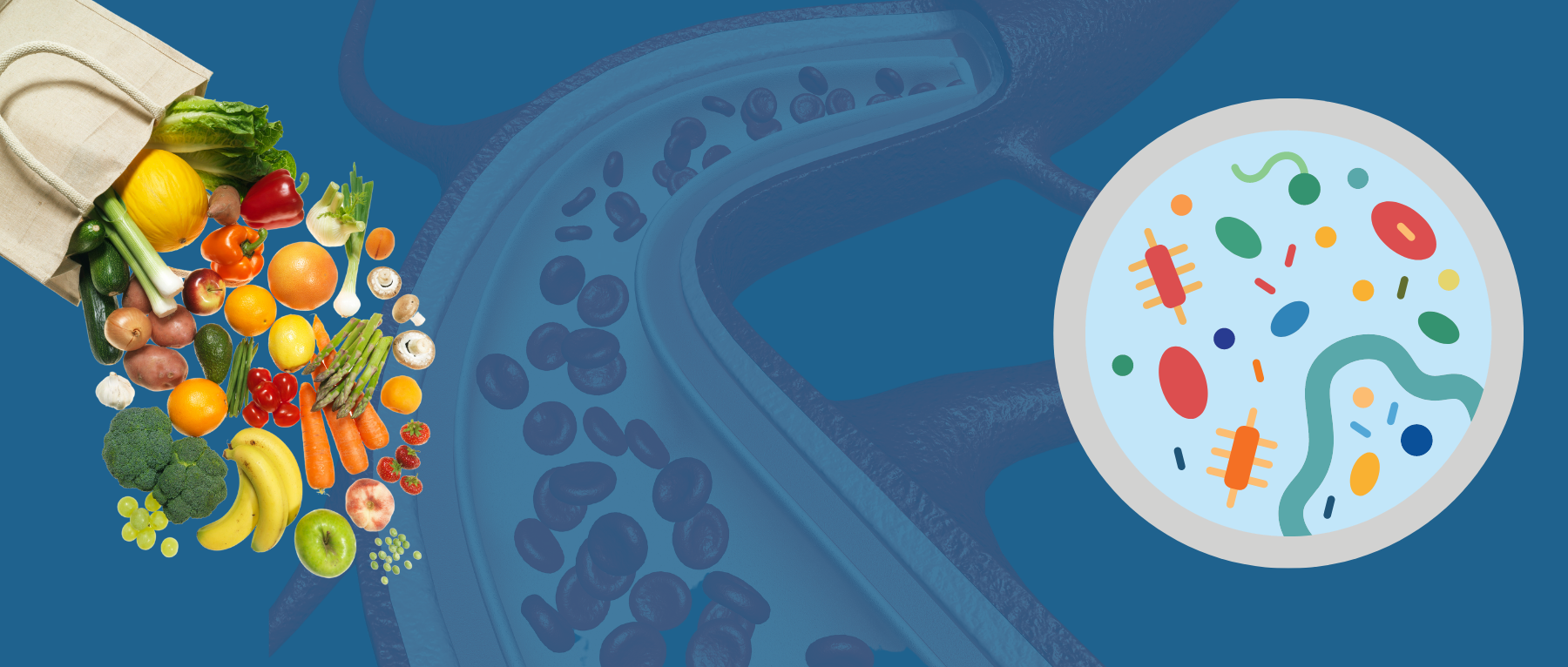
谷禾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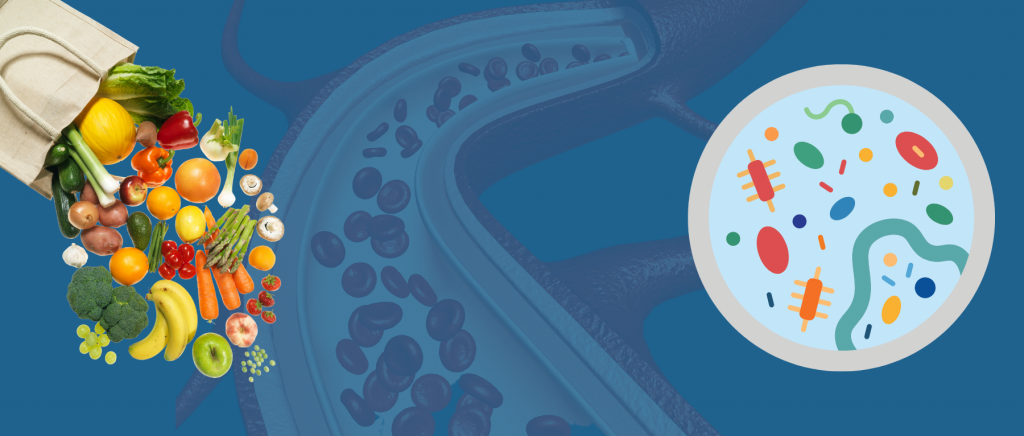

如果说前一篇文章《微生物组-神经免疫轴: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希望》更多的是借助心血管疾病(CVD),来宏观地阐述肠道-神经免疫-菌群之间的关联,那么这篇文章更多地是具体讨论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参与CVD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饮食和微生物群的串扰机制,基于上述理论,从更实际具体的角度来了解饮食相关的干预措施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隐形器官”,在人类新陈代谢和包括心血管疾病在内的疾病状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可能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许多内源性和外源性因素中,饮食成为宿主-微生物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与 CVD 易感性有关。
本文主要介绍肠道微生物群饮食调节的主要概念,及其参与心血管疾病发展。还讨论了调节 CVD 进展的饮食-微生物群串扰的机制,包括内毒素血症、炎症、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脂质代谢功能障碍。也阐述了关于微生物群产生的代谢物,包括三甲胺-N-氧化物、次级胆汁酸、短链脂肪酸以及芳香族氨基酸衍生的代谢物如何在 CVD 发病机制中发挥作用。最后,列举了与肠道微生物群相互作用的潜在饮食干预措施,作为 CVD 管理的新型预防和治疗策略。
在了解CVD中基于菌群的饮食干预之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饮食变化对肠道微生物群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主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1) 快速/短期效应
对在植物性(高纤维)之间切换的人类受试者和以动物为基础的(高脂肪)饮食的研究表明:
所有受试者的微生物群组成在 1-2 天内发生变化,厚壁菌门在植物性饮食中代谢膳食纤维的丰度增加,在动物性饮食中耐胆汁微生物Alistipes和Bilophila增加。然而,即使经过 10 天的干预,短期饮食改变对肠型也没有影响。
(2) 长期影响
尽管微生物群落迅速调节,但长期的饮食干预不仅与成分改变有关,还与生理变化有关。
例如,用高脂肪饮食 (HFD) 喂养大鼠 8 周或 12 周会导致肠杆菌门(变形杆菌门)的丰度增加,这与全身炎症、肠道通透性和肥胖表型的升高相结合。相反,人类队列干预 3 个月的低碳水化合物或低脂肪健康饮食导致 14 或 12 种与体重减轻相关的菌群变化,这表明长期干预是必要的。此外,肠型主要与长期饮食影响而不是短期影响有关。
(3) 特定饮食引起的特定微生物变化
例如,膳食纤维的摄入促进了肠道微生物群的丰度或多样性以及厚壁菌门的增加。抗性淀粉饮食干预下 Ruminococcus bromii 增多。
有趣的是,不仅是微生物组成,还有特定的微生物代谢与特定的饮食和疾病模式相关。例如,富含红肉饮食的受试者血浆中的三甲胺-N-氧化物 (TMAO)(红肉中胆碱的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比素食者多。已在人类受试者中发现 TMAO 水平升高,肠型普氏菌比例较高,并且与 CVD 风险增加有关。
人类队列中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



Xufei Zhang,et al., Comput. Struct. Biotechnol. J. 2022
在健康状态下,适当的肠道屏障提供了抵御病原体的关键第一道防线,它由多种生理成分支持,包括粘液层、由紧密连接蛋白连接的上皮细胞和免疫细胞。
然而,心力衰竭或高血压的 CVD 患者经常观察到肠道屏障功能障碍,伴随全身微生物成分LPS和炎症的增加。
那么CVD过程中,引发肠道渗漏和炎症的风险因素是什么?
其中一个假设是,长期食用西方饮食或 HFD 会导致生态失调并损害肠道屏障,从而增强 LPS 易位和全身炎症,导致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
有鉴于此,富含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酸的饮食摄入量较高与 CVD 风险的增加高度相关,而饮食中饱和脂肪的摄入量较低可使 CVD 降低约 30%。
在大型队列研究中,长期(6 个月)食用 HFD 会导致微生物菌群失调,其中革兰氏阴性菌(如Alistipes和Bacteroides)的比例增加,同时参与 LPS生物合成的基因水平更高。同时,已发现膳食脂肪通过激活促炎细胞因子(例如 TNF-α、IFNγ 和 IL-1β)的分泌来损害肠道屏障。促炎细胞因子的上调进一步激活 MLCK(肌球蛋白轻链激酶)信号通路,重组紧密连接蛋白,包括occludin、ZO-1(Zonula occludens-1)并导致肠漏。
当肠道屏障被破坏时,LPS或病原体可能转移到循环中,引起内毒素血症,从而刺激全身性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一旦在血流中易位,内毒素可以通过与细胞表面的 TLR-4(Toll 样受体 4)相互作用来触发内皮细胞的损伤,并增强 ROS(活性氧)的产生,从而降低内皮细胞 NO(一氧化氮)的生物利用度导致形成斑块和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这一假设已在动物模型中得到证实,其中 ApoE-/-西方饮食下的小鼠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加重,变形菌(革兰氏阴性促炎细菌)和全身 LPS 水平显着增加。
此外,西方饮食促进炎症细胞因子(如 TNF-α 和 IL-1β)的上调,增加肠道通透性,同时修饰 ApoE-/- 小鼠中的紧密连接蛋白(如 occludin)。
然而,在人类队列中仍然缺乏数据来解释,由于西方饮食导致的肠道屏障受损和相关的内毒素血症增加在什么情况下会诱发CVD发病机制。
除了饮食-微生物群对炎症和肠道屏障功能的相互作用外,肠道微生物还通过宿主脂质代谢影响 CVD。
越来越多的动物和人类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与脂质代谢紊乱有关,如血脂异常或高脂血症,它们是 CVD 发展的主要危险因素。
肠道微生物群将胆固醇转化为粪(甾)醇降低胆固醇
例如,GF 小鼠的胆固醇代谢发生了改变 ,而ApoE -/-小鼠肠道微生物群的消耗导致与传统的 ApoE -/-小鼠相比,血浆胆固醇伴有更大的主动脉病变。
此外,从高血浆胆固醇人类到小鼠的微生物群移植引发了上调循环胆固醇的表型以及肝脏胆固醇合成 的减少。
这可能是由于肠道微生物群将胆固醇转化为粪(甾)醇,这可以促进体内胆固醇的消除和降低胆固醇血症。
胆固醇代谢的数学模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最近发现肠道菌群的胆汁盐代谢和胆固醇向粪(甾)醇的转化都会影响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
此外,最近对人类队列进行的一项有趣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并确定了含有胆固醇代谢酶ismA的Eubacterium coprostanoligenes等粪(甾)醇形成菌的个体,粪便胆固醇水平显著降低,血清总胆固醇显著降低。
然而,在斑块面积较小的无菌 ApoE-/- 小鼠中也发现了有争议的结果,尽管血浆总胆固醇(TC)上调可能是由于缺乏与无菌状态相关的内毒素。
有趣的是,肠道微生物群的缺失似乎减弱了长期膳食脂质消耗的致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具体而言,与传统小鼠相比,HFD 喂养的无菌 Ldlr-/- 小鼠的血栓大小显着减小。尽管无菌和常规 Ldlr-/- 喂食 HFD 小鼠的血浆 TC 水平没有差异,但与喂食的无菌小鼠相比,富含脂质的饮食仍然诱导无菌小鼠的 TC 水平(TC≈1.6 mg/dlx103)约两倍配合食物(TC≈0.8 mg/dlx103)。
相比之下,HFD 诱导常规小鼠血浆 TC 增加约 8 倍(TC ≈1.6 mg/dlx103) 与以食物喂养的小鼠相比 (TC≈0.2 mg/dlx103 )。在这项研究中也发现了 VLDL 的类似发现。富含脂质的饮食还加剧了 Ldlr -/-小鼠的微生物群失调,梭菌科、葡萄球菌科、芽孢杆菌科的丰度增加,乳酸杆菌科的丰度降低。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在晚期主动脉粥样硬化方面,无菌Ldlr-/-与常规小鼠之间没有发现显着差异。
总之,不同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对血脂代谢。这种影响对 CVD 发展是否具有保护作用或加重作用仍不清楚。这种差异可能取决于动物模型、动物年龄、饮食类型、喂养期以及住宿条件。未来的研究可以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以便进行更好的调查。
TMAO,是一种饮食诱发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微生物生物标志物。
★ 饮食-肠道菌群代谢物TMAO(三甲胺-N-氧化物)
这是一种从饮食营养素衍生的肠道微生物共同代谢物,十年前首次被发现并被报道预测CVD的风险。饮食前体磷脂酰胆碱、胆碱和L-肉碱通常存在于奶酪、红肉、海鲜、蛋黄和其他西式营养素中,主要由特定的肠道微生物酶代谢,产生高水平的三甲胺(TMA)。
具体而言,含有功能性微生物CutC/D基因的TMA裂解酶负责胆碱相关TMA转化。TMA进一步被血液吸收,并在肝脏中被黄素单加氧酶(FMO,主要是FMO3)氧化,生成TMO。
在人类肠道中发现了七种不同的表达TMA裂解酶CutC/D的菌株,包括:
此外,TMA可以通过微生物里斯克型左旋肉碱加氧酶CntA/B从左旋肉碱合成。
虽然CntA/B编码基因已在变形杆菌中鉴定,但尚未证明共生肠道微生物群形成依赖于L-肉碱的TMA。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两种细菌菌株Emergencia timonensis和Ihubacter Massilensis的新组合在肉碱转化的TMA积累中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
有趣的是,最近发现的细菌E.timonensis通过L-肉碱促进TMAO的产生→ γ-BB(γ-丁基甜菜碱,肉碱的前体)→ TMA→ TMAO途径。然而,与肉碱TMA转化途径相关的特定共生微生物群仍需进一步发现。
★ 饮食-微生物群衍生的TMAO在CVD发病机制调节中的作用
最初的研究表明,高胆碱或肉碱饮食饲养的小鼠循环TMAO水平升高,巨噬细胞泡沫细胞形成的增加和主动脉粥样斑块形成的增强(图1)。
相反,在无菌或抗生素治疗的ApoE−/−小鼠中,TMAO产生能力和胆碱或肉碱饮食相关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负荷分别被消除或抑制 (C57BL/6株)。有趣的是,ApoE−/− 研究发现,当从高TMA/TMAO产生的供体C57BL/6小鼠接受盲肠微生物群移植时,小鼠比从低TMA/TMAO产生的供体NZW/LacJ小鼠产生更高的胆碱饮食依赖性主动脉病变聚集。
类似地,在无菌小鼠体内移植产生高TMA的微生物可诱导血小板高反应性,并增强与高血浆TMAO水平相关的血栓形成。
因此,微生物群对于TMAO的产生是必要的,TMAO通过以下几种机制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
1)泡沫细胞形成
微生物群衍生的TMAO可以激活应激诱导的热休克蛋白(HSP)HSP70或HSP60的表达,这可能触发巨噬细胞中清道夫受体(例如SR-A1)和CD36的激活,以刺激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的摄取和泡沫细胞的形成。
2)炎症
TMAO通过激活Ldlr中的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和NF-κB信号通路,诱导促动脉粥样硬化炎症标志物表达,包括IL-6、环氧合酶2(COX-2)和细胞内粘附分子 Ldlr−/− 小鼠吃富含胆碱的食物。
循环TMAO的增加与促炎细胞因子TNF-α和IL-1β的升高以及抗炎细胞因子IL-10的降低有关。
3) 脂质代谢
TMAO可抑制胆固醇逆向转运(RCT),导致动脉胆固醇沉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4) 血小板高反应性和血栓形成
饮食诱导的高水平微生物TMAO可刺激血小板激活次最大刺激物,包括凝血酶、二磷酸腺苷(ADP)和胶原,并诱导细胞内钙的释放,导致血小板高反应性。
然而,一些研究显示了相反的结果,表明饮食中的TMAO、胆碱或肉碱不会诱发ApoE−/− 的动脉粥样硬化或者Ldlr−/− 小鼠模型。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居住条件和小鼠模型造成的,但确切的原因仍有待进一步发现。
最近证明,TMA(而非TMAO)降低了心肌细胞和血管平滑肌细胞的活力。在大鼠体内静脉注射TMA时,平均动脉血压显著升高,表明TMA对CVD有有害影响。
进一步证实TMA在CV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并验证相关机制,还需要进行更多的体内和体外研究。
图1 肠道菌群产生的膳食代谢物在心血管疾病发病中的潜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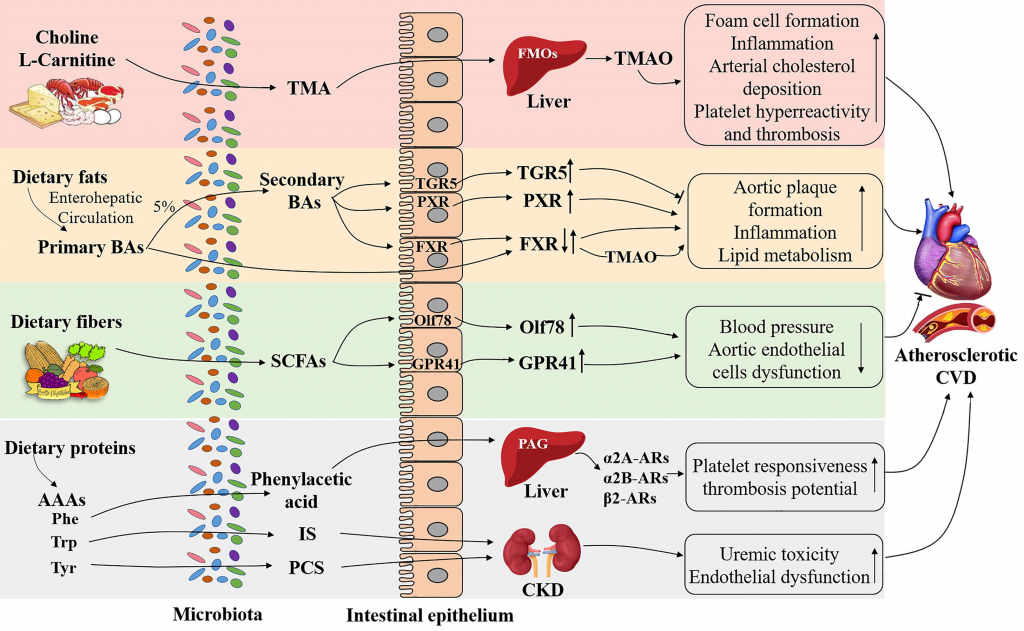
Xufei Zhang,et al., Comput. Struct. Biotechnol. J. 2022
★人体循环TMAO在心血管疾病预测和预后中的研究
大量人体研究已经证明肠道微生物衍生的TMAO在预测CVD风险中的作用。
最初的研究调查了1800多名受试者的人类队列,发现血浆TMAO升高与多种CVD亚型的发生有关,包括外周动脉疾病(PAD)、冠状动脉疾病和心肌梗死史。
在临床结果研究中,大量参与者表明,循环TMAO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事件死亡率和动脉梗死的风险增加呈正相关。在许多研究中,血浆TMAO的临界值超过6μM,以预测全因死亡率的风险,最近对10000多名受试者进行的荟萃分析提出,CVD预后的血浆TMAO临界值为5.1μM。
此外,已发现高水平的TMAO与人类队列中促炎性单核细胞和心血管风险的增加有关。
同样,一项系统回顾和剂量反应荟萃分析招募了13000多名参与者,发现血浆TMAO水平升高与炎症标志物C反应蛋白(CRP)升高之间存在非线性关联。然而,并非所有的人体研究都发现了类似的数据。例如,无症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和血液TMAO水平没有明显变化。然而,中风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表现出肠道微生物群的显著失调,但血浆TMAO水平降低。
相比之下,在一组35-55岁的参与者(n=817)中,在10年的随访中,TMAO浓度与动脉粥样硬化进展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TMA而非TMAO与高血压负荷和CVD风险因素有关,并与早期慢性肾病(CKD)受试者中Akkermansia属、粪杆菌属、Ruminococcus、Subdoligranulum的丰度降低有关。
然而,仍需对人类队列进行进一步研究,以调查TMAO前体TMA是否是早期CVD发病机制调节中被遗忘的毒素或预测因子。
胆汁酸(BAs)是羟基化和饱和类固醇,有助于乳化和肠道吸收膳食脂肪和脂溶性分子。
在人类肝细胞中,初级胆汁酸(胆酸和鹅去氧胆酸)由胆固醇通过催化酶合成,如胆固醇7a羟化酶(CYP7A1)、甾醇27羟化酶(CYP27A1)、氧化甾醇7a羟化酶(CYP7B1),其表达受肠道微生物群的调节。
然后,初级胆汁酸与甘氨酸或牛磺酸结合,95%以上的初级胆汁酸被重新吸收并再循环回肝脏。非再吸收的胆汁酸可通过催化酶胆盐水解酶(BSH)解结合,该酶由几种共生肠道细菌表达,包括革兰氏阳性双歧杆菌、梭菌、肠球菌、乳酸杆菌和革兰氏阴性拟杆菌。
除了去结合,肠道微生物如梭菌和真杆菌也是7-脱氢酶的来源,以生成次级胆汁酸,包括来自CDCA的石胆酸(LCA)和来自CA的脱氧胆酸(DCA)。
此外,胆汁酸的氧化和差向异构化是通过羟类固醇脱氢酶(HSDHs)催化的,这种酶已在各种细菌中发现,包括放线杆菌、变形杆菌、梭菌和其他细菌。
一旦微生物代谢的胆汁酸进入循环血液,胆汁酸受体就可以介导信号通路来调节宿主代谢,有助于CVD的发展。
最重要的胆汁酸受体之一是FXR,它是肝脏初级胆汁酸和肠道次级胆汁酸的主要传感器。FXR在调节脂质和葡萄糖代谢方面已被证实。
有趣的是,在动脉粥样硬化易感小鼠中FXR的激活在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形成中显示出保护作用。相应地,ApoE−/−中FXR的缺失导致脂质代谢缺陷的严重程度增加,主动脉斑块形成增强。相比之下,对FXR/ApoE或FXR/Ldlr双缺陷小鼠的其他研究显示主动脉病变和血浆LDL胆固醇降低。有趣的是,FXR还通过调节FMO3活性来调节TMAO途径。
另一个重要的胆汁酸受体是TGR5,通过继发性胆汁酸激活该受体,可通过减少斑块内炎症、斑块巨噬细胞含量和脂质负荷来减轻血管病变的形成。
PXR是另一种与胆汁酸代谢相关的核受体,由次级胆汁酸(如LCA)激活。
与其他受体相比,PXR的激活提高了脂蛋白VLDL、LDL和CD36的表达水平,从而聚集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中的ApoE−/− 小鼠,而PXR在载脂蛋白E中的抑制作用ApoE−/− 小鼠,通过减少巨噬细胞的脂质摄取和CD36表达减轻了主动脉病变区域。
尽管大多数关于胆汁酸在CVD发病机制中的研究都是在小鼠模型上进行的,但在临床队列中发现胆汁酸的循环水平与CVD表型相关。
例如,研究发现,人类受试者的初级和次级胆汁酸水平降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总体生存率降低。此外,较低的空腹血浆总胆汁酸与冠状动脉疾病、MI和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显著相关。
总之,肠道微生物群衍生的胆汁酸通过多种类型的胆汁酸受体调节CVD的发展,而血浆胆汁酸可能是CVD发生的另一个重要预测因子,仍需进一步研究。
短链脂肪酸是膳食纤维(主要是多糖)发酵的主要微生物产物,主要由乙酸盐、丁酸盐和丙酸盐组成。肠道微生物群的特定成员参与短链脂肪酸合成的特定发酵途径。
肠道微生物群调节富含纤维的饮食与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的保护性关联。具体而言,许多研究已经阐明了膳食纤维或短链脂肪酸在缓解高血压或其他CVD亚型中的功能作用(图1)。
其中一项研究发现,高纤维饮食和补充乙酸盐都可以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心肌纤维化和左心室肥厚,这与改善肠道失调和增加拟杆菌的数量有关。
类似地,丙酸盐治疗可保护小鼠免受高血压心血管损伤,而产丁酸盐的细菌(如Roseburia intestinalis)可减少主动脉粥样硬化病变面积。
研究发现,Olfr78和GPR41参与调节宿主血压和内皮功能。具体而言,丙酸盐通过调节Olfr78和GPR41表达的中断,在野生型小鼠中诱导急性低血压反应。然而,抗生素治疗Olfr78−/− 小鼠(而非野生型小鼠)血压升高,GPR41升高,与野生型小鼠相比,小鼠也有收缩性高血压。
此外,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乙酸盐和丁酸盐通过仅对丁酸盐进行GPR41/43激活,从而提高NO的生物利用度,从而改善大鼠主动脉内皮功能障碍。为了揭示短链脂肪酸在CVD发病机制中的机制作用,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 人类研究
在人类中,大多数关于CVD风险的研究都与短链脂肪酸相关的血压调节有关。早期临床干预研究发现,增加膳食纤维摄入量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降低有关。
在一项荟萃分析研究中也发现了粘性可溶性纤维对血压的类似保护作用。
相比之下,最近的一项干预研究报告称,高纤维高蛋白饮食可能通过上调循环短链脂肪酸水平增加CVD的风险。具体来说,高蛋白高纤维饮食诱导丙酸水平升高,这与LDL胆固醇和血压的上调有关;较高的丁酸水平与葡萄糖的上调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下调有关。然而,它仍然局限于短链脂肪酸对人类CVD风险或保护作用的直接证明,需要进一步澄清。
芳香族氨基酸(AAA)是含有芳香环的氨基酸,包括苯丙氨酸(Phe)、色氨酸(Trp)和酪氨酸(Tyr)。
芳香族氨基酸的主要来源是膳食蛋白质,如牛肉、猪肉、鸡肉或鱼。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了肠道微生物群产孢梭菌Clostridium sporogenes产生芳香族氨基酸代谢物的途径。
最近,几项研究发现,苯丙氨酸衍生的微生物代谢物苯乙酰谷氨酰胺(PAG)与主要心脏不良事件(如心肌梗死、急性缺血性中风或冠状动脉疾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具体来说,膳食中的苯丙氨酸通过富含porA基因的肠道微生物群转化为苯乙酸,随后在肝脏中转化为PAG。PAG进一步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包括α2A、α2B和β2肾上腺素能受体,以促进动脉损伤动物模型中的血小板反应性和血栓形成潜能。
同样,来自Trp的肠道微生物衍生代谢物吲哚硫酸酯(IS)和来自Tyr的对甲酚硫酸酯(PCS)也被确定为预测CKD患者CVD事件的有价值标记物。
这可能是由于IS和PCS通过诱导尿毒症毒性和内皮功能障碍而产生的有害影响。
然而,一些研究发现IS、PCS或PAG与CVD结果无关。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研究的阈值效应造成的。这些肠道微生物代谢物在心血管疾病进展中的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
健康饮食模式已被建议预防 CVD 进展(图 2),包括地中海饮食(Med-diet)、阻止高血压的饮食方法(DASH)和间歇性禁食(IF)等喂养模式。
图2 针对肠道微生物群的饮食干预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的潜在疗法


Xufei Zhang,et al., Comput. Struct. Biotechnol. J. 2022
★ 饮食类型
多项临床试验证实了地中海饮食对主要血管事件、冠状动脉事件、中风和心力衰竭的保护作用。这种效应与微生物群多样性和微生物代谢物短链脂肪酸的增加以及TMAO 和血浆LPS水平的降低有关。
然而直到最近,才发现地中海饮食的长期干预可以通过肠道微生物群调节来预防 CVD。
具体来说,地中海饮食的长期干预可以通过富含膳食纤维代谢物(如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和Bacteroides cellulosilyticus )显着改变整体肠道微生物组。
特别是,在没有普氏菌的情况下,地中海饮食对 CVD 危险因素(包括脂质代谢、炎症和葡萄糖稳态)显示出强大的保护作用。
尽管多项数据表明 DASH 饮食可以通过降低血压和血脂异常来改善心脏危险因素,仍然缺乏关于 DASH 饮食与 CVD 预防中微生物群改变之间直接联系的数据。
★ 喂养模式
间歇性禁食(IF)是一种重要的饮食喂养模式,是一种周期性能量限制的做法,可以通过改变肠道微生物群来降低CVD风险。
具体而言,自发性高血压卒中易感大鼠在IF干预50天后,肠道微生物群β多样性发生显著变化,这与通过调节胆汁酸代谢降低血压有关。这些发现已通过对GF大鼠的粪便移植得到证实。
此外,在8周内对患有IF的人群进行临床干预,显著改善了血管舒张参数,减轻了氧化应激、与微生物群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增加相关的炎症,并降低了血浆LPS。有趣的是,短期禁食5天也可以降低血压和体重,调节微生物群,包括脱硫弧菌科、阿克曼菌和瘤胃菌科。
★水果和蔬菜中的多酚
多酚是一大类常见于植物产品中的有机化合物,尤其是水果和蔬菜。超过90%的总多酚在小肠中不可吸收,并被大肠中的肠道微生物群进一步代谢。
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膳食多酚对肠道微生物群的修饰和CVD保护的作用。
白藜芦醇(在葡萄、苹果和浆果等水果中发现)已被确定通过下调TMAO水平和上调BAs合成来减轻ApoE-/-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而BAs合成与有益菌拟杆菌、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和阿克曼菌的丰度增加有关。
口服槲皮素(在洋葱、西兰花和西红柿等蔬菜中发现)可以抑制体重增加,改善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程度,降低胆固醇水平、致动脉粥样硬化溶血磷脂酰胆碱水平,减少革兰氏阴性菌疣状芽胞菌的丰度,同时增加微生物多样性。
在人类受试者中,富含多酚的饮食干预发现,饮食多酚可以显著增加微生物多样性和Ruminococcaceae,这些与心脏代谢危险因素(如血浆甘油三酯和大 VLDL 中的胆固醇)的改善有关 。
总的来说,水果和蔬菜中的多酚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潜在治疗干预措施,它们的部分保护作用可以通过肠道微生物群的修饰来介导。
关于多酚详见这篇文章:肠道微生物群与膳食多酚互作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是不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包括水溶性或不溶性形式,通常存在于水果、蔬菜、全谷物、坚果和豆类等中。
膳食纤维不能被小肠吸收,“喂养”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群,导致短链脂肪酸的多样性和产量增加。
如前所述,短链脂肪酸激活特异性受体,从而改善高血压和主动脉内皮细胞功能障碍。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鹰嘴豆膳食纤维提高了微生物多样性,增加了拟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相对丰度,并提高了丙酸水平。鹰嘴豆膳食纤维也可以通过对肠道微生物群进行类似的修饰来改善高血糖症。
全谷物燕麦还能降低血浆胆固醇水平,提高胰岛素敏感性,这与微生物群中有益乳酸杆菌的增加有关。同样,人类食用全谷物产品时,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较低,双歧杆菌含量较高。
关于膳食纤维详见这篇文章:你吃的膳食纤维对你有帮助吗?
益生元是植物源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成分,可刺激胃肠道中“友好”微生物的生长。
大多数益生元是膳食纤维,而不是所有膳食纤维都可以归类为益生元。常见的益生元包括低聚糖和多糖,如菊粉、低聚果糖、β-葡聚糖,它们通常能诱导肠道微生物群的特定修饰。
许多研究通过三个主要方面有趣地研究了益生元对宿主代谢的有益影响,以改善CVD状况(图2):
1)降低血脂
补充益生元纤维(例如菊粉)可以降低血浆胆固醇水平,并减少肝脏中的TAG积累;
2)减少内毒素血症和炎症
益生元低聚果糖可以增加双歧杆菌的数量,与血浆和脂肪组织中的内毒素血症和炎症呈负相关;
3)降低血压
补充富含益生元纤维的饮食可以通过GPR43信号通路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
益生菌被定义为“活的微生物,当给予足够的量时,会给宿主带来健康益处”。人类饮食中的大量发酵食品,如酸奶、酸菜、开菲尔、泡菜,都含有益生菌菌株。
作为益生元,益生菌菌株也被确定在更多方面防止CVD进展(图2):
1) 改善血管内皮功能
服用植物乳杆菌299v可改善冠心病患者阻力动脉的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同样,发酵乳杆菌CECT5716治疗可降低大鼠的血管氧化应激并改善内皮功能。
2) 降低血糖和氧化活性
益生菌酸奶的干预显著降低血糖,提高总抗氧化状态。
3) 降低胆固醇
补充长双歧杆菌BB536对降低总胆固醇、肝脏脂质沉积和脂肪细胞大小有显著效果。
4) 减轻内毒素血症和炎症
通过恢复肠道屏障功能,通过改善系统性内毒素血症诱导的炎症,口服粘液阿克曼菌已被证明可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此外,补充乳酸杆菌 L.reuteri V3401可降低炎症标志物水平,如TNF-α、IL-6、IL-8,这与降低CVD风险有关。
更多益生菌、益生元等介绍详见这篇文章:
如何调节肠道菌群?常见天然物质、益生菌、益生元的介绍
一些来自中药的天然成分也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群被用作潜在的CVD疗法(图2)。
小檗碱(BBR),一种生物活性异喹啉生物碱,广泛存在于各种中草药中并从中提取,已被证明具有许多有益的作用。
最近发现,高剂量的小檗碱不仅通过降低总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来改善脂质代谢,还下调促炎细胞因子TNF-α、Il-1β、Il-6和上调的抗炎性Il-10水平,这些水平与参与短链脂肪酸产生的Alistipes和Roseburia的丰度增加有关。
Roseburia菌 详见: 肠道重要基石菌属——罗氏菌属(Roseburia)
此外,BBR可以通过重塑肠道微生物群成分来抑制TMAO的产生,从而减轻胆碱诱导的动脉粥样硬化。
红曲米(RYR)可以通过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来缓解斑块的形成,而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与厚壁菌/拟杆菌的比例降低有关,同时也降低了黄曲霉和黄酮类提取物的丰度。
RYR干预还能改善肠道屏障功能,并通过TLR信号通路减轻炎症。
灵芝是一种药用蘑菇,通过降低携带内毒素的变形菌水平和增加有益细菌(包括梭菌和真杆菌),来减少肥胖、内毒素血症、慢性炎症以及恢复肠屏障功能。
肠道微生物群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着重要而复杂的联系。作为肠道微生物群中重要的调节剂之一,膳食成分可改变与全身内毒素、炎症、肠道屏障功能障碍以及脂质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微生物成分,从而增加CVD风险。
然而,更多的研究数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对饮食代谢在调节CVD发病机制中的主要作用包括:
1) 代谢饮食胆碱或L-肉碱以诱导TMAO的释放,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
2) 调节胆汁酸代谢,可能通过多种受体途径调节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
3) 产生芳香族氨基酸代谢物PAG、IS、IPA或PCS,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形成;
4) 发酵膳食纤维以产生短链脂肪酸,这对CVD的进展起到了一些有益的作用。
这些发现为开发CVD的新型潜在预防和治疗方法提供了一些极好的支持,例如可以通过健康饮食和喂养模式、含有健康膳食成分的饮食等干预措施改善菌群,从而预防改善CVD。当然也包括:来自水果和蔬菜的膳食多酚、膳食纤维和益生元、益生菌以及饮食中药等干预措施。主要参考文献:
Xufei Zhang, PhilippeGérard. Diet-gut microbiota interactions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omputational and Structural Biotechnology Journal. 2022,Mar: 1528-1540. doi: org/10.1016/j.csbj.2022.03.028
Safari Z, Gérard P. The links between the gut microbiome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Cell Mol Life Sci. 2019 Apr;76(8):1541-1558. doi: 10.1007/s00018-019-03011-w. Epub 2019 Jan 25. PMID: 30683985.
Bapteste E, Gérard P, Larose C,et al., The Epistemic Revolution Induced by Microbiome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View. Biology (Basel). 2021 Jul 12;10(7):651. doi: 10.3390/biology10070651. PMID: 34356506; PMCID: PMC8301382.
Tang WHW, Li DY, Hazen SL. Dietary metabolism, the gut microbiome, and heart failure. Nat Rev Cardiol. 2019 Mar;16(3):137-154. doi: 10.1038/s41569-018-0108-7. PMID: 30410105; PMCID: PMC6377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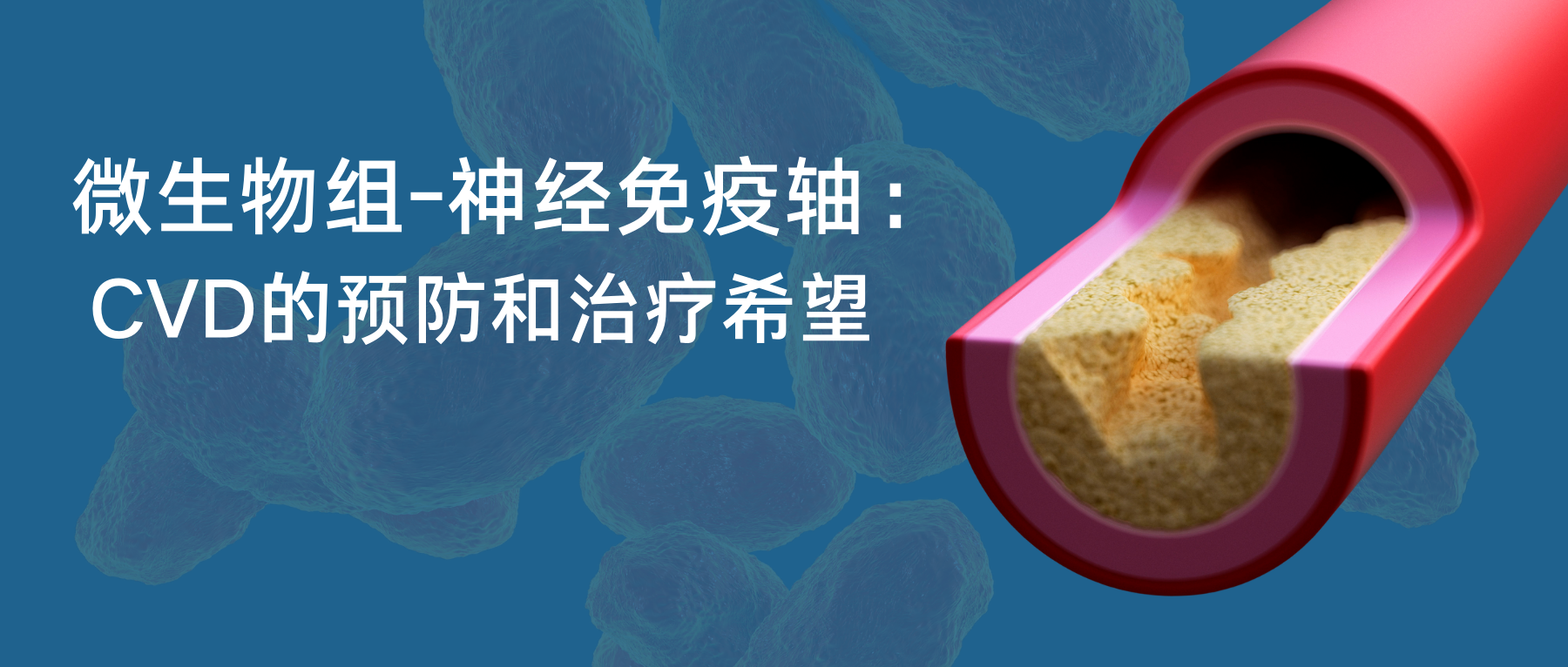
谷禾健康
神经免疫,菌群,心血管疾病
最新的《中国心血管病健康和疾病报告2019》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心血管病现患人数已达3.30亿,拐点尚未到来,且7-17岁儿童青少年高血压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
心血管疾病(CVD)仍然是全世界发达国家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此外,广泛存在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如代谢综合征、糖尿病、肥胖和性类固醇激素代谢紊乱,有效预防策略已成功减少急性心血管事件和死亡的影响。
大脑和其他器官系统之间的双向通信对于大脑健康和生物体的整体健康至关重要。曾经被认为具有免疫特权的大脑现在被认为是一个高度免疫特化的器官,拥有自己的大脑驻留免疫细胞。这些细胞形成神经元回路和淋巴系统,这些系统调节免疫细胞的复杂流出,以及从脑脊髓空间与循环的其余部分交换的液体。
而共生微生物群是个体间异质性的重要来源,可以通过调节宿主免疫来影响人类健康。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CVD 的许多潜在原因,包括免疫和肠道菌群失调可能是 CVD 的致病因素,提出了对新的免疫调节治疗策略的需求。
本文总结了免疫、炎症的神经调节以及肠道菌群如何参与 CVD 的发病和进展,并探索菌群-神经免疫通讯是否为 CVD 的潜在治疗靶点。
本文缩略词:
CVD: 心血管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 )
心血管疾病,又称为循环系统疾病,是一系列涉及循环系统的疾病,循环系统指人体内运送血液的器官和组织,主要包括心脏、血管(动脉、静脉、微血管),可以细分为急性和慢性,一般指心脑血管疾病。
ANS: 自主神经系统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自主神经系统是脊椎动物的末梢神经系统,由躯体神经分化、发展,形成机能上独立的神经系统,是外周传出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能调节内脏和血管平滑肌、心肌和腺体的活动,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不随意神经系统,故名自主神经系统(参考自:百度百科)。
SFO: 穹窿下器神经元 (Neurons of the subfornical organ )
穹窿下器官,室周器官,位于第三脑室前背侧壁、海马连合腹侧穹窿柱分歧处、适平室间孑L平面。
OVLT: 下丘脑终板血管区(Organum vasculosum laminae terminalis)
终板就是第三脑室前缘的隔膜。下丘脑终板血管区,内生致热原作用于血脑屏障外的脑血管区,即下丘脑终板血管区,该区位于第三脑室壁的视上隐窝处。
PVN: 下丘脑室旁核 (paraventricular nucleus)
下丘脑室旁核 位于第三脑室下丘脑部的上端两侧,呈长楔形轮廓,是下丘脑前区最显著的核团之一,与神经内分泌活动和植物性功能等有关的复合体结构,参与体内电解质与体液平衡,心血管活动调节及其它多项生理功能的调控。
NTS: 孤束核 (nucleus tractus solitarius)
孤束核为延髓内重要内脏感觉性核团,为一般内脏感觉和味觉传导通路上的第一级中继站。随着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孤束核的认识日趋深入,近年来HRP和ARG技术有关孤束核的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孤束核不但与低级中枢(脊髓、脑干)具有传入、传出神经联系,而且与高位中枢(前脑、小脑)也具有复杂的往返联系。
DMV:迷走神经运动背核 (dorsal nucleus of vagus nerve)
迷走神经背核是2014年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发布的人体解剖学名词。位于延髓室底灰质内,迷走神经三角深面的神经核。属一般内脏运动核,支配颈部、胸部所有内脏器官和腹腔大部分内脏器官的平滑肌、心肌的活动和腺体的分泌。
神经和免疫系统通常通过特定的大脑区域、传入和传出周围神经以及神经激素通路进行交流(下图)。
大脑和周围器官之间的通讯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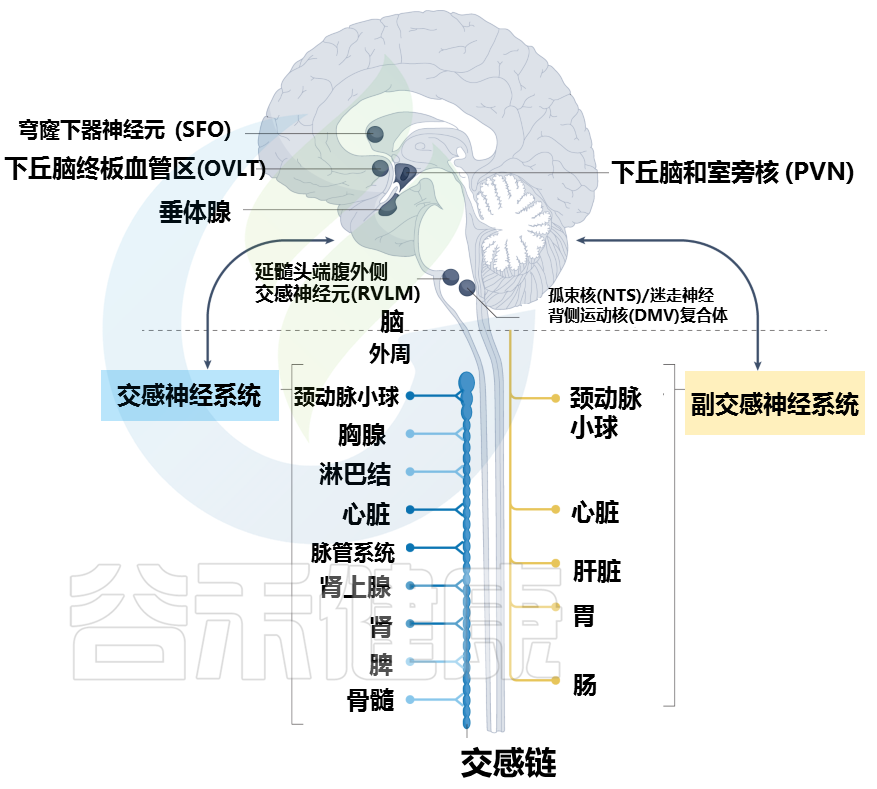
Carnevale D. Nat Rev Cardiol. 2022
大脑通过不同的途径与周围器官和组织相连。特定的大脑区域,统称为脑室周围器官,与周围形成自然的大脑界面,内衬有渗漏的血脑屏障。神经网络从脑室器官延伸到周围神经系统,并建立重要的神经解剖学连接。
穹窿下器官 (SFO) 和终板血管器官 (OVLT) 的神经元密集表达 1 型血管紧张素 II 受体和渗透压感受器,并为下丘脑的室旁核 (PVN) 提供神经支配。反过来,PVN 与延髓腹外侧 (RVLM) 的交感神经元相连,RVLM 具有调节外周交感神经活动的重要功能。
PVN 的其他神经元连接到孤束核 (NTS) 和迷走神经背运动核 (DMV) 的复合体,它们负责通过迷走神经传递的外周胆碱能神经支配。
所有主要的外周器官通常都有交感神经支配(包括心脏、脉管系统、肾脏和颈动脉体)和副交感神经支配(包括心脏、颈动脉体、肝脏、胃和肠)。
交感神经支配是免疫器官(以浅蓝色显示)和内脏组织的神经控制的主要途径。大脑、心血管系统和免疫器官之间的进一步整合轴是由神经内分泌系统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形成的。
循环物质,如细菌源性肽、宿主源性细胞因子和组织代谢物,向特定的大脑区域发出信号,这些区域的特点是存在渗漏的血脑屏障。
脑室周围器官由穹窿下器官(SFO)、终板血管器(OVLT)和末梢区组成,是监测周围组织并在神经免疫过程中发挥关键功能的大脑区域。同时,脑室周围器官在心血管疾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穹窿下器官富含血管紧张素II受体1型,它是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关键介质。
OVLT的神经元同时表达血管紧张素II受体1型和渗透压感受器,它们对感知细胞外钠/盐负荷浓度至关重要。
它们共同传递有关血容量、血压和细胞外液渗透压的外围信息。
有趣的是,从穹窿下器和OVLT投射到下丘脑室旁核(PVN)的神经元也被描述过,脑室旁核也接受后脑的投射,这表明它具有整合功能。虽然它们位于脑室周围器官之外,但孤束核(NTS)和迷走神经背侧运动核(DMV;心血管功能最有效的调节器之一)接收来自末梢区的输入。
大脑通过在脑室旁核和脊髓中间外侧细胞柱之间建立直接投射,或通过延髓头端腹外侧间接连接,来控制周围交感神经反射反应。外周的稳态扰动由延髓头端腹外侧感觉到,并通过蓝斑的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以反射反应传递。
作为补充,神经元表达细胞因子受体,这有助于神经免疫串扰和脑与身体的相互作用。
当细胞因子在各种生理和病理生理环境中的外周组织中分泌时,神经元活动就会改变。虽然神经元细胞因子受体的生理功能仍在研究中,但细胞因子在脑发育、外周组织损伤和动物行为方面的作用已被证明。这些观察表明存在由细胞因子介导的脑-体双向轴。
接下来进一步的讨论这些信号是如何在心血管疾病中启动、传播和转移到大脑的。
投射到中枢神经系统之外的神经被称为外周神经系统,它双向连接大脑和外周器官和组织。
外周神经系统分为两个部分:
躯体神经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ANS)
躯体神经系统与中枢神经系统交换感觉和运动信息,而ANS调节非自愿功能,并在神经免疫和心血管相互作用中起决定作用。
ANS由传入和传出神经元组成,将大脑与周围内脏器官和组织连接起来。历史上,ANS被定义为平行的交感和副交感臂,分别负责所谓的“逃跑或战斗”和“休息和消化”反应。
ANS作为大脑与外周沟通的关键途径的概念不断发展,有证据表明,ANS也发挥了神经免疫调停者的作用。生理和心血管反应的改变都受到ANS的深度影响,ANS的失衡是许多心血管疾病的典型特征。
我们对ANS如何调节心血管功能的理解有了实质性的进步,这得益于实验方法的发展,使直接分析神经系统活动成为可能。
实验性和临床性的显微神经学被用来测量指向心血管系统的节后交感神经传出的电活动。例如,骨骼肌血管的显微神经造影术成为评估人类区域交感神经活动的金标准方法。
应用于动物实验的类似程序有助于确定ANS调节心血管功能的解剖路线和分子机制。在过去5年中,已经制定了直接评估调节免疫系统的ANS臂的实验方案,从而能够定义神经免疫机制如何促进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进展。
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的进一步相互作用是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进行的,主要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进行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通常对心理压力敏感,是免疫反应和心血管功能的有效调节剂。
神经元顺行和逆行追踪技术已被用于通过周围神经系统的传入和传出臂绘制大脑和免疫器官之间的连接(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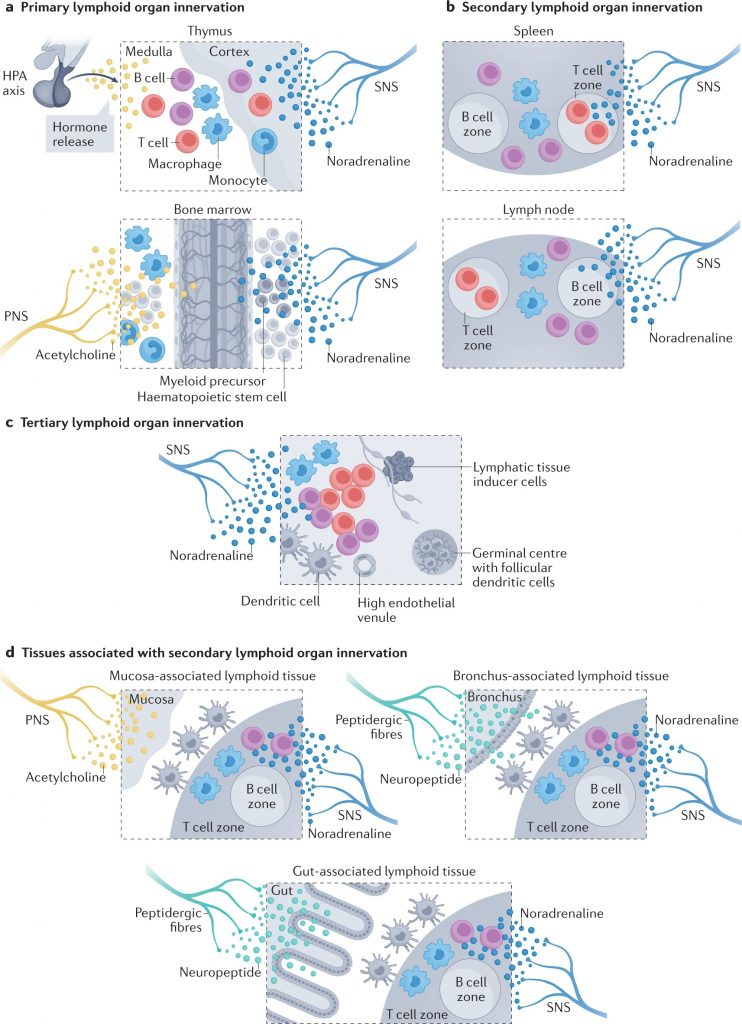

Carnevale D. Nat Rev Cardiol. 2022
a |初级淋巴器官神经支配。胸腺主要由去甲肾上腺素能纤维支配。虽然不存在直接的胆碱能神经支配,但交感神经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之间的相互作用已被证实。相反,骨髓神经支配更为复杂,包括交感神经系统(SNS)、副交感神经系统(PNS)和与大脑建立双向通讯的感觉纤维。骨髓的造血和免疫功能受到这种神经网络的严格调节。
b |次级淋巴器官包括脾脏和淋巴结,由去甲肾上腺素能纤维密集支配,其起源于大脑,已通过神经调节研究确定。淋巴结也有一个明显的感觉神经网络,可以严密监测外周免疫状态。
c |三级淋巴器官是为了应对非淋巴器官的病理挑战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的组织特异性组织。控制第三淋巴器官神经支配的神经纤维仅在少数解剖部位被发现。
d |粘膜相关淋巴组织在粘膜组织(如支气管或肠道)中形成,以响应稳态的扰动,并由神经网络严格控制,包括SNS、PNS和肽能感觉纤维。
神经元追踪确定外周器官神经支配路线
神经元连接性的研究需要对轴突进行双向追踪,包括从神经元细胞体到轴突终末的顺行追踪,以及从终末到胞体的逆行追踪。神经解剖学追踪是一种通过追踪神经元在突触前或突触后水平的连接来识别神经元的常用方法。神经解剖学追踪技术在确定包括免疫器官在内的外周器官的神经支配途径方面变得特别有用。
原始追踪研究的基础是将氟金注射到免疫器官中,使研究人员能够逆行识别节前神经元,或注射生物素化葡聚糖胺以顺行识别神经元连接。几十年来,这些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的示踪剂使研究人员能够研究连接大脑和周围器官的神经回路。
随后的技术进步利用伪狂犬病病毒(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神经营养性α疱疹病毒,Pseudorabies virus,PRV)的能力来定义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多突触回路。病毒的逆行扩散只发生在突触相连的神经元链中。在将伪狂犬病病毒注射到感兴趣的器官或组织后,更高阶的神经系统结构在稍后的时间点被标记。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定义神经元连接的精确路径,从外周器官开始,追溯到大脑。此外,伪狂犬病病毒在神经元细胞体中复制的过程具有自我放大的能力,这使得在受感染动物的大脑中识别二级、三级甚至四级神经元成为可能。
初级免疫器官包括胸腺和骨髓,它们参与淋巴细胞的产生和初始选择。胸腺在新生儿和青春期前发育阶段活跃,逐渐退化,只有残留的淋巴细胞生成持续到成年期。骨髓包含在骨腔中,从未成熟的造血祖细胞开始产生红细胞和免疫细胞。
胸腺神经支配和神经元调节
不同类型的细胞参与胸腺器官发生,这需要神经嵴细胞的协调相互作用。基于旧追踪技术的初步研究显示,交感神经纤维错综复杂,主要释放去甲肾上腺素,并在胸腺中形成血管周围神经网络。使用经典单突触逆行和顺行示踪剂的类似方法并没有识别胸腺的副交感神经支配。
后续的研究使用伪狂犬病病毒(PRV)的逆行跨神经元多突触追踪,来确定负责交感神经流出到胸腺的中枢神经系统区域。PRV感染的神经元分布在脊髓、延髓、脑桥、下丘脑室旁核、去甲肾上腺素能细胞A5组、延髓头端腹外侧核和中缝尾侧核。
值得注意的是,PRV感染的动物在DMV中没有PRV阳性细胞核,这与之前的观察结果一致,之前的观察排除了支配该区域胸腺的迷走神经纤维的存在。
虽然连接胸腺和大脑的硬连线路径的证明来自动物研究,追踪技术是可行的,但报告显示人类存在类似的胸腺神经支配模式,为这些发现提供了转化相关性。
神经样纤维和垂体激素通过人胸腺的免疫组织进行化学鉴定。胸腺糖皮质激素通过调节儿茶酚胺释放和肾上腺素受体表达,对胸腺细胞的存活和分化以及交感神经系统功能都很重要。相反,接受肾上腺切除术的动物胸腺去甲肾上腺素水平显著降低。
典型的感觉神经肽,如P物质和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已在胸腺中被发现,但没有明确的报告表明,这些神经肽可以为大脑提供感觉通路,这意味着交感神经支配可能是调节胸腺免疫功能的唯一神经通路。
骨髓神经支配和神经元调节
骨髓神经支配沿着主动脉传导,并通过血管丛穿透骨髓。实质以神经纤维树枝状排列为特征,末端靠近造血细胞和淋巴细胞。大多数纤维支配骨髓血管系统,但其他一些神经末梢支配实质性和血窦元素以调节造血和细胞迁移。
酪氨酸羟化酶是去甲肾上腺素合成的限速酶,存在于大动脉周围的所有神经中,并延伸至骨髓实质。除了主要的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支配外,还确定了神经肽Y的免疫反应性,从而表明骨髓的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支配和肽能神经支配是混合的。
在很久以前发表的研究中也检测到对 P 物质和 CGRP 呈阳性的神经纤维,但感觉神经元的功能直到最近才被发现。CGRP感觉纤维与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一起延伸到骨髓,在那里它们与酪氨酸羟化酶神经元合作,控制造血干细胞的动员。这些发现表明大脑通过硬连接的交感神经和感觉连接控制骨髓的免疫和稳态功能。
随后的研究还发现了支配骨骼和骨髓的副交感神经纤维。尽管在造血生态位附近检测到合成乙酰胆碱的胆碱乙酰转移酶的免疫反应性,但仅在骨中发现了明显的功能性副交感神经支配,其中胆碱乙酰转移酶调节骨重塑。
后来的研究表明,骨髓神经支配与昼夜节律密切相关。骨髓中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依赖于昼夜振荡,进而调节与控制白细胞和造血干细胞的保留和排出过程相关的基因表达。尽管这种构成过程在生理上是相关的,但神经介导的白细胞和造血干细胞转运的节律过程在疾病背景下可能特别重要。
未来的研究将有必要澄清清晨急性心血管事件的高发病率是否与神经调节白细胞和造血干细胞运输的影响有关。
次级淋巴器官包括淋巴结、脾脏和与粘膜相关的淋巴组织,通常由交感神经和感觉神经支配。
淋巴结神经支配和神经调节
淋巴结的结构包括血管系统和淋巴管,它们穿透髓质实质,在 T 细胞区域中被复杂的去甲肾上腺素能纤维网络缠绕。相比之下,富含B细胞的生发中心缺乏神经支配。
在稳定状态下,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依赖于昼夜节律的激活,进而通过β2-肾上腺素受体信号调节淋巴细胞的生理日常再循环。
通过使用各种技术,从整体免疫标记到逆行神经元追踪、单细胞基因组学和光遗传学,研究人员发现了支配淋巴结的独特感觉神经元阵列。将腺相关病毒注射到淋巴结后,四种类型的神经元被追溯到背根神经节。对这些不同的神经元群体进行的单细胞RNA测序确定了肽能伤害感受器的密集表达,形成了与大脑的双向通讯途径,并持续监测周围免疫环境。
脾神经支配和神经调节
脾脏是最大的次级淋巴器官,监测血液传播的物质和抗原。脾脏主要由去甲肾上腺素能脾神经支配,通常通过神经信号调节免疫功能。
脾神经从腹腔神经节分支,从脾门进入脾脏,沿着脾动脉外侧走行。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分布穿过边缘区,伸入白髓,在白髓中,T细胞、B细胞和树突状细胞附近可以发现神经末梢。相反,红髓的神经支配似乎稀疏而分散。通过组织学和追踪的方法,在脾脏中没有发现直接的胆碱能神经支配。
白髓,位于脾脏内部,包含着一种特殊的白细胞,这些细胞聚集在血管周围,当血液流过脾脏的时候,白髓中的淋巴细胞辨认并吞噬掉任何侵入的细菌和病毒,以此方式过滤人体血液,防止机体被病菌感染。
红髓,动物体内最大的淋巴器官。位于左上腹胃的背面,胃与膈之间,呈内侧向内凹陷的扁椭圆形或条索状等。
一项使用完整全组织3D成像的研究提供了有关脾脏神经支配的额外信息。实质内交感神经支配的结构被揭示为圆锥状结构,这在其他免疫器官中是不存在的,这表明独特的神经调节功能发生在脾脏中。
在脾脏中发现了具有独特特征的神经胶质细胞,这又增加了复杂性。自主神经支配通常包含非髓鞘神经胶质细胞。虽然神经胶质细胞在由周围神经系统支配的内脏器官中的特定功能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它们在免疫器官中的存在可能在神经细胞和免疫细胞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使用逆行示踪剂和后来的跨神经元多突触PRV追踪的研究明确证明,脾脏神经支配完全是去甲肾上腺素能的,起源于腹腔神经节。
通过对脾脏注射PRV后较长时间点的分析,确定了脑干、桥脑和下丘脑的运动前脑核团。随后,光遗传学领域出现了一种追踪神经元回路的完全创新工具,它在功能上映射直接投射到腹腔神经节的DMV胆碱能神经元。
当DMV神经元被光激活时,会诱发脾神经放电,从而直接证明腹腔迷走神经和脾神经之间的解剖联系。
粘膜相关淋巴组织神经支配
身体内的粘膜,如呼吸道和胃肠道的粘膜,有分散的粘膜淋巴组织区域,这些区域共同构成了最广泛的淋巴组织,这些区域统称为粘膜相关淋巴组织,保护机体免受各种挑战。
虽然传统的次级淋巴器官是在胚胎发生过程中发育起来的,但淋巴滤泡,如支气管相关淋巴组织或肠道相关淋巴组织,在出生后会因炎症或感染而聚集。尽管如此,这些异位淋巴组织与传统淋巴组织在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粘膜相关淋巴组织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广泛的神经支配。早期研究描述了支气管相关淋巴组织和肠道相关淋巴组织的交感神经和肽能神经支配,这些淋巴组织含有大量神经肽,如P物质、血管活性肠肽和生长抑素。通常情况下,神经纤维沿着小血管排列,然后在与淋巴细胞接触的粘膜组织的实质中分支,在含有T细胞的区域,神经占优势。
随后的研究通过专门检测和解码各种有害外周刺激的伤害感受器,确定了粘膜相关淋巴组织神经支配的感觉通路。
支配肠道相关淋巴组织的伤害感受器感知胃肠道的扰动,并建立具有保护功能的神经反射。虽然肠道相关淋巴组织的感觉神经支配在抵御微生物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对心血管疾病中肠道神经系统的影响仍不清楚。
支气管相关淋巴组织的神经支配作用研究较少,但交感神经、胆碱能神经和感觉神经纤维已被确定。
三级淋巴样器官是指在成年期由淋巴样新生在随机、典型的非淋巴样和非粘膜部位形成的淋巴样组织,以应对慢性炎症。这些组织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微生物感染、慢性同种异体移植排斥反应、癌症甚至动脉粥样硬化中都被观察到。
在几种转基因小鼠模型中诱导第三淋巴器官,可以表征炎症细胞因子和淋巴趋化因子的模式,这些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是其发育和调节所必需的。
虽然已经描述了三级淋巴器官的形态、细胞和血管成分,与第二淋巴器官(如B细胞和T细胞室的独特组织、含有滤泡树突状细胞的B细胞滤泡和生发中心)有相当大的相似性,他们在疾病进展中的参与是有争议的,并且仍然是研究的主题。
例如,在微生物感染期间,三级淋巴样器官会在局部保留病原体,从而阻碍它们进入生物体的其他部位。相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进展可能因同时存在三级淋巴器官而加剧。通过选择性地去神经支配肠道交感神经或胆碱能神经,迷走神经在三级淋巴器官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已在实验性结肠炎中得到证实。目前还尚不清楚ANS是否有助于其他器官中第三淋巴器官的发育、组织和功能。
神经免疫相互作用是对挑战体内平衡的应激源做出快速反应的基本适应机制。这一概念首次出现时,脾脏神经支配在细菌内毒素血症(对身体最危险的疾病之一)期间被观察到具有保护功能。
去甲肾上腺素能纤维和淋巴细胞之间的直接神经免疫相互作用被描述,同时确定在脾脏中引起去甲肾上腺素能放电的神经回路,该回路在抑制脂多糖诱导的细胞因子负荷和对抗感染性休克方面有效。
神经免疫相互作用已被确定为心血管危险因素和心血管疾病病理生理学的潜在机制。
神经免疫相互作用促进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发生及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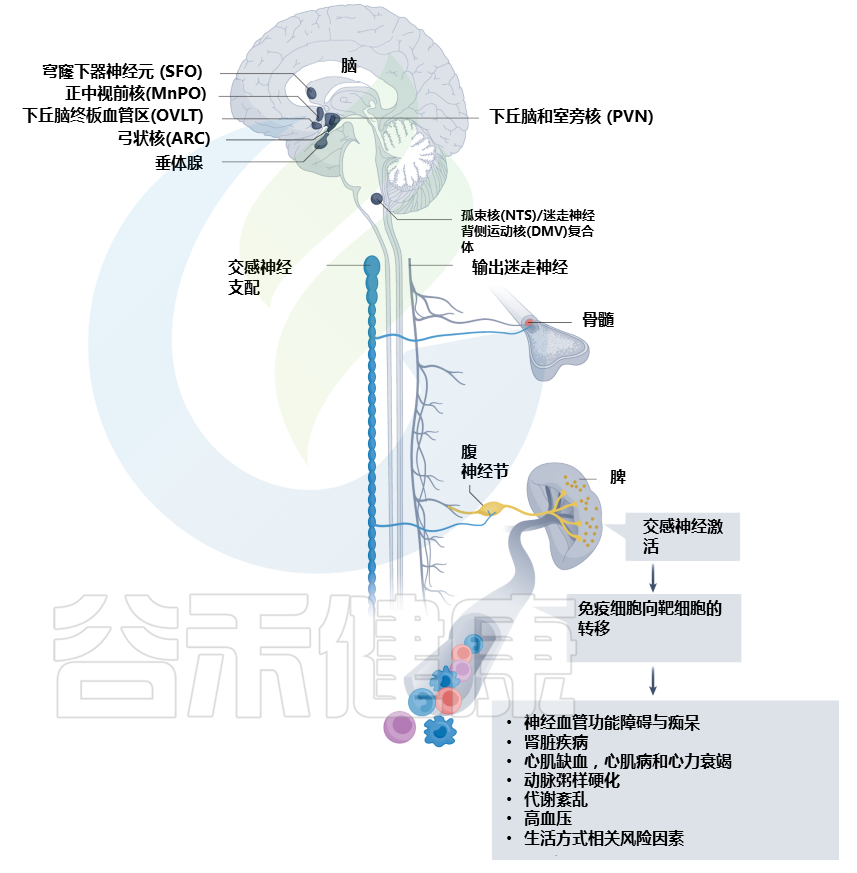
Carnevale D. Nat Rev Cardiol. 2022
大脑中的环室器官被心血管系统的挑战激活。通过一系列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的解剖连接,大脑在免疫器官中建立神经反射来控制和调节免疫功能。心血管危险因素,如高血压、代谢紊乱和动脉粥样硬化,是常见的神经免疫机制改变的基础。心血管疾病,例如心肌缺血、压力过载心肌病、心力衰竭、肾脏疾病和神经血管功能障碍,其特征在于受影响的心血管组织中局部和免疫器官中的神经免疫改变。ARC,弓状核;DMV,迷走神经背运动核;MnPO,正中视前核;NTS,孤束核;OVLT, 终板的血管器官;PVN,下丘脑室旁核;SFO,穹窿下器官。
高血压
与高血压相关的炎症和免疫反应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然而,这些过程大多被认为是高血压导致靶器官损害的结果。
免疫系统在高血压中的机制作用的第一个证据,来自缺乏 T 细胞和 B 细胞且典型的高血压刺激不会增加血压的Rag1 -/-小鼠的研究。通过过继转移重建Rag1 -/-小鼠中的 B 细胞或 T 细胞池,这项研究表明,血管紧张素II或脱氧皮质酮醋酸盐(DOCA)仅在小鼠具有成熟 T 细胞时才会诱发高血压。
随后大量研究调查了特定的T细胞亚群是否对高血压的发展至关重要,发现血管紧张素II给药不会增加Cd8 -/-小鼠的血压,但会增加Cd4 -/-小鼠的血压。免疫系统在血压升高中所起作用的细胞和分子机制仍有待研究。
与血压稳态有关的基本生理变量,如血管张力和肾脏钠排泄,依赖于严格的神经控制。因此,神经调节系统、免疫器官和心血管功能之间建立的关系值得研究。
重要的研究揭示了大脑和免疫系统之间的联系可能对高血压至关重要。首先,在动物模型中,脑室内注射血管紧张素II可通过交感神经系统诱导外周细胞因子的释放。此外,选择性的脑室周围器官损伤阻碍了小鼠对血管紧张素II的典型血压升高反应。
有趣的是,脑室周围器官受损的小鼠无法激发T细胞并促进T细胞在血管系统中的浸润,这表明高血压患者的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存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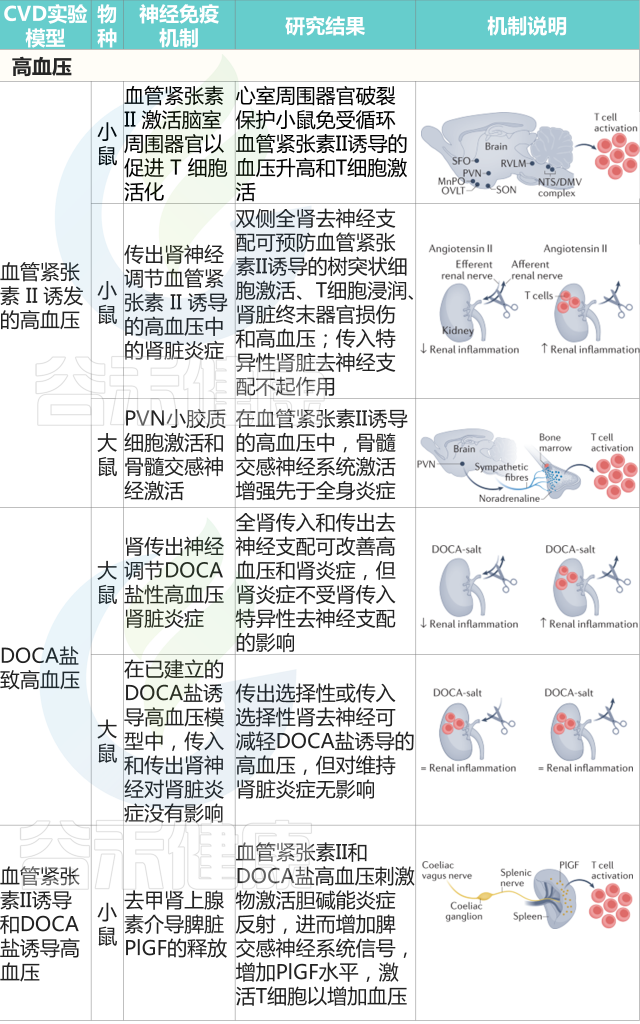

Carnevale D. Nat Rev Cardiol. 2022
高血压患者免疫系统的直接神经控制随后被证实。利用小鼠脾神经的显微神经学检查,血管紧张素II和DOCA盐均能增加神经放电,促进脾脏中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选择性脾脏去神经可防止血压升高以应对任何一种高血压刺激,脾切除术也重现了这一效应。
逆行追踪法,加上在测量脾神经放电时进行的选择性去神经手术,阐明了腹腔迷走神经输出是由高血压刺激激活的节前神经元。
在分子水平上,脾脏中的去甲肾上腺素释放是促进胎盘生长因子激活所必需的,胎盘生长因子是一种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家族的血管生成生长因子,也具有对血压升高至关重要的免疫调节功能。
高血压患者的神经免疫另一个相互作用的水平被称为双向脑-骨髓轴,即骨髓中交感神经流出增加先于全身炎症。
有关高血压患者肠道失调的证据正在迅速积累,来自小肠的激活免疫细胞已被证明与血压升高和大脑靶器官损伤有关。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存在相反的途径,即神经信号控制与高血压发病和进展相关的肠道和免疫机制。
动脉粥样硬化
脂质在动脉壁的积聚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并伴随着免疫细胞的进行性浸润,导致斑块的形成。这一过程以慢性低度炎症为特征,逐渐增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大小并导致动脉阻塞。
尽管有很多工作研究了导致斑块形成和决定斑块稳定性的机制,但神经免疫通讯的潜在作用才刚刚开始研究。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没有神经支配,但在斑块形成和进展过程中调节免疫反应的神经线索已被确定。Netrin 1首先被确定为指导轴突生长锥的神经信号,在人和小鼠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的巨噬细胞中也发现了Netrin 1,它通过趋化因子驱动的迁移过程抑制巨噬细胞的排出。
巨噬细胞中的Ntn1缺失阻碍了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促进巨噬细胞从斑块中流出。
另一种蛋白质通常存在于神经元中,与胆碱能途径有关,可调节高胆固醇血症Ldlr–/–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过程。在骨髓来源的细胞中,编码α7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α7-nAChR)的Chrna7被切除会恶化小鼠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特征是存在α7-nAChR+免疫细胞,表明该受体的通用相关性。
对受动脉粥样硬化影响的动脉周围三级淋巴器官的鉴定表明,神经机制可能与这些淋巴聚集相互作用,以控制和/或调节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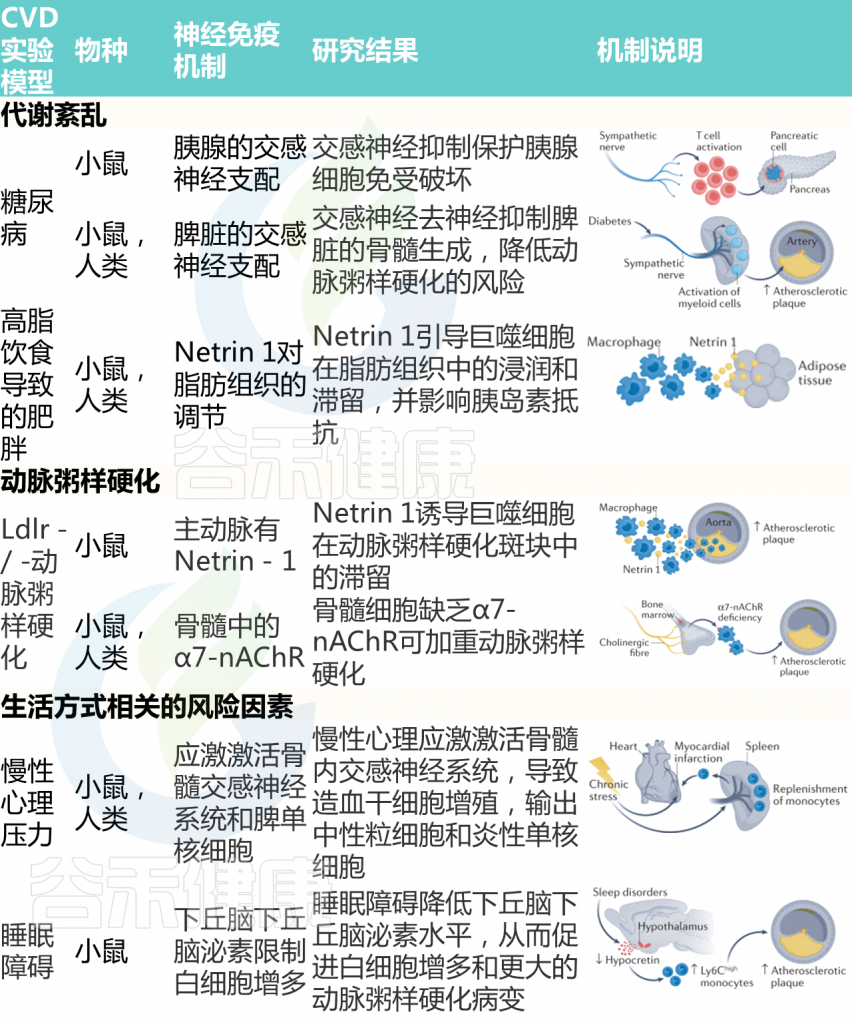

Carnevale D. Nat Rev Cardiol. 2022
代谢紊乱和肥胖
代谢综合征通常指可能单独或合并发生的一系列疾病,总体上增加了CVD的风险。除了血压升高,通常还包括高血糖和肥胖。
已知ANS失衡和免疫系统激活是代谢综合征的特征。在小鼠中发现了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的神经免疫机制。由CD8+T细胞介导的对胰腺β细胞的攻击诱导,糖尿病的发病取决于完整的胰腺神经支配的存在。
事实上,6-羟基多巴胺的化学消融或去甲肾上腺素能胰腺纤维的手术去神经支配阻碍了这些小鼠糖尿病的发病。在分子水平上,这种效应是由α1-肾上腺素能受体信号诱导的,因为使用哌唑嗪而不是普萘洛尔可以重现胰腺去神经支配的保护作用。
神经信号还可以控制与高脂饮食诱发的肥胖相关的糖尿病。患有肥胖症的小鼠和人类的脂肪组织被免疫细胞密集浸润,这些细胞导致脂肪组织炎症和胰岛素抵抗。
值得注意的是,脂肪组织中存在神经免疫指导线索netrin 1,这表明netrin 1可能调节巨噬细胞向脂肪组织的动员。此外,选择性缺失小鼠造血细胞中的Ntn1可有效促进巨噬细胞从脂肪组织中排出,减少炎症,并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这些发现确定了靶组织中的神经免疫相互作用,但免疫器官的神经控制也参与了疾病相关炎症状态的系统调节。例如,由脾交感神经驱动的神经通路已被确定为糖尿病的关键。通过手术或使用6-羟基多巴胺实现的选择性脾脏去神经支配,阻碍了糖尿病小鼠的过度脾脏骨髓生成。
一种连接大脑和脂肪组织的新型神经免疫途径已经被描述。在小鼠的脂肪间充质细胞附近发现了交感神经,交感神经控制着一个特定免疫细胞亚群的活动:2型固有淋巴细胞。
反过来,2型固有淋巴细胞通过释放神经营养因子来调节脂肪组织的稳态和肥胖。重要的是,通过在小鼠身上使用逆行追踪技术,结合外科手术和化学遗传学操作,定义了一个新的神经回路,通过交感主动脉-肾回路将脂肪组织中的2型固有淋巴细胞连接到高阶脑区,如室旁核。未来的研究应该调查这种新发现的神经免疫回路是否与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的心血管并发症有关。
生活方式相关的危险因素
众所周知,生活方式相关的风险因素对CVD的发病率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免疫系统构成挑战。此外,心理或身体上的应激状态与ANS的紊乱有关。对生活方式相关风险因素对心血管系统有害影响的潜在相关神经免疫相互作用的研究可以揭示创新的治疗机会。
正如在人类身上经常观察到的那样,慢性应激状态会增加小鼠的血压。值得注意的是,Rag1–/–小鼠对应激诱导的高血压具有抵抗力,并能减轻靶器官损伤。
除了血压升高,慢性应激还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肌梗死的易感性。经过反复和各种应激性挑战的小鼠显示出造血干细胞增殖增加,导致产生高水平的促进疾病的炎性白细胞。这种效应是由骨髓交感神经纤维释放的去甲肾上腺素增加介导的,而去甲肾上腺素又反过来调节造血干细胞增殖、中性粒细胞和炎性单核细胞的排出。
睡眠障碍对心血管健康构成了重大挑战。小鼠正常睡眠节律的改变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与过度造血和促炎性单核细胞积聚有关。
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发现,睡眠碎片化可下调小鼠130的下视黄醇水平。下视黄醇是一种下丘脑神经激素,在控制睡眠、觉醒和觉醒方面具有重要功能。鉴于下视黄醇通过减少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1的产生来限制骨髓生成,睡眠不良引起的下视黄醇水平降低与白细胞增多有关。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定期的体育活动,可以降低患CVD的风险。尽管许多观察分析都支持这种关联,但很少有机制研究调查这种有益关系的根本原因。有趣的是,习惯性自愿性跑步会降低小鼠的造血活动。在动脉粥样硬化小鼠中,运动抑制了慢性白细胞增多,但不影响紧急造血。通过降低脂肪-瘦素水平,这种效应促进造血生态位静止,改善心血管炎症和预后。
心肌缺血、心肌病和心力衰竭
ANS通过控制血管张力和各种心肌细胞特性,如收缩力、传导和频率,调节心脏功能。交感神经流出增加是慢性心力衰竭不良后果的最强预测因子之一。此外,非心肌细胞,尤其是常驻和非常驻免疫细胞,在应对各种挑战的心脏重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神经、免疫和心脏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值得研究。
急性缺血性心脏损伤通过增加骨髓中的交感神经信号与脾髓样细胞的生成增加有关。从脾脏部署的一部分单核细胞积聚在缺血心肌中,并参与心脏重塑。心-脾轴也被发现参与慢性心肌缺血的长期免疫反应,这总体上有助于不良的心脏重塑。脾脏的神经控制是否与这些表型有关仍有待阐明。
慢性高血压和肾功能衰竭会对心肌造成压力或容量过载,如果没有得到充分补偿,最终会导致心力衰竭。
在舒张功能不全的小鼠中,由于单核细胞募集和骨髓和脾脏造血增加,心脏巨噬细胞的数量增加。当巨噬细胞进入心肌时,会产生促纤维化细胞因子IL-10,进而促进胶原沉积和心肌僵硬,进一步加重舒张功能损害。
然而,其他巨噬细胞群体可以通过依赖于多器官相互作用的机制,促进慢性压力超负荷的适应性重塑。受到横向主动脉收缩以诱导心脏压力超负荷的小鼠增加了肾交感神经流出,由此去甲肾上腺素刺激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分泌,并对心脏巨噬细胞产生旁分泌作用。这项研究表明,心肌对慢性压力超负荷的适应取决于肾脏和心脏的神经和免疫反应之间的整合。
随后的研究阐明,心肌在稳定状态下含有大量不同的免疫细胞,对挑战的反应取决于常驻和招募的免疫细胞群体之间的整合。
鉴于ANS通过从颈上神经节、星状神经节和胸上神经节分支的纤维直接支配心肌,可以想象,参与心脏重塑的免疫反应的神经调节可能发生在心脏局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颈上神经节的去神经支配对心肌缺血引起的急性心脏重构没有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一过程减少了炎症浸润,减轻了心力衰竭。
肾脏疾病
肾钠处理、肾素分泌和肾血管张力受ANS的严格调节。肾传入和传出神经支配构成了最广为人知和研究最广泛的心血管反射系统之一。此外,炎症和免疫浸润通常伴随肾脏疾病。
急性肾损伤或慢性肾脏疾病均可导致肾功能衰竭,总的来说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促炎症环境和ANS平衡改变是肾病的特征,但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刚刚开始澄清。
已经证实神经免疫调节在急性缺血再灌注反应中对肾损伤的重要作用。当用能引起胆碱能炎症反射的胆碱能激动剂进行预处理时,患有双侧肾缺血-再灌注或细菌内毒素血症的啮齿类动物对肾损伤的敏感性较低,这意味着神经反射调节由不同原因引起的肾损伤引起的炎症过程。
鉴于在类似的肾缺血再灌注损伤小鼠模型中,通过超声激活胆碱能炎症反射通过抑制炎症减轻了结构和功能损伤,该发现具有转化相关性。
2021发表的一项研究确定在小鼠急性肾损伤期间连接肾脏、大脑和脾脏的神经通路。通过光遗传学,迷走神经的传出或传入纤维被选择性地刺激,表明两者都对肾脏损伤有保护作用。通过激活传入的顺行感觉纤维,可以描绘出从肾脏追溯到延髓头端腹外侧的神经回路,以补充迷走神经-脾反射。
肾脏也是高血压损害的主要目标,这是心血管疾病不良后果的一个强有力的独立风险因素。浸润肾脏的活化免疫细胞和ANS失衡是高血压性慢性肾病的特征。
在动物模型中,肾脏去神经支配可有效对抗过度的肾交感神经流出和血压升高,并抑制T细胞聚集和由此引起的炎症反应、肾纤维化和蛋白尿。
在分析传入和传出肾神经支配的差异贡献时,在DOCA盐大鼠中,传入特异性肾去神经支配降低动脉血压和交感神经活动的程度与总(传入+传出)肾去神经支配的程度相同,但对血管紧张素II诱导的高血压没有影响。
有趣的是,在随后的一项研究中,同样的研究人员对已建立高血压和肾炎症的DOCA盐大鼠进行了传入特异性或全肾去神经支配。在这些动物中,虽然传入特异性和全肾去神经支配在降低血压方面仍然轻微有效,但两种治疗均未显着改变已确立的肾脏炎症。
总之,这些研究表明,肾神经(传入神经和传出神经)和炎症在高血压和肾脏炎症的发病机制中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在确定高血压后,去肾神经支配不是抑制炎症过程的有效治疗,是通过其他机制维持的。
内脏器官炎症由ANS调节的观察可以追溯到之前研究肾传入和传出神经支配的作用。
一项初步研究表明,肾脏去神经支配可有效预防大鼠实验性肾小球肾炎,从而减少蛋白尿、系膜血管溶解、肾小球胶原沉积和转化生长因子-β的表达。这些数据表明,来自肾脏神经输入的信号分子可能在各种疾病环境下引发肾脏炎症和纤维化,进一步导致终末器官肾损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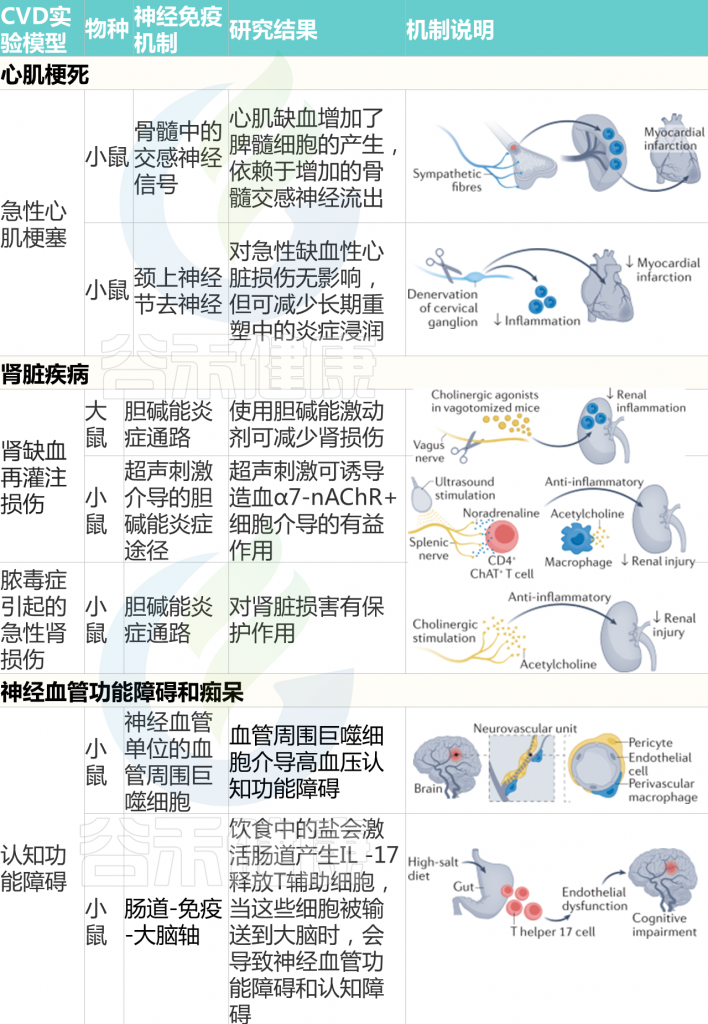

Carnevale D. Nat Rev Cardiol. 2022
神经血管功能障碍和痴呆
大脑由于没有能量储备,一直依赖于通过循环提供的营养,必须根据动态区域激活来适应其需求。因此,大脑对循环系统的改变特别敏感。
多种细胞类型构成脑实质和血管周围组织,包括免疫细胞。正如在其他器官和组织中观察到的那样,大脑中含有常驻免疫细胞(主要是小胶质细胞和血管周围巨噬细胞),当挑战干扰血脑屏障通透性时,这些细胞可以与招募的免疫细胞相互作用。
心血管风险因素会影响血脑屏障的完整性,改变脑血管内稳态,增加患痴呆症的风险。在小鼠和人类中,高血压会导致进行性脑血管损伤,并伴有典型的认知障碍症状。
免疫系统在高血压发病中的作用已得到明确证明,但免疫细胞如何参与高血压诱导的脑损伤才刚刚开始研究。
血管紧张素II诱导的高血压小鼠脑血管周围巨噬细胞的耗竭抵消了血管氧化应激和神经血管损伤,表明免疫的关键作用。
相反,在小鼠中,募集的免疫细胞会导致由血管危险因素(例如过度盐摄入)引起的脑损伤。脑血流、内皮功能和认知能力的损害取决于T淋巴细胞产生的IL-17,而IL-17是通过摄入肠道中的盐激活的。随后的一项研究还阐明了辅助性T淋巴细胞17对大脑有害影响的机制,表明肠道免疫轴对神经的调节非常关键。
外周神经系统的解剖结构和组织结构对轴突亚群的选择性和精确治疗提出了挑战,轴突亚群在特定器官中发挥独特的调节功能。因此,研究人员试图开发出越来越复杂的电极,以刺激更靠近目标组织的较小神经。这种方法有助于获得有关生理学和疾病中免疫神经调节的病理生理学基础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靶向脾神经并直接测量其活性的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能够确定该免疫器官是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之间串扰的中枢介质。相反,选择性去神经提供了有关该通路在CVD发病和进展中的相关性的机制信息。
研究表明,ANS调节免疫功能的功能障碍是心血管风险和CVD进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免疫器官自主神经外流的靶向调节是将这些发现转化为患者治疗的一种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神经免疫通讯的机制研究被认为与一系列临床条件有关,如克罗恩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所有这些都涉及免疫和炎症过程的失调。在临床前模型以及随后的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类临床试验中进行了探索,以非侵入性方式针对神经免疫机制的可能性也可能成为CVD的一种可能性。
对心血管疾病中调节免疫反应的神经通路的分子和电生理成分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为创新疗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能够对涉及心血管疾病的神经免疫反射进行精细调节的工具将有助于设计针对组织靶向免疫调节作用的策略,而不会增加感染风险或导致其他不良反应的普遍免疫抑制。根据特定疾病的特定背景和炎症环境,可以通过设计对腹腔迷走神经传出神经的生物电子刺激的选择性模式来微调脾脏的迷走交感神经激活。迄今为止,只有临床前工具已被开发并证明可有效调节免疫细胞从脾脏排出的过程。相反,通过手术切除腹腔神经节或热消融脾动脉周围的交感神经纤维,可以减弱脾交感神经流出的过度激活。
到目前为止,迷走神经刺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使用颈部植入装置,这些装置会触发传出和传入神经通路的混合,并产生潜在的不良影响。因此,尽管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临床试验中取得了有希望的结果,但迷走神经刺激方案具有引起脱靶刺激的局限性。
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已经实施了改进的实验性迷走神经刺激方案,以选择性地刺激腹腔传出迷走神经并诱发脾神经流出。有趣的是,一系列研究提供了交感神经介导的脾神经控制的证据。特别是,通过腹腔神经节与脾神经相连的内脏神经已被证明可调节脾介导的炎症反应。具体作用是整合的还是单独作用的,取决于具体的病理生理学背景。
对腹腔迷走神经刺激后的脾脏免疫细胞的分析显示,特定的生物电子调节模式促进选择性T细胞亚型的排出,这表明可能会发展出靶向免疫调节。
使用活体和离体制剂对小鼠、大鼠、猪和人脾神经进行神经解剖学和功能比较,表明将临床前发现转化为临床相关工具的可行性。然而,尽管这种方法需要在实验模型中进行进一步研究,以揭示CVD中神经免疫通讯的病理生理学基础,但临床应用可能会受到该过程侵入性的限制。
肠道微生物群决定下丘脑-垂体系统的激活水平。特别是,肠道微生物群是心血管疾病发病机制中神经免疫介质的重要来源。
心肌缺血、心肌病和心力衰竭
与 CVD 相关的压力通过激活 ANS 的交感神经分裂来影响整个生物体,包括胃肠道。在 ANS 的影响下,肠道内微生物群的血液供应减少,从而降低了消化腺的活动,胃肠道的肠道蠕动减慢。上述机制决定了由于 CVD 相关应激导致的肠上皮细胞的进一步紊乱。
CVD相关应激期间肠道上皮损伤的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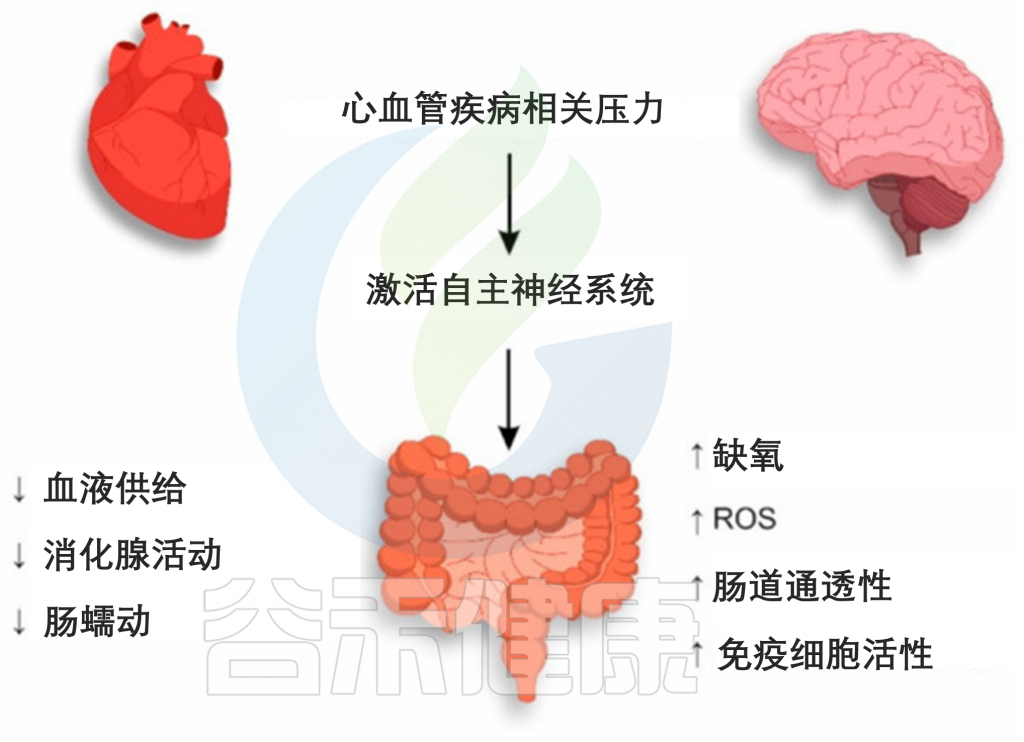
Suslov, Andrey V,, et al. J Clin Med. 2021
肠壁由肾上腺素能交感神经纤维支配,在刺激期间增加水和钠的吸收,伴随着肠道通透性的增加。同时,在大肠迷走神经的影响下,肠上皮杯状细胞产生的粘液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粘液为肠道上皮细胞提供保护,使其免受共生体及其代谢产物的影响,另一方面,粘液阻止免疫细胞的过早激活。因此,粘液层的减少和肠壁通透性的增加可导致肠道细菌的紊乱和肠上皮细胞的空间分离。
在Wistar大鼠中显示,出生后早期有限的筑巢压力会导致高皮质类固醇激素血症,增加肠道通透性,减少粪便微生物多样性,导致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失衡。肠道血供减少不仅是由于ANS交感分裂的影响,也是由于CVD的致病影响。
几项研究表明,肠道供血衰竭伴随着多种类型的CVD:心肌梗死、严重动脉粥样硬化、慢性心力衰竭、糖尿病和肥胖。因此,CVD期间肠道内的血供衰竭是由多种机制同时决定的。
肠血供减少伴有组织缺氧,而肠粘膜对缺氧最为敏感。
肠粘膜是一种支持粘液层以及微生物群与上皮下组织空间分离的解剖结构。在缺氧期间,有氧和无氧分解代谢循环中的葡萄糖转化会在中间阶段损害能量的生物合成。这导致活性氧(ROS)的释放。
由于活化免疫细胞的积累和 ROS 的产生,再灌注会增加缺血性损伤的破坏性影响。活性氧对蛋白质、脂质、碳水化合物和核酸具有高反应性,导致肠上皮完整性受损。至于肠道菌群与缺血性肠道损伤之间的关系,在大鼠模型中显示,肠道缺血-再灌注损伤导致肠道菌群发生显著变化,大肠杆菌和口腔普氏杆菌数量增加,随后在愈合阶段乳酸杆菌数量增加。
同时,在急性心肌梗死大鼠模型中证明,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会导致肠道炎症和细胞凋亡的发展,也就是说,肠道缺血不仅会导致肠道微生物群失衡,反之亦然,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会导致肠道损伤。
除粘液层外,肠上皮层在提供肠屏障功能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肠上皮层由与紧密连接蛋白连接的上皮细胞组成,特别是紧密连接蛋白、封闭蛋白、钙粘蛋白和粘附分子。
紧密连接蛋白作为肠-脑轴结构中肠屏障的重要元素。研究表明,脑肠肽ghrelin可以减轻动物模型脑出血后激活紧密连接蛋白 zonula occludens-1 和 claudin-5 的肠道屏障功能障碍。
一些研究通过改变紧密连接蛋白证明了肠道微生物组变化与肠道屏障损伤的关系。例如,植物乳杆菌增强上皮屏障刺激基因的表达,这些基因参与紧密连接zonula occludens-1、zonula occludens-2 和 occludin 的信号通路。
在小鼠模型的另一项研究中也证明了相同的效果,其中用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和链球菌的混合物治疗增加了紧密连接 zonula occludens-1 和紧密蛋白的表达。紧密连接完整性的改变可导致与代谢宿主状态受损相关的细菌或细菌代谢物的流入增加,表现为心脏代谢疾病。
肠上皮和粘液屏障位于肠道环境、肠道细菌和免疫系统之间。
众所周知,肠上皮层包括不同类型的细胞:
肠细胞
杯状细胞
肠内分泌细胞
潘氏细胞
簇状细胞
M细胞
以及多种专业免疫细胞,如
淋巴细胞
树突状细胞
巨噬细胞
均位于肠粘膜表面附近
上皮内淋巴细胞是第一个对致病因素做出反应的免疫细胞,它侵入上皮并传播树突以检测肠腔抗原。
其他细胞位于有组织的淋巴结构中,如派尔斑和隐斑,或分散在固有层内。
与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等专业免疫细胞类似,肠上皮细胞表达先天免疫受体,如模式识别受体,包括 Toll 样受体 (TLR) 和核苷酸结合蛋白,含有寡聚化结构域 (NOD)。
潘氏细胞合成抗菌分子受 TLR4/MyD88 和 NOD2 信号传递的调节,这些信号传递受肠道微生物的控制。
TLR 通过激活促炎信号通路以响应微生物抗原,在先天免疫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肠道免疫细胞通过细胞因子或直接的细胞连接支持肠道黏膜的屏障功能。因此,由 Th17 细胞或 3 型先天性淋巴细胞 (ILC3) 产生的 IL-17 和 IL-22 会增加肠上皮细胞分泌的 AMP 和 Reg3 家族蛋白 。
此外,上皮内淋巴细胞产生的 IL-6 可增强肠上皮细胞增殖并促进损伤后黏膜的修复。然而,其他促炎细胞因子,如 TNF-α 和 IFN-γ,通过抑制 β-连环蛋白/T 细胞因子 (TCF) 信号传递来抑制上皮细胞增殖 。
肠上皮细胞还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来调节宿主免疫反应。
在用革兰氏阴性细菌大肠杆菌和变形杆菌的鞭毛蛋白刺激肠内皮期间,TLR5 / MyD88 信号促进 IL-8 的产生,IL-8 将中性粒细胞募集到固有层中。
前面CVD中提到的胆囊收缩素、胰高血糖素样肽 (GLP) 和血清素由肠道内分泌细胞分泌,影响肠道免疫系统的活动。
胆囊收缩素通过 CD4+ 细胞和 B 细胞调节细胞因子的分化和产生。值得注意的是,交感神经系统调节的消化腺活性的降低间接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
有趣的是,微生物群对上皮肠屏障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免疫成分,还取决于其他影响。特别是,由肠道微生物群合成的短链脂肪酸被用作上皮细胞的能量来源,并间接增强上皮屏障。微生物代谢产物吲哚通过激活孕烷-X 受体具有防御屏障作用,并增加胰高血糖素样肽-1 的分泌。
无法保存肠上皮的复杂解剖和功能特征会降低上皮屏障的抗菌、免疫调节和再生能力。粘膜的破坏导致共生细菌及其代谢物从肠腔转移到上皮下组织,导致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反过来,这会导致器官功能障碍,并伴有肠粘膜炎症。
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细菌的代谢物在炎症过程中通过被破坏的肠道屏障进入循环。
微生物组介导疾病的三个因素:
首先,肠道细菌的代谢物是慢性免疫反应的永久激活剂,会在肠道以及整个生物体中引起持续性炎症。
其次,先天免疫系统成熟期肠道微生态失调导致免疫耐受性受损,随后表现为自身免疫和自身炎症性疾病。
第三,微生物组可以影响控制肠道远处组织特异性免疫的免疫因素。
考虑到肠道微生物群在神经免疫网络形成中的作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是一种应激蛋白,是神经营养因子家族的成员,可增加大脑中神经元对功能障碍的抵抗力,并提供神经系统的可塑性。
BDNF 控制了广泛的过程,包括微生物群-肠-脑轴参与心脏代谢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表明,BDNF 信号可能介导间歇性禁食对血糖调节和心血管功能的影响 。此外,研究表明,用高剂量益生菌治疗可以调节斑马鱼的行为,导致一些大脑相关基因的表达发生显着变化,例如 BDNF。因此,BDNF 可能代表了微生物-肠-脑轴的分子机制。
神经免疫轴:微生物群-肠-脑-CVD
肠道粘液膜的缺氧损伤、微生物群转移到上皮下组织、肠上皮屏障功能的破坏、肠道细菌代谢产物和炎症细胞因子的合成使肠道成为最大的内毒素源。炎症介质通过全身血液和淋巴循环到达神经系统中心。
血脑屏障
血脑屏障 (BBB) 在妊娠期间形成,充当大脑和血液循环系统之间的选择性过滤器。肠道微生物群和微生物代谢物在血脑屏障形成中的重要性已在不可知菌小鼠身上得到证实。在没有肠道微生物的情况下,与正常动物的血脑屏障相比,小鼠的血脑屏障变得具有渗透性。
研究发现,大脑的淋巴系统流入脑脊液,进入蛛网膜下腔,并进一步进入颈深淋巴结。脂质的溶解度、蛋白质的三级结构、浓度、分子质量和化合物的电荷决定了介质从外周血供应和淋巴系统到大脑的通道。
外周血中的细胞因子主要是亲水性的,可以调节神经系统的免疫功能。研究还表明,静脉注射吲哚(类似于色氨酸的细菌代谢产物)可以克服BBB。
LPS(脂多糖)的神经炎症效应通过外周组织中的TLR激活发挥作用,通过血脑屏障阳性的促炎细胞因子在神经系统中引起继发效应。
血脑屏障和淋巴血管系统被认为是信号进入大脑的入口。例如,循环免疫细胞和炎症介质(包括宿主和细菌的激素和神经递质)以及迷走神经刺激代表了有助于直接或间接微生物信号从肠道传输到大脑的机制 。
炎性细胞因子也是激活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对各种刺激的反应,包括在肠道病理过程中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促炎性细胞因子。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皮质醇和促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6和IL-8显著升高。IL-1α细胞因子在中枢神经系统水平上刺激机体的整个葡萄糖代谢;IL-6、IL-1、TNF-α和IFN细胞因子相互独立地刺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
除了炎性细胞因子外,炎症期间环氧合酶系统合成的前列腺素也参与HPA轴的激活。多项研究发现炎性细胞因子(TNF-α、IL-1和IL-6)在HPA轴激活中的作用。任何炎性细胞因子的注射都会刺激HPA轴,并导致循环皮质酮水平升高。值得注意的是,在LPS穿透后,任何细胞因子的阻断都不会阻断HPA轴的激活,也就是说,如果肠上皮屏障功能停止,LPS进入血液,那么细胞因子激活HPA轴的复制效应就会实现。那么接下来就是神经免疫性疾病和靶器官损伤了。
因此,所有炎症介质都会促进HPA轴的激活,而阻断任何一种细胞因子都不能减少HPA轴的刺激,因为它们之间存在重复效应。
因此,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激活是大脑介导的对疾病的基本反应之一。HPA 轴被认为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基础,它在心理和生理压力(包括感染)的影响下调节机体的稳态,促进对压力的充分反应。
所考虑的机制在慢性应激中非常重要。由于情绪唤醒的阈值不足以在CVD期间形成压力,因此神经系统中形成全值压力反应,随后通过肠内炎症介质持续激活HPA,激活ANS的交感分裂。
值得注意的是,机体的整个复杂病理变化是通过急性应激途径发展起来的,而情绪成分(情绪刺激)与慢性应激阈值相对应或完全缺失。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综述的机制对神经系统中心(包括ANS中心)有激活作用,ANS中心反过来又支配内脏器官,包括微生物群居住的肠道。
结合有关肠道微生物群的机制及其与神经系统通过肠-脑轴发育紊乱的关系,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在CVD期间,来自肠道的介质通过血流和淋巴进入大脑,并激活下丘脑核团。然后,只要下丘脑是ANS的节段上整体中心,ANS的交感神经分裂就会被激活。
因此,来自肠道的介质到达ANS的节段上中心,并激活交感和副交感分裂的工作,从而关闭肠道微生物群参与CVD发病机制的病理循环。许多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微生物群介导的炎症介质的增加会加重CVD的病程和预后。
研究还发现,恢复CVD患者的肠道菌群可以改善疾病的预后。使用增加阿克曼菌属、双歧杆菌、乳酸杆菌、拟杆菌和普氏杆菌的细菌数量的复合治疗制剂可改善CVD的病程。
众所周知,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属的细菌对肠壁具有局部抗炎作用。肠上皮屏障功能的恢复是因为肠壁炎症的减少,这意味着炎症介质在体循环中的水平降低,因此它们对神经系统的激活作用降低。
尤其是,高血压与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和肠脑轴失调有关。在高血压大鼠模型中证明,长期开菲尔治疗可降低IL-6和TNF-α蛋白密度,并消除在下丘脑室旁核和延髓头端腹外侧区观察到的小胶质细胞激活,保护心脏调节核免受肠道介导炎症的影响,从而提供开菲尔的降压作用。在小鼠缺血性中风或脑缺血模型中进行的一些研究表明,缺血性中风脑损伤通过增加促炎反应和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免疫细胞浸润大脑结构,促进肠道失调的发展,这与不良预后有关。
CVD患者肠道菌群与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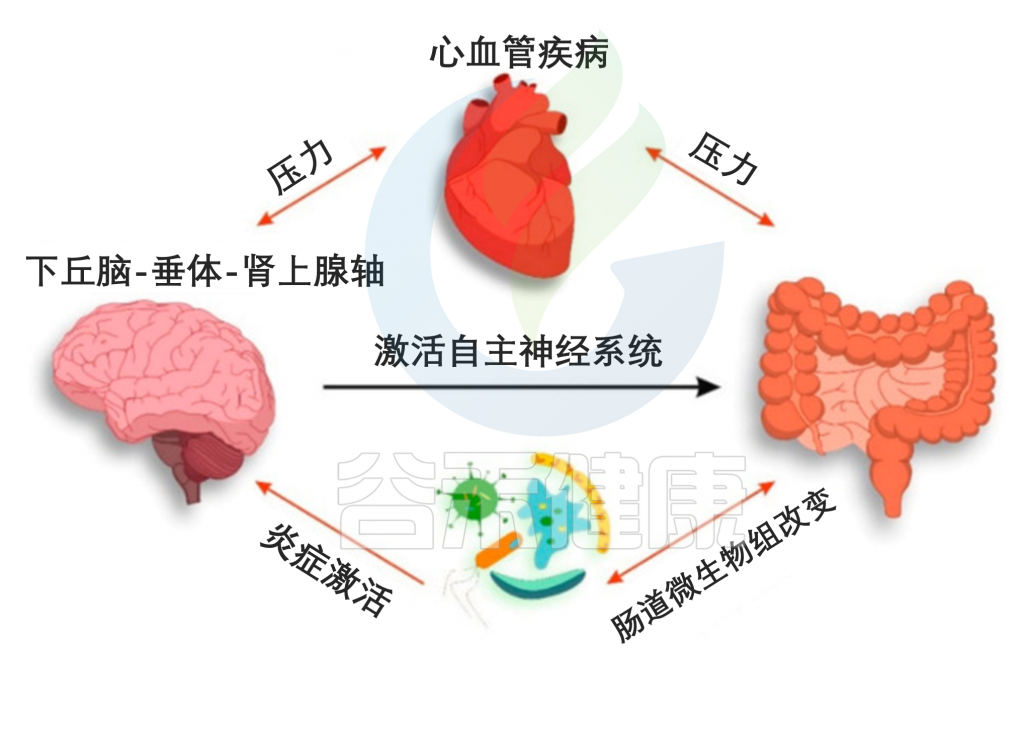

Suslov, Andrey V,, et al. J Clin Med. 2021
肠道微生物群参与了 CVD 的发病机制并决定了 HPA 轴的炎症激活。
一些研究调查了微生物组靶向制剂可改善 CVD 病程,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和主要 CVD 并发症的风险 。
在这里,我们可以假设基于微生物组治疗的有益心脏保护机制是由于其对微生物组-肠道-脑轴的影响。
通过阻断左前冠状动脉诱发心肌梗死的大鼠中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使用基于瑞士乳杆菌和长双歧杆菌组合的益生菌可降低与心肌梗死相关的不同脑区的凋亡倾向。
另一项针对小鼠的研究表明,在实验性中风后,抗生素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可降低缺血脑内的LPS水平和神经炎症。一项针对冠心病患者的研究发现,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与益生元菊糖复合物对抑郁、焦虑和炎症生物标志物具有有益作用。
建议所有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或75-15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或两者的同等组合。当然要视身体状况而定,如果自身基础不太好,在能力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保持一些低强度活动。
减少久坐时间,适当进行轻度体力活动是有益的。
饮食对人类健康的多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不健康的饮食模式(例如高脂肪的西式饮食)与动脉粥样硬化、代谢综合征和肥胖症等一系列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免疫系统正在成为这种关系的关键中介,通过食物诱导调节与慢性炎症相关的促炎/抗炎因子以及增加/减少各种病理结果的风险。
支持这一观点的大型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以高摄入饱和脂肪和低纤维为特征的饮食模式与促炎生物标志物水平升高有关,例如 C 反应蛋白 (CRP) 和白细胞介素 IL- 6。相反,摄入大量水果和蔬菜和/或经常食用鱼类的饮食模式与较高的脂联素血清浓度相关,脂联素具有抗炎特性。
这些观察性研究得到了干预试验的进一步支持,干预试验表明饮食可能会影响血清炎症生物标志物谱。例如,高胆固醇食物的饮食干预增加了对胰岛素敏感的参与者的 CRP 和血清淀粉样蛋白 A 浓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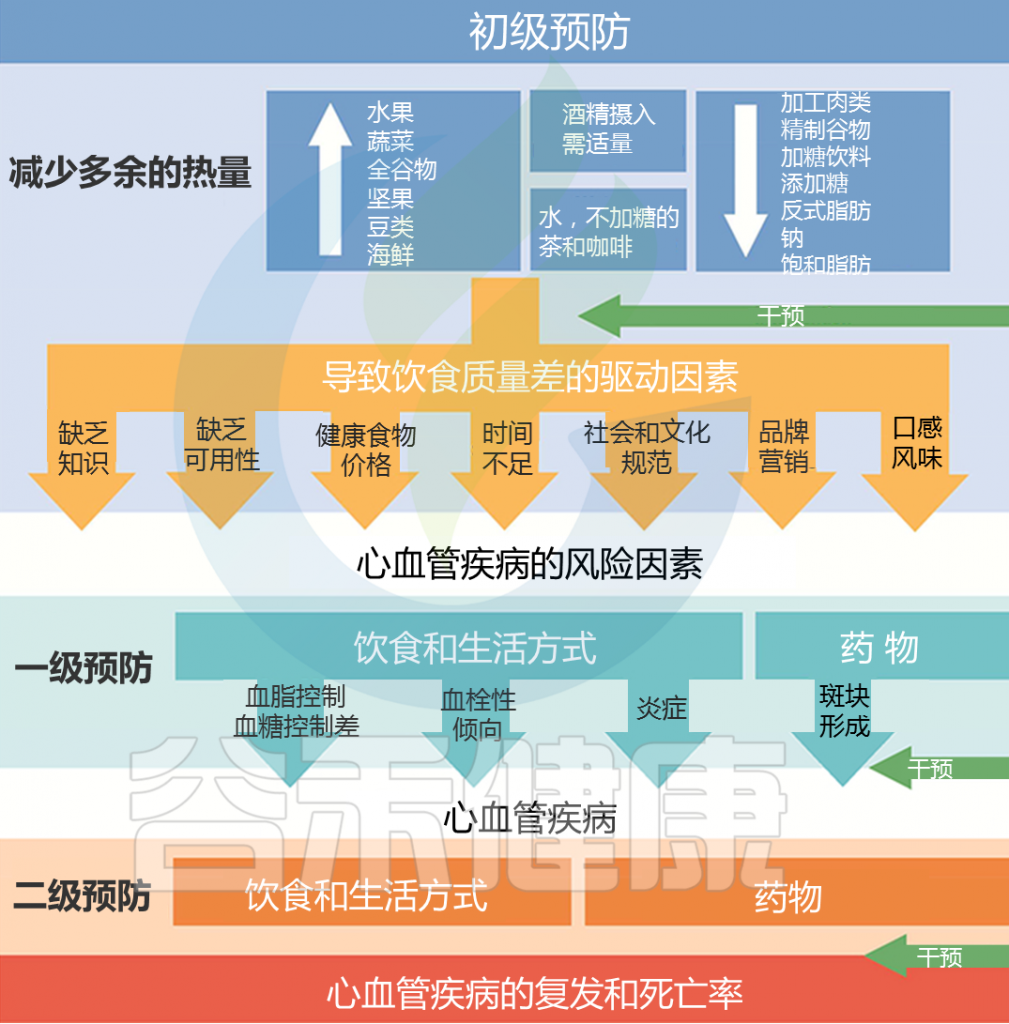

Yu E, et al.,J Am Coll Cardiol. 2018
健康的饮食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和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从更多荤食(以动物为基础的)饮食模式转变为素食(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模式,可能会减少心血管疾病。
建议饮食中多吃水果、蔬菜、坚果等;少量食用低脂乳制品和海鲜;而且尽可能少摄入加工肉类、含糖饮料、精制谷物、盐等。
戒烟可迅速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最具成本效益的策略。
建议限制饮酒或戒酒,每周最多饮酒100g。
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达到和保持健康体重,对这些指标可产生有利影响(如血压、血脂、血糖等),并降低CVD风险。
当饮食和体力活动改变以及其他常规的非侵入性干预措施效果不佳时,应考虑对高危人群行减重手术;也可以考虑使用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的抗肥胖药物。
新指南提出心理压力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需要加强对心理障碍患者的关注和支持,对其进行生活方式和药物干预,方式包括呼吸练习、冥想、写日记、适当锻炼、与大自然接触、与他人建立联系等,尽可能改善压力症状和生活质量,可改善心血管疾病。
通过对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的日常监测来了解健康状况,也可以通过肠道菌群健康检测等方式来了解慢病风险,阻断这类慢病的进程,预防控制代谢紊乱,从根本上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本文主要基于研究阐述免疫、炎症的神经调节以及肠道菌群如何参与 CVD 的发病和进展。
在CVD的初始阶段,肠道微生物群在其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是次要的,这意味着细菌的定性和定量变化不像在随后的阶段那么重要。
然而,后来,当肠道微生物群决定了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炎症激活水平时,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对CVD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CVD进展过程中,肠道细菌与肠壁的病理过程密切相关,成为CVD发病机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方面,试图确定与CVD进展过程最相关的肠道细菌,可能是开发CVD诊断、预防和治疗新相关方法的重要一步。
此外,注意通过饮食衍生的微生物代谢物、炎症反应转变、校准神经免疫从而影响CVD干预和治疗反应。
·
具体基于肠道菌群的饮食调节,以及CVD 进展中的饮食-微生物群串扰的机制,菌群代谢产物的作用等详见本次推文的第二篇:
《 饮食-肠道微生物群对心血管疾病的相互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Carnevale D. Neuroimmune axis of cardiovascular control: mechanisms and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Nat Rev Cardiol. 2022 Mar 17. doi: 10.1038/s41569-022-00678-w.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35301456.
Yu E, Malik VS, Hu FB.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evention by Diet Modification: JACC Health Promotion Series. J Am Coll Cardiol. 2018;72(8):914-926. doi:10.1016/j.jacc.2018.02.085
Suslov, Andrey V et al. “The Neuroimmune Role of Intestinal Microbiota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 vol. 10,9 1995. 6 May. 2021, doi:10.3390/jcm10091995
Thaiss CA, Zmora N, Levy M, Elinav E. The microbiome and innate immunity. Nature. 2016 Jul 7;535(7610):65-74. doi: 10.1038/nature18847. PMID: 27383981.
Huh JR, Veiga-Fernandes H. Neuroimmune circuits in inter-organ communication. Nat Rev Immunol. 2020 Apr;20(4):217-228. doi: 10.1038/s41577-019-0247-z. Epub 2019 Dec 17. PMID: 31848462.
Frank L J Visseren, François Mach, Bryan Williams,et al., ESC Scientific Document Group, 2021 ESC Guidelines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even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Developed by the Task Force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even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and 12 medical societies With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Preventive Cardiology (EAPC), European Heart Journal, Volume 42, Issue 34, 7 September 2021, Pages 3227–3337

谷禾健康
现状
全球肥胖患病率的上升是一个主要的社会经济负担,肥胖与许多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
尽管人们努力改善生活方式选择,提高对潜在病因的认识,但在预防和治疗肥胖方面的长期成功似乎有限,因为饮食诱导的体重减轻在5年随访后仅维持约25%。
近年来,在了解肠道微生物群作为宿主能量和底物代谢调节器参与肥胖和相关心脏代谢并发症方面取得了进展。因此,通过肠道微生物群靶向宿主代谢可能是饮食干预减轻体重的一项重要策略。
过去十年中,关于肠道微生物组对宿主代谢影响的研究数量呈指数增长,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在迅速发展,这些研究表明,基线微生物组成可以预测包括肥胖在内的代谢综合征。然而,研究同时表明微生物群组成的调节不可能会在所有条件下对人体代谢产生重要积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取决于个体的特征,例如年龄、习惯性饮食、代谢表型和基线肠道微生物谱。
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由可遗传、人口统计和环境因素决定,包括出生时的分娩方式、年龄、性别、胃肠道转运时间和药物使用。但是诸多因素中,饮食已成为塑造和定义肠道微生物组的关键因素。
饮食尤其是膳食纤维等引起的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和功能变化与肥胖和相关疾病的发展有关。这些研究结果发现肠道微生物群的个体间差异可以作为对抗肥胖代谢疾病的更精确饮食方法的基础。
本文将介绍有关饮食成分、肠道微生物组和宿主代谢之间相互作用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以及如何整合这些知识来制定基于精确的营养策略,以改善人类的体重控制和代谢健康。
厚壁菌/拟杆菌门
肠道微生物群影响免疫功能和上皮完整性、能量和底物代谢以及葡萄糖稳态。初步研究表明,与瘦个体相比,肥胖的人类和啮齿动物的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的比例增加,但也有个别研究未能观察到这种差异,甚至报告了比例下降。
多样性和微生物基因丰富度
在代谢健康与不健康个体的比较中,代谢不健康组的α多样性较低。而且重度肥胖症患者的低微生物基因丰富度比例高达75%,而瘦或超重/中度肥胖症患者的低微生物基因丰富度比例为23%-40%。
(小编推测可能是由于中重度肥胖人群其饮食比较丰富且量大,微生物不需要太多多余的基因就可以代谢获得生存繁殖的食物,而较瘦的个体食物不太丰富,那么菌需要更多的基因才获取生存的食物和繁殖生存)
具体菌属
具体而言,颤螺菌属(Oscillospira)和 红蝽菌科(Coriobacteriaceae)的细菌与良好的代谢健康相关。 在一项包含正常体重和超重/肥胖人群的研究人群中,特定菌属的丰度与代谢特征相关。 例如,产气柯林氏菌、Dorea formicigenans 和 Dorea longicatena 在超重/肥胖人群中的丰度更高。
Akkermansia属的细菌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它与患肥胖症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呈负相关。在超重/肥胖患者中,为期 3 个月的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补充剂可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并降低肝功能障碍和炎症的血液标志物。
基线菌属
另一项研究表明,在瘦肉型个体中,嗜粘菌A.muciniphila和Alistipes obesi显著富集,而在肥胖型个体中,Ruminococcus gnavus显著富集。该研究还确定,当在基线检查时高丰度存在的菌,如Blautia wexlerae 和 Bacteroides dorei 减肥前以高丰度存在时将有助于减肥。此外,基线普雷沃菌属 (Prevotella)普氏菌丰度可以预测肥胖人群在膳食纤维干预减肥中是否可以成功。
此外,与健康个体相比,II型糖尿病患者和代谢受损个体表现出微生物功能改变和发酵能力降低,尤其是产丁酸盐细菌丰度较低的个体。此外,胰岛素抵抗个体的肠道微生物组可能具有增加的生物合成潜力,并减少了支链氨基酸(BCAA,主要由Prevotella copri,B. vulgatus驱动)的吸收和分解代谢,这与有害代谢效果有关。
总之,代谢受损个体的微生物基因丰富度和多样性降低。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和功能的个体差异与饮食干预的反应变化有关。
在当前的西方世界,习惯性饮食结构已转向高能量密集型食物,包括相对较高的饱和脂肪和简单碳水化合物含量,以及较低的膳食纤维含量。尤其是膳食纤维的消耗,以及大量营养素的质量和消耗量都会强烈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基于人群的宏基因组分析揭示了微生物组成和多样性与60多种饮食因素的习惯饮食之间的关联。这些因素包括能量和大量营养素的摄入,以及面包和软饮料等特定食品的消耗。这些数据证实了饮食对塑造肠道微生物群的重要性。
饮食塑造肠型
在一项纵向单卵双生子研究中,粪便微生物群分析表明,能量的习惯性摄入、不饱和脂肪酸(FA)的类型和可溶性纤维会影响微生物群的组成,尤其是拟杆菌属和双歧杆菌的丰度。微生物肠道类型与长期习惯性饮食密切相关,尤其是蛋白质和动物脂肪(拟杆菌属)与碳水化合物摄入(普雷沃氏菌属)相比。
与此一致,长期坚持地中海饮食与特定分类群以及肠道微生物谱的功能有关。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是地中海饮食与心脏代谢疾病风险之间保护性关联的调节因素。当比较习惯性高脂肪饮食和高碳水化合物饮食时,高脂肪饮食的微生物多样性似乎较低。此外,与高(饱和)脂肪饮食和高碳水化合物/纤维饮食相比,微生物多样性似乎更低。这种饮食诱导的失调被认为是肥胖症代谢障碍的诱因。
饮食干预菌群变化较快,但是整齐菌群结构稳定
虽然主要在动物模型中得到证实,但数量有限的人体研究表明,饮食干预引起的微生物组成和功能改变可能已经在饮食摄入改变后的几周甚至几天内发生。在人类中,在严格转向完全以植物或动物为基础的饮食后,发现了适度的微生物变化。这些相当极端的饮食干预形式提供了对饮食-肠道微生物组相互作用的潜在机制的见解,并表明饮食干预引起的微生物变化可能会非常迅速地发生。
与此一致,一项小型控制喂养研究显示,在开始高脂肪/低纤维或低脂肪/高纤维饮食后 24 小时内微生物组组成发生了变化,尽管在整个为期 10 天的研究中肠型特征保持稳定。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成年人存在微生物复原力的趋势,这可能与长期习惯性饮食摄入有关。然而,由于缺乏对肠型动力学和复原力的理解,细菌肠型的概念受到了其他几项研究的质疑。
一项为期 1 年的干预研究比较了限制能量的地中海饮食和增加体力活动与等热量地中海饮食对超重/肥胖成年人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组之间肠道菌群组成的变化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如此,两种饮食的微生物转移趋势是相同的。这表明饮食模式对于肠道微生物的整齐迁移起关键作用。
饮食与肠道和宿主代谢中的糖酵解和蛋白水解发酵之间的相互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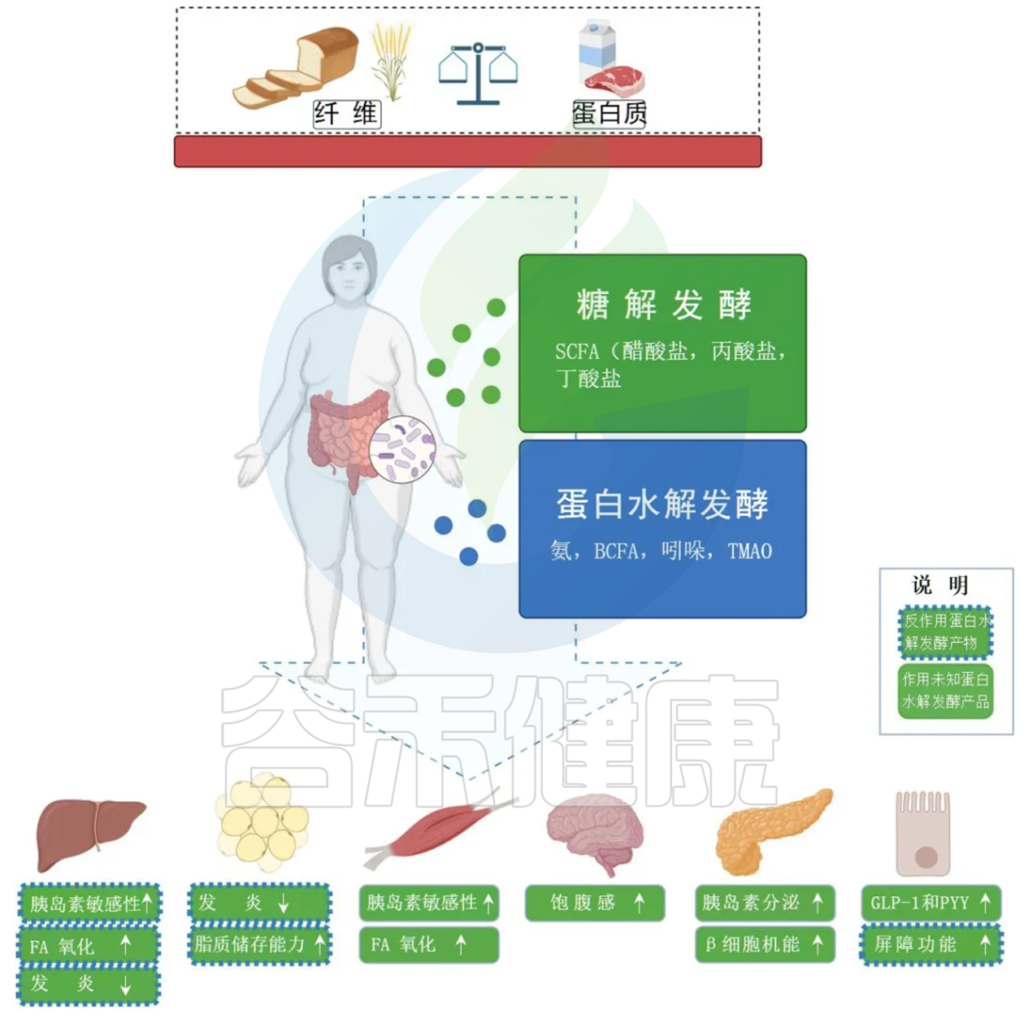
Jardon KM et al., Gut. 2022
膳食纤维的发酵主要发生在近端结肠并产生 SCFA,既可以用作肠细胞的燃料,也可以充当外周信号分子。SCFA 通过影响 GLP-1 和 PYY 的分泌,参与集中调节食物摄入和能量消耗。
蛋白质发酵主要发生在远端结肠并产生更多样化的代谢物,包括与肠道和代谢健康有害影响的 BCFA。
绿框表示 SCFAs 对周围器官代谢过程的影响。
蓝色边框表示蛋白水解发酵产物的相反方向位点方向(虚线)或未知方向(无线)的影响。
BCFA,支链脂肪酸;FA,脂肪酸;GLP-1,胰高血糖素样肽 1;PYY,肽YY;SCFA,短链脂肪酸;TMAO,三甲胺 N-氧化物。
成人肠道微生物组的塑造在生命早期就已经开始,这取决于诸如暴露于母体微生物组、分娩方式和早期暴露于膳食成分等因素。在所有生命阶段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和功能的众多因素中,饮食是调节特定细菌种类及其功能的丰度的关键。反之亦然,个人对某种饮食或饮食成分的反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肠道微生物群特征的影响。
肠道微生物群能够发酵宿主无法获得的食物成分。小肠中不能被酶分解的膳食纤维和其他复杂碳水化合物可以(部分)被大肠中的细菌发酵,这一般是细菌作为首选能源,发酵后产生微生物产品,如短链脂肪酸(主要是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
主要的产丁酸菌属于厚壁菌门,尤其是: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Clostridium leptum、Eubacterium rectale 、Roseburia.
其他短链脂肪酸的产生由双歧杆菌等细菌介导,双歧杆菌在碳水化合物发酵过程中产生乙酸盐和乳酸。此外,A. muciniphila 物种同时产生丙酸盐和乙酸盐。
稳定同位素技术与13 C标记的短链脂肪酸可根据呼吸、尿液和血液分析对体内结肠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进行量化。短链脂肪酸主要在结肠中形成,其中约95%随后被吸收。
短链脂肪酸的作用
丁酸盐主要用作结肠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而丙酸盐和乙酸盐则通过门静脉进入肝脏。特别是,乙酸盐在进入体循环后也能到达外周组织,引起多种代谢和饱腹感相关效应。
短链脂肪酸可与G蛋白偶联受体(GPRs)结合。研究最好的受体包括GPR41、GPR43、GPR109a和GPR164,它们在大量细胞中表达,包括结肠上皮、胰腺β细胞、免疫细胞和周围组织,如脂肪组织。
短链脂肪酸对外周组织的影响包括脂肪生成、抑制脂肪组织脂肪分解(尤其是通过乙酸盐)和减轻脂肪细胞炎症、骨骼肌脂质氧化能力增加、胰腺胰岛素分泌和β细胞功能增加,肝脏的胰岛素敏感性和脂质氧化增加并改变肠-脑相互作用。但是注意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体外和啮齿动物研究。
短链脂肪酸减脂(人类研究)
在人类研究中发现,长期结肠丙酸盐输送可防止体重增加,减少腹部肥胖和肝细胞内脂质含量,并防止超重成年人胰岛素敏感性的恶化。与这些发现一致,人体内数据表明,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中,饮食诱导微生物短链脂肪酸产生变化或直接结肠短链脂肪酸输注后,空腹脂质氧化和静息能量消耗增加。
碳水化合物的消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类型的特定酶。大多数可消化的膳食碳水化合物在小肠中被消化和吸收,而某些不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包括抗性淀粉和膳食纤维,很容易被结肠中含量最高的肠道微生物发酵。
膳食纤维对肠道菌群的有益影响
膳食纤维已被证明对与健康益处相关的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具有显著影响。这些因膳食纤维的结构、物理和化学特性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水溶性、粘度、粘合和膨胀能力以及发酵性。高度可发酵的纤维,如 β-葡聚糖、菊粉和低聚半乳糖,在对微生物群组成和肠道代谢物产生的影响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定义,而不溶性纤维虽然部分发酵,但大多数人都知道它们对粪便的有益作用一致性和结肠传输时间。

摄入高纤维饮食有益地影响宿主的健康,其中包括影响葡萄糖和脂质代谢。重要的机制包括调节营养吸收或产生短链脂肪酸,但有关膳食纤维对健康影响的数据存在争议。
对于膳食纤维研究中不一致发现的解释:
首先,在大多数人体研究中,只补充了一种特定的可发酵纤维,因此只刺激了一种或几种个体(潜在有益的)细菌属。后者的后果可能是其他必需细菌或核心菌属的丰度减少,这可能导致微生物生态系统的不平衡。因此,结合刺激多种不同细菌属的不同纤维可能对维持微生物丰富度以及对免疫状态和代谢健康产生更显著的(相加或协同)影响很重要,所以多样化膳食纤维和饮食摄入对于健康益处的微生物调节更有用。
有趣的是,一项研究表明,结肠中产生短链脂肪酸的部位可能是代谢健康的决定因素。急性远端结肠乙酸盐给药增加了超重男性的循环乙酸盐浓度,增加了脂肪氧化和刺激饱腹感激素 PYY,并降低了血浆肿瘤坏死因子-α。与远端输注相比,近端结肠中的乙酸盐给药不影响代谢特征。因此,通过结合不同的膳食纤维和/或更复杂的膳食纤维,针对远端结肠中微生物物种的膳食纤维可用性和短链脂肪酸形成,可能是改善免疫和代谢健康的有前景的策略。
TIPs
短链脂肪酸在一定范围内是越高越好,但是超过一定范围,也会产生害处。例如,高纤维饮食增加丁酸盐,诱导Stx受体球形三酰神经酰胺表达从而促进致病大肠杆菌定植。
此外,有益的短链脂肪酸一般需要通过结肠部位的菌群发酵产生,如果外源性的补充摄入,例如,丙酸盐有助于防止食物上霉菌,被广泛使用于烘焙食物、动物饲料和人造调味品中。如果长期摄入过量含有丙酸盐的食物,可能会增加人类患糖尿病和肥胖症的风险。
其次,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膳食纤维干预研究都没有考虑基线微生物组或代谢表型。基线肠道微生物组的特征可能与饮食干预结果密切相关。例如,已经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对膳食纤维(抗性淀粉与非淀粉多糖)的反应可以根据肥胖男性的基线微生物多样性来预测。高微生物多样性与微生物群的较低膳食反应性相关,这可能支持肠道微生物的更高多样性与微生物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关的假设。
与此一致,与基因计数低的个体相比,基线时的高微生物基因计数与对减肥饮食的不太明显的反应有关。在低基因计数组中,基因丰富度和临床参数有所改善,尽管在基因丰富度低的个体中炎症标志物的变化不太明显。
一项针对肥胖个体的研究表明,不是基线微生物多样性而是厚壁菌门的基线丰度预测了个体微生物群的饮食反应。总之,这些发现表明微生物多样性并不总是饮食反应性的预测指标,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复杂的饮食-微生物组-宿主代谢相互作用。
作为对菊粉型果聚糖益生元的反应,具有高习惯性膳食纤维摄入量的健康个体的肠道菌群组成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而习惯性纤维摄入量低的人肠道菌群似乎更能适应变化。在II型糖尿病患者中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膳食纤维促进了一组精选的产生短链脂肪酸的菌株,而许多其他微生物,包括蛋白水解发酵中的微生物,要么减少要么不变,表明微生物基因丰富度总体下降。粪便短链脂肪酸增加,尤其是丁酸盐,伴随着葡萄糖稳态的改善。因此,如几项人类纤维膳食干预研究所示,更高的微生物基因丰富度本身可能无益,但生理结果可能更依赖于微生物网络的功能。
在一项调查 6 周全麦饮食对体重变化影响的研究中,普雷沃氏菌属的高基线丰度与超重、健康成年人的体重减轻程度较高相关。这些发现表明,作为对特定饮食干预的反应,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调节剂具有预测能力。
此外,发现超重、前驱糖尿病个体与瘦个体相比,对短期施用长链菊粉和抗性淀粉的微生物多样性和餐后胰岛素敏感性的变化的反应降低。与此一致,最近的研究表明,基线肠道微生物特征可以预测补充 3 个月长链菊粉后 BMI 的变化,这种效应在不同个体的粪便微生物群定植的小鼠中得到了复制。
有趣的是,可溶性菊粉纤维已被证明可以降低空腹血糖受损人群的胰岛素抵抗,但不能降低葡萄糖耐量受损的人群。鉴于空腹血糖受损与肝脏胰岛素抗性密切相关的发现,后一发现可能表明纤维 – 肠道微生物群 – 宿主代谢串扰中的组织特异性。
总体而言,益生元膳食纤维对代谢健康结果的有效性可能取决于几个参数,包括基线微生物组成以及微生物发酵的部位。
在低膳食纤维的西方饮食人群中,结肠远端的微生物群更擅长于利用剩余肽和蛋白质的发酵,因为首选的燃料,可发酵碳水化合物,已经在近端结肠中被人体大量使用。这种蛋白水解发酵过程的产物包括气体产物,如氢、甲烷、二氧化碳和硫化氢;BCFAs异丁酸酯、2-甲基丁酸酯和异戊酸酯(源自BCAAs发酵)、酚类和吲哚类化合物(源自芳香族氨基酸微生物发酵)以及较小的、未知的短链脂肪酸。
与糖解发酵产物相比,大多数蛋白水解发酵产物被认为对宿主肠道和代谢健康有害,尽管一些动物数据表明吲哚和硫化氢对肠道和外周组织功能有益。
例如,一些只能由肠道细菌(吲哚)或哺乳动物宿主(酪胺、色胺和短链脂肪酸)产生的氨基酸衍生化合物通过影响GLP-1和肠内分泌细胞血清素的分泌,直接影响哺乳动物的饱腹感和肠道运动。
然而,大多数这些化合物对宿主肠道和周围组织的生理作用仍不清楚。许多此类化合物的人类来源和细菌来源之间的区别尚未完全确定,需要进一步的体内研究来验证此类效应。
结肠中糖酵解和蛋白水解发酵之间的平衡,以及对宿主生理的假定有益和有害调节之间的平衡,可能对制定饮食干预策略很有意义。
一些研究表明,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特别是缓慢发酵纤维的摄入量,会减少肠道微生物群仅产生有害的蛋白水解代谢物,使得整体发酵平衡向更有益的糖酵解发酵转变。
摄入的膳食蛋白质首先在小肠中被胰酶和来自肠细胞的肽酶消化。然后,大量的寡肽和氨基酸通过肠细胞转运蛋白被转运到门静脉血流中,在那里它们被用作蛋白质合成的氨基酸前体或被代谢为燃料或肠粘膜代谢物必需的前体。
由于远端小肠和近端结肠中的大多数细菌优先使用可发酵碳水化合物而不是蛋白质,因此大多数氨基酸作为能量来源的发酵发生在碳水化合物被耗尽的远端结肠。
摄入的蛋白质到达大肠的百分比也可能取决于蛋白质质量,估计约为 10%。由于植物的细胞壁不易消化,源自植物的蛋白质的消化率较低,而源自动物的蛋白质更容易在大肠中消化,这表明功能结果存在潜在差异。
酪蛋白是一种从动物产品中提取的相对缓慢消化的蛋白质,是防止高脂肪/高蛋白饮食小鼠体重增加和脂肪量增加的最有效蛋白质来源。
蛋白水解和糖酵解发酵之间的平衡可能决定对生活方式干预的反应情况,因此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考虑。


流行病学研究还表明,摄入乳制品和素食蛋白质来源与预防肥胖有关,而大量摄入肉类(尤其是红肉)则预示着体重增加会更高。
尽管研究较少,但蛋白质摄入已被证明会影响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效果取决于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和消化率,而蛋白质的来源和摄入量会影响它们。
蛋白质摄入影响微生物组成
在大鼠研究中,高蛋白饮食与C. coccoides, C. leptum, F. prausnitzii 减少有关,而超重或肥胖雄性中Roseburia, E. rectale, C. aerofaciens, Bacteroides, Oscillibacter 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以等热量的方式比较高脂肪/高蛋白饮食与中等蛋白质或低蛋白质饮食会导致饮食之间碳水化合物或脂肪含量的差异。因此,对于所有的等热量膳食宏量营养素交换研究,很难确定导致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变化的主要膳食因素,这可能归因于一种(宏量)营养素的增加或另一种营养素的减少。
膳食脂肪已被广泛研究与饮食相关的代谢疾病(如肥胖)相关,但其对人类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尚不明确,而且研究通常会得出相反的结果。
不同类型的脂肪酸(饱和、单不饱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碳链长度和饱和度可能对肠道微生物群组成有明显影响。
横断面研究表明,食用富含动物蛋白和脂肪的饮食与拟杆菌属肠型有关,而高纤维、水果和蔬菜的摄入与健康成年人的普氏菌肠型有关。

此外,主要饱和脂肪酸(SFA)的高摄入量与成人和婴儿肠道微生物丰富度和多样性的降低有关。在超重和肥胖人群中, 主要饱和脂肪酸与肠单胞菌属呈负相关,而主要饱和脂肪酸与Roseburia呈正相关,后者在体重正常的个体中也非常丰富。在这项研究中,根据 BMI,习惯性 主要饱和脂肪酸摄入量与产丁酸菌表现出相反的关联特征。
总体而言,应该注意的是,与膳食纤维相比,膳食脂肪-微生物组-宿主生理学相互作用的研究较少,而且其机理知识主要基于动物研究。根据人类生理学比较难解释这些发现,应进一步研究。
多酚主要作为酚类化合物存在于水果和蔬菜中,以其作为抗氧化、抗炎、心脏保护、癌症预防和神经保护剂的有益作用而闻名。
补充天然存在于茶中的表没食子儿茶素-3-没食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3-gallate) 2个月,对肥胖小鼠胆汁酸代谢和疣微菌科Verrucomicrobiaceae丰度均有影响,促进了A. muciniphila丰度的增加。在其他研究中,后者与有益的代谢作用有关。
此外,虽然也在动物模型中,但 8 周的多酚补充剂可防止饮食引起的肥胖和肠道炎症,这与Akkermansia的丰度增加有关。在健康、超重或肥胖的个体中,12 周的白藜芦醇和表没食子儿茶素-3-没食子酸酯联合补充剂改善了男性的代谢参数并减少了拟杆菌门,但女性没有。
以上两项研究都表明存在性别特异性微生物反应,在评估干预反应时应考虑这一点。

总体而言,在饮食中添加膳食多酚似乎可以促进肠道和代谢健康,尽管仍然需要对人体研究的机制见解。
基于微生物组的精准营养预测代谢健康参数,如血糖反应和变异性,或用于抵消代谢紊乱,目前已受到很大关注。
该领域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表明,尽管餐后血糖反应的人际差异很大,但在机器学习算法的帮助下创建的个性化饮食(基于习惯性饮食、身体活动和肠道微生物群)可能会成功降低血糖反应和不良代谢健康,还有助于减肥。
研究测试在对不同类型面包的血糖反应中发现了显著的人际差异,并且这种血糖反应可以通过基线微生物组特征来预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主要基于他们对急性膳食挑战和短期干预的反应,而不是长期干预反应。
肠道微生物组的预测能力正变得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检查纤维和粪便微生物群移植效果的研究中。在长期的肠道菌群检测经验实践中也证实,基线微生物特征是对饮食干预(例如,膳食纤维或复合蛋白质)的反应性的有趣生物标志物,也是个性化健康管理的应该纳入的指标基础。
微生物组-宿主代谢轴可能对胰岛素抵抗患者的饮食干预存在抗性,这表明干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或者需要摄入的功能性膳食成分(如膳食纤维)来诱导有益的效果。特定功能微生物群的特点是对膳食成分的不同消化能力,导致微生物代谢物(如 短链脂肪酸)的不同产生,随后影响宿主代谢的调节。
总的来说,在评估饮食模式和常量营养素组成不同的饮食时,重要的是要同时考虑饮食成分的数量和质量,由于与宿主的微生物和代谢表型的不同相互作用,在整体饮食方法中要考虑到微量营养素和生物活性成分,如多酚。
对饮食干预的反应不仅取决于肠道微生物群的特征,还取决于饮食、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以及代谢表型等临床特征之间复杂的多因素相互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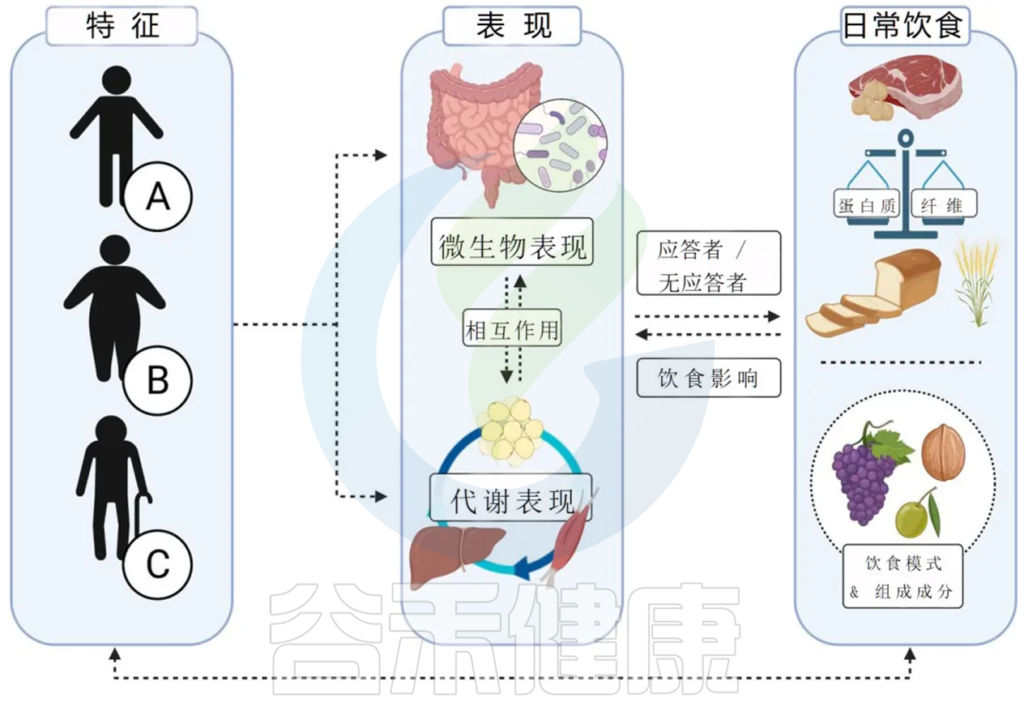
Jardon KM, et al., Gut. 2022
为了将基于精确的策略转化为医疗保健实践或指南,我们需要彻底了解为什么人们对饮食的反应不同,差异反应和相关表型是否长期保持,以及开发的算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重复的。
在饮食干预研究中通过最先进的方法进行详细的微生物和代谢表型分析至关重要。显然,鉴于复杂性,除了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的详细信息外,还需要详细的信息,包括出生方式、病史、药物使用情况(尤其是抗生素)、身体活动、心理压力和睡眠质量等。这也意味着需要先进的统计和建模方法来梳理不同因素的重要性。


主要参考文献:
Jardon KM, Canfora EE, Goossens GH, Blaak EE. Dietary macronutrients and the gut microbiome: a precision nutrition approach to improve cardiometabolic health. Gut. 2022 Feb 8:gutjnl-2020-323715. doi: 10.1136/gutjnl-2020-323715.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35135841.
Agus A, Clément K, Sokol H. Gut microbiota-derived metabolites as central regulators in metabolic disorders. Gut. 2021 Jun;70(6):1174-1182. doi: 10.1136/gutjnl-2020-323071. Epub 2020 Dec 3. PMID: 33272977; PMCID: PMC8108286.
Jie Zhuye,Yu Xinlei,Liu Yinghua et al. The Baseline Gut Microbiota Directs Dieting-Induced Weight Loss Trajectories.[J] .Gastroenterology, 2021
Jie Z, Yu X, Liu Y, Sun L, Chen P, Ding Q, Gao Y, Zhang X, Yu M, Liu Y, Zhang Y, Kristiansen K, Jia H, Brix S, Cai K. The Baseline Gut Microbiota Directs Dieting-Induced Weight Loss Trajectories. Gastroenterology. 2021 May;160(6):2029-2042.e16. doi: 10.1053/j.gastro.2021.01.029. Epub 2021 Jan 20. PMID: 33482223.

谷禾健康

本文原创:谷禾健康
自闭症谱系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疾病,其特征是社交和沟通困难、限制性和重复性行为以及异常的感觉反应。
自闭症的具体发病机制尚不能明确,但目前为止许多研究表明,自闭症与肠道微生物组之间存在很大关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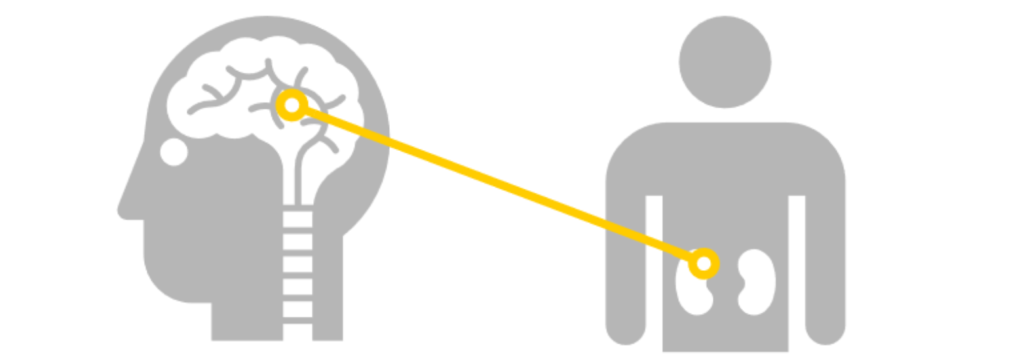
最新,Yap等人发表于Cell的一篇题为“Autism-related dietary preferences mediate autism-gut microbiome associations”的论文就自闭症与肠道菌群的关联给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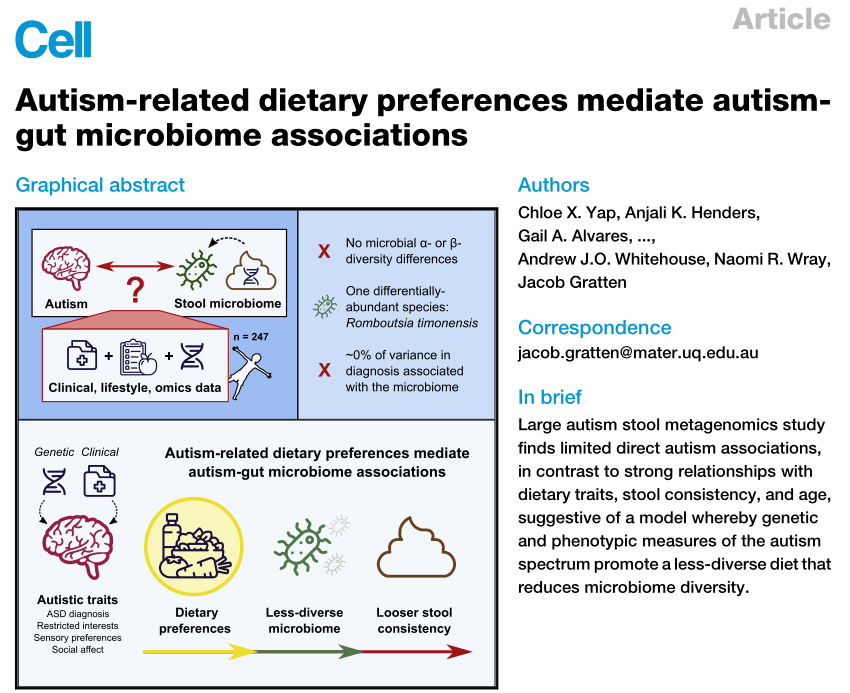
其核心结论是:
肠道菌群与自闭症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肠道菌群差异是由于自闭症症状导致患儿的饮食多样性下降,饮食类型狭窄,从而导致肠道菌群多样性减少,进而引发便秘和消化道症状。
我们来看看其研究设计情况。
关于肠道菌群这方面的研究,很关键的一个点是研究的样本数量。
首先,这项研究涵盖了共247名儿童(2-17岁),其中自闭症患者99名,51名患者的兄弟姐妹,97名非自闭症儿童,样本来自澳大利亚自闭症生物银行Australian Autism Biobank (A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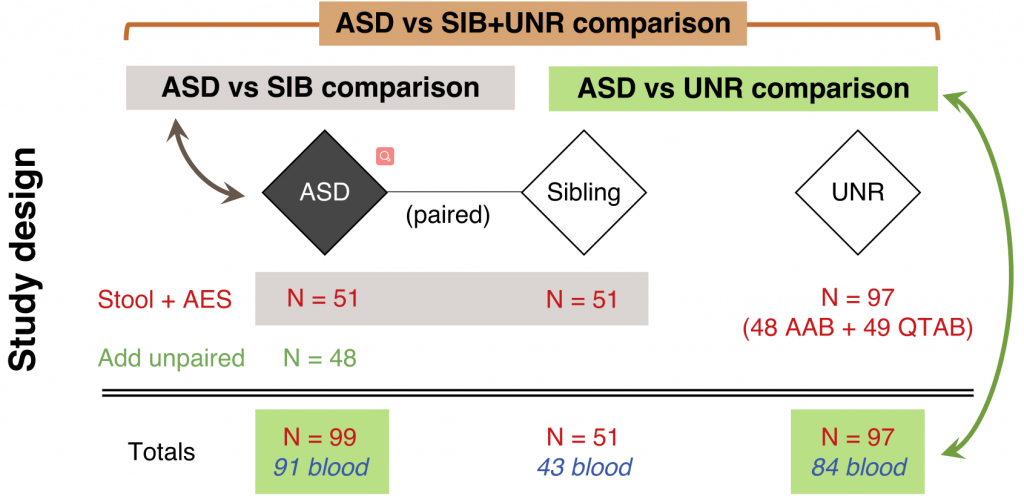

我们观察到样本人群相对于宏基因组来说样本数量还可以,但是99例自闭症患者样本还是让整个研究的统计效力及研究的适用范围有很大限制。
自闭症属于神经发育疾病,虽然其病因复杂,但是疾病的发生阶段绝大部分在出生到3岁左右,主要影响了儿童早期的神经系统发育,导致出现神经发育滞后、刻板行为和社交障碍。
类似的疾病还有注意力缺陷ADHD以及多动症等。越早期的干预其愈后和改善就越明显,因为早期神经系统发育是阶段性的,错过了发育阶段,很难在后期通过行为学等方面获得明显改善。
进一步查看研究样本的年龄分布我们发现,该研究的样本年龄均值在8.7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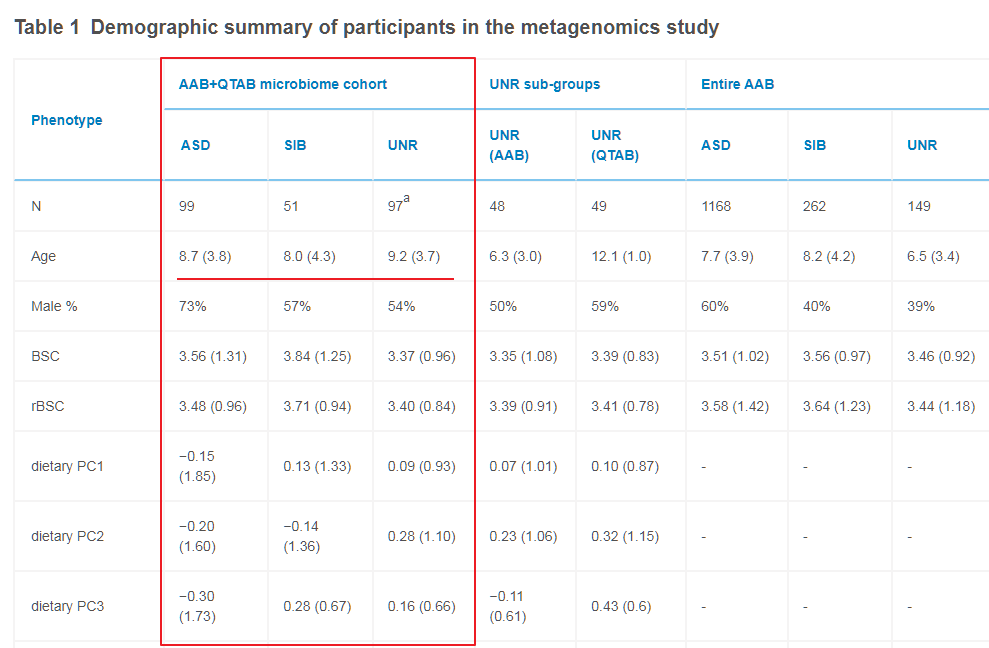
虽然范围在2-17岁,但是和自闭症发病阶段3岁以下的各组样本分别是7例、7例和8例,2岁以下的样本仅有1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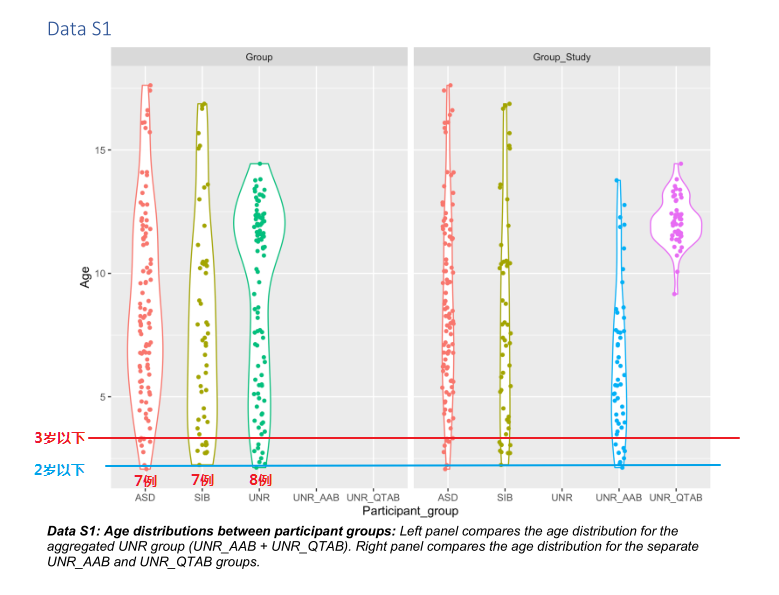
也就是说,研究涉及的自闭症患者虽然仍然有着自闭症的诊断和行为表现,但是绝大部分样本均不是处于神经发育的最核心阶段,而且大部分样本应该是经历过多年的包括行为干预或其他治疗。
因为自闭症与早期行为发育相关,大部分确诊儿童可能其行为表现和社交能力直到成年可能仍然没有完全恢复或达到正常水平,可能在多年后即便其引发自闭症的病因(主要是环境或生理因素)已经消失,但症状或诊断仍然没有变化,这就意味着这些样本可能不能反映真实的自闭症发生时的神经发育和菌群状况,因而也不能说明菌群在自闭症的发病和发展过程中并无联系。
更重要的是肠道菌群的组成变化尤其是生命早期与年龄和发育阶段密切相关,3岁之前的肠道菌群基本上每个月龄都存在变化,3岁之后的肠道菌群会趋向于接近成年人的菌群构成,并逐渐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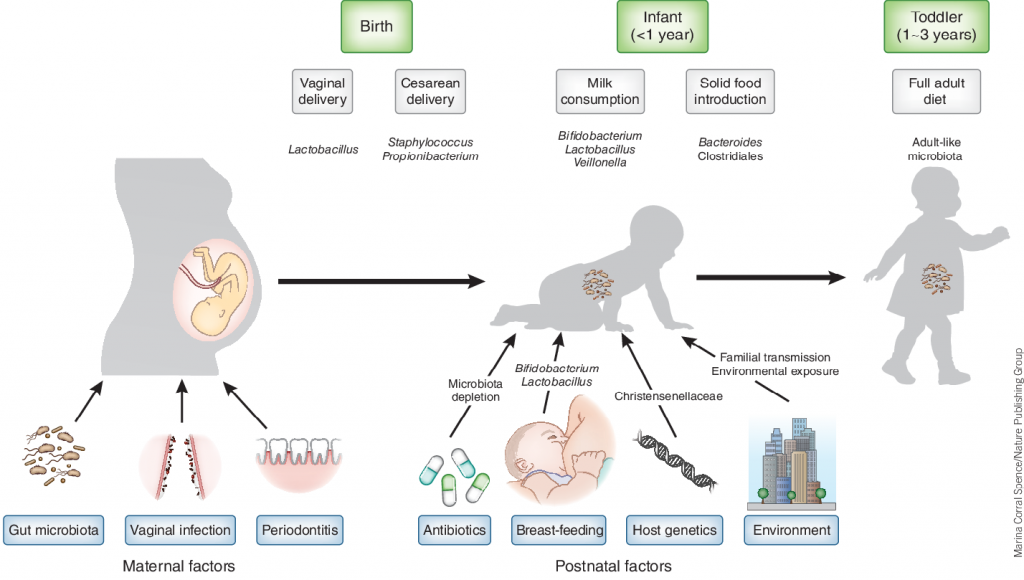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6个月左右,由于固体辅食的引入,婴幼儿的饮食结构会发生重要变化,相对应的肠道菌群也会发生重要的转变,从乳制品代谢为主的韦荣氏菌、双歧杆菌、大肠杆菌为主逐渐进入以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代谢为主的拟杆菌或普雷沃氏菌属等成年人常见核心菌群为主的菌群构成。这一变化阶段恰恰是自闭症对应早期神经发育的最重要阶段,而该研究基本没有这个阶段的样本。
研究中也明确提及肠道菌群构成和年龄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在分析中是将年龄和性别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但我们认为这种统计方式不足以解决儿童肠道菌群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变化差异,需要进一步对不同年龄阶段或年龄的儿童进行单独分组分析,但是这样该研究的样本数量就严重不足以获得足够的统计效力。
研究中包含有来自同一家庭的非自闭症兄弟姐妹,作为对照能较好的控制包括饮食、生活方式及居住环境等变量,因此很自然我们希望看到针对成对家庭兄弟姐妹的比较分析。
在论文的补充材料方法部分有描述了使用成对样本进行比较的内容,一个102个样本,形成51对样本。对于这样的成对样本分析,比较简单的方式是直接进行成对T检验。
然而,论文中并没有这么做,比较奇怪的将family ID作为随机变量从而控制成对样本的差异检验。但是家庭ID本身除了家庭之外并没有类似年龄或分层等信息量,作为随机变量加入后并不能有效实现成对分析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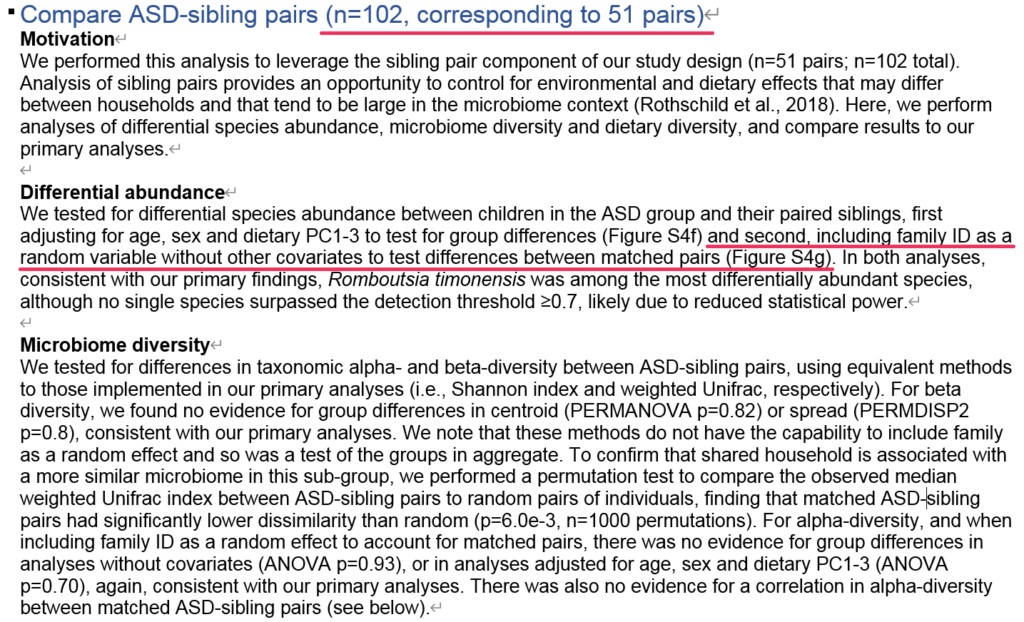
另外根据论文的结论,饮食结构单一引起了菌群的变化,进而诱发肠道问题,那么在成对家庭成员样本之间,自闭症儿童相较于同家庭的兄弟姐妹在相同饮食习惯和环境下是否饮食结构明显单一呢?
我们期待看到自闭症儿童的饮食多样性要显著低于其兄弟姐妹,且基本集中于低多样性的区间。
论文补充材料部分的下面这张图显示,同家庭兄弟姐妹之间的饮食多样性是显著相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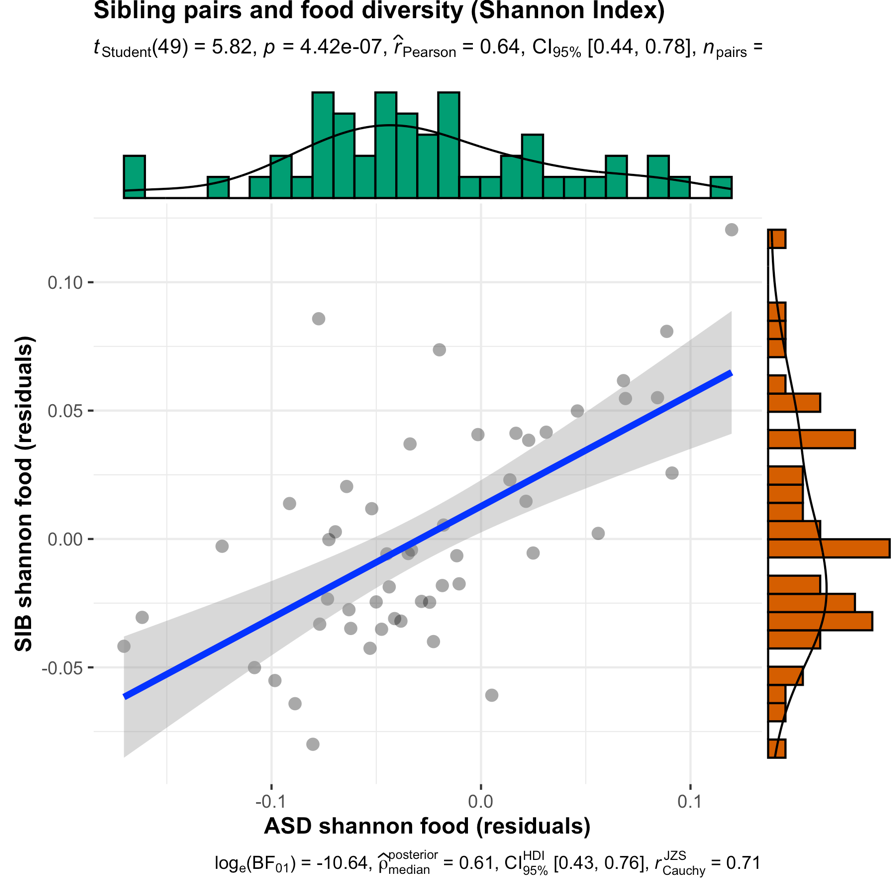
那么对应的菌群多样性呢?下面的图显示,基本没有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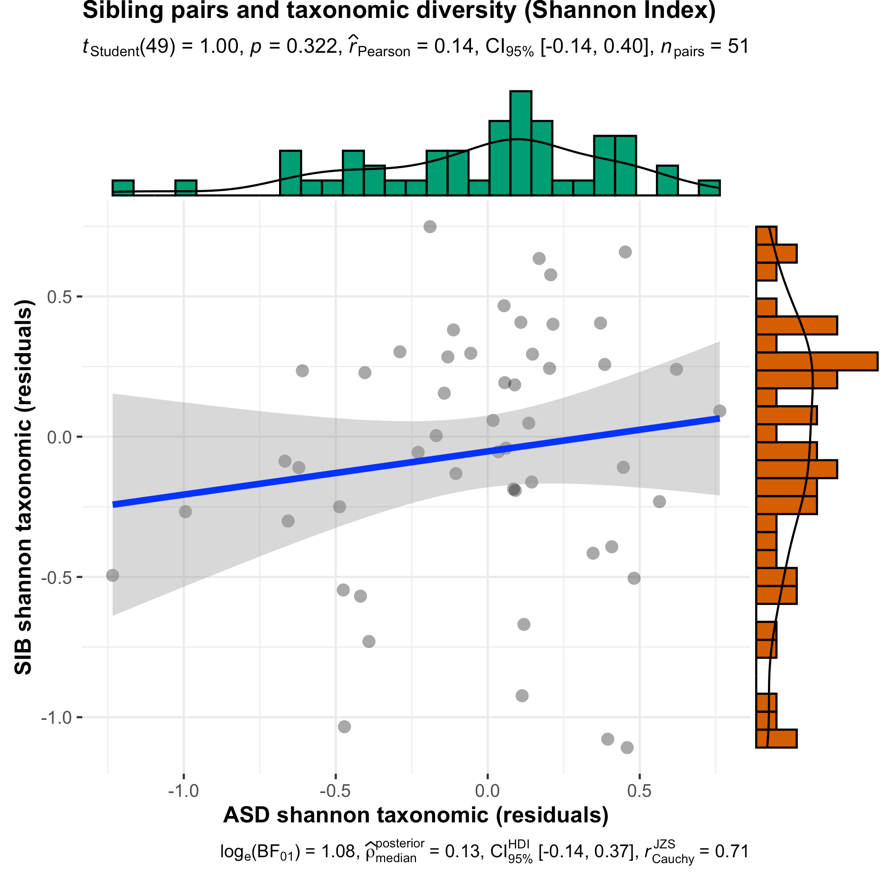
由于论文没有进行成对样本的检验,因此我们尝试下载数据进行单独分析,很遗憾,论文中提供的数据仅包括100例样本的数据,表型和分组等信息只有50例样本的,无法进行单独分析。
针对论文结论的自闭症儿童的饮食类型狭窄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早期婴幼儿期饮食构成本身就是相对单一的,而且非自闭症儿童中也存在相当一部分饮食结构单一的,单以饮食结构问题来解释自闭症儿童的菌群差异还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另外我们注意到,该研究将菌种和后续的基因及代谢途径分为常见和罕见两组,其中种部分中位数大于0的作为常见的,一共96个,其他的有607个种作为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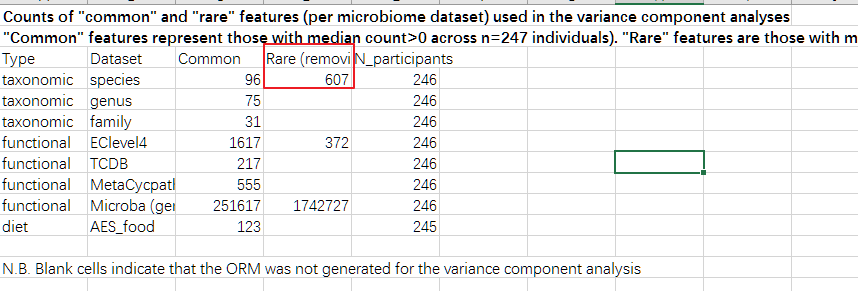

另外在后续对功能基因的分析时也是将分析集中于前面发现的Romboutsia timonensis菌种相关的基因。
当然这是受限于样本数量的因素,聚焦于普遍的高丰度的菌属和基因,但是也有很大可能丢失了可能的联系。
综上,文章否定的是菌群与自闭症之间的直接关联,与之相关文章识别到了自闭症与健康儿童间的差异菌(Romboutsia timonensis,经过年龄、性别、饮食偏好调整之后),以及菌群与重复刻板行为存在显著相关(Fig. 4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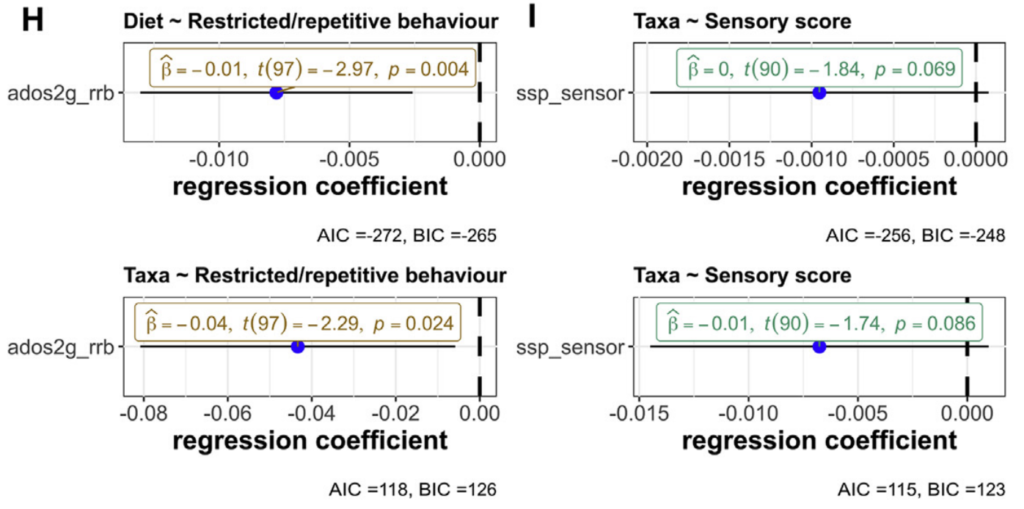
在这样的事实前面,文章依然要强行否认自闭症与菌群的关系,作者的行为很让人费解。
对此,网友们也各抒己见,就该文发表了一些见解:
他们的研究甚至没有试图确定:微生物群是否在自闭症谱系障碍中起驱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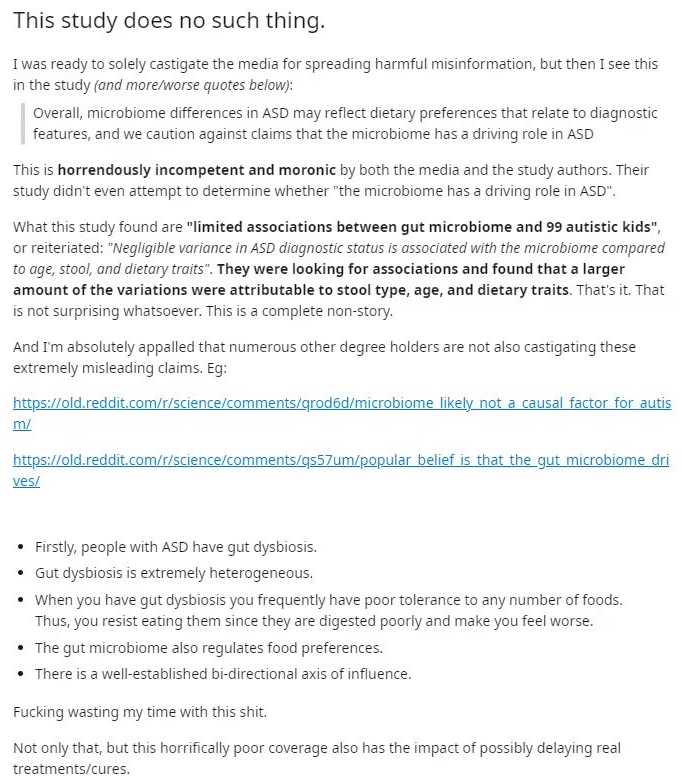
他们自己的研究需要收费,这让事情更糟糕。人们必须付费去看他们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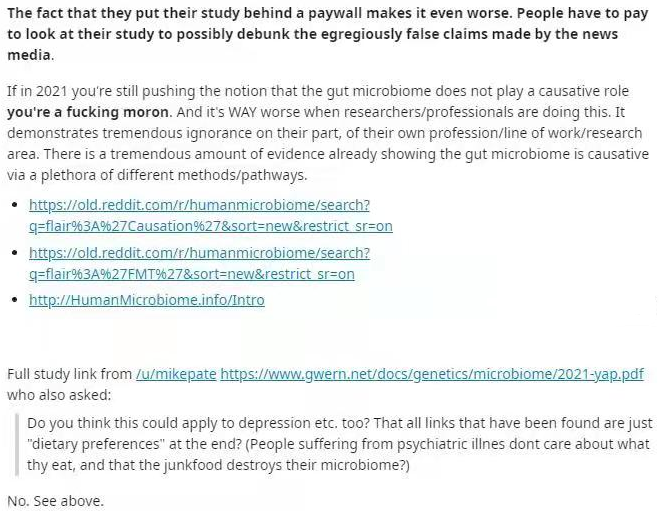
我们认为,以下系列问题仍有待回答
1. 他们的自闭症儿童都属于主要集中在轻度或者边缘程度,这个样本选择是否能代表自闭症的全部群体还存疑;
2. 如果将饮食归因于挑食等问题,那么在临床实践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正常孩子也有挑食。研究者如果要说明菌群和挑食等行为有关而不是自闭有关,那么应该要设置一组挑食的健康对照儿童,才能彻底屏蔽这个因素的可能影响;因为作者明确表示饮食和自闭症有关,而不认为菌群和自闭症有关;
3. 这些样本的分布是否有跨地区特点?如果有,那么区域也会带来极大的差异,如菌群、饮食习惯等等,如何规避这个的影响?
《cell》原文:doi.org/10.1016/j.cell.2021.10.015

谷禾健康

肠道菌群是居住在肠道中各种微生物。微生物群的建立甚至在个体出生之前就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并在体内持续存在,直到个体死亡。这些微生物群的组成是宿主特定的,在个体的一生中不断进化,并且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胎龄、分娩方式、饮食(母乳与配方奶)、卫生、抗生素,激素、疾病、衰老等都会影响并塑造肠道菌群。肠道菌群的定植、发育、成熟、稳定,老化与我们人类发育以及免疫成熟等高度吻合,不同阶段不同部位的菌群的构成以及丰度有不同特征。
肠道细菌是免疫系统发育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肠道菌群的变化可能是许多炎症性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而生活方式的改变可能改变了肠道菌群的初始发育或稳定维持。
本文从肠道菌群的功能,初始构建,到菌群健康/失衡的状态,以及相应的改善措施等进行全面阐述。
肠道菌群,居住在肠道(宿主)内的所有本土细菌的总和,被视为一个器官,执行着一系列重要的、对健康至关重要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无法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复制。
研究人员通过比较无菌实验动物(没有任何肠道菌群)和正常菌群对照动物来确定这些功能。这些发现也在人群中得到了证实。
以下是肠道菌群最重要功能的简要概述:
◥ 粪便中的水分滞留
粪便主要是由水组成(平均水含量75%;各项研究的平均范围为63-86%)。单细胞生物,如细菌,主要含有水,被无法穿透的膜包围。
◥ 形成正常粪便
由于细菌是正常粪便中最主要的成分,它们的缺失可能会导致持续性慢性腹泻。
◥ 生产必需维生素
细菌会合成各种物质,包括某些复合维生素 B、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K,这些物质对血液正常凝固至关重要。
◥ 保护肠道上皮(粘膜)免受病原体侵害
正常的肠道菌群控制着不良细菌的数量,例如白色念珠菌(酵母)或大肠杆菌的感染性菌株。保护机制有很多种,食物供应的竞争、对肠粘膜的粘附、维持所需的 pH 值平衡以及产生过氧化物和酶,从而杀死外来细菌。
◥ 组织发育和再生
与健康动物相比,无菌实验动物的肠粘膜(上皮)和淋巴组织(派尔氏斑)发育不良,肠道健康黏膜薄弱、免疫淋巴组织不发达等存在许多缺点。
◥ 免疫
正常肠道细菌负责实现吞噬作用:吞噬细胞在全身范围内破坏致病细菌、病毒、过敏原和其他异物,吞噬细胞是负责非特异性(抗体前)免疫系统防御的专门血细胞。
生命的前三年是可塑性增强的时期,肠道微生物群的发育很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婴儿期人与人之间的肠道微生物组差异变化最大,在成年期变得更加相似。
★ 婴幼儿
当婴儿出生后,在几口初乳后,大肠得到“培养”,初乳是一种淡黄色的液体,包含母亲的细菌,富含必需的营养。初乳先于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母乳流出。这个过程在母乳中继续,新生儿的肠道菌群在第6个月开始逐渐成熟,直到“成人”状态。
肠道微生物群的发育及主要影响环境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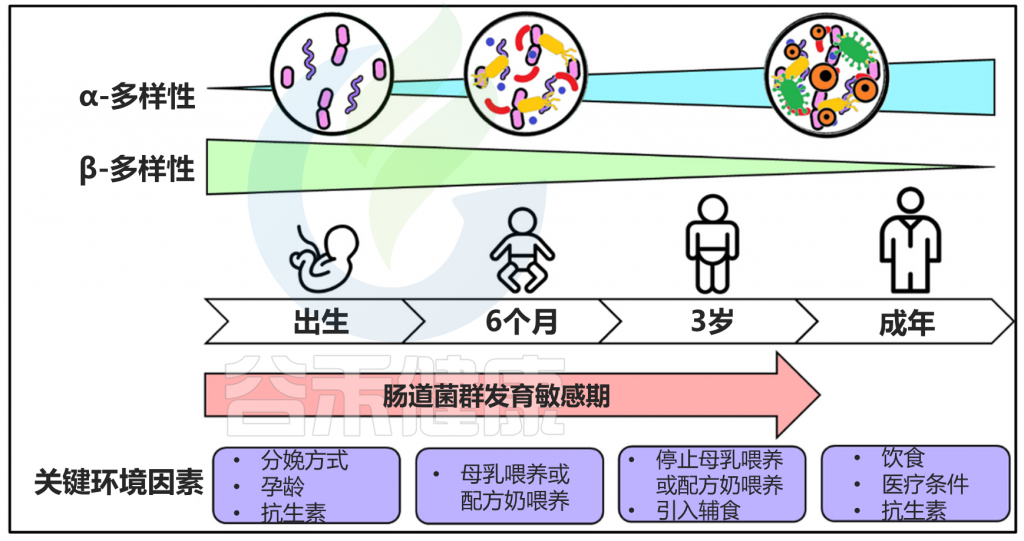

Parkin K et al., Microorganisms,2021

谷禾健康
写在前面
排便行为虽然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经历,但我们一般很少提及这个生理过程,开启“便便”这个话题并不是容易的事。如果可以抛开偏见,厌恶或者羞耻感,或许你可以尝试去了解更多这方面相关知识。如果这些知识能够普及更多人,或许世界上可以少一些胃肠道疾病患者。

排便是一个复杂而协调的过程,它整合了多个生理系统,包括神经、肌肉、激素、认知系统等。
结肠基本知识
在了解排便过程之前,我们先认识一些关于结肠结构的基本知识。
结肠和肛门直肠的神经肌肉解剖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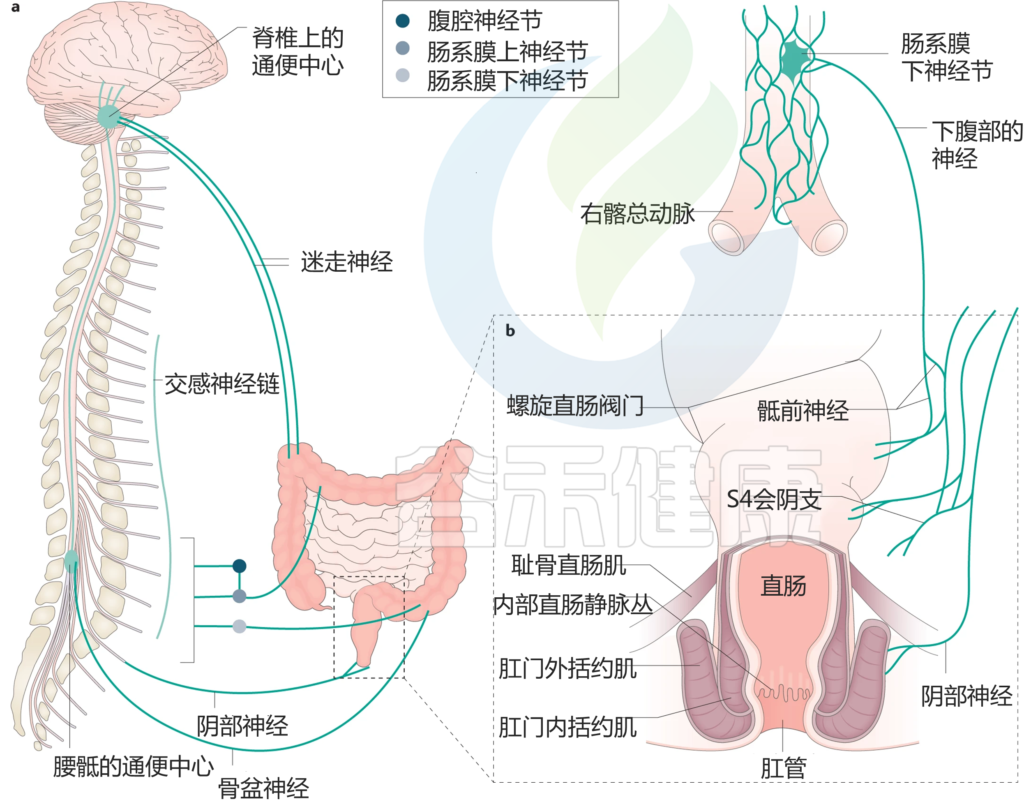
Heitmann PT, et al.,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1
a| 结肠和肛门直肠与排便生理有关的外源性感觉运动神经支配。
b| 肛门直肠的冠状图,显示了克制中结构重要性的特征。
结肠是一个粘弹性管状器官,从近端回盲肠交界处开始,远端直肠乙状结肠交界处结束。成人结肠长约130厘米,盲肠的管腔直径为60-80毫米,乙状结肠的管腔逐渐狭窄至25毫米。
结肠接受来自肠神经系统的内在神经支配,来自腰神经的外在交感神经支配,以及来自迷走神经(近端结肠)和盆腔内脏神经的外在副交感神经支配,这些神经支配结肠的感觉运动功能。
便便的产生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体内经历了什么?是如何变成粪便排出的?
进食的时候,食物与唾液相混合,唾液浸湿食物,同时也含有消化淀粉和脂肪的酶。
随后食道将食物推向胃。胃酸、胃液、酶进一步分解,完成后食物就到了小肠。
在胰腺、胆囊、微生物群的帮助下,脂肪、蛋白质、微量营养素等进一步被分解,通过小肠吸收后到肝脏,剩下的部分则转到大肠。
大肠吸收水分、电解质后产生的粪便进入直肠。直肠积累多了就会向大脑发出信号,大脑考虑现在是否是适合排便的时间。
思考的结果如果是适合的,那么大脑就会向肛门括约肌发出信号,让它放松…
排便过程
关于排便过程,这里主要涉及四个阶段:基础阶段、排出前阶段、排出阶段、结束阶段。下图详细说明了在每个阶段中为保持自制或促进排便所发生的具体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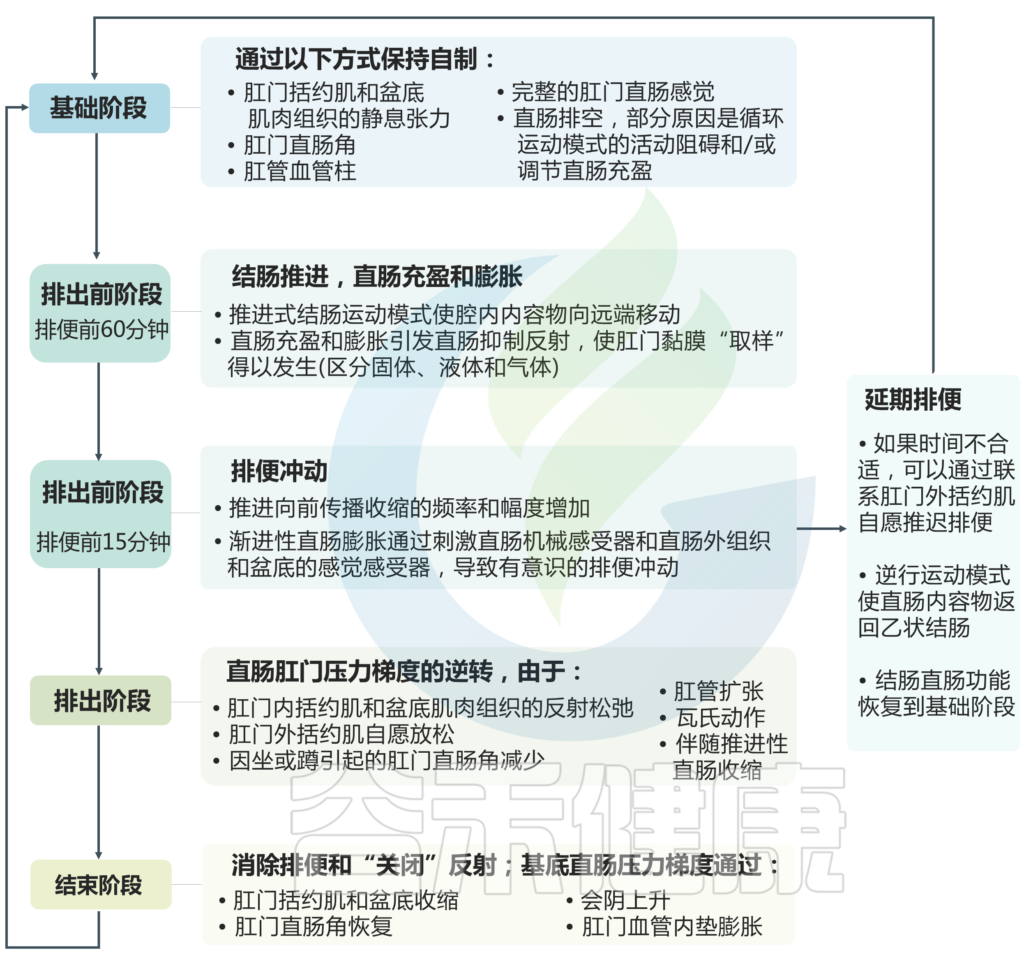
Heitmann PT, et al.,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