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AS L23010
CNAS L23010

 国家高新企业 | ISO9001认证 | 肠道健康精准检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 专精特新企业
国家高新企业 | ISO9001认证 | 肠道健康精准检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 专精特新企业 二级病原微生物安全实验室
二级病原微生物安全实验室- 联系电话:+13336028502
- +400-161-1580
- service@guheinfo.com


谷禾健康

小克里斯滕森氏菌(Christensenella minuta)是一种革兰氏阴性、不产生孢子、不运动的细菌:它属于厚壁菌门,这是细菌界中最大的门之一,包括多种对人类健康有重要影响的细菌。
在厚壁菌门下,C.minuta属于梭菌纲,这一纲的细菌多为厌氧菌,能在缺氧的环境中生长。梭菌目是梭菌纲下的一个目,包含了多种与消化道健康密切相关的细菌。
在梭菌目下,C.minuta属于Christensenellaceae属,这是一个与肠道健康紧密相关的科。由Christensenella minuta和少数其他菌种组成的属。
Christensenella minuta于2012年首次从健康人类粪便中发现,被认为是新一代益生菌。克里斯滕森菌科(Christensenellaceae)及其成员Christensenella minuta已被证明具有许多健康益处。
研究表明,Christensenella minuta在2型糖尿病和肥胖等代谢紊乱以及炎症性肠病中的丰度显著下降。其相对丰度与低 BMI 指数相关的瘦表型呈正相关。
除此之外,支气管哮喘和过敏性疾病、肾结石、情感障碍、甲状腺癌、粘膜类天疱疮、多囊卵巢综合征和复发性口疮性口炎等疾病中Christensenella minuta的丰度也较低。
Christensenella minuta能够代谢多种碳水化合物,例如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果胶,产生乙酸和丁酸等短链脂肪酸,这些物质不仅对肠道健康有益,还能调节宿主的代谢过程。
C.minuta通过几种机制影响代谢健康,包括使肠道微生物群重新正常化、产生功能性短链脂肪酸、抑制脂肪生成、维持肠道上皮完整性以及通过胆汁酸代谢调节能量代谢。
此外,C.minuta还通过抑制NF-κB信号通路和促炎细胞因子IL-8的分泌来缓解炎症性肠病。
C.minuta还可能对患有过敏性疾病的患者大有裨益,因为它可以改善肠道通透性并减轻全身炎症。而患有哮喘、湿疹和食物过敏的患者更容易出现“肠漏”,这被认为是导致疾病发病和诱发病情的一个因素。
鉴于其能够限制肠道干细胞增殖,未来C.minuta衍生的益生菌也可能对恶性肿瘤患者有益,尤其是结肠癌患者。
此外,Christensenella minuta显示出与其他潜在有益菌株的强烈相关性;由于C.minuta能够产生短链脂肪酸或塑造酸性环境,有利于其他有益菌(如Akkermansia muciniphila和Roseburia faecis)或与传统益生菌菌株(如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长,C.minuta还能够产生氢气,为M.smithii提供代谢底物(它利用H2和CO2产生甲烷),同时会抑制如克雷伯菌、大肠杆菌等机会性病原体的定值和增殖。
本文从基本属性、人群分布、Christensenella minuta的丰度与一些人体疾病(如肥胖、炎症性肠病和 2 型糖尿病)中的关联,以及与其他细菌的相关性,讲述了可能成为新一代益生菌的Christensenella munita。更好的了解Christensenella可以为基于肠道微生物群的个性化药物或疗法铺平道路。
▸ 发现历史
小克里斯滕森氏菌(Christensenella minuta)(DSM 22607) 于2012年通过 16S rRNA 测序发现,并首次从健康日本男性的粪便样本中培养出来。
2021年,发现了另一个C.minuta菌株DSM33407。其序列与菌株DSM22607有 99% 的一致性,并表现出相似的微生物学特性。次年,另一株菌株C.minuta DSM 33715 被公布并登记。
此外发现了两个新的细菌物种Christensenella massiliensis和Christensenella timonensis ,经 16S rRNA 测序,它们与C. minuta的序列相似性分别为 97.4% 和 97.5%。
而Caldicoprobacter oshimai JW/HY-331 T、Tindallia californiensis DSM 14871 T和Clostridium ganghwense JCM 13193 T是最近的亲属。
▸ 基本属性
从分类学上讲,Christensenella minuta属于厚壁菌门、梭菌纲和梭菌目。该细菌以丹麦微生物学家 Henrik Christensen 的名字命名,其种名反映其小巧的体型(Minuta在拉丁语中是“小”的意思)。该菌株的基因组相对较小,由大约150万个碱基对组成。
Christensenella minuta的细胞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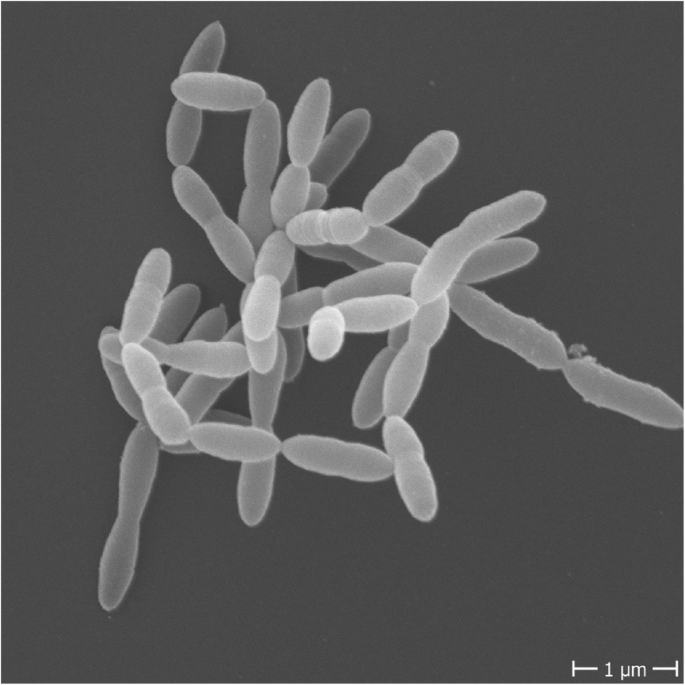
doi: 10.1186/s12915-019-0699-4.
Christensenella minuta是一种小型杆状细菌,末端呈锥形、大小从0.5毫米到1.9毫米不等、革兰氏阴性、不产生孢子、不运动的细菌,可形成圆形、几乎无色的菌落。菌落的平均尺寸为:宽度0.507±0.04μm、长度1.27±0.28μm、直径0.5–1.0μm,单独或成对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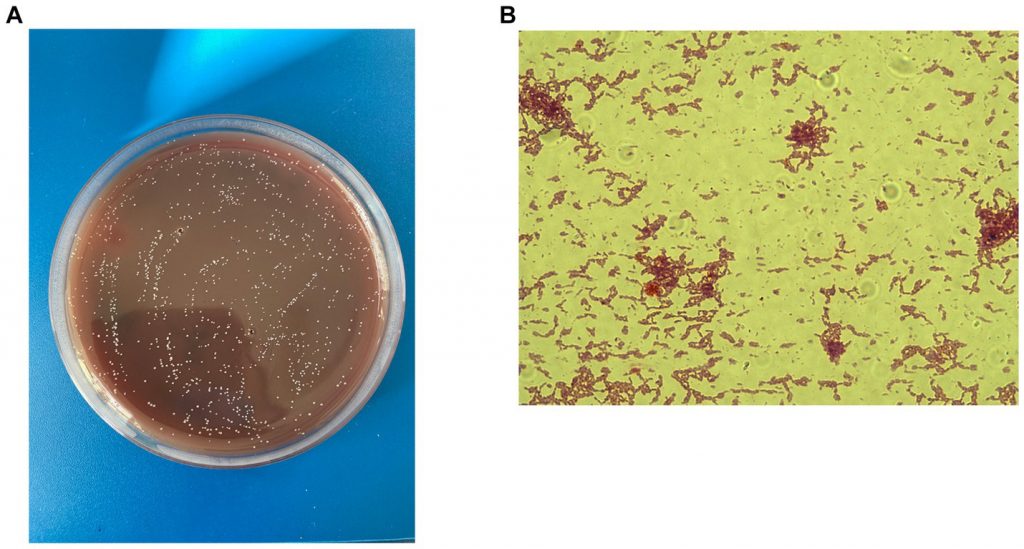
Ignatyeva O,et al.Front Microbiol.2024
A)革兰氏染色;B)在Schaedler琼脂上生长的菌落
-暴露于空气中会显著降低活性
它最初被描述为严格厌氧的;然而,后来的研究表明,它可以耐受氧气数小时。与普遍看法相反,暴露在大气中不会立即杀死细菌,而是会降低其活力。Christensenella minuta在37–40°和pH7.5时生长最快。它不是特别挑剔,可以在各种培养基中生长。
Christensenella minuta具有边界清晰的细胞壁,由丙氨酸、谷氨酸、丝氨酸和LL-二氨基庚二酸组成,这些细胞壁与半乳糖、葡萄糖、鼠李糖和核糖作为全细胞糖连接。
-对氨苄西林和四环素有抗性
菌株DSM22607的胆汁抗性为20%,而菌株 DSM33715的胆汁抗性高达80%。
对氨苄西林和四环素有抗性,但对氯霉素、克林霉素、美罗培南、甲硝唑、莫西沙星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
-可以利用多种单糖,但无法代谢色氨酸
在碳源利用方面,Christensenella minuta显示出对多种碳水化合物的利用能力,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果胶等。这些碳水化合物在肠道中不易被宿主消化酶分解,但C. minuta能够通过其独特的酶系统进行发酵,从而获取能量和营养物质。
C.minuta可以利用多种单糖,如葡萄糖、D-木糖、L-阿拉伯糖、L-鼠李糖和D-甘露糖,进行糖酵解发酵。C. minuta对葡萄糖的主要发酵产物是短链脂肪酸(乙酸和丁酸)。此外,已证明它可以通过发酵转化有机底物以产生大量氢气。
C. minuta对过氧化氢酶、氧化酶和脲酶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它也不能还原硝酸盐,也不能代谢色氨酸。最近, C. minuta菌株之一 DSM 22607被证明能产生一种新型胆盐水解酶(BSH)。
克里斯滕森菌科(Christensenellaceae)成员遍布各大洲。它们生活在各种动物的微生物群中,从蟑螂和蜥蜴到鸟类和哺乳动物,包括人类。这些细菌主要存在于胃肠道中,但也存在于灵长类动物的呼吸道和泌尿生殖道。
▸ 不同种族和性别之间丰度差异显著
Christensenella minuta作为健康成人结肠中的亚优势共生微生物种群,约占细菌总种群的0.2%到2%。其流行率在个体之间差异很大。在人群中,与克里斯滕森菌科(Christensenellaceae)不同相对丰度相关的特征包括种族和性别。
例如,对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2000多名不同种族的个体进行了研究,报告称荷兰受试者的Christensenellaceae科相对丰度最高。同样,比较了1673名居住在美国的人种族间微生物组差异,报告称与其他种族相比,亚太岛民的粪便样本中Christensenellaceae科的总体代表性较低。

一项研究还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中Christensenellaceae的相对丰度更高,在动物中也报告了类似的观察结果。这些种族和性别差异的根本原因尚不清楚。
▸ 百岁老人和瘦体型的人群中丰度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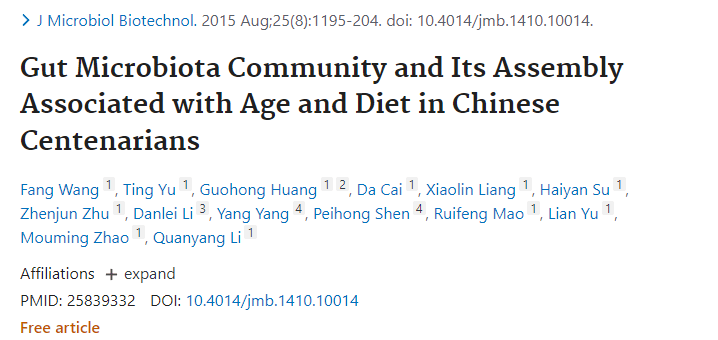
还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意大利和韩国等国,百岁老人和超百岁老人体内的Christensenellaceae相对丰度高于年轻人群,因此Christensenellaceae可能与人类长寿有关。
针对多个地理位置的相对年轻个体的研究也发现了Christensenellaceae与年龄的正相关的关系 。鉴于这些研究均未对同一个体进行长期跟踪,因此 Christensenellaceae 与年龄的关联可能反映的是队列效应,而非年龄效应。
例如,随年龄而变化的饮食模式可能会影响这种关联,或者较早出生的个体体内的Christensenellaceae含量可能一直高于较晚出生的个体。
基于 16S rRNA 基因的肠道微生物群检测,该菌群在瘦体型个体中较为丰富。M.smithii是最丰富的产甲烷菌,它利用H2和CO2(C.minuta细菌发酵膳食纤维的产物)产生甲烷,表明以H2为基础的共营养与瘦表型和健康状态相关。这表明C.minuta和M.smithii之间存在跨物种氢转移,并且这两个物种与瘦表型呈正相关。
▸ 炎症性肠病等疾病中丰度降低
研究发现,C. minuta在健康个体的肠道微生物群中普遍存在,但在患有炎症性肠病(IBD)等特定疾病的个体中,其丰度显著降低。
这种分布的差异性提示了C. minuta在维持肠道健康和预防疾病方面可能具有重要作用。
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Christensenella minuta在人体健康和疾病中的重要作用。Christensenellaceae与多种代谢过程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这种细菌在调节宿主的能量平衡、脂质代谢、脂多糖代谢、抗炎作用以及维持肠道屏障功能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Christensenellaceae的丰度与肥胖、糖尿病、炎症性肠病等多种疾病的风险呈负相关。它还与健康衰老有关。在短短10年内,已经积累了大量证据表明,Christensenellaceae在许多疾病中显著减少。
Christensenellaceae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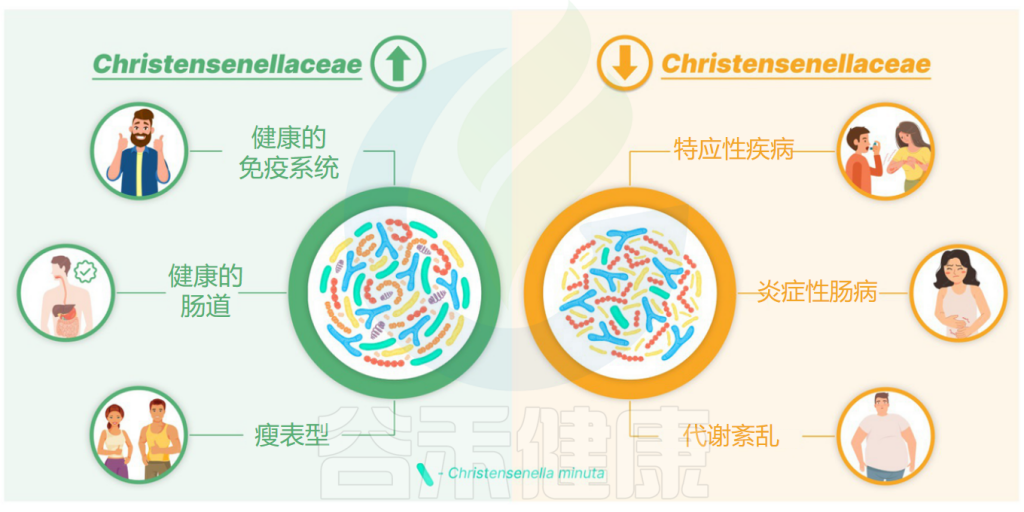
Ignatyeva O,et al.Front Microbiol.2024
▸ 肥胖患者中减少 ↓
肥胖是一种复杂的疾病,由体内过多的脂肪堆积引起,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许多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各种癌症、2 型糖尿病、高血压和中风,以及精神健康问题都与肥胖有关。
研究认为,肥胖的病因与肠道菌群失调和先天性瘦素缺乏有关。已提出了几种机制将肥胖的发生与肠道菌群组成联系起来,这些机制是通过代谢和炎症活动的功能障碍实现的。
肥胖的发生涉及肠道菌群和宿主,是通过与近端器官的直接相互作用或通过代谢物分泌与肝脏、脂肪组织和大脑等远处器官的间接相互作用介导的。
在许多研究中,C. minuta被反复与其治疗性抗肥胖潜力联系在一起,这表明C. minuta在肠道微生物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与宿主代谢的调节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C. minuta发挥治疗性抗肥胖作用的机制包括调节肠道上皮完整性、产生短链脂肪酸、改善脂质代谢和胆汁酸代谢。
Christensenella minuta抗肥胖作用的潜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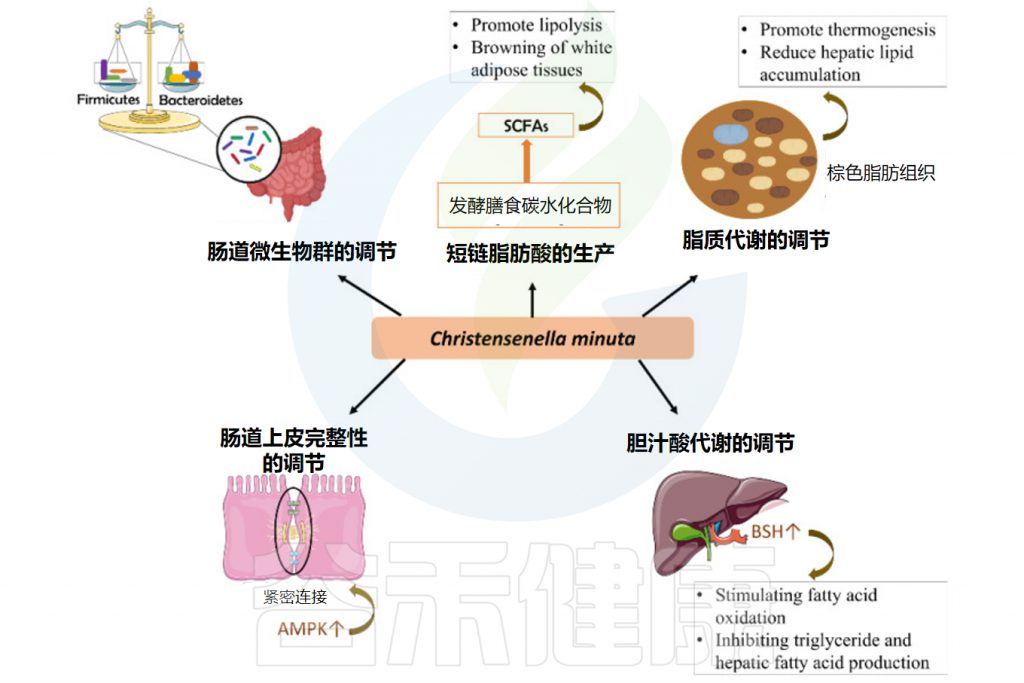
Ang WS,et al.Foods.2023
-产生短链脂肪酸来调节能量代谢和肠道稳态
研究发现C. minuta DSM 22607以5:1的比例产生高水平的乙酸盐和中等水平的丁酸盐,而不产生丙酸盐。
同时,在近端和远端结肠中均发现了低水平的支链脂肪酸,即异丁酸、异戊酸和异己酸,这表明C.minuta可降低细菌蛋白水解并刺激碳水化合物发酵。
肠道菌群通过短链脂肪酸(SCFA)产生参与调节能量代谢和肠道稳态。SCFA 被吸收并充当宿主体内葡萄糖和脂质代谢的能量来源或前体。SCFA可能通过G蛋白偶联受体,即游离脂肪酸受体2(FFAR2)和3(FFAR3)与结肠、肝脏、肌肉和脂肪组织相互作用。
-调节瘦素水平,减少脂肪的生成
此外,短链脂肪酸会上调抑制饥饿的瘦素合成,抑制脂肪生成并促进脂肪分解。研究评估了丁酸盐的施用可以通过促进脂肪细胞形成和脂肪组织褐变来减少能量摄入,增强脂肪氧化和能量消耗,从而治疗和预防肥胖。
这些由肠道微生物群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还与结肠粘膜中的肠内分泌细胞相互作用,诱导释放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肽YY(PYY)。这些激素进入体循环并对许多器官和组织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胃和胰腺。GLP-1和PYY共同防止胃排空过快,抑制酸分泌和运动,减缓胃肠道运输,从而导致食欲减少和食物摄入量减少。GLP-1还能刺激胰岛素分泌并防止胰腺β细胞衰竭。
–C.minuta改善了肠道上皮完整性,增强肠道屏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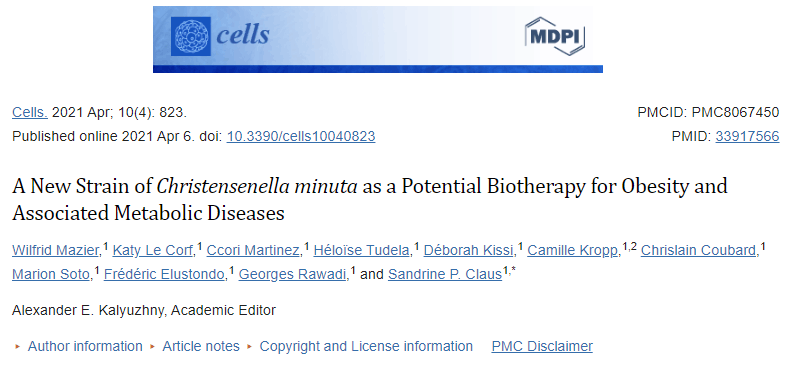
此外,C. minuta合成的两种短链脂肪酸可能都参与维持肠上皮屏障。例如,乙酸和丁酸可通过与G蛋白偶联受体GPR43和GPR109A 结合来激活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3(NLRP3)炎症小体,这会增加IL-18的释放,促进上皮细胞的修复。
丁酸能稳定缺氧诱导因子(HIF),后者是屏障保护和组织再生的关键分子,它上调紧密连接蛋白,增加杯状细胞的黏蛋白生成,从而增强肠道屏障。
一项研究表明,C. minuta在体外和涉及高脂饮食组的动物研究中改善了肠道紧密连接蛋白(ZO-1)、闭合蛋白(OCLN)和紧密连接蛋白-1(CLDN1)的表达。
肠道通透性增加被认为是脂肪诱导性肥胖的一个驱动因素,与肠道菌群失调和肠道炎症有关。已证实肥胖小鼠的紧密连接减少,这表明肥胖是由肠道通透性增加和跨上皮阻力降低引起的。
肠道紧密连接蛋白下调可导致肠道渗漏,其中脂多糖细菌物质和其他炎症介质通过紧密连接扩散并与宿主免疫细胞相互作用,导致低度炎症、暴食并最终导致体重增加。
-调节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的积累
此外,与肥胖水平或体脂相关的身体质量指数(BMI)也与肠道中C.minuta的丰富程度密切相关。调节脂肪酸的合成和氧化以及抑制脂肪生成对体脂和体重有有利的影响。
早期的一项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中C.minuta的存在与肥胖降低之间存在联系。一项针对C.minuta的干预研究表明,在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模型中,肝脏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的积累受到阻碍。这一发现与基因表达水平一致,在补充了C.minuta的动物模型中,编码肝脏葡萄糖激酶的gck基因受到强烈抑制。
葡萄糖激酶的过度表达促进了糖的过度吸收、肝脏脂质积累和棕色脂肪组织(BAT)中产热蛋白的下调,导致肥胖。从机制上讲,增强BAT中的脂肪组织产热作用并诱导白色脂肪组织(WAT)褐变可导致体重减轻。
-通过调节胆汁酸代谢来发挥抗肥胖能力
胆汁酸代谢对于调节葡萄糖和能量代谢、肠道完整性和免疫力至关重要。胆汁酸代谢的改变与肥胖密切相关。胆汁酸代谢通过刺激脂肪酸氧化和抑制甘油三酯和肝脏脂肪酸的产生。
C.minuta的抗肥胖潜力还通过结肠中的胆酸/牛磺胆酸(CA/TCA)比率来展现。这一发现意义重大,为抗肥胖与糖分解代谢以及初级胆汁酸的有效解离之间的关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C.minuta菌株 DSM33407和DSM22607在80%胆汁存在48小时的情况下均对胆汁酸具有高度耐受性。胆汁酸水解酶(BSH)基因已在两种C.minuta菌株中被鉴定,并且由于其水解结合胆汁酸的强能力而高度表达。
C.minuta还通过法尼醇x受体和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TGR5)促进胆汁酸代谢,而 TGR5 在肠道中高度表达。一些体内研究表明,肠道生态系统中BSH的高水平表达被认为是抗肥胖的关键调节因素,可显著降低体重、肥胖、循环低密度脂蛋白(LDL)胆固醇和甘油三酯。
注:BSH活性是肥胖控制的关键机制目标。利用具有高BSH活性的细菌菌株来丰富肠道微生物群可能是预防和控制肥胖的一种策略。
▸ 炎症性肠病中减少 ↓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影响胃肠道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主要有两种类型: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每种类型都有不同的生理症状。研究发现,IBD患者的微生物组成会发生变化,其特征是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的比例下降。
-抑制NF-κB信号通路和IL-8来减轻结肠炎症
肠道菌群失调伴有短链脂肪酸组成的变化,随后是肠道屏障完整性的破坏,最终通过免疫系统调节引发炎症反应。尽管 IBD 的病因仍不太清楚,但研究表明,它们是由不受控制的炎症反应引发的,与白细胞介素8(IL-8)细胞因子和活性氧(ROS)的增加有关。
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的Christensenellaceae会减少。在发作前立即观察到静止期CD患者中Christensenellaceae的丰度显著下降,这可能表明它们在疾病进展中发挥了作用。在腹泻患者中也观察到了Christensenellaceae的丰度较低。
最近的体外和体内研究表明,C.minuta具有强效抗炎和免疫调节特性。C. minuta通过抑制 NF-κB 信号通路和促炎细胞因子IL-8的分泌来减轻结肠炎症。
-克罗恩病患者缺乏C.minu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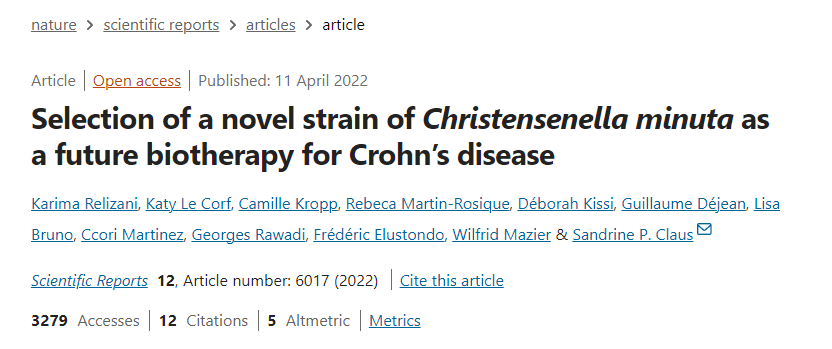
一项对C.minuta的介入研究表明,克罗恩病(CD)患者中缺乏Christensenella minuta(C.minuta),并且有记录证明它们会在人类上皮细胞中诱导抗炎作用,这支持了它们作为一种新型生物疗法的潜力。
在两种不同的急性结肠炎动物模型和一种人类肠道细胞系中,C.minuta限制结肠损伤、促进粘膜愈合并降低因炎症引起的中性粒细胞(特别是髓过氧化物酶和嗜酸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的活化。
在C.minuta治疗动物模型中,肠道炎症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人脂质运载蛋白-2(LCN-2)的浓度降低。在基因层面,携带克罗恩病风险基因 IL23R 的个体体内与C.minuta相关的微生物丰度降低,表明肠道微生物组受到宿主遗传学的影响。
据报道,当小鼠补充C.minuta时,IL23R 保护性编码变体会增加,从而预防克罗恩病。C.minuta还会产生丁酸,通过丁酸受体 GPR109a 来控制脂肪细胞、肠上皮细胞和免疫细胞中的炎症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C.minuta的抗炎功效已被证实与美沙拉嗪(也称为5-氨基水杨酸(5-ASA),一种用于治疗IBD的药物)相似。
▸ 2型糖尿病患者中减少 ↓
2型糖尿病(T2D)是一种复杂的代谢和内分泌功能障碍,其特征是胰岛素抵抗、胰腺β细胞功能障碍、低度全身炎症、肠道菌群失调、肥胖和其他内分泌疾病引起的高血糖。
中药是一种源自天然产物的补充药物,在治疗代谢综合征方面具有潜力。口服中药干预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但由于其活性成分(如黄酮类化合物)的亲脂性较差,因此生物利用度较低。肠道菌群的生物转化促进药物的吸收,这对药理学有重大影响。
-增加C.minuta有助于改善糖尿病
中药成分可能会调节宿主肠道菌群的数量。黄芪苓化散(HQLHS)由黄芪、灵芝、桦褐孔菌和苦瓜组成,是专门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中药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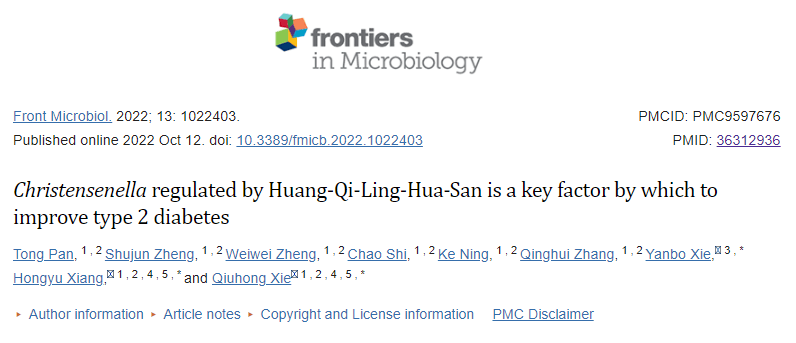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小鼠模型中,HQLHS抑制了致病菌并丰富了有益菌,特别是C.minuta和Christensenella timonensis。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表明HQLHS显著增加了小鼠肠道菌群中Christensenella的相对丰度。该研究还描述了C.minuta对肝脏代谢的影响,为理解C.minuta在糖尿病治疗和控制中的药理机制奠定了基础。
-减少氧化应激、改善葡萄糖代谢
在同一项研究中,C. minuta DSM 22607 降低了糖尿病大鼠体内的氧化应激、色氨酸和酪氨酸等糖尿病诱因。抗氧化酶和脂质过氧化生物标志物 MDA 的水平也得到了控制。
C. minuta的抗糖尿病特性有多种机制,例如改善糖脂代谢、通过抑制肠道葡萄糖转运中SGLT1和GLUT2的表达来抑制葡萄糖吸收、促进GLP-1分泌以刺激胰岛素抵抗并调节葡萄糖稳态。
▸ 支气管哮喘和过敏性疾病中减少 ↓
-C.minuta丰度较高时患哮喘的可能性较低
小克里斯滕森氏菌(Christensenella minuta)还与支气管哮喘和过敏性疾病有关。研究发现,粪便微生物组中富含C. minuta的儿童患湿疹和对吸入性过敏原致敏的可能性较小。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环境中克里斯滕森菌科的丰富程度可能在支气管哮喘中发挥重要作用。分析了从健康儿童以及患有哮喘的儿童和成人家中收集的灰尘的宏基因组学谱。他们发现,克里斯滕森菌科在“健康”房屋的灰尘中显著过多,而在“哮喘”房屋的灰尘中却很少。
其他一些研究还发现:肾结石、情感障碍、甲状腺癌、粘膜类天疱疮、多囊卵巢综合征和复发性口疮性口炎也与Christensenellaceae科丰度较低有关。
▸ 过高在一些患者中可能有害 ↑
然而,有证据表明,Christensenellaceae科的丰度较高可能与一些病理之间存在联系。在一项研究中,Christensenellaceae科的丰度较高会增加重症监护病房中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危重患者的死亡风险。
该分类单元在帕金森病患者中显著富集,尤其是在临床特征较差的患者中。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多发性硬化症和神经性厌食症的人中也观察到了Christensenellaceae科的丰富度增加。
Christensenellaceae科与健康表型或疾病之间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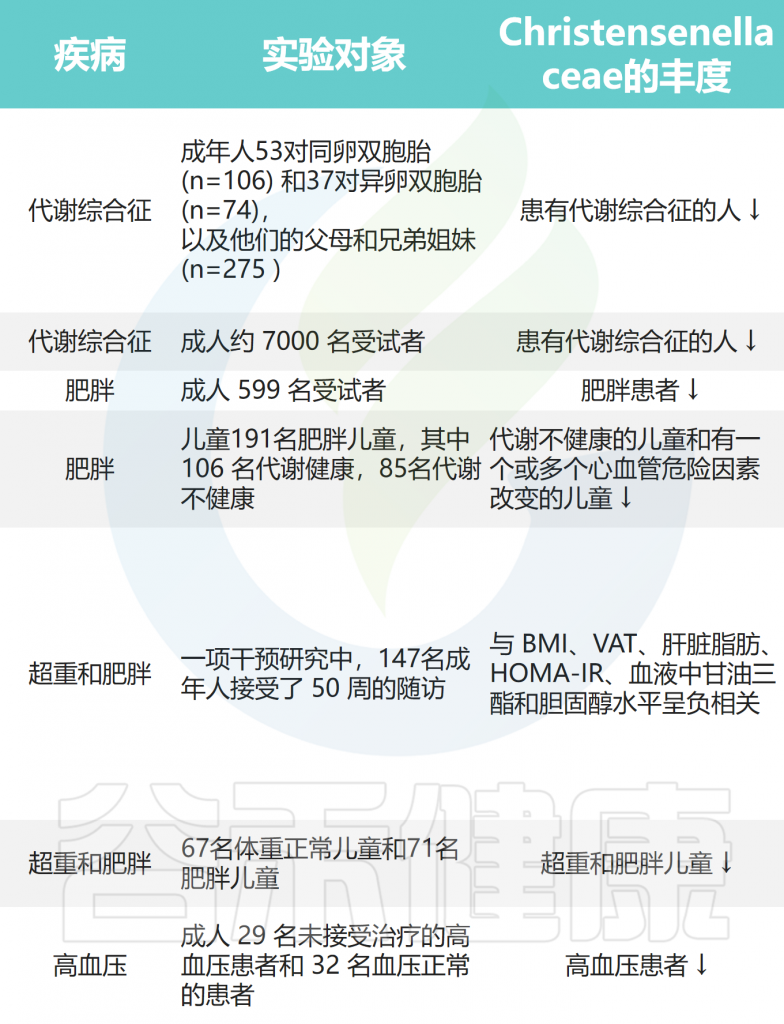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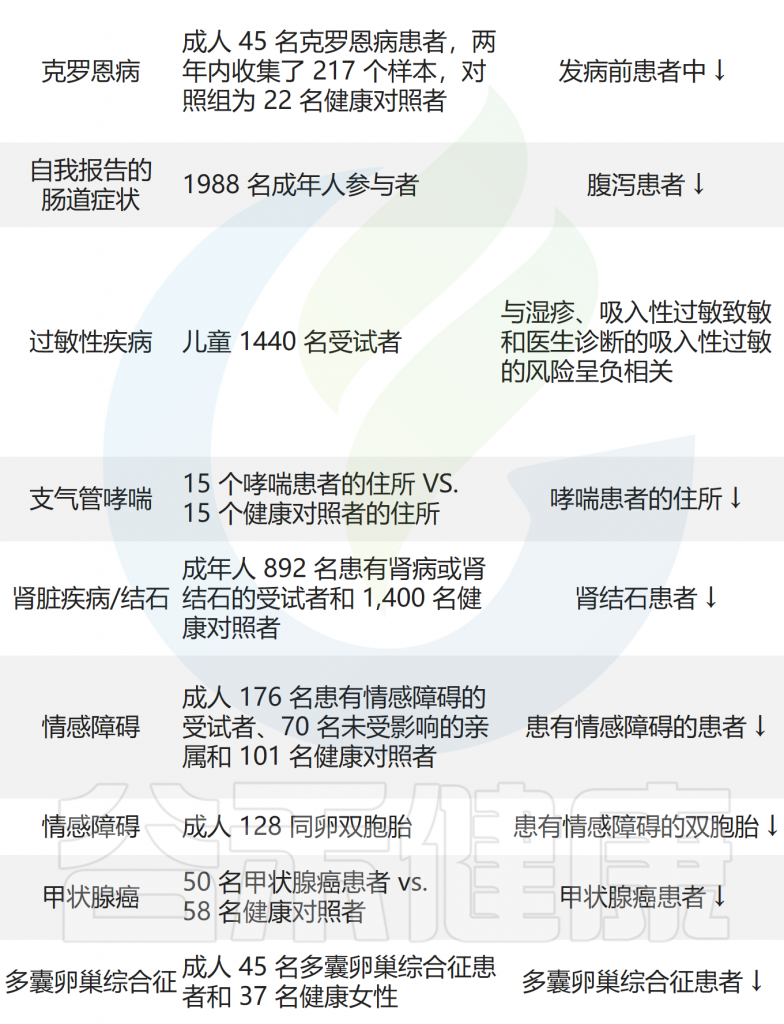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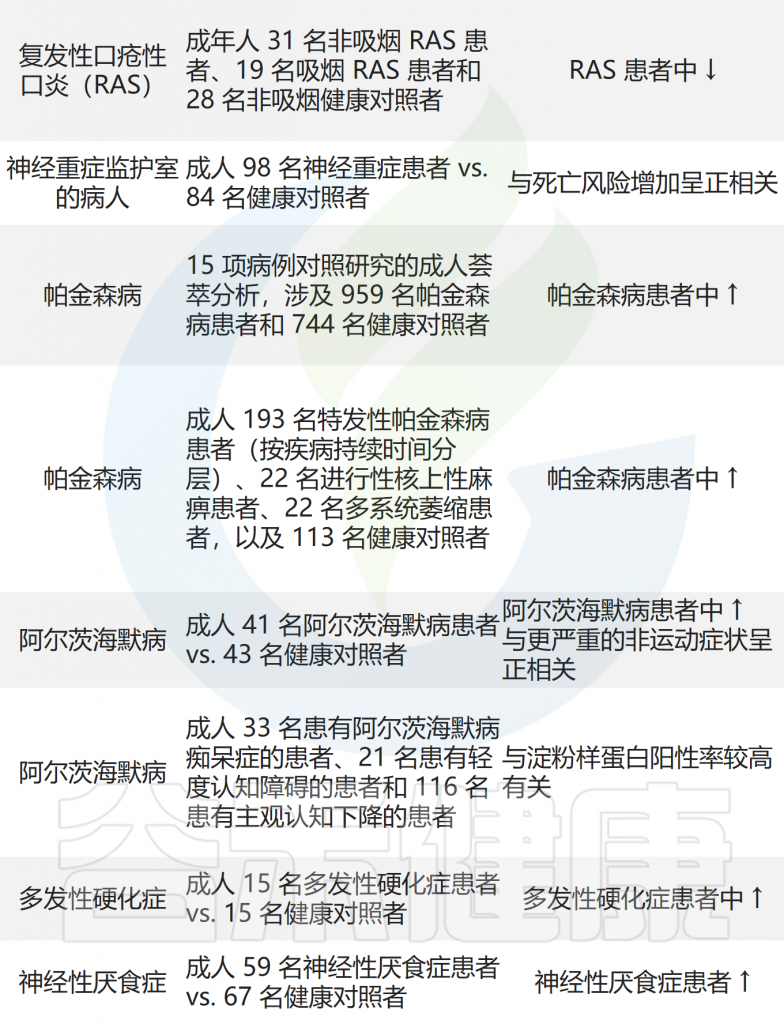
Ignatyeva O,et al.Front Microbiol.2024
C.minuta和Christensenellaceae科的有益作用可能归因于它们与肠道中许多其他细菌群落相互作用的特殊能力。除了直接作用外,C.minuta还可以通过促进或限制某些分类群的生长来间接影响宿主。
-与Christensenellaceae正相关的菌群
Christensenellaceae与许多菌群呈正相关,包括:
颤螺菌属(Oscillospira)
瘤胃球菌属(Ruminococcus)
粪球菌属(Coprococcus)
普雷沃氏菌属(Prevotella)
嗜粘蛋白-阿克曼氏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
罗氏菌属(Roseburia)
-与Christensenellaceae负相关的菌群
相反,几个属与Christensenellaceae呈负相关:
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
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
梭杆菌属(Fusobacterium)
经黏液真杆菌属(Blautia)
Magamonas
▸ 能够促进一些有益菌的生长
此外, Christensenellaceae丰度越高,微生物丰富度和多样性就越高。值得注意的是,几种与之呈正相关的菌群已被提议作为新一代益生菌(Oscillospira、Roseburia)或目前已经是这种身份(Akkermansia)。
–C.minuta能够促进双歧杆菌生长
C.minuta能够促进双歧杆菌属的生长,这是通过产生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SCFAs),特别是乙酸和丁酸,这些SCFAs是双歧杆菌属的重要能量来源。这种交叉喂养关系有助于双歧杆菌属在肠道中的定植和增殖。
–C.minuta塑造适合乳酸杆菌生长的环境
C.minuta可能通过产生乳酸来降低肠道pH值,从而为乳酸杆菌属创造一个更适宜的生长环境。此外,C.minuta产生的代谢产物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激活乳酸杆菌属的代谢途径,增强其在肠道中的竞争力。
–C.minuta促进普拉梭菌生长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是一种潜在的下一代益生菌,具有高丁酸生产、抗炎和预防肠道病原体的作用。
研究发现,Christensenella minuta通过产生外源乙酸、半胱氨酸、脯氨酸和赖氨酸来交叉喂养F.prausnitzii,这些都是F. prausnitzii发酵和繁殖所必需的。从而促进了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的增殖。
–C.minuta与粪肠球菌
C.minuta与F.prausnitzii之间存在正向的相互作用。C.minuta产生的代谢产物可能作为F.prausnitzii的底物,促进其生长和SCFA的生产,特别是丁酸盐,这是一种对肠道健康至关重要的短链脂肪酸。
▸ 减少一些有害菌群
有趣的是,在存在Christensenellaceae的情况下通常会减少几种有害菌群,例如机会性病原体,已知会导致人类和动物感染的克雷伯氏菌和链球菌,以及可能导致癌症的微生物梭杆菌。
因此,我们假设C. minuta可以通过支持有益物种的生长和抑制潜在有害物种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
–C.minuta抑制克雷伯菌的定植
C.minuta可能通过竞争营养物质或产生抗菌物质来抑制K.pneumoniae等潜在的病原菌。这种竞争和抑制作用有助于维持肠道微生物群的平衡,防止病原菌的过度生长。
–C.minuta限制大肠杆菌的增殖
C.minuta可能通过调节肠道中的氧化还原电位来影响大肠杆菌的生长。由于C.minuta是严格的厌氧菌,它可能通过降低肠道的氧化还原电位来限制需氧菌如大肠杆菌的增殖。
▸ 与甲烷杆菌存在互作并可能影响体重
不同细菌种属很可能通过代谢物转移进行相互作用。Christensenellaceae科和甲烷杆菌科的相互作用可能影响体重指数并呈负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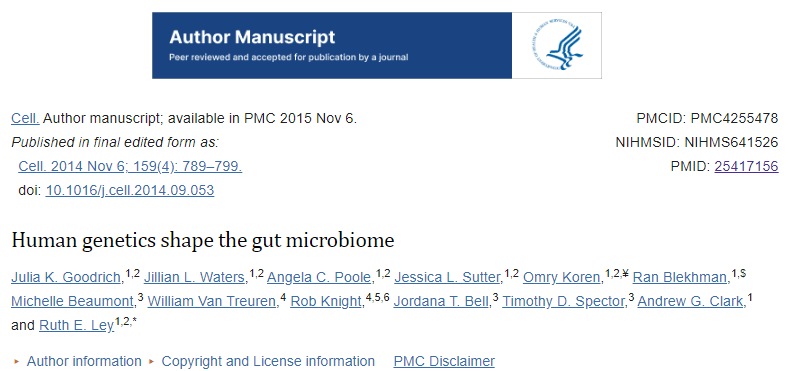
对来自10项独立研究的1821个样本进行了荟萃分析,证实了在科水平(Christensenellaceae科和甲烷杆菌科)和种水平(C.minuta和Methanobrevibacter smithii)之间均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
此外,发现了它们之间的物理和代谢相互作用。作为一种氢气生产者,C.minuta有效地支持了依赖氢气供应的M.smithii的生长。在共同培养时,C.minuta释放的氢气量足以确保M.smithii的生存力,与氢气过量的单一培养中相当。
反过来,M.smithii也能调节C.minuta的代谢,导致短链脂肪酸的产生从丁酸转向乙酸。根据观察到的乙酸盐产量的增加。除此之外,甲烷杆菌科的甲烷生产会导致碳损失和宿主可用能量减少,这可能部分解释了该细菌与体重减轻之间的关联。
Christensenellaceae可能是一种高效益生菌药物的来源,可使许多患者群体受益,尤其是那些患有代谢紊乱和炎症性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我们在下面总结了C.minuta作为益生菌在人体健康中的一些作用。
▸ 抗炎作用
C.minuta益生菌活性的所有潜在机制尚未完全了解;不过,已经取得了许多积极的进展。在一系列体外和体内实验中测试了C. minuta DSM 22607。首先,该细菌及其上清液均表现出强大的抗炎潜力,因为它们能够限制HT-29细胞中的IL-8产生,此外发现上清液还能抑制NF-kB信号通路。
从9位捐献者身上分离并测试了 32 株新的C.minuta菌株,以确定最佳候选益生菌药物。他们在一系列实验中分析了这些菌株的抗炎和保护特性,并选出了5种主要候选菌株。五种候选菌株均在体外细胞模型中阻止TNF-α刺激后的NF-kB通路激活并诱导IL-10的产生。
在动物模型中,五种菌株中的两种显著改善了TNBC引起的炎症病变,并具有明显的局部抗炎作用。
此外,还证明了C.minuta菌株在体外模型中刺激人源 PBMC 产生 IL-10的能力。
▸ 保护肠道屏障
其次,C.minuta还显示出保护 TNF-α 受损的 Caco-2 细胞中肠道屏障的能力。这些结果在二硝基苯磺酸(DNBS)和三硝基苯磺酸(TNBS)诱发的结肠炎小鼠模型中得到了证实。
在这两项实验中,C.minuta表现出独特的抗炎特性,保护结肠组织的效果与5-氨基水杨酸(5-ASA)一样有效。该细菌减少了宏观和微观化学损伤,减少了结肠中的免疫细胞浸润(ICI),限制了氧化应激,并降低了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和脂质运载蛋白-2的表达。
▸ 能够产生乙酸盐、丁酸盐
实验还揭示了C. minuta的代谢作用,特别是其产生大量乙酸盐和适量丁酸盐的能力。据报道, C.minuta可以同时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中的乙酸盐和丁酸盐,而大多数微生物只能产生丁酸盐或乙酸盐其中一种。
▸ 抗肥胖能力
对C.minuta DSM22607 的抗肥胖能力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每天施用2×10^9个C. minuta菌落形成单位(CFU)可防止喂食高脂饮食(HFD)的小鼠体重增加和高血糖,但不影响它们的食物摄入量。
令人惊讶的是,食用益生菌菌株的动物和喂食正常食物的动物在体重增加方面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然而,接受载体的HFD喂养小鼠体重增加明显且快速。这强烈表明C.minuta通过改变新陈代谢而不是影响进食行为来限制脂肪堆积。
这些发现与对血清代谢标志物的观察结果相关,即高脂饮食小鼠的瘦素和抵抗素水平下降。C.minuta可能破坏了肝脏脂肪生成,这通过编码葡萄糖激酶的Gck基因表达降低来证明。
此外,益生菌菌株通过上调编码主要紧密连接蛋白的Ocln和Zo1基因,对肠道通透性具有强大的保护作用。这也可能有助于C. minuta通过限制由肠漏引起的全身炎症而发挥抗肥胖作用。
▸ 改善糖尿病
进一步证实了C. minuta的有益作用及其在代谢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的证据。使用两种Christensenella属菌株(C.minuta DSM 22607 和C.timonesis DSM 102800)治疗小鼠2型糖尿病,两种菌株均改善了许多代谢指标。
管饲益生菌可降低血糖水平、限制氧化应激、促进受损胰岛和肝细胞的修复,并抑制肝脏和结肠中几种促炎细胞因子和 TLR4 的表达。
重要的是,用C.minuta和C.timonesis治疗还上调结肠中的Zonula occludens-1和Claudin-1,从而加强肠道屏障。测试对象血清脂多糖水平下降支持了这一发现。这两种菌株还通过刺激胰高血糖素原的表达、增加血清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水平和限制肝糖异生,对代谢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体而言,C.minuta和C.timonesis改善了2型糖尿病的代谢过程并减轻了炎症反应。
▸ 免疫调节作用
C.minuta能够通过调节肠道微环境影响宿主的免疫系统。研究表明,C. minuta能够促进Th17细胞的分化,这些细胞在维持肠道免疫耐受和防御病原体入侵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此外,C.minuta还可能通过与其他肠道共生菌的复杂相互作用,间接影响宿主的免疫系统。肠道微生物群落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C.minuta通过其代谢产物和分泌物,可以影响其他菌群的生长和功能,进而调节宿主的免疫反应。这种间接调节机制为宿主免疫系统提供了额外的调节途径。
最后,C.minuta对宿主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可能还与其在肠道中的定植能力有关。研究表明,C.minuta在人体肠道中具有较高的遗传性,这意味着它能够有效地定植并长期存在于宿主肠道中。这种定植能力可能是C. minuta发挥其免疫调节作用的基础。
▸ 增加有益菌丰度,改善肠道菌群组成
此外,Christensenella菌株通过增加许多有益微生物(如双歧杆菌和Phascolarctobacterium)的丰度来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
06
调节C.minuta的策略
调节C.minuta的策略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包括饮食调节、益生菌和益生元的使用、药物治疗以及功能性食品的摄入。
▸ 通过饮食调节C.minuta的策略
调节肠道共生菌C.minuta的一种有效方法是通过饮食。
研究表明,某些食物成分可以促进C.minuta的生长和活性。例如,高纤维食物,如全谷物、豆类、坚果和水果,可以作为益生元,为C.minuta提供必要的营养物质。这些纤维在肠道中被微生物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这些物质对C.minuta的生长至关重要。
此外,一些特定的益生元,如低聚果糖和菊粉,已被证明能够特异性地增加C.minuta的数量。
▸ 益生元和合生元的应用
益生元是指能够促进肠道内有益菌生长的非消化性食品成分,而合生元则是益生元和益生菌的组合。在调节C.minuta中,益生元和合生元的应用是两个重要的策略。
益生元如多糖、半纤维素、果胶等,能够通过刺激C.minuta的生长,增强其在肠道中的竞争力。合生元则结合了益生元和益生菌的双重优势,通过提供C.minuta所需的营养物质和直接补充C.minuta,更有效地调节肠道微生物群。
▸ 药物和功能性食品的作用
在某些情况下,药物和功能性食品也可以用于调节C.minuta。例如,某些抗生素可以在必要时用来减少有害菌的数量,为C.minuta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
功能性食品,如含有特定益生菌的酸奶或补充剂,可以直接补充C.minuta,增加其在肠道中的数量。此外,一些植物提取物和天然化合物也被研究用于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包括C.minuta。
主要参考文献
Ignatyeva O, Tolyneva D, Kovalyov A, Matkava L, Terekhov M, Kashtanova D, Zagainova A, Ivanov M, Yudin V, Makarov V, Keskinov A, Kraevoy S, Yudin S. Christensenella minuta, a new candidate next-generation probiotic: current evidence and future trajectories. Front Microbiol. 2024 Jan 11;14:1241259.
Ang WS, Law JW, Letchumanan V, Hong KW, Wong SH, Ab Mutalib NS, Chan KG, Lee LH, Tan LT. A Keystone Gut Bacterium Christensenella minuta-A Potential Biotherapeutic Agent for Obesity and Associated Metabolic Diseases. Foods. 2023 Jun 26;12(13):2485.
Pan T, Zheng S, Zheng W, Shi C, Ning K, Zhang Q, Xie Y, Xiang H, Xie Q. Christensenella regulated by Huang-Qi-Ling-Hua-San is a key factor by which to improve type 2 diabetes. Front Microbiol. 2022 Oct 12;13:1022403.
Mazier W, Le Corf K, Martinez C, Tudela H, Kissi D, Kropp C, Coubard C, Soto M, Elustondo F, Rawadi G, Claus SP. A New Strain of Christensenella minuta as a Potential Biotherapy for Obesity and Associated Metabolic Diseases. Cells. 2021 Apr 6;10(4):823.
Relizani K, Le Corf K, Kropp C, Martin-Rosique R, Kissi D, Déjean G, Bruno L, Martinez C, Rawadi G, Elustondo F, Mazier W, Claus SP. Selection of a novel strain of Christensenella minuta as a future biotherapy for Crohn’s disease. Sci Rep. 2022 Apr 11;12(1):6017.
Waters JL, Ley RE. The human gut bacteria Christensenellaceae are widespread, heritable, and associated with health. BMC Biol. 2019 Oct 28;17(1):83.
Pető, Á.; Kósa, D.; Szilvássy, Z.; Fehér, P.; Ujhelyi, Z.; Kovács, G.; Német, I.; Pócsi, I.; Bácskay, I. Scientific and Pharmaceutical Aspects of Christensenella minuta, a Promising Next-Generation Probiotic. Fermentation 2023, 9, 767.
Xu C, Jiang H, Feng LJ, Jiang MZ, Wang YL, Liu SJ. Christensenella minuta interacts with multiple gut bacteria. Front Microbiol. 2024 Feb 19;15:1301073.

谷禾健康

“胖!可怎么办?”《柳叶刀》发布的一项报告称,截止2022年,全球超过10亿人患有肥胖症,超过20亿人存在超重。从1990年到2022年间,全球患肥胖症的成年人增加了一倍多,患肥胖症的儿童和青少年(5至19岁)更是增加了约3倍。超重和肥胖已成为全球日益严重的流行病。
超重和肥胖的不良影响可能不会马上体现,有时会延迟十年或更长时间。流行病学研究证实,超重和肥胖程度的增加是寿命缩短的重要预测因素。在一项心脏研究中,在30岁到42岁之间,体重每增加一磅(0.45公斤),26年内死亡的风险增加1%,在50岁到62岁之间,死亡风险增加2%。
肥胖还会引起或加剧许多健康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独立的,也有与其他疾病相关的。例如超重和肥胖增加了患高血压、冠心病和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肥胖还是2型糖尿病主要风险因素;此外,肥胖和超重人群更容易患上睡眠呼吸暂停、哮喘和其他呼吸系统问题。过重的身体还会给骨骼和关节造成巨大压力,增加骨质疏松症和关节炎的风险。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改善或是预防肥胖呢?”除了常规的“管住嘴,迈开腿”,谷禾在最近与减肥前后相关的检测中发现,在不改变其他生活方式和饮食的情况下,额外补充一定量的膳食纤维对减肥的帮助效果显著。
肠道菌群已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宿主生理和病理的重要调节器。肠道菌群调节炎症、脂肪储存和葡萄糖代谢进而影响体重和代谢健康。
而对肠道微生物群影响最大的是饮食,人类从食物中提取和储存卡路里的能力至少部分受到肠道微生物的影响。这使得饮食成为驱动人类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重要因素。
膳食纤维是一种来自植物的复合多糖,在消化过程中不被小肠吸收,并通过为微生物生长提供底物来改变肠道微生态环境。膳食纤维可能会改变微生物群的丰度、多样性和代谢,包括短链脂肪酸的产生。最近的研究表明,富含膳食纤维的饮食具有预防肥胖的潜力。
首先,膳食纤维的物理化学性质(粘性、可发酵性等)具有预防肥胖的作用,因为粘稠的纤维可以延长胃排空和小肠运输时间,从而增加饱腹感,减少进食频率,降低热量的摄入。
其次,膳食纤维可通过增加代谢相关有益肠道菌群的丰度和多样性来改善能量稳态并预防肥胖,降低门水平上厚壁菌门/拟杆菌门的比例(F/B比)并增加罗氏菌属(Roseburia)的相对丰度。
第三,膳食纤维可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 (SCFA),通过降低肠道腔内pH值、抑制致病或有害肠道细菌、减少脂多糖(LPS)和代谢有害化合物,在能量代谢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研究还表明,在高脂膳食中添加纤维可降低外周血炎症水平,在本文一起了解下肥胖的原因,哪些肠道菌群参与肥胖及其作用机理,此外,我们还分享了几个根据检测报告针对性调整和补充膳食纤维合生元等干预措施减重改善健康的案例。
肥胖不仅仅是因为吃得多这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慢性代谢性疾病。
肥胖受到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因素、内分泌和健康状况、个体的微生物和营养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通过能量摄入和消耗的生理机制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肥胖。
变胖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能量摄入与能量消耗的不平衡。我们知道,要维持健康的体重,需要保持食物摄入和能量消耗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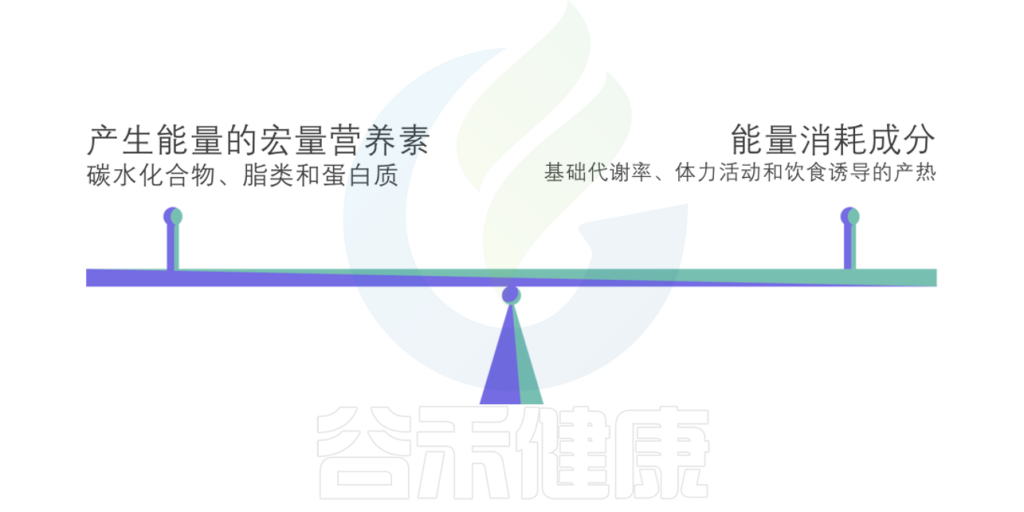
★ 摄入大于消耗时,变成脂肪慢慢堆积
当一天中人体的能量摄入大于能量消耗时,多余的能量就会被储存为脂肪、糖原或蛋白质,而体重就会上涨;相反,当摄入量小于消耗量时,机体就会通过转化储存能量(大部分来源于脂肪)来弥补热量差,体重就会下降。
简单来说就是:当你吃的比消耗的多时,能量储存=能量摄入-能量消耗
尽管在过去的20年里,环境变化导致了肥胖率的上升,但家庭和双胞胎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在肥胖的发展中也起着关键作用。
★ 瘦素等基因突变易导致肥胖
迄今为止,已确定十几个基因的变异是肥胖的单基因原因;包括瘦素、瘦素受体、黑皮质素3受体和黑皮质素4受体(MC4R)基因。
最著名的肥胖相关基因是瘦素(ob)及其受体(db)基因。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首次发现ob基因突变和缺乏ob基因的小鼠导致严重肥胖,能量摄入增加(暴饮暴食),但能量消耗减少(代谢率、产热和身体活动减少)。
注:该基因产物后来被描述为循环因子,命名为瘦素。瘦素主要由脂肪细胞分泌,循环至全身并穿过血脑屏障屏障来传递饱腹信号,从而减少食物摄入。
★ 肥胖的遗传原因大致可分为:
1)单基因原因:由单个基因突变引起,主要位于瘦素-黑皮质素通路。许多基因,如PYY(食欲促进基因)或MC4R(黑皮质素4受体),被发现与单基因肥胖有关,这些基因会破坏食欲和体重的调节系统以及位于下丘脑弓状核的受体感知激素信号(胃促生长素、瘦素、胰岛素)。
罕见的单基因缺陷与高饥饿水平有关,并可能导致幼儿严重肥胖。
2)综合征性肥胖是由神经发育异常和其他器官/系统畸形引起的严重肥胖。这可能是由单个基因或包含多个基因的较大染色体区域的改变引起的。
3)多基因肥胖是由许多基因的累积作用引起的。这些类型的基因存在会导致热量摄入增加、饥饿感增加、饱腹感减少、储存身体脂肪的倾向增加以及久坐不动的倾向增加。
★ 有肥胖家族史的人患肥胖风险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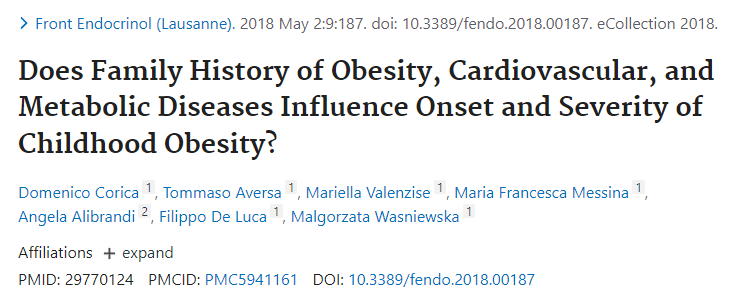
一项研究发现,如果父母一方肥胖,孩子成年后患肥胖的风险会提高3倍;而如果父母双方都肥胖,那么孩子成年后患肥胖的风险会提高10倍。(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与相同的生活方式有关)
一项针对260名儿童(139名女性、121名男性,年龄分别为2.4岁至17.2岁)的横断面观察研究表明,心脏代谢疾病家族史和肥胖是儿童期肥胖严重程度的关键危险因素。
生活方式等环境因素在肥胖发展中也发挥作用。肥胖患病率的显著增加与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密切相关。
在工业化国家,教育程度较低和收入较低的人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较高,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例如,生活在美国的皮马印第安人平均比生活在墨西哥的皮马印第安人重25公斤。生活在美国的非洲人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在男性和女性中,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直到50至60岁;这在20岁到40岁之间尤为明显。结婚后,超重的趋势也会增加。
★ 高糖的零食和饮料加剧了肥胖
在众多导致肥胖的因素中,过量食用高热量食物是罪魁祸首之一。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高热量食物在食品行业的大规模生产和营销方面都相当成功。这类食物在商店、餐馆、超市和家庭中随处可见。
两餐之间(尤其是晚餐后)吃零食,以及每天饮用果汁、碳酸饮料、糖果和高糖食物。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与肥胖风险增加密切相关。
★ 运动量的减少也导致肥胖率增加
体育锻炼应该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随着青少年的学业负担增加、中年人的工作负担沉重,运动量大幅减少。如果平时不注意运动,长时间久坐,会导致脂肪堆积,从而出现肥胖的现象。
其他可能导致身体活动减少的因素包括花在电子游戏和移动设备上的时间增加,而花在户外活动上的时间减少。这些不良习惯都会损害人们的健康。
★ 睡眠不足导致皮质醇升高也不利于减肥
缺乏充足睡眠会引发皮质醇水平的升高,这对身体的减肥过程是不利的,因为高水平的皮质醇可能会干扰新陈代谢和影响体重管理的效果。
你也许见过,本来身材挺匀称的一个人,因为生病或是吃了一些药物而迅速变胖,这就是内分泌紊乱进而导致肥胖的结果。
许多外周激素参与中枢神经系统(CNS)对食欲和食物摄入、食物奖励或成瘾的控制。美味的食物和一些药物都能激活中脑边缘多巴胺(DA)奖励系统,而该系统对于调节人类和动物的成瘾至关重要。
★ 瘦素、胰岛素等激素会影响进食行为
来自脂肪组织的瘦素、胰腺的胰岛素和胃肠道的胆囊收缩素、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肽YY3-36(PYY3-36)和生长素释放肽参与通过主要针对下丘脑和脑干的神经激素肠脑轴传递有关饥饿和饱腹信号,这些信号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调节食欲,影响个体的进食行为。
瘦素和瘦素受体的基因缺陷可导致儿童早发性严重肥胖。同时当内分泌系统出现紊乱时,可能会导致个体无法有效地控制食欲,进而对食物上瘾或是出现严重的暴饮暴食症。
肠道能量吸收、饱腹感调节和全身炎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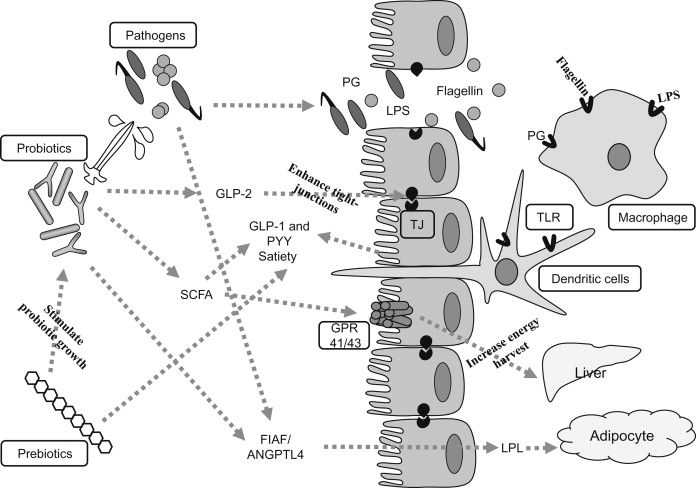
DOI:10.1016/B978-0-12-407825-3.00011-3.
★ 内分泌紊乱影响代谢更易导致肥胖
一些疾病如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影响基础代谢率,导致能量代谢异常,进而影响体重控制,甚至引发肥胖。
胰岛素抵抗是指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下降,导致血糖不能有效地被细胞吸收利用。这可能导致胰岛素分泌增加,促使脂肪细胞更多地吸收葡萄糖并转化为脂肪,从而引起肥胖。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一种影响女性生殖系统的疾病,患者常伴有胰岛素抵抗和雄激素水平异常。这些因素会导致体重增加和脂肪堆积,使得患者更容易发展为肥胖。
有证据表明,胎儿在宫内发育期间的营养不良可能决定了肥胖、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后期发病,而这与基因遗传无关。这种现象表明,由于宫内生长的改变,可能存在基因表达的长期编程。
★ 胎儿时期的营养不良可能导致中老年时的肥胖
研究人员假设,子宫内不良的营养环境会导致身体器官发育缺陷,从而导致“程序化”的易感性,这种易感性与后来的饮食和环境压力相互作用,在几十年后导致明显的疾病。
这表明胎儿的生长和新陈代谢为了适应出生后营养不足的预期。这可能在子宫内具有生存优势,因为它将可用的营养物质定向到重要器官,并在以后的生活中,通过增加以脂肪形式储存能量的能力,为食物短缺时提供能量储备。
有报告显示腹部脂肪与出生体重呈负相关,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妊娠早期和晚期是随后肥胖发展的关键时期。与没有在怀孕期间接触过饥荒的对照组相比,那些胎儿在怀孕的前两个月接触过饥荒等到成年后的肥胖患病率明显更高。
肠道微生物群在肥胖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并且与肥胖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肠道微生物群参与能量稳态的调节,并通过影响营养吸收、食欲和脂肪组织功能来影响肥胖的发生。
接下来我们详细了解下肠道微生物群在肥胖中的作用和角色。
越来越多的研究和谷禾实践检测数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群与肥胖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互作用,虽然大人群水平来看,肠道菌群只能解释其中部分的肥胖原因,但是在个体水平上,肠道菌群的状况和构成对于肥胖以及肥胖相关的能量摄入,炎症反应,食物消化等都息息相关。
肠道菌群在肥胖中的作用简单分为两个层面,直接参与与间接影响。
一,菌群是直接影响致肥胖途径还是通过其成分/代谢产物影响致肥胖途径?
二,是否存在导致肥胖的特定宿主-微生物信号传导机制?
队列人群和小鼠研究试验均表明,肥胖个体的肠道微生物群种类和丰富度与正常体重个体存在明显差异。
★ 肥胖人群与健康个体之间占主导的肠道微生物不同
大量研究集中于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水平变化与肥胖和减肥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比较瘦人和肥胖个体的肠道菌群,发现大人群水平上肥胖个体的拟杆菌门比例降低,而厚壁菌门水平升高。更有趣的是,经过饮食治疗后,拟杆菌门的相对丰度增加,而厚壁菌门的相对丰度降低。
在谷禾的检测案例里也发现,同一个人减肥前后的肠道菌群构成(如下桑基图展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的肠型也会发生改变。
减肥前后的主要肠道菌群构成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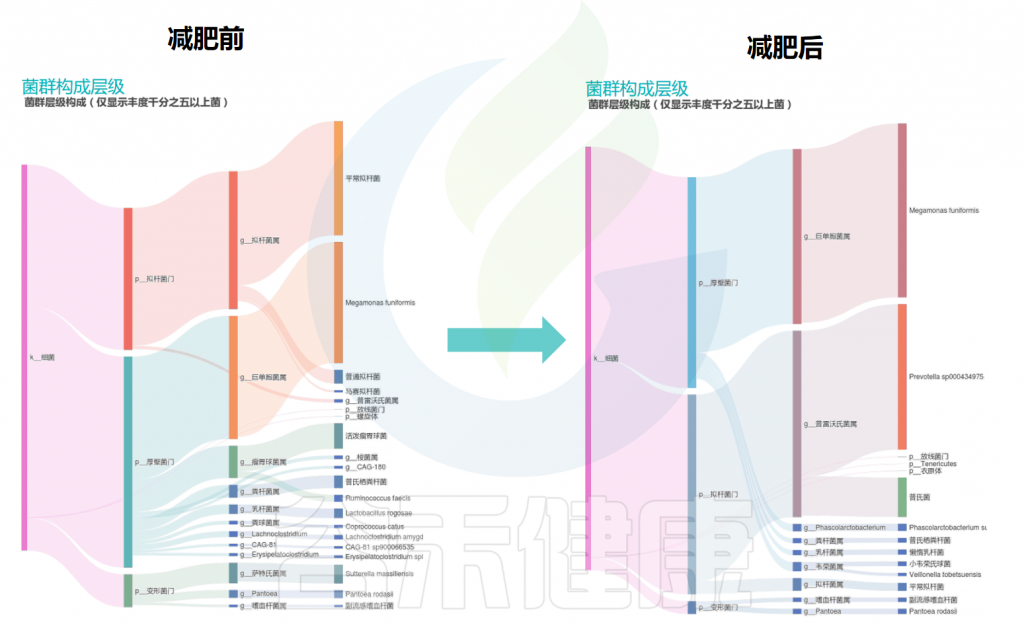
通过上图的变化可以看到:减肥之后拟杆菌门的比例增加,与此同时,普雷沃氏菌属的丰度也大大增加,其他菌属的构成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
该案例通过饮食管理和膳食纤维补充,减肥后普雷沃氏菌占比为主可能是水果蔬菜、高纤维豆类的饮食摄入相关。
★ 减肥的效果与基线肠道菌群相关
2021年,发表在《Gut Microbes》和《Gastroenterology》两篇研究分别以饮食控制和维生素给予为变量,同时都研究了基线时和干预后肠道菌群的变化。研究结论表示作为节食前个人体重减轻轨迹的预测指标,基线肠道微生物的作用超过了其他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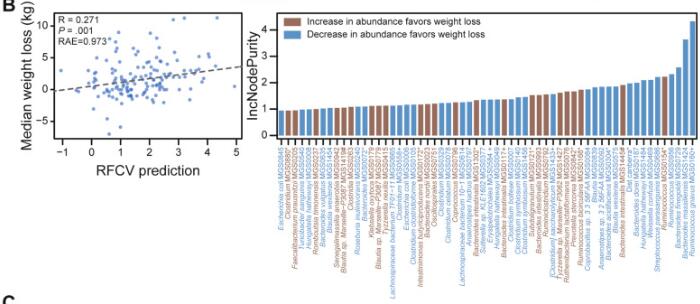
doi: 10.1053/j.gastro.2021.01.029.
同时使用随机森林算法,基于相对于基线的种水平物种变化来预测体重下降,预测精度R=0.271,发现R. gnavus (MGS0160), Bacteroides massiliensis (MGS1424)和Bacteroides finegoldii (MGS0729)这三个物种在模型中贡献度最大。
此外,基线菌属如普雷沃氏菌,罗氏菌属(Roseburia)的丰度也会影响饮食营养干预的减肥效果。
这些研究同时确定有哪些饮食因素与个体的体重下降相关。使用GLMMLASSO模型,结果如下图,当coef为非零时被认为是显著的。发现,在所有受试者中,体重下降与卡路里摄入量(系数=-0.153)、膳食中大量营养素组成(脂肪,系数=-0.161;碳水化合物,系数=-0.055;蛋白质,系数=0.084;纤维,系数=0.1)、膳食微量营养素含量和体力活动之间的具有弱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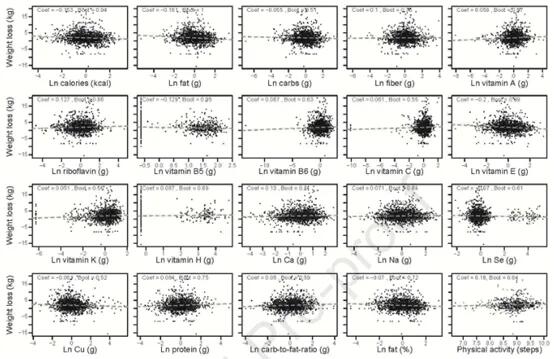
Jie Zhuye, et al., .Gastroenterology, 2021
但是在个体间有很大差异。例如在受试者F00161中,纤维摄入量的增加与减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F00147中,受试者的脂肪摄入量增加与体重减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相反,尽管纤维或脂肪摄入量发生变化,F00203人仍然对体重变化不敏感。所以,即使是相似的膳食大量营养素,体重反应也是高度个性化的。
饮食控制期间肠道菌群的组成变化是否会影响减肥轨迹?
研究发现许多参与者的肠道菌群组成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0-3个月的微生物群的变化幅度与体重下降的程度呈正相关,有15个个体肠型被改变了,体重变化范围从20公斤到+7公斤。这两个时间段都是一致的。这一发现表明,在饮食控制计划中,饮食和肠道菌群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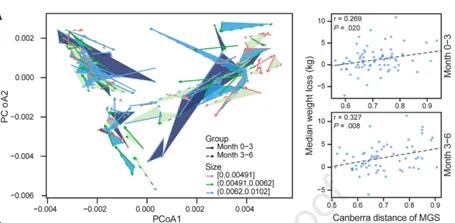
Jie Zhuye, et al., .Gastroenterology, 2021
这些结果表明可以基于基线肠道菌群组成和饮食数据建立个性化的体重预测模型。我们可以利用肠道菌群的分布做个性化的饮食推荐,以此调节体重,进而促进宿主健康。
此外,谷禾根据权威研究和检测大数据库,在菌群检测报告中给出了肥胖,便秘,失眠,过敏等症状相关菌(包括正相关,负相关菌,证据强度,菌的说明和异常菌的个性化干预调整措施)。
如下是谷禾菌群报告里肥胖相关菌的截图展示:
与肥胖症状相关的菌属

这些菌里,包括有益菌,核心菌,以及有害菌和致病菌等。部分菌在以往文章中详细介绍过:
★ 普雷沃氏菌——在摄入膳食纤维后对减脂更有利
普雷沃氏菌丰度高的健康超重成人在食用富含全谷类和纤维的随意饮食6周后,比普雷沃氏菌丰度低的受试者减脂更多。
普雷沃氏菌的高水平不仅与肥胖有关,且与非糖尿病患者的BMI指数、胰岛素抵抗、高血压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显著相关。
★ Blautia——治疗炎症肥胖相关的潜力菌
Blautia是肠道中常见的乙酸生产者,可通过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 GPR41 和 GPR43 来抑制脂肪细胞中的胰岛素信号传导和脂肪积累,进而促进其他组织中未结合的脂质和葡萄糖的代谢,从而减轻肥胖相关疾病。
Blautia是有效减肥组女性肠道菌群中的优势菌属,但在减肥无效组中则不然。Blautia,特别是B. luti和B. wexlerae,可能有助于减少与肥胖相关的炎症。
肠道核心菌属——经黏液真杆菌属(Blautia),炎症肥胖相关的潜力菌
★ Bifidobacterium——减轻体重和减少体脂
双歧杆菌对糖尿病、肥胖症和高脂血症的有益作用也得到了研究,证据显示其对普通人群的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具有有益作用,同时还能降低孕妇妊娠糖尿病的发病率。
★ Phascolarctobacterium——帮助减肥
比较容易减肥的人体肠道内考拉杆菌属(Phascolarctobacterium)水平较高,因此该菌也被认为可以用来预测肥胖指标。在代谢综合征女性中观察到的Phascolarctobacterium属的丰度高于代谢综合征男性。
肠道核心菌属——考拉杆菌属(Phascolarctobacterium),与减肥相关?
★ Ruminococcus——含量过多与炎症和肥胖有关
瘤胃球菌(Ruminococcus)在新陈代谢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项研究包括肥胖组(BMI≥40kg/m2)和对照组(BMI18.5~ 24.9kg/m2之间)的粪便菌群,其中Ruminococcus bromii, Ruminococcus obeum 在肥胖患者中丰度较高。
瘤胃球菌喜欢植物中的多糖。如果肠道中有过多的瘤胃球菌,细胞可能会吸收更多的糖,导致体重增加。
★ Desulfovibrio——含量过高与肥胖相关
脱硫弧菌属(Desulfovibrio)里的一种能够引起炎症的细菌,当其含量过多时与肥胖相关。并在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帕金森,系统性硬化症患者患者富集,可产生硫化氢对肠道上皮具有毒性,会导致人体腹泻。
★ 嗜胆菌属——喜欢脂肪、耐胆汁的促炎菌
嗜胆菌属(Bilophila)是变形菌门,脱硫弧菌科的一种厌氧、革兰氏阴性、耐胆汁,该菌是“喜欢动物脂肪喜欢胆汁”的微生物——在以动物为基础的饮食,尤其富含肉类和乳制品脂肪时,其肠道中Bilophila丰度会增加。
《Nature》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从素食转变为以肉类和奶酪为主的饮食结构上时,他们肠道里的细菌Bilophila几乎立即增加,但植物性为主的饮食结构可以降低该菌群的数量。
Bilophila是机会致病菌,其丰度的增加与肠道炎症相关。其代表菌种Bilophila wadsworthia增加了高脂饮食诱导的代谢综合征,这是一种与低程度全身炎症相关的疾病,伴随着较高的体重指数。
肠道重要菌属——嗜胆菌属 (Bilophila)喜欢脂肪、耐胆汁的促炎菌
★ 脆弱拟杆菌——肥胖儿童中含量较高
宿主的生活方式和生理状态也会影响肠道脆弱拟杆菌的丰度。例如,缺乏运动可能会导致脆弱拟杆菌和其他拟杆菌属物种显著富集。
以往的研究表明,脆弱拟杆菌过多与肥胖呈正相关,肥胖儿童中脆弱拟杆菌的丰度高于瘦儿童。
扩展阅读:
★ 短链脂肪酸影响饱腹感、促进能量消耗
菌群关键代谢物短链脂肪酸(SCFA)可以说是研究最广泛的微生物代谢物,对人体代谢有许多影响。
短链脂肪酸(SCFA)在维持宿主健康和影响代谢方面发挥着广泛的作用。SCFA调控体内各种生理过程,包括维持结肠上皮和粘液水平的先天性肠道屏障的完整性、调节肠道蠕动以及控制重要肠道激素的分泌,如肽YY(PYY)、血清素、胃抑制肽和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 。
短链脂肪酸参与L细胞产生的肽YY和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激素的调节。这两种激素都调节神经系统的饱腹感,GLP1在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敏感性和分泌中也起作用。
-乙酸盐
乙酸盐的健康影响还存在争议。一些研究将其与通过GPR41/43相互作用减少食欲、减轻体重以及增强胰岛素敏感性联系起来,而另一些研究则表明其作为肝脏和脂肪组织脂肪产生的底物,在促进肥胖方面发挥着作用。
-丙酸盐
丙酸可由拟杆菌属、考拉杆菌属(Phascolarctobacterium succinatutens)、戴阿利斯特杆菌属(Dialister)和韦荣氏球菌属通过琥珀酸途径产生;或是由埃氏巨球形菌属(Megasphaera elsdenii)、粪球菌属(Coprococcus catus)、沙门氏菌属(Salmonella spp.)、Roseburia inulinivorans和Ruminococcus obeum通过丙烯酸途径产生。
人体研究表明,丙酸具有整体抗肥胖作用,因为它可以增加餐后GLP-1和PYY水平,减少体重增加、腹部脂肪和肝细胞内脂质含量,并预防胰岛素敏感性问题。丙酸还通过减少中性粒细胞释放白细胞介素8(IL-8)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而表现出抗炎特性。
-丁酸盐
在胃肠道发酵产生的所有短链脂肪酸中,丁酸尤其值得注意。重要的产丁酸属和种有Coproccocus 属、Anaerostipes属、真杆菌属(Eubacterium)、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和罗氏菌属。
丁酸盐是成熟结肠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支持结肠健康,并且是一种具有强效抗炎特性的微生物代谢物,局部和系统性作用均有。此外,丁酸盐在调节局部和全身免疫、维持粘膜完整性和抑制细胞水平的肿瘤改变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丁酸盐与丙酸盐类似,具有通过刺激食欲抑制激素的释放和促进瘦素的合成来减少肥胖的作用。
★ 胆汁酸影响脂肪代谢
许多研究报告了肠道微生物组、胆汁酸和肥胖或肥胖相关疾病之间存在联系。胆汁酸在肠道中与脂肪分子结合,形成复合物,促进脂肪的分解和吸收。适当的胆汁酸可以帮助提高脂肪代谢效率,减少脂肪在体内的堆积。
此外,胆汁酸在消化系统中可以影响胃液分泌,从而影响饱腹感和食欲调节。适当的胆汁酸水平可以帮助控制饥饿感,减少摄入的热量,有助于减轻体重。
★ 吲哚——抗肥胖特性
一项研究发现较高的血浆吲哚丙酸水平与降低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之间存在关联。
另一项研究发现,与瘦对照相比,患有2型糖尿病的肥胖受试者的吲哚丙酸水平降低。吲哚丙酸显示通过与孕烷X受体结合并随后下调肿瘤坏死因子α来调节炎症。
吲哚丙酸也被证明在小鼠中具有抗肥胖活性,微生物衍生的吲哚乙酸进一步限制了巨噬细胞中脂肪酸的积累和炎症标志物的产生。
★ 谷氨酸过量与肥胖潜在危害有关
谷氨酸是一种多功能氨基酸,谷氨酸在生物体内的蛋白质代谢过程中占重要地位。根据对肥胖和瘦受试者的队列进行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显示,谷氨酸盐具有潜在危害。
通过进行途径分析,谷氨酰胺/谷氨酸转运系统在肥胖个体中高度富集。这与拟杆菌属(包括B.thetaiotaomicron)的物种呈负相关。事实上,与瘦受试者相比,肥胖者体内这种细菌的数量减少。因此谷氨酸与人体肥胖之间也存在一定联系。
★ 肥胖人群的肠道微生物能够更多地获取能量
对肠道微生物群影响膳食能量收集和储存过程的探索揭示了两种关键机制:肥胖人群具有分解难以消化的膳食细菌多糖水解酶从而对多糖降解;以及抑制一种名为禁食诱导脂肪因子(FIAF)或血管生成素样4(ANGPTL4)的脂蛋白脂肪酶(LPL)抑制剂的肠道基因表达。
一项比较肥胖小鼠及瘦小同窝小鼠的功能性宏基因组的研究发现,肥胖微生物群富含八个能够水解膳食多糖的糖苷水解酶家族。第二种机制涉及微生物对FIAF的抑制,通过影响LPL活性导致脂肪堆积增加。
细菌多糖水解产生脂肪形成底物,即单糖和短链脂肪酸。肠道微生物群还通过增强钠/葡萄糖转运蛋白-1(SGLT1)的表达以及使小肠毛细血管密度加倍来促进有效的单糖吸收。这些脂肪形成底物到达肝脏后促进了肝脏甘油三酯的合成。
★ 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影响从食物中获取的能量
“能量获取理论”最近也在人类受试者身上进行了测试。招募了12名瘦弱和9名肥胖的成年男性,在最初3天的体重维持饮食之后,以随机交叉的方式分配到2400或3400千卡/天的饮食,持续3天。
在初始体重维持饮食中,瘦人和肥胖个体的三大细菌门(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和放线菌门)存在显著差异。作为对改变的热量负荷的反应,肠道厚壁菌门增加、拟杆菌门减少与宿主能量吸收增加约150kcal有关。
瘦人似乎对增加热量摄入更为敏感,在2400vs. 3400 kcal/天饮食中,粪便能量损失和肠道微生物组成的变化均显著减少。而肥胖个体没有出现类似的变化。我们认为,与体重维持饮食相比,能量摄入的差异程度可能会通过肠道微生物群影响饮食中能量的吸收效率。
暴饮暴食是肥胖的主要诱因,是由调节食物摄入的过程失衡造成的,包括“饥饿”、“食欲”和“饱腹感”,以及环境因素。
★ 饱腹和饥饿信号影响人们的进食行为
正常的饮食行为在我们感到饱腹(饱腹感)时就会停止,并在感到饥饿一段时间后再次开始。两餐之间的时间是饱腹感的指标。有许多肠道激素会向大脑传递“饱腹”或“饥饿”的信号。肠内分泌L细胞分泌的胆囊收缩素(CCK)和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是与饱腹感相关的肠道激素,可传递“饱腹”信号。
肠内分泌L细胞分泌的肽YY(PYY)和肠内分泌K细胞分泌的葡萄糖依赖性胰岛素促泌多肽(GIP)也传达“饱腹感”,而胃细胞分泌的生长素释放肽则传达决定开始进餐的“饥饿”信号。
★ 短链脂肪酸可以影响激素水平进而调节饱腹感
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和其发酵产物短链脂肪酸可以影响肠道激素水平,进而调节饱腹感。肠内分泌L细胞分泌的GLP-1和PYY含有短链脂肪酸受体GPR41和GPR43,暗示结肠短链脂肪酸的生成与食欲或摄食量存在关联。
膳食纤维可选择性地支持肠道中有益细菌的生长和短链脂肪酸的产生。与饲喂对照饮食或高蛋白饮食的大鼠相比,饲喂高纤维饮食的大鼠血浆GLP-1和PYY水平较高,血浆GIP水平较低,结肠PYY mRNA水平增加5倍,胰高血糖素原mRNA水平增加11倍。
菊粉型果聚糖已被证明可以提高血浆GLP-1水平和结肠胰高血糖素原基因表达,保护免受高脂肪饮食引起的肥胖。一项人体研究表明,每天摄入21克低聚果糖(FOS)可降低超重成人的生长素释放肽并增加PYY,同时减少卡路里摄入量,有助于减肥。
★ 肠道微生物通过影响免疫也会导致贪食、肥胖
另一个影响食物摄入和肥胖的因素是肠道微生物群与先天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Toll样受体5(TLR5)是被广泛研究的受体之一。TLR5在小鼠肠粘膜中高表达,可以识别细菌鞭毛蛋白作为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MP),与肠道炎症和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有关。
最新研究表明,TLR5基因敲除小鼠(T5KO)表现出贪食、肥胖、代谢综合征以及相关的高脂血症、高血压和胰岛素抵抗。T5KO小鼠的贪食/肥胖表型与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细菌物种水平变化相关,T5KO小鼠有116种来自不同门类的细菌属丰富或减少。
将T5KO小鼠肠道微生物移植到健康小鼠中,导致健康小鼠发展代谢综合征,表明T5KO小鼠的肠道微生物影响代谢健康。
总的来说,肠道微生物群通过短链脂肪酸信号传导或与先天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在调节食欲、肥胖和糖尿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可发酵纤维和益生元等膳食成分以及肠道内生成的微生物代谢产物可以作为对抗这些疾病的简单而有效的手段。
肥胖与慢性、轻度全身性炎症相关。脂肪细胞和肥胖下的脂肪组织内的巨噬细胞都释放炎症细胞因子。这种轻度全身性炎症部分来源于细菌脂多糖(LPS)从肠道进入血液循环。
血浆中脂多糖浓度增加两到三倍,被称为“代谢性内毒血症”,与肥胖、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等多种慢性疾病相关。
★ 高脂饮食会加剧炎症状态
肠道脂多糖倾向于通过乳糜微粒携带,这些是脂蛋白颗粒,用于输送膳食脂质。因此,高脂饮食可能诱发或加剧代谢性内毒血症。
肠道通透性可能导致脂多糖位移,肠道微生态失调或引发肠道壁炎症可能增加通透性。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几种菌株及其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已被证实能促进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这些蛋白维持有效的肠道屏障。而肠道中双歧杆菌相对缺乏与肠道通透性增加相关。
★ 肥胖状态下促炎巨噬细胞比例增加
引起脂肪组织炎症加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巨噬细胞的渗入。产生促炎细胞因子的脂肪组织主要来自渗入的巨噬细胞。动物研究表明,巨噬细胞在肥胖中逐渐积累,瘦小鼠脂肪组织中不到10%的细胞是巨噬细胞,而肥胖小鼠中这一比例超过50%。
巨噬细胞本身表现出不同表型,可极化为促炎的“M1”或抗炎的“M2”表型。肥胖状态改变了M1和M2巨噬细胞的比例,导致M1巨噬细胞增加。
注:有趣的是,TLR4缺乏可减轻脂肪组织炎症,促进脂肪组织和腹膜巨噬细胞极化为M2型,但不会影响全身胰岛素敏感性。
另一项研究比较了无菌小鼠和大肠杆菌单个定植小鼠,结果显示单个定植小鼠脂肪组织中存在脂多糖依赖性巨噬细胞积累。大肠杆菌的定植还增加了巨噬细胞的极化,使其转变为促炎的M1型,并导致葡萄糖和胰岛素耐受性下降。
小结
肠道微生物组影响肥胖和相关代谢状态的三种机制,即通过能量获取、食欲调节和炎症状态,综合起来看,每条途径都是协同作用而非独立作用。这些调节过程的核心是宿主、微生物组和饮食之间复杂而动态的三向相互作用。
人体的消化过程和细菌作用在肠道中协同处理膳食成分。产生的代谢产物的特征取决于宿主遗传、宿主生理和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微生物与营养消化产物结合,可以通过与宿主细胞受体的特定相互作用或以非特定方式进入一般血液循环,对宿主代谢产生不同的影响。
以下是来自君好美健康科技公司的3个案例,采取“膳食纤维+后生元”君好美膳食片作为主食,三餐吃饱——肉鱼蛋奶豆制品蔬菜充分吃,水果干果控制吃,在基本不改变在原有饮食情况下,一段时间后,个案的体重体脂明显下降、肠菌菌群得到有效改善。
案例一
女,44岁,原本体重为182.5斤,属于严重偏胖。
经历144天的改善后,体重减轻了36.3斤,减脂了22.2斤,减肥效果非常明显。体脂率、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都有所减少。
身体数值的各项变化

编辑
改善前后的报告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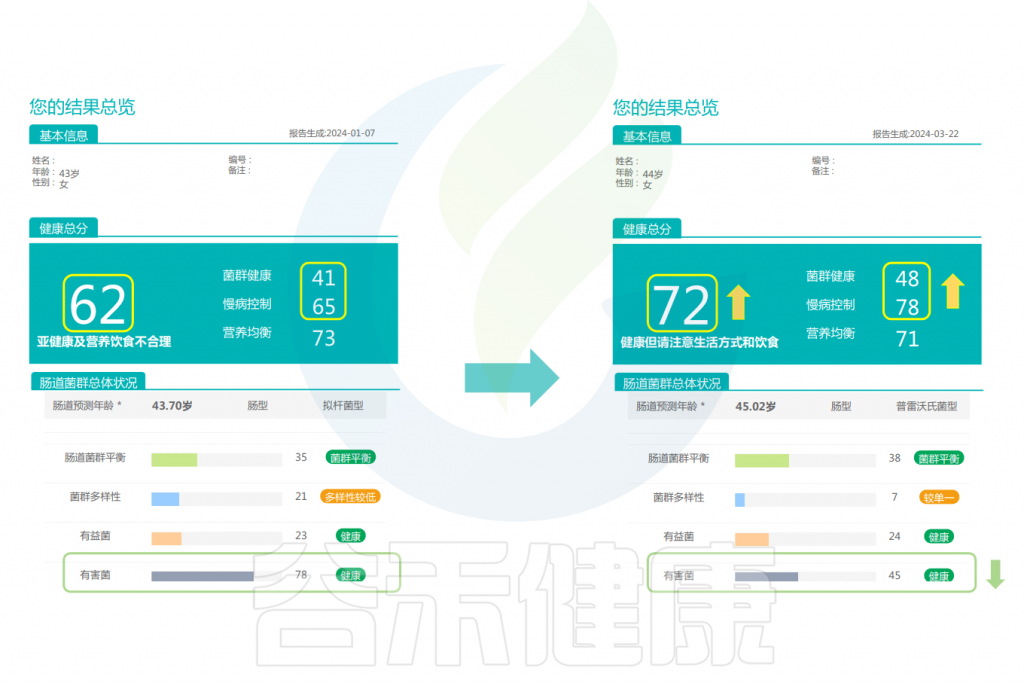
可以看到:在额外补充膳食纤维后,健康总分升高,肠道微生物的结构更健康,通过增加膳食纤维来增加微生物的数量和多样性是非常有效的。有益菌的分值提高,有害菌明显减少,肠型由原来拟杆菌型变成了普雷沃氏菌型,慢病风险总分下降。
▸ 具体到菌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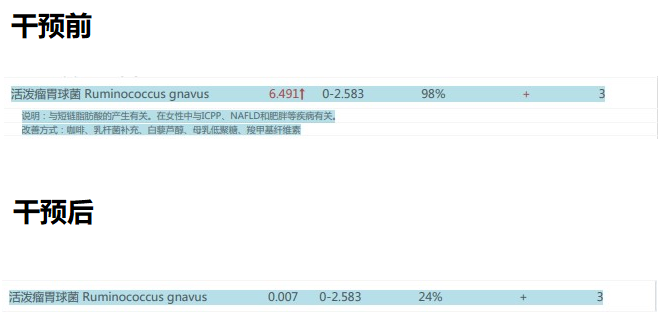
活泼瘤胃球菌与短链脂肪酸的产生有关。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和肥胖等疾病存在正相关。在改善后由原本的过高丰度,降低到了正常水平。
干预前:

干预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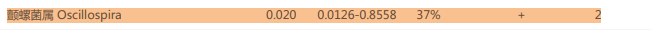
颤螺菌属也是与肥胖相关的菌群,过多或过少都可能影响肥胖。在改善后由原本的过低,丰度有所增加,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干预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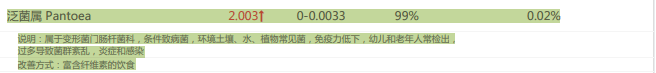
干预后:

泛菌属是一种条件致病菌,过多导致菌群紊乱,炎症和感染。而在补充膳食纤维后丰度有所降低(尽管还有一点偏高)。
干预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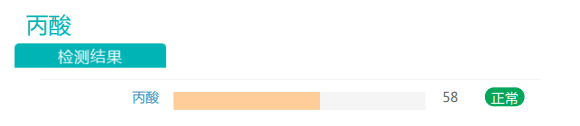
干预后:

此外,丙酸盐的丰度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有充分证据表明,随着膳食纤维摄入量的增加,产生的短链脂肪酸(SCFA)也增加。SCFA能够激活游离脂肪酸受体,从而促使厌食激素(如瘦素和肽YY)的分泌。在减肥中发挥益处。
根据以上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在额外补充膳食纤维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体的肥胖和代谢健康。
案例二
女,52岁,原本体重为142.4斤,属于严重偏胖。
经历73天的改善后,体重减轻了11.6斤,减脂了7斤,虽然没有上一个人减重多,但是BMI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体脂率、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也均有所减少。
身体数值的各项变化

改善前后的报告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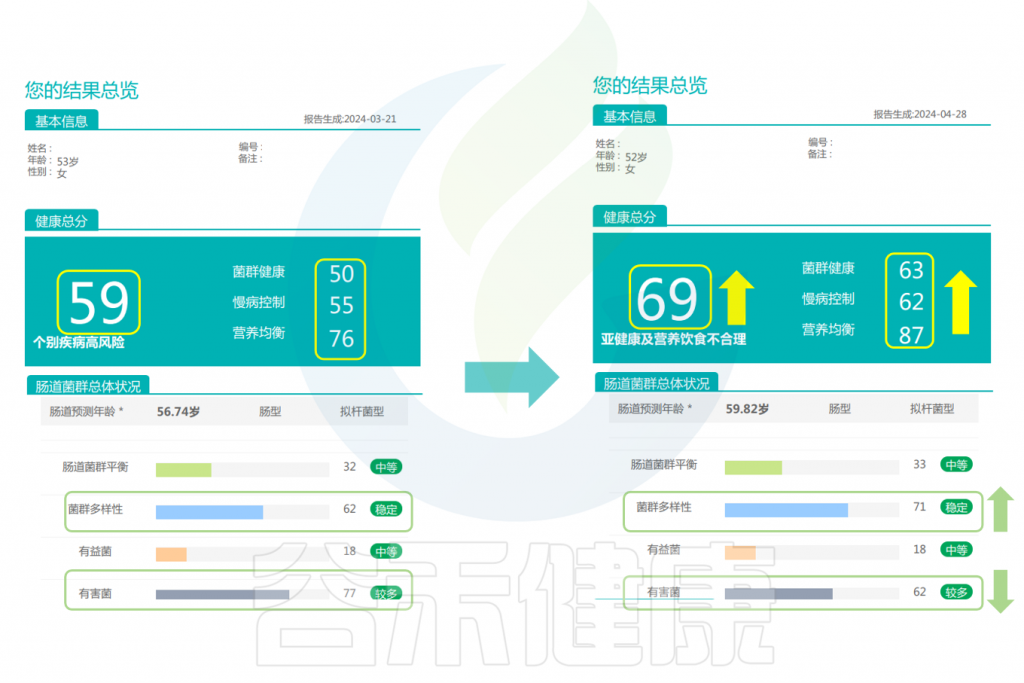
可以看到,该女性在经过干预后,健康总分也升高了。并且菌群变得更健康、对于慢病的控制评分更高,营养也更均衡了。肠道菌群多样性提高,有害菌明显减少。
与此同时,核心菌属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干预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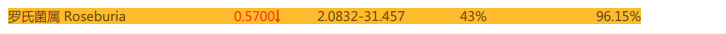
干预后:

重要的肠道基石菌,产短链脂肪酸菌属罗氏菌在改善后由原来的丰度过低变成了正常丰度。罗氏菌具抗炎特性,有助于分解不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如膳食纤维,对健康有利。
干预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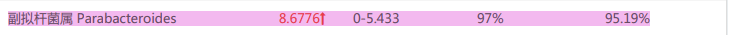
干预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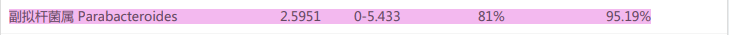
过多会导致菌群紊乱的副拟杆菌属由原本的过高丰度降低到了正常值。
肠道核心菌——副拟杆菌属(Parabacteroides),是否是改善代谢减轻炎症的黑马?
干预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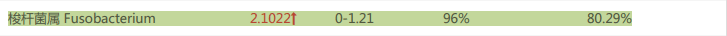
干预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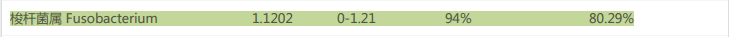
能够产生脂多糖,代谢生成苯酚,引发感染和并发症的梭杆菌属丰度由原来的过高水平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梭杆菌属Fusobacterium——共生菌、机会致病菌、致癌菌
干预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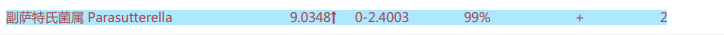
干预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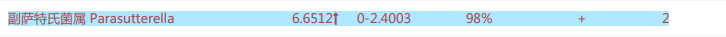
过高时会导致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副萨特氏菌属在额外补充膳食纤维后丰度也有所下降(尽管仍然高于正常值)。
干预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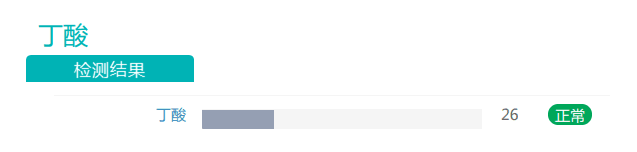
干预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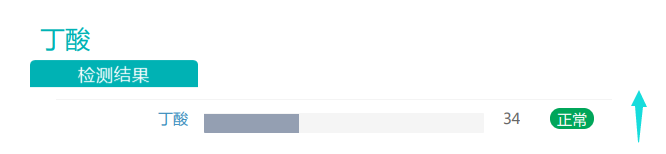
随着膳食纤维摄入量的增加,丁酸盐的丰度有所上升。丁酸对于维持肠道内环境温度预防结直肠癌发生具有重要作用,是肠上皮细胞最重要能量来源,对肠粘膜有营养作用,利于代谢健康的重要物质。
案例三
男,54岁,原本体重为131.1斤,属于标准体重,本来健康状态就比较好。因此在经历173天后,体重只下降了4.4斤,减脂2.1斤。体脂率、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也稍微有所下降,但都变得更健康了。
此外,三个案例可以看出膳食纤维对不同基础体重人群的作用效果不太一样,大体重人群在额外补充膳食纤维后减重更多。
身体数值的各项变化

改善前后的报告对比

<来源:谷禾肠道菌群健康检测数据库,下同>
根据谷禾的健康报告前后对比可以看到,该男性在经过干预后,健康总分升高,对于慢病控制的评分显著升高。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变得更丰富,有害菌减少明显。
干预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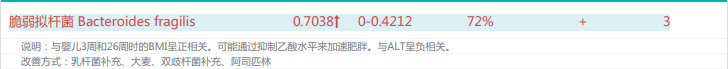
干预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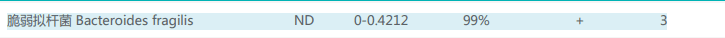
过高时与肥胖相关,可能通过抑制乙酸水平来加速肥胖的脆弱拟杆菌在额外补充膳食纤维后丰度降低到了正常水平。
干预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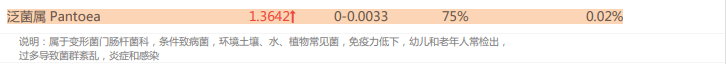
干预后:

肠道的条件性致病菌泛菌属,过多导致菌群紊乱,炎症和感染。在补充额外的膳食纤维后水平也下降到正常值。
肠道微生物群多样性和高纤维摄入量与长期体重增加较低有关
此外一项对1632个人的研究也发现,微生物群多样性会影响膳食纤维与体重增加之间的关系。在微生物群多样性较高的人群中,纤维摄入量与体重增加风险降低有显著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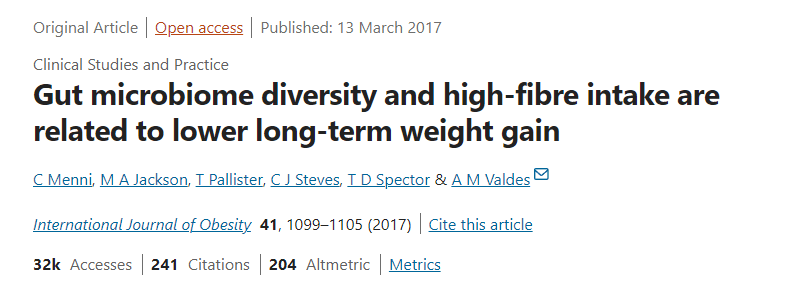
膳食纤维对体重的有益作用可能在微生物组多样性较高的个体中更为明显。实验表明,纤维摄入会降低饮食的能量密度,由此产生的短链脂肪酸促进肠道糖异生、肠促胰岛素形成并随后产生饱腹感,同时短链脂肪酸也会向宿主输送能量并影响脂肪异生。
TIPs: 膳食纤维与益生元的区别
膳食纤维和益生元虽然都是植物性食物中的复杂碳水化合物,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区别:
1.膳食纤维的定义: 膳食纤维是指植物性食物中不被人体消化酶分解的碳水化合物,包括不溶性纤维和可溶性纤维。不溶性纤维,如纤维素,主要作用是增加大便体积,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系统健康。可溶性纤维,如果胶和树胶,可以溶解在水中,形成凝胶状物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和胆固醇。
2.益生元的定义: 益生元是一种可溶于水的可溶性纤维,它作为益生菌的食物,可以被肠道中的有益细菌发酵,从而促进有益细菌的生长和活动。益生元主要包括低聚果糖(FOS)菊粉、低聚半乳糖(GOS)等。
3.作用机制: 膳食纤维的作用更广泛,包括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便、降低血糖和胆固醇等。而益生元的主要作用是喂养和促进益生菌的生长,尤其是那些能够产生短链脂肪酸(如丁酸盐)的细菌,这些短链脂肪酸对肠道健康至关重要。
4.种类: 膳食纤维的种类很多,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树胶、抗性淀粉等。而益生元的种类相对较少,主要是一些特定的低聚糖和某些类型的多糖。
5.健康益处: 膳食纤维对整体消化系统健康有益,而益生元则更专注于通过促进益生菌的生长来改善肠道微生物群的平衡。
总的来说,膳食纤维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包括了益生元但它们的作用和重点略有不同。膳食纤维对消化系统的整体健康有益,而益生元则专门针对促进一些细菌的生长。
拓展:不同纤维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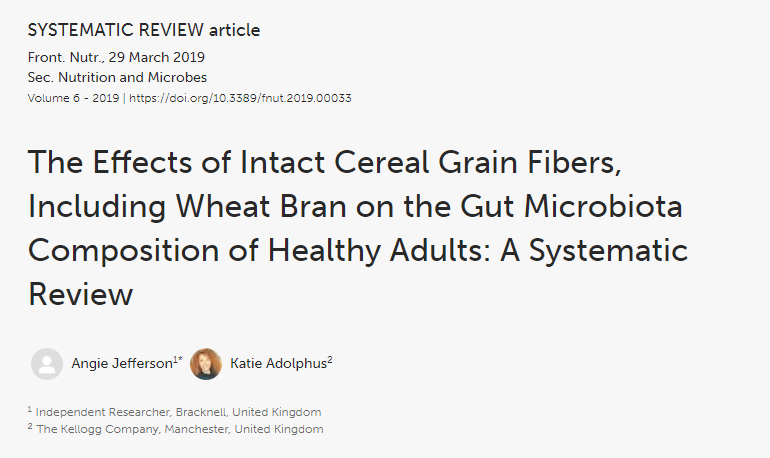
一项研究了不同谷物纤维(包括麦麸)对健康成人肠道菌群组成的影响。
-食用小麦纤维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食用小麦纤维或麸皮纤维对肠道菌群有显著影响,以下门类的菌群均显著增加:
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a) ↑↑↑
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 ↑↑↑
奇异菌属(Atopobium) ↑↑↑
肠球菌(Enterococci) ↑↑↑
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a) ↑↑↑
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 ↑↑↑
埃格氏菌(Eggerthella) ↑↑↑
柯林斯菌(Collinsella) ↑↑↑
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um) ↑↑↑
拟杆菌(Bacteroides) ↑↑↑
普氏菌属(Prevotella) ↑↑↑
-食用大麦纤维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所有研究都表明大麦纤维对肠道菌群标志物有显著影响:要么改变微生物群落 ,要么改变发酵代谢物。发现厚壁菌门和放线菌(特别是罗氏菌属、Dialister、真杆菌和双歧杆菌)显著增加,拟杆菌减少。
其余3项研究测量了发酵标志物,结果显示,在食用大麦纤维后,总短链脂肪酸、丁酸盐和乙酸盐显著增加,呼气氢显著增加。由于发酵代谢物的积极作用,血糖反应同时改善。
-食用燕麦纤维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燕麦粒的外层含有不溶性和可溶性(β-葡聚糖)纤维的混合物,这两种纤维都为肠道微生物群提供了食物来源。已证实可溶性燕麦β-葡聚糖有助于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
对患有轻度高血糖症或高胆固醇血症的参与者研究了每天早餐食用全麦燕麦片与精制谷物片的影响。据报道,食用全麦燕麦片后,粪便总细菌、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数量显著增加,而食用精制谷物片后,总细菌数量和双歧杆菌数量均下降。
-食用玉米纤维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玉米的淀粉含量相对于其他谷物来说较高,麸皮含量较低。
一项急性干预研究比较了单次食用48克全麦玉米早餐麦片(14.2克纤维)对肠道菌群的影响,并与48克低纤维玉米早餐麦片(0.8克纤维)进行了比较。
3周后,高纤维组和低纤维组均报告粪便双歧杆菌增加,高纤维组的增幅更大,但未达到显著性,乳酸杆菌、肠球菌和奇异菌属物种的增加不显著。
-混合全谷物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全麦谷物包括谷物的胚乳、胚芽和麸皮成分,因此其营养成分与谷物的麸皮纤维部分不同,这可能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
共计357人的研究发现,增加完整谷物纤维的摄入具有显著的益生元作用,细菌多样性、放线菌、双歧杆菌、梭菌、毛螺菌显著增加;但阿克曼氏菌、罗氏菌、乳酸杆菌和肠球菌的增加趋势不显著。促炎性肠杆菌科细菌的水平也显著下降。
作者认为,对高纤维干预的反应取决于基线肠道微生物丰富度——由于膳食纤维的增加,基线微生物丰富度有限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更大的微生物群变化。
如今全球肥胖症的流行,寻求新的有效解决方案已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无法长期坚持既定的饮食和身体活动方案,从而无法达到并保持健康的体重。
肠道微生物群由于位于宿主营养/能量代谢的关键位置并能够影响它,因此已成为一种有希望的新治疗靶点。
饮食、肠道微生物群和肥胖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高度互动和动态的。虽然饮食热量摄入是能量平衡方程的主要因素,研究估计现在知道某些肠道微生物可以从饮食中获取“额外”的能量,大约150千卡/天;相当于一年内可能增加6.8公斤的体重。
除了热量含量外,饮食成分也是与肥胖相关的饮食-微生物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例如肠道微生物失调以及高脂饮食引起的全身炎症。
肠道微生物还通过调节食欲、食物摄入和饱腹感来影响肥胖:这是能量平衡的一部分。膳食纤维、合生元是调节肠道微生物组成的有效方法,这些干预措施不仅降低了体重,体脂,而且同时改善了与肥胖和相关代谢状况相关的生物标志物,例如血糖水平、胰岛素敏感性、血浆脂联素等。
总体而言,这些结果表明,通过膳食纤维,合生元以及饮食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可以作为人类减肥的独立方法,同时可以有助于减轻风险并控制肥胖相关疾病(如心血管疾病、胰岛素抵抗和2型糖尿病)的症状。
在当前肥胖流行和健康挑战的背景下,个体化肠道菌群干预显得尤为重要。每个人的肠道微生物群独一无二,受基因、生活方式和环境等多方面影响。因此,针对个体的肠道菌群进行精准干预,可以更有效地调节体重、改善健康状况。
主要参考文献
Li H, Zhang L, Li J, Wu Q, Qian L, He J, Ni Y, Kovatcheva-Datchary P, Yuan R, Liu S, Shen L, Zhang M, Sheng B, Li P, Kang K, Wu L, Fang Q, Long X, Wang X, Li Y, Ye Y, Ye J, Bao Y, Zhao Y, Xu G, Liu X, Panagiotou G, Xu A, Jia W. Resistant starch intake facilitates weight loss in humans by reshaping the gut microbiota. Nat Metab. 2024 Mar;6(3):578-597.
Jie Zhuye,Yu Xinlei,Liu Yinghua et al. The Baseline Gut Microbiota Directs Dieting-Induced Weight Loss Trajectories.[J] .Gastroenterology, 2021.
Pham Van T,Fehlbaum Sophie,Seifert Nicole et al. Effects of colon-targeted vitamins on the composition and metabolic activity of the human gut microbiome- a pilot study.[J] .Gut Microbes, 2021, 13: 1-20.
Corica D, Aversa T, Valenzise M, Messina MF, Alibrandi A, De Luca F, Wasniewska M. Does Family History of Obesity, Cardiovascular, and Metabolic Diseases Influence Onset and Severity of Childhood Obesity? Front Endocrinol (Lausanne). 2018 May 2;9:187.
Bartsch M, Hahn A, Berkemeyer S. Bridging the Gap from Enterotypes to Personalized Dietary Recommendations: A Metabolomics Perspective on Microbiome Research. Metabolites. 2023 Dec 2;13(12):1182.
Zhang M, Liu J, Li C, Gao J, Xu C, Wu X, Xu T, Cui C, Wei H, Peng J, Zheng R. Functional Fiber Reduces Mice Obesity by Regulating Intestinal Microbiota. Nutrients. 2022 Jun 28;14(13):2676.
Menni C, Jackson MA, Pallister T, Steves CJ, Spector TD, Valdes AM. Gut microbiome diversity and high-fibre intake are related to lower long-term weight gain. Int J Obes (Lond). 2017 Jul;41(7):1099-1105.
Mayengbam S, Lambert JE, Parnell JA, Tunnicliffe JM, Nicolucci AC, Han J, Sturzenegger T, Shearer J, Mickiewicz B, Vogel HJ, Madsen KL, Reimer RA. Impact of dietary fiber supplementation on modulating microbiota-host-metabolic axes in obesity. J Nutr Biochem. 2019 Feb;64:228-236.
Jefferson A, Adolphus K. The Effects of Intact Cereal Grain Fibers, Including Wheat Bran on the 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of Healthy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Front Nutr. 2019 Mar 29;6:33.
Zhang, Y.; Liu, J.; Yao, J.; Ji, G.; Qian, L.; Wang, J.; Zhang, G.; Tian, J.; Nie, Y.; Zhang, Y.E.; et al. Obesity: Pathophysiology and Intervention. Nutrients 2014, 6, 5153-5183.
Lin X, Li H. Obesity: Epidemiology, Pathophysiology, and Therapeutics. Front Endocrinol (Lausanne). 2021 Sep 6;12:706978.Lin X, Li H. Obesity: Epidemiology, Pathophysiology, and Therapeutics. Front Endocrinol (Lausanne). 2021 Sep 6;12:706978. Pathophysiology, and Therapeutics. Front Endocrinol (Lausanne). 2021 Sep 6;12:706978

谷禾健康

植物多酚是一大类生物活性化合物,其特点是化学和结构特性不同、生物利用度低,并具有多种体外生物活性。在这些化合物中,木脂素因其类固醇类似物的化学结构而受到广泛研究,被认为是植物雌激素。
木脂素是一类与纤维相关的化合物,存在于许多植物家族和常见食物中,包括谷物、坚果、种子、蔬菜以及茶、咖啡或葡萄酒等饮品中。膳食木脂素浓度最高的食物是亚麻籽和芝麻,其中含有一种叫做松脂素二葡萄糖苷的化合物。其他膳食木脂素包括芝麻素、松脂醇、松脂素和落叶松脂素。
肠道细菌代谢能够将膳食木脂素转化为治疗相关的多酚(即肠木脂素),例如肠内酯和肠二醇。这些肠木脂素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包括组织特异性的雌激素受体激活、抗炎和促凋亡作用。因此,木脂素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不仅关系到个体对特定食物的响应,也关系到整体健康和疾病预防。
肠木脂素的生物利用度在个体间存在很大差异,受遗传、饮食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木脂素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具有针对各种肿瘤(如乳腺癌、结肠癌和前列腺癌)和/或心血管疾病的化学预防特性。
与其他多酚一样,木脂素在被全身吸收之前先被肠道细菌代谢。饮食等因素已被证明会影响微生物群的组成。植物性饮食者的微生物群在微生物多样性方面与非素食者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影响代谢物的产生和提取效率。
约 80% 的木脂素相关论文发表于 2000 年之后,其中约一半发表于 2010 年或之后;这清楚地表明在过去 20 年里人们对这一天然产物家族的兴趣显著增长。此外,亚麻、五味子、连翘的整体重要性在木脂素的文献分析中显而易见。许多论文不仅局限于植物生物学,还集中在药理学(约四分之一)和化学(约四分之一)上。
本文主要讲述了木脂素的多方面特性,包括其在自然界中的分布、如何通过肠道细菌的代谢转化,讨论了木脂素在降低某些疾病风险中的潜在作用,尤其是在乳腺癌、结直肠癌和前列腺癌的预防中。同时,也探讨了影响木脂素代谢的个体间差异因素,如性别、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等。了解这些可以为个性化的医学和营养方案提供更好的指导。
根据其来源,木脂素大致可分为:
植物木脂素主要在对位含有氧取代基,而哺乳动物木脂素则在间位具有羟基。这种细微的结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生物体内的不同作用和代谢途径。
木脂素在结构上类似于木质素,木质素是三维聚合物,与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果胶交织在一起,形成植物细胞的坚固细胞壁。此外,木脂素和木质素都是通过相同的初始苯丙烷途径产生的,它们是由单木质素(来源于苯丙氨酸或酪氨酸)合成的,但最终进入不同的生化途径。实际上,尽管木质素在植物界无处不在,但并非所有植物都会产生木脂素。
已知来自食用植物的糠醛型木脂素,包括落叶松树脂醇、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醇、马泰尔树脂醇和松脂醇,可被肠道微生物群转化为哺乳动物木脂素、肠二醇或肠内酯。与木质素前体相比,这些细菌副产物对人类健康更有益。
肠木脂素(哺乳动物木脂素)也是食物木脂素的代谢产物,是人类肠道细菌的产物。它们经常在人类血浆和尿液中被检测到。
作为食物成分,木脂素存在于大多数富含纤维的植物中:
常见食物中木脂素(以苷元形式)的每份和
100克(鲜重)总微克含量及其分布及其植物来源

Peterson J, Nutr Rev. 2010 (10):571-603.
食物中的木脂素含量通常较低,一般不超过2毫克/100克。芝麻和亚麻籽是例外,它们的木脂素含量比其他食物来源高出几倍。
亚麻籽来源于亚麻科植物亚麻(Linum usitatissimum L.),其含有的生物活性成分可能对健康有益,例如 α-亚麻酸(占总脂肪酸组成的 50–55%)、膳食纤维(25–28%)和酚类化合物。
亚麻籽是已知最丰富的木脂素来源 [ 9–30 毫克/克(约 301 毫克/100 克)],木脂素产量是谷物、豆类、其他油籽、蔬菜和水果的 75–800 倍。亚麻籽中存在的主要膳食木脂素是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酚(2,3-双(3-甲氧基-4-羟基苄基)丁烷-1,4-二醇),它以共轭 SDG 的形式储存,是植物中线性酯键复合物的组成部分。
芝麻(Sesamum indicum L.)是一种开花植物,属于胡麻科。芝麻籽中的木脂素浓度相对较高(接近29mg/100g,主要是松脂素和落叶松脂素)。芝麻素是一种呋喃型木脂素,是芝麻中的主要木脂素成分之一,在种子中的含量为 0.1–0.5%。
芝麻素还可以通过肠道微生物群转化为哺乳动物木脂素,这可能对乳腺癌等激素相关疾病具有保护作用。
木脂素的健康益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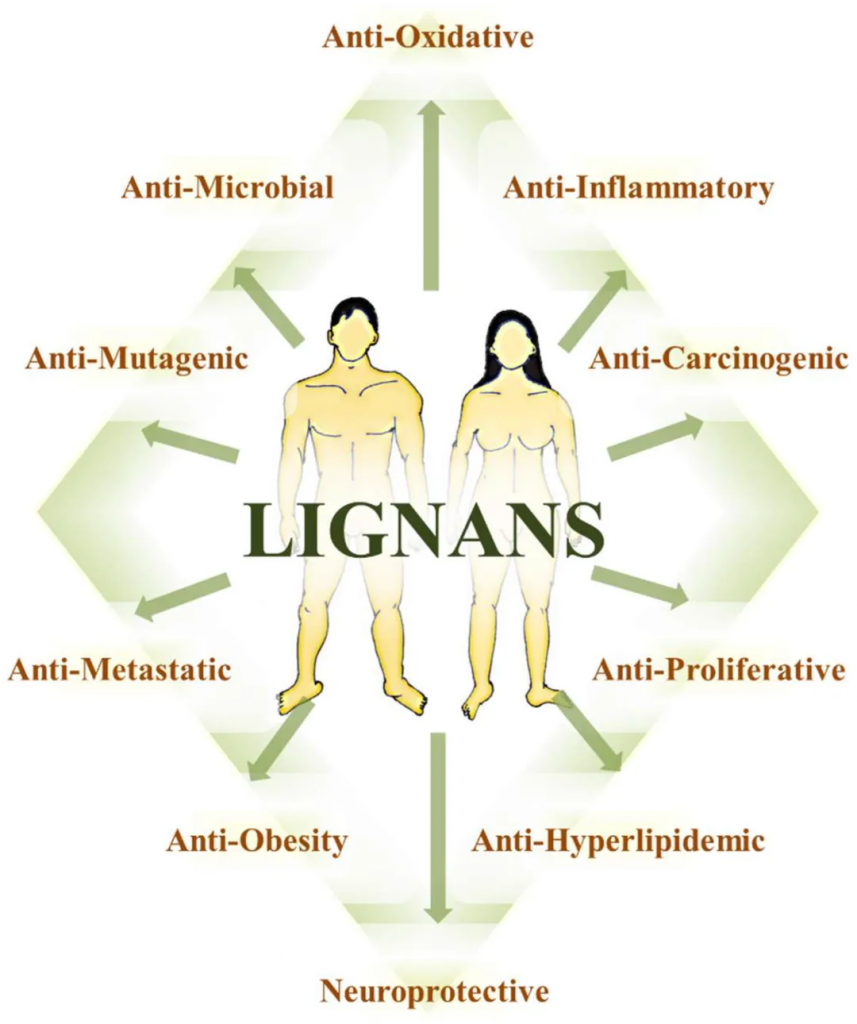
doi.org/10.3390/ph12020068
饮食中木脂素的消耗主要因地理位置而异,但饮食模式也受到文化和种族的影响。
传统的地中海饮食以植物为主,其特点是:
这种饮食的健康益处主要归因于纤维和生物活性化合物(包括抗氧化剂和功能性脂肪酸和脂质)摄入量的增加,以及饱和脂肪摄入量低。
木脂素来源
地中海人群饮食中的木脂素来源包括:
每种食物在总多酚摄入中所占的比例(11–70%)和亚型都不同。
事实上,许多典型的地中海饮食食品(例如谷物)都含有高浓度的木脂素和其他酚类化合物。
最近,人们开始评估全谷物摄入在预防慢性病方面的作用。许多研究表明,作为全谷物饮食的一部分,木脂素摄入与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病率降低之间存在联系。
栗子、特级初榨橄榄油
地中海饮食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栗子,是钙、抗氧化剂和酚类化合物的极佳来源。
特级初榨橄榄油是地中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经常食用特级初榨橄榄油与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类型癌症的发病率降低有关。这种效果可能归因于特级初榨橄榄油中含有高浓度的 (+)-1-乙酰氧基松脂醇和(+)-松脂醇。

这种饮食习惯常见于北欧和北欧地区,特点是:
大量食用海藻、贝类、多脂鱼(如鲭鱼、鲱鱼和鲑鱼)、瘦肉、菜籽油、豆类、坚果(如杏仁)、蔬菜、水果(如浆果)、全谷物(如燕麦)、低脂乳制品,并限制盐和糖的摄入量。
在北欧国家,植物木脂素的主要饮食来源是蔬菜、水果和全麦谷物。
在许多经常食用的富含木脂素的植物物种中,一些物种主要分布在北半球(例如菊科的蓟属植物)。这些植物的营养结构含有三萜、多乙炔、酚酸、黄酮类化合物和生物碱。欧洲蓟属植物的最新植物化学研究表明,其种子是新木脂素和木脂素的丰富来源。
印度餐桌上的木脂素宝库
各类食品构成了典型印度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鱼、葡萄、巧克力、油、咖啡、茶、饼干和面包。
巴戟天——传统医学中的木脂素宝库
巴戟天(印度桑树)的果实传统上被广泛用于治疗癌症、糖尿病、高血压、腹泻、头痛和炎症,这主要是由于其木脂素含量高。
芝麻:印度饮食中的木脂素明星
芝麻是印度饮食中的典型成分,芝麻和芝麻油都富含木脂素。芝麻油因其显著的抗氧化性和营养价值而闻名。
尽管木脂素仅占芝麻总质量的一小部分(0.5 %至 1.0%),但主要的芝麻木脂素——例如 (+)-芝麻素酚、(+)-芝麻林和 (+)-芝麻素葡萄糖苷——因其显著的健康促进特性而备受关注(已在体内和体外得到证实),包括抗炎、抗氧化和抗高血压活性。
疾病预防
有研究表明,长期摄入(+)-芝麻素酚可抑制阿尔茨海默病中观察到的致病性细胞外β-淀粉样蛋白聚集。同样,(+)-芝麻素具有预防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的作用,并且是肠二醇和肠内酯的前体(已证明具有抗癌、抗糖尿病和抗衰老作用。
亚洲饮食的特点是大量食用大米、面条、香料和蔬菜、芝麻和油。此外,人们也常食用海鲜、豆腐和其他大豆制品。
亚洲是木脂素的主要植物来源;这些植物通常被纳入饮食中,在中国也被用作药用植物。这类植物包括:
牛蒡
其果实提取物和种子是生物活性木脂素的丰富来源,包括牛蒡苷和牛蒡苷元。这两种木脂素具有抗炎活性,例如,抑制脂多糖诱导的一氧化氮生成和小鼠巨噬细胞中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此外,牛蒡中的木脂素在抗癌方面也显示出了强大的潜力,能诱导癌细胞凋亡并抑制其增殖。
某些草药通常用作水浸剂。其中包括香茶菜属植物和雷公藤属植物。
香茶菜属
香茶菜属植物包括近 150 个种,分布于亚洲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是极好的木脂素来源。一些种,如日本香茶菜,已被用于传统中药,治疗关节痛、胃痛、乳腺炎、胃炎和肝炎等。香茶菜还因其降血压、抗氧化、免疫、抗菌、抗肿瘤和抗炎特性而被用于传统医学。
雷公藤
一种传统药草,可以改善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症状。多项植物化学研究已从该植物的根部分离出数百种生物活性化合物,包括木脂素。
五味子
长期以来,中药一直将五味子果实用作镇静和止咳补药,广泛分布于中国四川东南部和湖北西部地区。其他国家还使用这种水果来生产功能性食品、果酱和饮料。
从五味子中分离出的二苯并环辛二烯木脂素具有抗炎和抗氧化特性,并能改善认知功能(如记忆力)。此外,先前的研究报告称,五味子果实提取物(其中主要生物活性成分是木脂素)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并具有有助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生物活性。
五味子果实可能对肝脏、胃肠道、免疫、交感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有积极作用。木脂素提取物已被证明能成功抑制肝细胞癌细胞增殖,并防止化学毒素引起的肝损伤。然而,整个五味子果实中只有 2% 由木脂素组成,而且大部分木脂素存在于种子中,而种子通常在制造水果衍生产品的过程中被去除。
这种藤本植物的茎被用作多种疾病的止痛药,包括关节炎、风湿病和挫伤。迄今为止,已从五味子中分离出 1 种倍半萜类化合物、25 种木脂素和 43 种三萜类化合物。此外,五味子浆果被认为对肾脏和肺部有益,例如可缓解哮喘症状。
山楂
已被用于功能性食品行业。一些研究报告称,它具有防止低密度脂蛋白 (LDL) 氧化、清除自由基和发挥抗炎作用的能力。山楂主要以新鲜水果、加工果汁或果酱的形式食用。果汁和果酱的制造会产生大量副产品,包括种子和叶子。
红花南洋参
根、茎、果实和叶均可入药,尤其是其果实,具有重要的药用和营养价值。其活性三萜类化合物和木脂素因其报道的生物活性而备受关注,包括抗炎和抗肿瘤作用 。
花椒
已被用于促进血液循环以及治疗各种疾病。由于其独特的味道和独特的香气(通常被描述为绿色、辛辣、花香和清新),花椒果实在许多传统的亚洲美食中被用作香料。先前的药理研究表明,这种植物的叶子和果实具有药用特性,包括抗肿瘤、抗炎和抗氧化活性,以及抑制血小板聚集和单胺氧化酶的产生。
拉丁美洲饮食的基础是玉米、土豆、花生和豆类。这种饮食中还包括亚麻籽。
亚麻籽是木脂素的最佳膳食来源之一,其木脂素含量高于豆类或谷物 。富含亚麻籽的饮食与降低各种疾病的风险有关,包括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症、糖尿病、前列腺癌和乳腺癌。可能的机制包括降低循环葡萄糖、LDL 和总胆固醇水平的能力。
亚麻籽具有重要的商业应用,例如在亚麻纤维制造中。就木脂素而言,亚麻籽主要含有secoisolariciresinol和 secoisolariciresinol二葡萄糖苷,但也含有少量的matairesinol 。事实上,亚麻籽总质量的 95% 以上是由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醇二葡萄糖苷组成,其主要位于种子的纤维壳中,而不是其内部 。
亚洲饮食似乎最有利于木脂素的摄入,而且木脂素的生物利用度也更高。这主要是由于亚洲人食用大量蔬菜,以及传统医学中使用富含木脂素的植物浸剂。
在大多数人群中,木脂素摄入量通常不超过 1 mg/天。木脂素摄入量的估计值从约 150 μg/天(马泰瑞香酚和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醇)到约 1600 μg/天(松脂醇、丁香树脂醇、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醇、中树脂醇、马泰瑞香酚、落叶松树脂醇、肠内酯、肠二醇)不等。
木脂素的肠道代谢
几种摄入的植物木脂素在结肠细菌的作用下去糖基化并部分转化为哺乳动物木脂素肠内酯和肠二醇。肠二醇很容易氧化成肠内酯。然后,这些代谢物在结肠中被吸收。
注:含有酚羟基的木脂素是 II 期代谢反应的靶点,并与谷胱甘肽(GSH)、硫酸盐或葡萄糖醛酸结合,导致木脂素的药理活性降低。
尽管植物木脂素具有抗微生物特性,但它们可以被居住在肠道中的细菌代谢并转化为肠内木脂素(”entero-“来源于希腊语的”enteron”,意为“肠”)。肠内木脂素也被称为哺乳动物木脂素,是由两支研究团队几乎同时独立发现的。随后,在人体中证明了植物木脂素是肠内木脂素的膳食前体。
代谢物的吸收与排出
一些代谢物可能经历肠肝循环。木脂素以结合葡萄糖醛酸苷的形式随尿液和胆汁排出,以非结合形式随粪便排出。
亚麻籽木脂素增强、吸收和生物利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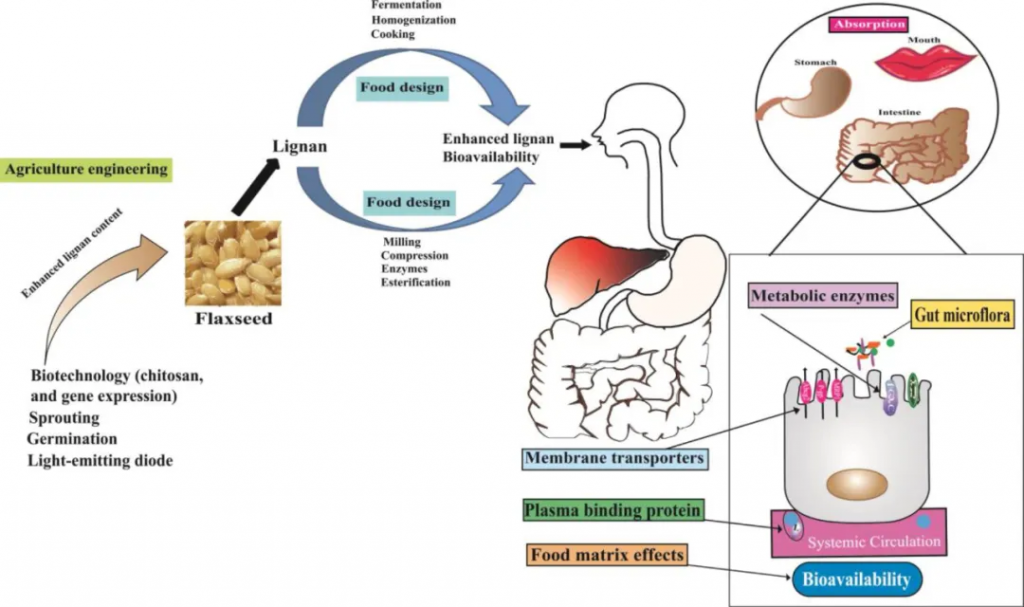
doi.org/10.1080/10408398.2022.2140643
在植物木脂素向哺乳动物木脂素的吸收和生物转化以及随后的吸收上,不同形态吸收不同,人与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关于个体之间的差异在后面章节会详细阐述)。
木脂素的不同形态与吸收
木脂素在植物中既以糖苷形式存在(含糖),又以糖苷配基形式存在(不含糖)。不同形态的木脂素在肠道中的释放和吸收效率不同,进而影响其生物利用度。
目前,亚麻籽中仅发现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醇作为木脂素低聚物。木脂素糖苷经肠道细菌代谢为肠木脂素(肠二醇和肠内酯)和木质素糖苷配基后,在胃肠道中被吸收。从亚麻中的糖和低聚物中释放木脂素的水解量以及肠木脂素的形成和其生物利用度因人而异。
亚麻籽木脂素结构变化导致生物利用度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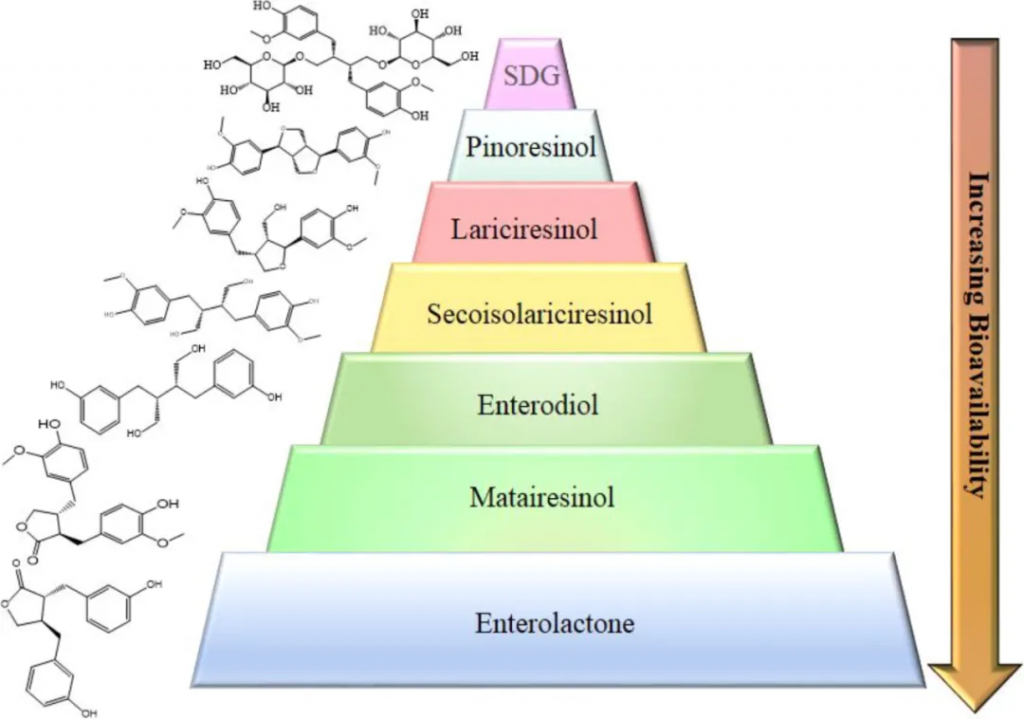
doi.org/10.1080/10408398.2022.2140643
不同吸收速度
肠木脂素肠内酯和肠二醇在结肠中被吸收,其中大部分与结肠组织中的葡萄糖醛酸结合。它们通常在饮食摄入后 8-10 小时出现在血液中。
另一项研究表明,一些植物木脂素(例如环松脂素、脱水开环异松脂素、7′-羟基松脂素、松脂素、松脂素、松脂素、落叶松脂素、开环异松脂素和芝麻素)在摄入芝麻籽一小时后被小肠迅速吸收并在体循环中检测到。
肠木脂素、开环异松脂素和芝麻木脂素的肠肝循环显著。肠内酯、肠二醇和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醇的硫酸盐和葡萄糖醛酸苷可能只是通过胆汁、尿液排出,或进行肠肝循环。
常见植物食物木脂素转换为肠内木脂素
(肠内木脂素和肠内二醇)的转化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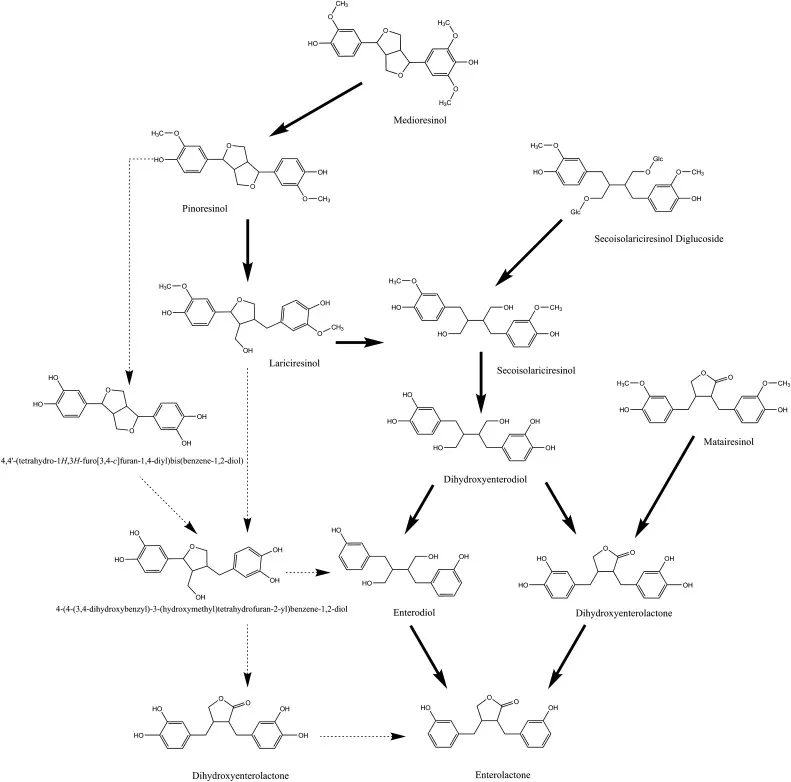
实箭头表示已知的途径。虚箭头表示理论路径。
木脂素糖苷,如芝麻芝麻林三葡萄糖苷和亚麻 SDG 酯基复合物,在肠道厌氧微生物的作用下水解为木脂素苷元。然后,游离木脂素在几种肠道细菌的代谢反应中转化为肠木脂素。转化效率取决于多种因素。
组织中的木脂素代谢受遗传因素影响,但这些因素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在体外粪便微生物群代谢系统中,落叶松树脂醇在 24 小时内完全转化为肠木脂素、肠二醇 (54%) 和肠内酯 (46%);而其他植物木脂素如松脂醇二葡萄糖苷(55%)、马泰尔木脂醇(62%)和 SDG(木酚素)(72%)转化不完全。
许多研究者评估了多种特定肠道细菌进行必要的反应以将糖苷化木脂素转化为肠内木脂素的能力。确定了脆弱的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卵拟杆菌(Bacteroides ovatus)、Clostridium cocleatum、丛形菌、噬糖梭菌(Clostridium saccharogumia)、多枝梭菌(Clostridium ramosum),吉氏拟杆菌(Bacteroides distasonis)其中前四个细菌在实验的20小时内可以完全去糖基化SDG。而且这些菌被证明可以降低李斯特菌相关的感染。
此外,有研究发现十种双歧杆菌菌株能够水解SDG。一旦去糖基化后,SECO 可以去甲基化生成中间产物DHEND。其中丁酸菌、Enterobacter Callander、 Clostridium limosum、Bacteroides Producta能够催化这一反应。
植物性食物或植物油主要以加工形式使用,如薯片、烘焙产品、焯水和煮熟的蔬菜。因此,在加工过程中考虑木脂素含量的变化非常重要。
烘焙、研磨、加热、干燥、煮沸和提取等加工技术可能会影响木脂素含量,因此可能会影响木脂素的生物利用度,因为在食用前会破坏天然食物基质或微观结构。
干燥和烹饪等其他加工过程对木脂素含量的影响各不相同,具体取决于木脂素的结构、木脂素概况、结合类型和食品基质的性质。
不同食物:大麦加工 vs 小麦加工
将大麦加工成膨胀大麦可以降低松脂醇、马泰瑞斯醇、开环异落叶松脂醇的含量,而提高落叶松脂醇的含量。
干燥精制小麦粉对木脂素的总浓度有总体积极影响,并提高了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醇、松脂醇和落叶松树脂醇的浓度。虽然全粒燕麦对松脂醇水平有积极影响,但其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醇、松脂醇和落叶松树脂醇的含量较低。
不同温度:蒸汽(100℃) vs 烘烤(250℃)
用蒸汽(或 100 摄氏度)处理谷物、黑麦粉和芝麻可以降解木脂素,而更高的烘烤温度(例如 250 摄氏度)会降解芝麻和黑麦中的糖苷和苷元。在亚麻籽中,松脂醇、落叶松脂醇、开环异落叶松脂醇和异落叶松脂醇主要以酯化化合物的形式存在,在 250 摄氏度下加热 3.5 分钟后,这些物质会保持稳定。
不同食物基质
在芝麻油中,加热条件几乎不影响芝麻素的含量,而芝麻酚的含量会增加,而芝麻林的含量会略有降低。此外,当油温保持在 200℃ 并持续 20 分钟时,芝麻素会降解。
报告称,煮沸十字花科蔬菜样品会降低木脂素含量,而胡萝卜的木脂素含量没有显著变化。研究表明,许多蔬菜(尤其是块茎类蔬菜)的木脂素含量在烹饪后会有所增加。
从芝麻饼中分离出的 STG 和芝麻中最丰富的木脂素糖苷与人体肠道细菌一起发酵时,与对照组相比,STG 样品中的系统发育群双歧杆菌、乳酸杆菌、肠球菌明显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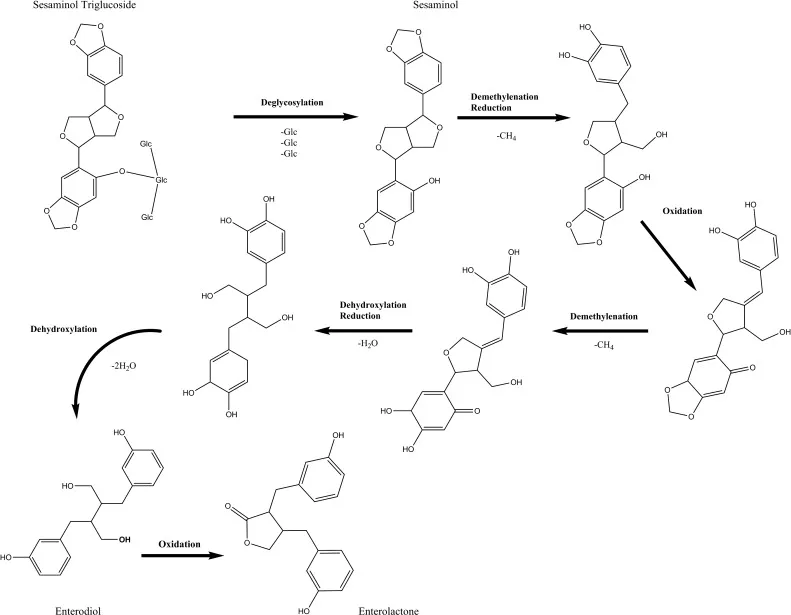
植物木脂素底物也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体产生肠二醇(Enterodiol,简称,END)和肠内木脂素(Enterolactone,简称,ENL)的潜力。不同的植物来源木脂素向END和ENL的转化率各异,从异落基瑞醇没有转化,到LARI的100%转化。类似地,生成ENL的效率在牛蒡苷葡萄糖苷和MAT之间分别为5%到62%。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植物木脂素与肠道微生物群体相互作用的重要性,这在决定肠内木脂素的暴露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注:END和ENL这两种化合物是植物木脂素在肠道内经过微生物代谢生成的生物活性代谢产物。在肠道微生物群体中,植物木脂素底物的摄入会影响肠道微生物产生肠二苯乙烯二醇和肠内木脂素的能力。这些代谢产物可能对健康和疾病风险具有一定影响,因此对它们的生成过程和机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食物中的大多数植物木脂素通过大肠上部的肠道菌群转化为肠木脂素。
血浆肠内酯含量低可能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主要是雌激素阴性乳腺癌。有证据表明,纯木脂素、亚麻籽和 SDG 可抑制肿瘤形成并减少血管细胞进展,从而预防前列腺癌、结肠癌、卵巢癌和转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症、肾脏和骨骼疾病等多种疾病。
功能性食品或营养食品是除提供基本营养成分外,还声称具有预防疾病或促进健康特性的食品。许多功能性食品或营养食品都是用亚麻粉、全亚麻籽和磨碎的亚麻制成的。
此外,通过添加木脂素等成分、加工或包装,可以增加食品的价值。与主要原始来源相比,这些产品更受消费者的接受和青睐。增值产品的一些例子有挤压零食、酸奶、脱脂牛奶、冰淇淋、奶酪、早餐麦片等。
木脂素在商业上用于烘焙、乳制品、挤压、零食、发酵、传统(印度薄饼、哈克拉、蔬菜奇拉)产品等产品。例如,亚麻籽可以作为整粒、烘烤、磨碎、碾磨和油的形式加入到烘焙产品中。
此外,亚麻籽木脂素已被添加到各种乳制品中,包括牛奶、酸奶、奶酪、冰淇淋、黄油和乳清饮料。研究发现,添加到牛奶、酸奶和奶酪中的 SDG 具有良好的耐受发酵、高温巴氏杀菌和牛奶凝乳酶工艺。
天然抗氧化剂花青素、黄酮类胡萝卜素和多酚在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近年来有多项研究表明天然抗氧化剂主要在过渡金属离子(主要是 Cu 和 Fe)存在下才具有促氧化活性。酚类化合物在某些条件下(例如高酚浓度、高 pH 值和存在金属离子)可诱导促氧化活性并产生自由基,最终导致诱变和 DNA 损伤。
研究报道了芝麻木脂素芝麻酚的反常作用。在这项研究中,芝麻酚在人类结肠直肠癌 (HCT116) 细胞中表现出高浓度(0.5、1、2 和 5 mM) 的促氧化活性和低浓度 (<0.05 mM)的抗氧化活性。芝麻酚基于其促氧化作用,通过细胞内 O2−生成诱导 HCT116 细胞中的线粒体凋亡途径。
活性氧 (ROS) 是有氧代谢的必然结果。
内源或外源产生的 ROS 可能导致多种病理因素,如细胞变性和DNA损伤。如果阻止氧化损伤的细胞抗氧化能力不能中和 ROS 的产生,细胞就会表现出一种称为氧化应激的状态。
氧化应激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多种疾病
ROS 在细胞器或细胞质中积累可以通过破坏核酸的结构和功能、激活凋亡途径、蛋白质氧化修饰、引起脂质过氧化、抑制抗氧化酶以及最终导致细胞功能障碍来破坏细胞的平衡。
木脂素的抗氧化活性可通过多种机制实现
包括减弱 ROS 生成和 MDA,以及通过增强 SOD、CAT、GSH-Px 和 GSH 活性来增加组织抗氧化酶能力。
它们还可以抑制脂质过氧化、蛋白质和 DNA氧化。抗氧化剂激活 JAK2/STAT3信号通路,通过P38MAPK磷酸化和Nrf2/ARE通路上调 PI3K/AKT 信号和 HO-1。
通过这些不同的机制,抗氧化剂可以通过下调I – κB激酶的活性和NF-κB的DNA结合活性,减少促炎细胞因子(IL-1β、IL-6、TNF-α)和介质(COX-2、iNOS、ROS)的产生,来调节参与氧化应激和炎症的关键分子。
大肠杆菌、克雷伯氏菌、肠杆菌、沙门氏菌和许多其他细菌是导致人类许多疾病的病原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可产生多种肠毒素,导致胃肠炎,而胃肠炎是大多数国家的主要食源性疾病。
一项研究表明,亚麻籽木脂素提取物在 MIC 值为 1.5 mg/ml 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弧菌等革兰氏阳性菌具有有效的抗菌活性。同样,由于含有多酚(包括木脂素),亚麻籽粗木脂素提取物和水解木脂素提取物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病原体都表现出抗菌活性。
亚麻籽粉酚提取物可抑制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其抑菌圈直径为 26 毫米,其次是鼠伤寒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其抑菌圈直径分别为 25 毫米、22 毫米和 10 毫米。
木脂素可以与 Ca+2和 Mg+2离子结合,降低外膜脂多糖的离子浓度,引发脂多糖释放,从而削弱膜,从而增加木脂素活性。
黄曲霉和黑曲霉这两种真菌都会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一种强烈的肝毒素和致癌物。它们是各种主要粮食作物收获前的感染物。这些化学物质可导致农场动物死亡或生产力下降。2.5-3.0 mg/ml 的木脂素粗提取物对黄曲霉和黑曲霉均表现出相当强的抗真菌功效。
一项研究表明,亚麻籽成分具有显著的抗真菌作用,特别是对抗白色念珠菌的生长。此外,与常用的制霉菌素相比,富含木脂素的亚麻籽水提取物表现出明显更强的抗真菌活性。亚麻木脂素能刺激胃中益生菌的生长,还能帮助消除引起真菌感染的酵母菌和念珠菌。
以上是木脂素抗氧化,抗菌的一些特性,这些特性为木脂素在维护健康方面的潜在作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步了解木脂素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
植物木脂素,尤其是其代谢产物——肠内木脂素,显示出了多种生物活性。
由于END和ENL结构上与常见性激素17β-雌二醇相似,使得肠内木脂素能够结合到雌激素受体α(ERα)上,从而产生微弱的雌激素或抗雌激素效应,这也是它们最初被归类为“植物雌激素”的原因。
然而,无论是在体外还是体内的研究,都鉴定出肠内木脂素可能影响几种慢性疾病风险的多种其他机制。这些机制包括抗增殖、抗炎和促进细胞凋亡的效应。这里我们总结了木脂素及其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现有证据。
在与木脂素暴露相关的研究中,探讨最深入的三类癌症是乳腺癌、结直肠癌和前列腺癌,这些癌症与木脂素的癌症预防作用有关。
注:关于其他类型癌症的研究较为稀少。人类关于子宫内膜癌和木脂素的少数几项研究倾向于无关联,另外在欧洲癌症与营养前瞻性研究(EPIC-Norfolk)中的一项嵌套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木脂素与胃癌之间没有关联。
尽管胃癌和子宫内膜癌的研究结果不显著,但总体证据倾向于支持木脂素与几种常见癌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木脂素与癌症风险的流行病学研究
在2005年,Webb和McCullough对已有的关于膳食木脂素暴露与癌症的文献进行了综述。他们得出结论,体外和动物研究支持富含木脂素的食物和提取的木脂素在调节结肠、乳腺和前列腺癌的癌变过程中的作用;然而少数可用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可能不一致。
结直肠癌是一种在结肠或直肠内发展的恶性肿瘤。它是一种常见的癌症,通常起因于结肠或直肠内的息肉转变成癌细胞。结直肠癌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随着病情不断恶化,患者可能出现腹痛、腹泻、便秘、便血等症状。
木脂素摄入降低结直肠癌风险
一项在加拿大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考察了通过食物频率问卷(FFQ)测量的木脂素摄入量与结直肠癌风险之间的关系,包括1095个病例和1890个对照组。
研究人员发现,摄入高水平的木脂素与降低结直肠癌风险相关。具体来说,摄入最高水平的膳食木脂素(每天超过0.255毫克)的个体显示出显著降低的结直肠癌风险,其几率比为0.73(95% CI 0.56–0.94)。也就说摄入较高水平的人群其患结直肠癌的风险更低。
血浆中END含量与结直肠腺瘤风险
2006年的一项荷兰研究发现,血浆中END(肠内一种木脂素)的含量与显著降低的结直肠腺瘤风险相关。在这项研究中,对首次确诊的结直肠腺瘤患者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END与降低的风险相关,其几率比为0.53(95% CI 0.32–0.88)。这意味着含有较高END水平的个体患结直肠腺瘤的风险更低。
ENL与结直肠腺瘤风险
另一种肠内木脂素ENL也与降低结直肠腺瘤风险相关,但其影响程度较弱。具体而言,ENL与降低的风险相关,其几率比为0.63(95% CI 0.38–1.06)。这表明相对于END,ENL对结直肠腺瘤风险的影响较轻。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了木脂素在降低结直肠癌和结直肠腺瘤风险中的潜在作用,尤其是高水平的木脂素摄入与较低的患病风险相关。然而,需要更多研究来确认这些关联以及木脂素对人类健康的确切影响。
性别差异在木脂素影响中的表现
在丹麦进行的一项病例队列研究同样探讨了血浆ENL与结直肠癌之间的关系,发现女性中血浆ENL浓度每增加一倍,结肠癌的发病率比值显著降低(IRR 0.76;95% CI 0.60–0.96)。然而,有趣的是,在男性中,直肠癌的发病率与血浆ENL浓度每增加一倍相关,风险增加(IRR 1.74;95% CI 1.25–2.44)。
乳腺癌是一种影响女性乳腺组织的恶性肿瘤。基于人类流行病学研究的结论对于木脂素在绝经前和绝经后乳腺癌风险中的作用存在差异。在2005年的综述中,Webb和McCullough总结道,当时关于木脂素在癌症预防中的作用,最有支持力的是绝经前乳腺癌。
一项综合分析包括了21个研究,其中有11个前瞻性队列研究和10个病例对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总体上植物木脂素摄入与乳腺癌风险无关。
绝经后的女性:木脂素摄入与降低乳腺癌风险显著相关
当研究根据绝经状态进行分析时,他们发现绝经后的女性中植物木脂素摄入与降低乳腺癌风险显著相关,合并风险比为0.85 (95%的置信区间是0.78-0.93,p<0.001),有显著性关联。而在绝经前女性中,植物木脂素摄入与乳腺癌风险之间则没有明显相关。
肠内木脂素与乳腺癌风险呈负相关
研究人员进一步检查了血液中肠内木脂素ENL的浓度,并尝试用体外发酵模型来估计肠内木脂素的暴露。他们发现,肠内木脂素暴露与乳腺癌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合并风险比为0.73(95%的置信区间是0.57-0.92)。但是,当考虑血液ENL水平时,这种关联性就不再显著。
在四项研究中观察膳食中的肠内木脂素,也发现了类似的关联,即高摄入肠内木脂素与降低乳腺癌风险相关。
近期的研究继续支持着肠内木脂素对乳腺癌的保护作用的假说,但这种作用取决于绝经状态。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绝经状态在木脂素与乳腺癌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能需要考虑不同的机制来理解这种复杂的关联。
另一研究表明,高木脂素摄入量的女性乳腺癌发生率降低40-50%,不受绝经状态影响。不过,在绝经前女性中,与PINO和LARI有较强关联,而绝经后女性与MAT有较强关联。
动物模型的研究显示,木脂素可以促进乳腺细胞的分化,延缓乳腺肿瘤的发生,并在妊娠和哺乳期对乳腺结构具有益处的变化。
实验证明,SES可以减少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增加凋亡。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肠内木脂素对抗癌效应产生影响。
综合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植物木脂素摄入可能对乳腺癌的风险有保护作用,尤其在特定类型的肿瘤和绝经后女性中表现更为显著。动物模型的研究也支持了木脂素在乳腺癌防治中的潜在作用。
前列腺癌是一种发生在前列腺组织中的恶性肿瘤。前列腺是男性生殖系统的一部分,位于膀胱下方,主要负责产生精液。前列腺癌通常会导致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性功能和生活质量。早期发现和治疗前列腺癌对于患者的康复非常重要。
木脂素在前列腺癌中作用的证据多样化
一方面,一些体外和动物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木脂素在前列腺细胞中具有化学预防作用。
最近的证据确认,即使在进食木脂素前体后体内可达到的浓度下,ENL(肠内植物雌激素)也能抑制早期前列腺癌细胞的增殖。
来自人类研究的数据却不一致
一些证据显示有益处,而一些研究则发现木脂素与前列腺癌之间没有关联。
有两项病例对照研究显示,较高的木脂素摄入与前列腺癌风险增加相关。
EPIC-Norfolk的一项嵌套病例对照研究考察了木脂素与前列腺癌的关系。
参与者完成了为期7天的饮食记录,用以估算每日木脂素摄入量。除了估算植物木脂素MAT和SECO的摄入量,研究人员还估算了来自乳制品和其他动物产品的预形成肠内木脂素的摄入量。
这是首次在木脂素暴露的总体估算中考虑动物来源的肠内木脂素。考虑到哺乳动物,尤其是反刍动物,能够在其瘤胃中生成大量肠内木脂素,因此一些动物产品,特别是乳制品,含有肠内木脂素。
该研究包括204例前列腺癌病例和812个对照组。估算的预形成肠内木脂素平均摄入量在前列腺癌病例中为20 μg/天(±9),在对照组中为18 μg/天(±9)。在年龄调整模型中,总木脂素摄入量与前列腺癌无关(OR 1.05; 95% CI 0.81–1.36; p=0.72)。然而,总肠内木脂素摄入量(包括非木脂素植物雌激素Equol)与前列腺癌呈正相关(OR 1.41; 95% CI 1.12–1.76; p=0.003),Equol(OR 1.43; 95% CI 1.14–1.80; p=0.002)和ENL(OR 1.39; 95%CI 1.12–1.71, p=0.003)单独考虑时也是如此。
然而,在进一步调整了年龄、身高、体重、身体活动、社会阶层、前列腺癌家族史和每日能量摄入等协变量后,这些关联性变得不显著,表明木脂素的对前列腺癌健康的影响可能取决于木脂素在肠内转化。
心血管疾病是指影响心脏和血管系统的疾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中风、心肌病等。心血管疾病是导致全球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0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木脂素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综述总结了随机对照试验(RCTs)和观察性研究的发现。虽然一些RCTs未显示出任何效果,但许多研究显示对血压、C反应蛋白和血脂分布有有益效果。作者还讨论了研究木脂素摄入的观察性研究以及研究血清中ENL(肠内木脂素)的观察性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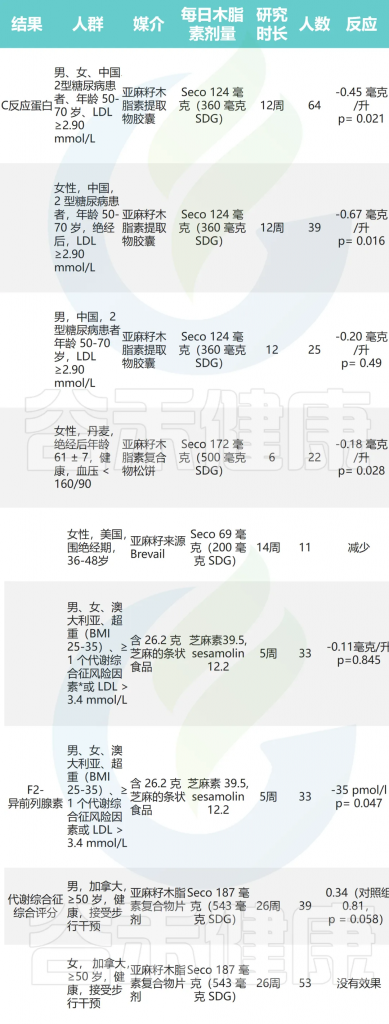
在11项观察性研究中,有5项显示随木脂素饮食摄入增加或血清ENL浓度增加,心血管风险降低;有5项被作者描述为具有边缘显著性,另有1项未发现任何关联。作者指出,由于研究间实验协议的差异,系统评估这些干预措施的能力受到限制。
2012年的一项横断面研究发现,尿液中的肠内木脂素与血清甘油三酯水平呈负相关,与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呈正相关。
以上是木脂素与各类疾病之间的关联,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木脂素潜在的健康益处的宝贵信息。
然而,每个人对木脂素的代谢能力是不同的,这可能会影响其健康效果的个体体验。接下来,我们深入了解个体间木脂素代谢的差异。个体间的这些差异可能由遗传因素、肠道微生物组成、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造成。
食物中木脂素的复杂摄入模式
研究人群中木脂素暴露与疾病风险之间的关系既具有挑战性又复杂。各种食物都是木脂素的来源,而且这些食物不会单独食用。传统上,饮食来源木脂素的菜肴也包含其他可能被视为健康或不那么健康的食物。要分辨一般高木脂素食物(通常也是高纤维食物)或特定木脂素的摄入量与疾病风险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困难的。
高木脂素食物与疾病风险的关联难度
比如在乳腺癌研究中,作者描述了几种可能导致流行病学研究中获得结果模糊的因素。他们指出,几种因素在肠木脂素暴露中起作用,包括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含木脂素食物的饮食摄入、抗生素使用、吸烟状况、便秘等。作者还指出准确可靠地确定肠木脂素暴露的难度,以及基因因素在癌症发展和肠木脂素作用中的复杂角色。
即使在受控条件下,关于肠木脂素生产的个体差异也很大。
一项药代动力学研究中显示,固定剂量的 SDG 会产生多种血浆曲线,其中一些个体产生大量的 ENL 和 END,或者产生较高量的其中一种(例如,高ENL、低END,反之亦然),或者两者产生量都很低。
肠道菌群
这种变异大部分被认为是由于个体之间的肠道微生物群差异所致。不同的 END 和 ENL 血液循环出现模式及累积排泄值范围表明,肠道微生物在处理 SDG 代谢的不同步骤上的能力不同(有些不能有效地将 SDG 水解成 SECO,有些则无效将 END 转换为 ENL)。
木脂素转换细菌的系统发育树显示参与肠木脂素生成的生物分布于不同门类中
不同个体肠道菌群,在肠木脂素生成中的差异
有研究将新鲜粪便样本与630 μmol/L 的亚麻籽提取物孵育72小时,发现100个个体中END和ENL的生成量存在很大差异。63%的样本生成了不同量的END,而只有39%的样本生成了ENL。此外,END和ENL的生成量呈正相关,并且与较高的β-葡萄糖醛酸苷酶活性相关,这支持了在SDG转换过程中初始步骤的重要性。
个体在肠木脂素生物转化过程中的差异
另一个导致尿液或血液中ENL和END测量值变异的潜在来源,可能是个体在肠木脂素生物转化过程中的差异。尽管尚未进行遗传变异对木脂素可利用性影响的控制评估。
在人体内,植物木脂素及其代谢物有效地与葡萄糖醛酸或在较小程度上与硫酸结合。结合过程在肠道上皮和肝脏中由UDP-葡萄糖醛酸转移酶(UGT)和硫转移酶进行,结合体通过尿液和胆汁排出。那些重新经胆汁排出的进行肠肝循环。
在尿液中,ENL和END主要以单葡糖醛酸结合物形式排出(分别为95%和85%),小部分以单硫酸盐形式(2-10%)和自由苷元形式(0.3-1%)排出。
结肠细胞系已被证明能快速葡糖醛酸化肠木脂素,这表明大多数木脂素的结合可能在结肠中发生。此外,肝微粒体氧化比葡糖醛酸化慢得多,这表明END和ENL的氧化产物是肠木脂素的小代谢物。
饮 食
饮食在肠木脂素生成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不仅是由于食物中前体物质含量的差异,还因为食物基质和其他饮食因素对植物木脂素的可用性和转换为肠木脂素的影响。
水果、蔬菜和浆果已被证明能增加ENL的生成。黑麦作为一种富含植物木脂素的食物,在三项饮食干预研究中被证明能增加ENL的生成。
然而,一项涉及黑麦制品的类似干预研究显示,ENL生成没有增加。这种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但研究作者指出,他们的参与者通常较年轻,可能比其他研究的参与者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这可能导致木脂素在肠道中的转运速度加快,从而导致不完全的植物木脂素生物转化。其他涉及富含木脂素的亚麻籽和芝麻的饮食试验显示显著的ENL生成。
食物基质和食物加工影响木脂素的生物利用度
在一项随机交叉研究中,12名参与者每天摄入全亚麻籽、压碎的亚麻籽和研磨的亚麻籽(0.3 g/kg体重)。结果表明,与研磨的亚麻籽相比,全亚麻籽的平均相对生物利用度为28%,压碎的亚麻籽为43%。
另一项饮食研究发现,烘焙对尿液或血浆中肠木脂素浓度没有影响,当参与者摄入混入苹果酱中的研磨亚麻籽或烘焙在面包和松饼中的研磨亚麻籽时,表明这些化合物是热稳定的。
不同类型膳食纤维,影响肠木脂素的生成
在体外实验中,通过不同提取方法得到的黑麦分馏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总体来说,不同类型的膳食纤维可能会影响木脂素的生物利用度。含有不可提取分馏的悬液产生了显著更多的ENL。
性 别
关于木脂素代谢的性别差异的证据不一,但似乎女性比男性生成更多的肠木脂素。
几项研究饮食与肠木脂素生成关系的横断面研究显示没有性别差异。
女性的血浆ENL和END更早达到更高的浓度
然而,一项对2380名芬兰男女的横断面研究显示,女性血清ENL浓度高于男性。确实,当服用一次SDG剂量(1.31 μmol/kg体重)时,女性的血浆ENL和END不仅出现的更早,而且达到了更高的最大浓度。
女性的平均基线血清ENL浓度更高
一项全谷物饮食试验,发现女性的平均基线血清ENL浓度更高,尽管全谷物饮食后血清ENL的上升在男女之间是相似的。
亚麻籽,无性别差异;
蔬菜,男性排泄ENL比女性多
另一个随机交叉试验中,研究人员给男女吃亚麻籽并测量尿液中的木脂素排泄量,结果显示男女之间没有差异。其他涉及木脂素剂量的类似试验也未显示男女之间的肠木脂素生成差异。相反,在一项蔬菜摄入的控制饮食研究中,男性在实验饮食期间排泄的ENL比女性多。
女性:更多生成ENL和END的细菌
女性可能比男性生成更多肠木脂素的趋势,往往女性携带更多生成ENL和END的细菌。
此外,研究表明女性的胃肠道通过时间较男性更长;这种含纤维食物和植物木脂素在肠道中停留时间更长,可能进一步导致更多肠木脂素生成。
其他因素
抗微生物剂使用
由于肠道微生物群对肠木脂素生成的关键作用,口服抗微生物药物的使用与血清ENL浓度呈负相关。
在一项横断面研究中,在2753名芬兰男女样本中,使用抗微生物剂的参与者,ENL浓度明显降低,尽管在取样前的12-16个月内未接受治疗。而且抗微生物剂使用次数也与ENL浓度呈负相关。
肠道停留时间
肠道停留时间似乎是影响ENL生成的另一因素,尽管大多数研究依赖于非定量测量方式评估此因素。同一研究还发现,在女性中,血清ENL浓度与年龄和便秘呈正相关,而与吸烟呈负相关。
体重
此外,体重正常的女性ENL浓度明显高于体重不足或肥胖女性。其他欧洲研究支持Kilkkinen的发现,报告了BMI、吸烟和排便频率与血浆ENL浓度成反比。
生活方式
最近,一项研究考察了其他生活方式因素与尿液ENL水平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在一大样本20岁以上的美国男女中进行。
在2003-2006年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NHANES)的一部分(n=3000)中,发现年龄、收入和体育活动与尿液ENL呈正相关。
此外,与欧洲研究相似,吸烟和BMI与尿液ENL呈负相关。尽管存在这些关联,选择的社会人口学和生活方式因素仅解释了总变异量的一小部分(R2≤4%),这表明,它们对肠木脂素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
木脂素作为一类多酚,由植物木脂素和哺乳动物木脂素组成。本文探讨了什么是木脂素,哪些食物和饮食方式中木脂素的分布差异,同时概括总结了在体外、动物和人类三个层面上可能的对健康的影响。
木脂素的健康效益并非一成不变,比如芝麻酚在低浓度下显示抗氧化活性,在高浓度下呈促氧化活性,并在细胞中引发线粒体凋亡途径。在动物和体外模型中,木脂素的氧化应激研究主要涉及亚麻木酚素、芝麻素、厚朴酚、五味子,而只有少数临床试验评估了其作用。
根据现有研究,我们了解到这种暴露因多种环境和生理因素而异,包括植物木脂素类型、食物基质、其他可能影响肠道微生物活性的摄入物(如膳食纤维、抗微生物药物)、肠道微生物组成和活性,以及肠道停留时间及其他影响因素。
测量尿液或循环中的肠二苯乙烯二醇(END)和肠木质素(ENL)可能更好地表征这些生物活性化合物的内部暴露水平。这种方法也可作为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的生物标志,甚至是肠道微生物活性的指标。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能够有效快速地表征肠道微生物组,将其信息整合到统计模型中,未来将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微生物对木脂素与疾病风险关联的调节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Seth C. Yoder, Samuel M. Lancaster, Meredith A.J. Hullar, Johanna W. Lampe, Chapter 7 – Gut Microbial Metabolism of Plant Lignans: Influence on Human Health, Editor(s): Kieran Tuohy, Daniele Del Rio, Diet-Microbe Interactions in the Gut, Academic Press, 2015,Pages 103-117
Senizza A, Rocchetti G, Mosele JI, Patrone V, Callegari ML, Morelli L, Lucini L. Lignans and Gut Microbiota: An Interplay Revealing Potential Health Implications. Molecules. 2020 Dec 3;25(23):5709.
D. Ayres, J. Loike, Lignans: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Clinical Proper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0)
Adlercreutz H. Lignans and human health. Crit Rev Clin Lab Sci. 2007;44(5-6):483-525.
T. Umezawa. Diversity in lignan biosynthesis
Phytochem Rev, 2 (2003), pp. 371-390
W.M. Hearon, W.S. MacGregor.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lignans. Chemical Rev, 55 (1955), pp. 957-1068
J.-Y. Pan, S.-L. Chen, M.H. Yang, J. Wu, J. Sinkkonen, K.
Zou. An update on lignans: natural products and synthesis.
Nat Prod Rep, 26 (2009), pp. 1251-1292
D.R. Gang, A.T. Dinkova-Kostova, L.B. Davin, N.G. Lewis. Phylogenetic links in plant defense systems: lignans, isoflavonoids, and their reductases.
P.A. Hedin, R.M. Hollingworth, E.P. Masler, J. Miyamoto (Eds.), Phytochemicals for Pest Control,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Washington, DC (1997), pp. 59-89
P. Mäki-Arvela, B. Holmbom, T. Salmi, D.Y. Murzin
Recent progress in synthesis of fine and specialty chemicals from wood and other biomass by heterogeneous catalytic processes
Catal Rev, 49 (2007), pp. 197-340
B. Holmbom, C. Eckerman, P. Eklund, et al. Knots in trees – a new rich source of lignans. Phytochem Rev, 2 (2003), pp. 331-340
I. Cesarino, P. Araújo, A.P. Domingues Júnior, P. Mazzafera. An overview of lignin metabolism and its effect on biomass recalcitrance
Braz J Bot, 35 (2012), pp. 303-311
L.B. Davin, M. Jourdes, A.M. Patten, K.-W. Kim, D.G. Vassão, N.G. Lewis. Dissection of lignin macromolecular configuration and assembly: comparison to related biochemical processes in allyl/propenyl phenol and lignan biosynthesis
Nat Prod Rep, 25 (2008), pp. 1015-1090
W.R. Cunha, M. Luis, R.C. Sola, et al. Lignans: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properties V. Rao (Ed.), Phytochemicals – A Global Perspective of Their Role in Nutrition and Health, InTech, Rijeka, Croatia (2012), pp. 213-234
J. Harmatha, L. Dinan.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lignans and stilbenoids associated with plant–insect chemical interactions. Phytochem Rev, 2 (2003), pp. 321-330
N.G. Lewis, M.J. Kato, N. Lopes, L.B. Davin. Lignans: diversity, biosynthesis, and function. P.R. Seidl, O.R. Gottlieb, M.A.C. Kaplan (Eds.), Chemistry of the Amazon,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Washington, DC (1995), pp. 135-167
I.E.J. Milder, I.C.W. Arts, B. Van de Putte, D.P. Venema, P.C.H. Hollman Lignan contents of Dutch plant foods: a database including lariciresinol, pinoresinol, secoisolariciresinol and matairesinol
A.I. Smeds, P.C. Eklund, S.M. Willför
Content, composition, and stereochemical characterisation of lignans in berries and seeds
Food Chem, 134 (2012), pp. 1991-1998
A.I. Smeds, P.C. Eklund, R.E. Sjöholm, et al.
Quantification of a broad spectrum of lignans in cereals, oilseeds, and nuts. J Agric Food Chem, 55 (2007), pp. 1337-13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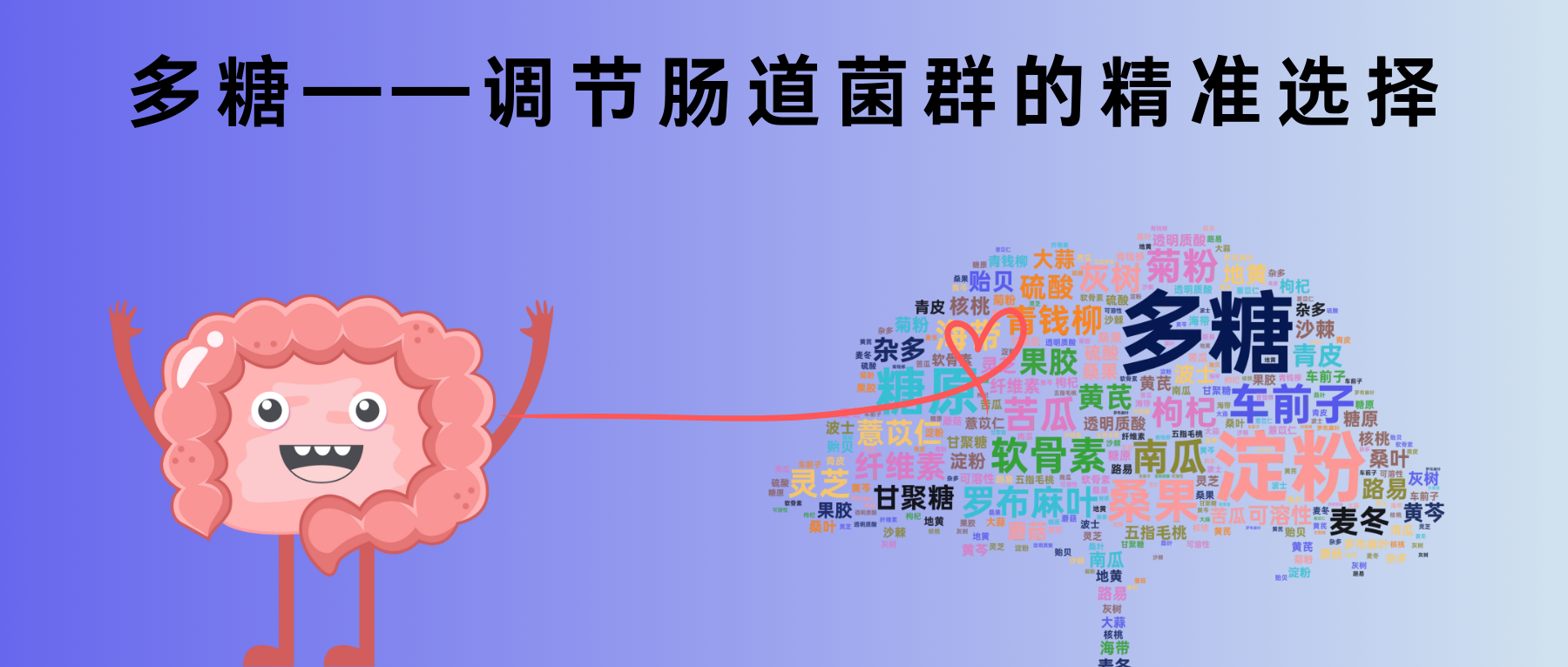
谷禾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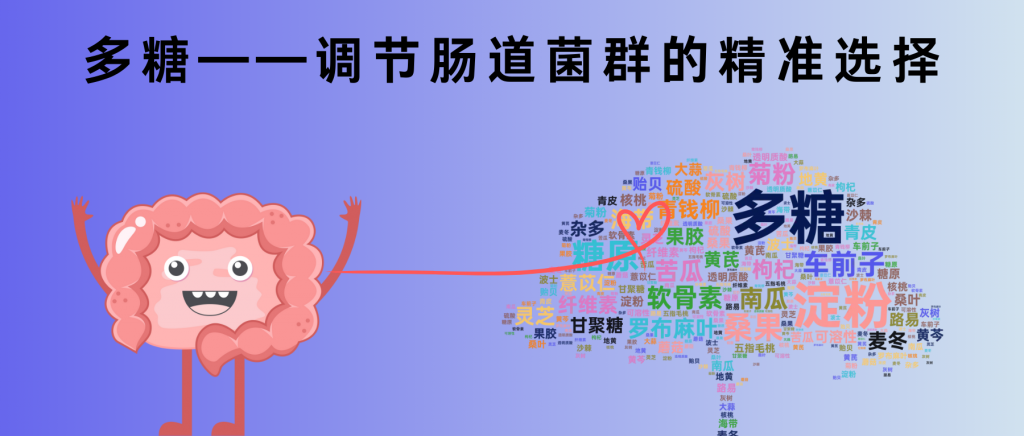
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让药物成为你的食物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疲劳、压力、不均衡的饮食,都在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多糖,这些来自植物、真菌乃至海洋生物的天然赠礼,正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健康支持。
多糖由单糖通过糖苷键结合而成的高分子碳水化合物。研究表明,多糖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包括调节免疫功能、降低血脂和血糖、抗癌、抗病毒、抗肥胖、抗精神病、抗氧化、抗炎、抗凝血、止吐、抗辐射等作用。因此,多糖已成为最重要的天然成分之一,并引起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虽然部分多糖如淀粉可以在人体胃和小肠中被消化吸收,但仍有许多特殊结构的多糖不能在这两个部位分解。对于那些不能被宿主消化的多糖,它们可以进入结肠,而结肠是大多数肠道菌群居住的地方。在结肠中,多糖可以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从而发挥营养或药理作用。
多糖与肠道菌群之间相互作用可以影响健康,同时也通过肠道菌群的代谢作用,转化为有益的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这些产物对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性、调节免疫反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扩展到了全身的健康状况,可以影响我们的精力水平、情绪状态,对疾病的抵抗力等方方面面。
本文将深入探讨多糖,了解其在人体内的消化过程、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代谢物影响健康,如短链脂肪酸、三甲胺、色氨酸,还讨论了多糖在疾病预防和治疗中的应用,包括它们在改善代谢性疾病、炎症性肠病、缓解疲劳、改善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方面的潜在效果。这为靶向肠道菌群开发新型的营养补充剂和药物提供了新的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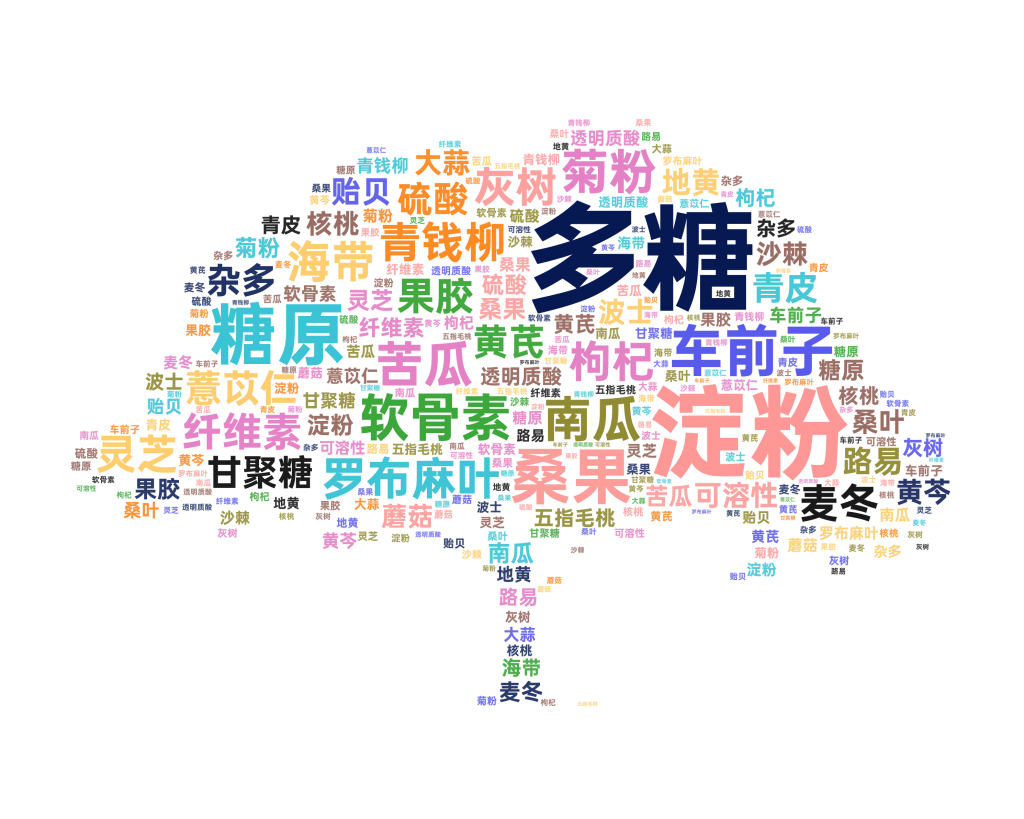
本文目录
01 多糖
02 多糖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
为什么多糖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
多糖促进或抑制肠道微生物群
多糖分子量、糖苷键影响其细菌调节活性
03 肠道微生物将多糖代谢为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的生物学效应
人体内的多糖代谢
多糖补充与短链脂肪酸的生成
04 多糖调节其他肠道微菌群代谢物
三甲胺和氧化三甲胺(TMAO)
色氨酸及其代谢产物
胆汁酸、脂多糖、胃肠道气体
05 多糖调节肠道菌群修复肠道屏障
06 多糖通过肠道菌群改善疾病
2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肥胖、高血脂症
炎症性肠病、其他肠胃疾病、肿瘤
疲劳、神经系统疾病(认知障碍、抑郁等)
07 部分多糖营养与菌群调节
路易波士茶多糖、地黄多糖、五指毛桃根多糖
大蒜多糖、槐耳多糖、黄芩多糖、枸杞多糖
岩藻多糖、桑叶多糖、沙棘多糖、蘑菇多糖
08 结语
糖,这个小小的分子,是能量的源泉,是细胞的加油站。除了我们熟知的葡萄糖以外,还有一种叫做多糖,由许多糖分子手拉手组成,从植物的根茎到海洋生物的细胞壁,它们以复杂多样的形态存在。
根据糖单元的数量,碳水化合物可分为几类:
多糖是由多个单糖分子通过糖苷键连接而成的聚合物,属于高分子碳水化合物。它们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包括植物、真菌和海藻等生物体内。根据其来源和结构特性,多糖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如免疫调节、抗氧化、抗肿瘤等。
多糖是由10个以上相同或不同的单糖通过α或β糖苷键连接而成的大分子化合物,分子量从几万到数百万。
多糖的空间构象非常复杂,具有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结构。研究表明,多糖的活性与其结构密切相关。此外,通过分子修饰,如乙酰化、硫酸化、羧甲基化、硒化、磷酸化和磺化等可显著提高多糖的生物活性。
根据来源和结构的不同,多糖可以分为天然多糖和合成多糖,其中天然多糖又可根据其在自然界中的分布分为植物多糖、动物多糖、微生物多糖等。
例如,透明质酸和硫酸软骨素属于动物多糖,而纤维素、淀粉和糖原是常见的植物多糖。
淀粉
由大量葡萄糖分子通过α-1,4-糖苷键和α-1,6-糖苷键连接而成,形成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两种结构。广泛存在于谷物(如大米、小麦、玉米)、薯类(如土豆、红薯)等食物中。在人体消化过程中,被淀粉酶逐步分解为葡萄糖,为身体提供能量。
纤维素
由葡萄糖分子通过β-1,4-糖苷键连接而成,形成长而直的链状结构。是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在蔬菜(如芹菜、菠菜)、水果(如苹果)中含量丰富。由于人体缺乏分解β-1,4-糖苷键的酶,纤维素难以被人体消化吸收,但对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等具有重要作用。
果胶
是一种复杂的多糖,由半乳糖醛酸等组成。常见于水果(如柑橘、苹果)中。在食品工业中,常用于制作果酱、果冻等,增加其黏稠度和稳定性。
尽管功能性糖因其在健康和疾病预防中的潜在作用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它们的天然可用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有益的分子,需要采用特定的提取方法来增加它们的可获得性,多糖提取常用的方法有热水提取、酸提取、碱提取和酶水解等。
近年来,一些新的方法,如超声波提取、微波提取、超滤、高压电场法、超临界流体萃取、亚临界水萃取等也用于多糖的提取。这些方法不仅能够提高多糖的提取率,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多糖的结构完整性,从而保留其生物活性。
通常,人体分泌的消化酶只能分解几种多糖,而纤维等许多多糖不能被吸收和直接使用。因此,多糖可以通过小肠进入结肠,这是大多数肠道细菌居住的地方,然后与肠道微生物群相互作用。
细菌在肠道中通过发酵降解多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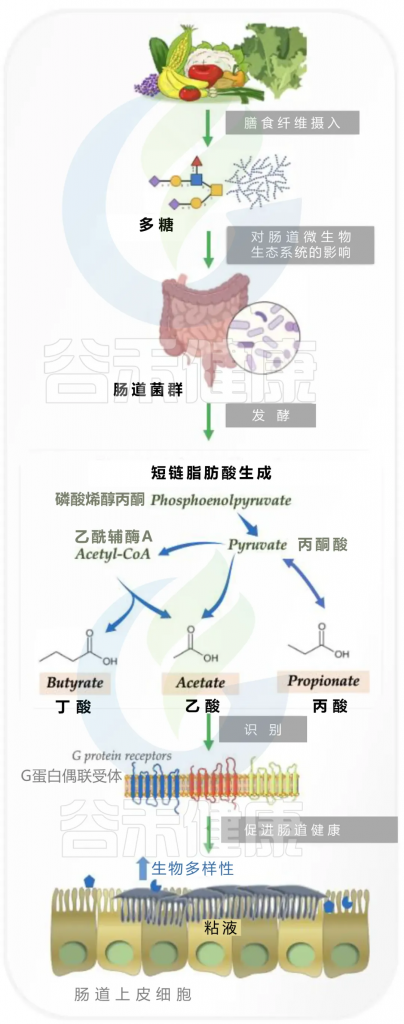
doi.org/10.3390/nu14194116
多糖转化为短链脂肪酸
首先与多糖能够发酵生成酸性的短链脂肪酸密切相关。未电离的短链脂肪酸能够穿过细菌细胞膜,对肠道细菌产生一系列影响,例如改变DNA合成和氨基酸摄取。
短链脂肪酸对肠道细菌的影响
例如,短链脂肪酸能够通过调节侵袭基因的表达,抑制沙门氏菌(一种常见的食源性病原体)的生长。因此,短链脂肪酸的增加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的功能,进而影响其组成。
肠道pH值的变化
短链脂肪酸的增加还会导致肠道pH值下降,影响细菌的适应能力。每种细菌都有其适宜的pH范围,不同细菌在特定pH条件下的适应能力各异。
多糖的降解产物作为能量来源
多糖对肠道菌群组成的调节作用还与其降解产物有关。一些肠道细菌能够利用多糖的降解产物作为碳源和能量来源,而另一些细菌则不能。
综上所述,多糖通过影响肠道菌群的代谢功能,直接调节了肠道菌群的组成。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多糖如何通过肠道菌群影响宿主健康提供了新的视角。
多糖的益生元效应
具有选择性刺激有益微生物生长能力的多糖被称为益生元,例如果聚糖,它能丰富乳酸菌和/或双歧杆菌。这些有益细菌的减少与糖耐量受损密切相关。一些多糖能够丰富这些细菌,因此可以用来改善糖尿病表型。
多糖抑制病原菌
病原菌在胃肠道中的定植和增加会导致一系列疾病,而抑制它们可以控制疾病的严重程度。例如,致病性 Sutterella、Desulfovibrionaceae、Streptococcaceae 、Clostridium 的比例较高与肥胖发展呈正相关。
多糖的双向调节作用
疾病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不同的微生物,包括有害细菌和有益细菌。例如:
多糖能够对肠道微生物发挥双向调节作用,即促进有益细菌的同时抑制有害细菌。
例如,口服灰树花多糖(GFHP)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积极作用与调节肠道菌群有关。
在分子量方面,不同分子量的魔芋葡聚糖(KGM)对2型糖尿病(T2DM)大鼠的降血糖作用研究表明,中等分子量的KGM显著增加了Muribaculaceae,减少了Romboutsia和Klebsiella,但高分子量和低分子量的KGM对这些细菌的影响不显著。
灵芝的低分子量多糖(<10 kDa)具有更好的发酵和更高的产气能力,刺激肠道细菌快速生长。另一方面,高分子量多糖(>100 kDa)更难被肠道细菌发酵,并且在肠道中的停留时间更长,导致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更长。
高分子量的黄芪多糖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但其相对分子量较大,溶解性差,生物利用度低,限制了其功效的发挥。低分子量的黄芪多糖具有较好的水溶性,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刺激巨噬细胞摄取中性红、NK细胞增殖,发挥免疫活性。
多糖由各种通过糖苷键连接的单糖组成,糖苷键的类型和位置导致肠道微生物群的选择性发酵存在差异。
多糖的单糖组成越复杂,调节细菌的活性越强
一项关于龙眼多糖和燕麦多糖的研究表明,龙眼多糖能显著促进干酪乳杆菌、嗜酸乳杆菌、植物乳杆菌、粪肠球菌的增殖,但燕麦多糖的作用并不明显。原因是龙眼多糖由葡萄糖、甘露糖和阿拉伯糖组成,而燕麦多糖的单糖主要是葡萄糖。
短链脂肪酸(SCFA)是一组含有少于六个碳的脂肪酸,包括甲酸盐、乙酸盐、丙酸盐、丁酸盐、戊酸盐。
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是肠道中的主要SCFA,约占所有SCFA的95%,三者的比例约为3:1:1。
作为肠道微生物群和宿主的重要能量来源,短链脂肪酸通过不同的作用模式在健康和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用机制
与GPRs的相互作用
抗炎作用
免疫调节
HDAC抑制作用
丁酸盐的作用
与疾病的关系
多糖对SCFA的调节及其对靶标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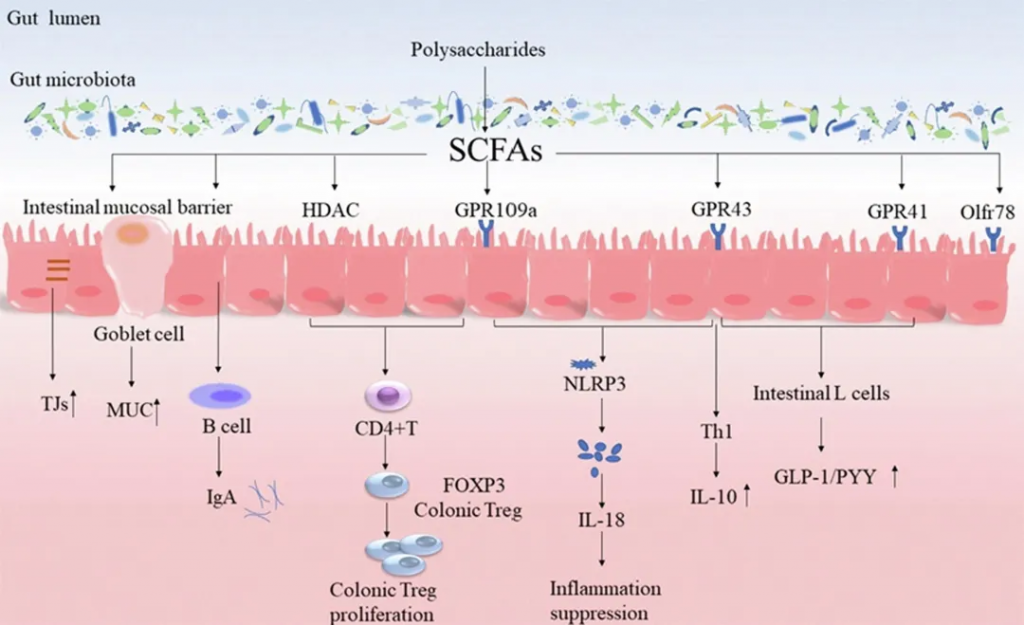
doi.org/10.1016/j.foodres.2022.111653
人体内消化酶的局限
在人体消化系统中,我们自身分泌的消化酶往往难以分解复杂的多糖。这些多糖分子,因其结构复杂,通常在我们体内无法被有效代谢。
肠道菌群的代谢作用
我们的肠道菌群拥有破解这些复杂多糖的秘密武器——一系列的酶,统称为碳水化合物酶(CAZymes)。这些酶能够分解多糖,将其转化为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短链脂肪酸。
碳水化合物酶的种类
肠道菌群中的“专家”与“通才”
在肠道菌群中,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是编码CAZymes的两大主力。
多糖的初步降解
在属的水平上,多糖最初可以由某些微生物降解,例如双歧杆菌属、真杆菌属、梭菌属、罗氏菌属(Roseburia spp.)。
SCFAs的生成途径
尽管人体自身无法分解复杂的多糖,但我们的肠道菌群却具备了这一能力,它们通过一系列特殊的酶,将多糖转化为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短链脂肪酸。
多糖对SCFAs生成的促进作用
饮食补充多糖可以为产生SCFAs的细菌提供有利的生长环境,从而促进SCFAs的生成。例如,沙棘多糖(CCPP)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SCFAs,能够缓解2型糖尿病。
沙棘多糖调节肠道菌群和SCFAs,缓解2型糖尿病
枸杞多糖调节肠道菌群,提高SCFAs
多糖结构对短链脂肪酸生成的影响
不同的多糖因其分子结构的不同,对SCFAs的调节作用也不尽相同。
多糖的疗效与SCFAs的非直接关联
尽管大多数多糖可以被代谢成SCFAs,但它们的疗效并不一定与SCFAs直接相关。
多糖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促进SCFAs的产生,对健康具有多方面的益处。然而,多糖的结构与它们对SCFAs生成的调节作用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此外,多糖的疗效可能不仅限于SCFAs的产生,还可能涉及肠道菌群产生的其他分子。
在肠道微生物群的作用下,脂质和蛋白质等饮食成分可以代谢为一系列代谢产物,如三甲胺-N-氧化物(TMAO)、色氨酸、脂多糖(LPS)等。此外,肠道微生物群还可以与宿主合成和释放的化合物相互作用。例如,肠道微生物群可以将初级胆汁酸(BA)转化为次级胆汁酸。由于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与肠道微生物群代谢物的产生直接相关,因此可以推断,除了SCFAs,多糖还可以调节其他肠道微生物群代谢产物,如BA。
三甲胺和TMAO的代谢过程
在肠道中,饮食中的四胺类物质如胆碱、L-肉碱和卵磷脂(来自红肉、鸡蛋、鱼、海鲜)首先被微生物胆碱三甲胺裂解酶分解成三甲胺(TMA)。随后,TMA被吸收进入门脉循环,并运输到肝脏,在黄素单加氧酶1和黄素单加氧酶3的作用下转化为三甲胺-N-氧化物(TMAO)。
TMAO的潜在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TMAO是一种潜在的有害代谢产物。多项研究指出,TMAO水平的增加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呈正相关。例如,TMAO可以直接增强血小板的反应性,促进血栓形成,并通过激活核因子κB(NF-κB)和NLRP3炎症体影响血管炎症。
多糖对TMA和TMAO代谢的影响
最近的研究表明,TMA和TMAO在理解多糖的作用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
不同多糖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不同的多糖可以通过调节相同的肠道细菌来降低TMA和TMAO的代谢,例如变形菌门。研究表明,变形菌门负责TMA的转化,增加变形菌门可能导致TMA增加。然而,也有研究表明TMAO与变形菌门呈负相关,这表明多糖调节变形菌门与TMA产生的效应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多糖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影响TMA和TMAO的代谢,从而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多糖与TMAO之间的关系复杂,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阐明这些相互作用的确切机制。
色氨酸代谢的重要性
色氨酸(Trp)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的代谢可以分为内源性代谢和细菌性代谢。内源性代谢主要通过犬尿氨酸途径(KP)和5-羟色氨酸途径进行,前者产生犬尿氨酸(KYN)、犬尿酸(KA)、烟酸、黄嘌呤酸等,后者转化为5-羟色氨酸(5-HT)和褪黑素。
色氨酸代谢物的生理功能
增强免疫:色氨酸可加强免疫力,减少炎症。
神经保护:KA作为谷氨酸受体拮抗剂,具有神经保护和抗惊厥作用,还能调节能量代谢。
情绪调节:5-HT作为神经递质,可调节情绪、肠道通透性和肠道蠕动。
肠道菌群在色氨酸代谢中的作用
肠道细菌代谢色氨酸产生吲哚及其衍生物,如吲哚丙酸、吲哚乙酸等,这些物质可以缓解炎症,促进肠道上皮屏障功能。肠道菌群的色氨酸代谢异常与肠易激综合症、代谢综合症和结肠癌等疾病有关。例如,结肠癌患者常伴有色氨酸水平下降和KP代谢物水平升高。
多糖影响肠道微生物色氨酸代谢,从而改善疾病
吲哚是硫酸吲哚酚的前体,是一种蛋白结合尿毒症毒素,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对于患有终末期肾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吲哚水平升高,患者粪便中产吲哚细菌丰富。
总的来说,多糖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改变色氨酸代谢,最常见的是增加乳杆菌和阿克曼菌,从而缓解疾病。
胆汁酸的生物合成与功能
胆汁酸(BAs)是一类由肝脏产生的特殊类固醇分子,经过肠道菌群转化。肝脏中存在两种BA生物合成途径:
CA和CDCA是体内的主要胆汁酸。经过肠道菌群的改造,CA转化为脱氧胆酸(DCA),CDCA转化为鹅去氧胆酸(LCA)。
胆汁酸受体及其作用
胆汁酸受体包括细胞表面受体和细胞内受体。细胞表面受体包括TGR5,细胞内受体包括法尼酰X受体FXR、孕烷X受体、维生素D3受体(VDR)和组成型雄烷受体。胆汁酸通过激活相应的受体调节脂质、葡萄糖和能量代谢。例如,TGR5和VDR的激活导致GLP-1和FGF19分泌,GLP-1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FGF19可以通过抑制脂肪生成减少肝脏脂肪变性。
多糖对胆汁酸代谢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多糖可以通过恢复胆汁酸的代谢来缓解疾病。
多糖对胆汁酸代谢影响的总结
多糖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特别是Bacteroides、Lactobacillus、Clostridium、Ruminococcus、Bifidobacteria,影响胆汁酸的代谢。
某些多糖如岩藻聚糖和灰树花多糖减少了Clostridium的水平,这与文献报道的促进胆汁酸转化的作用似乎矛盾,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这些肠道细菌与多糖之间的关系。
脂多糖的危害
脂多糖(LPS)是由革兰氏阴性细菌(如大肠杆菌)产生的内毒素。持续暴露于LPS或LPS异常增加,可通过减少肠道上皮细胞活性、降低肠道细胞增殖、抑制肠道细胞迁移和诱导肠道细胞凋亡等方式,导致肠道损伤。
LPS的转移还能损伤肠道,并可能通过与多种受体的相互作用,如LPS结合蛋白、簇分化14、髓样分化2和Toll样受体4,引发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肥胖、动脉粥样硬化等一系列疾病。
多糖对LPS产生菌的抑制作用
许多多糖能够抑制产生LPS的细菌。例如,在链脲佐素(STZ)诱导的糖尿病肾病模型中:
多糖调节肠道菌群的矛盾效应
尽管多糖可以通过调节肠道细菌来抑制LPS,但对特定细菌的调节作用可能存在矛盾。例如,作为LPS产生菌的拟杆菌门,在多糖处理后的水平变化并不一致。有研究表明,黄精多糖和蝉花多糖增加了拟杆菌门的水平,而竹荪多糖却降低了它。这些研究表明,多糖对肠道菌群的调节效应有时可能相互矛盾,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认结果。
胃肠道气体的生成
胃肠道内通过细菌发酵食物,会产生一系列气体,包括氢气(H2)、甲烷(CH4)、二氧化碳(CO2)、硫化氢(H2S)和一氧化氮(NO)。这些气体在胃肠道中发挥着调节作用,例如影响结肠蠕动、神经通讯、血管功能和免疫反应等。
气体产生的部位和作用
CO2 主要在胃中产生,而其他气体如 H2、CH4、CO2 和 H2S 主要在小肠和结肠中产生。
这些气体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它们可以调节肠道功能,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和疾病的发生。
多糖对气体产生的调节
尽管多糖对 H2、CH4 和 CO2 的产生有明显影响,但关于多糖结构与气体产生之间具体关系的研究会相对较少。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明确这些关系,以及多糖如何通过影响肠道菌群来调节气体的产生。
肠道菌群是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落,具有显著的组成和功能多样性。不同的微生物可以介导相同或不同的代谢物的产生,相同的微生物也有助于不同代谢物的生产。
例如,持续的研究表明:
拟杆菌门(特别是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Bacteroides fragilis)、厚壁菌门(如Clostridiaceae、Erysipelotrichia)、以及变形菌门可以促进TMA的产生。
放线菌门(如Bifidobacteria)、厚壁菌门(如Lactobacillus、Clostridium、Peptostreptococcus)、拟杆菌门(如Bacteroides)可以促进色氨酸(Trp)的转化。
双歧杆菌、乳酸菌、梭菌、Peptostreptococcus、拟杆菌也有助于次级胆汁酸(BAs)的产生。
因此,就像肠道菌群组成的调节一样,多糖对特定肠道菌群代谢物功能的调节作用不是孤立的。
肠道是我们抵御外界有害物质和病原体侵袭的第一道防线。它由多个层次的子屏障构成:
生物屏障:由肠道细菌和病毒组成;
化学屏障:包含免疫球蛋白A(IgA)、抗菌肽(AMPs)和粘液(MUC);
物理屏障:由肠道上皮细胞构成;
免疫屏障:含有T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细胞等免疫细胞。
这些子屏障协同工作,限制病原体与肠道的接触,维持肠道稳定。肠道屏障的损伤与多种疾病正相关,包括肠易激综合症(IBS)、代谢综合征、过敏、肝脏炎症等。
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肠道屏障: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多糖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对肠道屏障有益。正常的肠道菌群组成可以通过竞争性排除,通过消耗营养源和占据附着位点,作为抵御外界病原体的屏障。
多糖→ 调节肠道菌群→ 修复肠道屏障
肠道菌群可以刺激宿主产生抗菌化合物,如IgA和AMPs,这些是化学屏障的关键组成部分。
例如,菊粉型果聚糖可以促进乳杆菌的丰度和IgA的分泌。在DSS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小鼠模型中,金银花多糖通过增加双歧杆菌和乳杆菌,增加了分泌型IgA含量,从而调节肠道屏障。
在DSS诱导的结肠炎小鼠中,海蜇皮多糖增加Akkermansia,Akkermansia muciniphila作为粘液的降解者,可以增强肠道屏障的完整性,减少炎症。同时海蜇皮多糖增加结肠中TJs和MUC2的表达,保护了肠道屏障。
多糖→ 短链脂肪酸→ 修复肠道屏障
短链脂肪酸和胆汁酸等肠道菌群代谢物在调节肠道屏障功能中也扮演重要角色。
多糖→ 色氨酸和胆汁酸代谢→ 修复肠道屏障
这些研究表明,多糖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维护肠道屏障的完整性。
代谢性疾病包括一组因碳水化合物、脂质和蛋白质代谢错误而导致的疾病。2 型糖尿病 (T2DM)、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NAFLD) 和肥胖是常见的代谢性疾病。
生活方式干预、全身药物治疗和外科手术等多种方法被用于预防和治疗代谢性疾病。尽管代谢性疾病的药物治疗取得了最新进展,但潜在的不良反应仍然是关键挑战。
使用天然物质的药物治疗被认为是改善代谢疾病的一种有前途且可行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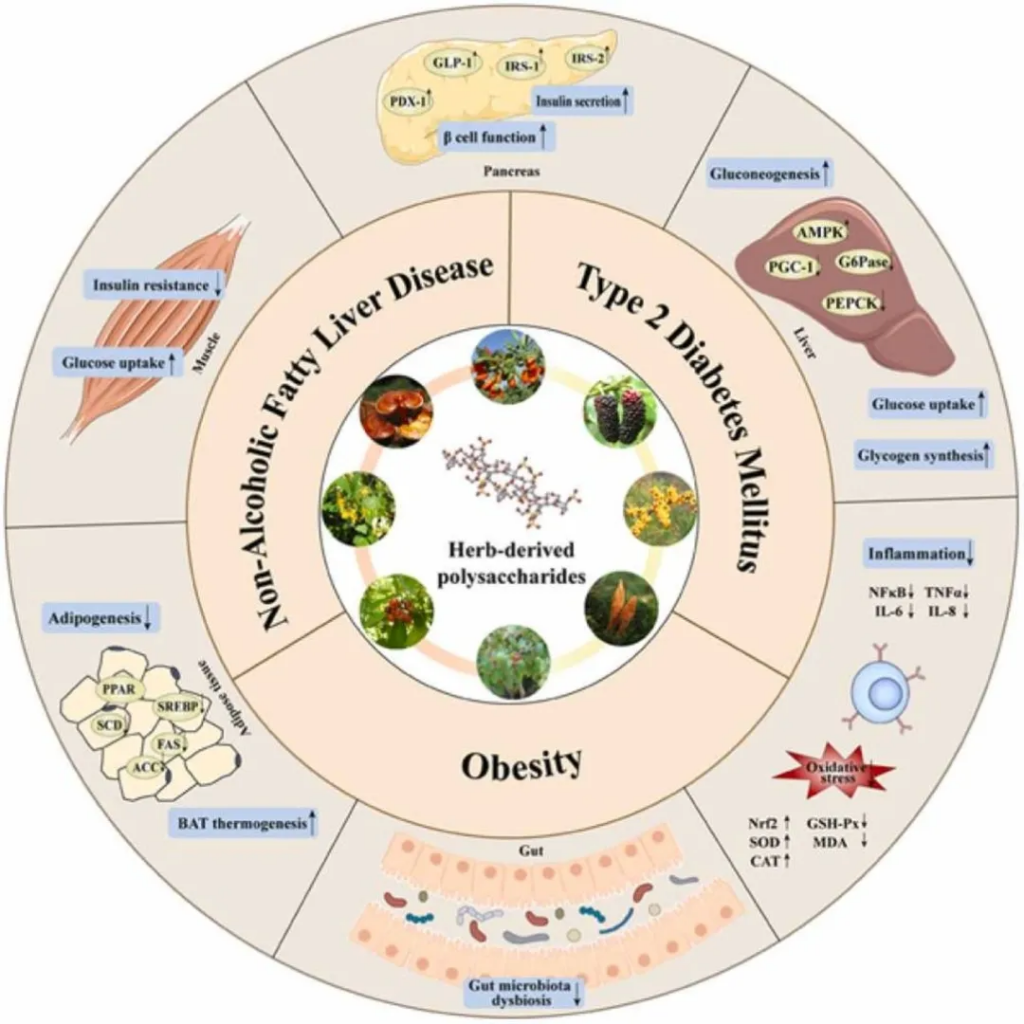
doi.org/10.1016/j.biopha.2023.114538
多糖通过多种机制在治疗2型糖尿病方面表现出良好的效果,比如:
肠道菌群在代谢紊乱,特别是 2 型糖尿病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车前子多糖 对 STZ 诱导的 2 型糖尿病大鼠有抗糖尿病作用,这可能与其调节肠道菌群和增加短链脂肪酸水平有关。车前子多糖可显著增加糖尿病大鼠粪便中Bacteroides vulgatus、发酵乳杆菌、Prevotella loescheii、Bacteroides vulgates等结肠细菌的多样性和丰度,以及短链脂肪酸的浓度。
◤桑果多糖 可以丰富糖尿病小鼠的功能菌并调节微生物多样性。具体而言,该多糖显著富集了一些有益细菌(拟杆菌目、乳杆菌属、Allobaculum、拟杆菌属、阿克曼菌属),同时减少了一些致病菌(葡萄球菌、棒状杆菌属、Jeotgalicoccus、Aerococcus、Enterococcus、Facklamia)。
◤罗布麻叶的两种富含多糖的提取物改善了糖尿病小鼠的肠道微生物群失调,包括增加了Odoribacter、Anaeroplasma、Parasutterella、Muribaculum的丰度,并降低了肠球菌属、克雷伯菌属、Aerococcus的丰度。这可能有助于它们的抗糖尿病作用。
◤菊粉补充增加了双歧杆菌的丰度并增强了肠道屏障的完整性,这与2型糖尿病呈负相关。
◤青钱柳叶中分离的多糖通过增加 SCFAs 含量和有益的肠道细菌瘤胃球菌科来减轻 HFD/STZ 诱导的 2 型糖尿病大鼠的糖尿病症状。
◤苦瓜中的天然多糖通过增加 SCFAs 含量和Prevotella loescheii、Lactococcus laudensis 的丰度来改善 HFD/STZ 诱导的 2 型糖尿病大鼠的高血糖、高脂血症、高胰岛素血症。
◤天然南瓜多糖通过增加阿克曼氏菌和减少丹毒丝菌科(Erysipelotrichaceae)来显示出对 HFD/STZ 诱导的 2 型糖尿病的降血糖作用。此外,南瓜多糖还能增加 2 型糖尿病模型中肠道短链脂肪酸的产生。
◤灵芝多糖(GLP)通过恢复HFD/STZ诱导的肠道微生物群失调,特别是通过增加Blautia、拟杆菌、Dehalobacterium、Parabacteroides,以及减少有害的肠道细菌Aerococcus、Corynebacterium、Ruminococcus、Proteus,显示出抗糖尿病作用。
◤薏苡仁多糖通过降低厚壁菌门/拟杆菌门的比例和增加SCFAs的含量,在HFD/STZ诱导的T2DM小鼠模型中表现出降血糖活性。
◤葡甘聚糖作为铁皮石斛、芦荟和魔芋的天然多糖,通过增加厚壁菌门的丰度和减少拟杆菌门、变形杆菌的丰度,改善HFD/STZ喂养大鼠的T2DM代谢紊乱。
多糖对改善NAFLD具有有益作用,比如:
多糖可以改善肠道菌群失调并保护非酒精性脂肪性肝动物的肠道屏障完整性
◤枸杞多糖结合有氧运动通过改善肠道菌群失调改善 NAFLD,包括调节肠道菌群的丰度和多样性,增加微生物代谢产物 SCFA 的水平,减少变形菌和厚壁菌门/拟杆菌门的比例。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是参与宿主代谢和脂肪积累的关键细菌。
◤麦冬多糖可以通过调节肠-肝轴显著保护 NAFLD。具体来说,这种多糖显著降低了一些有害细菌的相对丰度,包括乳球菌、肠杆菌、Turicibacter、Clostridium- sensu-stricto -1、Tyzzerella、Oscillibacter,并增加一些有益菌的相对丰度,如Alistipes、Ruminiclostridium、Rikenella。这种多糖还显著增加了两种产SCFAs菌( Butyricimonas、Roseburia )的丰度以及乙酸和戊酸的水平,从而改善了炎症反应和肝脏脂质代谢。
◤灰树花杂多糖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改善高脂饮食诱导的NAFLD,包括显著增加Allobaculum、拟杆菌属和双歧杆菌属丰度,减少Acetatifactor、Alistipes、Flavonifractor、Paraprevotella、Oscillibacter的丰度。
◤黄芪多糖可减轻HFD喂养小鼠的NAFLD,丰富了脱硫弧菌属,尤其是作为SCFAs、乙酸的产生者的Desulfovibrio vulgaris,减轻肝脂肪变性。
◤诺尼果多糖来源于辣木,通过促进短链脂肪酸的产生缓解HFD喂养小鼠的NAFLD,并通过改善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和组成逆转HFD诱导的肠道微生态失调。
◤核桃青皮多糖通过提高肠微生物群(包括普氏菌科、Allobaculum)的SCFAs含量和丰度,预防HFD喂养大鼠的肥胖和NAFLD。
◤从贻贝中提取的贻贝多糖,α-D-葡聚糖(MPA)可保护HFD喂养的大鼠的NAFLD,补充MPA可逆转HFD抑制的微生物微生态失调和SCFAs。
◤海带可溶性多糖通过降低厚壁菌门/拟杆菌门的比例,促进Verrucomirobia和丙酸盐产生菌拟杆菌和阿克曼菌,减轻高脂饮食喂养小鼠的NAFLD。
多糖通过多种机制表现出良好的抗肥胖作用,作用机制如:
◤枸杞多糖补充剂可降低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的比例,增加产短链脂肪酸菌,如Lacticigenium、Butyricicoccus、Lachnospiraceae_NK4A136_group数量,从而改善肥胖小鼠的肠道菌群失调。
◤桑叶多糖治疗可调节肥胖小鼠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这与增加Allobaculum、Parabacteroides、Porphyromonadaceae、Butyricimonas、Ruminococcus 的水平有关。
◤黄精多糖调节HFD喂养的肥胖大鼠的肠道微生物群结构,包括降低梭菌、肠球菌、Coprobacillus、乳球菌、Sutterella的相对丰度。
◤沙蒿多糖给药8周显著上调了屏障完整性的结肠基因,并通过增加有益细菌(双歧杆菌和Olsenella)和抑制有害细菌(Mucispirillum和幽门螺杆菌)改善了肥胖小鼠的肠道微生物微生态失调。同时,它显著富集了与促进SCFAs产生相关的碳水化合物代谢,同时显著抑制了与肥胖和肠道微生态失调相关的氨基酸代谢。
◤从海带中提取的天然多糖可通过使肠道菌群正常化来缓解小鼠HFD引起的肥胖,特别是通过增加拟杆菌目和Rikenellaceae的丰度。
◤从杏鲍菇中分离出的蘑菇多糖通过增加产生 SCFA 的肠道细菌Anaerostipes和Clostridium 的数量,在高脂饮食喂养的小鼠中表现出抗肥胖作用。
◤茶树菇多糖对HFD诱导的小鼠脂肪堆积和减肥的影响,发现脱硫弧菌减少,副拟杆菌增加,从而显著降低肥胖相关的TNF-α 和 IL-6 的水平。
◤从苦瓜中获得的多糖通过增加有益细菌(如放线菌、Coprococcus、乳酸杆菌)和减少有害细菌(变形菌和幽门螺杆菌)来改善HFD诱导的小鼠肥胖。
◤日本刺参的硫酸多糖通过富集益生菌Akkermansia、减少携带内毒素的变形杆菌和提高SCFAs含量来预防HFD诱导的小鼠肥胖。
◤ 破壁灵芝孢子多糖能逆转 HFD 喂养小鼠中许多细菌的相对丰度,特别是一些潜在的益生菌,包括Allobaculum、双歧杆菌,这与抗肥胖呈正相关。双歧杆菌、乳杆菌和阿克曼菌可促进SCFAs的产生,并抑制梭菌科、脱硫弧菌和肠球菌的丰度,这将有助于减少体重和脂质积累。
总的来说,多糖可通过作用于多个环节、调控多个疾病相关靶点来改善这三种代谢性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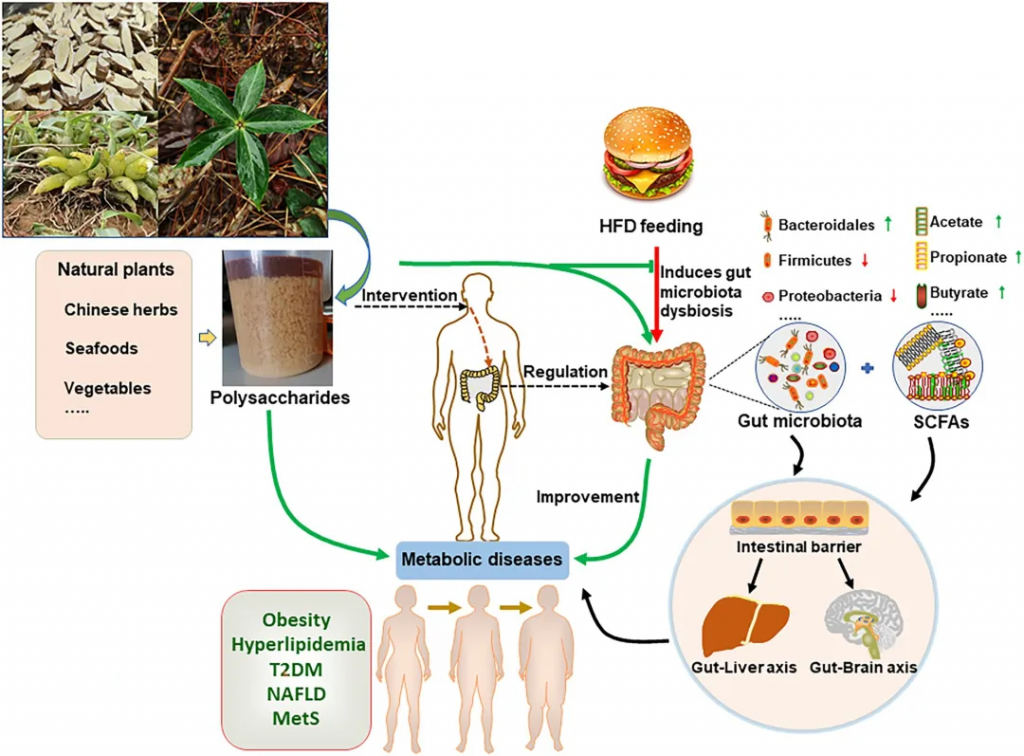
doi.org/10.3389/fmicb.2022.859206
高脂血症是指脂质代谢紊乱,其特征是甘油三酯 (TG)、总胆固醇 (TC) 和低密度脂蛋白浓度升高,同时高密度脂蛋白水平降低。
◤果胶多糖(高支链 RG-I,531.5 kDa)显著改善了 HFD 引起的脂质代谢异常,TG、TC、LDL-C 和游离脂肪酸水平降低。它还通过增加Roseburia、Clostridium等产生 SCFA 的细菌的数量来恢复肠道菌群失衡。
◤裙带菜多糖 ( Undaria pinnatifida )修复了高脂饮食引起的肠道微生物群改变,特别是Prevotellaceae_UCG-001,发现这与脂质代谢紊乱有关。
◤鲍鱼性腺多糖显著增加了丁酸水平,丁酸是一种重要的短链脂肪酸,它通过GPR依赖性途径抑制脂质相关基因的表达。
◤龙须菜多糖调节拟杆菌、瘤胃球菌_1和乳酸杆菌的相对丰度来增强胆固醇向BAs的转化。在遗传水平上,有人认为BA代谢的调节主要涉及CYP39A1和CYP7B1。
炎症性肠病 (IBD) 包括溃疡性结肠炎 (UC) 和克罗恩病 (CD),其特点是胃肠道持续炎症。IBD 的症状包括腹泻、腹胀、腹痛、便血、体重减轻和不适。
◤银耳多糖(TPs)通过多途径调节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改善了DSS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TPs可以增加Lactobacillus的丰度,从而改善色氨酸的分解代谢。这导致黄嘌呤酸、KA和吲哚衍生物(如5-羟吲哚、5-羟吲哚-3-乙酸、5-羟吲哚乙酰酸)的增加。
TPs还可以增加Romboutsia的水平,促进DCA的产生。因此,TPs可以通过影响色氨酸代谢和胆汁酸代谢来保护小鼠免受结肠炎的侵害。
◤金针菇多糖已被证明可以通过控制结肠微生物失调、增加短链脂肪酸和抑制 TLR4-NF-κB 信号通路来缓解结肠炎。能促进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恢复肠道稳态,缓解IBD症状。
◤竹荪多糖由59.84%的葡萄糖、23.55%的甘露糖和12.95%的半乳糖组成,已被证明可以通过增加粘蛋白和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抑制有害细菌(如γ-变形菌、变形菌、拟杆菌科、拟杆菌科和肠杆菌科)并增强有益细菌(如嗜酸乳杆菌)来改善肠道菌群组成和肠道屏障功能。
◤坛紫菜多糖通过上调紧密连接蛋白,增加粘液层及其分泌,调节肠道微生物群落,富集有益细菌,如拟杆菌、Muribaculum和乳酸杆菌,从而减轻DSS诱导的结肠损伤,从而改善结肠粘膜屏障的完整性。
◤白术多糖可以缓解在DSS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小鼠模型炎症。白术多糖可以增加Butybacterium、Lactobacillus,同时减少Actinomyces、Akkermansia、Faecalibaculum、Verrucomicrobia、Bifidobacterium等。
肠道菌群的变化逆转了DSS引起的短链脂肪酸的减少以及色氨酸和色氨酸相关代谢物5-羟基-N-甲酰基犬尿氨酸和吲哚-3-乙酸的减少。白术多糖还剂量依赖性地逆转了LCA、DCA、缬氨酸、亮氨酸等的异常变化。
天然植物多糖治疗IBD的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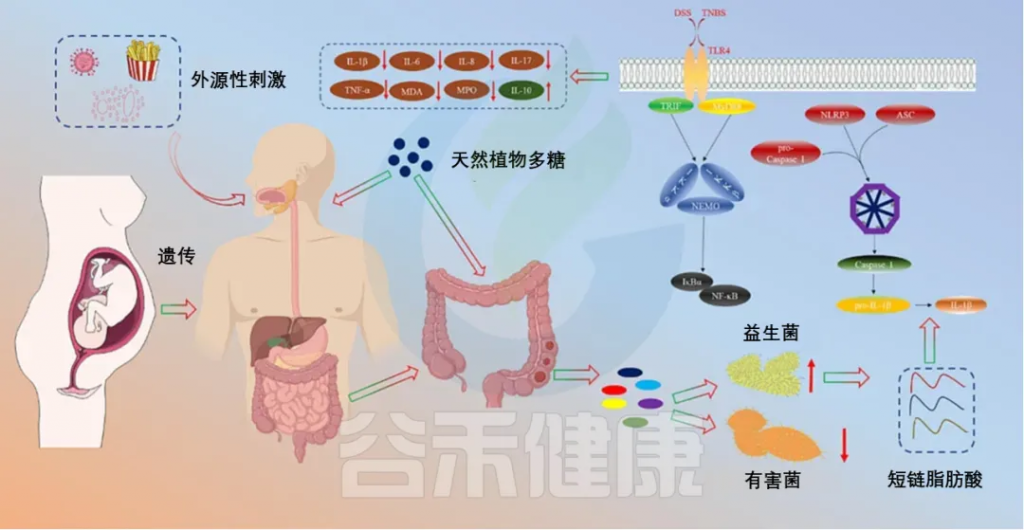
doi.org/10.1016/j.ijbiomac.2023.126799
◤甘草多糖GPS上调乳杆菌科、S24–7、Turicibacteraceae、Verrucomicrobiaceae和双歧杆菌科的丰度,下调脱硫弧菌科、瘤胃球菌科、毛螺菌科、肠杆菌科、丹毒丝菌科的丰度。GPS能促进乳杆菌、拟杆菌和产SCFAs菌的生长繁殖,起到减轻炎症、升高IL-10水平、抑制TLR4活化、降低血浆LPS水平的作用,从而保护肠道免受LPS诱导的炎症。
◤何首乌多糖(TSG)的给药显著增加了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的相对丰度,同时也降低了幽门螺杆菌和拟杆菌门的属水平,改善了肠道菌群,起到治疗IBD的作用。


doi.org/10.3390/nu15153321
◤乳果糖通过重塑肠道菌群组成和代谢物,改善了由洛哌丁胺引起的便秘小鼠模型中的肠道水和盐代谢。具体来说,乳果糖上调了Bacteroides的丰度,并显著降低了厚壁菌门和Verrucomicrobia的水平。
此外,乳果糖减少了胆汁酸(包括CA、DCA等)、粪便中高浓度的吲哚(高浓度吲哚对细胞有毒)并增加了丙酸。
◤西洋参多糖(WQP) 可增强大鼠肠道结构的恢复,降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改善短链脂肪酸 (SCFA) 水平,促进肠道菌群和肠黏膜屏障的恢复,并减轻盐酸林可霉素引起的腹泻和菌群失调等抗生素相关副作用。
◤葛根多糖( PPL )可缓解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引起的结肠病理改变和肠道菌群失调。
◤紫菜中提取的多糖(Nemacystus decipiens)能显著缓解小鼠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AD)的症状,并且显著增加了 Muribaculum、Lactobacillus 和 Bifidobacterium 的丰度,降低Enterobacter 、Clostridioides 的丰度。
◤茯苓多糖(PCP)通过恢复7种肠道菌菌缓解了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小鼠的症状,包括:Parabacteroides distasonis、Akkermansia muciniphila、Clostridium saccharolyticum、Ruminococcus gnavus、Lactobacillus salivarius、Salmonella enterica、Mucispirillum schaedleri.
适当调节免疫反应可以降低炎症反应引起的病原体入侵的风险。
结直肠癌
◤灵芝多糖在缓解结直肠癌症状方面比瓜尔胶更有效,因为它们能增加Akkermansia、结肠长度,并下调直肠癌相关基因。灵芝多糖通过动态调节肠道菌群和宿主免疫反应,已证明具有预防和治疗癌症的功能。
灵芝多糖通过调节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的相对丰度,诱导SCFAs的产生,改善肠道屏障损伤,抑制TLR4/MyD88/NF-κB信号通路,从而降低结肠炎和致癌风险。
◤绞股蓝与灵芝多糖联合使用显著提高了SCFAs产生菌的丰度,提高了丁酸和异丁酸水平,抑制了硫酸盐还原菌的丰度。
乳腺癌
◤来自灵芝破壁孢子(分子量为 3659 Da)的多糖可作为乳腺癌治疗的天然佐剂,增加细胞毒性 T 细胞和辅助性 T 细胞的数量。
灵芝孢子提取物(ESG)重塑了4T1荷瘤小鼠的肠道菌群:厚壁菌门和变形菌门的相对丰度增加,放线菌、拟杆菌门和蓝藻的相对丰度降低。
◤灵芝多糖联合紫杉醇对4T1乳腺荷瘤小鼠有抗肿瘤作用。联合治疗能显著富集拟杆菌、瘤胃球菌等5个菌属,降低脱硫弧菌和Odoribacter的丰度,平衡肠道菌群,抑制肿瘤代谢。
疲劳是一种普遍的不适感,表现为极度疲倦和力竭,通常在生理、病理或心理失衡时出现。体力劳动、心理压力、高原缺氧和长期疾病都可能引发疲劳。疲劳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还可能导致内分泌、免疫、代谢等系统功能受损,甚至与癌症、糖尿病等严重疾病相关。此外,疲劳还与焦虑、抑郁和神经系统疾病有关。
近年来,天然多糖因其在缓解运动性疲劳中的潜在效果和较少的副作用而受到关注。研究表明,肌肉功能与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组成密切相关,而天然多糖如决明子、灵芝、枸杞和冬虫夏草等可通过不同机制发挥抗疲劳作用。

doi.org/10.3390/foods12163083
多糖抗疲劳机制如下:
抗疲劳多糖干预后肠道菌群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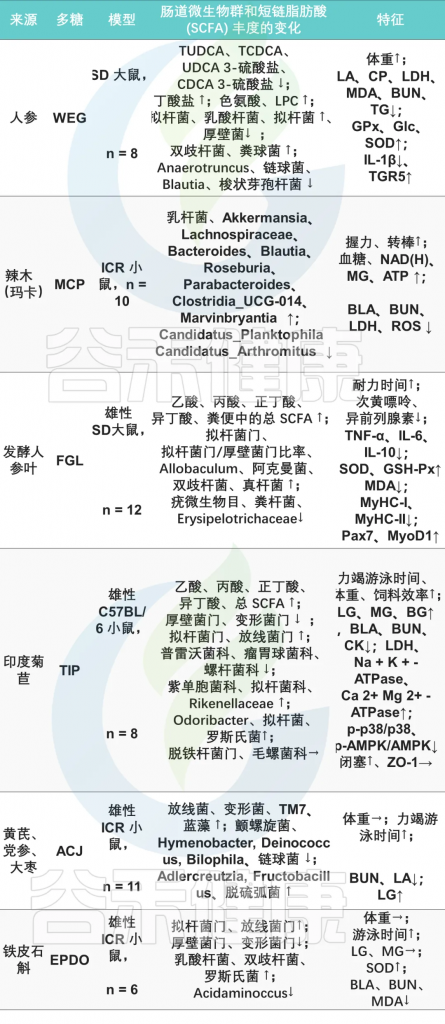
doi.org/10.3390/foods12163083
肠道-肌肉轴是肌肉与消化道之间的双向沟通,微生物可以通过微生物-肠道-肌肉轴作用于全身的肌肉。肠道微生物在膳食多糖的作用下,产生一些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等),有些代谢产物会直接穿过肠道上皮细胞,通过血液循环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肌肉组织和细胞,引起细胞发生生理生化反应,对疲劳产生一定的影响。
补充膳食多糖通过作用于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间接激活AMPK/PGC-1α、PI3K/AKT、NF-κB、Nrf2/Keap1信号通路,调节能量代谢,降低炎症水平,增强线粒体功能和抗氧化能力,进一步维持肌肉质量和功能,从而缓解疲劳。
扩展阅读:
◤银杏叶中的一种水溶性多糖(GPS)可减轻压力引起的抑郁症并逆转肠道菌群失调。GPS 治疗可以缓解压力引起的血清素阳性和多巴胺阳性细胞密度降低。GPS 逆转了与抑郁相关的肠道菌群失调,并增加了乳杆菌的丰度,而乳杆菌已被证明是缓解抑郁的途径。
◤从秋葵中提取的多糖,发现它对抑郁小鼠的肠道菌群有明显的恢复作用,表现为厚壁菌门比例上调,拟杆菌门和放线菌门相对比例下调。这种调节有助于强化肠黏膜屏障,维持肠道免疫系统正常功能,减少肠道炎症反应,对抗抑郁有效,抑郁症小鼠的抑郁症状有所改善。用秋葵多糖治疗的小鼠体内的SCFAs显著增加,而SCFAs作为重要的通讯介质,对抗抑郁障碍有积极的影响。
◤接受金针菇多糖 (FVP)治疗的小鼠的肠道微生物组成发生显著改变,放线菌、丹毒菌和拟杆菌的丰度增加,梭菌的丰度降低,并且接受FVP治疗的小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得到改善。
◤肉苁蓉多糖可以通过恢复小鼠模型中D-半乳糖诱导的衰老引起的肠道菌群稳态来抑制氧化应激和外周炎症,从而改善小鼠的认知功能。
◤从黄芪中提取的一种多糖已被证明可以通过改变糖尿病小鼠的肠道菌群来改善认知障碍。
扩展阅读:
以下是关于一些多糖的详细介绍,包括其功效,与肠道菌群的关联等,更深入地了解多糖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
路易波士茶是什么?
路易波士茶(Rooibos)又名Aspalathus linearis,中文也有译作“路易博士茶”,取自原产于南非的一种豆科植物的茎叶。虽然带有一个茶字,但路易波士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茶叶。
路易波士茶因不含咖啡因、单宁含量低而受到南非人的喜爱,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业化种植和销售。2014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路易波士茶作为新的食品原料,丰富了中国的食品和药物资源。
路易波士茶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抗过敏、解痉和降血糖作用。也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各种癌症、骨质疏松症等。
路易波士茶多糖
一项研究从路易波士茶中分离得到均一酸性多糖(ALPs) ,水溶性多糖ALP由β-糖苷键连接,含有吡喃糖环,主要由岩藻糖、鼠李糖、阿拉伯糖和半乳糖组成。
结合RT-PCR结果推测,ALP可能通过降低Cyp2e1和Keap1的mRNA表达,增加Nrf2和HO-1的mRNA表达,激活Cyp2e1/Keap1-Nrf2-HO-1信号通路,调控下游抗氧化酶活性和炎症因子表达,减轻氧化应激损伤和炎症反应造成的损伤,从而改善急性酒精性肝损伤。
路易波士茶多糖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多样性
急性酒精性肝病模型对照组(MC)的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显著降低(p≤0.05)。高剂量和低剂量ALP处理组的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有所增加,其中高剂量组的增加更为显著。
干预后改善的菌群
ALP 干预后疣微菌丰度显著升高(p≤0.01),而脱硫杆菌丰度及F / B值均降低,但差异不显著。
肠道菌群中乳酸杆菌科的丰度与肝脏 AST 和 ALT 水平呈负相关。小鼠ALP干预后,乳酸杆菌科的丰度显著增加(p ≤ 0.05),而Rikenellaceae的丰度显著降低(p ≤ 0.05)。
ALP 显著改善了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中Alloprevotella和Alistipes丰度显著降低的情况( p ≤ 0.05)。
“肠-肝轴”途径
对属级别排名前20位的菌种进行了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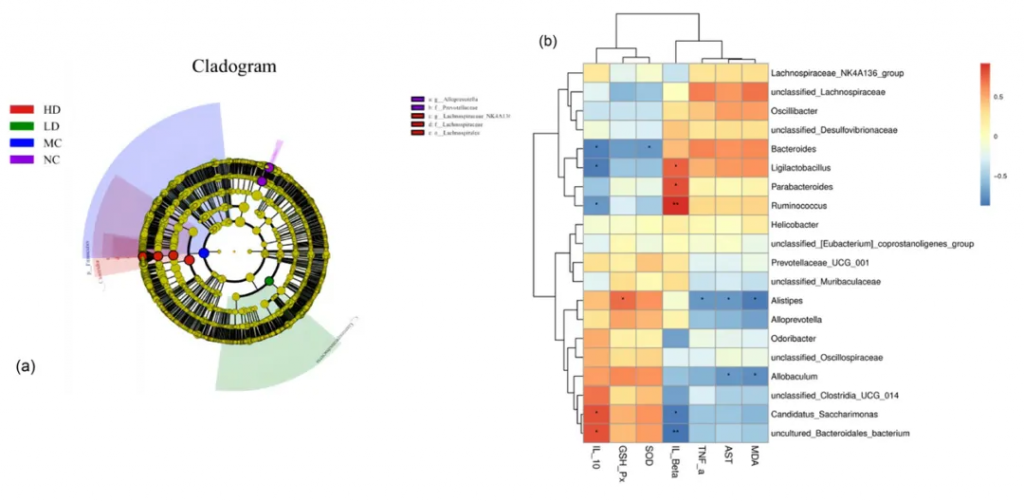
推测ALP可能通过“肠-肝轴”通路促进肠道菌群与抗氧化酶及炎症因子相互作用,从而减轻酒精性肝损伤,而上述菌群与酒精损伤标志物、抗氧化酶及炎症因子的表达均密切相关。
酒精及其代谢产物会影响肠道菌群的平衡和组成,导致肠道功能受损。这反过来又会影响肝脏健康,而肝脏健康与肠道菌群稳态密切相关。肠道和肝脏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称为“肠-肝轴”通路。
地黄是玄参科地黄属植物,在我国拥有久远的药用历史,作为滋阴补肾的传统中药,也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
多糖是地黄中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地黄多糖具有免疫调节、抗肿瘤、抗氧化、抗衰老等多种生物活性。
迄今为止,从地黄中分离纯化了20多种多糖,主要由阿拉伯糖、鼠李糖、半乳糖、葡萄糖、甘露糖、木糖、岩藻糖和半乳糖酸组成。
地黄多糖能增加DSS诱发小鼠的体质量指数和结肠长度、降低DAI评分,改善组织病理学损伤。同时,地黄多糖能阻断NF-κB信号通路,降低细胞内促炎因子表达,减轻炎症,增加紧密连接蛋白表达,维持肠道上皮屏障。
地黄多糖可能在肠道微生物作用下发酵转化为SCFAs,增加肠道中乙酸、丙酸和丁酸的含量,起到缓解IBD的作用。
拟杆菌属、乳酸杆菌属、Alistipes是导致DSS结肠炎组肠道微生物组失衡的关键细菌类型,而补充地黄多糖可以逆转这种有害变化。
五指毛桃,又叫粗叶榕(Ficus hirta Vahl),常被用作滋补品的草药成分,以其丰富的多糖含量和生物活性而闻名。
一项研究发现,FHVP-3 对肠道微生物群产生影响:
下列菌群富集:
FHVP-3 抑制了下列机会性致病菌属的丰度:
作为可发酵底物,FHVP-3 还增加了短链脂肪酸的浓度,包括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FHVP-3 对脂多糖 (LPS) 诱导的 RAW 264.7 巨噬细胞表现出显着的抗氧化活性和显着的抗炎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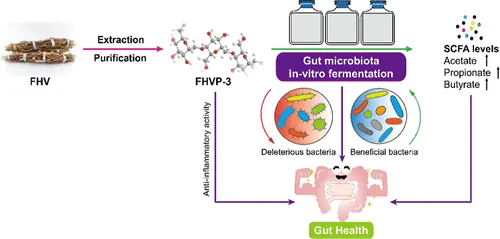
doi.org/10.1021/acsfoodscitech.3c00626
大蒜多糖 (GP) 占大蒜干重的 75% 以上。它们的特征是具有 2,1- β – d -Fruf 主链和 2,6- β – d -Fruf 分支的果聚糖。
研究表明,大蒜多糖在调节肠道微生物群方面发挥着作用,但它们是否具有维持肠道健康的全面功能并可作为有效的益生元仍不清楚。
为了探索这一点,通过管饲法给昆明小鼠施用不同剂量的大蒜多糖(1.25-5.0g/kg 体重)和菊粉(作为阳性对照),并评估它们对肠道上皮、化学和生物屏障的影响。还使用洛哌丁胺建立了便秘模型,以研究大蒜多糖对缓解便秘的潜在影响。
施用大蒜多糖显著上调昆明小鼠小肠组织中紧密连接蛋白和粘蛋白的表达。大蒜多糖提高了盲肠丁酸含量,降低了脱硫杆菌的丰度,并降低了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的比例(F/B)。大蒜多糖还促进了 Bacteroides acidifaciens、Clostridium saccharogumia的生长。
Tax4Fun 功能预测表明,大蒜多糖具有预防人类疾病的潜力,可降低胰岛素抵抗、传染病和耐药性的风险。
大蒜多糖还通过增强小肠转运、软化粪便稠度、加速排便和促进兴奋性神经递质的释放,在缓解洛哌丁胺引起的便秘症状方面表现出有益作用。
多年来,槐耳 (Trametes robiniophila Murr) 一直被用于药物治疗。槐耳含有多种成分,包括多糖、蛋白质、酮和生物碱,其中蛋白聚糖和多糖是主要的生物活性成分。
槐耳提取物具有免疫调节活性,并可通过激活自噬、抑制铁死亡、抑制内质网应激等过程对细胞发挥保护作用。研究表明,槐耳水提取物可通过抑制NLRP3炎症囊泡活化,减轻肠道屏障损伤和炎症反应,并抑制DSS和氧化偶氮甲烷 (AOM) 联合诱导的结肠肿瘤形成。
可缓解 DSS 引起的肠道菌群紊乱
一项小鼠研究显示,槐耳多糖干预显著逆转了 DSS 引起的Muribaculaceae_unclassified、Anaerotruncus、Ruminococcaceae_unclassified丰度的下降以及Escherichia-Shigella丰度的增加( p < 0.05)。
其中,Muribaculaceae_unclassified是健康人中发现的肠道微生物,参与丁酸代谢和色氨酸代谢,可产生对人体有益的短链脂肪酸。
相关性分析,Muribaculaceae_unclassified与结肠长度、SOD 和 T-AOC 呈正相关,而与 DAI 评分以及炎症和氧化指标呈负相关。
Anaerotruncus与结肠长度、SOD 和 T-AOC 呈正相关,但与炎症标志物 LPS、MDA 和 MPO 呈负相关。
黄芩的根通常用作药物,用于清热利湿、泻火解毒。多糖是黄芩的最重要成分之一。
一种来自黄芩的多糖通过抑制 NF-κB 信号传导和NLRP3 炎症小体活化来改善溃疡性结肠炎。在多糖的分离和纯化过程中,研究人员还获得了另一种名为 SP2-1 的均质多糖。SP2-1由甘露糖、核糖、鼠李糖、葡萄糖醛酸、葡萄糖、木糖、阿拉伯糖和岩藻糖组成。
研究人员发现其对肠道菌群紊乱、肠道屏障改善以及短链脂肪酸产生影响。
在UC患者中,SP2-1显著抑制了促炎性细胞因子IL-6,IL-1β和TNF-α。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屏障完整性被破坏,TJ 蛋白的表达发生改变,SP2-1增加小鼠TJ蛋白的表达,修复肠道屏障。
SP2-1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SP2-1组的粪便微生物群多样性明显高于DSS组。
临床上,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丰度降低。与模型组相比,SP2-1 组的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和Roseburia的水平提高。
而拟杆菌和葡萄球菌的种群受到抑制。肠道菌群中存在过量的拟杆菌和葡萄球菌对肠道免疫系统有害。
Roseburia 通过调节调节性 T 细胞的发育和分化、增加抗炎细胞因子的分泌和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来缓解UC。
枸杞多糖(简称LBPs)是从枸杞中提取的一类多糖物质。枸杞是一种多年生灌木,属于茄科,枸杞多糖因其多样的药理活性和生理功能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枸杞多糖 (LBPs)作为最重要的生物活性分子,可通过肠道微生物参与有益作用,包括调节代谢、降血糖、神经保护、抗衰老、保护各种器官免受氧化应激相关疾病的侵害。
枸杞多糖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癌症
一般来说,抗癌化疗药物除了会诱导癌细胞凋亡外,还会对肠道菌群产生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肠绒毛缩短,乳酸杆菌和肠球菌丰度下降,节段丝状菌丰度增加。而枸杞多糖治疗可通过增加有益菌相对丰度来改善肠道环境和免疫功能,逆转环磷酰胺引起的有害菌(瘤胃拟杆菌科、Longibraceae、脱硫弧菌和厌氧拟杆菌科)相对丰度的增加。
还发现毛螺菌科、瘤胃菌科、脱铁菌科、脱硫弧菌科、Aneoplasmataceae与细胞因子IL-2、IL-6、IL-1β、TNF-α、IFN呈负相关。因此,主要肠道菌群的相对丰度可能与免疫调节有关。
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F/B)比例的变化与许多疾病状态有关,它被视为菌群失调的重要指标,有助于了解肝脏和代谢疾病的发展。枸杞多糖可降低高脂饮食大鼠的 F/B 比,表明补充枸杞多糖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失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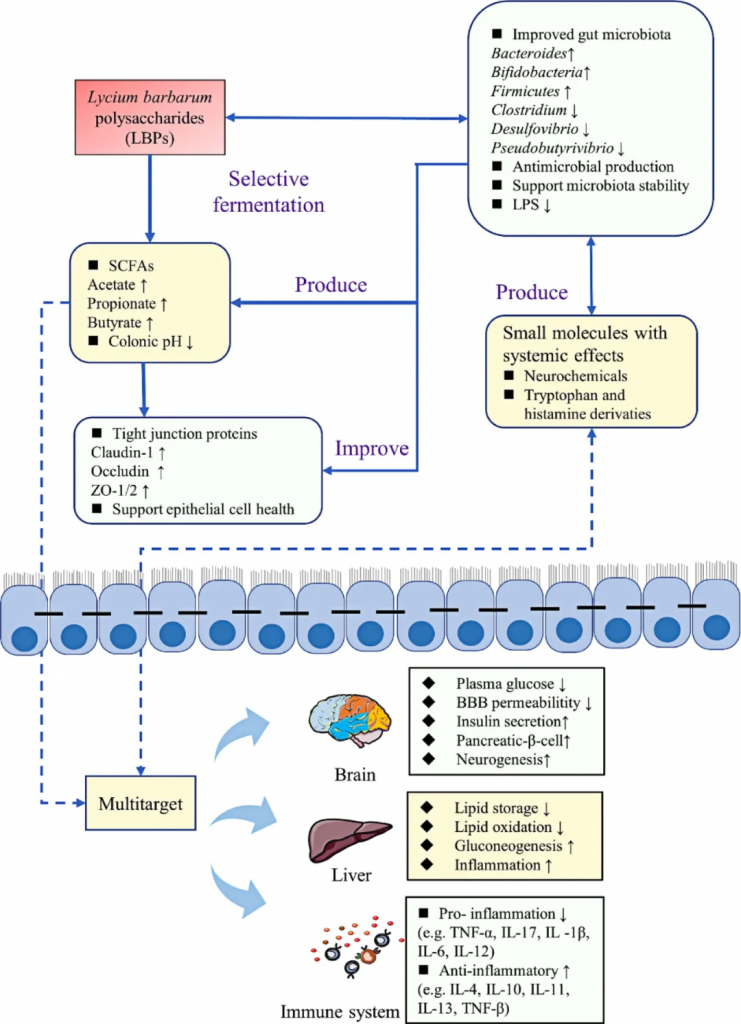
doi.org/10.1080/10408398.2022.2128037
神经系统
枸杞多糖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肠-脑轴的神经免疫通路,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多方面的保护作用。枸杞多糖可改善菌群失调、肠道屏障受损等问题,并通过抑制细胞凋亡、促进自噬等机制发挥神经保护效应。
肝脏
枸杞多糖能够影响NAFLD患者的肠道菌群组成、肠道屏障及肝脏炎症。
代谢(肥胖、糖尿病)
肥胖个体的研究中,肠道内F/B比例较高,因此推测肠道内F/B比例与肥胖呈显著正相关。
后续研究发现,LBPs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组成和短链脂肪酸生成来改善肥胖。
枸杞多糖可作为2型糖尿病的潜在辅助药物。
LBPs能调节肠道菌群,激活大鼠肠黏膜TLR2+上皮细胞γδT细胞,增强肠道屏障功能,改善糖尿病。此外,LBPs能明显降低血浆中促炎性细胞因子IL-1β、IL-6、IL-17A和TNF-α,而抗炎性细胞因子IL-10水平在糖尿病大鼠中有所升高。
哮喘
枸杞多糖还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改变肠道菌群,参与炎症介质的调控,从而改善肺功能和过敏性哮喘症状。
肠道菌群测序分析显示,LBPs能够促进哮喘小鼠肠道中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增加,并降低厚壁菌门和放线菌水平,通过肠道介导缓解哮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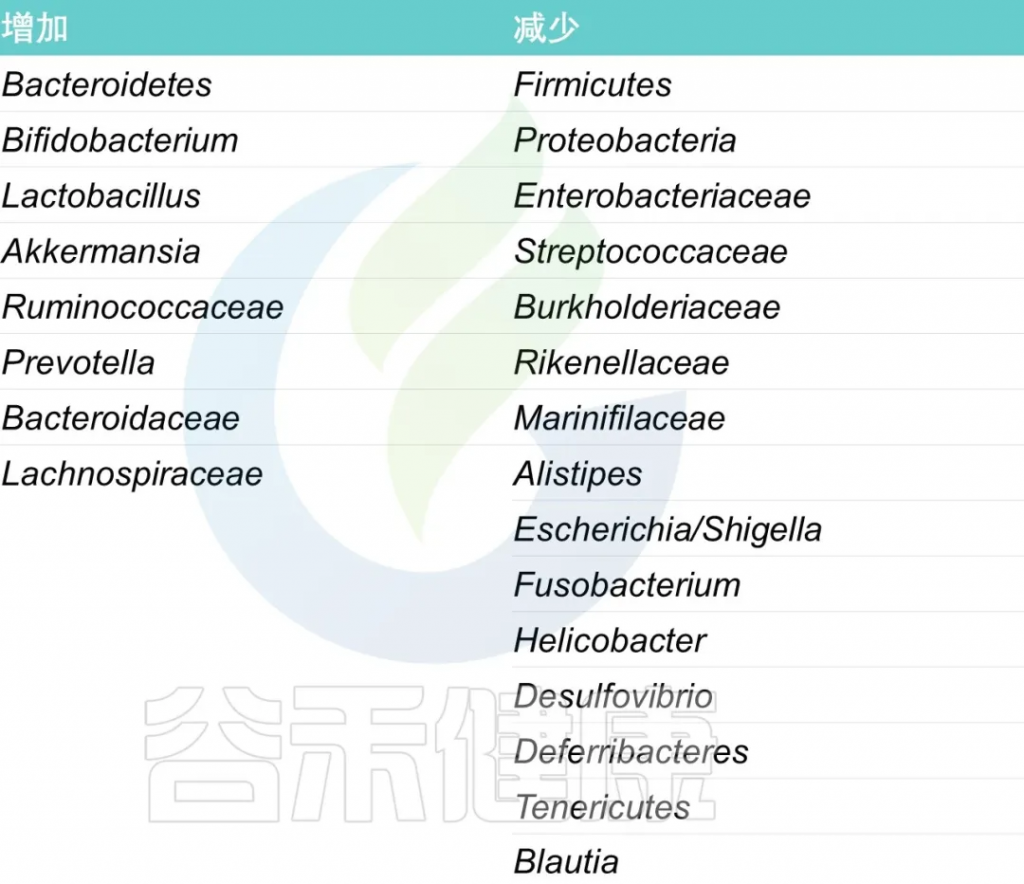
岩藻糖(Fucose),参与构成肠上皮细胞(IEC)顶端表达的聚糖,并介导肠道中的许多生物过程,尤其是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
释放的岩藻糖可被微生物用作膳食聚糖、能量来源或合成结构蛋白。肠道中岩藻糖的变化影响微生物群的定植。
岩藻多糖
岩藻多糖是一种含有岩藻糖和硫酸基团的多糖,可改善糖尿病肾病。
一项小鼠研究发现,岩藻多糖可显著改善肾小球滤过率高滤过和肾纤维化,其机制与短链脂肪酸产生菌富集、增加盲肠内乙酸浓度、提高肾脏ATP水平以及改善线粒体功能障碍有关。此外,岩藻多糖还可通过抑制MAPKs通路来改善肾脏炎症和纤维化。总之,岩藻多糖可通过改善线粒体氧化应激和抑制MAPKs通路,靶向肠道菌群-线粒体轴,改善早期糖尿病肾病。
桑叶的药用功能最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被发现,并记载于《神农本草经》。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桑叶的药用功效有更详细的描述,包括活血化瘀、祛风、清热解毒等功能。桑叶已被列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食药同源资源名单。
桑叶多糖(Mulberry Leaves Polysaccharides,MLPs)是从桑树(Morus alba L.)叶片中提取的一种植物多糖。它们是桑叶中主要的活性成分之一,由多种单糖组成,主要包括木糖、阿拉伯糖、果糖、半乳糖、葡萄糖、甘露糖等。
桑叶多糖对人体的影响
桑叶多糖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包括降低血糖、抗氧化、免疫调节、抗肿瘤、抗菌、抗凝和调节肠道菌群等。这些活性使得MLPs在医药和食品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并且安全、有效、低毒、副作用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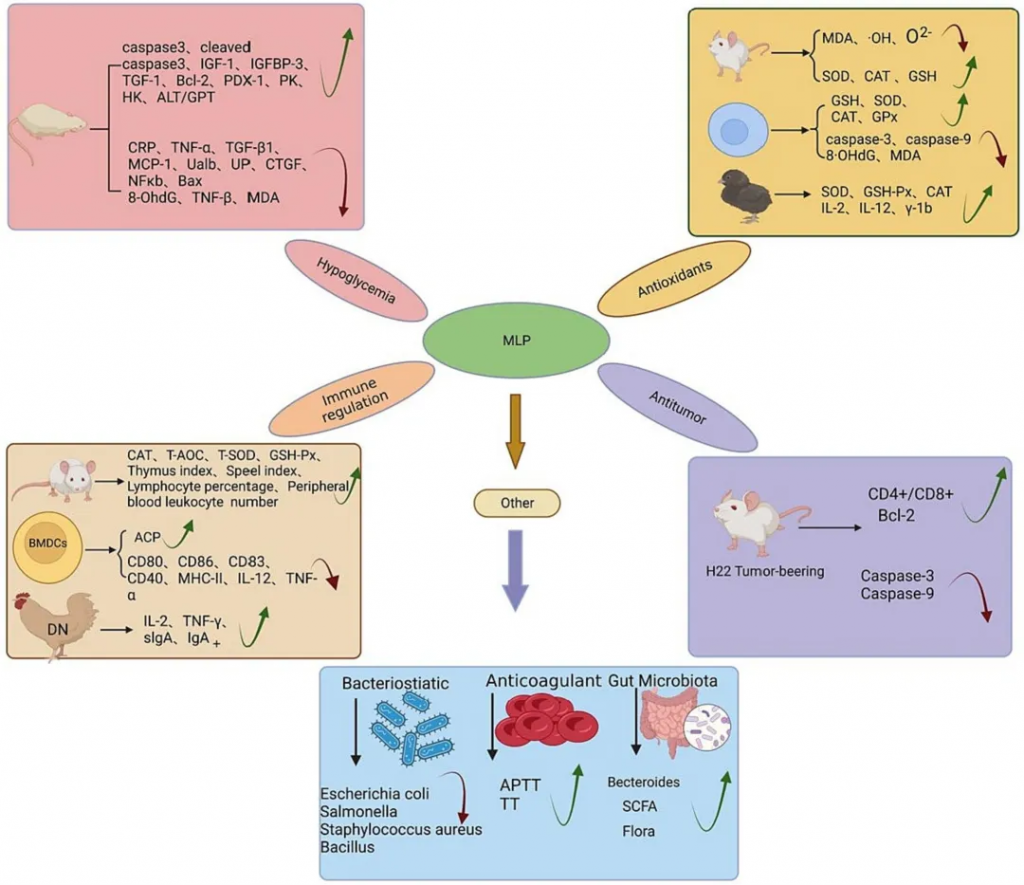
doi.org/10.1016/j.ijbiomac.2023.128669
桑叶多糖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桑叶多糖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进而对人体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以下是桑叶多糖影响的肠道菌群及其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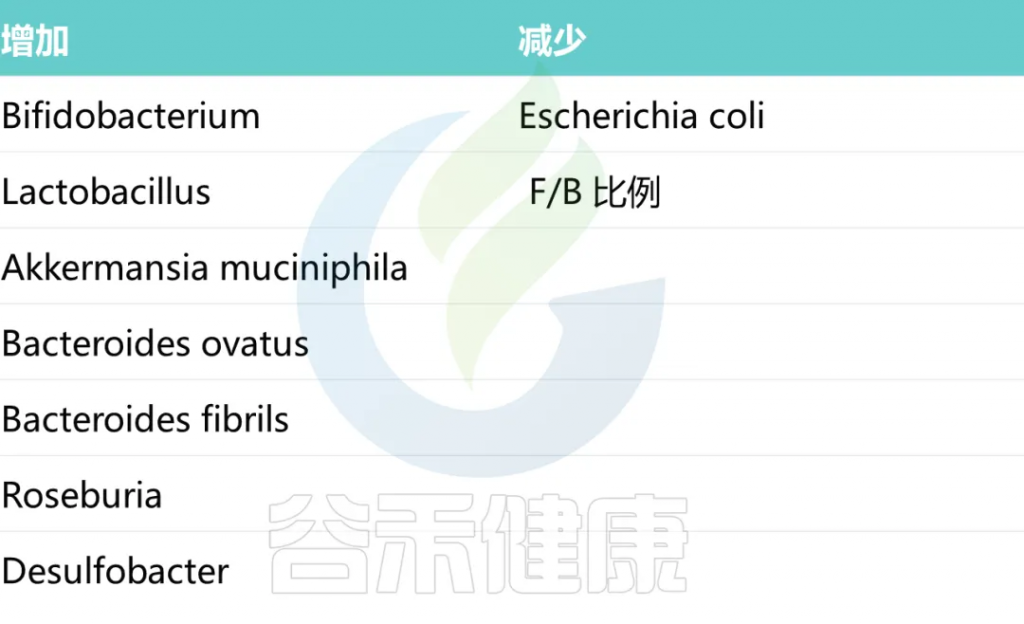
桑叶多糖能够调节短链脂肪酸和肠道菌群的相对丰度,降低真细菌与过敏性细菌的比例,从而改善肠道屏障功能。
沙棘果实在藏族食品和药物中已有数千年的传统。沙棘多糖 (SP) 是沙棘果实中的主要功能成分之一。
对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沙棘多糖治疗提高了 p-AMPKα 和 PPARα 蛋白的表达,刺激了小鼠肝脏中 ACC1 的磷酸化,并抑制了 FAS、PPARγ 和 CD36 的蛋白表达。
沙棘多糖上调Muribaculaceae_unclassified、双歧杆菌、Rikenellaceae_RC9_gut_group、Alistipes、Bacteroides的比例,并下调Lactobacillus、 Firmicutes_unclassified 、Dubosiella Bilophila、 Streptococcus 的比例,重组了HFD诱导的肥胖小鼠的肠道微生物群。
此外,粪便中的微生物代谢物短链脂肪酸 (SCFAs) 的产生也有所增加。此外,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沙棘多糖的肥胖改善作用与粪便中的SCFAs水平高度相关。因此,沙棘多糖对肝脏脂质代谢的调节可能是由于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和SCFAs产生量的增加。这些结果表明,沙棘多糖可以通过调节肠-肝轴发挥改善肥胖的潜在营养保健作用。
蘑菇多糖是一类存在于蘑菇中的生物活性多糖,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几丁质、甘露聚糖、半乳糖聚糖、木聚糖、葡聚糖、云芝多糖、灵芝多糖、半纤维素。这些多糖在蘑菇细胞壁中含量丰富,赋予蘑菇独特的结构和生物活性。
蘑菇多糖的功效
蘑菇多糖对人体具有多种潜在的健康益处。它们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具有抗肿瘤活性、调节肠道菌群、抗氧化、抗糖尿病、抗衰老作用。
蘑菇多糖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促进益生菌生长
蘑菇多糖通过选择性地促进益生菌的生长,增强肠道健康。例如,灵芝和茯苓中的多糖被发现可以增加有益细菌的数量,这些细菌可以对抗肥胖、产生短链脂肪酸和乳酸。香菇中的多糖也显示出对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有促进作用。
抑制病原菌
蘑菇多糖能够通过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和促进益生菌的生长来间接抑制病原菌。双孢蘑菇中的多糖已被证明可以限制大肠杆菌的生长。
增强肠道屏障功能
蘑菇多糖通过增强肠道上皮细胞的功能,提高肠道屏障的完整性,减少有害物质的渗透。云芝(Trametes versicolor)中的多糖肽PSK和PSP能够调节肠道菌群,增加有益菌双歧杆菌和乳杆菌的数量,同时减少有害菌如梭状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在降低腹泻、艰难梭菌感染、炎症性肠病等方面发挥作用。
调节免疫反应
蘑菇多糖通过激活肠道相关淋巴组织,增强机体的免疫反应。灵芝多糖能刺激和增加免疫细胞如自然杀伤细胞、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数量。
产生短链脂肪酸
蘑菇多糖在肠道发酵过程中产生短链脂肪酸,这些物质对维持肠道健康和调节宿主代谢具有重要作用。蚝菇(Pleurotus ostreatus)中的β-葡聚糖衍生物能够诱导前列腺癌细胞的凋亡,并且显示出免疫调节、巨噬细胞激活、抗肿瘤和免疫刺激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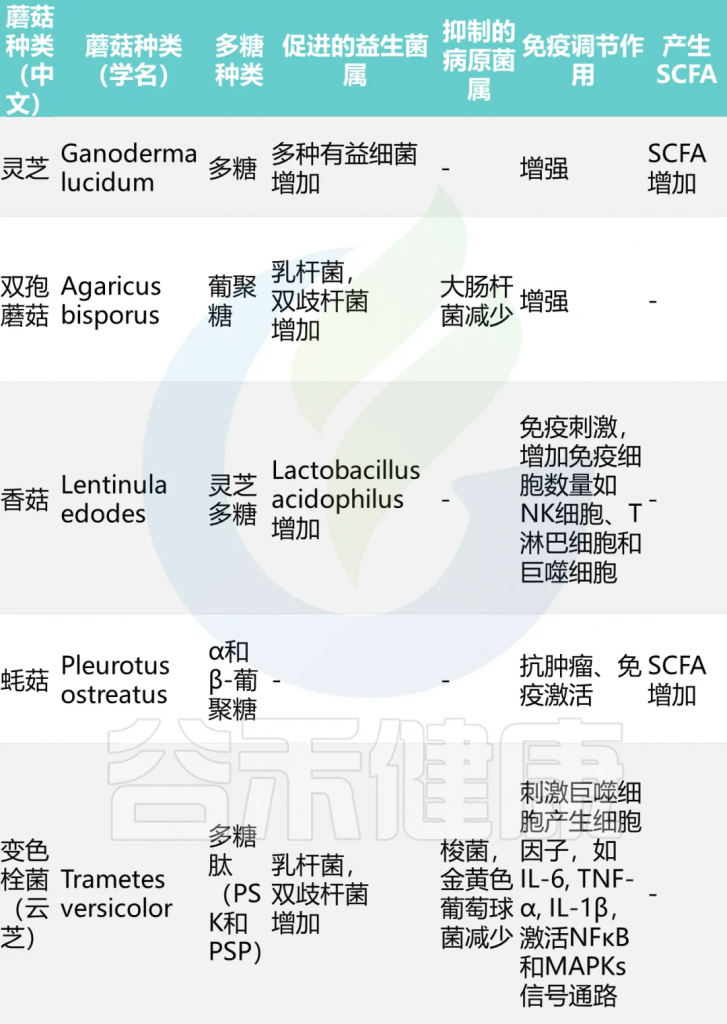
多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其在人体内的作用千变万化,它们能够通过与肠道菌群的互动,从调节免疫功能到改善代谢性疾病等。
然而,利用天然多糖通过肠道菌群治疗疾病仍存在一些限制和挑战。对肠道菌群和多糖之间相互作用的全面了解需要进一步研究,由于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因此开展研究多糖-微生物组-疾病相互作用的临床试验并实现临床转化至关重要。
幸运的是,随着生命科学领域新兴技术的发展,我们有了更多的工具来揭示这些复杂问题。高通量测序技术、多组学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的交叉融合,为研究多糖和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快速发展。
此外,多糖与肠道菌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揭示了多糖的生物活性,也突显了肠道菌群对健康的重要贡献。多糖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了解个体的肠道菌群组成,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更为个性化的营养和健康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肠道菌群检测可以揭示个体对多糖等营养成分的响应差异,从而为制定个性化的饮食和治疗计划提供指导。
注:本账号内容仅作交流参考,不作为诊断及医疗依据。
主要参考文献
Xue H, Mei CF, Wang FY, Tang XD. Relationship among Chinese herb polysaccharide (CHP), gut microbiota, and chronic diarrhea and impact of CHP on chronic diarrhea. Food Sci Nutr. 2023 Aug 6;11(10):5837-5855.
Xu X, Wang L, Zhang K, Zhang Y, Fan G. Managing metabolic diseases: The roles and therapeutic prospects of herb-derived polysaccharides. Biomed Pharmacother. 2023 May;161:114538
Zhang D, Liu J, Cheng H, Wang H, Tan Y, Feng W, Peng C. Interactions between polysaccharides and gut microbiota: A metabolomic and microbial review. Food Res Int. 2022 Oct;160:111653.
Chen R, Zhou X, Deng Q, Yang M, Li S, Zhang Q, Sun Y, Chen H. Extraction,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and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mulberry leaves: A review. Int J Biol Macromol. 2024 Feb;257(Pt 2):128669.
Lan Y, Sun Q, Ma Z, Peng J, Zhang M, Wang C, Zhang X, Yan X, Chang L, Hou X, Qiao R, Mulati A, Zhou Y, Zhang Q, Liu Z, Liu X. Seabuckthorn polysaccharide ameliorates high-fat diet-induced obesity by gut microbiota-SCFAs-liver axis. Food Funct. 2022 Mar 7;13(5):2925-2937.
Feng Y, Song Y, Zhou J, Duan Y, Kong T, Ma H, Zhang H. Recent progress of Lycium barbarum polysaccharides on intestinal microbiota, microbial metabolites and health: a review. Crit Rev Food Sci Nutr. 2024;64(10):2917-2940.
Cui L, Guan X, Ding W, Luo Y, Wang W, Bu W, Song J, Tan X, Sun E, Ning Q, Liu G, Jia X, Feng L.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polysaccharide ameliorates DSS-induced ulcerative colitis by improving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and modulating gut microbiota. Int J Biol Macromol. 2021 Jan 1;166:1035-1045.
Tang YF, Xie WY, Wu HY, Guo HX, Wei FH, Ren WZ, Gao W, Yuan B. Huaier Polysaccharide Alleviates Dextran Sulphate Sodium Salt-Induced Colitis by Inhibiting Inflammat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Maintaining the Intestinal Barrier, and Modulating Gut Microbiota. Nutrients. 2024 Apr 30;16(9):1368.
Zhao Q, Jiang Y, Zhao Q, Patrick Manzi H, Su L, Liu D, Huang X, Long D, Tang Z, Zhang Y. The benefits of edible mushroom polysaccharides for health and their influence on gut microbiota: a review. Front Nutr. 2023 Jul 6;10:1213010.
Álvarez-Mercado AI, Plaza-Diaz J. Dietary Polysaccharides as Modulators of the Gut Microbiota Ecosystem: An Update on Their Impact on Health. Nutrients. 2022 Oct 3;14(19):4116.
Tang M, Cheng L, Liu Y, Wu Z, Zhang X, Luo S. Plant Polysaccharides Modulate Immune Function via the Gut Microbiome and May Have Potential in COVID-19 Therapy. Molecules. 2022 Apr 26;27(9):2773.
Sun CY, Zheng ZL, Chen CW, Lu BW, Liu D. Targeting Gut Microbiota With Natural Polysaccharides: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Against High-Fat Diet-Induced Metabolic Diseases. Front Microbiol. 2022 Mar 15;13:859206.
Gan L, Wang J, Guo Y. Polysaccharides influence human health via microbiota-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pathways. Front Nutr. 2022 Nov 9;9:1030063.
Chen J, Gao Y, Zhang Y, Wang M.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treatment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with natural polysaccharides and related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s. Food Funct. 2024 Jun 4;15(11):5680-5702.
Chen P , Hei M , Kong L , Liu Y , Yang Y , Mu H , Zhang X , Zhao S , Duan J . One water-soluble polysaccharide from Ginkgo biloba leaves with antidepressant activities via modulation of the gut microbiome. Food Funct. 2019 Dec 11;10(12):8161-8171.
Wang, A.; Liu, Y.; Zeng, S.; Liu, Y.; Li, W.; Wu, D.; Wu, X.; Zou, L.; Chen, H. Dietary Plant Polysaccharides for Cancer Prevention: Role of Immune Cells and Gut Microbiota,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Nutrients 2023, 15, 3019.
Zhou, Y.; Chu, Z.; Luo, Y.; Yang, F.; Cao, F.; Luo, F.; Lin, Q. Dietary Polysaccharides Exert Anti-Fatigue Functions via the Gut-Muscle Axis: Advances and Prospectives. Foods 2023, 12, 3083
Shen, Y.; Song, M.; Wu, S.; Zhao, H.; Zhang, Y. Plant-Based Dietary Fibers and Polysaccharides as Modulators of Gut Microbiota in Intestinal and Lung Inflammation: Current State and Challenges. Nutrients 2023, 15, 3321
Lv H, Jia H, Cai W, Cao R, Xue C, Dong N. Rehmannia glutinosa polysaccharides attenuates colitis via reshaping gut microbiota and short-chain fatty acid production. J Sci Food Agric. 2023 Jun;103(8):3926-3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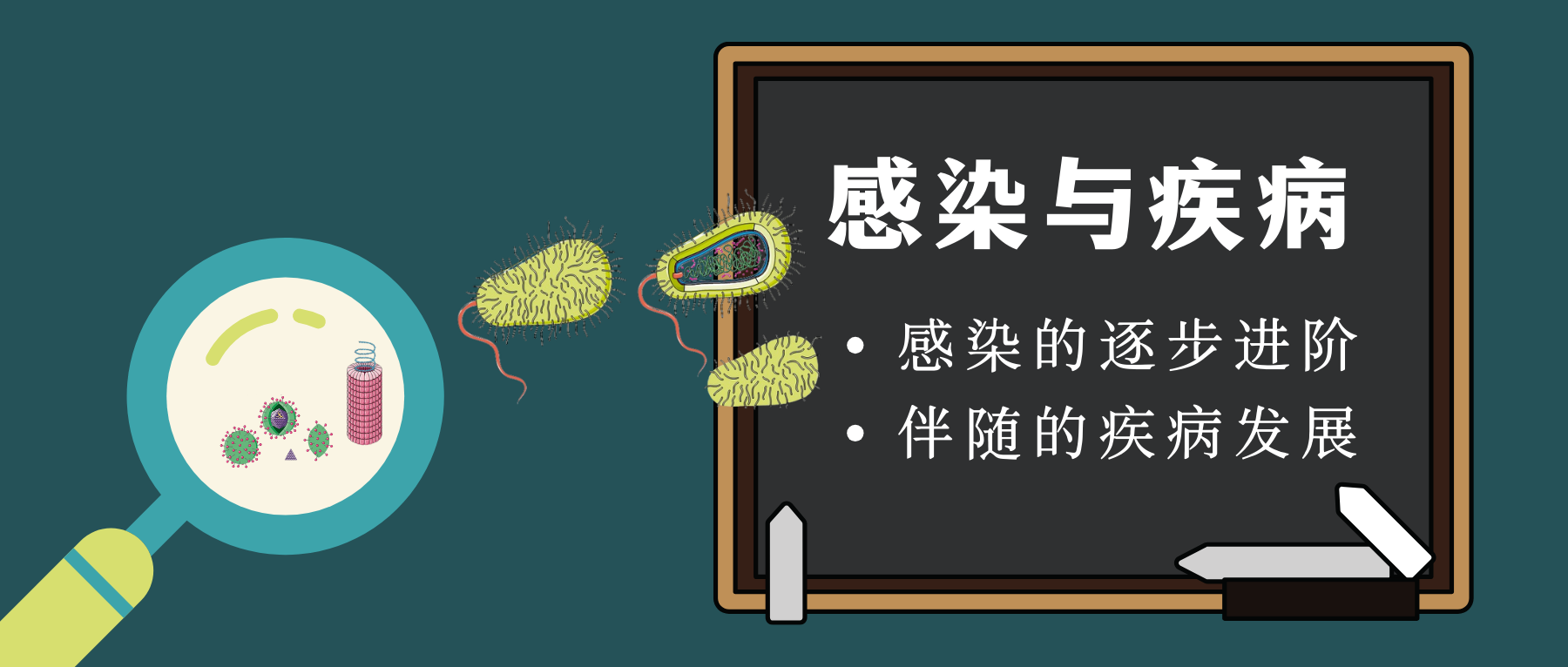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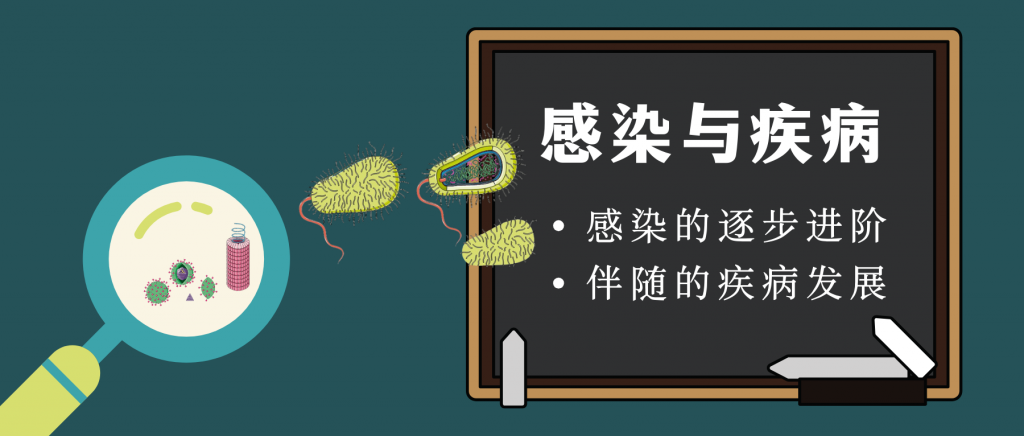
病原微生物和/或有害微生物成功入侵、繁殖并定居于宿主的体内或体内,从而导致健康障碍,称为感染。简单地说,它可以定义为由微生物引起的疾病。感染也被称为传染病或传染病或传染性疾病。
感染每年导致 1300多万 人死亡;2019 年死亡人数为 1370万人(新英格兰医学,2022年统计)。在这 1370 万人死亡中,有 770 万人与细菌感染有关。由于抗菌素耐药性的迅速出现和蔓延,与传染病相关的病例严重程度和死亡率也在增加。
感染和疾病是两个经常互换使用的术语,但它们的含义截然不同。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对于有效预防、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
感染是指有害微生物(如细菌、病毒或真菌)侵入人体。这些病原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体,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或皮肤等。感染可以是局部的,也可以是全身性的,程度可轻可重。
疾病是指由于感染或其他原因而出现的症状或异常的表现。感染是原因,而疾病是结果。简而言之,感染是体内存在病原体,而疾病是感染导致的症状的表现。感染可能只是局部的轻微症状,而疾病则是影响身体正常功能的更严重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免疫系统无法控制微生物的传播,感染可能会发展成疾病。
在诊断时,区分感染和疾病非常重要。一个人可能感染了病原微生物,但没有表现出任何疾病症状。另一方面,一个人可能患病但没有活动性感染。在这种情况下,疾病可能是由感染以外的因素引起的,例如遗传易感性或环境诱因。
虽然预防策略主要侧重于避免感染,但防止感染发展为疾病也同样重要。及早发现和适当治疗感染有助于防止发展为严重疾病。比如,长期的呼吸道或肠道感染被认为是相关肿瘤发生的高风险因素之一。
因此,早期识别感染、诊断、治疗和预防是控制感染和疾病的重要组成部分。感染可以用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物等药物治疗,而疾病可能需要更专业的治疗方案。准确诊断潜在病因对于有效治疗至关重要。
疾病的定义,原因,诊断
// 定义
疾病是一种以身体或精神功能异常为特征的医疗状况。它通常由感染或受伤等外部因素引起,但也可能是由内部失衡或遗传倾向造成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会影响身体的不同器官或系统。
// 原因
疾病有多种原因,包括:
// 症状
疾病可表现出各种症状,包括疼痛、疲劳、发烧和身体功能异常,以及癌症。疾病的症状会因具体情况而有很大差异。
常见症状包括发烧、疲劳、疼痛、炎症和身体功能变化。某些疾病还可能导致与受影响器官或系统相关的特定症状,例如呼吸系统疾病的咳嗽或胃肠道疾病的消化问题。
疾病的形成方式多种多样。有些疾病,例如由遗传性疾病引起的疾病,是天生的。其他疾病可能是通过接触有害物质或环境因素而获得的。感染也会导致疾病的发展。当病原体侵入人体并造成伤害时,免疫反应可能会引发炎症、组织损伤和其他导致疾病的变化。
// 诊断和预防
诊断疾病通常需要结合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等。
预防疾病对于保持整体健康至关重要。这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例如保持良好卫生习惯、接种疫苗、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避免危险因素。早期发现和治疗感染也有助于防止其发展成更严重的疾病。
疾病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其他疗法或这些方法的组合。
总之,疾病涉及身体或精神的异常功能,可能由感染、受伤、遗传因素或失衡引起。识别症状、诊断和了解疾病的原因对于有效预防和治疗疾病至关重要。
感染的定义,原因,诊断
// 原因
感染是一个术语,用于描述有害微生物在体内的入侵和繁殖。这些微生物被称为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当这些病原体进入人体时,它们会引起感染。
感染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这些微生物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体,例如吸入、摄入或通过皮肤破损。
// 症状
虽然感染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但它们通常具有共同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发烧、疲劳、咳嗽、打喷嚏、喉咙痛和炎症。在某些情况下,感染还可能导致更具体的症状,具体取决于所涉及的病原体类型。
感染可能是局部的,即传染源仅感染特定的器官或组织,或者可能是全身性的,即传染源通过血液或淋巴到达身体的不同部位,从而感染不同的器官和组织。
感染可能不会导致疾病等特定症状,因为大多数感染往往是亚临床的。相反,其他感染可能导致严重的症状和并发症。
虽然有些感染可能不被宿主的免疫系统察觉并自行消退,但其他感染可能会引起症状并发展为疾病。
// 预防与治疗
预防是控制感染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可以通过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来实现,例如经常洗手和避免与受感染者密切接触。疫苗接种也可以通过提供针对特定病原体的免疫力来帮助预防某些感染。
预防在降低感染和疾病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接种疫苗和避免与受感染者接触等措施有助于防止感染传播。此外,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增强免疫系统可以降低感染发展为疾病的可能性。
一旦感染,治疗可能涉及使用抗生素、抗病毒药物、抗真菌药物或抗寄生虫药物,具体取决于引起感染的具体微生物。在某些情况下,支持性护理(如休息、补液和缓解症状的药物)可能足以恢复。
// 原因与传播
感染的原因可能因所涉及的微生物类型而异。例如,细菌可通过直接接触受污染的表面、咳嗽或打喷嚏时产生的飞沫,或通过食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引起感染。另一方面,病毒通常通过呼吸道飞沫、与受感染者的直接接触或通过受污染的表面传播。
总之,了解感染的原因和传播方式对于预防、诊断和治疗感染至关重要。通过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并及时就医,个人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并最大程度地减少相关疾病的影响。
感染的诊断是基于通过不同的诊断过程对传染源的识别。
某些感染可能会表现出可用于症状诊断的症状,但通常需要进一步确认。感染直接取决于传染源以及宿主对该传染源的免疫反应。
现在我们认为手术是理所当然的,但不久前,即使是最小的手术,如果感染进入体内,也可能是致命的。消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预防手术感染和确保手术安全的方法。
消毒法是使用化学物质(称为防腐剂)来消灭引起感染的细菌的方法。它是由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发明的。
约瑟夫·李斯特找到了一种预防手术期间和手术后伤口感染的方法。他是第一个将细菌理论的科学应用于外科手术的人。李斯特消毒系统是现代感染控制的基础。
感染和疾病的区别在于症状的严重程度以及对个人整体健康的影响。
感染的定义是细菌、病毒和真菌等微生物在体内的入侵和生长。
感染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接触病原体、卫生条件差、免疫系统受损以及食物或水受污染。感染的症状因感染类型和部位而异,但通常包括发烧、疼痛、炎症和疲劳。
疾病是指影响身体或精神功能的特定状况。
疾病可能是由感染引起的,但也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例如遗传异常、环境毒素、生活方式选择或自身免疫反应。疾病的症状范围从轻微到严重,并且可能持续很短时间或变成慢性病。
感染的诊断通常涉及检测体液或组织样本以确定病原体的存在。另一方面,疾病的诊断通常需要结合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
在治疗方面,感染通常使用抗生素、抗病毒药物或抗真菌药物治疗。治疗的目的是消除入侵的微生物并缓解症状。另一方面,疾病可能需要更全面的方法,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改变生活方式和支持疗法。
大致的区别总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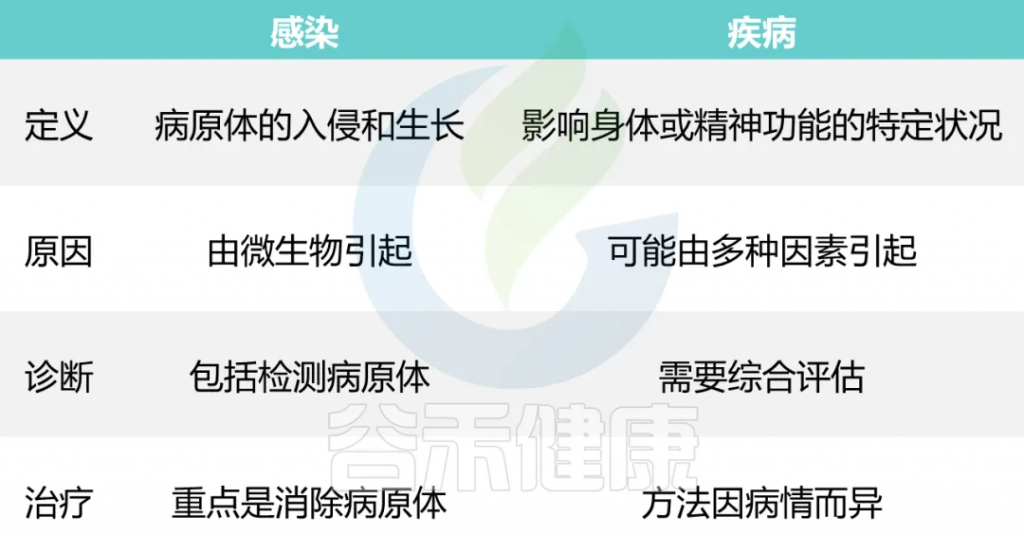
总之,虽然感染和疾病相关,但它们的定义、原因、症状和治疗方法不同。了解两者的区别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和个人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预防和控制疾病。
感染常见类型
细菌感染是由有害细菌进入人体引起的。它们会影响身体的不同部位,例如呼吸系统、泌尿道或皮肤。常见症状包括发烧、疼痛、肿胀和发红。细菌感染通常用抗生素治疗。
病毒感染是由病毒引起的。它们可导致各种疾病,例如普通感冒、流感或 COVID-19。症状从轻微到严重不等,可能包括发烧、咳嗽、喉咙痛和疲劳。病毒感染通常会自行痊愈,但有些可能需要抗病毒药物。
真菌感染是由真菌引起的,例如酵母菌或霉菌。它们会影响皮肤、指甲或内脏器官。常见的真菌感染包括足癣、酵母菌感染和癣。症状可能包括瘙痒、发红和不适。真菌感染的治疗方法包括抗真菌药物和外用药膏。
寄生虫感染是由寄生在人体内或体表的寄生虫引起的。寄生虫感染的例子包括疟疾、虱子感染和贾第虫病。症状可能因寄生虫类型而异,但可能包括发烧、瘙痒、腹泻和疼痛。寄生虫感染的治疗可能涉及抗寄生虫药物。
性传播感染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感染。常见的性传播感染包括衣原体感染、淋病和疱疹。症状范围从轻微到严重,可能包括生殖器分泌物、疼痛和溃疡。性传播感染通常通过检测诊断,可以用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物治疗。
通过了解不同类型的感染、其症状、原因和治疗方法,个人可以采取预防措施来降低感染风险并在需要时寻求适当的医疗护理。
说到疾病和健康,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会影响人体。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疾病类型:
– 传染性疾病
传染病是由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等微生物引起的。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包括直接接触、呼吸道飞沫和受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染病的例子包括普通感冒、流感、肺结核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症状和治疗方法因具体感染而异。
– 慢性疾病
慢性病是一种长期疾病,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并且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这些疾病通常有多种原因,并可能受到遗传、生活方式选择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慢性病的例子包括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和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治疗通常侧重于控制症状和预防并发症。
其他常见疾病类型
– 自身免疫性疾病
当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健康细胞和组织时,就会发生此类疾病,从而导致炎症和组织损伤。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狼疮和多发性硬化症。
– 心血管疾病
影响心脏和血管。包括冠状动脉疾病、心力衰竭和中风等。
– 呼吸系统疾病
这些疾病会影响肺部和呼吸。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包括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炎。
– 精神健康障碍
这些障碍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心理和社会健康。例如抑郁症、焦虑症和精神分裂症。
– 遗传性疾病
这些疾病是由遗传异常基因或突变引起的。这些疾病包括囊性纤维化、镰状细胞病和亨廷顿氏病等。
这些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策略因具体情况而异。
预防感染
预防是感染和疾病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治疗和诊断很重要,但采取措施预防感染可以大大降低疾病的发病率。
预防感染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了解病因和传播方式。感染可通过与感染者直接接触、受污染的表面或空气中的颗粒传播。通过了解传播途径,个人可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将感染风险降至最低。
定期洗手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措施之一。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 20 秒或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有助于消除有害微生物。
此外,例如咳嗽或打喷嚏时捂住口鼻,有助于防止呼吸道感染的传播。
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疫苗刺激免疫系统产生对抗特定病原体的抗体,从而提供免疫力。通过接种疫苗,个人可以保护自己并为社区免疫做出贡献,从而降低传染病的总体流行率。
教育和意识在预防感染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了解常见感染的体征和症状可以及早发现并及时治疗,防止进一步的并发症。此外,提倡卫生习惯并提供有关适当预防措施的教育可以使个人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并保护自己和他人。
总之,预防是对抗感染和疾病的关键。通过采取积极措施,例如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接种疫苗和提高认识,个人可以大大降低感染风险,并为整个社区的健康做出贡献。
预防疾病
预防在减轻疾病负担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了解各种感染和疾病的原因、症状和诊断有助于制定有效的预防策略。
预防疾病不仅仅是避免感染。它涉及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做出明智的选择以降低患病风险。这包括保持均衡饮食,定期进行体育锻炼,避免吸烟和过量饮酒等行为,这些行为会增加患某些疾病的风险。
定期筛查和检查对于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治疗也很重要。通过早期发现疾病,医护人员可以及时治疗,改善治疗效果并减轻疾病的总体负担。
感染和疾病预防还涉及教育公众预防的重要性,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服务。
总之,预防在减少疾病的发生和影响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了解感染和疾病的原因、症状和诊断,实施预防措施并促进健康行为。
感染治疗
在治疗感染时,了解这些疾病的病因、预防和诊断非常重要。
治疗感染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防止其传播。
感染的诊断对于有效治疗至关重要。医生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包括体检、实验室检查和成像技术来确定感染的原因并确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感染的治疗方法取决于感染的类型和严重程度。细菌感染通常用抗生素治疗,而病毒感染则使用抗病毒药物。真菌感染使用抗真菌药物,寄生虫感染则使用抗寄生虫药物。
症状管理
除了针对感染的根本原因外,症状管理也是治疗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可能涉及使用非处方药来缓解疼痛、发烧和充血等症状。
治疗持续时间
感染的治疗时间各不相同。有些感染可能需要短期用药,而有些感染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疗。即使症状有所改善,也必须完成处方药物的全部疗程,以确保感染完全根除。
总之,感染的治疗涉及多方面的方法,包括解决根本原因、症状管理和防止感染扩散。通过了解感染的原因、预防和诊断,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可以为患者提供最有效的治疗。
疾病治疗
疾病的治疗取决于具体症状和致病因素。
在感染病例中,治疗通常侧重于消除引起感染的生物体。这可能涉及使用抗生素、抗病毒药物或抗真菌药物,具体取决于感染的具体类型。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预防性地使用抗病毒或抗真菌药物,以防止感染传播给他人。
另一方面,疾病的治疗不仅仅是治疗感染本身。当疾病被诊断出来后,治疗的目的是缓解症状、控制并发症,并改善整体健康和福祉。
疾病的治疗可能涉及药物治疗、生活方式改变和支持疗法的结合。对于糖尿病或高血压等慢性疾病,主要重点通常是通过药物治疗和生活方式改变(包括定期锻炼和健康饮食)来控制病情。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手术干预来治疗疾病。这可能涉及切除受感染或患病的组织、修复受损器官,或在受伤或退化的情况下恢复功能。
预防也是疾病治疗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解决风险因素并实施预防措施,例如接种疫苗、定期健康检查和改变生活方式,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和严重程度。
诊断在确定疾病的最适当治疗方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准确及时的诊断使医疗保健提供者能够根据每位患者的个人需求量身定制治疗计划。
总之,治疗疾病需要综合考虑具体症状、潜在病因和个体因素。通过了解感染和疾病之间的区别,医护人员可以就治疗方案做出明智的决定,并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
▼
与心血管系统相关的感染,包括血液,即心脏、血管和血液的感染,也称为血流感染或血液循环系统感染。与心血管系统相关的一些常见感染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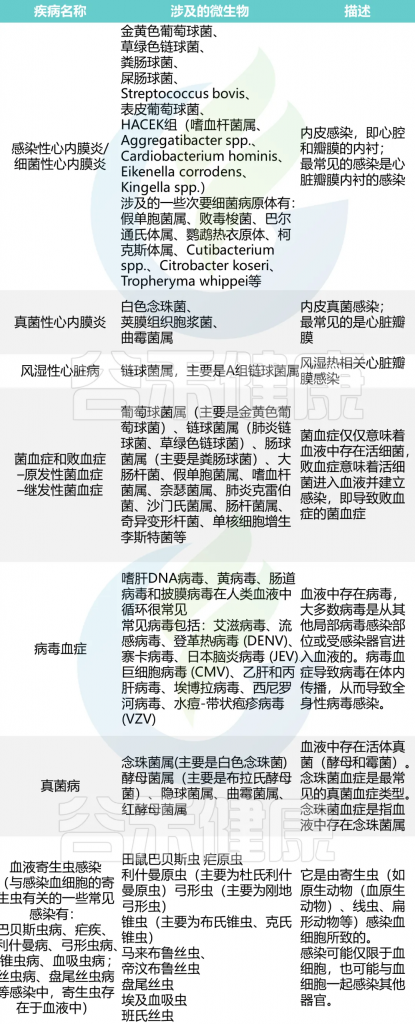
▼
消化系统是参与食物消化的身体系统。它包括胃肠道 (GI 道) 和相关消化器官。胃肠道两端开放,是外来、可能受污染的物质(包括食物和饮料)的停靠点。这使得消化系统极易受到感染。
幽门螺杆菌感染
消化系统感染包括胃肠道任何部位(从口腔到肛门)和任何消化器官(如肝脏、胰腺和胆囊)的感染。消化系统感染主要包括细菌、病毒、原生动物和寄生虫,真菌病原体感染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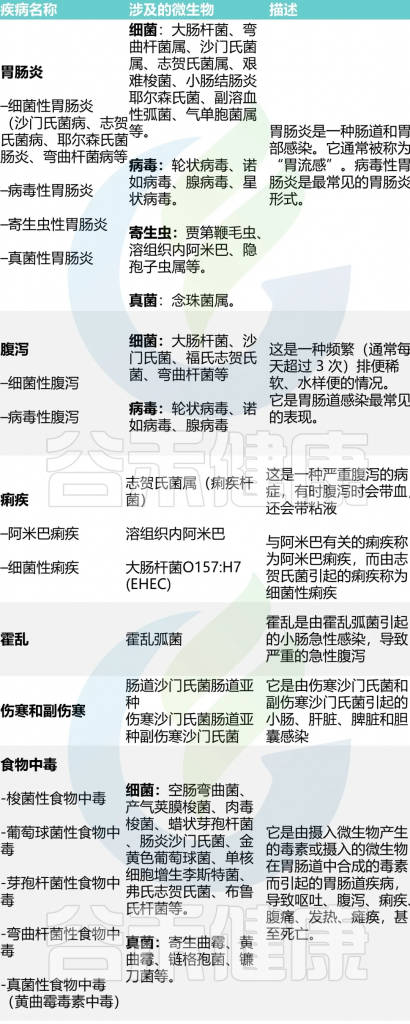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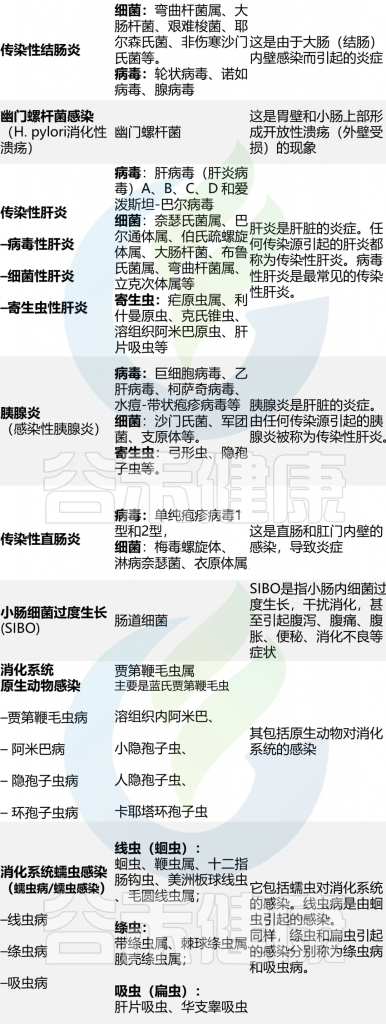
▼
呼吸道感染 (RTI) 是指呼吸系统任何器官的感染。它是人类最常见的感染类型。根据感染呼吸道的部位,RTI 可分为上呼吸道感染 (URTI)(即鼻、鼻窦、咽和喉感染)和下呼吸道感染 (LRTI)(即气管、支气管、细支气管和肺感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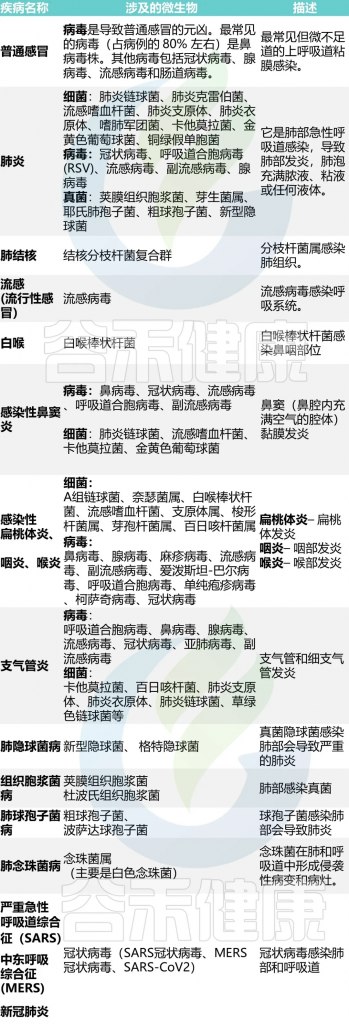
▼
神经系统感染是指大脑、脊髓和/或人体神经的任何形式的感染。此类神经系统感染可能危及生命。它们是由不同的微生物引起的,主要是病毒和细菌。
▼
泌尿系统包括尿道、膀胱、输尿管和肾脏。这些器官中的任何一个感染都称为尿路感染 (UTI)。UTI 主要由细菌引起,但也有真菌和病毒感染的报道,但这种情况很少见。由于女性尿道较短,因此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 U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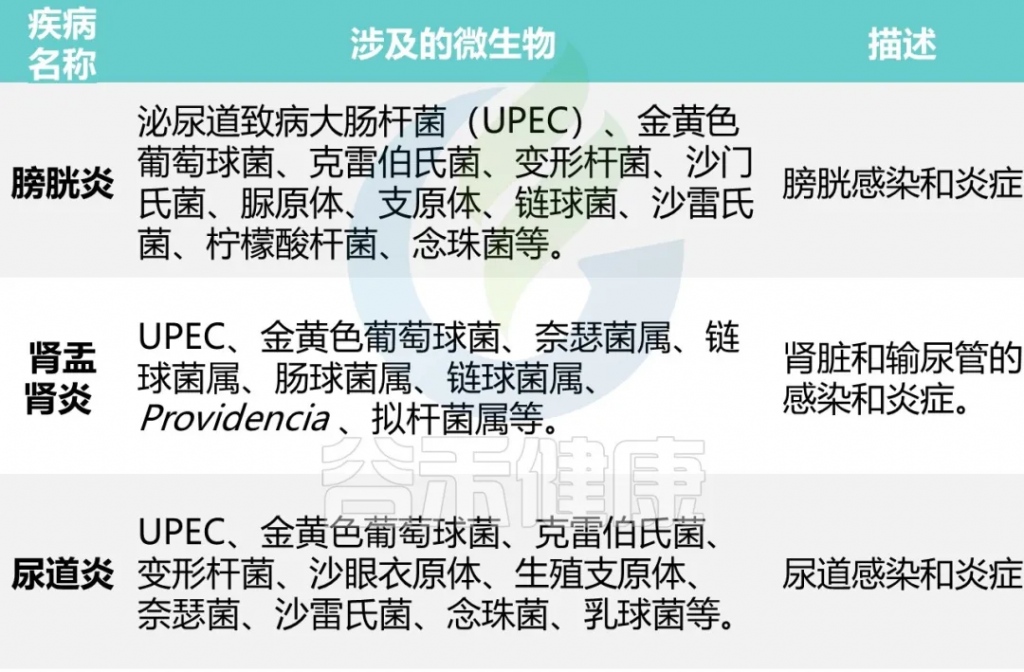
▼
生殖系统包括所有参与生殖过程的器官。它在人类中与泌尿系统非常接近。许多引起尿路感染的微生物是造成生殖系统感染的原因。生殖系统感染分为三种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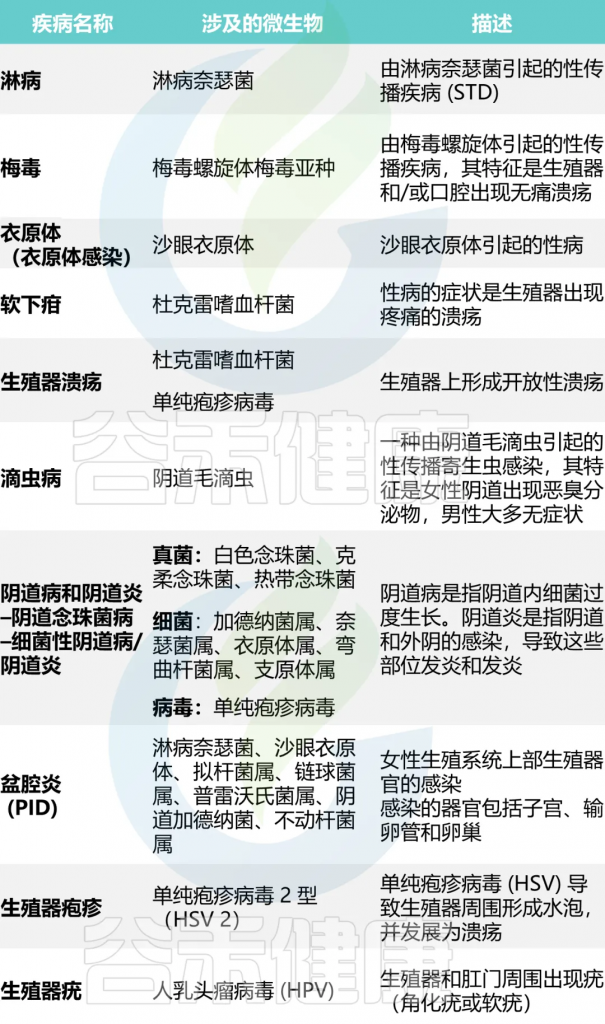
▼
淋巴系统是淋巴管、淋巴结和淋巴器官的网络,淋巴液在其中流动。它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也是循环系统的一部分。淋巴感染并不常见,但有报道称存在多种细菌和寄生虫感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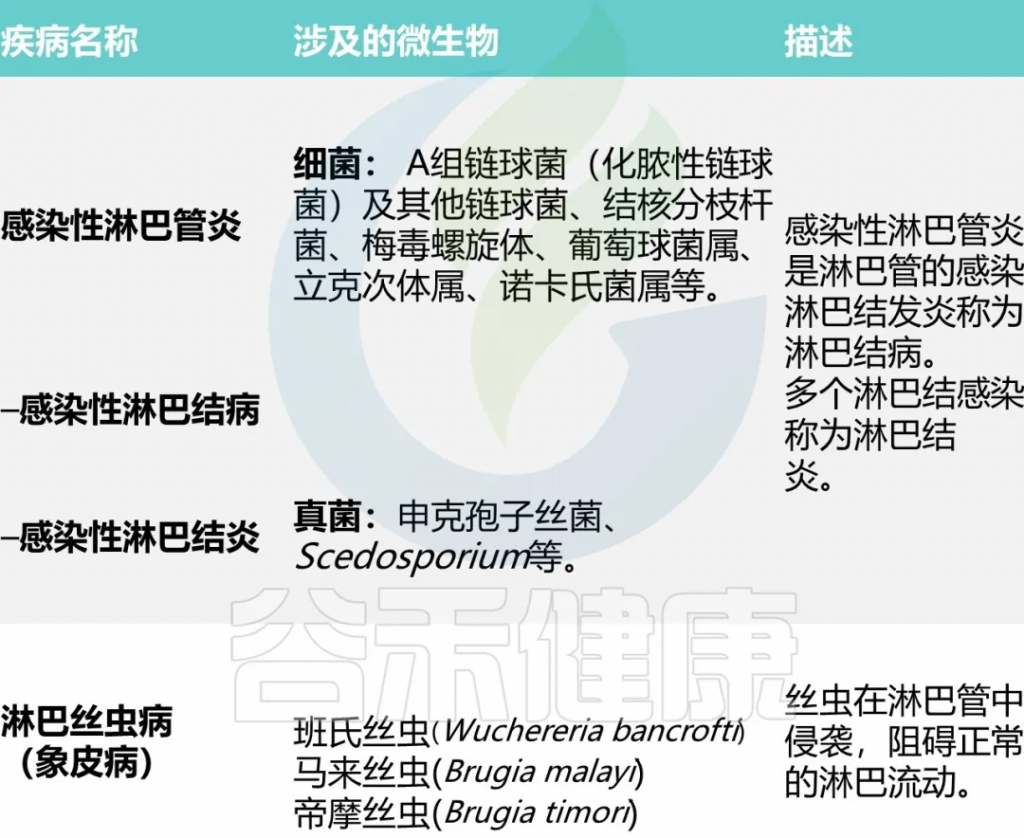
▼
外皮系统包括身体的所有外部覆盖物。它包括皮肤、头发和指甲。外皮系统是我们身体的第一层防御。它是数百万微生物作为正常菌群的家园。病原体在侵入身体之前首先与外皮接触。

▼
肌肉系统包括我们身体的所有肌肉。肌肉感染通常是血源性或传染性传播,但通常很严重,需要立即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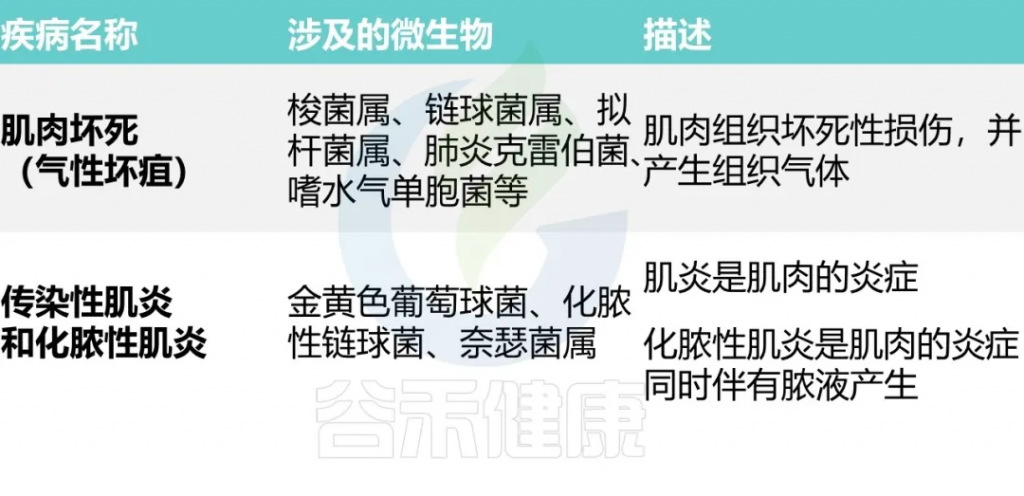
骨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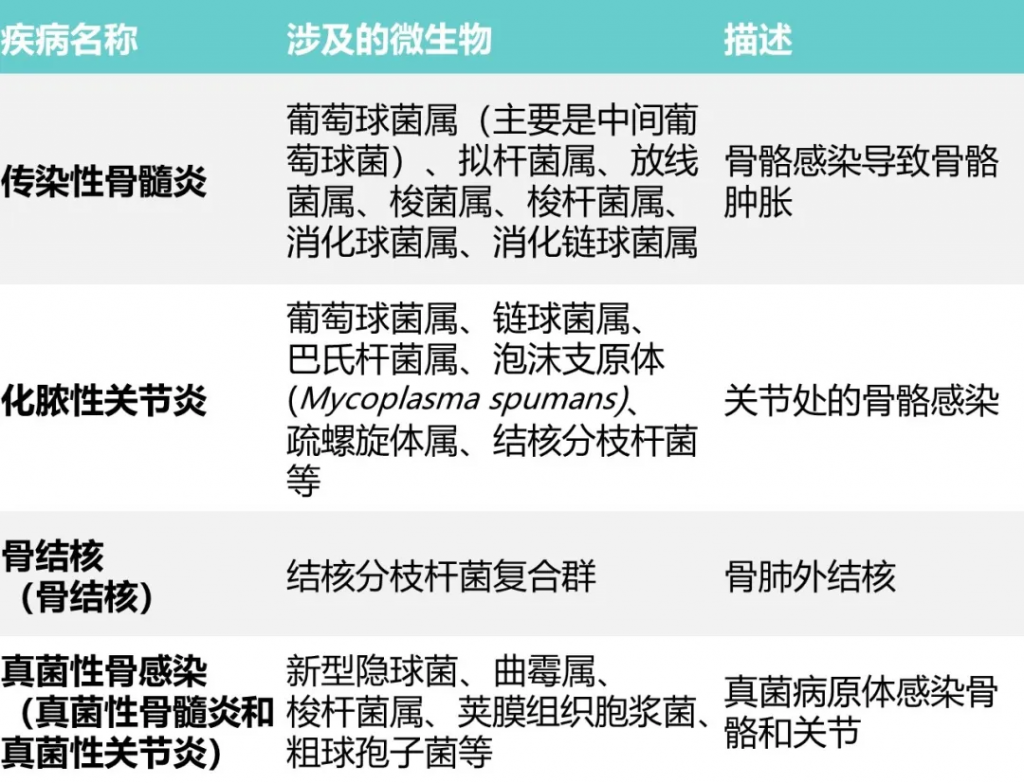
▼
内分泌系统由内分泌腺组成,内分泌腺感染主要是通过血源性播散感染或进行性全身感染而引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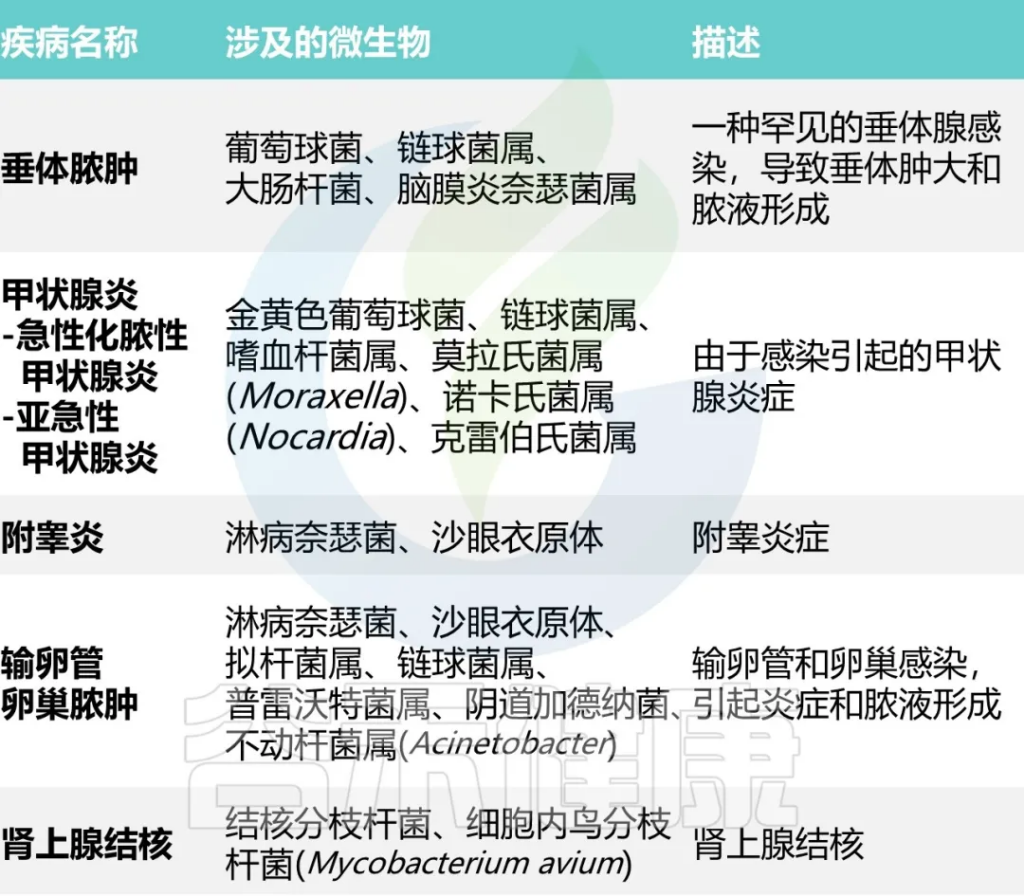
在当今世界,传染病始终是一个威胁,了解感染的各个阶段对于有效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从感染到康复的过程可以粗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症状和结果。
了解感染的四个阶段对于确定适当的行动方案至关重要,从预防和早期发现到治疗和康复。识别前驱期及其独特症状有助于早期干预,降低传播率并预防并发症。下面详细了解一下每个时期不同的特征及相关干预。
▼
潜伏期
感染的第一阶段称为潜伏期,在此期间,患者接触到病原体,但可能不会出现任何症状。潜伏期的长短取决于具体感染源,可能为几小时至数周不等。
最初接触病原体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接触受污染的表面、空气中的颗粒物,或直接接触受感染者。在此期间,患者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接触到病原体。
潜伏期内可能出现前驱期
此阶段的特点是出现轻微症状,这些症状通常不具特异性,容易被忽视或归因于其他因素。前驱期的症状可能包括疲劳、头痛、轻微发烧和全身不适。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感染都会经历前驱期。有些感染可能直接从潜伏期进入急性期,这取决于具体病原体和个人的免疫反应。
▼
潜伏期过后,感染进入第二阶段,即入侵和复制。在此阶段,病毒或细菌已成功侵入宿主体内,并开始快速繁殖。这导致体内病原体的浓度较高,从而导致症状的出现。
前驱期是侵袭和复制阶段的一部分,其特点是出现初始症状。这些症状可能是一般性的和非特异性的,例如疲劳、发烧、头痛和肌肉疼痛。前驱期是感染正在发展的警告信号,可让免疫系统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准备。
随着感染的进展,它会进入急性期,症状会变得更加严重,并且针对特定病原体。人体的免疫系统在各种防御机制的帮助下,试图对抗入侵的病原体。然而,在这个阶段,战斗仍在继续,结果尚不确定。
在慢性期,一些感染可以在体内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此阶段的特点是症状较轻,甚至完全没有症状。然而,病原体继续复制并慢慢损害身体组织。如果不及时治疗,慢性感染会导致长期并发症和后遗症。
在某些情况下,随着人体免疫系统成功消灭病原体,感染会自然消退。这会导致康复,症状逐渐消退,患者恢复正常健康状态。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并发症,如继发感染或器官损伤,这会延长康复过程,并可能需要额外的医疗干预。
值得注意的是,感染过程的各个阶段可能因具体病原体、个人免疫反应和医疗条件而异。
▼
经过潜伏期和症状出现后,感染者进入前驱期,预示着疾病急性期的开始。
在前驱期,症状逐渐恶化,变得更加明显。感染者可能会出现疲劳、不适和发烧等一般症状,以及特定感染特有的特定症状。
此阶段至关重要,因为它通常表明免疫系统正在积极对抗感染。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感染都有明确的前驱期。有些人可能会直接从潜伏期进入急性期,而不会出现任何前驱症状。
可能出现并发症
如果不及时治疗或免疫系统无法有效控制感染,前驱期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的严重程度可能因感染类型和个人的整体健康状况而异。
前驱期可能出现的一些并发症包括继发感染、器官损伤或感染扩散至身体其他部位。这些并发症会延长病程,增加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
前驱期的恢复
对于大多数感染来说,前驱期标志着急性期的开始,在此期间症状达到顶峰。急性期过后,身体逐渐恢复并进入缓解期,症状开始消退,患者开始感觉好些。
从前驱期和随后的急性期恢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因此遵循处方治疗并根据需要休息很重要。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感染痊愈后,也可能出现复发或出现长期后遗症,如慢性疲劳或器官损伤。
总体而言,了解前驱期的进展和症状对于有效管理和治疗感染至关重要。认识到这一阶段的开始可以帮助个人寻求适当的医疗护理并采取措施预防进一步的并发症。
▼
潜伏期结束后,感染者进入感染的急性期。在这个阶段,症状会完全显现,感染也会达到高峰。
前驱期是急性期的初始阶段,其特点是出现发烧、疲劳、头痛和肌肉疼痛等症状。在此阶段,感染者还可能感到全身不适。
严重感染的急性期通常持续数天至数周。此阶段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可能因具体病原体和个人的免疫反应而异。
并发症和后遗症
在某些情况下,感染的急性期会导致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可能是由于病原体对身体的直接影响或身体对感染的免疫反应而引起的。常见的并发症包括肺炎、器官衰竭和继发感染。
一旦成功控制了急性期,感染者就会进入恢复期。在此阶段,身体会逐渐消除感染,症状开始改善。根据感染的严重程度,恢复可能需要几天到几周的时间。
在某些情况下,感染可能会发展为慢性阶段。当身体无法完全消除病原体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并且感染会持续很长时间。慢性感染可能导致长期健康问题,可能需要持续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感染都会经历所有阶段,并且进展和症状可能因具体病原体和个体因素而异。
常见症状
在感染的这个阶段,可能会出现常见症状,这些症状可能因具体病原体和个人的免疫反应而异。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相同的症状,有些人的表现可能比其他人更严重。
在急性期,患者可能会出现发烧、疲劳、身体疼痛和头痛等症状。这些症状通常表明身体对感染产生了免疫反应,可能会持续数天。
急性期过后,患者可能会进入慢性感染期。在此阶段,症状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有时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常见的慢性症状包括持续疲劳、关节疼痛、肌肉无力和认知困难。
有些感染还可能产生后遗症,即感染导致的长期后果或并发症。这些后遗症的严重程度可轻可重,可能影响身体的各个器官或系统。后遗症的例子包括器官损伤、神经系统疾病和免疫功能受损。
复发是另一种可能的结果,尤其是某些病原体引起的感染。经过一段时间的明显缓解后,症状可能会再次出现,表明感染复发。这可能是由于各种因素造成的,例如病原体根除不彻底或休眠感染重新激活。
▼
在感染的呼吸道症状阶段,病毒已到达呼吸系统并开始影响肺部和呼吸道。此阶段通常是在前驱期结束后,发烧和疲劳等一般症状开始消退。
呼吸道症状的严重程度因个人和引起感染的特定病毒而异。常见症状包括咳嗽、呼吸急促、胸痛或不适以及喘息。这些症状通常表明呼吸系统发炎和充血。
在某些情况下,呼吸道症状可能导致肺炎、支气管炎或呼吸衰竭等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可能需要额外的医疗干预,并可能延长整体康复过程。如果呼吸道症状恶化或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请务必就医。
一旦呼吸道症状开始改善,患者即被认为处于康复阶段。在此阶段,身体继续抵抗感染,免疫系统努力清除呼吸系统中的病毒。康复阶段的持续时间可能因个人和感染严重程度而异。
在极少数情况下,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与呼吸道症状相关的后遗症或长期影响。这些可能包括慢性肺损伤、肺功能下降或感染痊愈后仍持续存在的呼吸道疾病。同样,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呼吸道症状复发,即症状在改善一段时间后再次出现。
为了帮助康复和预防并发症,休息、保持水分充足并遵照处方治疗或药物非常重要。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均衡饮食和定期锻炼)也可以支持免疫系统并促进整体呼吸系统健康。
▼
在感染的第七阶段,即胃肠道阶段,患者可能会出现一系列与消化系统相关的症状。这些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可能有所不同,
可能包括:
这些胃肠道症状可能是感染扩散至肠道或人体对感染的免疫反应所致。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症状可能会随着时间和休息而自行缓解。但是,可能会出现脱水等并发症,需要医疗干预。
对于处于此阶段的人来说,控制症状并在必要时寻求适当的医疗护理非常重要。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可能会建议休息、补充水分和改变饮食。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开药来缓解症状或治疗并发症。
还要注意的是,虽然有些人可能在此阶段后症状完全消失,但其他人可能会继续经历其他阶段,例如复发或出现后遗症。
▼
神经系统症状可发生在感染的急性期,也可发生在恢复期、复发期和并发症期。这些症状可能是病毒直接入侵的结果,也可能是病毒对神经系统的继发影响。
在感染的急性期,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晕和精神错乱等神经症状。这些症状通常较轻且短暂,可在数天或数周内缓解。
但在某些情况下,神经系统症状可能会在恢复阶段持续存在。这些症状可能包括持续性头痛、注意力不集中和记忆力问题。
在复发阶段,神经系统症状可能会再次出现或恶化。这可能是病毒重新激活或对神经系统造成进一步损害的结果。
此阶段还可能出现并发症,导致更严重的神经系统症状。这些并发症可能包括脑炎、脑膜炎和中风。
经过适当的医疗护理和治疗,大多数人可以从这些神经症状中恢复过来。然而,有些人可能会出现长期的神经后遗症,如认知障碍或运动功能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感染潜伏期也可能出现神经症状。这是接触病毒和出现症状之间的阶段。此阶段的神经症状很少见,但可能包括嗅觉或味觉丧失。
在慢性感染病例中,神经系统症状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症状可能是间歇性的,严重程度也各不相同。
如果您在感染的任何阶段出现任何神经系统症状,请务必重视。
▼
在感染的急性期,个人通常会出现皮肤症状。皮肤症状是指影响皮肤的任何症状。这些症状的范围从轻微到严重,并可能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具体取决于感染的类型。
在潜伏期,个人可能不会出现任何皮肤症状。然而,随着感染进展到慢性阶段,皮肤症状可能开始出现。这些症状可能包括皮疹、水泡、病变或皮肤变色。这些症状的严重程度因人而异,有些人只会出现轻微症状,而另一些人可能会出现影响日常活动的严重症状。
在某些情况下,皮肤症状可能导致并发症。当感染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或免疫系统对感染反应强烈时,就会出现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皮肤症状,甚至可能导致其他健康问题。
感染急性期过后,患者可能会出现感染的后遗症或长期影响。这些后遗症可能包括持续的皮肤症状,如疤痕或色素沉着变化。这些长期影响因人而异,取决于感染的严重程度和个人的免疫反应等因素。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感染痊愈,患者也可能会出现皮肤症状复发。如果感染未从体内完全清除,或者免疫系统受损,则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患者出现皮肤症状复发,请务必就医,因为这可能表明感染复发或其他潜在健康问题。
总之,皮肤症状可发生在感染的各个阶段,从急性期到慢性期,甚至感染消退后。这些症状可从轻微到严重,并可能对皮肤产生长期影响。个人必须注意这些症状,并在必要时寻求医疗帮助,以确保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
血液学症状通常出现在感染的恢复期。此阶段发生在急性期之后,急性期的特点是出现症状并出现并发症。
在此阶段,人体的血液系统开始稳定并恢复正常。前驱症状(即感染前出现的一般症状)开始消退。人体开始产生更多的白细胞,负责抵抗感染。
在某些情况下,血液学症状可能会复发。如果感染在急性期没有完全解决,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复发可能是由于病毒重新激活或出现新的细菌菌株引起的。
常见的血液学症状:
潜伏期(即从接触感染到症状首次出现之间的时间)也会出现血液学症状。然而,此阶段的症状通常较轻微,可能不明显。
如果血液学症状在恢复期持续存在或恶化,则可能表明出现并发症或发展为慢性感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额外的医疗干预。
在感染的不同阶段密切监测血液学症状对于确保正确的诊断和治疗非常重要。可以定期进行血液检查以跟踪血液系统的变化并指导治疗计划。
▼
在感染的肌肉骨骼症状阶段,患者可能会出现肌肉、关节和骨骼的急性疼痛、僵硬和肿胀。这些症状通常发生在前驱期之后,可能是身体对感染的免疫反应的结果。
肌肉骨骼症状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个人和引起感染的具体病原体。有些人可能只会感到轻微不适,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会感到剧烈疼痛和活动受限。
在某些情况下,肌肉骨骼症状可能是感染的后遗症,这意味着即使感染已经消退,这些症状仍会持续存在。这在某些病毒感染中更为常见,例如寨卡病毒或基孔肯雅病毒。
注:寨卡病毒属黄病毒科,黄病毒属,单股正链RNA病毒,直径20nm,是一种通过蚊虫进行传播的虫媒病毒,宿主不明确,主要在野生灵长类动物和栖息在树上的蚊子。
基孔肯雅病是由伊蚊传染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其临床症状为突然发烧、头疼、呕吐、关节痛及腰下部疼痛等,而最有效的应对途径是采取预防措施,减少蚊虫的滋生。
肌肉骨骼症状的恢复通常包括休息、疼痛管理和物理治疗,以改善力量和活动能力。如果症状严重或持续,可能需要更密集的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肌肉骨骼症状也可能是感染的并发症,可能需要额外的医疗干预。并发症可能包括关节炎症、骨骼或软骨损伤或周围组织感染。
在极少数情况下,患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缓解或恢复后可能会出现肌肉骨骼症状复发。这可能是由于引起最初感染的病毒或细菌重新激活,或被同一病原体再次感染。
总体而言,感染过程中的肌肉骨骼症状会极大地影响个人的生活质量。如果您出现任何这些症状,建议处理以便获得准确的诊断和适当的治疗。
▼
泌尿生殖系统症状可作为某些传染病发展的一部分出现。这些症状可能表明感染已到达泌尿生殖道,包括生殖系统和泌尿系统的器官。并非所有感染都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并且出现泌尿生殖系统症状并不总是表明感染严重或晚期。
泌尿生殖道阶段通常发生在感染的初期阶段之后,例如急性期和前驱期。在此阶段,病毒或细菌可能已经通过血液或其他身体系统到达泌尿生殖道。
出现泌尿生殖系统症状的患者可能会注意到泌尿系统的变化,例如排尿频率或尿急增加、排尿疼痛、尿液浑浊或带血,或难以完全排空膀胱。影响生殖系统的感染也会导致阴道分泌物、异常出血、盆腔疼痛或男性睾丸疼痛等症状。
在某些情况下,泌尿生殖系统症状可能伴有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可能包括肾脏感染、尿路感染、盆腔炎或性传播感染。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或怀疑有感染,请务必就医。
泌尿生殖系统阶段的持续时间可能因具体感染和个人因素而异。在某些情况下,症状可能会通过适当的休息、补水和对症治疗自行缓解。但是,如果感染未得到适当治疗或存在潜在健康问题,感染可能会发展为慢性阶段或导致复发。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感染会对泌尿生殖系统产生长期影响或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可能包括不孕症、慢性疼痛、疤痕或其他可能需要持续医疗管理的并发症。
常见的泌尿生殖系统症状:
▼
在感染过程中,个人可能会经历多个阶段。这些阶段包括潜伏期、复发、并发症、缓解,甚至慢性和急性后遗症。然而,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阶段是心理症状阶段。
心理症状可发生在感染的任何阶段,程度从轻微到严重不等。这些症状通常表现为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变化。常见的心理症状包括焦虑、抑郁、易怒、困惑和注意力难以集中。
心理症状的存在会对个人的整体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产生重大影响。这些症状会影响一个人进行日常活动、维持人际关系甚至工作或上学的能力。为了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治疗,识别和解决这些症状非常重要。
病原微生物检测在感染管理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通过病原微生物检测可以有效地控制和预防医院内感染,并加速患者的恢复过程。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检验技术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正在成为指导临床感染辅助诊断和治疗的重要依据。
多种检测手段应用于病原体检测,例如:
在感染的临床管理中,除了传统的病原体检测方法外,肠道菌群检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肠道菌群有助于消化、吸收营养物质,同时还调节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对人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肠道菌群失衡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肠道菌群与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维持内稳态很重要,但这种相互作用一旦受到干扰,就会成为许多慢性疾病的核心驱动因素。
在肠道、相关微生物群和各种器官之间的双向或多向通信连接(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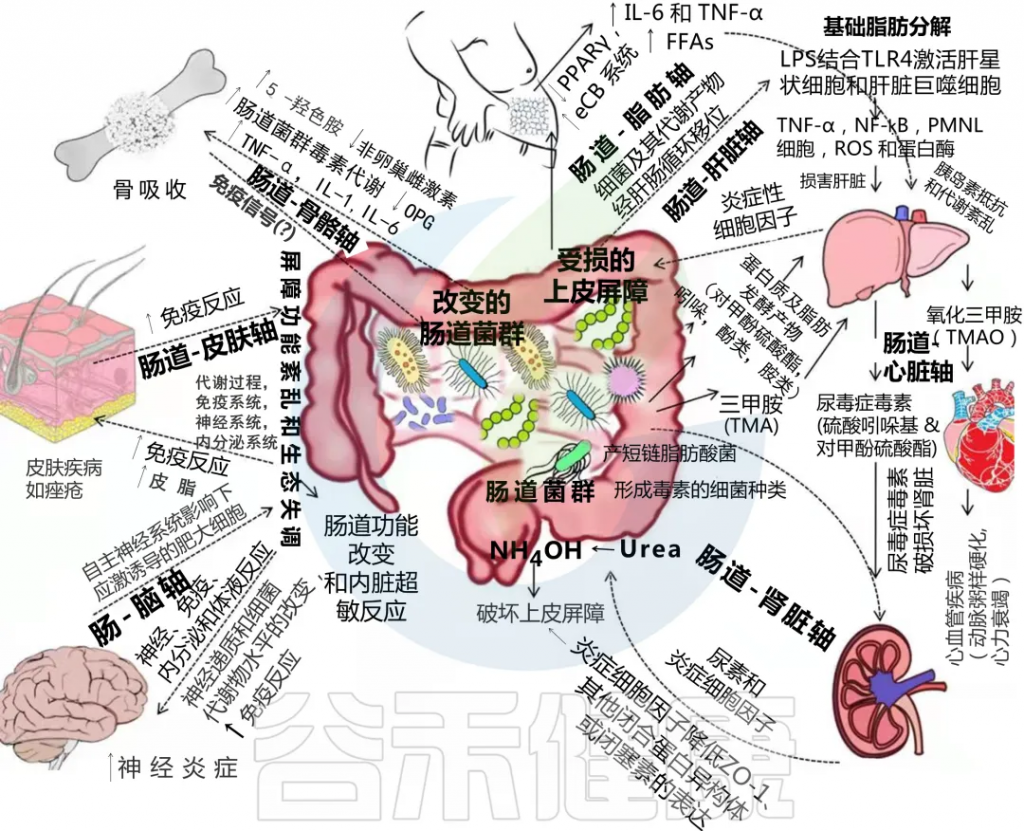
Ahlawat S,et al.,Lett Appl Microbiol. 2021
关于这方面可详见我们之前的文章:
肠道菌群报告中会有致病菌超标等明确指示,此外我们还可以判断整个肠道微生态的健康状况。肠道微生物群的失调可能导致肠道易感性增加,使得易感性疾病如艰难梭菌感染更容易发生。
通过分析肠道微生物组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感染过程,评估治疗效果,并为个性化干预提供依据。
感染,作为全球健康的主要威胁,其影响甚至超过个体的病痛,它触及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本文在了解各种感染阶段、症状的同时,也强调了病原体检测在感染管理中的重要性,病原体相关检测手段让我们能够及时识别感染类型,评估其严重程度,并预测可能的并发症。
面对不断演变的病原体和日益严峻的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我们在推动科研创新的同时,也需提高公众对感染性疾病的认识,强化预防措施,如感染源的识别、个人卫生习惯等,对于控制感染的传播同样至关重要。
在治疗方面,针对病原体的特异性治疗是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关键。这需要医疗相关专业人员根据相关诊断结果,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包括抗生素、抗病毒、抗真菌等。同时,症状管理和支持性护理也是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医疗知识的积累,整合病原体相关检测,加强跨学科的研究,以及普及健康教育,有望不断提升治疗效果,为患者带来更好的康复和生存机会。
免责声明: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医疗建议。请务必咨询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以正确诊断和治疗任何感染。
主要参考文献:
Murray, P. R., Rosenthal, K. S., & Pfaller, M. A. (2013). Medical microbiology. Philadelphia: Elsevier/Saunders
Parija S.C. (2012). Textbook of Microbiology & Immunology.(2 ed.). India: Elsevier India.
Sastry A.S. & Bhat S.K. (2016). Essentials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New Delhi : Jaypee Brothers Medical Publishers.
Joseph Lister’s antisepsis system,2018,Science Museum
sciencedirect.com/topics/immunology-and-microbiology/germ-theory-of-disease
biologydictionary.net/germ-theory/
infectioncycle.com/articles/infection-stages-understanding-the-progression-of-infectious-diseases-and-their-impact-on-health
germ theory,Adam Augustyn,2024, 5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S) Committee to Update Science, Medicine, and Animals. Science, Medicine, and Animal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US); 2004.
Murray, P.R., Rosenthal, K.S., & Pfaller, M.A. (2015). Medical microbiology (8th ed.). Elsevier.
Fauci, A.S., Braunwald, E., Kasper, D. L., Hauser, S. L., Longo, D. L., & Jameson, J. L. (Eds.). (2008). 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 (17th ed.). McGraw-Hill Medical
Mandell, G. L., Bennett, J. E., & Dolin, R. (2010). Mandell, Douglas, and Bennet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7th ed.). Churchill Livingstone.
Brook, I. (2013). Microbiology and management of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CRC Press.
Control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Manual by David Heymann.
G. Authia, S. Fablina, 2022. Global and regional sepsis and infectious syndrome mortality in 2019: a systematic analysis.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 Published:March, 2022
Loretta J. Bubenik (2005). Infections of the Skeletal System. , 35(5), 0–1109. doi:10.1016/j.cvsm.2005.05.001
Morrison WB, Kransdorf MJ. Infection. 2021 Apr 13. In: Hodler J, Kubik-Huch RA, von Schulthess GK, editors. Musculoskeletal Diseases 2021-2024: Diagnostic Imaging [Internet]. Cham (CH): Springer; 2021.
Megran DW. Enterococcal endocarditis. Clin Infect Dis. 1992 Jul;15(1):63-71. doi: 10.1093/clinids/15.1.63. PMID: 1617074.
Roberts RB, Krieger AG, Schiller NL, Gross KC. Viridans streptococcal endocarditis: the role of various species, including pyridoxal-dependent streptococci. Rev Infect Dis. 1979 Nov-Dec;1(6):955-66. doi: 10.1093/clinids/1.6.955. PMID: 551516.
Infective endocarditis: A contemporary update. Ronak Rajani, John L Klein. Clinical Medicine Jan 2020, 20 (1) 31-35; DOI: 10.7861/clinmed.cme.20.1.1
Lamas, C. C., & Eykyn, S. J. (2003). Blood culture negative endocarditis: Analysis of 63 cases presenting over 25 years. Heart, 89(3), 258-262.
Smith DA, Nehring SM. Bacteremia. [Updated 2022 Jul 31]. In: StatPearls [Internet]. Treasure Island (FL): StatPearls Publishing; 2023 Jan-.
Britannica, The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septicemia”.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3 Jun. 2022
Martinez RM, Wolk DM. Bloodstream Infections. Microbiol Spectr. 2016 Aug;4(4).
Akhondi H, Simonsen KA. Bacterial Diarrhea. 2022 Aug 8. In: StatPearls [Internet]. Treasure Island (FL): StatPearls Publishing; 2023 Jan–. PMID: 31869107.
Bacterial gastroenteritis: Causes,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medicalnewstoday.com)
Typhoid (who.int)
Imam Z, Simons-Linares CR, Chahal P. Infectious causes of acute pancreatitis: A systematic review. Pancreatology. 2020 Oct;20(7):1312-1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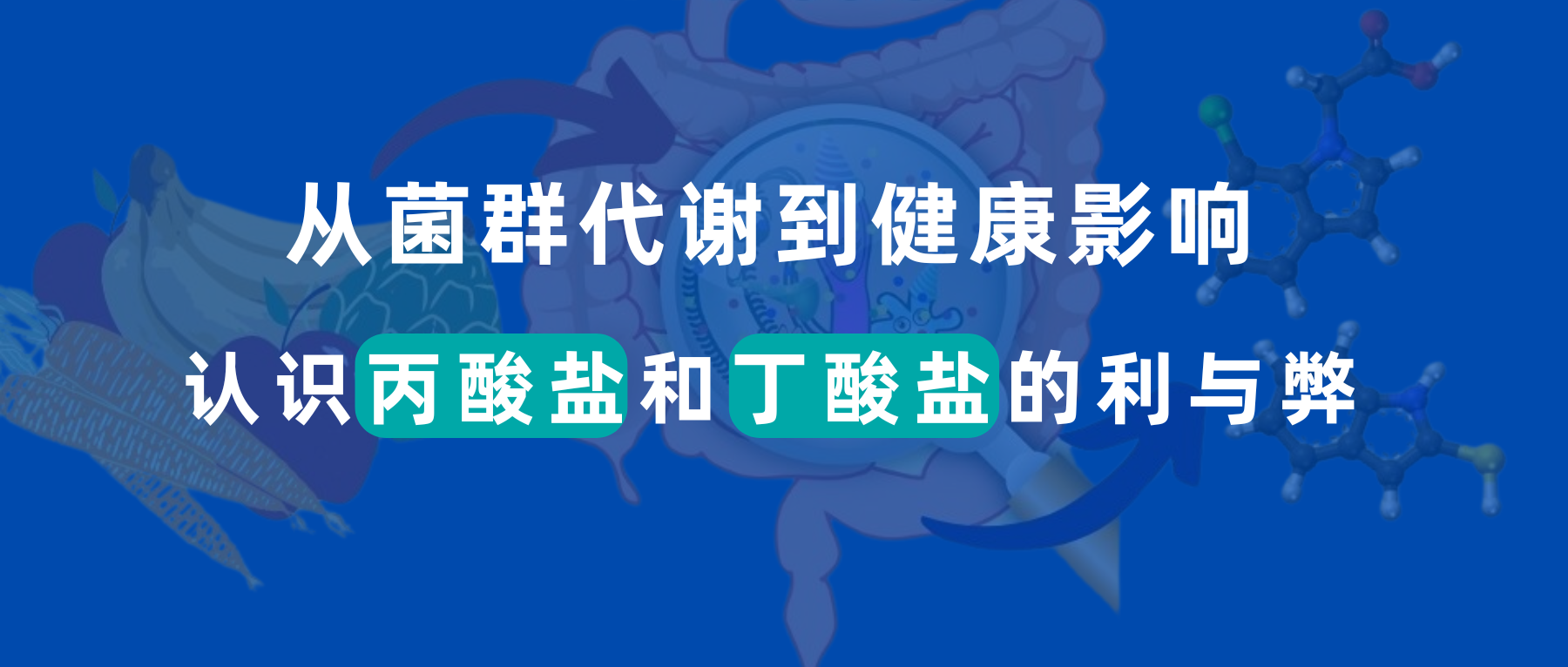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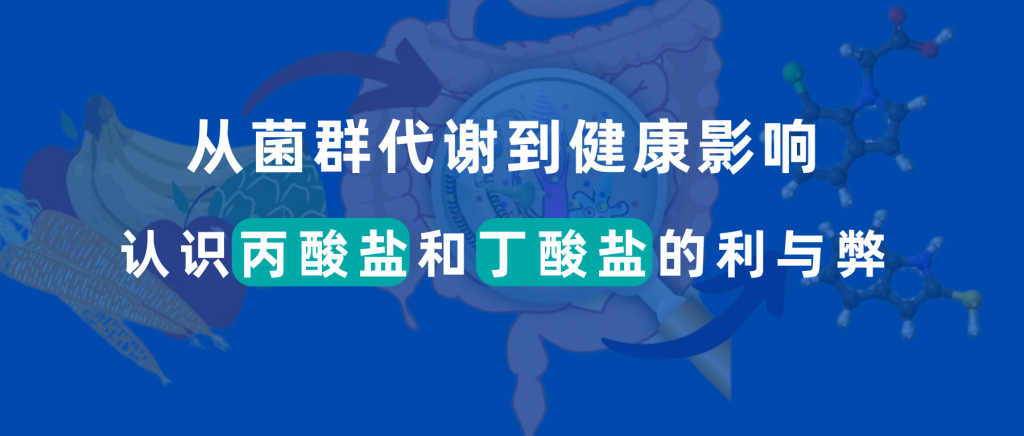
短链脂肪酸这一词经常出现在谷禾的文章和报告中,那你真的了解短链脂肪酸吗?短链脂肪酸(SCFA)主要是肠道微生物群在结肠内通过发酵碳水化合物(包括膳食和内源性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抗性淀粉和膳食纤维)和一些微生物可利用的蛋白质而产生的。
短链脂肪酸主要是乙酸、丙酸和丁酸,在结肠中的浓度比大致为60-70%:20-30%:10-20%。这些代谢产物能够被宿主利用,尤其是丙酸和丁酸,它们发挥一系列促进健康的功能。它们能被肠粘膜有效吸收,作为能量来源,还能作为基因表达调节剂以及特定受体识别的信号分子,对宿主生理产生重要影响。近几年的研究还发现其能够调节免疫细胞发育并抑制炎症。
然而,三种主要短链脂肪酸——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它们在体内的功能和组织分布不同,对宿主生理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丁酸盐优先被肠粘膜用作能量来源,还具有抗炎特性,可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和粘膜免疫。丙酸盐有助于抵抗肝脏中的脂肪形成、降低胆固醇、也有一定的抗炎和抗致癌作用。而乙酸在血液中浓度最高,可用作肝脏胆固醇和脂肪酸合成的底物,增加结肠血流量和氧气吸收,并通过影响回肠收缩来增强回肠运动。
其次,它们与宿主蛋白(如丁酸和丙酸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和受体的相互作用也不同。因此,特别需要考虑这些短链脂肪酸的微生物来源。与此同时,饮食结构和肠道生理变化如何影响这些脂肪酸的相对产量和在结肠中的浓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将重点介绍丙酸盐和丁酸盐,因为这两种短链脂肪酸被认为对健康有重要影响,包括丁酸预防结直肠癌,丙酸促进饱腹感并降低胆固醇。而乙酸是大多数肠道厌氧菌的主要发酵产物,也可由还原性乙酸生成,而丙酸和丁酸则由不同的肠道细菌群产生。
我们将探讨在人类结肠微生物群中已知的形成这两种短链脂肪酸的途径,以及各种饮食和环境因素对其产生的调节可能性。详细了解肠道微生物群的短链脂肪酸代谢及其生理功能对于制定个性化的健康营养方案是必不可少的。
丙酸盐和丁酸盐在结构、来源、生理功能以及对健康的影响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 结构上的差异:
丙酸盐(Propionate)含有三个碳原子,羟基(-OH)位于第二个碳原子上。
丁酸盐(Butyrate)含有四个碳原子,羟基(-OH)位于第四个碳原子上。
▸ 来源上的差异:
丙酸盐通常由肠道细菌通过发酵L-鼠李糖、聚葡萄糖、阿拉伯木聚糖、D-塔格糖、甘露寡糖、昆布多糖等糖类物质产生。
丁酸盐可以通过肠道微生物群发酵富含抗性淀粉和果聚糖的食物来增加,如菊粉、马铃薯、洋葱等。
▸ 功能上的差异:
丙酸盐在体内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肝脏中糖原合成的前体物质,有助于调节血糖水平,影响食欲。
丁酸盐是结肠上皮细胞的首选能源,有助于维持肠道屏障,发挥免疫调节和抗炎作用。丁酸盐还可以通过减少NF-kB信号传导和诱导凋亡来促进神经保护。
▸ 对健康的影响:
丙酸盐的健康益处主要是调节能量代谢和改善代谢综合征,可能对调节肠道菌群平衡也有积极作用,但其具体影响取决于个体的肠道菌群组成。
丁酸盐对健康的影响更为广泛,包括维持肠道稳态、促进肠道屏障的完整性、刺激绒毛的生长、促进粘蛋白的产生。以及改善认知功能、促进睡眠、调节社交行为和在糖尿病中的潜在益处。
丙酸盐是许多生物(从细菌到人类)的代谢副产物,产生丙酸的代谢途径可分为三类。主要发酵途径将不同的碳源分解代谢为丙酸盐(图A);分解代谢途径则能将多种氨基酸降解为丙酸盐(图B);此外,通过与从丙酮酸或二氧化碳生成生物质前体相关的合成代谢途径也可以生产丙酸盐(图C)。
产生丙酸盐的代谢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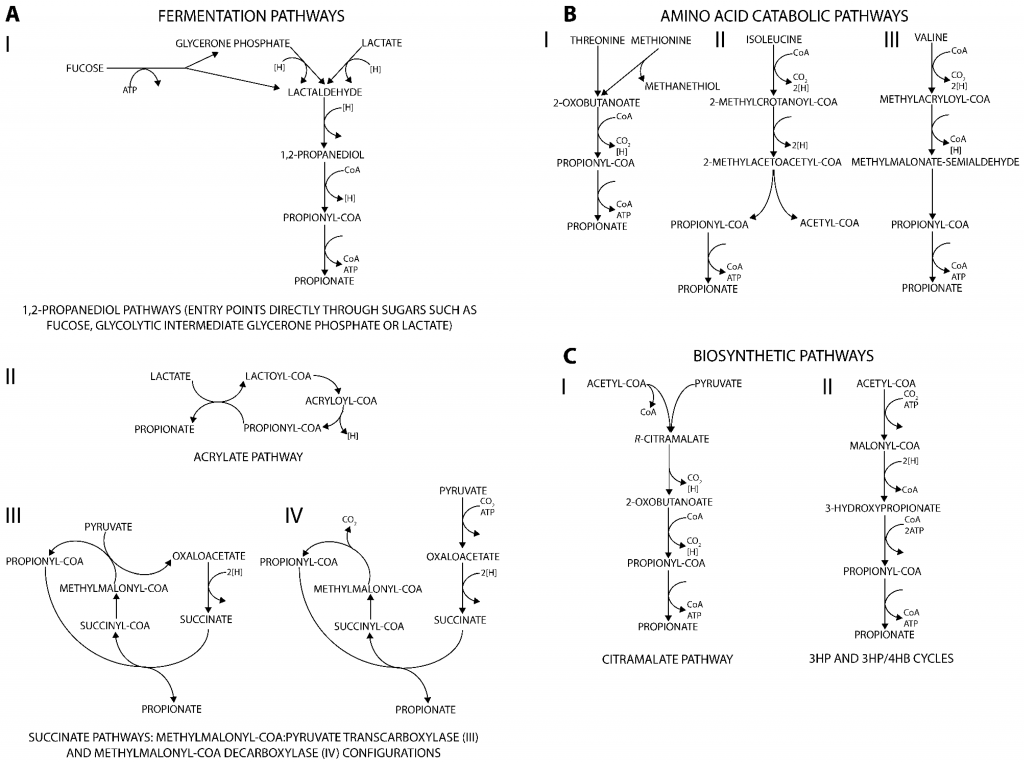
doi.org/10.3390/fermentation3020021
肠道微生物通过发酵不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产生的丙酸盐是体内丙酸盐的主要来源。下面将讲述肠道中丙酸盐通过发酵碳水化合物的三种主要产生途径以及参与这些途径的微生物。
与氨基酸降解和生物合成途径相比,发酵途径不仅提供能量,还帮助消耗由糖分解代谢产生的还原辅因子。它们在能量产生和维持氧化还原平衡中的作用,使这些途径能够与细胞生长相耦合。
能够产生丙酸盐的微生物种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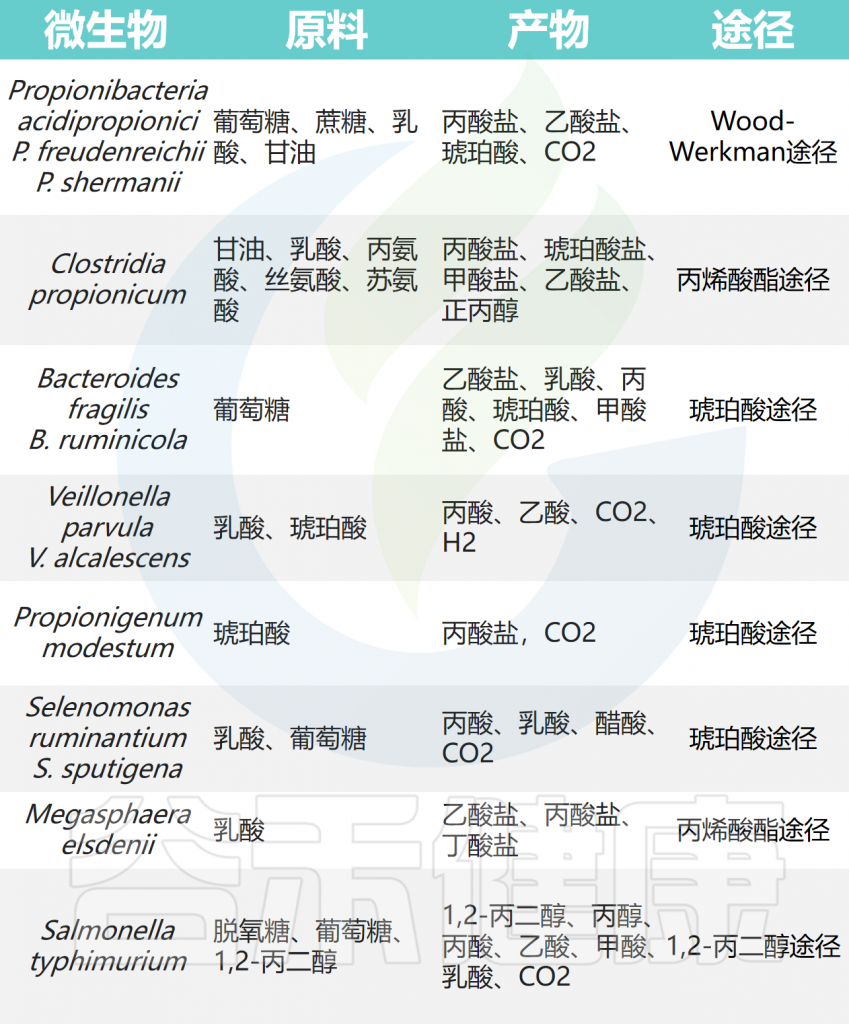
doi.org/10.3390/fermentation3020021
▸
丙二醇相关途径
• 鼠伤寒沙门氏菌和Roseburia inulinivorans在这一过程可以产生丙酸
丙酸盐在肠胃中的生成是由1,2-丙二醇(PDO)发酵菌和PDO消耗菌组成的微生物联合作用的结果。已知一些生物体(如鼠伤寒沙门氏菌和Roseburia inulinivorans)能同时进行这两种过程。
在二醇脱水酶和两种常与乙酸代谢相关的混杂酶(辅酶A依赖性醛脱氢酶磷酸转酰基酶和乙酸激酶)的共同作用下,PDO分解代谢为丙酸,同时生成一个ATP和一个还原辅因子。
然而,通过该途径产生丙酸取决于可用于其他细菌生长的碳水化合物,据报道岩藻糖和鼠李糖是丙酸的前体。
通过1,2-丙二醇形成丙酸的微生物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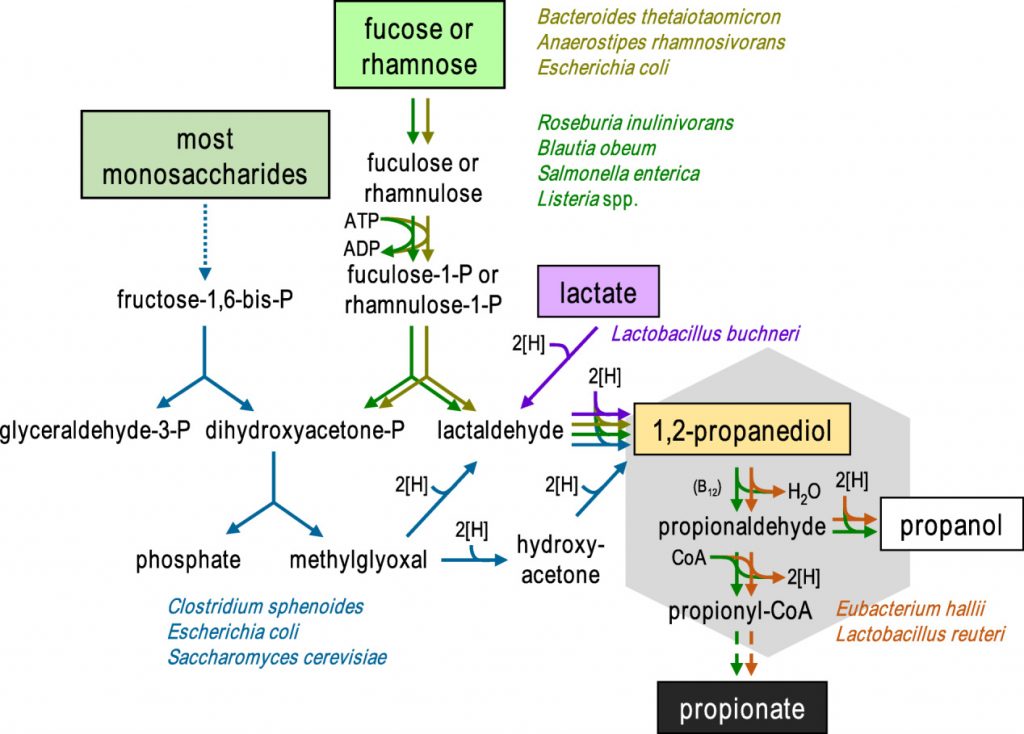
doi: 10.1111/1462-2920.13589.
霍氏大肠杆菌(E.hallii)和罗伊氏乳杆菌(Lactobacillus reuteri)虽然无法在岩藻糖或鼠李糖上生长,但仍然能够利用1,2-丙二醇产生丙酸和丙醇。此外,宏基因组研究表明,其他肠道厌氧菌,包括Flavonifractor plautii、Intestinimonas butyriproducens和Veillonella spp. 也可能能够从这种底物中产生丙酸。因此,不同细菌之间中间体 1,2-丙二醇可能在脱氧糖生产丙酸中发挥重要作用。
▸ 丙烯酸酯途径
丙烯酸酯途径在消耗NADH的情况下,使乳酸在ATP中性条件下转化为丙酸。该途径存在于几种细菌中,包括丙酸梭菌(Clostridium propionicum)、埃氏巨球菌(Megasphaera elsdenii)和瘤胃普氏菌(Prevotella ruminicola)。
虽然多种底物可以分解为丙酸和乙酸,包括乳酸、丝氨酸、丙氨酸和乙醇,但葡萄糖发酵在这过程中似乎不会导致任何天然生产者产生丙酸,这可能是因为葡萄糖发酵不会触发启动循环所需的乳酸消旋酶的表达。
▸ 琥珀酸途径
琥珀酸途径主要存在于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中,拟杆菌门的一些细菌从膳食碳水化合物生成丙酸,并且拟杆菌门的相对丰度与人类粪便中丙酸盐的相对水平相关。
• 琥珀酸转化为丙酸盐还需要维生素B12
琥珀酸是丙酸的前体,但在高pCO2(二氧化碳分压)和高稀释率等条件下,它可在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受到抑制的拟杆菌属培养物中积累。琥珀酸转化为丙酸还需要维生素B12,如果缺乏B12,琥珀酸可能无法转化成丙酸盐。
人类结肠中的一些厚壁菌门细菌(例如Phascolarctobacterium succinatutens)能将琥珀酸转化为丙酸;其他革兰氏阴性菌通过琥珀酸途径(如韦荣氏球菌属)或丙烯酸酯途径(Megasphaera elsdenii)将乳酸转化为丙酸盐。
▸ 氨基酸降解产生丙酸
缬氨酸、苏氨酸、异亮氨酸和蛋氨酸的降解可导致通过丙酰辅酶A产生丙酸和ATP。
由于氨基酸的合成和随后的分解代谢途径存在于多种微生物中,因此可以使用氨基酸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途径的组合从葡萄糖生产丙酸。
几种拟杆菌在蛋白水解和肽形成丙酸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苏氨酸的产生和分解代谢已在大肠杆菌中得到广泛研究,作为丙酰辅酶A的可能来源,可用于生产各种化学物质,包括丙醇、红霉素和3-羟基戊酸。此外,考虑到氧化还原和能量平衡,缬氨酸/异亮氨酸和苏氨酸途径的组合具有协同作用,可以略微提高丙酸产量。
除此之外,可以利用丙酮酸经过柠檬酸途径产生丙酸,由于和菌群关联较小,在这就不展开描述了。
▸ 增加丙酸盐生成的底物
一些益生元等化合物可以影响丙酸盐的生产,不过由于浓度以及肠道微生物群落构成的不同,这些化合物的调节丙酸盐产生时具有一定差异。
• L-鼠李糖能够明显增加丙酸盐产量
L-鼠李糖或6-脱氧-L-甘露糖是一种天然脱氧糖。它存在于多种动物、植物和细菌多糖中。在短期体外实验中,L-鼠李糖已被证明能使丙酸产量增加四倍于乳果糖。
在一项人体体内研究中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其中受试者在三个不同的时间被给予25克L-鼠李糖、乳果糖或D-葡萄糖。摄入后24小时测量血清丙酸,L-鼠李糖的血清丙酸明显高于乳果糖或D-葡萄糖的血清丙酸。
一项长期研究也证实了L-鼠李糖诱导丙酸的作用,该研究结果表明,与摄入D-葡萄糖作为对照相比,摄入25克L-鼠李糖可显著提高人体28天内的血清丙酸水平。
• 抗性淀粉有助于增加丙酸
抗性淀粉对淀粉酶降解具有抗性,但它会发酵成丁酸或丙酸。特别是,来自大米的抗性淀粉与丙酸产量增加有关。
研究了抗性淀粉在大鼠体内的发酵情况,饲喂抗性淀粉(630g/kg饲料)的大鼠的肝脏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与此同时,血清丙酸浓度也显著增加。
• 菊粉对于增加丙酸和丁酸非常有效
菊粉属于果聚糖家族,主要由β-(2,1)连接的果糖基组成。它天然存在于菊苣和菊芋等开花植物中。作为益生元,菊粉已被证明对增加丁酸和丙酸的产量非常有效。使用人体肠道微生物体外模拟研究了菊粉增加丙酸的效果。
补充菊粉1周(5g/d)后观察到短链脂肪酸产生的代谢变化。较高浓度的短链脂肪酸源于丙酸和丁酸产量的增加。
此外一项针对喂食菊粉(10%)的大鼠的体内研究也导致丙酸产量大幅增加,高达 58.4mmol/。
• 聚葡萄糖
聚葡萄糖是一种支链、随机聚合的多糖,主要由葡萄糖合成,在胃肠道上部不会被消化。使用结肠模拟器研究了这种底物对结肠微生物组成和代谢活性的调节作用。与对照糖木糖醇(8.3mmol/L)相比,短链脂肪酸产量显著增加,尤其是丙酸盐(22.9mmol/L)。
• 阿拉伯木聚糖
阿拉伯木聚糖是许多谷物中发现的主要非淀粉多糖,是膳食纤维的一部分。
在体内研究中,比较了54只大鼠,这些大鼠分别喂食对照饮食(含710g/kg小麦)、阿拉伯木聚糖补充饮食(610g/kg小麦淀粉加100g/kg玉米阿拉伯木聚糖)和胆固醇补充饮食(不含或含2g/kg 胆固醇)。由于短链脂肪酸的积累,尤其是丙酸(摩尔百分比>45%),盲肠pH值从7降至6。然而,丁酸的产生不受影响。
车前草是一种可溶性纤维来源,可提供与麦麸阿拉伯木聚糖相当的多糖。在一项大鼠体内研究中,比较了车前草(5%)对盲肠和结肠发酵的影响与麦麸 (10%) 的影响。研究发现,车前草发酵可产生更高的短链脂肪酸,尤其是盲肠和所有结肠中的丙酸更多。
除此之外,D-塔格糖、甘露寡糖、昆布多糖等物质也可以增加人体丙酸盐的产生。
丙酸盐已被证明具有抗脂肪形成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它还对体重控制和进食行为有很强的影响。此外,有研究表明,丙酸和丁酸一样,对结肠癌细胞具有抗增殖作用。
丙酸盐对健康的影响

doi: 10.1111/j.1753-4887.
然而,与结肠细胞用作能量来源的丁酸不同,丙酸在血液循环中的浓度较高。因此,丙酸的生物活性可能不仅限于结肠本身,还扩展到人体的其他部位。需要强调的是,了解体内结肠丙酸浓度或短链脂肪酸浓度不足以推断健康状况。
▸ 影响肝细胞的脂质合成
肝脏的脂质合成包括将饮食来源的脂肪酸和甘油转化为具有不同脂肪酸组成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然后,这些肝脏脂质分子被结合到脂蛋白中,从而通过循环分布到各种组织中。
• 脂质合成受到短链脂肪酸的强烈影响
有趣的是,肝细胞中的脂质合成受到肠道纤维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的数量和类型的强烈影响。丙酸盐已被确定在其中一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肝脏脂质合成的饮食调节早期观察显示,膳食纤维摄入与肝脏脂质合成密切相关。这种影响的部分原因如下:1)粪便中胆固醇和胆汁酸从肠道排出的增加;2)胆固醇向胆汁酸的肝脏转化率较高;3)通过减少乳糜微粒的大小和降低胆固醇在乳糜微粒中的掺入来优化脂蛋白的外周代谢。
• 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抑制脂肪酸合成
短链脂肪酸作为微生物碳水化合物发酵的产物,在肝脏脂质合成中发挥着特定作用,已被证明在喂食大鼠时可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对分离的大鼠肝细胞的体外研究表明,丙酸对脂肪酸合成有抑制作用,但对胆固醇合成没有抑制作用。
其他大鼠实验表明,加入纤维的饮食可降低肝和血浆胆固醇水平及血浆甘油三酯中的胆固醇,而肝甘油三酯没有受到影响。
尽管这些研究的结果令人信服,但其他研究并不总是能够证实丙酸盐对脂质代谢的抑制作用。例如,每天在面包中补充9.9克丙酸盐不会改变6名健康志愿者的脂质代谢,甚至会导致5名受试者的甘油三酯浓度升高。
在另一项研究中,比较了丙酸盐对人和大鼠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影响。发现浓度为0.1mmol/L的丙酸盐对大鼠乙酸盐合成脂质有抑制作用。然而,在人类肝细胞中,需要更高浓度的丙酸盐(约10-20 mmol/L)才能获得同样的抑制作用。该值比门静脉血中丙酸盐的浓度高100-200倍,表明大鼠模型不能完全外推到人类的情况。
▸ 作为影响饱腹感的分子
丙酸盐不仅具有降低胆固醇和抗脂肪生成的作用,还可能通过刺激饱腹感来控制体重。已有研究表明,短链脂肪酸(如乙酸、丙酸、丁酸)具有诱发饱腹感的作用。
• 丙酸盐影响肠道激素的形成进而影响饱腹感
现有证据表明,细菌调节肠道激素(如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肽YY(PYY))的形成,是通过短链脂肪酸介导的。乙酸、丙酸和丁酸的生理浓度,以及pH值从7.5降至6.0,会显著增加肠内分泌结肠细胞系STC-1中的胰高血糖素原和PYY。
GLP-1和PYY是刺激饱腹感的激素,由L细胞(主要位于回肠和结肠)响应营养摄入而释放。GLP-1促进胰岛素分泌和胰腺β细胞增殖,同时控制肌肉细胞中的糖原合成;而PYY则减缓胃排空。相反,生长素释放肽刺激食欲,主要由胃中的P/D1细胞产生。
不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如低聚果糖、乳糖醇和抗性淀粉,通过调节肠道肽GLP-1、PYY和生长素释放肽的产生,有效地诱导饱腹感,这一机制还涉及肠道微生物群落。
• 丙酸盐对摄食行为有显著影响,诱导瘦素产生
在短链脂肪酸中,丙酸盐被重点研究作为一种饱腹感诱导剂,对能量摄入和摄食行为有显著影响。人体和动物试验表明,丙酸盐给药(体内范围为130-930mmol/L,体外范围为0.01-10mmol/L)显著增强饱腹感并降低进食欲望。
丙酸盐触发的饱腹感信号之一是瘦素,这是一种强效的厌食激素,通过中枢神经系统中表达的受体抑制食物摄入。研究显示,每天服用500µmol的丙酸盐几乎使小鼠血浆中的瘦素浓度翻了一倍。
在另一项研究中,浓度为3mmol/L的丙酸在mRNA和蛋白质水平上诱导了人内脏脂肪组织中瘦素的产生。这些数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对肥胖的调节作用可能部分由短链脂肪酸(特别是来自微生物碳水化合物发酵的丙酸)介导。
▸ 影响心脑血管健康
丙酸盐通过与肠道受体GPR 41和GPR 43(也称为脂肪酸受体FFAR2和FFAR3)相互作用,对心脑血管健康具有一些潜在的影响。
• 脑血管患者体内的丙酸盐含量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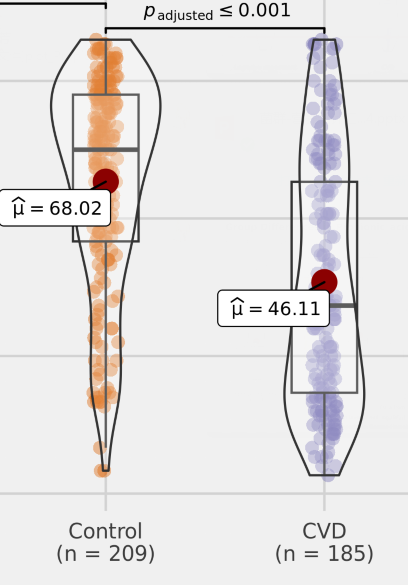
编辑
谷禾的数据中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脑血管疾病患者中的丙酸盐含量较低,并且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因此丙酸盐的含量可能是影响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
• 较高的丙酸盐浓度患冠状动脉硬化风险较低
最近一项大型横断面研究表明血浆丙酸浓度与冠状动脉疾病存在关联,较高浓度的丙酸盐与较低的冠状动脉粥样硬(CAD)风险相关,且与已知的心血管风险因素无关。
如上所述,越来越多的实验数据表明,丙酸盐可能对高血压、内皮功能障碍和高胆固醇血症等心血管风险因素产生有益影响。
▸ 丙酸盐在癌症中的潜在作用
短链脂肪酸对癌症(尤其是结肠癌)的影响已被广泛研究。丁酸能够调节基因表达,并对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的关键调节因子产生影响。
几种机制促成了丁酸对基因表达的调节作用。这些机制包括组蛋白和非组蛋白的过度乙酰化以及DNA甲基化的改变,从而增强了转录因子对核小体DNA的可及性。
• 丙酸盐诱导结直肠癌细胞凋亡
在一项研究中,丙酸盐和乙酸盐(浓度分别为26-40和9-16mmol/L)在人类结直肠癌细胞系中诱导了典型的细胞凋亡迹象。这些迹象包括线粒体跨膜电位的丧失、活性氧的产生、胱天蛋白酶3加工和核染色质凝聚。
• 抑制结肠癌细胞系的生长
短链脂肪酸对结肠上皮细胞增殖具有矛盾作用。虽然这些阴离子刺激正常隐窝细胞,但它们抑制结肠癌细胞系的生长。
丁酸盐和丙酸盐也是诱导分化和细胞凋亡的最有效脂肪酸。因此,它们通常可以预防癌症的发展,尤其是预防结直肠癌。虽然丁酸比丙酸更有效,但它主要被结肠细胞吸收作为能量来源。相比之下,丙酸和乙酸盐进入血液循环的浓度比丁酸高得多,并且它们被肝脏大量吸收(约60%)。由于这些阴离子在肝脏中的浓度很高,它们很可能会影响肝癌细胞以及已知会导致肝脏转移的其他典型癌细胞,例如乳腺癌和结肠癌。
一项针对猝死患者的研究表明,外周血中的短链脂肪酸数量可以量化。因此,这种循环中的丙酸盐、乙酸盐和丁酸盐的抗癌作用非常值得研究;例如,这种影响会在多大程度上延伸到小肠、大肠和肝脏之外,从而影响不同的组织?
!
• 丙酸盐过量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
最近的几项研究提供了丙酸盐与阿尔茨海默病(AD)之间联系的证据。例如,分析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唾液样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丙酸水平比健康对照者高出1.35倍。分析了轻度认知障碍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唾液样本,也发现AD患者的丙酸水平显著升高。
几项啮齿动物研究也将粪便和循环中丙酸盐水平与阿尔茨海默病联系起来。接受AD患者粪便微生物群移植的小鼠丙酸水平高于对照组。
此外,发现阿尔茨海默病小鼠海马体中的丙酸增加了1.23倍。也发现阿尔茨海默病小鼠前额叶皮层中的丙酸浓度显著高于野生型小鼠,6个月大的阿尔茨海默病小鼠粪便中的丙酸浓度也显著更高。
• 丙酸血症的丙酸盐代谢异常
丙酸血症是人类最常见的有机酸代谢紊乱,是一种由丙酰辅酶A羧化酶基因缺陷引起的先天性代谢错误,丙酸过量且无法通过丙酰辅酶A转化。
丙酸血症患者的体内丙酸及其代谢物水平显著升高,会引起代谢性酸中毒、血氨升高,可能还会诱导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如脑损伤、心肌病发生。
•有研究认为过多的丙酸盐可能导致肥胖和糖尿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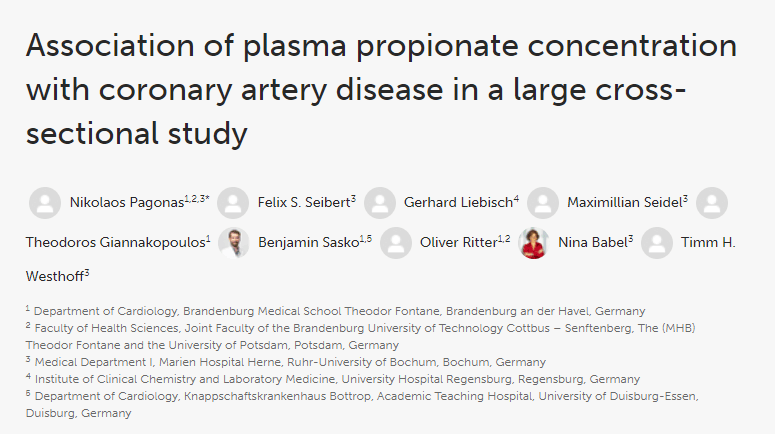
2019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篇文献称:小鼠长期接触丙酸将导致肝细胞产生更多葡萄糖,形成高血糖症,这是糖尿病的一个典型特征。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长期服用丙酸盐剂量的小鼠,其体重会显著增加,胰岛素抗性也会增大。
还对14名健康人开展对照试验,受试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的餐食中添加1克丙酸盐,另一组添加安慰剂。结果显示,进餐后不久,丙酸盐组受试者血液中的去甲肾上腺素水平显著升高,胰高血糖素等激素水平也有所增长。这表明丙酸盐可能会作为“代谢破坏者”,增加人类患糖尿病和肥胖症的风险。
而这与前文丙酸盐会影响脂质合成与摄食行为相矛盾,因此,丙酸盐对人体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其含量以及人体独特的肠道菌群结构与代谢能力。
内源性丙酸盐与外源性丙酸盐存在区别
内源性丙酸:指的是人体内部产生的丙酸,通常情况下,人体中的微生物能够在结肠中通过发酵未完全消化的碳水化合物来产生丙酸,这些丙酸对人体是有益的。
外源性丙酸:指的是从外部来源摄入的丙酸,比如通过食物摄入或作为补充剂。以及在一些药物中也可能含有丙酸盐。
★ 外源性丙酸盐摄入过多对代谢健康有害
但已经有各种研究表明,外源性地摄入和自体产生的丙酸作用并不一样,外来的丙酸对个体的许多代谢过程有不利影响。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完成了一项实验,发现从食品中摄入的丙酸在短期内会导致高血糖、胰岛素偏高,而且长期摄入将会造成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等更严重的症状。
我们通过口腔摄入含丙酸添加剂的食物后,会激活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并促使体内胰高血糖素和脂肪酸结合蛋白4等激素的升高。受到激素影响,肝糖原持续分解,血糖升高。身体开始分泌更多胰岛素进行代偿降低血糖浓度,最终导致胰岛素抵抗和肥胖产生。
这项研究表明,自身产生的丙酸和外界摄入的丙酸具有不同的功能,我们推测,这是因为从食物中摄入会极大地增加细胞和丙酸的接触,而细菌产生的仅仅只会局限在结肠部分。
在人体肠道中,丁酸由膳食纤维经细菌发酵产生,通过两种代谢途径。在第一条途径中,丁酰辅酶A被磷酸化形成丁酰磷酸,并通过丁酸激酶转化为丁酸。在第二条途径中,丁酰辅酶A的辅酶A部分通过丁酰辅酶A:乙酸辅酶A转移酶转移到乙酸盐,从而形成丁酸和乙酰辅酶A。其中丁酰辅酶A:乙酸辅酶A转移酶途径占主导地位。
对人类粪便微生物群的放射性同位素分析也表明,肠道中的大多数丁酸盐是由碳水化合物通过Embden-Meyerhof-Parnas(糖酵解途径)由乙酰辅酶A产生的。
• 少量的丁酸盐也可由蛋白质合成
除了碳水化合物,少量的丁酸也可以通过谷氨酸、赖氨酸、戊二酸和γ-氨基丁酸途径由蛋白质合成。厚壁菌种也对氨基酸表现出高活性,特别是肠单胞菌(Intestinimonas AF211),它通过不同的途径将葡萄糖和赖氨酸发酵成丁酸。
形成丁酸盐的微生物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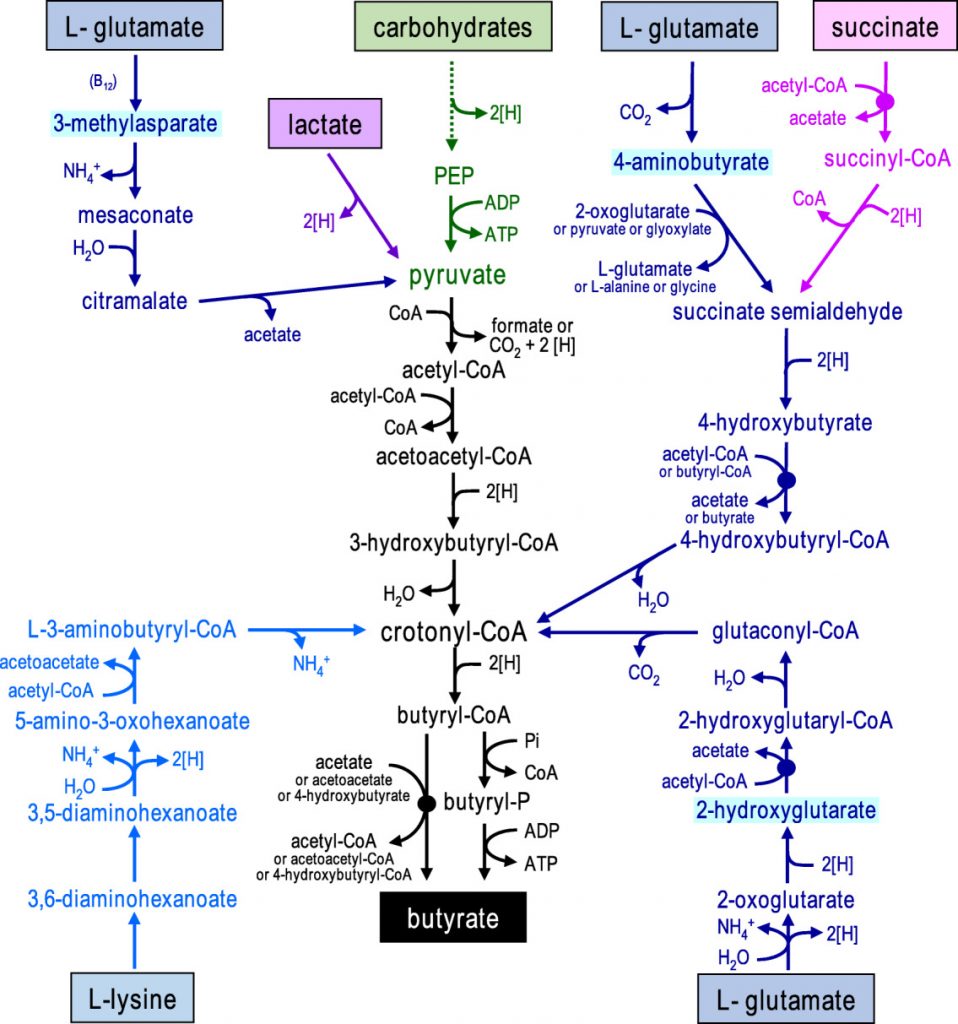
doi: 10.1111/1462-2920.13589.
碳水化合物通过糖酵解发酵为丙酮酸显示为绿色,从乙酰辅酶A形成丁酸盐显示为黑色,氨基酸发酵途径显示为蓝色(以中间体命名不同的谷氨酸途径),乳酸和琥珀酸发酵分别显示为紫色和粉色。
• 人结肠中的瘤胃球菌和毛螺菌是产丁酸的主力
除食源性丁酸,人体内丁酸主要是由盲肠和结肠的厌氧型细菌发酵产生,而由胃和小肠产生的丁酸含量极低。大肠产丁酸的菌种主要是梭菌属XIVa和IV族,以及真杆菌属和梭杆菌属
盲肠和结肠中丁酸的产生速度和数量主要取决于肠道微生物组成、日常膳食中可利用发酵成分组成等。在人的结肠中,厚壁菌门中的瘤胃球菌科(Ruminococcaceae)和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这两个主要科,以及包括丹毒丝菌科(Erysipelotrichaceae)和梭菌科(Clostridiaceae)在内的其他厚壁菌门物种,都发现了丁酸生产菌种与非生产菌种的交替存在。
但应注意,许多人类结肠的主要厚壁菌门(例如Blautia spp.、Eubacterium eligens、Ruminococcus spp.)缺乏从碳水化合物中生成丁酸的能力。
产生丁酸盐的细菌被认为在生命的第一年内定植于宿主,并且在成年时占总细菌群落的20%以上。在消化道中发现的已知丁酸盐生产者中,大多数似乎属于毛螺菌科和瘤胃球菌科。我们将简要介绍两个丁酸生产菌。
▸ 普拉梭菌
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是健康人类微生物群中最丰富的菌种之一,也是主要的丁酸盐生产者之一。它通过丁酰辅酶A:乙酸辅酶A转移酶产生丁酸,并消耗乙酸。
虽然F.prausnitzii菌株是专性厌氧菌,但在核黄素(维生素B2)和还原性化合物(如半胱氨酸或谷胱甘肽)存在的情况下,低浓度氧气也能促进其生长。
氧气消耗会伴随丁酸形成的减少。F. prausnitzii分离株在利用食物多糖(如淀粉和半纤维素)生长方面能力有限,但一些菌株可以利用菊粉和果胶衍生物,并且普遍利用糖醛酸。
• 肠道炎症患者产生丁酸会减少
F. prausnitzii在炎症性肠病患者中很少见,尤其是克罗恩病,有证据表明它具有抗炎作用,因此引起了人们对其作为潜在治疗药物的兴趣。同样,据报道,Butyricicoccus pullicaecorum在炎症性肠病患者中较少见,并且也可能具有治疗潜力。
注:其他瘤胃球菌科细菌也能产生丁酸,但人们对大多数此类生物知之甚少。关于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详见:肠道核心菌属——普拉梭菌(F. Prausnitzii),预防炎症的下一代益生菌
▸ 毛螺菌科
直肠真杆菌(Eubacterium rectale)和密切相关的罗氏菌属(Roseburia)构成了产丁酸毛螺菌科的主要群体,它们具有相同的丁酰辅酶 A:乙酸辅酶 A 转移酶途径来生产丁酸,并且其丁酸合成基因的基因组组织也相同,从乙酰辅酶A到丁酰辅酶A。
• 罗氏菌属通过代谢饮食多糖产生丁酸
在某些Roseburia菌株中,特别是在弱酸性pH值下,丁酸几乎是唯一产生的发酵酸,乙酸的净消耗通常伴随着丁酸的形成。一些其他菌株和物种除了产生丁酸外,还产生甲酸和乳酸。基因组分析表明,该群体具有相当大的利用饮食来源的多糖的能力,包括淀粉、阿拉伯木聚糖和菊粉,不同菌株和物种之间的差异很大。
其他拥有丁酰辅酶A:乙酸辅酶A转移酶基因的毛螺菌科包括Eubacterium hallii、Anaerostipes hadrus、Coprococcus catus、与分离株SS3/4和M62/1有关的未鉴定物种。
• 一些毛螺菌科细菌利用乳酸和乙酸来产生丁酸
某些毛螺菌科能够在乳酸和乙酸盐存在下生长并产生丁酸,其总净化学计量为4mol乳酸和2mol乙酸盐产生3mol丁酸 。
这包括仅使用D-乳酸的物种Anaerostipes hadrus和能够利用两种乳酸异构体的E. hallii。
此外,双歧杆菌等常见益生菌配方中的微生物与丁酸盐生产者之间的交叉喂养相互作用已被证明是可以产丁酸盐的。
人体肠道中的主要丁酸生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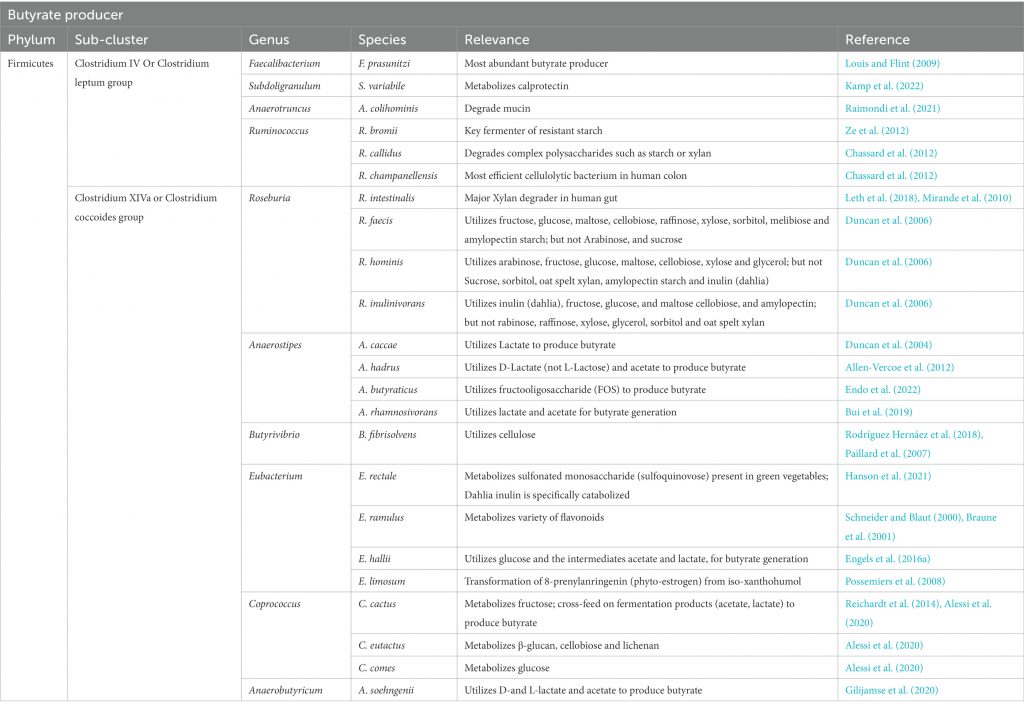
doi: 10.3389/fmicb.2022.1103836.
▸ 增加丁酸盐生成的食物
饮食对人体微生物群有显著影响,通过饮食干预可显著改变细菌数量并增加微生物多样性。富含纤维的饮食对丁酸盐的产生特别有益,因为它可以滋养产生丁酸盐的细菌。
• 高纤维饮食能够有效增加丁酸盐的生成
蔬菜、水果、豆类和全谷物,它们含有膳食纤维,可被肠道细菌发酵成丁酸盐等有机化合物。通过食物增强微生物群是促进消化系统健康和丁酸盐生成的有效且安全的方法。因此,增加丁酸盐产量的最佳方法是通过高纤维饮食。
• 高脂、低纤维饮食不利于丁酸盐的生成
高蛋白、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已被证明会破坏微生物组中丁酸盐的产生。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短期饮食限制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肥胖参与者的微生物组,从而限制了他们对植物性膳食纤维的消耗。
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每天24克)和中等碳水化合物饮食(每天164克)4 周后,短链脂肪酸的浓度低于高碳水化合物饮食(每天399克)。具体来说,当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减少时,丁酸盐浓度会降低。
同时还发现,厚壁菌门细菌Roseburia和E.Rectale的密度与丁酸盐浓度之间存在联系,两者都随着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减少而降低。
一些食源性物质产生短链脂肪酸的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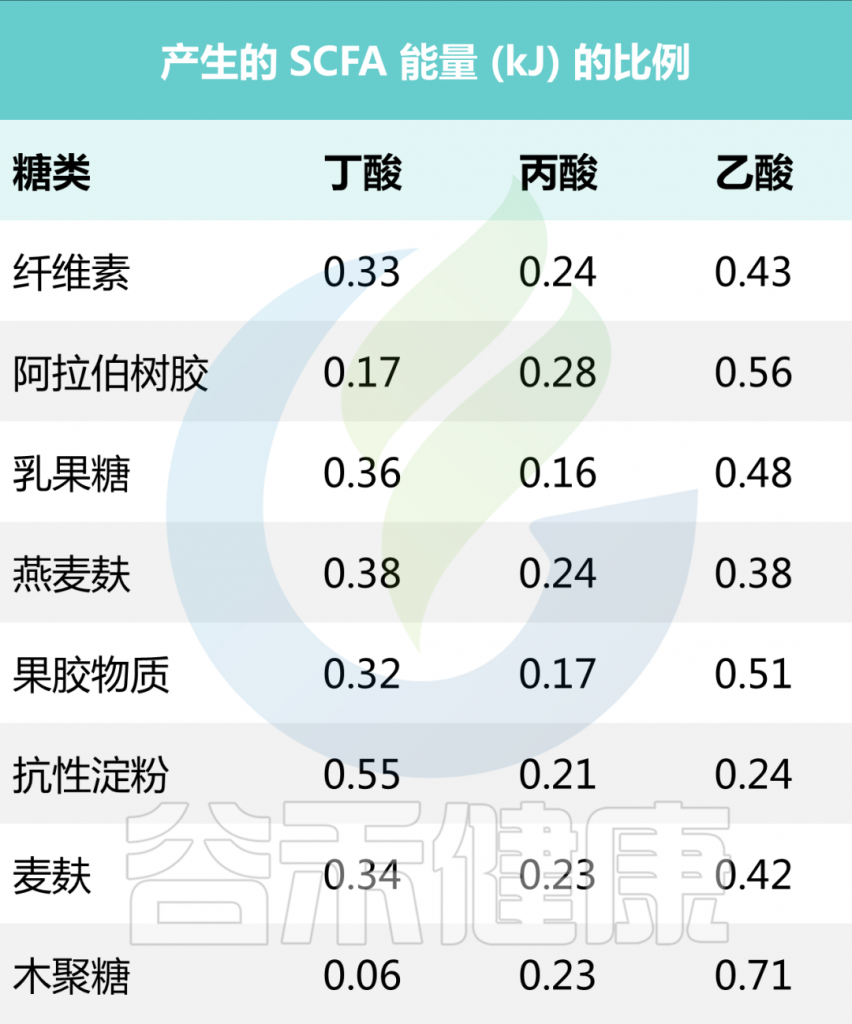
• 抗性淀粉
研究表明,从生马铃薯、高直链淀粉玉米和全谷物中提取的阿拉伯木聚糖中,含有高含量2型抗性淀粉的食物显著增加了丁酸盐的产量。
在174名健康年轻人的饮食中添加马铃薯抗性淀粉后,丁酸盐产量增加。玉米、菊苣和玉米中的抗性淀粉也进行了测试,但只有当食用土豆中的抗性淀粉时,粪便中的丁酸总量才会显著增加。
• 果聚糖(菊粉)
许多研究表明,菊粉可以增加短链脂肪酸的产量,包括丁酸盐。这可能解释了香蕉在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患者的饮食中如此有效的原因之一。然而,链长较短的果聚糖通常比链长的果聚糖(如菊粉)更容易喂养产丁酸菌。
也就说,抗性淀粉和果聚糖(短链低聚果糖和长链菊粉)在肠道中发酵时会产生丁酸盐。
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全麦面包、燕麦、大麦和糙米等全谷物;黑豆、红豆、绿豆等豆类;马铃薯、玉米、菊苣根、牛蒡根、魔芋根、亚麻籽。
富含果聚糖的食物:洋葱、菊苣、香蕉、朝鲜蓟、芦笋、大蒜、韭菜、西兰花、开心果。
需要注意的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常驻微生物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它们消化某些底物的能力不同,因此比较明智的选择是食用包含多种抗性淀粉和果聚糖的饮食。例如以马铃薯抗性淀粉、燕麦麸皮纤维或车前草种子或短链低聚半乳糖、长链低聚果糖和谷氨酰胺的混合物的形式短期补充,增加丁酸盐水平。
丁酸盐作为一种重要的的调节因子,是宿主-微生物串扰的关键介体。丁酸盐在体内可以通过脂肪酸氧化为机体供应能量,是肠道上皮细胞的主要供能物质。
丁酸盐还与机体健康密切相关,对调节肠道健康、修复肠道屏障、抑制炎症及癌症等病症意义重大。在养殖业中常添加丁酸盐保护动物健康生长,如预防断奶仔猪腹泻、调节鸡肠道菌群并增强其免疫力等。
▸ 为肠道细胞提供能量
丁酸盐是结肠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结肠细胞是构成肠道内壁的细胞。
与身体中使用糖(葡萄糖)作为主要能量来源的大多数其他细胞不同,肠道内壁细胞(结肠细胞)主要使用丁酸盐。如果没有丁酸盐,这些细胞就无法正确执行其功能。
• 丁酸盐为结肠细胞提供能量,细胞利于产丁酸盐细菌的生长
厚壁菌属的成员以产生丁酸盐而闻名,像Roseburia,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直肠真杆菌(E.rectale)等。
这种关系是相互的。丁酸盐为结肠细胞提供燃料,作为回报,这些细胞有助于提供一个无氧环境,有益的肠道微生物在其中茁壮成长。这可以控制炎症,保持肠道细胞健康,并使肠道细菌保持健康。
▸ 促进肠道运动
实验研究表明,丁酸盐通过作为短链脂肪酸受体的配体和激活剂,诱导肠道激素肽YY或介导肠嗜铬细胞释放5-羟色胺来促进肠道运动。
丁酸盐还可以通过上调Na+—H+交换器和诱导ATPase离子交换器基因来增强水和电解质的吸收。并且可能有益于预防某些类型的腹泻。
▸ 抗炎、抗癌特性
丁酸盐对肠道具有抗炎和抗癌功能。
肠道内壁会保持低水平的炎症,以防与微生物群接触的粘膜表面发生任何变化。低水平的炎症受到严格控制,但如果它被破坏,会导致氧化损伤,并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导致癌症。
• 丁酸盐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
丁酸盐会阻止体内的一些促炎物质发挥作用。丁酸盐的抗炎作用可减少氧化应激并控制自由基造成的损害。
丁酸盐的抗炎特性,部分原因是其抑制核转录因子(NF-κB)的激活,通过下调NF-κB信号通路,丁酸盐可以调节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
• 丁酸盐阻止结肠癌细胞的生长
丁酸盐也是一种组蛋白脱乙酰酶(HDAC)抑制剂。组蛋白脱乙酰酶是大多数癌症中产生的酶。因为丁酸盐是一种抑制剂,它实际上会改变基因表达,抑制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分化或凋亡。因此,它可以阻止癌细胞的发展。
有证据表明,结直肠癌(CRC)患者的微生物组图显示主要产丁酸菌属减少,包括罗氏菌属(Roseburia)、Clostridiales、Faecalibacterium和Lachnospiraceae科成员,而使用产丁酸的丁酸梭菌可有效减少癌细胞增殖并增强癌细胞凋亡。
▸ 修复肠道屏障,防止肠漏
肠上皮细胞的屏障功能是重要的第一道防线,确保上皮层具有适当的通透性。研究发现丁酸盐能够修复和增强肠上皮细胞的屏障功能。
• 丁酸盐上调粘蛋白的表达,增强粘液屏障
最新研究表明,丁酸对肠屏障功能具有保护作用。例如,丁酸能够上调粘蛋白2(MUC2)的表达。粘蛋白2是肠粘膜表面主要的粘蛋白,可增强粘膜层,从而限制有害物质通过肠道。
• 丁酸盐对肠道屏障的影响可能具有浓度依赖性
此外,丁酸还能增加三叶因子(TFF)的表达,这是一种粘蛋白相关肽,有助于维持和修复肠粘膜。丁酸还调节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以降低细胞旁通透性。其中一种机制是通过激活单分子层中的AMP活化蛋白激酶。
体外模型研究表明,丁酸对肠道屏障功能的影响可能具有浓度依赖性。丁酸在低浓度(≤2 mM)时可促进肠道屏障功能,但在高浓度(5或8 mM)时可能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来破坏肠道屏障功能。
根据哺乳动物胃肠道中的生理浓度,目前体外模型中推荐使用的丁酸浓度为0-8mM。然而,考虑到大多数丁酸在结肠上皮中被代谢为能量底物,体内和体外模型中治疗剂量可能存在差异。
▸ 抗氧化能力
说起抗氧化,我们先了解一下自由基。它基本上是体内化学反应产生的废物。另一方面,抗氧化剂是身体抵御它们的防御措施。大量自由基会造成损害并压倒身体的修复系统。我们称之为氧化应激。氧化应激被认为是导致衰老和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 丁酸盐增加谷胱甘肽,可以中和自由基
结肠或大肠是身体产生的废物的储存容器。较高的丁酸盐水平已被证明会增加谷胱甘肽的水平,谷胱甘肽是一种在人体细胞中产生的抗氧化剂,可以中和肠道中的自由基(自由基与炎症和许多疾病有关),从而起到抗氧化作用。
▸ 调节肠道免疫
• 维持厌氧环境,阻止有害菌生长
丁酸通过增强结肠细胞的氧消耗和稳定缺氧诱导因子(HIF)来维持结肠内的厌氧环境,而丁酸的缺失则会促进潜在有害细菌和分子的积聚,例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和一氧化氮(NO)。
肠道中丁酸水平降低,这促进了肠道上皮氧合和鼠伤寒沙门氏菌(S.Typhimurium)的生长,鼠伤寒沙门氏菌是食源性肠道炎症和腹泻的已知病因。
• 影响免疫细胞迁移、粘附
除了营造无氧环境外,短链脂肪酸,尤其是丁酸盐,还可以作为免疫细胞趋化和粘附的调节剂。丁酸可以调节肠上皮细胞介导的中性粒细胞向炎症部位的迁移,并且这种作用是浓度依赖性的。
此外,丁酸在细胞增殖和凋亡中发挥作用。丁酸刺激细胞生长和DNA合成,并诱导细胞周期G1期的生长停滞。虽然低浓度的丁酸会增强细胞增殖,但高浓度的丁酸会诱导细胞凋亡。
丁酸盐等短链脂肪酸可以在先天反应过程中通过影响巨噬细胞和粒细胞以及树突状细胞的抗原呈递发生,也可能在适应性免疫反应过程中通过影响T细胞和B细胞功能发生。
短链脂肪酸的免疫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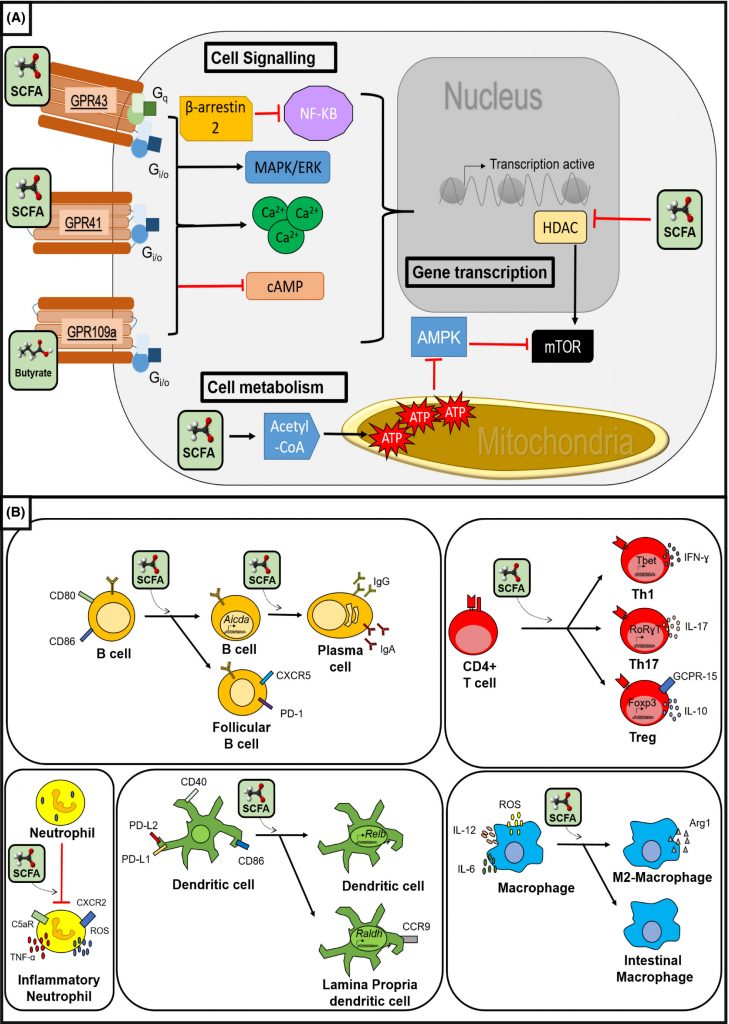
doi: 10.1111/apt.14689.
▸ 影响代谢健康
• 对肥胖存在一定影响,但还不能完全确定
包括丁酸盐在内的短链脂肪酸可通过激活肠细胞内的FFAR来降低食欲和体重。这促进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肽YY的释放,前者促进胰岛素分泌并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后者降低食欲并减缓胃排空。
短链脂肪酸还能减少所谓的“饥饿激素”——胃促生长素(ghrelin)的分泌;FFAR2存在于ghrelin分泌细胞上,包括丁酸盐和丙酸盐在内的FFAR2激动剂可减少ghrelin分泌。
丁酸盐影响脂质代谢的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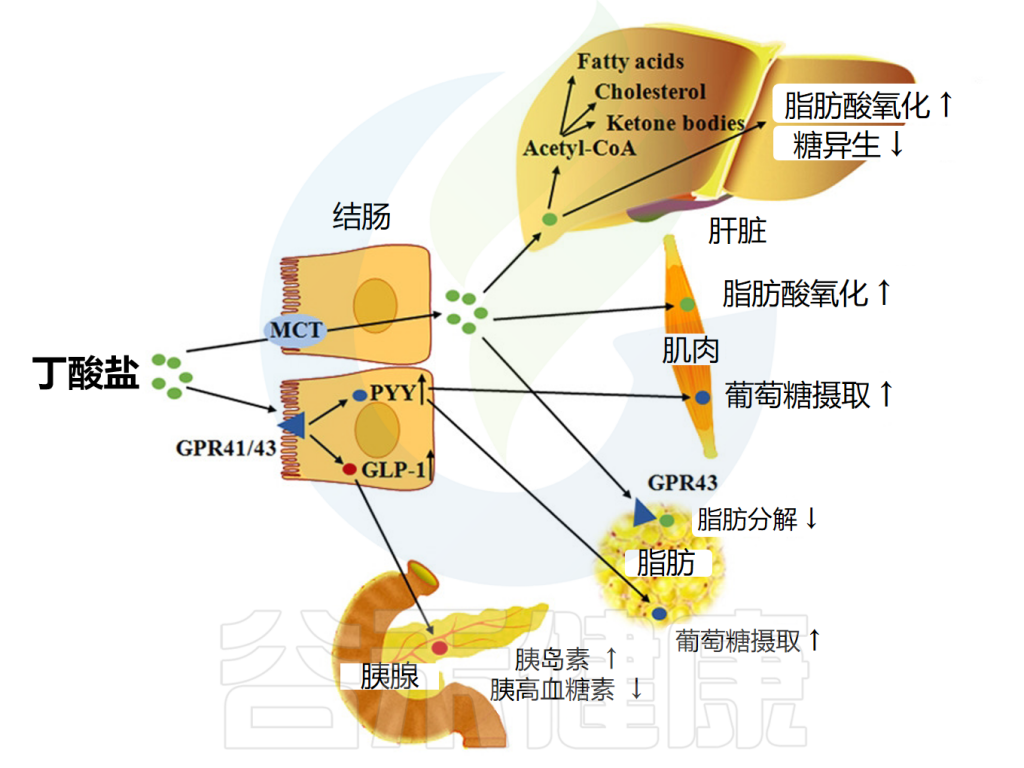
doi: 10.1093/advances/nmx009.
也有证据表明短链脂肪酸作用于交感神经系统,交感神经节中FFAR3的激活导致能量消耗增加。
然而,与丙酸盐一样,关于丁酸盐对食物摄入的影响,有相互矛盾的结果报道。
• 丁酸盐对控制血糖水平可能有潜在好处
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前期受试者中丁酸盐水平降低。
丁酸在肠内分泌细胞(EEC)中与游离脂肪酸受体(FFAR)FFAR2和FFAR3结合,调节肠道激素释放,如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肽YY(PYY)。
丁酸盐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糖代谢的调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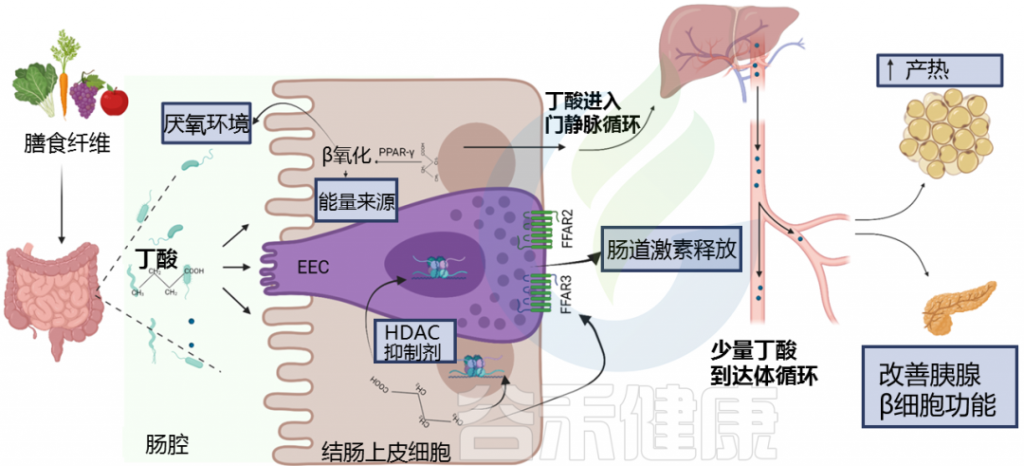
doi: 10.3389/fendo.2021.761834.
这些激素共同作用以保持血糖水平稳定。当血糖过高时,胰岛素会告诉身体的肌肉和脂肪细胞吸收多余的葡萄糖,所以说这些激素对肥胖和糖尿病很重要。丁酸盐增加这些肠道激素的释放,表明对控制血糖水平和防止体重增加有潜在的好处。
!
丁酸盐过低可能会导致以下危害:
•肠道屏障功能受损:丁酸盐有助于维持结肠的“生理性缺氧”,并提供能量给结肠细胞,有助于维持肠道稳态。丁酸盐的减少可能导致肠道屏障功能受损。
•增加慢性疾病风险:变形菌门的兼性厌氧细菌的扩张几乎总是伴随着产丁酸盐细菌丰度的减少,并与许多慢性疾病有关,包括炎症性肠病、肠易激综合症、结直肠癌、2型糖尿病、肥胖等。
•神经炎症:丁酸盐具有抗炎特性,对大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丁酸盐过低可能导致炎症增加,影响大脑健康。
•睡眠问题:丁酸盐可能作为细菌源性促睡眠信号,丁酸盐过低可能影响睡眠,导致睡眠问题。
•肠道菌群失衡:丁酸盐过低可能导致肠道菌群失衡,因为变形菌门的扩张伴随着产丁酸盐细菌的减少。
•不利于肠道损伤修复:在轻微炎症或轻度溃疡部位添加丁酸盐可以促进肠道损伤的修复,而丁酸盐过少可能不利于溃疡的恢复。
!
丁酸盐并不总是越多越好,低浓度丁酸促进细胞增殖和生长,高浓度丁酸反而抑制细胞增殖和生长,增加肠道的通透性。
• 不同部位对丁酸盐的耐受阈值存在差异
胃肠道不同部位对丁酸盐的耐受阈值也存在一定差异,胃和小肠对丁酸的耐受阈值低,结肠和盲肠耐受阈值高。
添加普通丁酸钠制剂(主要在肠道前端被吸收利用),反而造成肠道炎症、菌群失调。
• 肠道严重溃疡时丁酸盐可能加剧症状
更有意思的是,轻微炎症或者轻度溃疡部位添加丁酸盐可以促进肠道损伤的修复,在严重溃疡肠道部位添加,不利于溃疡的恢复,甚至加剧整个溃疡。
有学者发现溃疡部位的粘膜组织对丁酸的代谢降低,甚至只有正常粘膜组织的一半,主要是由于其转运载体和氧化相关的酶活降低。
主要参考文献
Louis P, Flint HJ. Formation of propionate and butyrate by the human colonic microbiota. Environ Microbiol. 2017 Jan;19(1):29-41.
Gill PA, van Zelm MC, Muir JG, Gibson PR. Review article: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as potential therapeutic agents in human gastrointestinal and inflammatory disorders.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18 Jul;48(1):15-34.
Hosseini E, Grootaert C, Verstraete W, Van de Wiele T. Propionate as a health-promoting microbial metabolite in the human gut. Nutr Rev. 2011 May;69(5):245-58.
Arora T, Tremaroli V.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Butyrate for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 Front Endocrinol (Lausanne). 2021 Oct 19;12:761834.
Singh V, Lee G, Son H, Koh H, Kim ES, Unno T, Shin JH. Butyrate producers, “The Sentinel of Gut”: Their intestinal significance with and beyond butyrate, and prospective use as microbial therapeutics. Front Microbiol. 2023 Jan 12;13:1103836.
Gonzalez-Garcia, R.A.; McCubbin, T.; Navone, L.; Stowers, C.; Nielsen, L.K.; Marcellin, E. Microbial Propionic Acid Production. Fermentation 2017, 3, 21.
Reichardt N, Duncan SH, Young P, Belenguer A, McWilliam Leitch C, Scott KP, Flint HJ, Louis P. Phylogenetic distribution of three pathways for propionate production within the human gut microbiota. ISME J. 2014 Jun;8(6):1323-35.
Liu H, Wang J, He T, Becker S, Zhang G, Li D, Ma X. Butyrate: A Double-Edged Sword for Health? Adv Nutr. 2018 Jan 1;9(1):21-29.

谷禾健康

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 是一组神经发育疾病,其特征是社交互动和沟通的质量障碍、兴趣受限以及重复和刻板行为。
环境因素在自闭症中发挥重要作用,多项研究以及谷禾队列研究文章表明肠道微生物对于自闭症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存在明显的菌群和代谢物的生物标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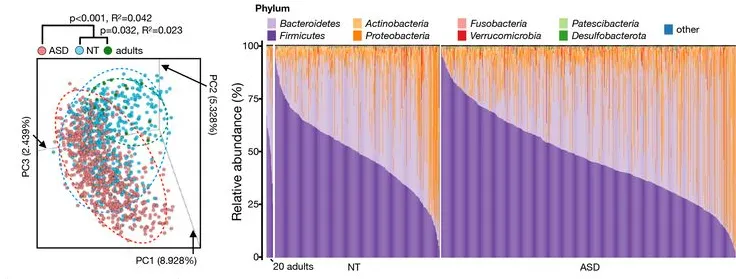
doi: 10.1136/gutjnl-2021-325115.
尽管环境因素在自闭症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将饮食与疾病的发生和进展联系起来。然而,最近关于饮食如何塑造肠道-大脑轴的研究可能会为环境对疾病机制的影响提供新的见解,并提出至少通过饮食改善某些自闭症谱系障碍症状的可能性。
此外,在谷禾检测实践过程中,也发现部分自闭症儿童的消化功能,以及饮食营养存在问题,主要集中表现为挑食,消化不良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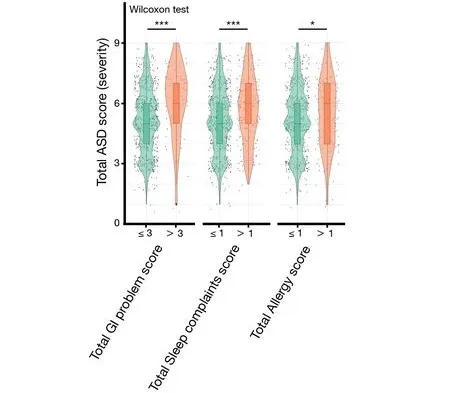
doi: 10.1136/gutjnl-2021-325115.
本文参考以往相关研究性文章,详细讨论饮食和肠道微生物群-肠-脑轴如何影响自闭症,主要概述肠道微生物群对分子代谢(各类氨基酸、γ-氨基丁酸、不饱和脂肪酸、短链脂肪酸、胆固醇、丁酸盐、乙酸盐、N-乙酰天冬氨酸、多酚等)和与自闭症发病和进展相关的酶(二糖酶、己糖转运蛋白和单羧酸转运蛋白等)。还回顾了饮食模式、益生菌和肠道微生物群在大脑发育中的作用及与自闭症的关联,这些都为自闭症的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 是一组神经发育疾病,一般在 3 岁之前发病,其特征是社交互动和沟通的质量障碍、兴趣受限以及重复和刻板行为。
直到几十年前,自闭症谱系障碍还被认为相当罕见,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世界自闭症谱系障碍快速增加,这给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的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后果。
目前在临床上自闭症谱系障碍的诊断仍然是根据行为来定义的,通过详细的发展史、父母对孩子日常行为的描述以及对孩子的社交互动方式以及沟通和智力功能的直接评估。
一个重要问题让人对自闭症表型发病机制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简而言之,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发病和表现远非同质:
此外,除了核心症状之外,这些儿童通常还表现出一系列其他相关特征,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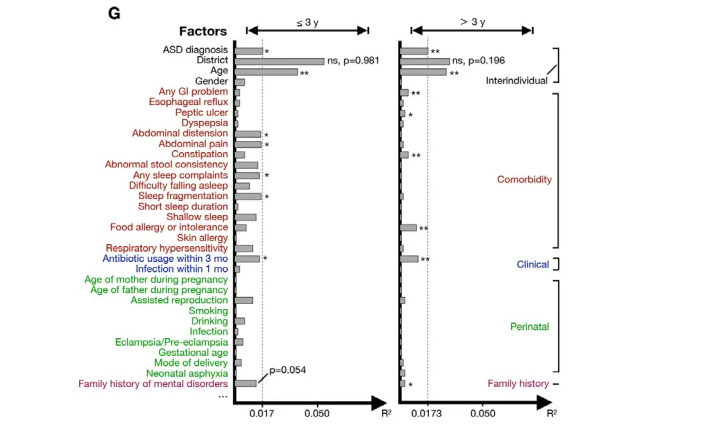
doi: 10.1136/gutjnl-2021-325115.
饮 食
人体必需氨基酸必须由食物供给,喂养可能代表环境因素和神经生物学因素之间的桥梁,因此可能在导致疾病表型的途径中发挥作用。从临床经验和文献中都知道,自闭症儿童往往与喂养和饮食态度有特殊的关系。
部分自闭症儿童可能有进食困难及胃肠道症状,对食物的味道和颜色非常挑剔。因此,自闭症儿童必需氨基酸 (赖氨酸、色氨酸、苯丙氨酸、组氨酸) 减少,可能部分是由于食物摄入不足或饮食习惯不良所致。
非常有限的饮食可能会使任何儿童面临营养缺乏和发育不良的风险,包括大脑发育。
遗 传
强有力的证据支持遗传因素对自闭症和相关疾病的疾病风险有影响。
然而,与自闭症风险有关的许多不同基因编码参与各种生理过程的各种不同蛋白质,包括大脑发育和功能、神经递质受体或转运蛋白、细胞粘附/屏障功能蛋白、免疫相关蛋白、参与胆固醇代谢或运输的蛋白质,以及影响线粒体功能的蛋白质。
近期,发表在《Cell》的一项研究对一个出生队列进行了 20多年的跟踪,详细的早期纵向问卷记录了感染和抗生素事件、压力、产前因素、家族史等饮食,在随访的 16,440 名瑞典儿童中,1,197 名患上神经发育障碍。下面一些有关自闭症风险的研究数据出自该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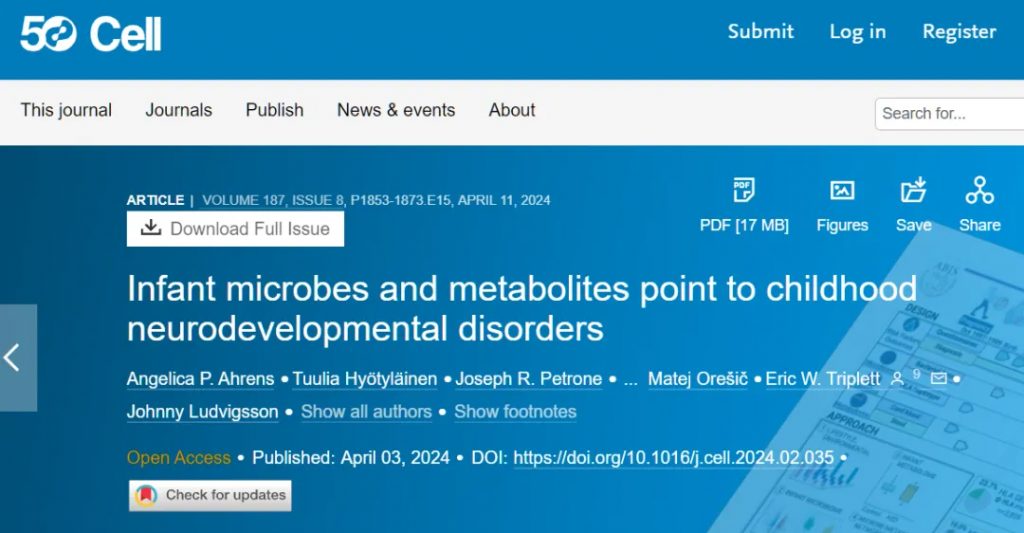
家族病史
环 境
并非所有携带这些特定突变的个体都会患自闭症谱系障碍。最近的一项同卵双胞胎研究强调,环境因素可能解释了他们患自闭症谱系障碍相对风险的 55%,环境因素为自闭症谱系障碍型症状的出现提供了选择性压力,这些症状从各种不同的症状中出现。各种易诱发的遗传异常,结合起来会引起明显的疾病。
重大生活事件
化学物质暴露
早期感染和抗生素
儿童早期(出生至 5 岁)感染与自闭症风险增加显著相关,最显著的是第一年内中耳炎和反复湿疹。
微生物组
胃肠道症状长期以来表明,肠道和大脑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即”肠-脑轴”。
——胃肠道问题
在未来患有神经发育障碍的儿童中,早期胃肠道问题明显,情绪问题程度较轻。
——肠道菌群
肠道细菌可能在自闭症病理生理学中发挥一定作用。事实上,各种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在自闭症中发生了改变, 尽管文献中对于参与其中可能发挥作用的细菌几乎没有达成一致。
肠道细菌及其代谢产物不仅影响肠道功能和饱腹感,还可能与情绪、认知、行为、抑郁以及大脑发育等方面有关。
饮食在塑造哺乳动物代谢通量(包括神经化学物质的通量)以及塑造肠道微生物群及其活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例如,纤维和益生元尤其支持有益的糖分解肠道微生物群,其特征是双歧杆菌和乳酸菌的相对丰度增加以及短链脂肪酸 (SCFA) 的产生。来自水果、谷物和蔬菜等全植物食品的多酚也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免疫功能,充当抗氧化剂,防止大脑炎症并改善血脑屏障 (BBB) 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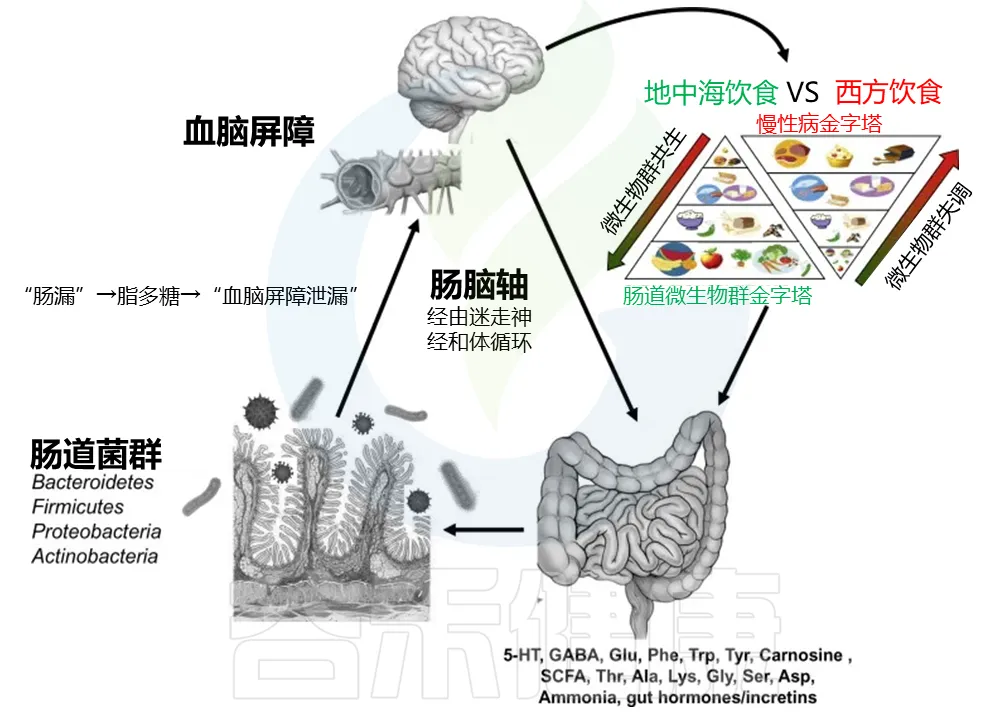
Kieran M. Tuohy, et al.,Diet and the Gut Microbiota,2015,225-245
接下来我们着重就微生物组这方面,详细探讨肠道微生物群如何在自闭症的发展中起作用,以及相关的最新研究进展。
肠-脑轴作为外部环境与人类大脑之间的沟通通路,在体内有重要的“内部”通道——人类肠道微生物群。许多营养物质和摄入的化学物质必须经过这些通道,转化为生物可利用和活跃的中间产物,然后通过肝门静脉被吸收并在全身分布。
许多对大脑重要的化学物质也由肠道微生物群在肠道中产生,包括色氨酸、多巴胺、血清素、GABA、β-羟基丁酸、胆碱、牛磺酸、乙酸盐、琥珀酸、乳酸、乙酰辅酶A、肌酐、甜菜碱、谷氨酸、谷氨酰胺、对甲酚、反式吲哚丙烯酸甘氨、脂肪酸和马尿酸。
一些其他化学物质可能由细菌(例如在消化和发酵过程中)调节,或者是细菌成分,如革兰氏阴性细菌细胞壁的组成部分脂多糖(LPS),它可剂量依赖性地减少人类肠道细胞对血清素的吸收,并在外周和大脑引发炎症,影响大脑功能。
神经递质:GABA、血清素
最近有研究表明,神经递质GABA在自闭症谱系障碍神经元发育中可能起作用,尤其是考虑到它在婴儿期从神经递质兴奋剂到抑制剂的转变。
另一种神经递质,血清素(5-羟色胺,5-HT),也被怀疑在自闭症中起作用。自闭症患者的血液中,血清素和 GABA 水平均发生了变化。有趣的是,这两种神经递质都是由氨基酸代谢产生的,分别是色氨酸和谷氨酸。
肠道代谢物是否直接影响大脑的神经发育?
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穿过血脑屏障(BBB)。
比如说,肠道细菌可以产生GABA,这个 GABA 可能会影响到肠道神经系统的工作,或者改变血液中 GABA 的含量。但是,在正常健康的情况下,肠道产生的 GABA 是不能直接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的。
反之,乙酸盐作为肠道微生物群发酵碳水化合物的主要终产物和哺乳动物细胞胆固醇生物合成的底物,可以迅速通过血脑屏障。
然而,血脑屏障可能会因氧化或炎症压力等原因受到损伤,与胃肠道屏障类似出现“漏”,允许不需要的化学物质进入大脑。在自闭症患者中血脑屏障受到损伤。
为什么说肠道菌群可用于区分自闭症与非自闭症?
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在影响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代谢产物谱和生理参数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首先,自闭症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与健康对照组或非自闭症的兄弟姐妹有显著差异,显示出异常的肠道微生物组成和活动是自闭症的一个特征。
研究报告显示,自闭症群体与非自闭症对照组之间在拟杆菌门、厚壁菌门、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的组成上存在差异。
前面提到的发表在《Cell》大队列的自闭症儿童研究,在 11.9 ± 2.9 个月时采集了 1,748 名婴儿的粪便样本,将所有可用的对照与未来的神经发育障碍进行比较,然后匹配风险因素和微生物组多样性混杂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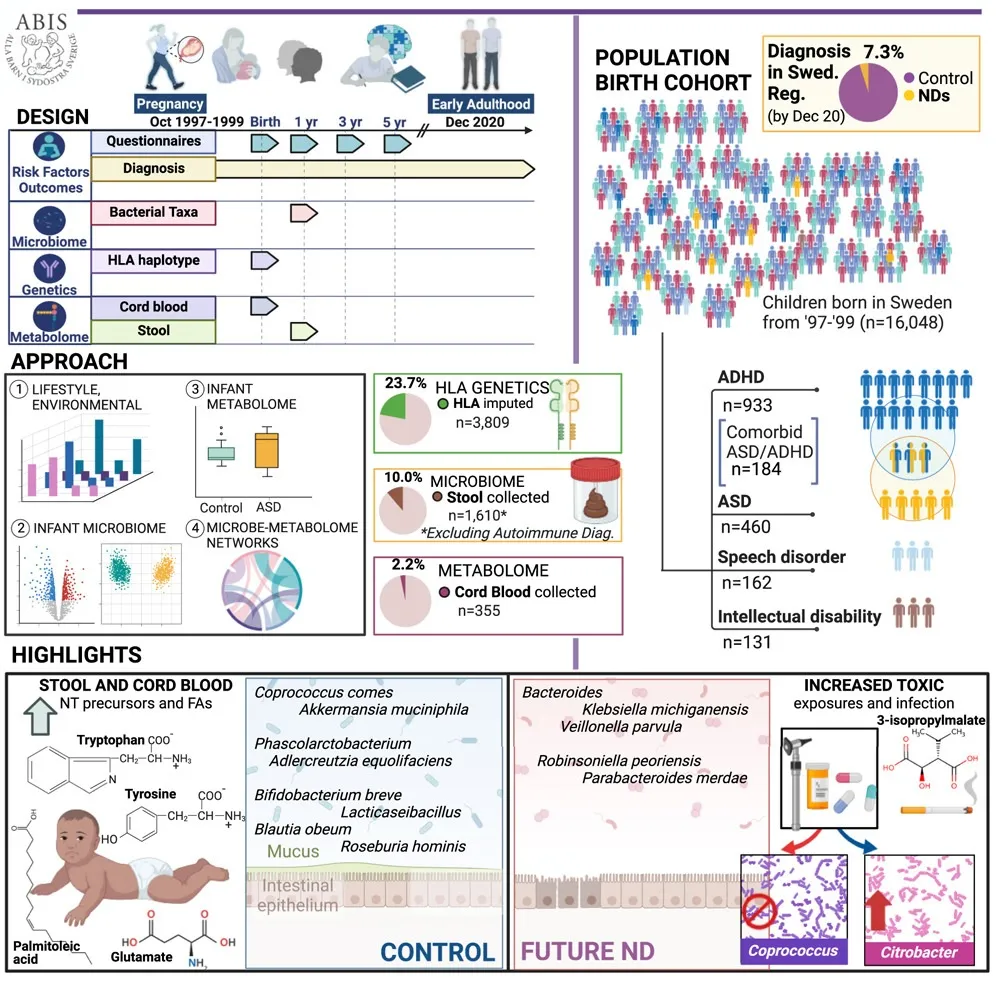
doi.org/10.1016/j.cell.2024.02.035
在未来的神经发育障碍中,下列菌群丰度较高:
在我们的GUT队列里,也发现自闭症儿童这个菌的Veillonella显著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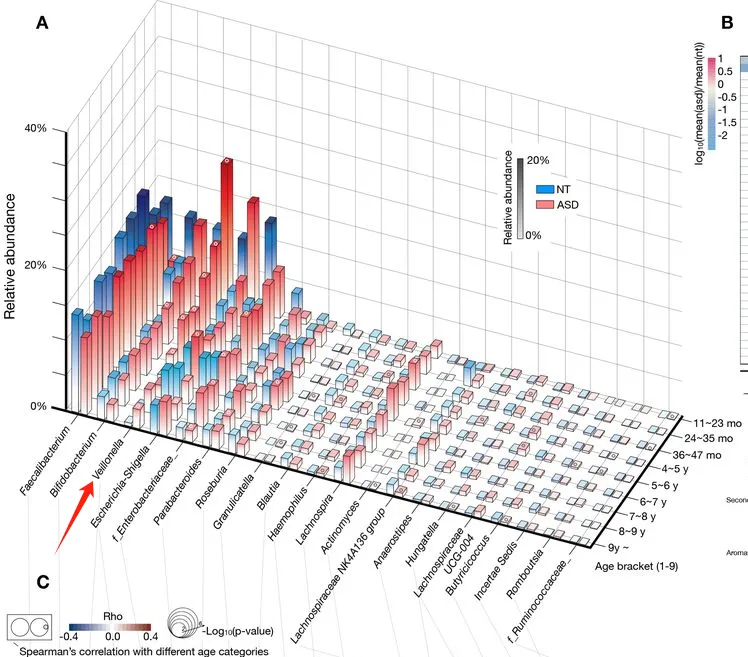
doi: 10.1136/gutjnl-2021-325115.
注:Veillonella是一种革兰氏阴性的厌氧球菌,正常情况下通常存在于人体口腔和胃肠道中。该菌以其乳酸发酵能力而闻名,能代谢乳酸产生丙酸、CO2和H2。
下列菌群始终较少富集:
这些菌属具有抗炎、维护肠道屏障、产生短链脂肪酸等有益作用,其减少可能导致肠道功能紊乱和免疫失调。
Akkermansia muciniphila在后来被诊断患有自闭症或自闭症-多动症合并的婴儿中不存在,并且与儿童早期的胃肠道和情绪症状呈负相关。
Akkermansia muciniphila促进粘蛋白并产生叶酸,丙酸和乙酸;以增强肠细胞单层完整性和强化受损的肠道屏障而闻名;并具有免疫调节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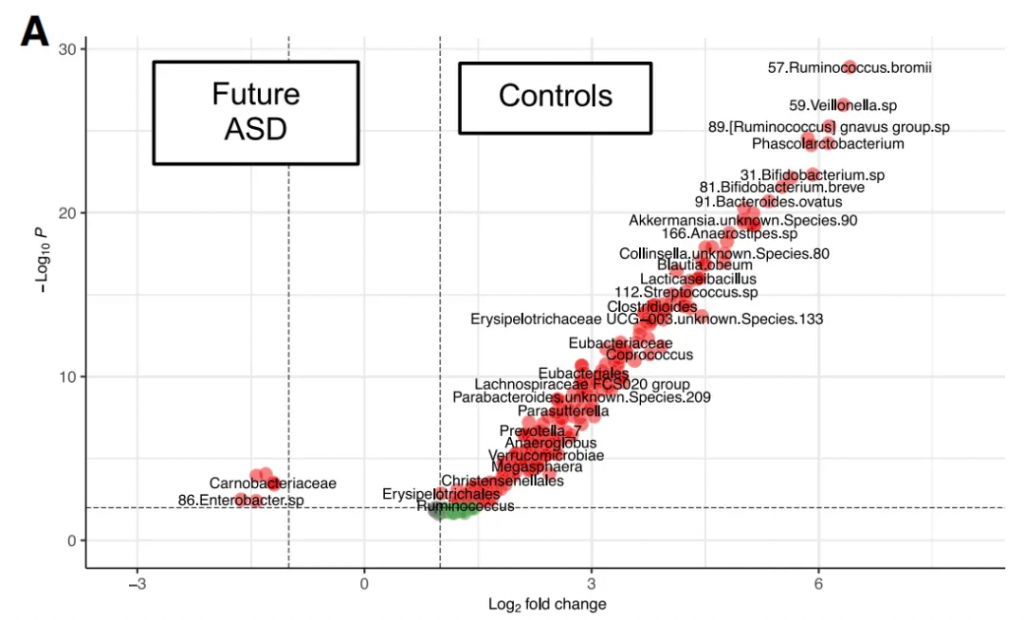
doi.org/10.1016/j.cell.2024.02.035
特定菌群:
与对照组(21.7%)相比,两种Klebsiella michiganensis菌株(HCXXMCOL0180 和 HCXXMCOL0513)在自闭症儿童中更普遍(43.6%),携带这两种菌株的婴儿日后患自闭症的风险更高。
携带这两种菌株的对照组婴儿抗生素使用频率更高(27.1%),提示抗生素暴露可能促进了这些菌株的定植。
性别和诊断年龄影响:
菌群自闭症男童的肠道菌群组成可能因诊断年龄不同而异,如晚期诊断与Akkermansia muciniphila丰度增加相关,而这种模式在女童中并不明显,女童中一些Bacteroides菌株丰度升高。
而早期诊断男童,Enterobacteriaceae科一些菌属如Enterobacter、 Klebsiella丰度升高。
这提示自闭症的肠道菌群变化可能具有性别特异性,且随年龄和病程进展而动态变化。
代谢物异常与菌群相关:
粪便代谢组学分析显示,自闭症儿童的某些代谢物如酪氨酸、色氨酸(儿茶酚胺、血清素前体)、精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亚油酸等脂肪酸以及维生素B6等水平异常。
注:关于氨基酸,脂肪酸等详细介绍与自闭症的关联详见后面章节。
精氨酸水平与Roseburia、Coprococcus、Akkermansia丰度呈正相关,提示菌群失调可能影响宿主氨基酸代谢。
色氨酸代谢产物:吲哚-3-乙酸盐(AhR激动剂)在自闭症组中升高,且与Ruminococcaceae和Lachnospiraceae科菌属丰度正相关。
其他的一些与自闭症相关菌群的研究结果:
多样性降低
一些菌群减少,包括:
一些菌群增多,包括:
下列菌群可作为3-6岁有胃肠道症状儿童自闭症的可靠生物标志物:
菌群代谢产物LPS→慢性炎症→血脑屏障损伤
研究表明,细菌脂多糖(LPS)会引发慢性低度系统性炎症或“代谢性内毒素血症”,在动物模型中,这被证明会损害包括血脑屏障(BBB)在内的屏障功能。实际上,出生期暴露于LPS引发的系统性炎症的小鼠表现出永久性的血脑屏障损伤和渗透性增加,且在青少年和成年期表现出行为改变。对自闭症患者而言,血脑屏障功能的永久性损害将只会加剧肠道微生物及异常代谢产物输出所带来的病理后果。
母亲妊娠期:LPS诱导的系统性炎症如何影响孩子神经发育,增加自闭症风险?
妊娠期由LPS诱导的系统性炎症可以改变后代的神经发育和脑功能。自闭症中的这种先天性或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可能会因获得性免疫系统中明显的自身免疫成分而加剧。由系统性炎症或母体自身免疫疾病触发的自身抗体在妊娠期间产生,现在被怀疑在胎儿异常神经发育和受损的血脑屏障发展中起作用,并影响婴儿期的大脑功能,包括增加自闭症的风险。
肠道菌群失调诱导产生自身抗体,影响神经系统发育
在自闭症患者中,对叶酸、血清素和GABA受体的自身抗体水平,以及一些重要的免疫相关酶如转谷氨酰胺酶2的抗体水平也有所升高。尽管自身抗体生成的分子触发机制尚不完全了解,但有一个可能性是,对关键代谢物如神经递质受体的自身抗体可能是在血液中异常代谢物浓度、早期生活中的不当免疫教育或由肠道细菌模拟引导下由免疫系统产生的。
这样的“代谢组-炎症组”调控网络也在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出现,包括1型糖尿病和炎症性肠病(IBD),并且似乎与肠道微生物群密切相关。
氨基酸代谢在神经传递相关代谢物的生物合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期以来被怀疑在自闭症谱系障碍中发挥作用。
血液分析氨基酸变化
Glu:Gln比率升高
有许多研究报告称,自闭症患者的血液中谷氨酸与谷氨酰胺(Glu:Gln)的比率升高。
将谷氨酸转化为谷氨酰胺是大脑中处理氨废物的主要方式,这对于避免氨中毒和在突触中谷氨酸的过度积累以减少兴奋性毒性非常关键。因此,血液中Glu:Gln比率的升高可能表明自闭症患者大脑中的氨解毒和谷氨酸循环发自闭症生了变化,这会影响行为。
注:低纤维高蛋白饮食可能会使这种氨中毒恶化,因为这样的饮食会导致肠道中的蛋白水解微生物群发酵氨基酸,从而增加系统性氨贡献。饮食中氨基酸的微生物分解会影响哺乳动物体内氨基酸的可用性和循环,也可能产生生物活性化合物,如短链脂肪酸、支链脂肪酸和生物胺。
蛋氨酸
一项包括87项研究的自闭症氧化应激生物标志物的汇总荟萃分析发现,参与甲基化循环和硫酸盐转移途径的几种代谢物异常。
蛋氨酸在硫酸盐转移途径中利用半胱氨酸合成,该途径连接蛋氨酸和谷胱甘肽的生物合成,蛋氨酸显著降低(p < 0.001),异常甲基化会增加自闭症谱系症状的风险 。
瓜氨酸
有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的瓜氨酸水平与刻板行为(ADOS-2 上的 RRB 评分)之间存在正相关,且具有统计学意义。瓜氨酸和氨的累积暴露是经典瓜氨酸血症(精氨琥珀酸合成酶缺乏症)患者认知功能较差的最可靠标志。
尿液代谢物分析氨基酸变化
色氨酸
色氨酸因与自闭症症状相关而闻名,它是血清素 (5-HT) 的前体,血清素是一种抑制性单胺类神经递质,一些研究报告色氨酸水平升高,而另一些研究报告色氨酸水平降低 。
关于色氨酸,详见我们之前的文章:
苏氨酸
有研究发现,自闭症组男孩的苏氨酸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男孩。5 岁以下自闭症儿童的尿液苏氨酸含量高于 5 岁以上儿童。苏氨酸属于天冬氨酸家族,是一种蛋白质氨基酸,其分解产生乙酰胆碱酯酶 A 和甘氨酸,促进各种生理过程和整体身体稳态 ,它也可以通过影响色氨酸进入大脑,间接影响5-羟色胺的合成。
脯氨酸
有研究发现,5 岁以下自闭症儿童的脯氨酸含量明显低于 5 岁以上儿童。
与 22q11.2 染色体缺失的 CMPT158 基因型相关的脯氨酸水平异常升高,会影响自闭症谱系症状的严重程度,尤其是影响面部情绪识别、行为和认知。
β-丙氨酸
β-丙氨酸,在肉类中常见的氨基酸,会抑制肠道细胞(如Caco-2细胞)对GABA的吸收。β-丙氨酸也可以在肠道内由白色念珠菌产生的丙酸和氨反应形成,尽管这些化合物也由肠道内的许多其他微生物产生。
HPHPA
有研究报告了一种稀有代谢物3-(3-羟基苯基)-3-羟基丙酸(HPHPA)的出现。HPHPA是梭菌属细菌特有的代谢产物,会耗尽大脑中的儿茶酚胺,导致自闭症症状。
HPHPA在患有艰难梭菌感染的个体中也有发现,并且在急性精神病发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甚至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以上这些研究是基于血浆、尿液氨基酸变化,血液和尿液中的氨基酸(AA)水平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从食物中吸收的氨基酸、氨基酸和蛋白质的降解、宿主蛋白质的分泌和在粪便中的排泄。这些氨基酸相对比例的改变也可能对它们参与的代谢途径的产物产生连锁反应,包括不同神经递质的生产或相对比例。
肠道菌群代谢分析氨基酸变化
大多数氨基酸来自饮食或由体内合成,但肠道微生物群也会影响饮食氨基酸的回收以及氨基酸的生产或分解。
目前,我们对参与氨基酸生物利用度和肠道微生物群体生物转化的微生物种类或代谢过程知之甚少,对于其对神经功能的可能影响了解更少,也不清楚不同食物和食物成分如何相互作用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对氨基酸的摄取或代谢。
有早期体外研究显示,人类肠道微生物群对氨基酸的发酵受到低pH值和可发酵纤维/碳水化合物(抗性淀粉)存在的抑制。然而,目前不知道这种过程在体内如何转化,或在自闭症等疾病状态或抗生素治疗下如何变化。
谷禾肠道菌群健康检测数据库中有这样的案例,一起来看一下:
一名5岁自闭症男孩,检测结果,自闭症为中等风险,符合实际情况。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这是谷禾利用几十万例的临床和人群样本数据(其中4895例自闭症患者),结合机器学习方法,使用肠道菌群数据进行疾病状态和风险的预测,并给出了的风险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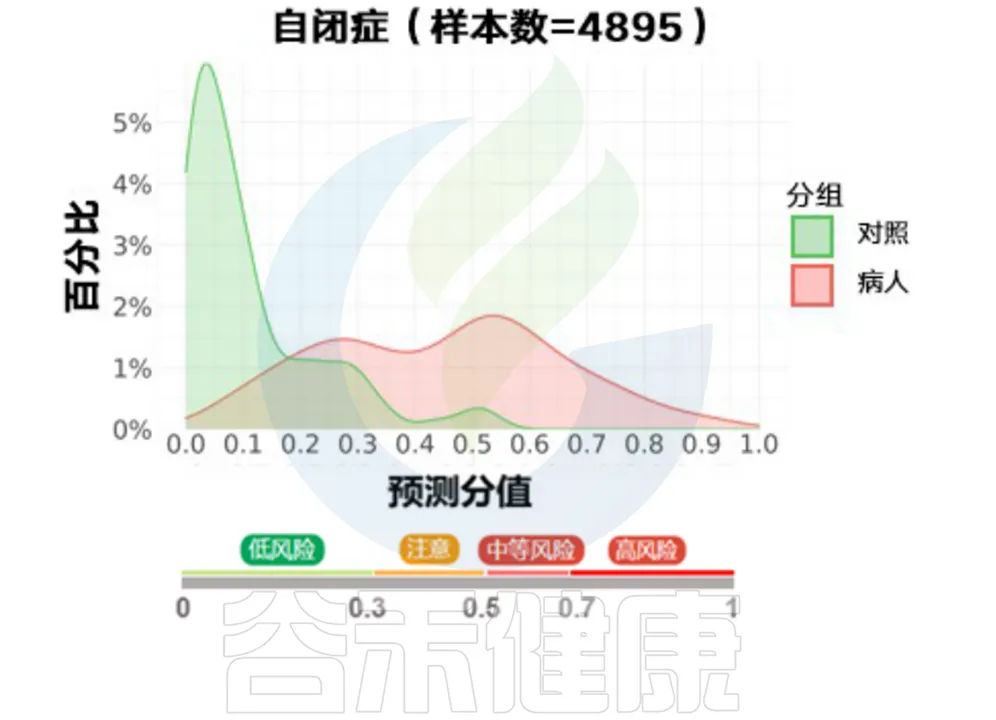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从该患者肠道菌群检测报告可以看到,蛋白质,脂肪水平都相对偏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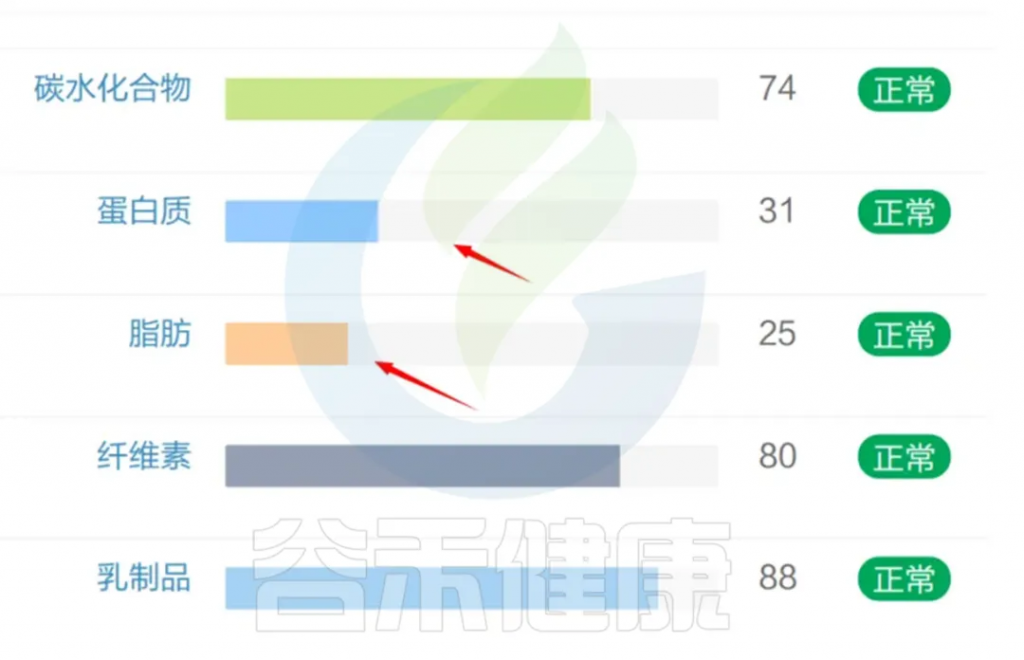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我们再来看肠道菌群检测报告中的氨基酸水平,部分氨基酸严重缺乏,例如组氨酸;
其他氨基酸如酪氨酸、谷氨酸、甘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蛋氨酸也都相对偏低。
酪氨酸是一种与认知功能相关的儿茶酚胺前体。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组氨酸通过清除氧自由基发挥抗氧化作用,从而参与缓解氧化应激。组氨酸是肌肽的前体,肌肽是一种含有 β 丙氨酸和组氨酸的二肽,在人脑中起到缓冲剂和抗氧化剂的作用。肌肽可以调节与智力障碍相关的各种生物途径。
组氨酸是组胺的前体,而组胺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和神经调节因子。关于组胺,详见之前的文章:
有小鼠研究显示,组氨酸缺乏的小鼠表现出一些类似自闭症的行为,如社交互动减少、刻板重复行为增多等。其他也有多项研究表明,组氨酸血症与自闭症和语言发育迟缓之间存在关联。
谷氨酸,可以调节记忆和学习等认知功能,而这些功能在自闭症患者中通常会受损,关于谷氨酸,详见谷禾之前的文章:
甘氨酸是一种具有抗炎、细胞保护和免疫调节特性的抑制性神经递质,甘氨酸以多种方式与线粒体代谢相关。
其他,赖氨酸,蛋氨酸,亮氨酸都属于人体必须氨基酸,是人体不能自行合成或以适合人体需要的速率合成的氨基酸,必须通过食物摄入来获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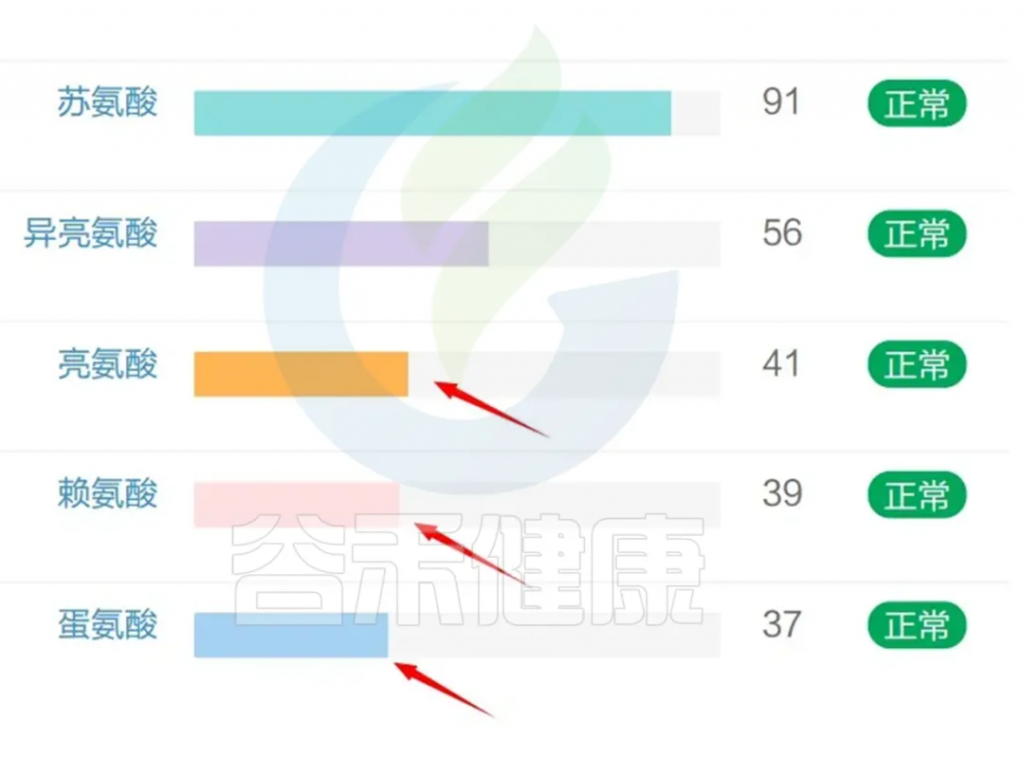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亮氨酸,属于支链氨基酸,支链氨基酸生物合成与自闭症症状、甲基化潜力和细胞内 GSH 比率相关。支链氨基酸具有多种生理作用,包括调节葡萄糖和脂肪酸代谢以及调节重要的分子途径和促进蛋白质合成,它们通过琥珀酰辅酶 A 进入 CAC 与线粒体功能相连。大多数自闭症患者都会有线粒体功能障碍。
赖氨酸,是一种生酮氨基酸,通过合成谷氨酸作为其分解的副产物,参与肠道菌群-肠-脑轴。
经过几个月的干预,再次检测肠道菌群,该患者的自闭症风险有所下降,症状也有相应好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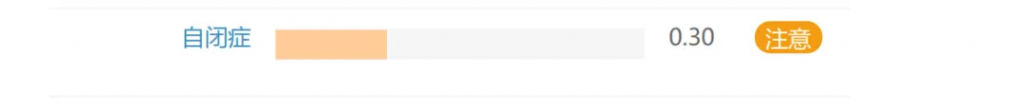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未来患有自闭症的新生儿中关键脂质减少,如亚油酸、α-亚麻酸、胆汁酸、甘油三酯。
这些必需脂肪酸、它们的衍生物、相对比例和个体分子种类在许多哺乳动物的生理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包括磷脂生成、膜流动性和大脑发育。
亚油酸和α-亚麻酸
亚油酸和α-亚麻酸是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的必需脂肪酸(EFA),必须通过饮食摄取。
注:亚油酸: LA,C18:2n-6,n-6脂肪酸的前体
α-亚麻酸: ALA,C18:3n-3,n-3脂肪酸的前体
它们对大脑具有抗炎作用,并调节自噬、神经传递和神经发生。它们通过抑制神经递质(例如GABA)的释放来调节内源性大麻素系统,从而影响突触功能和可塑性。
ARA、DHA、EPA
与其他身体组织相比,大脑中亚油酸和α-亚麻酸的浓度较低,而其衍生物,特别是ARA(花生四烯酸)和DHA(即二十二碳六烯酸)的浓度较高。
在妊娠晚期,胎儿大脑快速积累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DHA。
亚油酸和α-亚麻酸的衍生物可以进一步被宿主磷脂酶修饰,转化为主要来自ARA的二十碳烷类,如前列腺素、白三烯和血栓素。这些二十碳烷是促炎分子,作为局部激素来激活免疫细胞、启动血小板聚集和引发分娩。
相反,DHA和EPA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抗炎的消退素(resolvins)和保护素(protectins)。
胆汁酸
关于胆汁酸,UDCA,熊去氧胆酸,一种天然存在的次级胆汁酸,在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炎症性疾病和神经病理学等疾病中显示出治疗前景。研究发现,UDCA在未来自闭症患者中较低。
ARA加DHA改善自闭症
一项双盲、安慰剂对照随机试验发现膳食补充ARA加DHA(ARA占优势)显著改善了自闭症患者(n=13)在异常行为检查表-社区量表测量的社交退缩和社交回应量表测量的沟通情况。虽然样本量较小,但这个研究证明了通过饮食调节大脑脂肪酸谱可能带来的好处,这种脂肪酸调节在动物研究中也可以通过益生菌达到。
n-3和n-6脂肪酸
一些小规模的n-3和n-6脂肪酸的膳食干预研究显示,自闭症患者的症状有所缓解,虽然并非所有研究都显示有改善。
自闭症患者可能与母乳喂养较少有关
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较少接受母乳喂养,而健康对照组则较多,这表明富含ARA、EPA和DHA的人类母乳对婴儿大脑发育的最佳饮食份额的重要性。相反,早期断奶与自闭症风险增加相关。这些观察结果不仅强调了早期产后饮食对大脑发育和自闭症风险的重要性,还暗示了肠脑轴和肠道微生物群在这一发育过程中的可能早期作用。
补充益生菌,改变脂肪酸
一些肠道微生物,最著名的是某些乳酸菌属和双歧杆菌属的菌种,具备进行脂肪酸生物氢化所需的酶,从而增加脂肪酸的不饱和度。
研究表明,饮食补充α-亚麻酸(ALA)会改变小鼠肝脏、脂肪组织和大脑中的脂肪酸谱,并且在联合补充α-亚麻酸与益生菌Bifidobacterium breve NCIMB 702258时,脂肪酸谱会进一步改变。
注:B. breve NCIMB 702258是高效生产共轭亚油酸(CLA)的菌。
相比于对照组喂养或单独补充α-亚麻酸的情况,食用n-3脂肪酸加益生菌的动物其大脑中的DHA水平升高,而ARA水平下降。
同一组作者随后表明,单独使用B. breve NCIMB 702258菌株,相比于另一种共轭亚油酸(CLA)产生的B. breve菌株和对照组,小鼠的大脑中DHA和ARA的水平也有所上升,证实了益生菌调节大脑脂肪酸谱的能力,并显示这种活动具有明显的菌株特异性。
LA和ALA不够,其他饱和脂肪酸来凑
尽管亚油酸(LA)和α-亚麻酸(ALA)是磷脂形成所必需的必需脂肪酸,但当饮食中这些脂肪酸含量偏低时,其他脂肪如饱和脂肪酸有时可作为替代品,从而对最终磷脂的结构和可能的功能产生影响。
磷脂代谢异常、脂肪酸缺乏或血脂异常已牵涉到多种神经和大脑发育或退行性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抑郁症、广泛性发育障碍、发育性协调障碍、癫痫、双相情感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尼曼-皮克病、亨廷顿舞蹈病、中风。
胆固醇代谢和磷脂代谢异常在自闭症中起作用
自闭症患者血液中磷脂酶A2水平较高,细胞膜中的ARA和DHA水平较低,并且可能具有更高的n-6脂肪酸与n-3脂肪酸的比例。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自闭症儿童(n=16)的红细胞脂质谱被修改,表现为较低的胆固醇水平和细胞膜中单唾液四己糖神经节苷脂(GM1)的比例较高。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反映了更普遍的胆固醇合成缺陷,在大脑中,结合GM1表达的变化,可能会促成自闭症的病理生理机制。
BDNF对突触传递和神经元胆固醇合成的影响
自闭症与BDNF和益生菌的关联
然而,并非所有益生菌研究都显示BDNF与实验动物观察到的脑功能改善有关。
益生菌、益生元与改善脑功能
然而,需要在人类受试者和相关实验模型中进行基础研究,以验证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并在机制上将肠道细菌与这些病情联系起来。
大脑占人体质量约2%,但却占胆固醇约20%。血脑屏障(BBB)对脂蛋白是不可通透的,这意味着大脑所需的胆固醇是内源性形成的。
其中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分别是胆固醇的净生产者和使用者,体现了胆固醇生物合成机制的独特分区化。
神经元——胆固醇的使用者
神经元需要大量的胆固醇来维持其广泛的膜表面积并提供突触前囊泡的形成。它们还有稍微不同的酶途径,将鲨烯转化为胆固醇。出生后的胆固醇主要由星形胶质细胞提供,并优先来源于乙酸盐。
注:鲨烯(C30H50)是一种多不饱和烃类,也称为角鲨烯或三十碳六烯。 它是一种在人体胆固醇合成等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萜类化合物。鲨烯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尤其是在鲨鱼肝油中含量较高,同时也是橄榄油、米糠油等少数几种植物油中的成分。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在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领域广泛应用。
星形胶质细胞——胆固醇的净生产者
星形胶质细胞是包裹神经细胞的细胞,负责供应细胞外钾、谷氨酸、能量和抗氧化剂,并调节大脑中的活性依赖性血流,并可能影响突触活动。
星形胶质细胞在大脑胆固醇运输中的关键作用
ApoE缺乏的啮齿动物模型,表现出各种行为和神经系统症状,并在感觉系统中也有缺陷,这些缺陷与随年龄增长而丧失的突触和树突,突触膜胆固醇分布的改变有关。
CYP46,在维持大脑胆固醇稳态中的作用
短链脂肪酸——乙酸,对神经发育的作用
出生后乙酸在神经发育中重要,母乳喂养乙酸多
AceCS1的表达及其功能
乙酸是胆固醇的组成成分
乙酸的代谢去向
乙酸作为特殊代谢产物的重要性
NAA——乙酸的主要来源之一
N-乙酰天冬氨酸(NAA)在大脑中的作用
自闭症儿童大脑中NAA浓度降低
短链脂肪酸——丙酸,对大脑的负面影响
饮食如何影响大脑中短链脂肪酸的可用性?
自闭症中二糖酶和己糖转运蛋白减少
研究发现,在自闭症儿童中,二糖酶和己糖转运蛋白的表达显著减少,这些变化与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变化相关。这些变化与厚壁菌门相对丰度较高,拟杆菌门较少,以及β-变形菌门升高有关。
注:至少是三种常见肠道二糖酶之一:蔗糖酶-异麦芽糖酶(SI)、麦芽糖酶-异麦芽糖酶(MGAM)、乳糖酶(LCT)
己糖转运蛋白:SGLT1、GLUT2
肠道二糖酶和糖转运蛋白的表达受到多种因素的调控,包括饮食、肠道微生物以及肠神经系统等。
丁酸:结肠健康的关键能量源与吸收机制
考虑到丁酸是结肠细胞的首选能量来源、黏膜更新和分化的介质,以及其生产率在早期肠道微生物群继发发育过程中发生变化,丁酸在肠黏膜成熟中的作用可能非常重要。
丁酸吸收机制:MCT1负责运输,GPR109A助攻
在了解了丁酸在肠黏膜中的重要性及其吸收机制之后,我们再探讨不同饮食和环境因素对MCT1表达的影响及其对丁酸和其他短链脂肪酸吸收的调节作用。
饮食影响短链脂肪酸(丁酸)吸收的机制
高纤维饮食和益生元→MCT1表达和短链脂肪酸吸收↑
高脂肪饮食→抑制短链脂肪酸在结肠中的吸收
肠道炎症和氧化应激→MCT1表达↓→丁酸吸收↓
以上我们知道,MCT1表达异常会影响丁酸吸收,不仅如此,MCT1表达异常还可能与肥胖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有关。
在饮食诱导和遗传性肥胖动物中,MCT1-4 表达都增加,特别是在神经元和神经元胞体中,说明这种变化可能不全是饮食因素,也可能是由于肥胖引起的激素变化间接导致的。
前面我们知道,MCT与短链脂肪酸转运相关,那么MCT表达异常,短链脂肪酸也异常,可能会影响大脑的能量代谢,如果这些变化发生在生命早期,可能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过程,并与个体成年后的肥胖易感性相关。
注:从母乳到固体食物的饮食结构转换可能会影响生理发育、代谢途径和营养转运蛋白(如MCT)的表达,从而对大脑功能产生重要影响。
谷禾发表在 GUT上的队列也表明,随着断奶或引入辅食,自闭症儿童的肠道菌群发育轨迹逐渐偏离健康儿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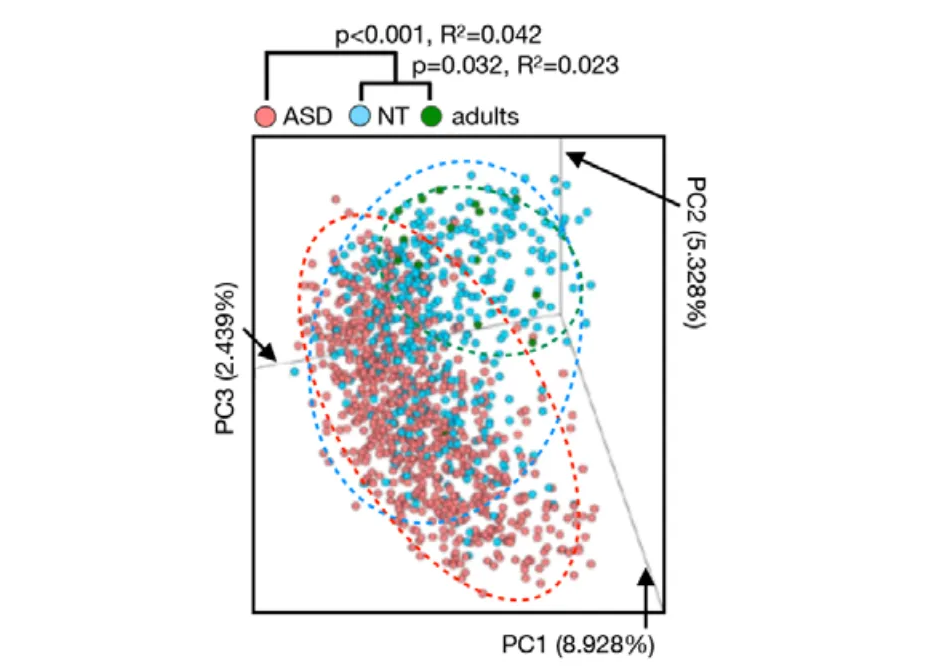
doi: 10.1136/gutjnl-2021-325115.
不良饮食,尤其是在断奶后采用现代西式饮食,实际上可能通过将营养素转运蛋白关闭,重定向营养流向,从而下调了必需营养素(如氨基酸、脂肪和SCFA)的肠道流动。
对比现代西式饮食和古老传统的饮食,有助于重新定义营养不良的范式。营养不良不再仅限于某些必需营养素的缺乏,还包括营养过剩和异常的营养素比例和结构。

在人类“超级有机体”中,这种改变的营养环境的代谢后果,最明显地体现在肠道微生物群与宿主能量代谢和大脑功能的相互作用中。
生命早期:母乳喂养
前面我们了解到,早期断奶与自闭症风险增加相关。很多自闭症患者较少接受母乳喂养,这表明母乳中含有ARA、EPA和DHA,是婴儿大脑发育的最佳饮食。
随着年龄增长:其他饮食
多酚及其代谢物
现有的研究确认了流行病学数据,表明多酚及其代谢物可能有助于促进大脑健康。提出的作用机制包括抗氧化活动、改善血管功能和脑部血流、直接增强神经元信号传递、缓冲钙离子、增强神经保护性应激蛋白和减少应激信号。
线粒体功能障碍在自闭症谱系障碍、神经退行性疾病和一般脑老化的发病机制中得到了关注。线粒体常被认为是氧化应激的启动者和目标,植物多酚代谢物可能具有保护作用。
体外研究在生理相关剂量下测试了选定多酚代谢物对高级糖化终产物形成的抑制能力以及对人类神经元细胞中轻度氧化应激的对抗能力。例如:
药用植物的多酚提取物
少数研究探讨了来自药用植物的多酚提取物对自闭症动物模型的影响,发现:
注:尚需确定这些高剂量植物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仅与减轻丙戊酸引起的氧化损伤相关,还是在氧化损伤可能只是一个影响因素的神经病理情况下更具广泛相关性。
——黄酮类化合物
肠道菌群对黄酮类化合物的吸收转化
估计有95%的膳食植物多酚在上肠道内无法消化和吸收,并最终到达结肠中的肠道微生物群。一些黄酮类糖苷进入结肠,被肠道菌群分解为更简单的代谢物,比如:
黄酮类化合物对肠道菌群的调节
膳食类黄酮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自闭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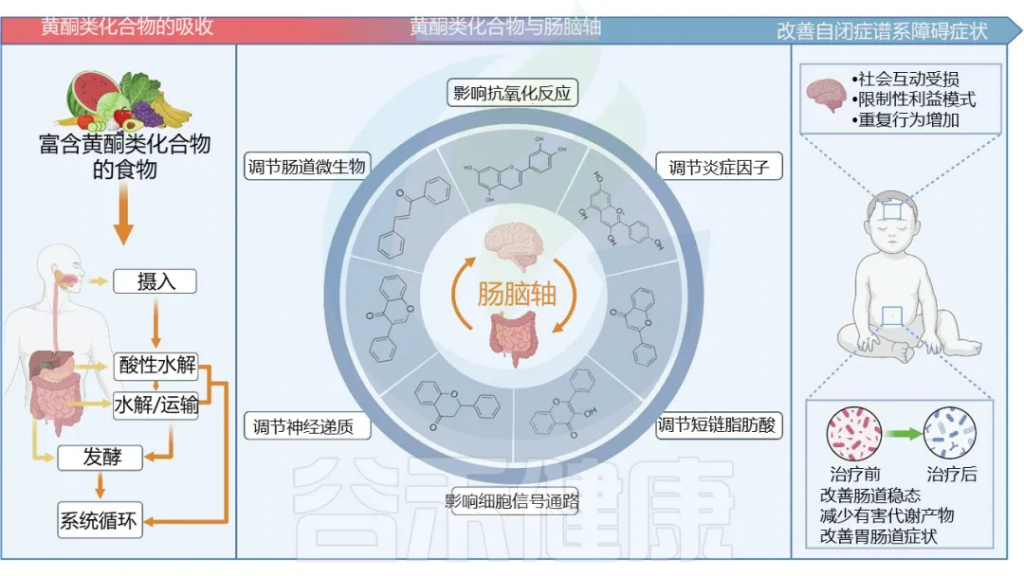
doi.org/10.1016/j.foodres.2024.114404
黄酮类化合物抗自闭症作用的实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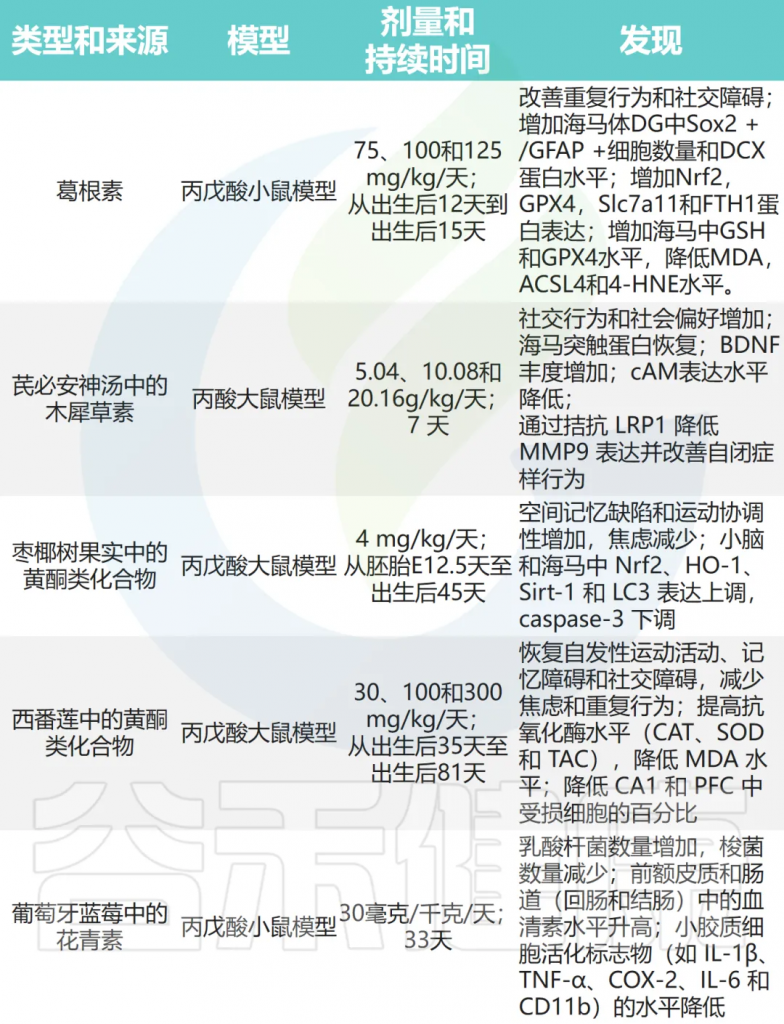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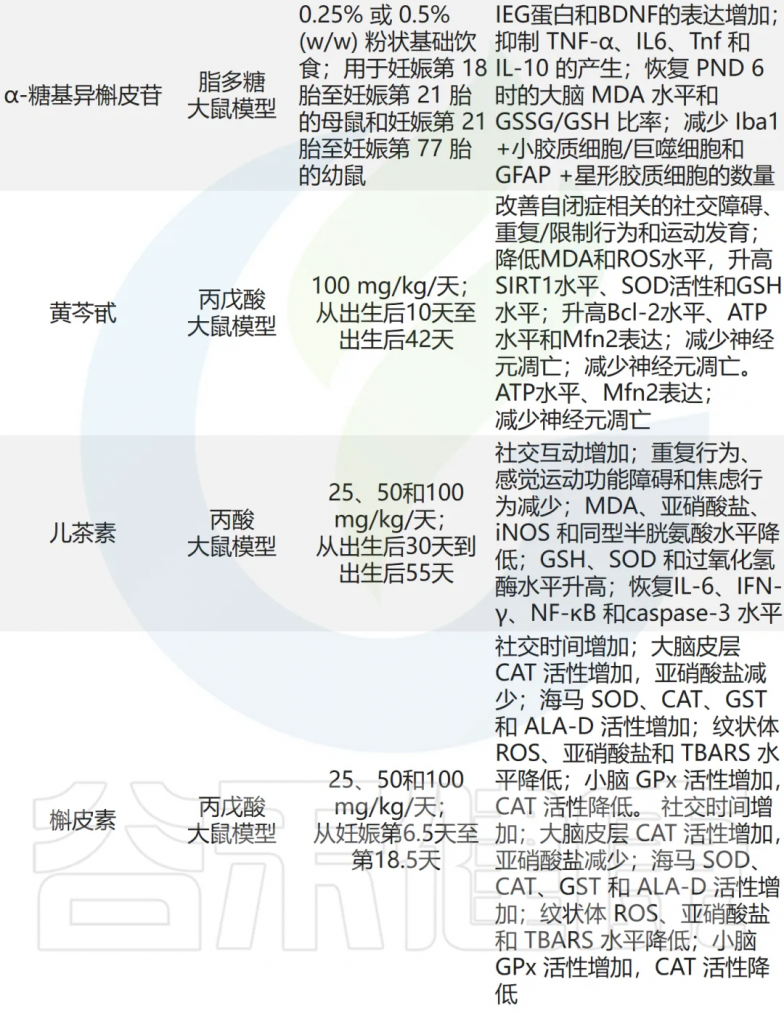
doi.org/10.1016/j.foodres.2024.114404
肥胖和不良饮食与抑郁症和自闭症谱系障碍发病率增加有关。同样,母亲的不良饮食(特别是高脂肪饮食),健康状况(特别是肥胖/代谢综合症),会影响胎儿和新生儿的大脑发育过程,从而增加焦虑、抑郁、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自闭症等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
神经内分泌系统,特别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代表了肠道环境和中枢神经系统(CNS)之间的主要通信通道。
在动物模型中,使用各种益生菌微生物干预,既包括乳酸杆菌也包括双歧杆菌,已显示能够减轻标准动物应激挑战下的类似焦虑行为。
婴儿双歧杆菌
L. helveticus R0052 和 B. longum R0175
L. rhamnosus JB-1
脆弱拟杆菌NCTC 9343
注:脆弱拟杆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菌种,里面既有潜在的益生菌株,也有致病的病原菌株,具体可以查看我们以前文章:
益生元
最近的研究表明,饮食中补充益生元发酵纤维,可以选择性地刺激对人体有益的肠道细菌,如双歧杆菌,从而对大脑产生重要变化。
实验动物在摄入果寡糖(FOS)或半乳寡糖(GOS)后,海马中的BDNF和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s)亚基NR1的表达增加,并且GOS似乎通过诱导肠道激素PYY来介导这一过程。FOS和GOS都能够上调肠道微生物群中短链脂肪酸的产生,特别是乙酸和丁酸,同时增加肠道双歧杆菌的相对丰度。
L-肌肽
胆固醇或DHA
从模拟人类婴儿营养的猪仔研究中,发现婴儿配方奶粉中的胆固醇补充会改变大脑中的氨基酸谱,降低谷氨酸、丝氨酸、谷氨酰胺、苏氨酸、β-丙氨酸、丙氨酸、蛋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和γ-氨基丁酸的浓度,同时增加甘氨酸和赖氨酸的浓度。
二十二碳六烯酸(DHA)也有类似的效果,但会降低牛磺酸水平,对异亮氨酸和赖氨酸没有影响。胆固醇或DHA膳食补充剂也会影响猪仔肝脏、肌肉和血浆中的氨基酸水平。DHA还会减少肌肉和大脑中的肌肽和氨的含量。
这些观察结果确实对食物选择或家庭饮食对营养可用性和代谢的影响有重要启示,进而影响早期儿童的大脑发育和功能,当然还需在人类队列中进一步研究其潜在机制。
药物
对自闭症儿童每周使用万古霉素治疗,可显著改善神经行为和胃肠道症状。
粪菌移植
一项开放标签研究对18名自闭症儿童进行了粪菌移植(每日口服8周),结果表明移植后其胃肠道症状和自闭症核心症状评分均有所改善。
移植后8周,受试者的肠道菌群多样性增加,厚壁菌门丰度下降,拟杆菌门和变形菌门丰度上升。
随访2年后,受试者的部分症状改善仍然维持。这提示通过重建肠道菌群可能成为干预自闭症的新策略。
关于粪菌移植,仍需更多深入研究。
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 是一组神经发育疾病,一般在 3 岁之前发病,目前的发病率在全世界逐渐升高,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饮食会影响和塑造肠道微生物群,孕期和幼儿期似乎是一个关键时期,尤其从哺乳/配方奶→断奶→成人“家庭”饮食的过渡过程中饮食和环境暴露影响较大。
人类微生物组对宿主代谢过程和膳食化合物加工的核心贡献,许多营养物质和摄入的化学物质必须经过肠道及肠道微生物,转化为生物可利用和活跃的中间产物,然后通过肝门静脉被吸收并在全身分布。
研究表明,大部分自闭症患者的肠道菌群异常,这可能与饮食习惯、抗生素使用等因素有关。同时,自闭症患者某些氨基酸水平也存在异常。
饮食作为塑造肠道微生物群的重要因素,可能在自闭症的发病中扮演重要角色。优化孕期和幼儿期的饮食结构,如母乳喂养、合理添加辅食、避免过多加工食品和添加剂等,有助于维持肠道菌群平衡,从而有助于大脑健康。
针对自闭症患者的饮食干预,如补充益生元、益生菌,调整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比例等,可能对改善部分症状有一定帮助。但由于自闭症的高度异质性,饮食干预的效果可能因人而异,还需要更多的结合个体化健康信息及相应症状进行个性化指导和干预。
此外,幼儿早期尤其6-12个月能够更早判别出自闭症风险,对于神经发育的改善和行为的扭转非常重要,希望临床上与相关机构能够合作共同推进自闭症的研究和个性化干预。
注:本账号内容仅作交流参考,不作为诊断及医疗依据。
主要参考文献:
Lou M, Cao A, Jin C, Mi K, Xiong X, Zeng Z, Pan X, Qie J, Qiu S, Niu Y, Liang H, Liu Y, Chen L, Liu Z, Zhao Q, Qiu X, Jin Y, Sheng X, Hu Z, Jin G, Liu J, Liu X, Wang Y. Deviated and early unsustainable stunted development of gut microbiota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Gut. 2022 Aug;71(8):1588-1599.
Ahrens A P, Hyötyläinen T, Petrone J R, et al. Infant microbes and metabolites point to childhood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J]. Cell, 2024, 187(8): 1853-1873. e15.
Chen, WX., Chen, YR., Peng, MZ. et al. Plasma Amino Acid Profile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 Southern China: Analysis of 110 Cases. J Autism Dev Disord 54, 1567–1581 (2024).
Chang, X., Zhang, Y., Chen, X. et al. Gut microbiome and serum amino acid metabolome alteration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Sci Rep 14, 4037 (2024).
Kieran M. Tuohy, Paola Venuti, Simone Cuva, et al, Chapter 15 – Diet and the Gut Microbiota – How the Gut: Brain Axis Impacts on Autism, 2015, Pages 225-245,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1994)
Anastasescu, C.M.; Gheorman, V.; Popescu, F.; Stoicănescu, E.-C.; Gheorman, V.; Riza, A.-L.; Badea, O.; Streață, I.; Militaru, F.; Udriștoiu, I. Serum Amino Acid Profiling in Children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Insights from a Single-Center Study in Southern Romania. Healthcare 2023, 11, 2487
V. Hughes. Epidemiology: complex, disorder, Nature, 491 (2012), pp. S2-S3
S. Baron-Cohen, F.J. Scott, C. Allison, et al., Prevalence of autism-spectrum conditions: UK school-based population study. Br J Psychiatry, 194 (2009), pp. 500-509
T.S. Brugha, S. McManus, J. Bankart, et al., Epidemiology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adults in the community in England Arch Gen Psychiatry, 68 (2011), pp. 459-466
B.S. Abrahams, D.H. Geschwind., Advances in autism genetics: On the threshold of a new neurobiology, Nat Rev Genet, 9 (2008), pp. 341-355
Brister, D.; Rose, S.; Delhey, L.; Tippett, M.; **, Y.; Gu, H.; Frye, R.E. Metabolomic Signature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J. Pers. Med. 2022, 12, 1727.
S. Ozonoff, B.J. Williams, R. Landa, Parental report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with regressive autism: The delays-plus-regression phenotype, Autism, 9 (2005), pp. 461-486
S. Ozonoff, G.S. Young, M.B. Steinfeld, et al., How early do parent concerns predict later autism diagnosis?
J Dev Behav Pediatr, 30 (2009), pp. 367-375
G. Esposito, P. Venuti, Symmetry in infancy: Analysis of motor development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Symmetry, 1 (2009), pp. 215-225
Zhao Y, Wang Y, Meng F, Chen X, Chang T, Huang H, He F, Zheng Y. Altered Gut Microbiota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 Early Childhood. Neuroscience. 2023 Jul 15;523:118-131.
G. Esposito, P. Venuti, F. Apicella, F. Muratori, Analysis of unsupported gait in toddlers with autism, Brain and Development, 33 (2011), pp. 367-373
F. Happé, A. Ronald, R. Plomin, Time to give up on a single explanation for autism, Nat Neurosci, 9 (2006), pp. 1218-1220
T. Charman, C.R.G. Jones, A. Pickles, E. Simonoff, G. Baird, F. Happé, Defining the cognitive phenotype of autism, Brain Res, 1380 (2011), pp. 10-21
P. Krakowiak, C.K. Walker, A.A. Bremer, et al.,Maternal metabolic conditions and risk for autism and other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Pediatrics, 129 (2012), pp. e1121-e1128
J.A. Hollway, M.G. Aman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of sleep disturbance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Res Dev Disabil, 32 (2011), pp. 939-962
Shen L, Liu X, Zhang H, Lin J, Feng C, Iqbal J. Biomarker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Current progress. Clin Chim Acta. 2020 Mar;502:41-54.
C.A. Molloy, P. Manning-Courtney,Prevalence of chronic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Autism, 7 (2003), pp. 165-171
D.V. Keen , Childhood autism, feeding problems and failure to thrive in early infancy: Seven case studies, Eur Child Adolesc Psychiatr, 17 (2008), pp. 209-216
L.G. Bandini, S.E. Anderson, C. Curtin, et al., Food selectivity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nd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J Pediatr, 157 (2010), pp. 259-264
S.A. Cermak, C. Curtin, L.G. Bandini, Food selectivity and sensory sensitivity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J Am Diet Assoc, 110 (2010), pp. 238-246
Y. Martins, R.L. Young, D.C. Robson, Feeding and eating behavior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J Autism Dev Disord, 38 (2008), pp. 1878-1887, View at publisher
E. Cornish, A balanced approach towards healthy eating in autism, J Hum Nutr Diet, 11 (1998), pp. 501-509
P. Whiteley, J. Rodgers, D. Savery, P. Shattock, A gluten-free diet as an intervention for autism and associated spectrum disorders: Preliminary findings, Autism, 3 (1999), pp. 45-65
K. Fitzgerald, M. Hyman, K. Swif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Glob Adv Health Med, 1 (2012), pp. 62-74
E. Courchesne, K. Campbell, S. Solso, Brain growth across the life span in autism: age-specific changes in anatomical pathology, Brain Res, 1380 (2011), pp. 138-145
M. Rutter, Aetiology of autism: findings and questions, J Intell Disabil Res, 49 (2005), pp. 231-238, View at publisher
J.J. Michaelson, Y. Shi, M. Gujral, et al.
Whole-genome sequencing in autism identifies hot spots for de novo germline mutation, Cell, 151 (2012), pp. 1431-1442
B.N. Vardarajan, A. Eran, J.Y. Jung, L.M. Kunkel, D.P. Wall, Haplotype structure enables prioritization of common markers and candidate gene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Transl Psychiatry, 3 (2013), p. e262
Yu X, Qian-Qian L, Cong Y, Xiao-Bing Z, Hong-Zhu D. Reduction of essential amino acid levels and sex-specific alterations in serum amino acid concentration profile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Psychiatry Res. 2021 Mar;297:113675.
J. Veenstra-Vanderweele, R.D. Blakely
Networking in autism: Leveraging genetic, biomarker and model system findings in the search for new treatments, Neuropsychopharmacol, 37 (2012), pp. 196-212
K.T.E. Kleijer, M.J. Schmeisser, D.D. Krueger, et al. Neurobiology of autism gene products: towards pathogenesis and drug targets, Psychopharmacology (Berl), 231 (6) (2014), pp. 1037-1062
Li H, Dang Y, Yan Y. Serum interleukin-17 A and homocysteine level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BMC Neurosci. 2024 Mar 12;25(1):17.

谷禾健康

俗话说:“病从口入”。饮食是决定个人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饮食与疾病的发展有关,特别是胃肠道(GI)疾病。
与膳食相关的症状发生率很高,例如在吸收不良(如乳糖不耐症)情况下出现的腹痛和腹泻;乳糜泻、食物过敏人群在食用麸质类后出现的腹胀、腹痛、水肿;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在摄入一些刺激性食物后(酸、辣)的腹痛、排便异常等。饮食作为胃肠道症状的驱动因素已经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然而对出现食物相关症状的机制仍不太清楚。随着对肠道微生物研究的深入,肠道微生物群也被认为是胃肠道疾病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促使人们研究微生物作为饮食和宿主生理之间的关键联系。
同样的饮食摄入效果会因人体的健康状况以及肠道个性化的微生物群落而产生的不同的效果。例如低聚果糖(FOS)会加重炎症性肠病(IBD)患者的炎症,但在健康个体中却具有抗炎作用。麸质、小麦、牛奶和大豆等物质直接注射到粘膜下层可以通过激活IBS患者的肥大细胞来引发免疫反应,但在健康受试者中则不然。还有纵向研究报告称,饮食蛋白质摄入量相似,但IBS-D患者的色氨酸和色胺水平(而非吲哚衍生物)高于健康人。另一方面,结肠内乙酸盐可增强对结肠直肠扩张的敏感性。具体影响可能取决于宿主健康和肠道中的整体代谢环境。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个性化的饮食干预在预防和治疗胃肠道疾病中的潜力。个性化饮食不仅考虑到个体的遗传背景、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还特别关注其独特的微生物群组成。通过分析和调整个体的饮食,可以优化肠道微生物群的平衡,增强其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在本文中,主要关注两种胃肠道疾病:肠易激综合征和炎症性肠病。宿主和肠道微生物群对膳食营养素的利用决定肠道中最终的生物活性代谢物特征以及这些代谢物对胃肠道生理学的生物效应。此外强调了单个代谢物的不同作用如何影响不同的胃肠道疾病,类似的饮食干预对多种疾病状态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
食物在肠道内会被肠道菌群代谢、转化。食物成分本身的性质,加上肠道菌群作用后的代谢产物,共同决定了食物对人体健康的作用。因此,仅考虑食物成分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个人肠道菌群状况,两者结合才能判断食物的健康效应。
例如,传统观点认为,大部分可消化的食物成分会通过小肠表面吸收。剩余的不可消化成分传递到远端,作为肠道微生物群的能量来源,产生如短链脂肪酸(SCFA)等发酵最终产物。
然而,这种观点简化了过程。肠道微生物群不仅依赖于难以消化的膳食成分,还可以从宿主上皮表面粘液层中的糖蛋白和多糖获取营养,尤其是在碳水化合物缺乏的情况下,如低纤维摄入时。
★ 不同的肠道微生物结构造就了独特的代谢
肠道微生物群与营养物质的利用:肠道微生物群如何利用营养物质取决于具体的营养成分和每种微生物的代谢能力。不同微生物有不同的代谢途径,使得营养利用变得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化学计量问题。
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肠道中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可以影响宿主和微生物之间的营养合作动态。比如,在体内平衡期间,宿主在小肠中有效吸收氨基酸,从而使得一些微生物无法获得这些氨基酸。
营养物质的竞争:某些细菌(如梭状芽孢杆菌)如果过度生长,就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如膳食蛋白质有限时)与宿主竞争氨基酸的吸收。
营养层次与利用率:更高级的营养物质(如单糖和双糖)的增加会降低某些细菌对氨基酸的利用率。这意味着营养物质的可用性对微生物代谢有影响。
调节信号的作用:肠道中的特定信号分子(如短链脂肪酸或肽YY)也能影响宿主对营养物质的利用方式。
在下面小节中,我们重点介绍两个例子(色氨酸和膳食纤维),以说明宿主和肠道微生物群在营养利用上的差异如何影响宿主的生理学。
色氨酸是一种必需氨基酸,是宿主神经递质血清素 (5-HT;胃肠道生理的重要调节剂) 的前体,也是微生物代谢物(如色胺和吲哚衍生物)的前体。色氨酸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饮食。
色氨酸被整合到蛋白质中并被宿主利用,通过不同的途径产生5-HT(1-2%)和犬尿氨酸(∼95%)。肠道微生物成员如Ruminococcus gnavus和Clostridium sporogenes含有色氨酸脱羧酶,可将色氨酸转化为色胺,而色胺则是血清素受体4(5-HT 4R)的激动剂。
同时,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和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等细菌含有色氨酸酶,这种酶有助于从色氨酸产生吲哚和吲哚衍生物。如吲哚乙酸和吲哚丙酸,可以通过激活芳烃受体(AHR)对宿主的免疫途径发挥生物学效应。
这些细菌产生的色氨酸衍生生物活性代谢物的水平取决于肠道菌群的组成、肠道细菌利用色氨酸的程度和位置,以及宿主色氨酸利用相关基因的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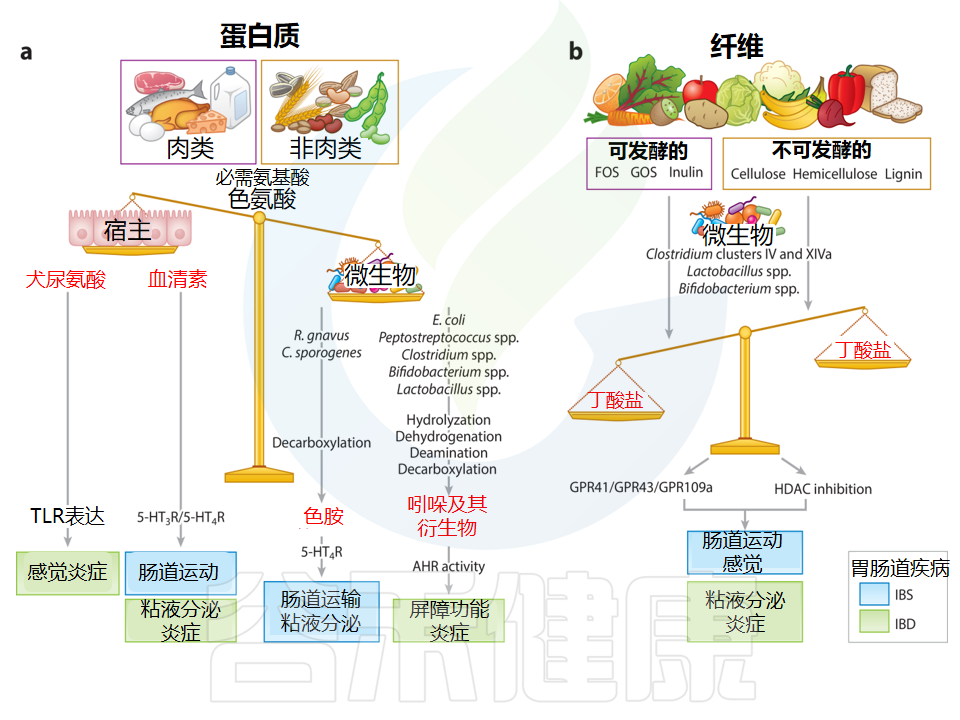
Jadhav A,et al.Annu Rev Nutr.2023
饮食衍生的代谢物可改变多种生物途径,而这些途径是多种胃肠道(GI)疾病的基础。
a)饮食蛋白质,包括肉类和非肉类(例如谷物、种子和坚果),都含有不同水平的氨基酸,例如色氨酸。可被宿主代谢产生犬尿氨酸和血清素(5-HT)。肠道微生物群还可以通过不同的代谢途径将色氨酸转化为色胺或吲哚和吲哚衍生物。色胺通过激活血清素受体4来增加肠道分泌和杯状细胞的粘液释放,而吲哚和吲哚衍生物是芳烃受体(AHR)的配体,在调节屏障功能和免疫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
b)膳食纤维包括可发酵[例如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和菊粉]和不可发酵(例如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纤维。根据肠道细菌的类型和纤维的类型,它们会发酵成不同的短链脂肪酸,例如丁酸盐和乙酸盐。丁酸盐可以增加血清素合成,增强结肠收缩力,缓解内脏过敏,增强屏障。
色氨酸衍生的生物活性代谢物取决于肠道菌群,那么纤维的发酵产物与微生物组成有关吗?
富含膳食纤维的饮食被认为是有益的,因为肠道微生物群会发酵纤维产生丁酸、乙酸和丙酸等短链脂肪酸,这些短链脂肪酸会影响宿主生理学的重要方面,包括代谢、细胞周转和免疫系统。
然而,人类研究表明,个体对纤维摄入量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基于纤维类型的差异也很大。这并不奇怪,因为纤维是一个总称,包括具有不同连接和分子结构的不同碳水化合物群体。不同细菌携带的基因使它们能够利用具有特定连接和结构的碳水化合物。
膳食纤维的生物学效应取决于纤维的成分、个体肠道微生物群代谢特定纤维的潜力以及不同发酵最终产物的相对量。
▸ 低聚果糖在健康人体和炎症性肠病患者中作用大为不同
编辑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低聚果糖(FOS)会加重炎症性肠病(IBD)患者的炎症,而肠道细菌代谢它会减轻其在活动性炎症的IBD患者的炎症作用。
有趣的是,低聚果糖在健康个体中具有抗炎作用。因此,低聚果糖的炎症潜力取决于肠道微生物组成以及宿主疾病状态。
产生的短链脂肪酸的水平和类型可能因纤维组成和肠道微生物群而异。在饮食中添加菊粉会增加丁酸盐,但会降低乙酸盐的产生。相反,在消耗相同纤维量的患者亚组中,粪便丁酸水平较低,这归因于产生丁酸的细菌水平较低。这些结果有助于解释对纤维反应的个体间差异。
鉴于微生物代谢产物对宿主发挥多效性作用,因此,相同的代谢物可以影响多种宿主功能,每种功能都可能与不同的疾病状态相关。
色氨酸代谢物如色胺和5-HT会影响胃肠道转运,这与肠脑轴(DGBA)相关,而色胺和吲哚衍生物可以改变粘液和免疫反应,这对炎症性肠病具有影响。
同样,丁酸等发酵终产物会影响胃肠道运动以及上皮屏障功能,这分别与DGBA和IBD相关。
肠道微生物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饮食,它会对肠道微生物组产生长期和短期影响,它们会随着个体饮食的变化而变化。
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化社会个体饮食的成分显著改变和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减少能证明习惯饮食的长期影响。
▸ 低纤维饮食会导致肠道微生物多样性逐渐减少
研究证明,低纤维饮食会导致人肠道微生物多样性逐渐丧失,这在早期阶段是可逆的,但可能会导致后代特定分类群的灭绝,而仅靠饮食干预是无法恢复的。
这一观察结果为西方人群中观察到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较低提供了一种解释,并强调了微小的变化是如何在几代人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因此,个体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可能反映了人群的长期饮食模式。
▸ 短期饮食改变也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但可逆
短期的饮食改变也会改变肠道微生物组。虽然这些变化在不同程度上是可逆的,这取决于人体的基本恢复力和适应性,但短期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慢性病患者症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不同。
这些短期影响也强调了微生物群导向的饮食干预作为治疗策略的潜力。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全球患病率约为11.2%。根据过去3个月内每周至少出现一次腹痛、伴有排便或大便频率或形式的变化并在过去6个月内出现症状进行诊断。
IBS一般可分为腹泻型(IBS-D)、便秘型(IBS-C)、混合型和未分类亚型。
胃肠道运输、分泌、感觉、免疫激活、肠道通透性和肠脑轴的改变等生理变化是IBS症状的基础。与IBS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宿主遗传、压力、抗生素使用和幼儿期经历,但饮食最常被认为是肠易激综合征的潜在罪魁祸首。基于人群的研究表明,近70%的IBS患者认为自己存在食物不耐受。
饮食引起症状的机制仍在研究中,但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阐明IBS中由饮食驱动的症状背后的微生物群独立机制和微生物群依赖机制。
研究发现将食物抗原(例如麸质、小麦、牛奶和大豆)直接注射到粘膜下层可以通过激活IBS患者的肥大细胞来引发免疫反应,但在健康受试者中则不然。
他们进一步表明,肥大细胞激活会引起内脏疼痛,并通过组胺刺激内脏神经元的敏化增加肠道通透性。虽然这项研究证明了一种独立于微生物群的机制,但其他研究发现,富含可发酵寡糖、二糖、单糖和多元醇(FODMAP)的饮食也可以通过Toll样受体4(TLR4)途径激活肥大细胞,这表明肠道微生物群的参与。
据报道,IBS-D患者中受饮食影响的微生物产物(如脂多糖和鞭毛蛋白)的血清水平显著升高。
脂多糖(LPS)是肠道细菌的一组异质细胞壁成分,充当TLR4的配体,在食用高脂肪饮食或高FODMAP饮食的个体中也会增加。除了在肥大细胞激活中的作用外,不同形式的LPS还能促进肠神经元的存活并增强平滑肌收缩力,这表明LPS浓度或结构的差异可能会驱动不同的宿主反应。
除微生物细胞壁成分外,宿主微生物代谢膳食成分产生的代谢终产物也可影响胃肠道生理,从而引发胃肠道症状。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等短链脂肪酸由特定肠道微生物成员产生,其水平取决于微生物组成和膳食纤维摄入量。
丁酸盐是一种多效性代谢物,可通过G蛋白偶联受体(GPCR)直接发出信号,并通过表观遗传调控改变转录反应。丁酸盐可以浓度依赖性方式改变肠嗜铬细胞中的5-HT合成,通过直接影响肠道神经肌肉装置增加结肠收缩力,增强肠道上皮屏障,并通过与肠道神经胶质细胞相互作用调节内脏高敏感性。
另一方面,结肠内乙酸盐可增强对结肠直肠扩张的敏感性。具体影响可能取决于宿主健康和肠道中的整体代谢环境。
饮食、宿主粘液和微生物代谢都是肠道中氨基酸的主要来源。一项纵向研究报告称,尽管饮食蛋白质摄入量相似,但IBS-D患者的色氨酸和色胺水平(而非吲哚衍生物)高于健康人。
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肠道微生物群增加了色氨酸的产生和转化,或由于宿主对其利用率降低。胰蛋白酶激活肠细胞上的5-HT4R,进而增加肠液分泌。
另一项研究发现,IBS患者和健康受试者在结肠组织对色胺的5-HT4R表达或反应方面没有差异,这表明较高的色胺水平可能是腹泻的重要驱动因素。
在腹泻型(IBS-D)患者中,其他饮食和微生物驱动的途径也被描述了。无乳糜泻的IBS-D患者中经常报道麸质不耐症,这似乎部分依赖于宿主基因型和肠道微生物群组成。据报道,与阴性患者相比,HLA-DQ2/HLA-DQ8 阴性的IBS-D患者在无麸质饮食后腹胀显著减轻。
HLA-DQ2和HLA-DQ8基因是导致乳糜泻的主要基因。
其他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可以对麸质的消化和免疫原性产生不同的影响。麸质对IBS-D影响的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确定。
胆汁酸(BA)在肝脏中合成,储存在胆囊中,用于脂质乳化。膳食脂肪和姜黄是刺激初级胆汁酸释放到小肠中的重要因素。
近95%的初级胆汁酸在远端小肠中被重新吸收,剩余的初级胆汁酸在进入结肠后被肠道微生物去偶联、脱羟基和差向异构化为次级胆汁酸。
初级胆汁酸如鹅去氧胆酸通过氯化物通道增加结肠分泌,并降低健康个体的直肠感觉阈值。在啮齿类动物模型中,鹅去氧胆酸通过激活核受体法尼素X受体、释放神经生长因子和在背根神经节中下游表达瞬时受体电位香草素1(TRPV1),影响内脏敏感性。
▸ IBS-D患者的胆汁酸水平较高
IBS-D患者的粪便胆汁酸水平可能更高,这归因于胆汁酸吸收不良或肠道微生物群减少导致的继发性胆汁酸转化减少。因此,高脂肪饮食可以通过调节胆汁酸的释放,直接或通过胆汁酸的微生物代谢间接改变胃肠道生理学。
除此之外,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感染后IBS-D患者的细菌编码的β-葡萄糖醛酸酶水平较低,这种酶可以解除胆红素的结合。
这些患者的结合胆红素水平较高,导致对宿主蛋白酶的抑制作用降低,肠道通透性增加,从而引发内脏超敏反应。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特发性、慢性、使人衰弱的炎症性胃肠道疾病,包括两种疾病——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克罗恩病表现为遍布整个胃肠道的斑片状透壁炎症,而溃疡性结肠炎则是结肠的持续性粘膜炎症。
这两种疾病都是由于环境、遗传和免疫因素共同作用下,对肠道微生物信号产生的不受控制的炎症反应引起的。从流行病学角度来看,IBD曾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的疾病,欧洲和北美的发病率最高。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IBD的高发区已大幅向东方扩展,在非洲、亚洲(如印度每10万人9.3例,中国每10万人3.3例)和南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发病率迅速上升。
▸ 炎症性肠病的风险升高与饮食改变紧密相关
这些流行病的转变与全球饮食模式的转变相吻合,包括引入包装和加工食品;广泛接受和使用食品添加剂、防腐剂和抗生素;推广快餐连锁店,同时减少针对特定地区的当地饮食。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饮食是形成炎症性肠病(IBD)的关键环境因素之一,从低发病地区迁移到高发病地区的人群中,IBD的患病率有所上升。此外,法国和西班牙的南北流行率差异也很微妙。在这些国家的北部地区观察到较高的IBD负荷,那里的个人食用更多的黄油、土豆、火腿、奶酪、香肠和啤酒,而南部地区的个人则遵循地中海饮食,主要由橄榄、新鲜水果和蔬菜、葡萄酒和海鲜组成。
饮食成分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炎症性肠病的病理生理学,而且还可以通过其在肠道微生物群中的转化间接影响疾病进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其中的具体机制。
饮食在炎症性肠病发病机制和预防中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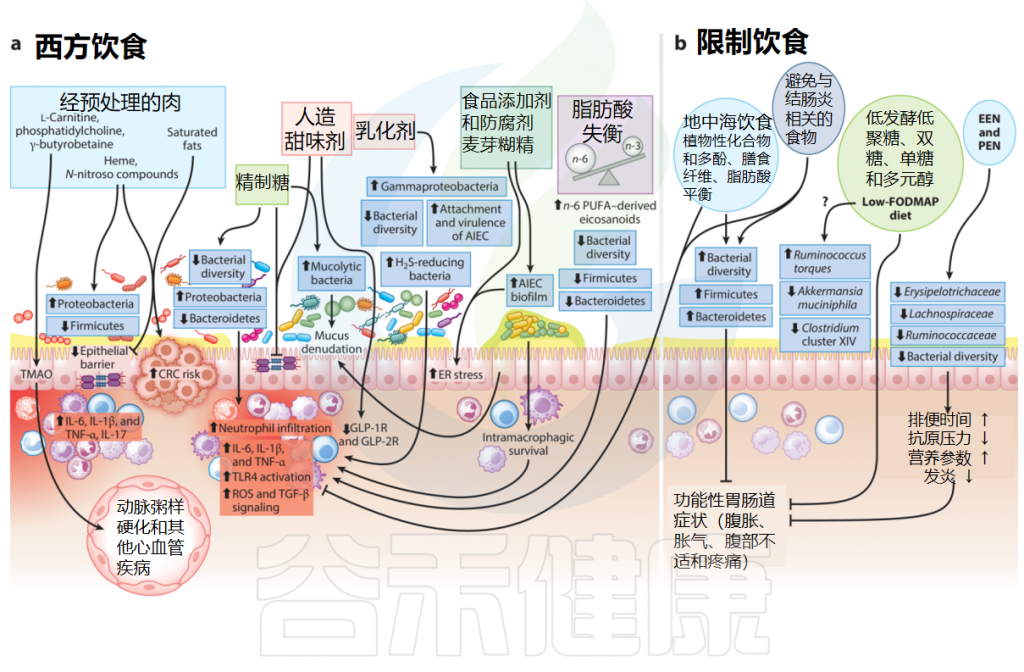
Jadhav A,et al.Annu Rev Nutr.2023
膳食中的大量营养素、微量营养素、添加剂和热量含量之间相互作用复杂;宿主免疫、遗传学和肠道微生物组可能是炎症性肠病(IBD)风险和临床病程的重要决定因素。
▸ 红肉饮食可能加剧炎症性肠病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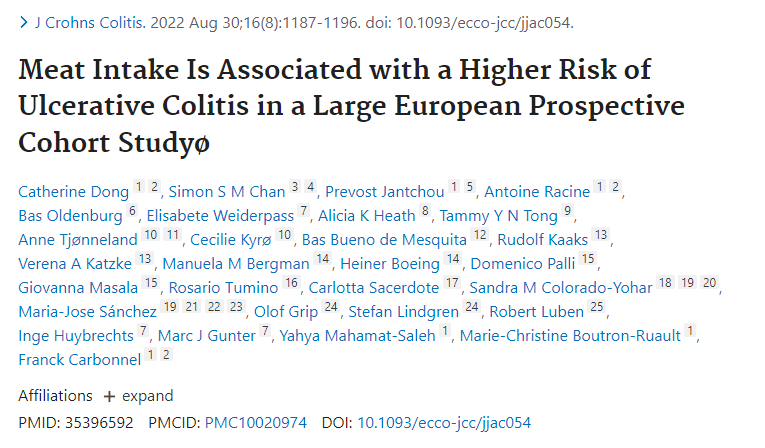
最近一项由125445名参与者组成的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西方饮食(包括红肉、家禽和加工肉类等动物蛋白)与溃疡性结肠炎发展可能性增加之间存在关联。
此外,红肉加剧炎症性肠病的影响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欧洲癌症和营养前瞻性调查队列表明,红肉摄入增加了亚油酸摄入量,从而使溃疡性结肠炎风险增加超过一倍。
同时,一项法国大型前瞻性问卷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加工红肉的摄入,与克罗恩病患者死亡率的显著增加有关。
▸ 红肉中的左旋肉碱等物质经微生物转化为氧化三甲胺与炎症呈正相关
红肉主要由蛋白质、脂肪和血红素组成,这些成分水平的增加会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进而对上皮细胞更新和肠道屏障完整性产生负面影响,并加剧肠道炎症。
值得注意的是,红肉中富含左旋肉碱、磷脂酰胆碱和γ-丁甜菜碱,这些物质通过肠道微生物代谢转化为三甲胺。三甲胺在宿主肝脏中通过含黄素单加氧酶形成氧化三甲胺(TMAO)。动物研究和人类流行病学研究表明,TMAO与炎症、心血管疾病、结直肠癌和死亡率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与传统的饮食习惯不同,西方饮食富含简单的精制碳水化合物、饱和脂肪以及超加工食品,而新鲜水果和蔬菜、豆类、全谷物和膳食纤维的含量较低。
超加工食品是在已经加工过的食品基础上再加工的食品,这类食品通常是高糖、高脂、高热量的食品。可涵盖多种食物,包括肉类、淀粉类零食、乳制品、豆类、水果和蔬菜。
研究报告了西方饮食对人类健康的不利影响,并将其与肥胖、糖尿病、炎症性肠病、慢性肾病和其他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联系起来。食品的(超)加工旨在提高其保质期、适口性以及储存和分销的便利性,其中涉及掺入许多非天然成分和添加剂,例如人造香料、稳定剂、防腐剂和乳化剂。
▸ 超加工食品的摄入量较高与炎症性肠病风险增加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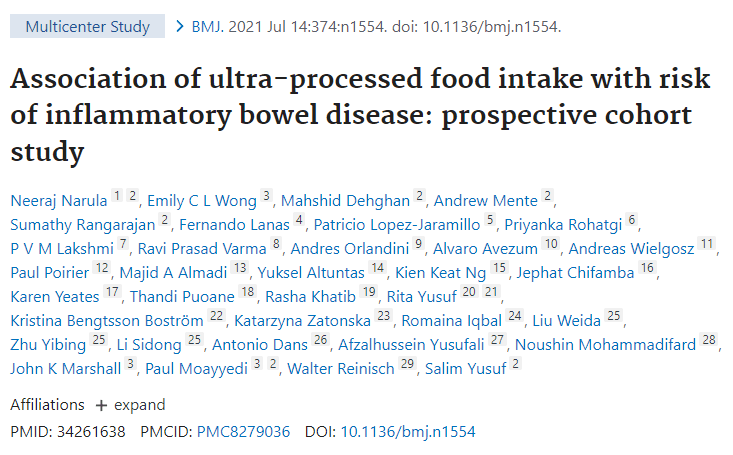
最近一项针对来自7个地理区域 21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大型前瞻性队列(116,087名成年人)的研究发现,超加工食品的摄入量较高与炎症性肠病风险呈正相关;然而,未加工的白肉、红肉、乳制品、淀粉、水果和蔬菜的摄入与炎症性肠病的发病率无关。
研究发现,炎症性肠病(IBD)风险与非酒精含糖饮料的消费存在正相关关系。
▸ 含糖饮料摄入过多增加炎症性肠病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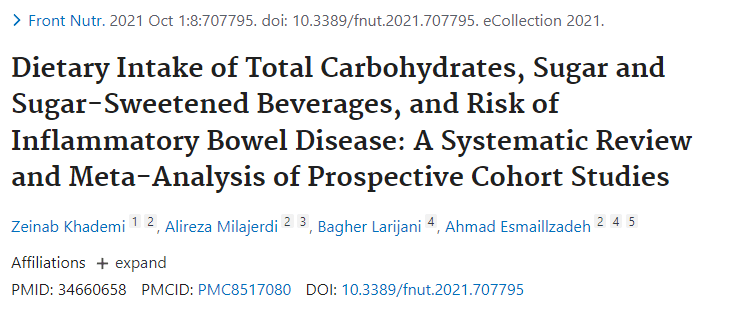
最近的两项荟萃分析整合了关于饮料摄入量与IBD风险的观察性研究,表明高摄入量的含糖饮料与IBD风险增加相关。实验显示,高膳食糖摄入与炎症诱导和肠道微生态失调有关。一项基于问卷的研究比较了IBD患者与健康人群的饮食模式,发现IBD患者的含糖饮料消费量更高。
阿斯巴甜、糖精、安赛蜜和三氯蔗糖等人造甜味剂因其在不增加额外热量的情况下赋予食物甜味而广泛流行。然而,动物研究和健康人类试验报告称,这些非营养性甜味剂降低了肠道微生物多样性,使肠道炎症永久化,通过增加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成员和减少有益微生物(如瘤胃菌科、毛螺菌科和梭状芽孢杆菌群XIVa)的比例来改变肠道微生物群,并损害肠道屏障的完整性。
▸ 麦芽糊精会加剧肠道炎症
麦芽糊精(E1400)是一种重要的食品添加剂,可用作加工食品的增稠剂,在小鼠结肠炎模型中,它通过诱导内质网应激和改变粘液层,以剂量依赖性方式加剧肠道炎症。小鼠模型中的报告还表明,麦芽糊精通过调节细菌基因表达,促进克罗恩病相关的粘附侵袭性大肠杆菌形成生物膜。
▸ 防腐剂会降低肠道微生物多样性
加工食品中的防腐剂会加剧有害影响。苯甲酸钠(E211)、亚硝酸钠(E250)和山梨酸钾(E202)这三种最常用的防腐剂会降低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在人类肠道微生物群相关的小鼠模型中,变形菌门增加,梭状芽胞杆菌的减少。
注:尽管人类和动物研究已经提供了关于这些非营养性膳食添加剂对肠道菌群失调和肠道健康的负面影响的机制见解,但仍缺乏评估这些甜味剂对炎症性肠病人群影响的人体随机对照试验。
▸ 乳化剂过量食用会导致肠道微生物失调并促进慢性炎症
类似地,合成乳化剂,如聚山梨酯80和羧甲基纤维素,被用作增强质地和延长保质期的添加剂。在动物研究中,这些乳化剂被广泛认为会导致肠道微生态失调并促进慢性炎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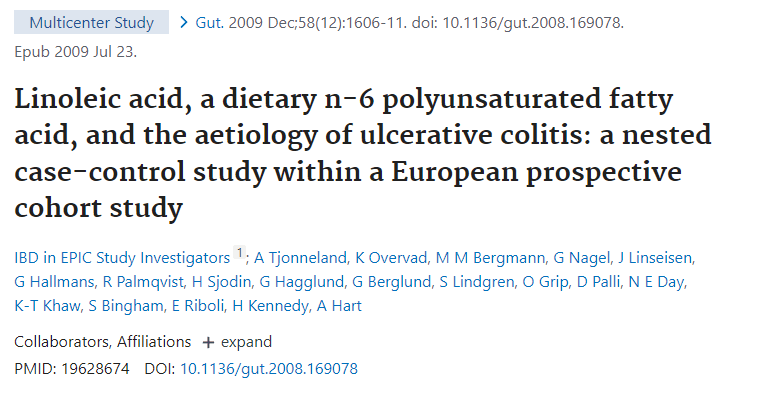
▸ 摄入过多的脂肪增加炎症性肠病风险
进行的一项大型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基于超过200,000名参与者的食物频率调查问卷,显示ω-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与溃疡性结肠炎(UC)风险增加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高摄入总脂肪、ω-6多不饱和脂肪酸和肉类会增加患溃疡性结肠炎的风险;高摄入饱和脂肪、ω-6多不饱和脂肪酸和肉类也会增加患克罗恩病的风险。
▸ ω-6脂肪酸在炎症性肠病中具有促炎性
虽然主要的膳食ω-3不饱和脂肪酸,即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及其下游类二十烷酸具有抗炎特性,但ω-6多不饱和脂肪酸,如花生四烯酸(AA)及白三烯、羟基二十碳四烯酸、脂氧素和环氧二十碳三烯酸等在炎症性肠病中表现出强烈的促炎活性。
这些介质增强中性粒细胞的趋化性;增强血管通透性;以及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例如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细胞介素(IL)-1β、IL-6和IL-8。有趣的是,这些脂肪酸介质的代谢在炎症粘膜中发生了改变,ω-6 花生四烯酸水平较高,ω-3 EPA水平较低,这表明脂肪酸代谢与炎症性肠病之间存在关联。
▸ ω-6促进肠道炎症与肠道微生物失调相关
最近的动物研究和人体试验已经将饮食中的ω-6多不饱和脂肪酸与肠道微生物微生态失调联系起来。γ-亚麻酸水平越高,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越高;肠道微生物多样性降低;有益微生物如普雷沃菌属(Prevotella)、Odoribacter、粪杆菌属、Paraprevotella、经黏液真杆菌属(Blautia)和丁酸弧菌属,以及梭菌目、Rikenellaceae和Coriobacteriaceae的成员减少。
在断奶阶段补充ω-6高脂肪饮食的小鼠显示,成年期结肠炎症和增生性病变的数量增加,厚壁菌门、梭状芽孢杆菌和毛螺菌属成员显著减少。在衰老小鼠模型中,补充ω-6也有类似效果,高ω-6脂肪饮食减少了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的有益成员,并导致肠道炎症。而补充鱼油可以逆转观察到的肠道微生态失调。
饮食成分在肠易激综合征和炎症性肠病等胃肠道疾病的病理生理学中发挥作用,使得通过饮食调节成为一种无创、更日常便利的治疗方法。
然而,目前的饮食策略缺乏特异性,在具有不同病理生理学的胃肠道疾病(如肠易激综合征和炎症性肠病)中也采用类似的方法。最常见的策略是限制、改变或补充营养。
▸ 可发酵碳水化合物不利于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健康
治疗肠易激综合征(IBS)最常见的饮食干预之一是减少FODMAP食物(通常是吸收不良的“可发酵”碳水化合物,包括果糖、乳糖、多元醇、果聚糖和低聚半乳糖)摄入12周,然后缓慢恢复上述食物组。
这类营养素被认为是疾病病理生理学的重要驱动因素。基于这样的观点:FODMAP会增加渗透负荷并产生更高水平的氢,从而导致管腔扩张。这些碳水化合物还会会被结肠中的细菌发酵,并引起肠易激综合征特有的腹胀、胀气和腹痛等症状。
▸ 低FODMAP饮食改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症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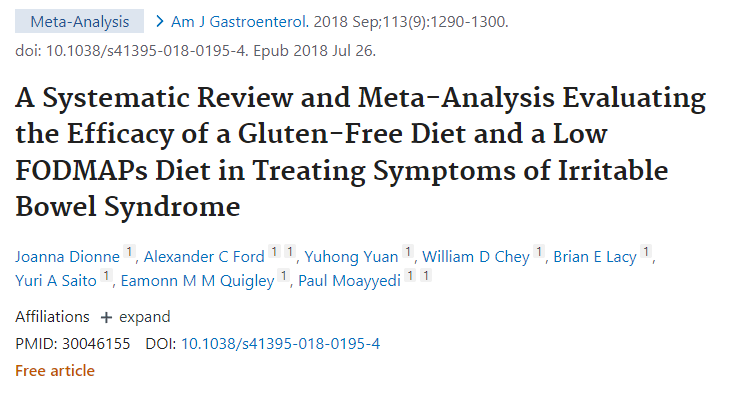
对澳大利亚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进行的一项关键研究显示,与西方饮食相比,低FODMAP饮食可显著改善症状。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纳入了397名患者的七项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干预相比,低FODMAP饮食可减轻整体症状。
然而,这项荟萃分析中的三项随机对照试验比较了低FODMAP饮食和严格的对照饮食,这些试验之间的异质性较小,且效应量有限。因此,虽然低FODMAP饮食能够使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受益,但数据的整体质量较低。
这一发现表明,几种不同的饮食干预措施都可以改善IBS症状,找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将会很有帮助。
▸ 低FODMAP饮食的效果会因肠道微生物组成不同而存在差异
有趣的是,一项针对健康受试者的研究发现,低FODMAP饮食并没有减少结肠体积,这表明症状改善背后可能存在其他机制。低FODMAP饮食的效应是与肠道菌群存在重要联系。
荟萃分析还发现无麸质饮食对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无显著益处。如上所述,这种影响可能取决于宿主基因型或其他宿主/环境因素。麸质主要存在于小麦、大麦和黑麦中,它们是高FODMAP饮食的一部分;因此,在部分患者中观察到的改善也可能是限制FODMAP的结果,而不仅仅是麸质的结果。
最近的一项综述显示,炎症性肠病患者中非腹腔麸质敏感性患病率很高;但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些患者采用无麸质饮食。临床前研究发现无麸质饮食可以改善炎症和通透性,但缺乏针对人类受试者的高质量前瞻性研究。关于麸质微生物降解对炎症性肠病和乳糜泻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领域。
地中海饮食(MD)富含水果、蔬菜、面包、谷物、豆类、坚果和初榨橄榄油,以及适量的乳制品、鱼和肉。地中海饮食被认为是一种平衡且健康的长期饮食选择。
地中海饮食和低FODMAP饮食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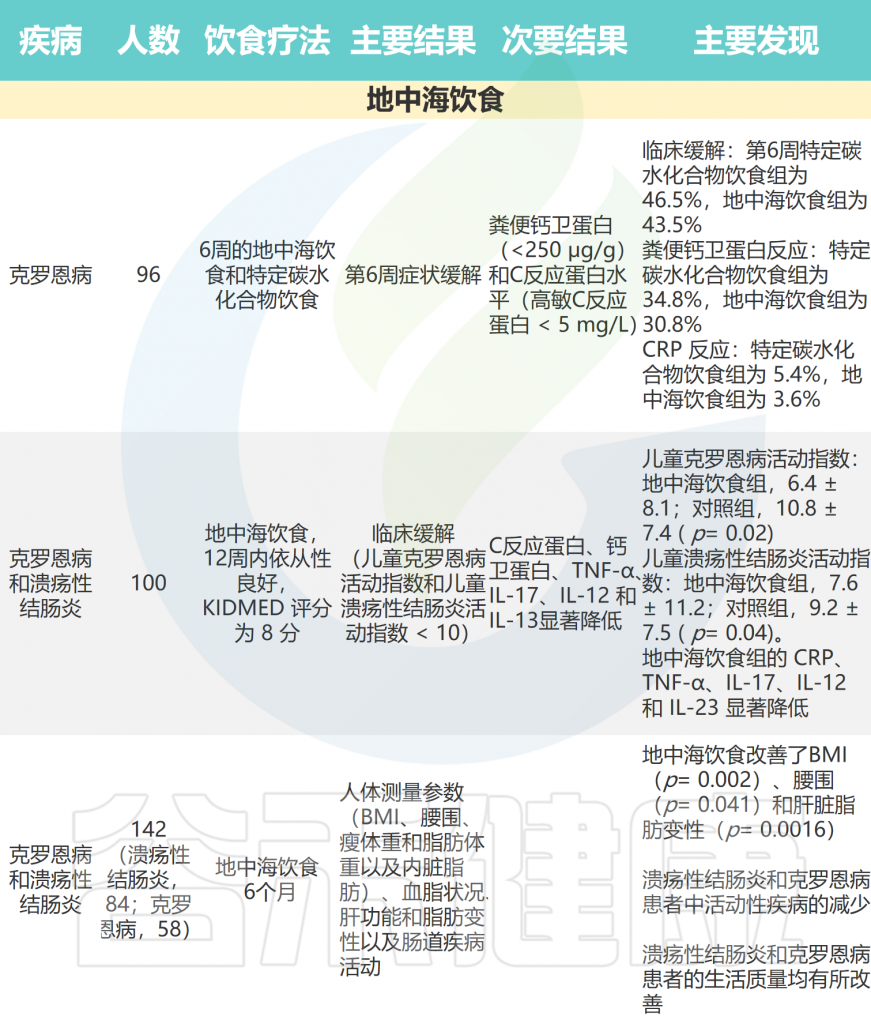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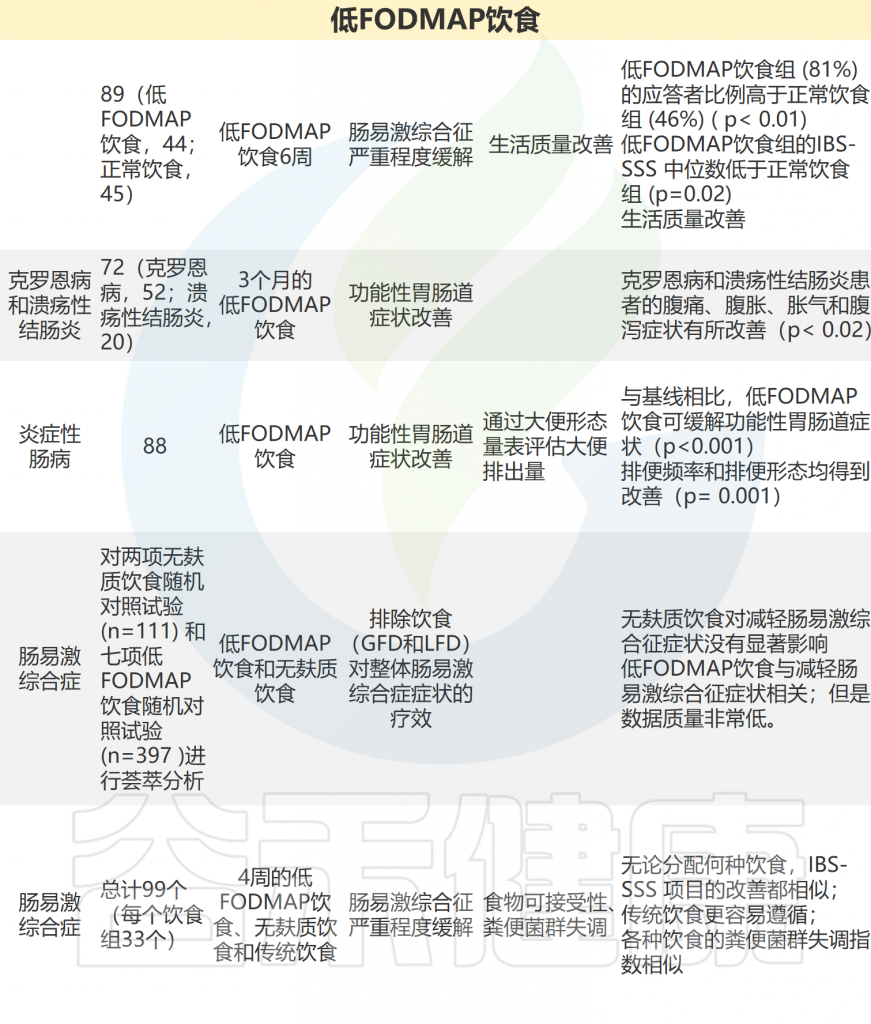
Jadhav A,et al.Annu Rev Nutr.2023
▸ 地中海饮食的炎症性肠病患者症状减轻
最近的一项前瞻性、随机研究纳入了100名患有轻度至中度疾病的青少年炎症性肠病患者,比较了地中海饮食与常规饮食的疗效,结果显示,小儿克罗恩病活动指数和小儿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指数的临床评分显著下降。以及较低水平的炎症标志物,例如血清C反应蛋白、钙卫蛋白、TNF-α、IL-17、IL-12和IL-13。
临床试验,也观察到地中海饮食对炎症性肠病的有益作用。这项研究涉及142名炎症性肠病患者(84名 溃疡性结肠炎和58名克罗恩病)。接受地中海饮食治疗6个月,显著改善了体重指数和腰围,并导致肝脏脂肪变性和营养不良相关参数显著减少。其中40%的轻度至中度克罗恩病患者在接受6-12周的地中海饮食治疗后病情得到缓解。
▸ 地中海饮食与健康有益的微生物特征相关
地中海饮食与有益的肠道微生物特征相关,特别是与膳食纤维代谢物的富集有关,例如普拉梭菌、解纤维素拟杆菌和普雷沃氏菌,以及参与植物多糖降解和短链脂肪酸和次级胆汁酸生产的其他微生物。
地中海饮食富含ω-3不饱和脂肪酸,使得ω-3和ω-6脂肪酸达到平衡。在前瞻性溃疡性结肠炎队列中证明了EPA和其他不饱和脂肪酸的积极作用,其中肠道炎症细胞因子水平与PUFA、EPA和二十二碳五烯酸呈负相关。
▸ ω-3 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对抗肠道相关炎症
涉及ω-3脂肪酸代谢的三个关键基因(CYP4F3、FADS1和FADS2)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克罗恩病风险增加相关,这显示了炎症性肠病饮食相关调节的额外遗传因素。
ω-3 不饱和脂肪酸可能通过下游脂质介质(例如消解素、保护素和噬消素(maresins))发挥抗炎作用,这些介质可以对抗IBD相关炎症。从机制上讲,ω-3 不饱和脂肪酸已被发现:
(a)降低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对各种化学引诱剂的趋化性;
(b)通过阻断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释放核因子κB来抑制TLR4表达和NOD2信号传导;
(c)抑制NLRP3炎性体激活并随后阻碍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
(d)增加产生丁酸盐的细菌属如双歧杆菌属、罗氏菌属和乳杆菌属以及毛螺菌科成员的丰度。
▸ 地中海饮食通过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也有助于减轻肠道炎症
由于可发酵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地中海饮食可导致肠道微生物群产生更多的短链脂肪酸。此外还发现,地中海饮食可改善坚持饮食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腹胀和腹痛。
膳食纤维、益生元和合生元等营养物质具有促进细菌群落生长的作用,对健康有益,并被证明可以改善宿主肠道炎症。
益生元和合生元在IBS和IBD中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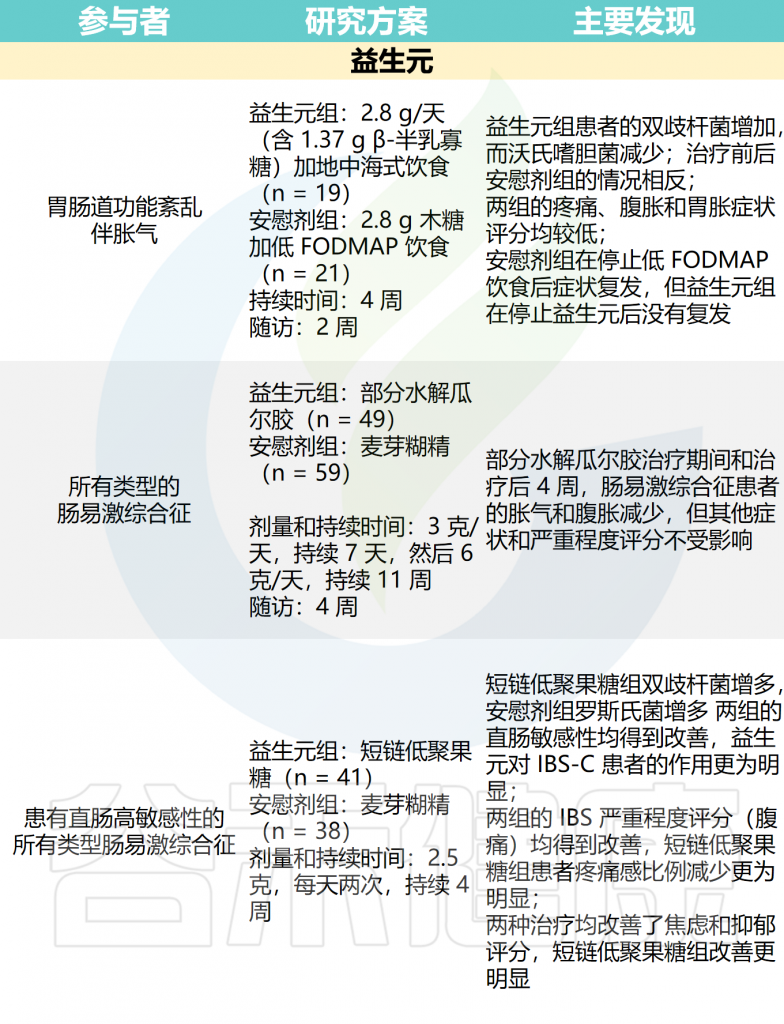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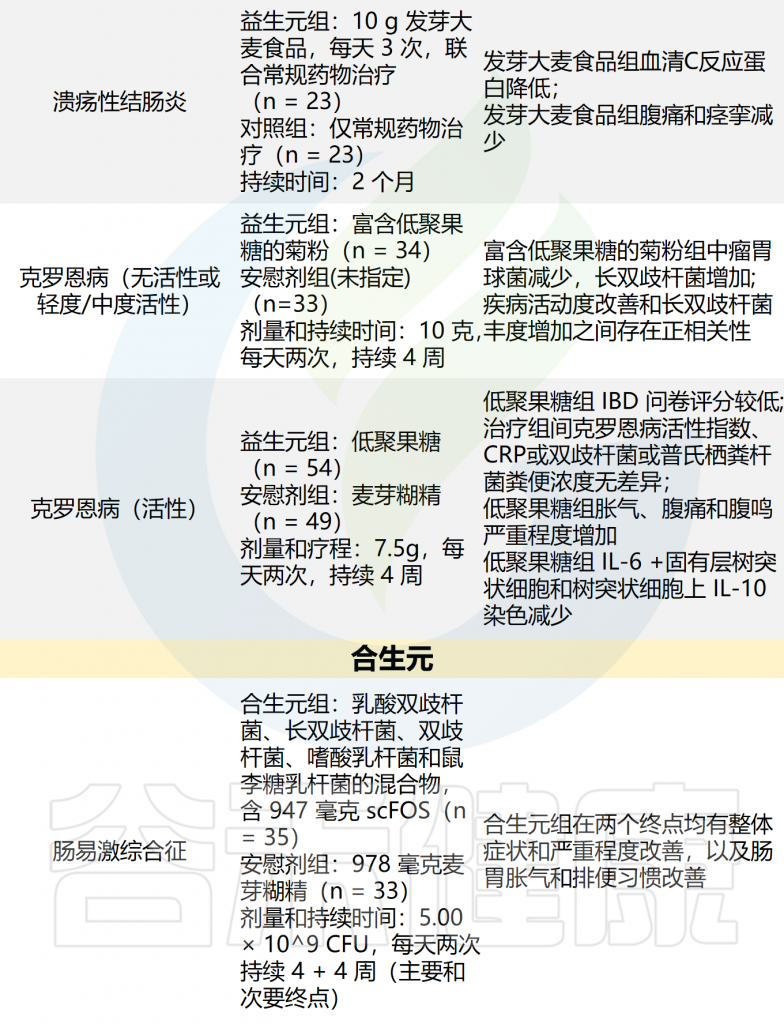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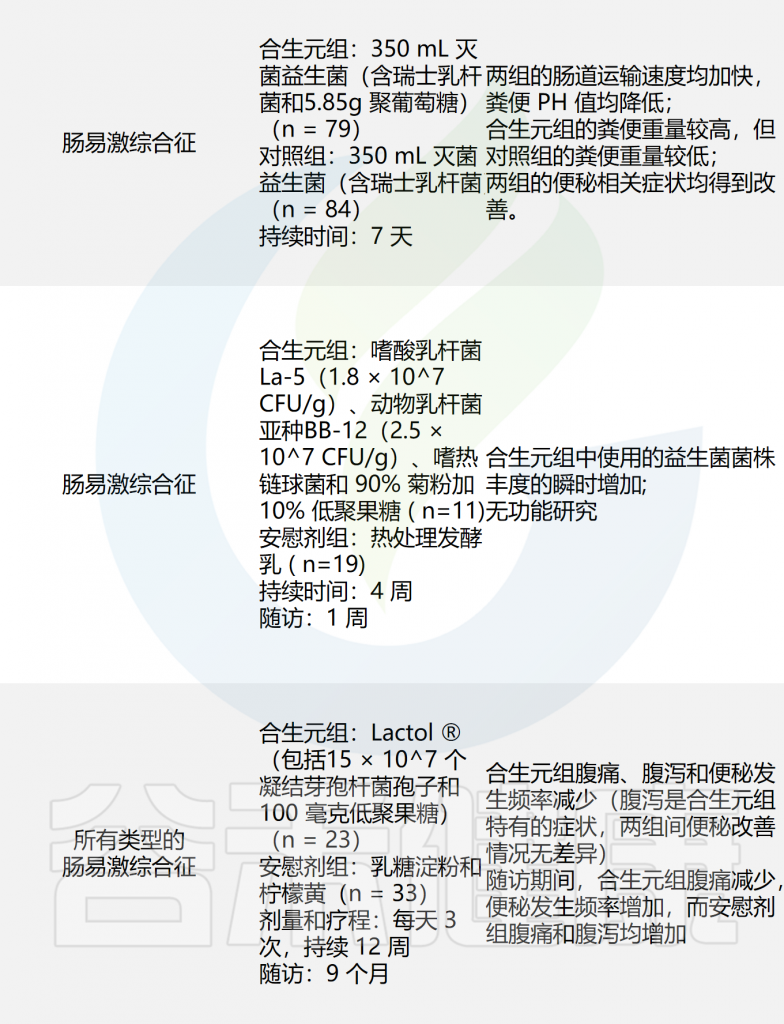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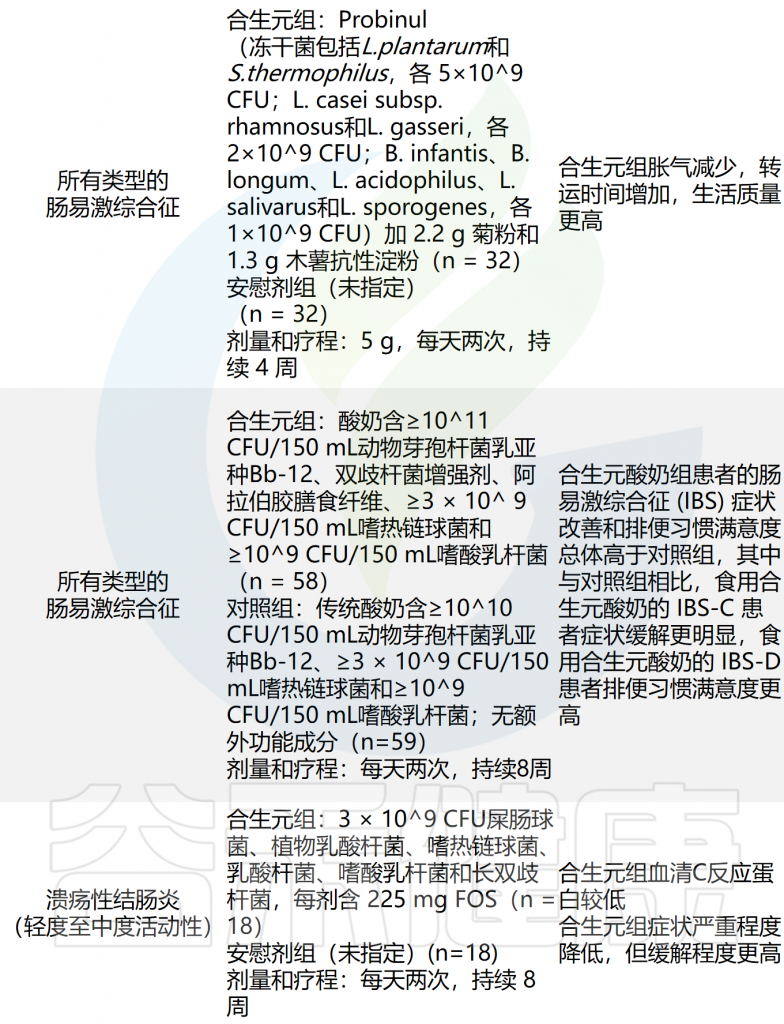
Jadhav A,et al.Annu Rev Nutr.2023
▸ 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改善肠道炎症
对14项随机对照研究(包括906名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进行的荟萃分析发现,可溶性膳食纤维可显著改善症状,但麸皮则不然。
注:但这些研究大多数都使用纤维补充剂;他们中很少有人改变饮食以增加纤维摄入量。尽管有几项研究调查了益生元和合生元,但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提出建议。
炎症性肠病的临床前模型发现,高纤维(主要是车前草)、低蛋白饮食可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并减少炎症。因此,可溶性纤维似乎对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和炎症性肠病患者都有益。
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还发现,膳食纤维摄入量与克罗恩病风险之间存在线性剂量依赖性关系,每天每增加10克纤维摄入量,克罗恩病风险就会降低 13%。
▸ 补充益生元可以降低疾病活动性
一项针对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随机、平行、双盲研究比较了地中海饮食和益生元补充剂(β-低聚半乳糖)与低FODMAP饮食和安慰剂木糖补充剂的效果,发现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症状有所改善,但补充益生元后肠道微生物群分布更有利。这一发现突显了饮食调整和补充作为胃肠道疾病管理中限制性饮食习惯的替代方案的潜力。
基于食物和补充剂的纤维和益生元干预研究报告指出,富含纤维的半素食、车前子种子、燕麦麸和发芽大麦食品在缓解和显著改善胃肠道症状(如腹痛和反流)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
在接受低聚果糖(每天15克,持续3-4周)、富含低聚果糖的菊粉(每天两次,每次10克,持续4周)、全麦麸(每天0.5杯,持续4周)、菊粉型果聚糖(每天7.5克,持续9周)和发芽大麦食品补充的活动性疾病队列中也报告了类似的结果,特别是显著降低了疾病活性并提高了生活质量。
▸ 纤维和益生元的益处会因个体健康状况和肠道菌群组成而不同
一项评估纤维摄入量对肠道微生物组组成影响分析表明,与安慰剂/低纤维饮食相比,高膳食纤维摄入与双歧杆菌属和乳杆菌属的丰度显著增加以及粪便丁酸盐含量增加相关。
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针对成年炎症性肠病患者进行,对儿童的益处尚不清楚。膳食纤维被广泛用于包括一系列复合碳水化合物(包括益生元)。但如上所述,膳食纤维的效果可能会因碳水化合物结构、健康状况和肠道微生物群组成而异。
一些研究表明合生元对成年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有益。与安慰剂组相比,补充长双歧杆菌和富含低聚果糖的菊粉4周可改善症状,并降低炎性细胞因子(TNF-α和IL-1β)的表达。
在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报告了类似的结果,该试验涉及补充8周由屎肠球菌、植物乳杆菌、嗜酸乳杆菌、嗜热链球菌、乳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和低聚果糖组成的合生元混合物。
纯肠内营养(EEN)已被接受为儿科克罗恩病患者的一线饮食干预措施。特指经消化道途径(包括口服和管饲)提供营养物质的一种营养支持治疗方式,包含所有必需的常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
▸ 纯肠内营养有助于减轻克罗恩病患者症状
许多研究表明,纯肠内营养(EEN)在诱导轻度至中度克罗恩病儿科患者缓解方面的效果与皮质类固醇相当。例如,在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独立试验中,补充EEN8周分别使84%和80%的受试者达到临床缓解。
EEN对患有克罗恩病的围手术期成年患者也有效。两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术前接受EEN的患者(22%)与未接受EEN的患者相比,术后并发症显著减少。尽管有限,但其他研究已经描述了EEN在治疗穿透性克罗恩病、狭窄性克罗恩病和肠外克罗恩病方面的益处。
▸ 纯肠内营养增强肠道微生物群的抗炎作用
从机制上讲,EEN可能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发挥作用。尽管它反而降低了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和通常被认为有益的菌群的丰富度(粪杆菌属、瘤胃球菌属和双歧杆菌属以及丹毒丝科、毛螺菌科的其他成员),但它根据代谢物的变化增强了肠道菌群的功能。
由于EEN的组成简单,降低抗原压力和肠道休息也可能是其重要的作用机制。此外,EEN配方中的活性成分可以改善营养参数,并可能对肠上皮产生抗炎作用。
在成人中,EEN作为二线或三线治疗使用,而皮质类固醇则是主要的诱导治疗,因为这些药物比EEN更有效地诱导临床缓解。
▸ 排除饮食减少肠道微生物的有害变化有助于病情缓解
部分肠内营养(PEN),即补充患者一半的热量需求作为肠内营养和全食物饮食,有助于克罗恩病患者维持病情缓解。
一项儿科克罗恩病队列研究中,无限制的PEN与元素配方结合效果有限;因此,研究人员认为需要一种针对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的排除饮食,排除某些有害食物。
克罗恩病排除饮食(CDED)与PEN相结合,是一种全食物饮食制度,旨在减少与肠道微生物群有害变化(如变形杆菌的扩张)、屏障完整性受损和胃肠道炎症相关的饮食成分和食物的暴露。
CDED不包含加工食品,并含有有益的纤维,再加上液体配方奶粉,以满足患者的能量需求。一项前瞻性研究报告称,与EEN相比,CDED加PEN在CD队列中具有更好的耐受性和更有效的效果,并且75%的CDED加PEN患者获得了无类固醇的临床缓解。
饮食衍生的代谢物因宿主健康状况和肠道微生物群中不同代谢途径而异,这反过来影响了饮食的生物学效应。因此,同一种食物可能对不同人群的生理功能具有不同的作用,可以影响多种疾病的病理生理,这也解释了相同饮食干预对不同疾病有益。
我们仍处于研究饮食-宿主-肠道菌群相互作用产生的生物活性分子如何影响慢性胃肠道疾病的病理生理和治疗反应的早期阶段。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在评估饮食干预的反应时观察到的显著个体间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饮食中生物可利用营养素的差异(由于成分和加工方式(如烹饪)的差异)、影响宿主代谢途径或免疫状态的基因多态性,以及肠道菌群代谢能力的差异。此外,其他环境和宿主因素也可能影响反应。我们需要考虑所有这些因素,以便能够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饮食建议。
编辑
Jadhav A,et al.Annu Rev Nutr.2023
总而言之,饮食与个性化微生物群在胃肠道疾病中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潜力的研究领域。理解这种相互作用不仅有助于揭示疾病的发病机制,还为个性化医疗和精准营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优化饮食和微生物群的相互作用,可以实现对胃肠道疾病更加有效的预防和治疗。
在应用方面,谷禾专注于高通量检测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结合,通过精确、便捷、无创的检测方式,以肠道菌群为核心,结合蛋白质及代谢物检测的多组学检测,开发多模态表征和大模型框架。肠菌检测作为一种基于实证的工具,它不仅可以评估个人肠道菌群及营养状况,还可以从整个个性化营养生态的视角出发,多场景、全方位地为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帮助。
注:本账号内容仅作交流参考,不作为诊断及医疗依据。
主要参考文献
Jadhav A, Bajaj A, Xiao Y, Markandey M, Ahuja V, Kashyap PC. Role of Diet-Microbiome Interac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and Strategies to Modulate Them with Microbiome-Targeted Therapies. Annu Rev Nutr. 2023 Aug 21;43:355-383.
Armstrong HK, Bording-Jorgensen M, Santer DM, Zhang Z, Valcheva R, Rieger AM, Sung-Ho Kim J, Dijk SI, Mahmood R, Ogungbola O, Jovel J, Moreau F, Gorman H, Dickner R, Jerasi J, Mander IK, Lafleur D, Cheng C, Petrova A, Jeanson TL, Mason A, Sergi CM, Levine A, Chadee K, Armstrong D, Rauscher S, Bernstein CN, Carroll MW, Huynh HQ, Walter J, Madsen KL, Dieleman LA, Wine E. Unfermented β-fructan Fibers Fuel Inflammation in Selec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atients. Gastroenterology. 2023 Feb;164(2):228-240.
Dong C, Chan SSM, Jantchou P, Racine A, Oldenburg B, Weiderpass E, Heath AK, Tong TYN, Tjønneland A, Kyrø C, Bueno de Mesquita B, Kaaks R, Katzke VA, Bergman MM, Boeing H, Palli D, Masala G, Tumino R, Sacerdote C, Colorado-Yohar SM, Sánchez MJ, Grip O, Lindgren S, Luben R, Huybrechts I, Gunter MJ, Mahamat-Saleh Y, Boutron-Ruault MC, Carbonnel F. Meat Intake Is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Ulcerative Colitis in a Large European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ø. J Crohns Colitis. 2022 Aug 30;16(8):1187-1196.
Narula N, Wong ECL, Dehghan M, Mente A, Rangarajan S, Lanas F, Lopez-Jaramillo P, Rohatgi P, Lakshmi PVM, Varma RP, Orlandini A, Avezum A, Wielgosz A, Poirier P, Almadi MA, Altuntas Y, Ng KK, Chifamba J, Yeates K, Puoane T, Khatib R, Yusuf R, Boström KB, Zatonska K, Iqbal R, Weida L, Yibing Z, Sidong L, Dans A, Yusufali A, Mohammadifard N, Marshall JK, Moayyedi P, Reinisch W, Yusuf S. Association of ultra-processed food intake with risk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BMJ. 2021 Jul 14;374:n1554.
Khademi Z, Milajerdi A, Larijani B, Esmaillzadeh A. Dietary Intake of Total Carbohydrates, Sugar and Sugar-Sweetened Beverages, and Risk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Front Nutr. 2021 Oct 1;8:707795.
IBD in EPIC Study Investigators; Tjonneland A, Overvad K, Bergmann MM, Nagel G, Linseisen J, Hallmans G, Palmqvist R, Sjodin H, Hagglund G, Berglund G, Lindgren S, Grip O, Palli D, Day NE, Khaw KT, Bingham S, Riboli E, Kennedy H, Hart A. Linoleic acid, a dietary n-6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 and the aetiology of ulcerative colitis: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within a European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Gut. 2009 Dec;58(12):1606-11.
Dionne J, Ford AC, Yuan Y, Chey WD, Lacy BE, Saito YA, Quigley EMM, Moayyedi P.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of a Gluten-Free Diet and a Low FODMAPs Diet in Treating Symptoms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Am J Gastroenterol. 2018 Sep;113(9):1290-1300.

谷禾健康

爱格氏菌属(Eggerthella),厌氧、不产生孢子、不活动的革兰氏阳性杆菌,是人类肠道微生物组的常见成员,人群检出率比较高,属于放线菌门。
大多数时候,Eggerthella与多种疾病相关
Eggerthella存在于人类结肠和粪便中,并被认为是溃疡性结肠炎、肝和肛门脓肿以及全身性菌血症的原因。
研究表明Eggerthella还与多种人类慢性疾病有关,包括哮喘、抑郁、肾病、多发性硬化症和类风湿性关节炎,尽管Eggerthella在这些疾病中的因果作用尚未确定。
哮喘
出生队列研究和大型国际研究发现哮喘与生命早期抗生素使用之间存在关联,特别是关于头孢菌素类和大环内酯类药物。研究发现,在大环内酯类暴露后观察到的Eggerthella水平增加了10倍。大多数Eggerthella是病原体并可能促进炎症反应。来自动物模型的实验证据表明,生命早期使用抗生素会破坏微生物群,从而破坏免疫系统的发育,导致易感个体的气道反应过度。
神经系统疾病
多项研究表明在抑郁,情感障碍以及精神分裂患者中Eggerthella丰度富集。
有16项观察到重度抑郁症患者和健康对照者之间的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存在显著差异。与健康对照相比,重度抑郁症患者的Eggerthella、Atopobium、Bifidobacterium的相对丰度增加,粪杆菌的相对丰度降低。
在患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肠道中,Lachnospiraceae、Eggerthellaceae、Dorea、Blautia、Eggerthella的丰度减少,而Veillonellaceae增加。然而,在衰老过程中,这些变化并没有出现。表明衰老过程中和认知障碍特有的微生物群变化是独立于年龄的。
用于早期诊断肝细胞癌的微生物标志物
一项研究评估中国人群乙型肝炎病毒相关肝病(包括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和肝细胞癌)肠道微生物组的改变,Eggerthella的相对丰度随着HC向慢性乙型肝炎和肝硬化的进展而逐渐降低,但在肝细胞癌中显著增加。
肌肉减少症合并肝硬化
肌肉减少症肝硬化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缺乏与身体功能相关的细菌(甲烷杆菌、普雷沃氏菌和阿克曼菌),并且富含Eggerthella,这是一种虚弱的肠道微生物标志物。
肾病
在肾病中该菌的增加或减少有争议,在人类肾脏疾病的肠道微生物群数据库中发现 Eggerthella 属减少。然而,一项横断面研究,评估了中国原发性IgA肾病患者粪便菌群特征,与健康对照组相比,IgA肾病组中显著增加的属为Escherichia-Shigella、Hungatella、Eggerthella。
影响药物吸收和脂质水平
Eggerthella和相关的人类肠道Coriobacteriaceae 细菌还参与多种代谢转化,包括广泛使用的心脏药物地高辛的灭活、膳食植物化学物质的各种反应、儿茶酚的脱羟基以及胆汁的代谢酸。
一些Eggerthella菌株负责将地高辛转化为一种无活性的微生物代谢产物,限制了10%左右的患者吸收到系统血流中的活性药物的数量。 最近的研究证明,地高辛与抗生素或富含精氨酸的饮食共同给药,都会导致全身地高辛水平升高和药物水平的临床相关波动。
注:地高辛(Digoxin)是一种强心苷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心力衰竭和某些心律失常。
此外,Eggerthella与甘油三酯增加和高密度胆固醇减少存在相关性,它可通过将胆固醇转化为不可吸收的粪甾醇和粪甾酮,或将胆固醇转移至胆汁酸代谢过程中,直接限制体循环中的胆固醇水平,从而影响脑血管的发展。Eggerthella 也被证明参与生物活性次生植物化合物的代谢,例如葡萄中的白藜芦醇或大豆中的大豆苷元。
Eggerthella作为有潜在保护菌
谵妄被定义为一种突然、精神状态下降的临床综合征,其特征是意识模糊和认知状态波动,一项
大规模孟德尔随机化研究显示,Eggerthella属与谵妄的风险降低有关(P = 0.047)。
代表菌种:迟缓埃格特菌
该属的典型菌种是Eggerthella lenta(迟缓埃格特菌)。Eggerthella lenta 可引起血流感染,被认为是一种机会性人类病原体。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它也可能是人类的重要病原体,甚至在某些条件下引起危及生命的感染。Eggerthella lenta已从血液、脓肿、伤口、皮肤溃疡、产科和泌尿生殖道感染以及腹腔内感染中分离出来。
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包括免疫功能受损状态(类固醇使用、近期化疗、终末期肾病和糖尿病)、恶性肿瘤和胃肠道疾病,如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
Eggerthella lenta菌血症最常见的潜在健康状况是实体癌或血液器官癌、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而所有这些患者的主要感染源是胃肠道、皮肤和软组织和脓肿。
在所有首发症状中,阑尾炎所占比例最高,远高于第二大的结肠炎。阑尾炎常伴有穿孔甚至腹膜炎。
Eggerthella lenta通常存在于消化道中,但可能会导致因胃肠道疾病导致粘膜内层破坏的患者或免疫系统受损的患者发生全身感染。然而,其他研究表明,患有癌症、褥疮、阑尾炎和糖尿病的患者更容易患迟缓埃格特菌菌血症。
Eggerthella lenta 非运动型革兰氏阳性杆状体和革兰氏染色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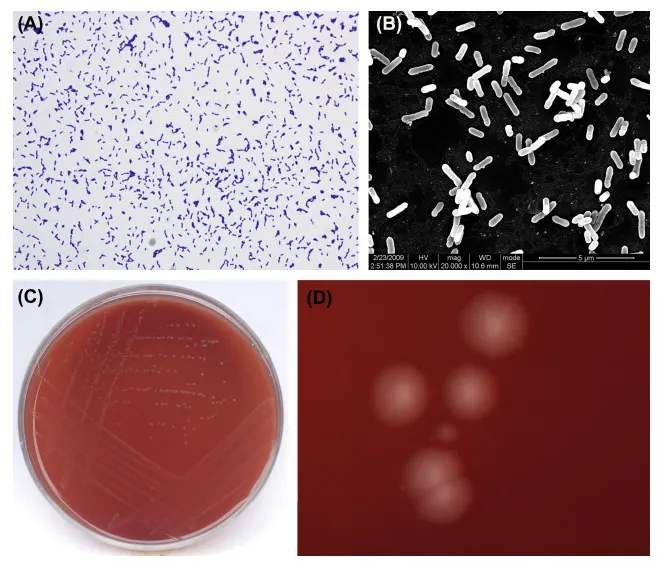
这些生物体能够扩展人类超级生物体的代谢潜力,在多糖的消化、维生素和氨基酸的合成以及内源性化合物的修饰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它们在外源物质(包括药物、膳食化合物和环境毒素)的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这些化合物的生物利用度、活性和毒性。
例如,某些Eggerthella lenta菌株还可以使药物 L-多巴(一种用于治疗帕金森病的多巴胺的氨基酸前体)失活,因为该细菌能够将 L-多巴代谢物多巴胺脱羟基为间酪胺。
此外,Eggerthella lenta还会把白藜芦醇转化为二氢白藜芦醇。
有研究从人类肠道菌群中分离出一种能够有效代谢白藜芦醇的细菌Eggerthella lenta J01,通过诱导富集转录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分析,研究人员进一步鉴定了来自 E. lenta J01 的白藜芦醇还原酶 (RER),该酶特异性催化白藜芦醇的 C9-C10 双键氢化并启动白藜芦醇的体内代谢。
注:RER及其同系物代表了一类新型的烯还原酶。健康个体肠道菌群中RER的丰度显著高于炎症性肠病患者,表明其至关重要的生理功能。
关于白藜芦醇和二氢白藜芦醇:
• 白藜芦醇
白藜芦醇是一种强抗氧化剂,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害。
潜在健康益处:
1.心血管健康:研究表明白藜芦醇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增强动脉弹性,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抗炎作用:白藜芦醇具有抗炎特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对抗慢性炎症相关的疾病。
3.抗癌潜力:白藜芦醇的抗癌作用在实验室研究中得到了很大关注,它能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
4.延缓衰老:白藜芦醇可能通过激活某些基因(如SIRT1)来延缓衰老过程。
• 二氢白藜芦醇
二氢白藜芦醇是白藜芦醇的代谢产物,通常通过肠道微生物的代谢活动生成。
潜在健康益处:
1.抗氧化作用:与白藜芦醇一样,二氢白藜芦醇也具有抗氧化特性,可以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
2.抗炎作用:也具有抗炎特性,可能对抗慢性炎症。
3.肠道健康:作为肠道微生物代谢的产物,二氢白藜芦醇可能对肠道健康有益。
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白藜芦醇上,而关于二氢白藜芦醇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更广泛且深入的研究可能仍需要对二氢白藜芦醇的确切健康益处进行验证。从现有研究来看,白藜芦醇因其广泛的健康效益被更多地关注和研究。
超过五十种不同的药物化合物已被确定对这种代谢改变敏感。参与这些生物转化过程的一种人类肠道共生细菌是迟缓埃格特菌(Eggerthella lenta) (以前称为迟缓真杆菌)。
该菌的名字来源于 Arnold Eggerth,他于 1935 年首次描述了这种细菌。从历史上看,由于该生物体生长缓慢且物种形成需要营养密集型,因此很难培养和鉴定。16S rRNA 基因测序的出现使得鉴定变得更加快速和准确。鉴于其高死亡率,由这种微生物引起的菌血症始终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并需要立即寻找其来源。
干预
抗生素
尽管缺乏临床指南,但是治疗成功案例报告对抗迟缓肠球菌感染最有效的抗菌药物是甲硝唑、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和碳青霉烯类;它对头孢曲松具有耐药性。
但之前的病例报告也报道使用广谱 β-内酰胺(例如碳青霉烯或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单一疗法或甲硝唑加 β-内酰胺联合疗法取得成功。
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TZP) 是一种覆盖厌氧菌的广谱联合抗菌剂,通常用于腹腔内感染的经验性治疗。
此外,头孢唑肟,也显示出良好的疗效。
中药
对抗生素诱导腹泻小鼠进行七味白术散灌胃3天后发现,可特异性地产生门乳糖酶的肠道菌群如放线菌门、厚壁菌门和变形菌门,具有明显的检测水平。与其他组相比,来自治疗组小鼠Acidovorax sp.KKs102、Stenotrophomonas sp. LMG11000、Pseudomonas oleovorans、 Eggerthella 、Burkholderia的乳糖酶基因表达更丰富。七味白术散治疗对腹泻的疗效可能与其促进新的或一些关键的乳糖酶产生菌株的生长有关。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显示,益肾化湿颗粒可降低慢性肾病患者蛋白尿,减轻肠道菌群失调,益肾化湿颗粒干预4个月后,Faecalibacterium、Lachnospiraceae、Lachnoclostridium、Sutterella等对机体有益的细菌相对丰度明显增加,而Eggerthella和Clostridium innocuum组等致病菌相对丰度降低。
益生菌
在12周植物乳杆菌Q180干预后,Eggerthella的丰度趋向于减少。Eggerthella所属的放线菌门在内源性脂质代谢中起作用,并且与血浆胆固醇呈正相关。此外,有研究通过年龄、性别和宿主基因分析了肠道微生物群与脂质水平的关系,发现Eggerthella属的丰度与其有显著正相关。在上述研究中,Eggerthella属被证明会增加血液甘油三酯水平并降低HDL胆固醇。因此,目前的结果表明,摄入植物乳杆菌Q180可能通过减少Eggerthella的水平来改善血脂。
长双歧杆菌(B.longum)可改善心血管疾病。研究人员通过体外厌氧发酵研究了从健康人粪便中分离的长双歧杆菌L556在冠心病患者中的作用。结果显示,在冠心病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中,长双歧杆菌L556增加了乳酸杆菌、粪杆菌、普雷沃氏菌和Alistipes,同时减少厚壁菌/拟杆菌门、Eggertella、Veillonella、Holdemanella、Erysiperotrichacee_UCG-003。长双歧杆菌 L556还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和SCFAs等代谢产物来增强抗炎作用。此外,它还调节冠心病组发酵代谢产物中的脂质和氨基酸代谢。
饮食
调查研究发现健康饮食分数越高,该菌的丰度相对更低。■
•◆
Flavonifractor(解黄酮菌属)属于厚壁菌门,梭菌目,通常为革兰氏阳性,大多数物种形成椭圆形/球形内孢子,通常为过氧化氢酶阴性,大多数物种是专性厌氧的,尽管对氧气的耐受性差异很大。
肠道微生物群中 Flavonifractor 丰度升高与较高的情感障碍相关,吸烟和女性是造成这种关联的原因之一,可能导致氧化应激增强,以及儿茶酚途径和低度炎症有关。此外,肠癌或息肉病人该菌富集。
该菌的典型菌种是 Flavonifractor plautii ,是人类肠道微生物中一种常见的专性厌氧菌,通常黏附在肠壁上,在粪便中可提取得到。 Flavonifractor plautii可以通过裂解类黄酮分子的 C 环来降解类黄酮。黄酮类化合物是人类饮食的重要成分,主要由具有广谱药理活性的多酚类次级代谢产物组成。
几种常见的黄酮类食物,如茶、咖啡、苹果、番石榴、榄仁树皮、葫芦巴籽、芥菜籽、肉桂、红辣椒粉、丁香、姜黄和豆类,都含有大量的类黄酮。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发挥类黄酮潜在有益作用和生物利用度,需要控制Flavonifractor plautii其丰度。
Flavonifractor 作为有益菌
肥胖
Flavonifractor 是肠道健康的重要菌群,其含量与肥胖呈负相关。
口服Flavonifractor plautii可减轻肥胖脂肪组织的炎症反应,F. plautii可能参与抑制炎症环境中的 TNF-α 表达。
前列腺癌
PRACTICAL 和 FinnGen 联盟汇总的数据结果表明,Eubacterium fissicatena和Odoribacter与前列腺癌风险增加有关。相反,Adlercreutzia、Roseburia、Holdemania、Flavonifractor、Allisonella属则是预防前列腺癌的潜在保护因素。
过敏(哮喘)
针对690名参与者生命第一年期间肠道微生物 (16S rRNA 测序)与随后的哮喘风险相关联研究显示,Veillonella与 5 年内较高的哮喘风险相关;而罗斯氏菌、Alistipes和Flavonifractor的相对丰度较高,与哮喘风险较低有关。
糖尿病
两项或以上研究中一致报告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下列细菌在糖尿病前期和新发糖尿病中有所增加,包括乳杆菌、链球菌、埃希氏菌、Veillonella 、Collinsella等,而普拉梭菌、Roseburia、Dialister、Flavonifractor、 Alistipes、Haemophilus 、Akk菌则减少。这些菌作为健康生物标志物的作用已被广泛认可,其有益效果主要归因于其生产短链脂肪酸,尤其是丁酸盐的能力,这对于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性、能量稳态、减轻炎症和调节血糖反应起着重要作用。
其他
个别研究报道,口服 Flavonifractor plautii(一种在绿茶摄入量中增加的肠道细菌)可通过抑制 IL-17 信号传导促进小鼠急性结肠炎的恢复。
口服 Flavonifractor plautii 可有效抑制小鼠的 Th2 免疫反应,可能有助于减轻抗原诱导的 Th2 免疫反应。
与Flavonifractor 过高相关的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抑郁、认知障碍)
肠道微生物群中Flavonifractor 丰度升高与较高的情感障碍相关,Flavonifractor属的种类增加和抑郁症相关。
注:一项研究显示,在重度抑郁症和所有个体中,Flavonifractor 与疲劳呈正相关。
Flavonifractor与新诊断的双相情感障碍有关。
NEAD 研究 (左) 和BIO研究 (右) 中情感障碍 (AD) 患者、其未受影响的亲属 (UR)和健康个体 (HC) 中Flavonifractor的流行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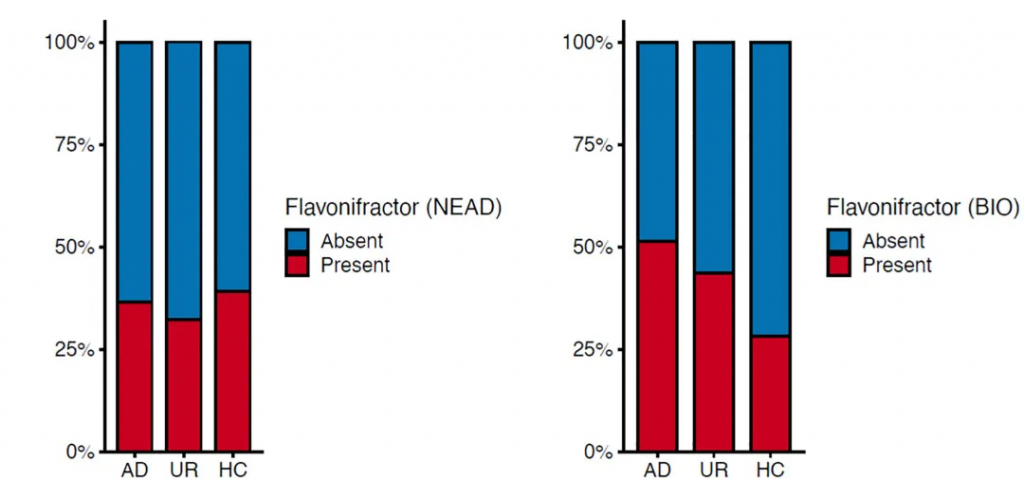
doi.org/10.1016/j.pnpbp.2021.110300
一项双样本孟德尔随机化研究显示,鞘磷脂水平与Flavonifractor呈负相关 (p = 0.026, beta 95%CI = -0.218 [-0.411, -0.026]) 。鞘磷脂代谢异常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制有关。在患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个体中, Flavonifractor 属也被发现有所增加。
结直肠癌
肠癌或息肉病人该菌富集。
来自江南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的对 85 名接受结肠镜检查的结直肠癌患者的样本进行了 16S rRNA 测序、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结果发现Catabacter、Mogibacterium的相对丰度从粘膜内癌到晚期持续增加,而Clostridium、Anaerostipes、Vibrio、Flavonifractor、Holdemanella和Hungatella仅在中期病变中发生显著改变。
血清代谢组学发现,在中期病变阶段,胆素、甘油酯和核苷水平最高,而胆汁酸和氨基酸水平最低。
食管癌
食管癌是目前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位居第九位。食管癌可分为两种主要病理亚型: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和食管腺癌(EAC)。
一项双样本孟德尔随机化研究显示,在食管腺癌 (EAC) 的情况下,Flavonifractor表现出正相关性。
慢性心力衰竭合并心房颤动
小型研究显示,慢性心力衰竭合并心房颤动患者肠道菌群显著富集在Flavonifractor属(p=0.003,FDR p adj =0.12)和 L-赖氨酸生物合成途径(p=0.04,FDR p adj =0.26),而Alistipes属(p=0.02,FDR p adj =0.29)和淀粉降解(p=0.02,FDR p adj =0.26)和糖酵解(p=0.03,FDR p adj =0.26)途径,相对缺乏。
慢性肾病
根特大学医院招募的 110 名非慢性肾病和慢性肾病患者,Flavonifractor属在慢性肾病个体中的水平高于非慢性肾病个体。
泌尿道结石
泌尿道结石可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如尿路阻塞、感染、不适以及对肾脏的潜在不可逆损害。
一项双向双样本孟德尔随机化研究显示,Flavonifractor 属丰度增加(IVW OR = 0.69,95%CI 0.53-0.91,P = 8.57 × 10-3)与尿路结石形成风险降低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肌肉减少症
肌肉减少症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全身性骨骼肌疾病,其特征是肌肉质量损失和肌肉功能下降,它会增加跌倒、骨折、残疾等有害后果的风险。与 正常骨骼肌质量组相比,低骨骼肌质量组中的Flavonifractor属大幅增加。
酒渣鼻(红斑痤疮)
一项横断面对照试点研究显示,与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对照者相比,红斑痤疮中的Flavonifractor plautii显著增加(coef. 0.011,p = 0.037)。
注:被认定为诱发红斑痤疮的食物比有益食物多。主观上认为酒精是主要的饮食诱因,其次是香料、精制糖、油炸/油腻食物、热食、咖啡、乳制品、肉类和糖替代品。而蔬菜、水果、鱼、益生菌、茶、全麦和豆类被认为是最有利的。
典型菌种 Flavonifractor plautii
Flavonifractor plautii,是人类肠道微生物中一种常见的专性厌氧菌,通常黏附在肠壁上,在粪便中可提取得到。这个细菌还有一个超能力,它可以「吃掉」红细胞的 A 抗原。
Flavonifractor plautii可以通过裂解类黄酮分子的 C 环来降解类黄酮。黄酮类化合物是人类饮食的重要成分,主要由具有广谱药理活性的多酚类次级代谢产物组成。从流行病学、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中积累的证据支持这些多酚在预防癌症、心血管疾病、2 型糖尿病和认知功能障碍方面的作用。
Flavonifractor plautii 改善动脉硬化程度
人类粪便宏基因组测序显示,在正常对照组中,F. plautii丰度显著较高,并在微生物群落中处于中心地位,而在动脉僵硬度升高的受试者中,F. plautii缺失。此外,血压只部分介导了F. plautii对降低动脉僵硬度的影响。
正常对照组的微生物组表现出增强的糖酵解和多糖降解能力,而动脉僵硬度增加的受试者的微生物组则以脂肪酸和芳香族氨基酸的生物合成增加为特征。
整合代谢组学分析进一步表明,顺式乌头酸的增加是F. plautii对动脉硬化保护作用的主要效应物,通过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2的激活,维持弹性纤维网络,缓解动脉功能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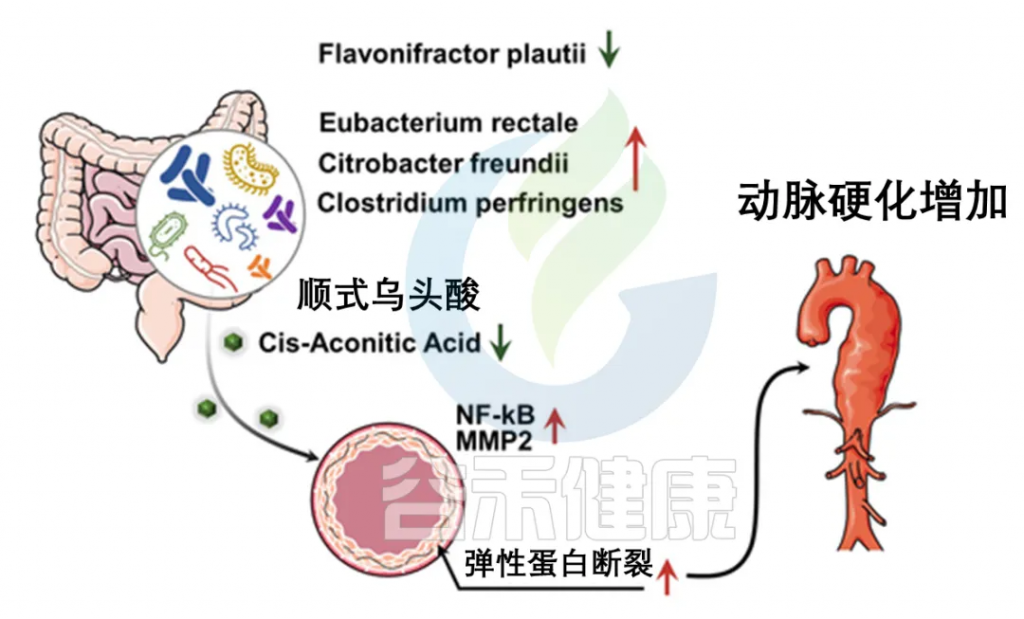
doi.org/10.1161/CIRCRESAHA.122.321975
如何调节
★ 增加
一项随机、单盲、平行组、安慰剂对照研究显示,红茶摄入增加了肠道中Flavonifractor plautii的数量,尤其是在基线水平较低的个体中。
一项交叉研究显示,乳制品摄入会改变高胰岛素血症个体的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其中Faecalibacteria(p = 0.05)和Flavonifractor(p = 0.06)丰度增加,Flavonifractor的丰度变化与HOMA-IR的变化呈负相关。
注:HOMA-IR为胰岛素抵抗的稳态模型评估
在一项小鼠实验中,帕金森患者在7天的利福昔明治疗在治疗6个月后导致Flavonifractor的相对丰度增加,血浆促炎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与基线血浆白细胞介素-1α水平呈负相关。
膳食纤维改善了结肠炎引起的肠道微生物种类减少问题。其中可溶性膳食纤维的效果更明显:大豆壳膳食纤维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抑制TLR-4/NF-κB信号通路来缓解BALB/C小鼠的炎症,在属水平上Barnesiella、乳杆菌、瘤胃球菌、Flavonifractor的相对丰度都比正常对照组更高。
在结肠癌模型中,小蘖碱治疗改善了隐窝的发育不良和粘膜中的腺瘤增生,并减少了结肠癌的发生。此外,小蘖碱治疗后放线菌门、疣微菌门、双歧杆菌、Barnesiella和Odoribacter的相对丰度减少,而Alloprevotella、Flavonifractor、 Oscillibacter和副拟杆菌的相对丰度增加。
★ 减少
一项研究显示,灰树花杂多糖在喂食高脂饮食的大鼠中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能力。与高脂饮食组相比,补充灰树花杂多糖组的大鼠肠道菌群中Flavonifractor显著降低。
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的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相比,乳香树提取物治疗后,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Flavonifractor相对丰度较低。
贝特类药物治疗后,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肠道菌群中的Flavonifractor下降。
注:关于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黄酮类化合物特征的数据是矛盾的,与健康人相比,其水平要么增加,要么减少。
一项针对复发性尿路感染女性的安慰剂对照研究,长期每日食用蔓越莓,研究组之间检测到的唯一显著差异是Flavonifractor属 OTU41,与安慰剂消费者相比,蔓越莓消费者的OTU41相对丰度显著降低。
注:有研究表明,24 周内每天饮用蔓越莓饮料的复发性复发性尿路感染患者中,复发性尿路感染症状减少了 39%。
一项随机对照实验显示,食用油炸肉的受试者的IGI值(胰岛素生成指数)低于对照组,但胰岛素和脂多糖、TNF-α、IL-10和IL-1β水平的MIRI(肌肉胰岛素抵抗指数 )和AUC值较高(P < 0.05)。油炸肉摄入降低了Lachnospiraceae、Flavonifractor,增加了Dialister、Dorea 、Veillonella丰度 (FDR <0.05)。油炸肉类的摄入会影响肠道菌群和微生物宿主共代谢物,从而损害血糖稳态并增加肠道内毒素和全身炎症水平。
注:该研究中共 117 名超重成年人被随机分为两组。59 名参与者每周提供四次煎炸肉类,58 名参与者被限制食用煎炸肉类。
一项随机临床试验比较低FODMAP黑麦面包与普通黑麦面包对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道菌群的影响,结果显示食用低FODMAP黑麦面包减少了拟杆菌、Flavonifractor、Holdemania、Parasutterella和克雷伯菌的丰度,并显示出双歧杆菌增加的趋势。Flavonifractor利用γ-氨基丁酸(GABA)作为生长基质,因此该菌过多的话可能减少肠道中的GABA含量。由于GABA在肠道中具有多种调节作用,包括减少通便时间和缓解疼痛,增加谷物纤维摄入会减少IBS患者体内“食GABA”菌Flavonifractor的数量。通过饮食调整减少Flavonifractor丰度并增加双歧杆菌丰度可能有助于缓解IBS患者的腹痛或加速通便时间。
注:在患有功能性胃肠道疾病的自闭症儿童的直肠黏膜中发现了较高水平的Flavonifractor,尤其是那些报告有腹痛的儿童。Flavonifractor的数量与组织活检样本中的5-羟色胺水平呈线性相关。在抑郁成年人的粪便中也检测到了较高水平的Flavonifractor。这些都加强了进一步研究的理由,以阐明Flavonifractor、肠道疼痛和情绪障碍之间的联系。
主要参考文献:
Wang J, Guo R, Ma W, Dong X, Yan S, Xie W. Eggerthella lenta Bacteremia in a Middle-Aged Healthy Man with Acute Hepatic Abscess: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1970-2020. Infect Drug Resist. 2021 Aug 19;14:3307-3318.
Wong D, Aoki F, Rubinstein E. Bacteremia caused by Eggerthella lenta in an elderly man with a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cy: A case report. Can J Infect Dis Med Microbiol. 2014 Sep;25(5):e85-6.
James A S, Chaudhari D S, Jain S, et al. Specific Microbiome Signature Dynamics Could Predict Aging Continuum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Older Adults[J]. Physiology, 2024, 39(S1): 1991.
Hu, X., Du, J., Xie, Y. et al. Fecal microbiota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primary IgA nephropathy: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Nephrol 21, 97 (2020)
Vázquez-Martínez ER, García-Gómez E, Camacho-Arroyo I, González-Pedrajo B. Sexual dimorphism in bacterial infections. Biol Sex Differ. 2018;9(1):27.
Cho G.-S., Ritzmann F., Eckstein M., Huch M., Briviba K., Behsnilian D., Neve H., Franz C.M.A.P. Quantification of Slackia and Eggerthella spp. in human feces and adhesion of representatives strains to Caco-2 cells. Front. Microbiol. 2016;7:658.
Haiser H.J., Seim K.L., Balskus E.P., Turnbaugh P.J. Mechanistic insight into digoxin inactivation by Eggerthella lenta augments our understanding of its pharmacokinetics. Gut Microbes. 2014;5:233–238.
Yu H, Wan X, Yang M, Xie J, Xu K, Wang J, Wang G, Xu P. A large-scale causal analysis of gut microbiota and delirium: A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 J Affect Disord. 2023 May 15;329:64-71.
Gupta RS, Chen WJ, Adeolu M, Chai Y. Molecular signatures for the class Coriobacteriia and its different clades; proposal for division of the class Coriobacteriia into the emended order Coriobacteriales, containing the emended family Coriobacteriaceae and Atopobiaceae fam. nov., and Eggerthellales ord. nov., containing the family Eggerthellaceae fam. nov. Int J Syst Evol Microbiol. 2013 Sep;63(Pt 9):3379-3397.
Korpela, K., Salonen, A., Virta, L. et al. Intestinal microbiome is related to lifetime antibiotic use in Finnish pre-school children. Nat Commun 7, 10410 (2016).
Koppel N., Bisanz J.E., Pandelia M.-E., Turnbaugh P.J., Balskus E.P. Discovery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prevalent human gut bacterial enzyme sufficient for the inactivation of a family of plant toxins. eLife. 2018;7:e33953.
Dong X, Zhang J, Li W, et al. Yi-Shen-Hua-Shi regulates intestinal microbiota dysbiosis and protects against proteinuria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J]. Pharmaceutical Biology, 2024, 62(1): 356-366.
Ponziani FR, Picca A, et al., GuLiver study group.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gut-liver-muscle axis in cirrhotic patients with sarcopenia. Liver Int. 2021 Jun;41(6):1320-1334.
Park, Y.E.; Kim, M.S.; Shim, K.W.; Kim, Y.-I.; Chu, J.; Kim, B.-K.; Choi, I.S.; Kim, J.Y. Effects of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Q180 on Postprandial Lipid Levels and Intestinal Environment: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Parallel Trial. Nutrients 2020, 12, 255
Yang, L., Wu, Y., Zhao, X. et al. An In Vitro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Bifidobacterium longum L556 on Microbiota Composition and Metabolic Propertie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Probiotics & Antimicro. Prot. (2024).
Claus S.P., Ellero S.L., Berger B., Krause L., Bruttin A., Molina J., Paris A., Want E.J., de Waziers I., Cloarec O., et al. Colonization-induced host-gut microbial metabolic interaction. mBio. 2011;2:e00271-10.
Bode L.M., Bunzel D., Huch M., Cho G.-S., Ruhland D., Bunzel M., Bub A., Franz C.M.A.P., Kulling S.E. In vivo and in vitro metabolism of trans-resveratrol by human gut microbiota. Am. J. Clin. Nutr. 2013;97:295–309.
Kawada Y., Goshima T., Sawamura R., Yokoyama S., Yanase E., Niwa T., Ebihara A., Inagaki M., Yamaguchi K., Kuwata K., et al. Daidzein reductase of Eggerthella sp. YY7918, its octameric subunit structure containing FMN/FAD/4Fe-4S, and its enantioselective production of R-dihydroisoflavones. J. Biosci. Bioeng. 2018;126:301–309.
Gardiner B.J., Tai A.Y., Kotsanas D., Francis M.J., Roberts S.A., Ballard S.A., Junckerstorff R.K., Korman T.M. Clinical and micro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ggerthella lenta bacteremia. J. Clin. Microbiol. 2015;53:626–635.
Ugarte-Torres A., Gillrie M.R., Griener T.P., Church D.L. Eggerthella lenta bloodstream infec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mortality following empiric piperacillin-tazobactam (TZP) Monotherapy: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Clin. Infect. Dis. 2018;67:221–228.
Koh A., Molinaro A., Ståhlman M., Khan M.T., Schmidt C., Mannerås-Holm L., Wu H., Carreras A., Jeong H., Olofsson L.E., et al. Microbially produced imidazole propionate impairs insulin signaling through mTORC1. Cell. 2018;175:947.e17–961.e17.
Luo S, Zhao Y, Zhu S, Liu L, Cheng K, Ye B, Han Y, Fan J, Xia M. Flavonifractor plautii Protects Against Elevated Arterial Stiffness. Circ Res. 2023 Jan 20;132(2):167-181.
Karpat I, Karolyi M, Pawelka E, Seitz T, Thaller F, Wenisch C. Flavonifractor plautii bloodstream infection in an asplenic patient with infectious colitis. Wien Klin Wochenschr. 2021 Jul;133(13-14):724-726.
Pan Y, Su J, Liu S, Li Y, Xu G. Causal effects of gut microbiota on the risk of urinary tract stones: A bidirectional two-sample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 Heliyon. 2024 Feb 14;10(4):e25704.
Amerikanou C, Kanoni S, Kaliora AC, Barone A, Bjelan M, D’Auria G, Gioxari A, Gosalbes MJ, Mouchti S, Stathopoulou MG, Soriano B, Stojanoski S, Banerjee R et al., Effect of Mastiha supplementation on NAFLD: The MAST4HEALTH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Mol Nutr Food Res. 2021 May;65(10):e2001178.
Coello K, Hansen TH, Sørensen N, Ottesen NM, Miskowiak KW, Pedersen O, Kessing LV, Vinberg M. Affective disorders impact prevalence of Flavonifractor and abundance of Christensenellaceae in gut microbiota. Prog Neuropsychopharmacol Biol Psychiatry. 2021 Aug 30;110:110300.
Mehrotra, I, Snyder, M, Mamic, P. CHARACTERIZING THE GUT MICROBIOTA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HOST IN THE CHRONIC HEART FAILURE-ASSOCIATED ATRIAL FIBRILLATION. J Am Coll Cardiol. 2024 Apr, 83 (13_Supplement) 1033.
Stokholm J, Blaser MJ, Thorsen J, Rasmussen MA, Waage J, Vinding RK, Schoos AM, Kunøe A, Fink NR, Chawes BL, Bønnelykke K, Brejnrod AD, Mortensen MS, Al-Soud WA, Sørensen SJ, Bisgaard H. Maturation of the gut microbiome and risk of asthma in childhood. Nat Commun. 2018 Jan 10;9(1):141.
Wang, L., Zheng, Yb., Yin, S. et al.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ut microbiota and prostate cancer contributes to the gut-prostate axis: insights from a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 Discov Onc 15, 58 (2024).
Jian Gao, Xiaoyu Guo, et al., The Association of Fried Meat Consumption With the Gut Microbiota and Fecal Metabolites and Its Impact on Glucose Homoeostasis, Intestinal Endotoxin Levels, and Systemic Inflammati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Feeding Trial. Diabetes Care 1 September 2021; 44 (9): 1970–1979.
Mavrogeorgis, E.; Valkenburg, S.; Siwy, J.; Latosinska, A.; Glorieux, G.; Mischak, H.; Jankowski, J. Integration of Urinary Peptidome and Fecal Microbiome to Explore Patient Clustering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Proteomes 2024, 12, 11.
Hong, C.-T.; Chan, L.; Chen, K.-Y.; Lee, H.-H.; Huang, L.-K.; Yang, Y.-C.S.H.; Liu, Y.-R.; Hu, C.-J. Rifaximin Modifies Gut Microbiota and Attenuates Inflammation in Parkinson’s Disease: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Studies. Cells 2022, 11, 3468.
Yang L, Lin Q, Han L, et al. Soy hull dietary fiber alleviates inflammation in BALB/C mice by modulating the gut microbiota and suppressing the TLR-4/NF-κB signaling pathway[J]. Food & function, 2020, 11(7): 5965-5975.
Tomioka R, Tanaka Y, Suzuki M, et al. The Effects of Black Tea Consumption on Intestinal Microflora—A Randomized Single-Blind Parallel-Group, Placebo-Controlled Study[J]. Journal of Nutritional Science and Vitaminology, 2023, 69(5): 326-339.
Cheng H, Liu J, Tan Y, Feng W, Peng C. Interactions between gut microbiota and berberine, a necessary procedure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of berberine. J Pharm Anal. 2022 Aug;12(4):541-555.
He, L., Liu, Y., Guo, Y. et al. Diversity of intestinal bacterial lactase gene in antibiotics-induced diarrhea mice treated with Chinese herbs compound Qi Wei Bai Zhu San. 3 Biotech 8, 4 (2018)
Straub, T.J., Chou, WC., Manson, A.L. et al. Limited effects of long-term daily cranberry consumption on the gut microbiome in a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of women with recurrent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BMC Microbiol 21, 53 (2021).
Laatikainen, R., Jalanka, J., Loponen, J. et al.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 effect of low-FODMAP rye bread versus regular rye bread on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patients: association with individual symptom variation. BMC Nutr 5, 12 (2019).
Xu YJ, He Y, Chen C, Shi J, He M, Liu Y, Zhang Y, Liu Y, Zhang Y. Multiomics Analysis Revealed Colorectal Cancer Pathogenesis. J Proteome Res. 2024 Apr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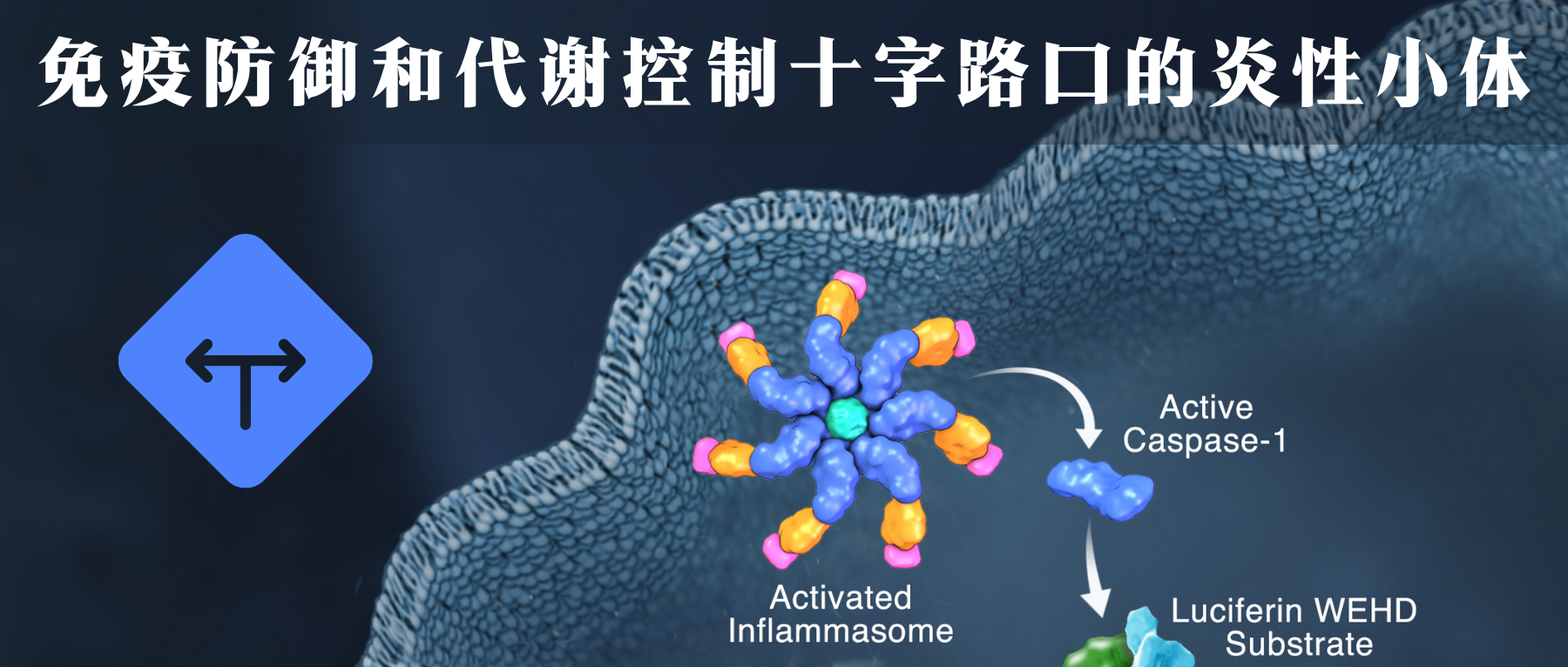
谷禾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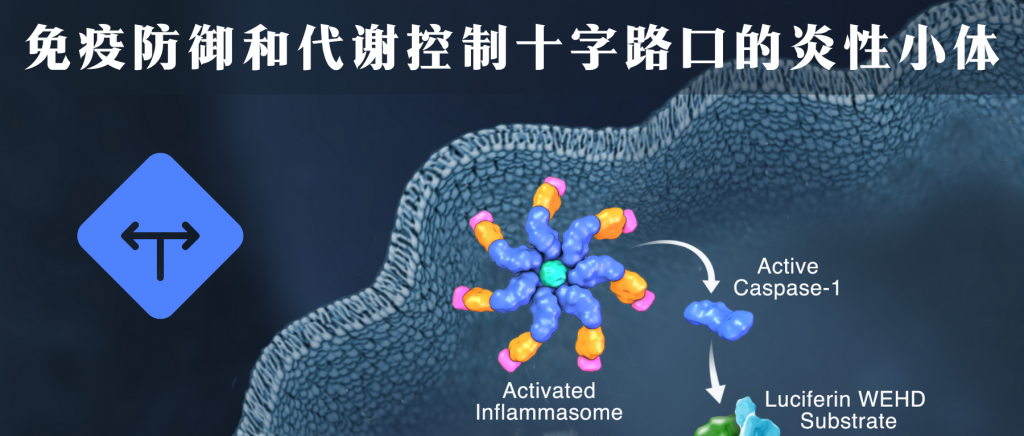
人体的肠道粘膜内层形成物理屏障和免疫防御系统,以防止微生物入侵。当身体受到感染或细胞遭受损伤时,免疫系统会启动炎症反应来应对这些情况。炎症是对感染和组织损伤的一种急性反应,以限制对身体的伤害,这种反应是身体自然的防御机制,旨在清除病原体并修复受损细胞或组织。
先天免疫系统包含多种种系编码的模式识别受体(PRRs),这些受体可以检测由细胞损伤或组织损伤产生的微生物抗原,称为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或损伤关联分子模式(DAMPs)。
这些PRRs包括位于细胞膜上的Toll样受体(TLRs)和C型凝集素受体(CLRs),以及细胞内PRRs如RIG样受体。NOD样受体(NLRs)是其他可以识别来源于病原体和受损细胞的分子模式的PRRs。
炎性小体的概念在2002年首次被提出,它是细胞内多种蛋白质组成的复合体,处在免疫防御和代谢控制十字路口,是细胞完整性的守护者并调控各种关键细胞功能。主要介导宿主对微生物感染和细胞损伤的免疫反应,在骨髓细胞中产生,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感知外界病原体或损伤后,传递信号给免疫系统,启动炎症。它们形成大型多蛋白信号传导平台来裂解和激活caspase-1,这是一种主要的炎症途径。活性caspase-1可以将非活性形式的促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IL-18裂解为活性形式来调节炎症和宿主防御反应,这些相关细胞因子介导针对感染的多种局部和全身免疫反应,包括诱导发热、白细胞迁移至损伤或感染部位,以及Th1、Th2和Th17反应的激活和极化。
此外,炎性小体激活与细胞焦亡有关,细胞焦亡又称细胞炎性坏死,是一种程序性细胞死亡。在对抗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其参与宿主防御鼠伤寒沙门菌(Salmonella typhimurium)、土拉热弗郎西丝菌(Francisella tularensis)和炭疽芽孢杆菌(Bacillus anthracis)。
各种内源性和外源性刺激已被证明可以激活炎性小体。由于大量微生物寄居在粘膜表面,维持人体和微生物群之间的稳定需要与炎性小体的共生相互作用。

炎性小体主要充当复杂的传感器,使宿主能够区分有益细菌和有害细菌,但它们也充当宿主与其肠道微生物群之间沟通的介质。肠腔的环境状态持续影响宿主反应,导致通过产生IL-1β或IL-18产生特定信号,进而调节肠道微生物群。
随后,调节的微生物群可以通过短链脂肪酸和胆汁酸衍生物等微生物副产物增强宿主反应。但是炎性小体的激活需要受到严格调节,以限制异常激活和对宿主细胞的损害。如果失调,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疾病。包括自身免疫疾病、癌症、胃肠道(GI)疾病和炎症性疾病。
因此,炎性小体对于协调体内精确的相互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通过针对与炎症小体信号传导相关的结构来研究炎症小体活性的适当调节和治疗干预,可能是一个有前途的研究领域。
本文旨在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炎性小体,讨论了不同炎性小体在人体内的功能、外来细菌、病毒等病原体入侵时,炎性小体在抵抗感染的作用。此外,炎性小体的失调或异常激活可能与人体一些疾病相关。炎性小体和微生物群的相互作用影响着人类健康。
✦
炎性小体(inflammasome)是由多种蛋白质组成的复合体,也称炎症小体,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概念由于2002年首次提出。
炎性小体可识别多种炎症诱导的刺激,包括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和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并控制重要的促炎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IL-18的产生。
▼
炎性小体的功能
炎症小体是细胞内多聚蛋白复合物,是细胞完整性的守护者并控制各种关键细胞功能的完整性。具体来说,炎症小体的功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参与免疫反应,加工IL-1β和IL-18
在体内,炎性小体已被证明参与抗微生物先天免疫反应。在这方面研究最广泛的炎症小体是NLRP3炎性小体,它参与了抗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的免疫反应。
caspase-1的激活受炎症小体调节,caspase-1的激活会导致IL-1β和IL-18的加工。
在非经典途径中,小鼠体内caspase-11(人类直系同源物包括caspase4和5)的裂解会激活NLRP3炎症小体,该炎症小体在维持肠道免疫稳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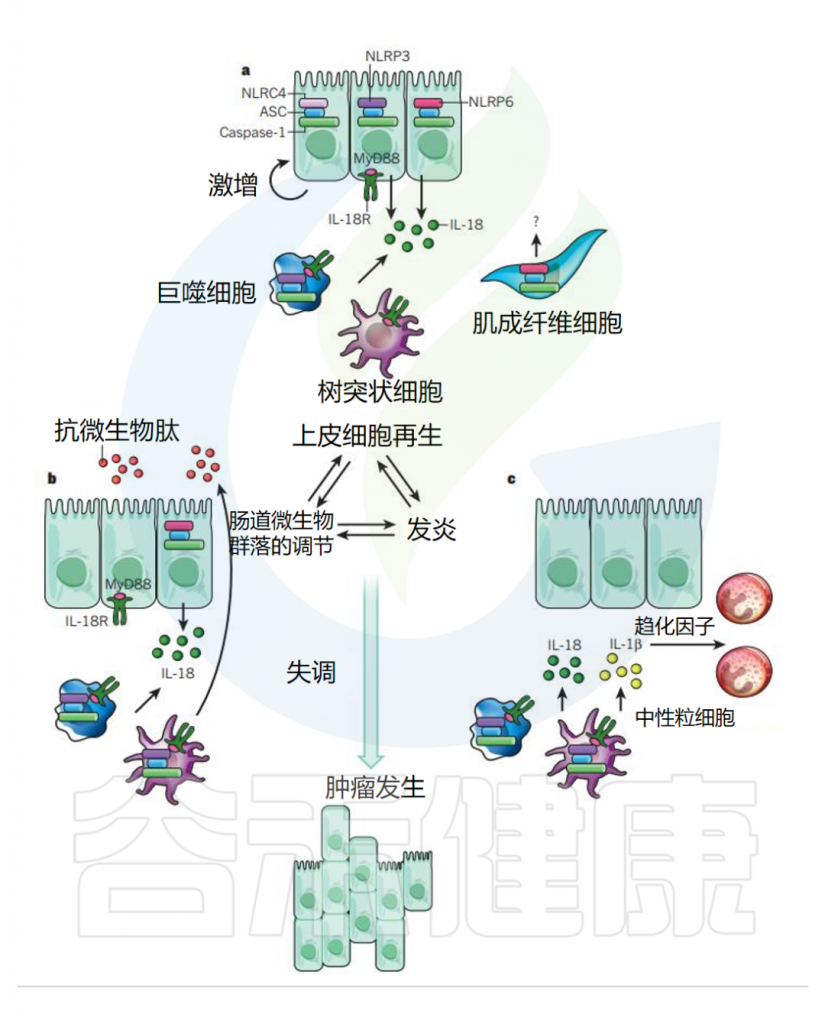
doi: 10.1038/nature10759.
需要注意的是,在急性炎症中,炎症小体的激活有助于去除死细胞并启动组织修复。然而,在慢性炎症中,炎症小体的持续激活是有害的,因为它会损伤组织。
▸ 促进细胞焦亡
此外,炎症小体激活与细胞焦亡有关。细胞焦亡是一种程序性细胞死亡,表现为细胞不断胀大直至细胞膜破裂,导致细胞内容物的释放进而激活强烈的炎症反应,是机体一种重要的天然免疫反应,在抗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
细胞焦亡最常发生在细胞内病原体感染时,并且可能形成抗菌反应的一部分。焦亡是caspase-1依赖性的,并且独立于促凋亡caspase发生。
注:尽管细胞焦亡被认为是程序性细胞死亡的一种形式,但它与细胞凋亡所呈现的免疫沉默细胞死亡不同。焦亡伴随着质膜破裂、水流入、细胞肿胀、渗透溶解和促炎细胞内容物的释放。焦亡还伴随着DNA裂解和核浓缩,这与细胞凋亡的DNA阶梯特征不同,因为核完整性并未受到损害。
细胞焦亡的调控尚不明确;然而,细胞焦亡的程度似乎随着炎症体刺激的增加而增加。细胞焦亡是否在产生更活跃的炎症小体途径(下文讨论)的遗传性自身炎症疾病中发挥病理作用尚待确定。
▸ 与炎症性疾病相关,调节肠道稳态
炎性小体激活需要严格调节,以限制异常激活和对宿主细胞的损害。炎症小体活性失调与多种炎症性疾病有关,包括自身免疫、癌症和胃肠道疾病。
尽管炎症小体主要充当复杂的传感器,使宿主能够区分有益细菌和有害细菌,但它们也充当宿主与其肠道微生物群之间沟通的介质。
肠腔的环境状态持续影响宿主反应,导致通过产生IL-1β或IL-18产生特定信号,进而调节肠道微生物群。
随后,调节的微生物群可以通过短链脂肪酸和胆汁酸衍生物等微生物副产物增强宿主反应。因此,炎症小体对于协调体内精确的相互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在这方面,通过针对与炎症小体信号传导相关的结构来研究炎症小体活性的适当调节和治疗干预,可能是一个有前途的研究领域。
炎症小体调节微生物感染和自身炎症性疾病期间的炎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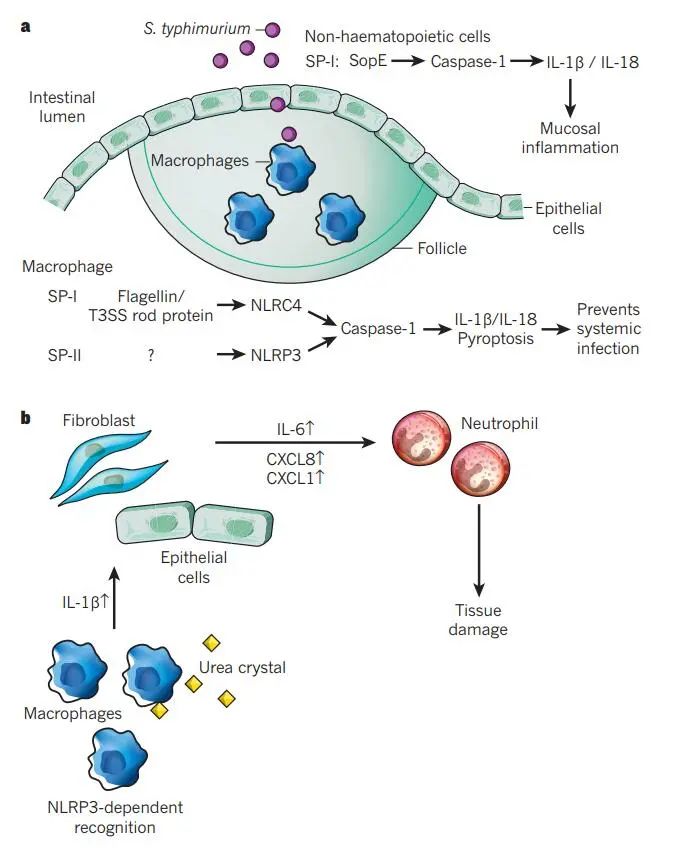
doi: 10.1038/nature10759.
a.鼠伤寒沙门氏菌通过肠上皮屏障进入宿主。M细胞是一种特殊的上皮细胞类型,分布在Peyer’s斑块上,特别参与沙门氏菌的胞吞作用和Peyer’s斑块中巨噬细胞的感染。炎症小体和caspase-1参与了几种细胞类型和感染的几个步骤。将细菌效应蛋白SopE注射到上皮细胞中,通过涉及GTPase Rac1的过程诱导caspase-1独立于NLRP3和NLRC4的激活。由此产生的粘膜炎症依赖于非造血细胞产生的IL-1β和IL-18。在巨噬细胞感染时,细菌蛋白鞭毛蛋白和PrgJ (T3SS的一部分)通过NLRC4被感知。这导致caspase-1的激活,导致IL-1β/IL-18加工和焦亡,从而限制全身感染。NLRP3通过识别未知信号参与这些过程。
b.巨噬细胞吞噬尿酸钠(MSU)晶体诱导nlrp3依赖性caspase-1激活和IL-1β释放,刺激非造血细胞产生IL-6和趋化因子(CXCL1和CXCL8),吸引中性粒细胞。然后,活化的中性粒细胞引起组织损伤。治疗性阻断人IL-1β可改善痛风的炎症发作。
▸ 和自噬途径的相互调节
自噬是一种细胞保护过程,细胞通过该过程将受损的蛋白质、细胞器或病原体隔离在双膜室(自噬体)中,靶向这种细胞材料在溶酶体中降解,并回收组成分子。
自噬发生在正常生理条件下,但可以通过细胞应激(如饥饿、促炎信号传导(例如 IFNγ)或细菌感染)上调。
最近的报告揭示了炎症小体和自噬途径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在没有污染配体的情况下,用TLR4激动剂脂多糖处理不会诱导野生型巨噬细胞中的炎症小体活化。然而,通过自噬调节因子Atg16L1或 Atg7 的基因消融来阻断自噬,可以实现LPS依赖性炎症小体激活,这表明自噬通常会对抗LPS引起的炎症小体激活。
另一项研究发现,炎症小体对自噬有负向调节作用,这使炎症小体和自噬之间的联系更加复杂。
!
炎性小体是好是坏
“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炎症小体过少或过于活跃对健康都是不利的。炎症小体的活动是需要严格控制的,不能随意抑制和刺激,以避免产生过多的炎性细胞因子导致细胞死亡,伤及自身。
所以正常情况下,炎症小体,特别是NLRP3的表达在许多细胞中相对较低,需要诱导去引发信号。
先天免疫系统包含多种编码的模式识别受体(PRR),可检测微生物抗原,称为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或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由细胞或组织损伤产生。
炎症小体如何被激活尚不清楚。由于激活炎症小体的PAMP、DAMP和病原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可能存在多种途径。
炎性小体在感知到PAMPs和DAMPs的结构多样性后进行组装。已经提出了几个模型来解释这些信号是如何被感知的,包括基于一般细胞应激识别的模型(图a和b)或基于激活信号的直接和间接识别的模型(图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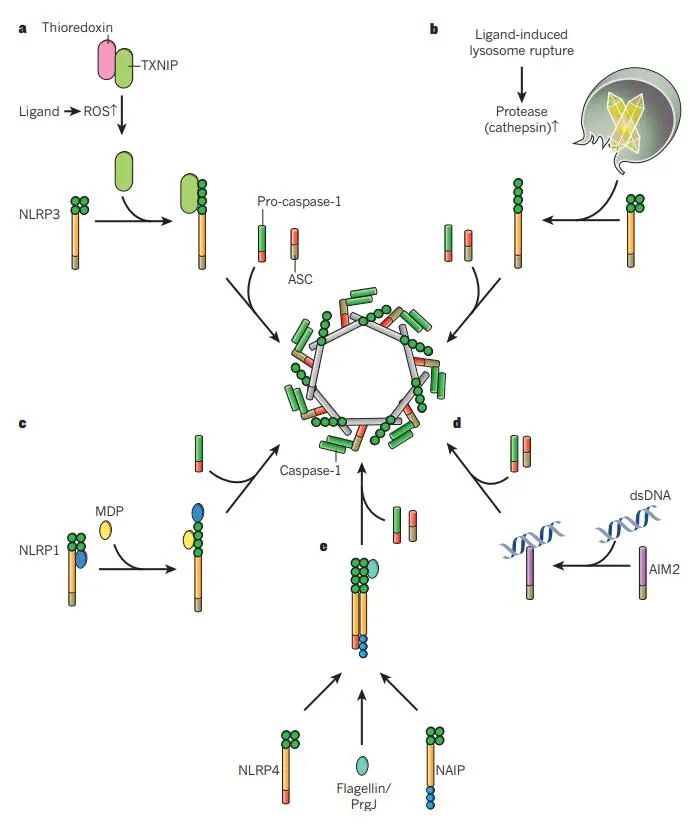
doi: 10.1038/nature10759.
(a) NLRP3感知细胞内(可能由线粒体)直接或间接由NLRP3炎症小体激活剂产生的活性氧(ROS)。硫氧还蛋白和硫氧还蛋白相互作用蛋白(TXNIP)的复合物可以感知ROS的增加,从而导致该复合物的解离。
随后,TXNIP与NLRP3结合导致NLRP3的激活,ASC和前caspase-1的募集,以及活性炎性体复合物的形成。
(b) 溶酶体失稳后,NLRP3被激活。特定晶体和颗粒结构的吞噬可导致溶酶体不稳定和溶酶体内容物(包括蛋白酶)的释放。这些蛋白酶可导致负调节因子的蛋白水解失活或NLRP3正调节因子的蛋白水解激活,导致炎性小体组装。
(c, d) NLRP1和AIM2直接感知配体。特异性配体(muramyl二肽(MDP)和双链DNA (dsDNA))的直接结合可导致NLRP1和AIM2的构象改变,导致炎性小体活化。
(e) NLRP1炎症小体的形成不依赖于ASC。NAIP蛋白感知细菌蛋白,导致NLRC4的募集和NLRC4炎症小体的组装。
此外,构成信号的限制因子如pro-IL1β和-IL18的转录上调是炎症小体激活的先决条件。除了编码原细胞因子的基因的诱导转录之外,NLRP3转录的激活也由NF-κB 激活剂(例如TLR配体)诱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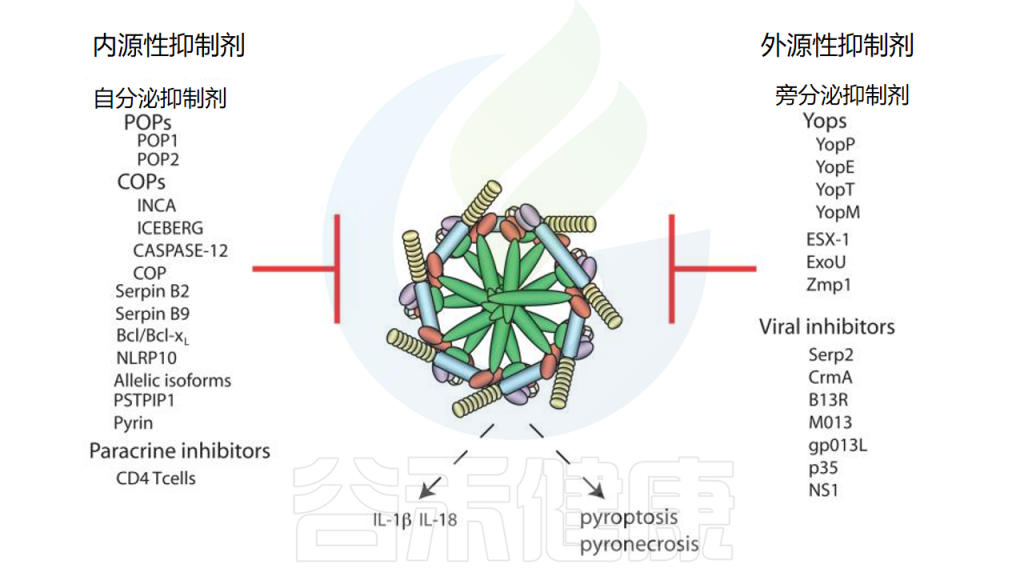
doi: 10.1146/annurev-immunol-031210-101405.
大部分炎性小体主要由受体蛋白(NLR或ALR家族的成员),衔接蛋白ASC和效应蛋白caspase组成。
炎性小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细胞结构,它在炎症和免疫反应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不同类型的炎性小体在形态和功能上都有所不同,对于了解炎症过程和治疗炎症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将探讨不同类型的炎性小体的特点和对肠道微生物群的作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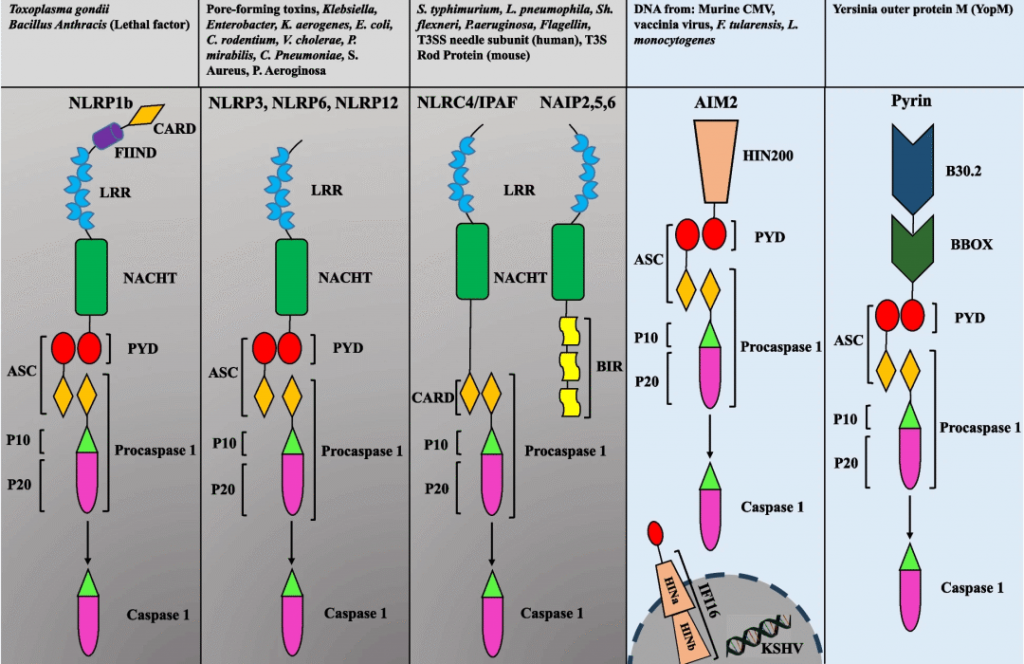
Manshouri S,et al.Cell Commun Signal.2024
NLRP1炎症小体
NLRP1是第一个报道的形成炎症小体的分子,对caspase-1、caspase-5和ASC的需求最低。
NLRP1在结构上与其他NLR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额外的C端延伸,由具有未知功能的结构域和CARD结构域组成。
NLRP1炎症小体在小鼠和人类中是不同的。小鼠NLRP1炎症小体由Nlrp1a、b和c的三个旁系同源物组成,其中包含NR100结构域,而不是人类中看到的PYD。
▸ NLRP1会影响产生丁酸盐的菌群
研究发现NLRP1炎症小体可以影响肠道微生物群。Nlrp1缺陷的小鼠表现出产生丁酸盐的细菌数量增加。丁酸盐已被证明通过促进肠道屏障的功能(例如粘液产生和紧密连接)对炎症性肠病(IBD)具有有益作用。
NLRP1炎症小体可能通过减少肠道微生物群的丁酸盐产生而对IBD产生负面影响。IBD有两种主要的临床形式,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短链脂肪酸(SCFA)是由有益肠道细菌通过高纤维饮食发酵产生的。这些SCFA在减少炎症、调节免疫功能和防止过度活跃的免疫反应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减缓IBD的临床进展。
NLRP3炎症小体
NOD样受体蛋白3(NLRP3)炎性小体包括N末端的热蛋白结构域(PYD)、中央NACHT结构域(包括带有核苷酸三磷酸腺苷/三磷酸鸟苷 (ATP/GTPase) P 环的七个基序和Walker A 和 B 结合位点),以及C端的9个富含亮氨酸的重复序列 (LRR)。
▸ 与其他炎症小体相比,NLRP3炎症小体需要两个信号
信号1(启动)由微生物分子或内源性细胞因子或 PRR(例如 TLR)的激活提供,导致经典和非经典 NLRP3 炎性体成分的转录上调。
它由NLRP3和pro-IL-1β的转录上调以及非转录机制组成,例如N端 PYD 内残基的去磷酸化、PYD 和 NACHT 结构域之间关键丝氨酸残基的磷酸化和 NLRP3 去泛素化。
Caspase-8和FAS相关死亡结构域蛋白(FADD)通过调节NF-kB通路介导此步骤。Lys-63 特异性去泛素酶 BRCC36 (BRCC3) 和 IL-1 受体相关激酶 1 (IRAK1) 调节 NLRP3 的激活。
信号2(激活)由PAMP或DAMP、成孔毒素、K +外流、溶酶体破坏、线粒体活性氧产生、心磷脂重新定位到线粒体外膜以及氧化线粒体DNA的释放提供,然后Cl -流出。
NLRP3炎症小体的经典和非经典激活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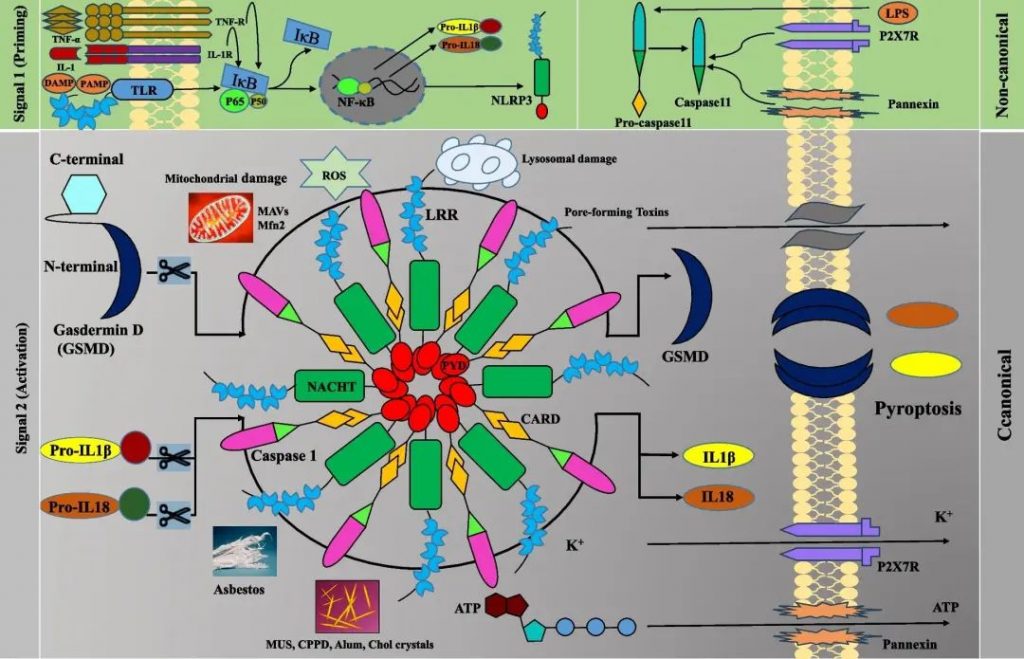
Manshouri S,et al.Cell Commun Signal.2024
经典途径涉及TLR信号传导,通过NF-κB途径诱导IL-1β、IL-18和NLRP3的转录。非规范途径涉及脂多糖等刺激,需要caspase-11来激活caspase-1。
▸ 微生物与NLRP3炎症小体的相互作用
一些共生肠道微生物可能会激活肠粘膜巨噬细胞中的NLRP3炎性小体。据报道,奇异变形杆菌(Proteus mirabilis)可能通过产生溶血素成为 NLRP3 激活剂。肠杆菌(Enterobacter)和克雷伯菌属(Klebsiella spp)在口腔定植可能会触发NLRP3炎症小体。存在于小鼠口腔中的产气克雷伯菌(K.aerogenes)通过巨噬细胞分泌IL-1β导致牙周炎。
研究还报道了肠道微生物群异常积累对年龄相关性心房颤动的因果影响,表明微生物群-肠道屏障-心房NLRP3炎性体相互作用可能作为治疗年龄相关性心律失常的潜在靶点。
在临床前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将线粒体与吞噬体隔离开,以逃避杀菌活性氧。这种巨噬细胞死亡的逃避依赖于NLRP3炎性体。使用小干扰RNA(siRNA)靶向NLRP3可以改善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小鼠的细菌清除率。研究人员还发现,NLRP3 抑制和电子传递链复合物 II 抑制相结合,可以提高对人类单核细胞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杀伤力。
最近,证明了NLRP3炎性体在接触香烟烟雾后被激活,从而为肺部造成铜绿假单胞菌引起的急性损伤做好准备。这项研究表明,靶向NLRP3炎性体可能是治疗香烟烟雾引起的肺损伤的潜在治疗方法。
NLRP6炎症小体
NLRP6,也称为 PYPAF5,被描述为大多数免疫细胞中NF-κB和caspase-1表达的调节剂。这种蛋白质存在于肠上皮细胞中。研究表明,NLRP6对于调节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和功能至关重要。
▸ 调节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和功能
NLRP6通过炎症小体依赖性和炎症小体独立途径、结肠炎相关肿瘤发生和杯状细胞中的粘液分泌来协调宿主与肠道病毒和细菌感染的相互作用。肠上皮细胞中的NLRP6缺陷与IL-18产生和caspase-1激活中断有关。NLRP6缺陷小鼠表现出普氏菌科和 TM7 的生长,以及乳杆菌和厚壁菌门的减少。
这些不平衡会引发结肠炎和肠道自发炎症。微生物群相关代谢物,例如牛磺酸和肠道共生细菌,可以激活NLRP6炎性体产生抗菌肽。杯状细胞可以通过 TLR-Myd88 信号传导激活 NLRP6 炎症小体,从而产生muc2。革兰氏阳性病原体产生脂磷壁酸,通过ASC募集激活NLRP6炎症小体,导致全身感染。应激诱导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抑制NLRP6炎症小体的激活,后者会导致肠道炎症和肠道微生物组的改变。
▸ NLRP6缺陷会导致胃肠道生态失调
NLRP6 缺陷的小鼠容易发生炎症。NLRP6 炎症小体在正常条件下是自我抑制的。脂磷壁酸和双链 RNA (dsRNA) 可以直接与 NLRP6 结合,从而产生可能的构象变化,以帮助液-液相分离(LLPS),这是炎症小体组装所必需的早期步骤。
此外,脂多糖可以直接与NLRP6结合,这可能导致LLPS的形成。然后,它与ASC相互作用激活 caspase-1或 caspase-11,从而激活 GSDMD 并导致质膜中孔的形成以及促炎细胞因子和细胞内内容物的释放。如果与ASC的相互作用不形成 NLRP6 炎症小体,则 LLPS 中的 NLRP6 通过诱导干扰素 (IFN) 和 IFN 刺激基因,诱导替代的炎症小体独立途径。
总而言之,在强烈的炎症反应具有破坏性的情况下,NLRP6可能通过 TLR 轴发挥保护作用,而其作用对于维持肠道稳态是必要的。NLRP6炎症小体与胃肠道的稳态有关。先前的研究表明NLRP6失调可能导致胃肠道生态失调。
此外,NLRP6炎症小体刺激抗菌肽(AMP)的表达,包括血管生成素-4(Ang4)。一些微生物代谢物,包括牛磺酸、精胺和组胺,似乎可以诱导NLRP6依赖性IL-18和AMP的产生。
NLRP12炎症小体
NLRP12,也称为Nalp12和Pypaf-7,与ASC和胱天蛋白酶1形成炎症小体,使IL-1β成熟。它是最早与衔接蛋白ASC共定位并相互作用形成炎症小体的NLR之一。人类基因组中NLRP12编码序列的突变与IL-1介导的炎症性疾病有关。
▸ 识别鼠疫耶尔森氏菌等病原菌
尽管我们对NLRP12在健康和疾病中的作用的了解有限,但最近的数据表明,NLRP12对于识别鼠疫耶尔森氏菌(鼠疫病原体)至关重要。
NLRP12在巨噬细胞感染鼠疫杆菌后控制caspase-1裂解以及IL-1β和IL-18分泌。然而,NLRP12可以抑制骨髓源性巨噬细胞产生IL-12,并负向调节宿主对流产布鲁氏菌的防御。
NLRP12的确切配体目前未知;然而,它的激活需要一个功能正常的T3S系统。这表明细菌毒力因子进入宿主细胞质可能是直接激活NLRP12或改变宿主信号通路所必需的。无论激活机制如何,NLRP12驱动的IL-18分泌和相关的IFN-γ产生在小鼠抵抗鼠疫耶尔森氏菌感染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NLRP12缺陷小鼠在感染后表现出更高的死亡率和细菌载量。
▸ 抑制肠道炎症和肿瘤
除了形成炎症小体之外,NLRP12还通过负向调节NF-kB信号传导来抑制肠道炎症和肿瘤发生。几项独立研究表明,NLRP12 在生化检测、结肠癌和结肠炎模型中对经典和非经典NF-κB信号传导有负向调节作用。
NLRP12被认为在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期间独立于炎症小体抑制宿主防御,因为Nlrp12缺陷小鼠比WT对照对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具有更强的抵抗力,并且炎症细胞因子水平较低。
NLRP12在造血细胞中发挥抑制肿瘤发生的作用,但它不是造血细胞,而是非造血细胞,这对于限制肿瘤数量至关重要。尽管如此,两项研究都表明NLRP12在控制结肠炎症反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NLRC4炎症小体
NLRC4(以前称为IPAF,Card12)在感染各种革兰氏阴性菌后可形成炎症小体,如鼠伤寒沙门菌(S.typhimurium)、嗜肺军团菌、福氏志贺菌和铜绿假单胞菌。NLRC4在髓系中表达,其基本作用是防止细菌入侵。
与其他炎症小体不同,NLRC4与另一种NLR蛋白NAIP结合被激活,NAIP作为NLRC4激活剂的受体。
▸ 有效抵御铜绿假单胞菌和伤寒沙门氏菌
几项研究表明,NLRC4在宿主防御有鞭毛的铜绿假单胞菌方面是有效的。在缺乏NLRC4或胱天蛋白酶-1激活的情况下,含有军团菌的吞噬体不能与溶酶体融合。相反,鞭毛蛋白突变的军团菌不能激活巨噬细胞中的胱天蛋白酶1。
鼠伤寒杆菌可以激活NLRC4和NLRP3,这导致ASC的形成和胱天蛋白酶向炎症小体的募集。NLRC4炎症小体感知PrgJ,一种III型分泌系统(T3SS)的成分,并通过CARD-CARD与胱天蛋白酶-1的相互作用启动炎症小体组装。
▸ 与婴儿期肠炎伴自体炎症相关
研究人员证明, NLRC4的功能获得性突变与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有关,这种疾病称为婴儿期肠炎伴自体炎症(AIFEC)。这种疾病的特点是巨噬细胞激活和胃肠道严重炎症。常驻肠道单核吞噬细胞(iMP),例如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可以对抗肠道病原微生物,同时保持对共生微生物的耐受性。
由于胃肠道的免疫细胞主要与许多共生微生物发生反应,它们应用多种机制来限制针对胃肠道共生微生物的不受控制的免疫反应。iMP中的NLRC-4激活后,分泌IL-1β诱导内皮细胞中粘附分子的表达。这些粘附分子促进中性粒细胞募集到肠粘膜和外来微生物的摄入。
PYHIN炎症小体
另一类与NLR不同的炎症小体已被鉴定为PYHIN家族。PYHIN是由四个人类基因(AIM2、IFI16、MNDA和IFIX)和13个小鼠基因组成的家族,并包含一个PYD和一个或两个HIN-200DNA 结合域。
AIM2和IFI16已被证明可形成caspase-1激活炎症小体。与NLR不同,AIM2和IFI16在这两种情况下都直接与其配体dsDNA结合。ASC是招募pro-caspase-1所必需的,因为AIM2和IFI16缺乏 CARD。
▸ AIM2对于肠道微生物群稳态非常重要
在感染过程中,AIM2感知来自鼠巨细胞病毒、牛痘病毒、土拉弗朗西斯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的 DNA 。
AIM2炎症小体的一个功能是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研究表明,AIM2炎症小体的激活导致肠道中IL-18和AMP的产生。Aim2缺陷小鼠的IL-18和AMP(例如REG3c和REG3b)减少。AIM2 的缺乏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从而增加对结肠炎的易感性。
同时研究发现, Aim2缺陷小鼠粪便中肠杆菌科成员(例如大肠杆菌)的数量比普通小鼠高数百倍。当新杀弗朗西丝菌(F.novicida)(一种胞质病原体)从液泡逃逸到细胞质时,AIM2炎性小体就会受到刺激。缺乏逃离液泡的关键基因的F. novicida突变体无法触发AIM2炎症小体。
与NLRP6类似,AIM2炎性小体对于维持肠道微生物稳态至关重要。在胃肠道中,未经治疗的Aim2缺陷小鼠显示,Akkermansia muciniphila和 Anaeroplasma的数量较高,而双歧杆菌、普雷沃菌、Anaerostipes和Paraprevotella的数量较低。
Pyrin炎症小体
Pyrin是一种高分子量(86kDa)蛋白质,主要存在于免疫细胞中,包括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树突状细胞。
与其他免疫传感器不同,pyrin通过细胞骨架重塑而不是微生物化合物来检测细菌毒力。
Pyrin在识别病原体对RhoA GTPase的失活修饰后,以ASC依赖性方式介导caspase-1炎症小体组装。小鼠pyrin有两个功能性磷酸化位点:Ser-205 和Ser-241,它们通过与14-3-3蛋白结合而使pyrin 失活。当毒素刺激或细菌感染时,导致Rho修饰,Ser-205和Ser-241去磷酸化,导致14-3-3解离。该级联导致吡啶激活并形成寡聚吡啶-ASC炎性体复合物。
▸ 在维持肠道稳态中发挥作用
尽管关于肠道微生物群产生的特定pyrin炎症小体激活剂的知识很少,但最近的研究揭示了它们在维持肠道稳态中的作用。在一项使用小鼠结肠炎的研究中,pyrin炎症小体信号可防止生物失调,促进肠道屏障完整性,并改善结肠炎症和肿瘤发生。
最近一项使用全基因组合并CRISPR筛选技术的研究中,两种胆汁酸类似物(BAA485和BAA473)被鉴定为在髓系和IEC系中诱导pyrin炎症小体信号传导的特异性配体。由于肠道细菌是胆汁酸代谢的丰富来源,类似的微生物组衍生的pyrin炎症小体激活配体可能有助于调节肠道稳态。
总体而言,pyrin炎症小体为与细胞骨架结合的先天免疫成分提供了新的范例,为细胞免疫的结构调节提供了新的机制。
✦
炎症小体正在成为宿主针对微生物病原体反应的关键调节因子。当微生物侵入组织或引起细胞损伤时,这些胞质多蛋白复合物会招募并激活半胱氨酸蛋白酶caspase-1。
炎症小体激活的caspase-1通过将促炎细胞因子IL-1β和IL-18裂解为其生物活性形式并将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释放到细胞外环境中来诱导炎症。此外,炎症小体通过称为细胞焦亡的炎症细胞死亡程序来对抗细菌复制并清除受感染的免疫细胞。
跟着谷禾一起来深入了解炎症小体在宿主与微生物相互作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探讨其对免疫调节和疾病防御的影响,以及在维持体内微生物稳态和免疫平衡方面的关键功能。
炎症小体的组装和caspase-1的激活在病原体特异性方式下发生,尽管不同的炎症小体在感染过程中可能具有相似的作用。
▸ Nlrp1b炎症小体
Nlrp1b炎症小体识别细胞质中存在的炭疽芽孢杆菌致死毒素,Nlrp1b基因突变被确定为炭疽致死毒素诱导巨噬细胞死亡的关键易感位点。值得注意的是,Nlrp1b炎性体诱导的细胞焦亡赋予体内对炭疽芽孢杆菌孢子感染的抵抗力,突显了细胞焦亡对于宿主防御病原体的重要性。
▸ Nlrp3炎症小体
NLR家族成员Nlrp3的激活包括一个两步过程,需要用TLR和NLR配体启动以增强NF-κB驱动的Nlrp3转录,然后将巨噬细胞暴露于微生物毒素和离子载体(例如尼日利亚菌素和蓖麻毒素)或内源性毒素。
在巨噬细胞分别感染细菌、病毒和真菌病原体如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流感病毒和白色念珠菌的过程中,可以结合Nlrp3启动和激活步骤。类似于Nlrp1b炎症小体在炭疽杆菌感染中的作用,Nlrp3炎症小体激活缺陷使小鼠对念珠菌病高度敏感。
▸ Nlrc4炎症小体
Nlrc4炎性体可检测沙门氏菌(Salmonella)、假单胞菌(Pseudomonas)、军团菌(Legionella)和志贺氏菌(Shigella spp.)的III型和IV型细菌分泌系统的细菌鞭毛蛋白和基体杆成分。
除了分泌IL-1β和IL-18之外,最近还确定诱导焦亡细胞死亡是一种关键的体内机制,Nlrc4炎性体通过该机制清除表达鞭毛蛋白的细菌,例如嗜肺军团菌和伯克霍尔德菌。
人们认为细胞焦亡使细胞内细菌暴露于细胞外免疫监视,从而使它们被抗菌肽、免疫球蛋白和补体系统破坏,并被中性粒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摄取。
▸ AIM2炎症小体
最后,AIM2响应土拉热弗朗西斯菌(F.tularensis)、单核细胞增多性李斯特菌和某些DNA病毒(例如CMV和痘苗病毒)以诱导caspase-1激活。caspase-1缺陷型小鼠对土拉菌病(土拉菌病的病原体)感染的敏感性增加,说明AIM2炎性小体在宿主对微生物病原体的防御反应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细菌和病毒效应物对炎症小体途径的调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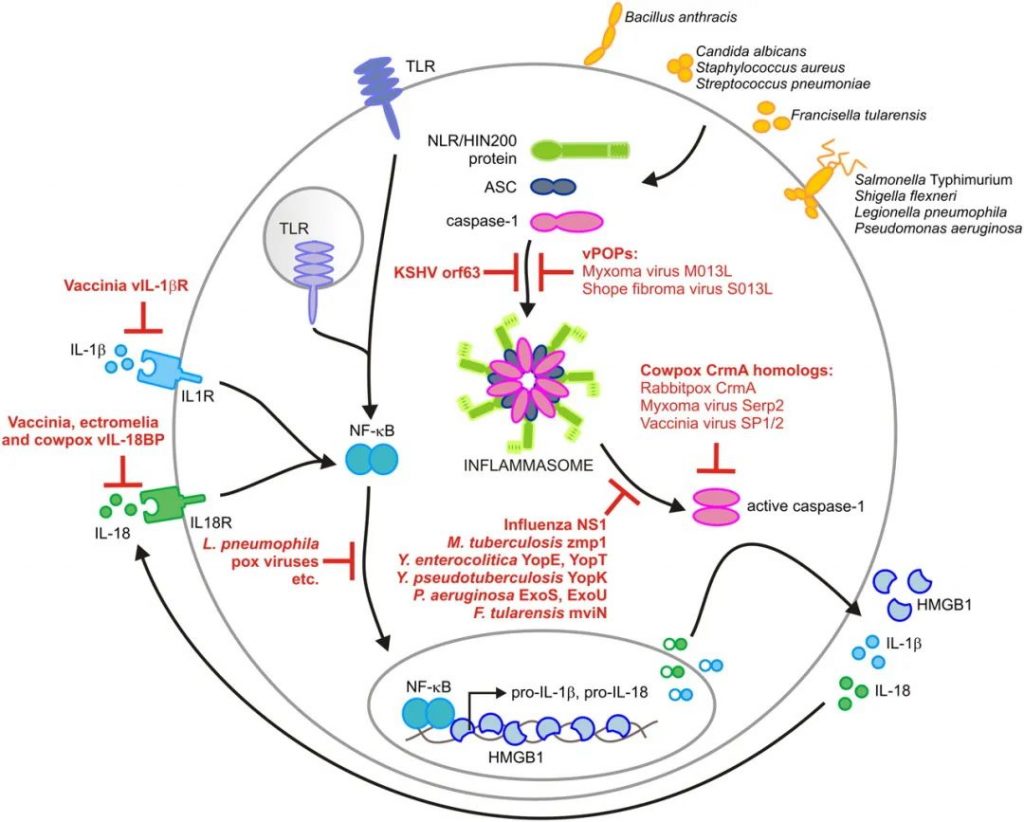
doi: 10.4049/jimmunol.1100229.
细菌、病毒和真菌病原体感染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会诱导炎性体复合物的组装。这些多蛋白复合物驱动诱导caspase-1的激活,从而使IL-1β、IL-18和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释放到细胞外。
鉴于炎症小体在控制微生物病原体复制和传播中的重要性,细菌进化出一套机制来对抗炎症小体组装并干扰caspase-1效应机制的诱导也就不足为奇了。
▸ Yop蛋白等毒力因子抑制IL-1β分泌
例如,肠道病原性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通过专用的III型分泌系统将称为Yop蛋白的毒力因子注入宿主细胞胞浆中。在这些效应蛋白中,YopE和YopT抑制caspase-1激活以及随后成熟IL-1β的分泌。
这些Yop蛋白是Rho GTP酶和Rho介导的过程(例如细胞骨架重组和吞噬作用)的负调节因子。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Yop效应蛋白和细胞骨架过程如何干扰炎症小体信号传导,但显性失活蛋白和化学抑制剂导致Rho GTPase Rac1失活表明该Rho GTPase在caspase-1激活和IL-1β分泌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假结核耶尔森氏菌使用名为YopK的第三种效应蛋白来掩盖细菌III型分泌系统并阻止其被Nlrp3和Nlrc4炎性体识别。这导致宿主巨噬细胞中的细菌存活率增加,说明炎症小体在控制侵入性耶尔森氏菌细胞内增殖中的重要性。
▸ 毒力因子外酶抑制caspase-1激活
表达毒力因子外酶(Exo)U的铜绿假单胞菌分离株使用不同的策略来抑制人类吞噬细胞中caspase-1的激活。这种革兰氏阴性病原体编码一种名为ExoU的具有磷脂酶A2活性的酶,可抑制Nlrc4炎性体驱动的受感染巨噬细胞分泌IL-1β和IL-18。
ExoS是另一种假单胞菌毒力因子,可干扰炎症小体诱导的IL-1β产生。该效应蛋白通过涉及其ADP-核糖基转移酶活性的不完全表征过程抑制caspase-1激活。
▸ 干扰炎性小体的信号传导
嗜肺军团杆菌(L.pneumophila)代表了革兰氏阴性病原体如何干扰炎症小体信号传导的另一个例子。Nlrc4炎性小体限制体外培养的巨噬细胞和受感染小鼠肺部的军团菌生长。该病原体干扰炎性小体接头ASC的转录上调,以保护其在人单核细胞中的增殖。
F.tularensis利用假定的脂质II翻转酶mviN来抑制AIM2炎症小体的激活。mviN突变株感染小鼠,由于AIM2炎性体介导的IL-1β分泌增强和巨噬细胞焦亡,导致体内毒力受损。
革兰氏阳性病原体(例如结核分枝杆菌)也已进化出干扰炎性体功能的机制。被称为Zmp1的推定Zn2+金属蛋白酶对Nlrc4炎性体激活和IL-1β分泌的抑制使这种人类结核病病原体在骨髓细胞中增殖。
炎症小体信号传导的调节并不局限于细菌病原体。事实上,病毒提供了一些最具特征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影响炎症小体。
▸ 牛痘病毒编码的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抑制 Caspase-1
牛痘病毒细胞因子反应修饰物A(CrmA)及其在牛痘病毒中的同源物直接靶向影响Caspase-1的酶活性。
CrmA和其他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在增强痘病毒毒力方面的重要性通过以下观察得到证实:CrmA的缺失会减弱BALB/c和C57BL/6小鼠鼻内和颅内感染的毒力。同样,感染缺乏CrmA同源Serp2的粘液瘤病毒突变体的兔子的病毒滴度显著降低。
此外,正痘病毒、痘苗病毒和副痘病毒产生可溶性IL-18结合蛋白,可防止细胞因子诱导的IL-18受体激活。因此,正痘病毒通过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和清道夫受体分别对caspase-1活性和下游炎症体效应子的联合抑制作用来增加毒力。
注:清道夫受体是吞噬细胞表面的一组异质性分子
▸ 病毒诱饵蛋白对炎症小体组装的抑制作用
除了直接靶向caspase-1的酶活性并干扰IL-1和IL-18受体的连接外,病毒还部署了阻止炎症小体组装的分子。
卡波西肉瘤相关疱疹病毒(KSHV)Orf63的作用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Orf63是一种病毒Nlrp1同源物。KSHV Orf63与人Nlrp1和Nlrp3相互作用,以阻止其各自炎症小体的组装以及随后的caspase-1依赖性先天免疫反应。
KSHV Orf63表达的转录下调降低了病毒复制率,这是由于Nlrp1和Nlrp3介导的IL-1β分泌增强以及KSHV感染的人单核细胞和293T细胞中焦亡诱导的结果。
吡啶结构域蛋白(POP),例如粘液瘤病毒M013L和纤维瘤病毒S013L,代表了病毒诱饵蛋白抑制炎性体的另一个例子。由于宿主炎症反应增加和病毒复制减弱,缺乏编码M013L基因的粘液瘤病毒突变体的病毒血症显著减少,从而强调了粘液瘤病期间病毒POP的重要性。
此外,人类CARD蛋白ICEBERG、COP、INCA和CASP12 S被认为通过与caspase-1前结构域中的CARD基序的同型CARD相互作用来清除caspase-1,从而干扰炎症小体组装。然而,与病毒POP不同,人类CARD-only蛋白的病毒对应物仍有待鉴定。
炎症小体的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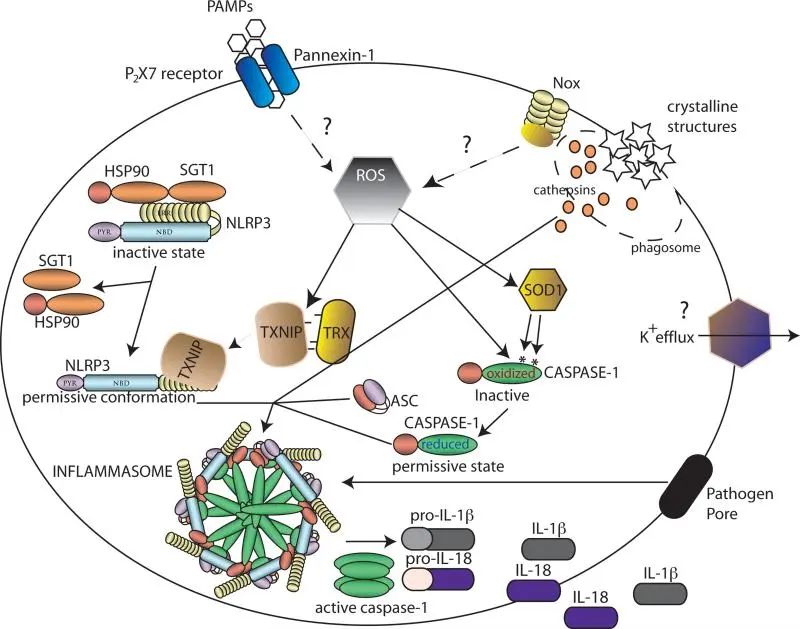
doi: 10.1146/annurev-immunol-031210-101405.
▸ 流感病毒抑制炎症小体信号传导
有趣的是,流感病毒使用与上述正痘病毒无关的机制来阻止caspase-1的激活并干扰炎症小体信号传导。人类流感A/PR/8/34(H1N1)的突变病毒,其中流感NS1基因被删除,触发受感染宿主细胞分泌显著增加的IL-1β和IL-18水平,并未能阻止巨噬细胞中caspase-1的成熟。
这些突变病毒在体外被减毒,但caspase-1依赖性和非依赖性机制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表型尚不清楚。流感NS1驱动的caspase-1激活抑制似乎仅依赖于NS1的N-末端RNA结合/二聚化结构域,而羧基末端效应结构域对于抑制IL-1β和IL-18分泌是可有可无的。对流感病毒NS1抑制胱天蛋白酶-1激活的分子机制的进一步分析可能揭示病毒靶向炎症小体的有趣的新机制。
我们的观点
总体而言,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本质上是动态的。病毒利用了人体的基因,并利用它们来规避免疫系统。细菌也进化出了复杂的机制。病原体对炎症小体的特异性靶向强调了其在先天免疫中的重要性。
✦
炎症小体是一种在人体免疫系统中起关键作用的多蛋白复合物,其异常活化或抑制与多种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炎症小体在调节炎症反应、细胞焦亡和免疫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由于炎症小体成分的遗传突变以及调节缺陷而导致的不适当的炎症小体反应与多种人类疾病有关。研究表明,炎症小体的功能异常与自身免疫疾病、感染性疾病和肿瘤等的发生有关。
1
在肠道炎症和肿瘤发生中的作用
结直肠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居高不下。据统计,结直肠癌是全球第三常见的癌症,也是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等炎症性肠病的主要并发症。炎症性肠病和结直肠癌通常与炎症细胞因子的过度产生有关。
IL-1α/β、IL-6和TNF-α等炎症细胞因子在炎症促进的肿瘤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炎症小体在IL-1β加工中的关键作用,研究了NLRP3炎症小体在结肠炎和结肠炎相关癌症(CAC)中的作用。
▸ 炎症小体在控制肠道稳态和预防肿瘤中起作用
多个研究小组意外地发现炎症小体的成分在控制肠道稳态和预防肿瘤发生方面发挥着保护作用。
NLRP3、ASC或caspase-1缺陷的小鼠更容易患结肠炎和CAC。这种表型与局部和全身IL-1β和IL-18分泌减少有关。数据表明,NLRP3负责防止肠道炎症和肿瘤发生增加。
此外,观察到caspase-1对DSS诱导的结肠炎具有类似的保护作用。Casp1−/−小鼠在DSS治疗后表现出肠道炎症和NF-κB激活增强以及组织修复受损。
▸ IL-18可能介导了炎症小体对肠道的保护作用
IL-18是肠道稳态和炎症所必需的。研究发现,IL-18信号传导可防止DSS诱导的结肠炎和DSS+氧化偶氮甲烷诱导的CAC动物模型中的组织损伤。此外,外源性IL-18使Casp1−/−小鼠免受结肠炎诱发的体重减轻影响。因此,IL-18似乎负责NLRP3炎性体介导的针对肠道炎症、组织损伤和肿瘤发生的保护作用。
▸ NLRP3炎症小体在化疗抗肿瘤反应中起作用
还研究了NLRP3炎症小体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研究指出,NLRP3炎症小体对化疗诱导的抗肿瘤反应是必不可少的。从机制上看,化疗诱导的垂死肿瘤细胞释放的ATP激活了NLRP3炎症小体,进而通过IL-1β的分泌进一步激活产生IFN-γ的CTL。
考虑到用于激活NLRP3炎症小体的外源性ATP浓度远高于化疗诱导的垂死肿瘤细胞释放的ATP浓度(mM与μM),其他内源性NLRP3激活剂,如尿酸,可能在化疗期间释放,从而激活体内的NLRP3炎性小体。
2
NLRP3炎症小体和代谢紊乱
近几十年来,肥胖、2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急剧上升,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 肥胖患者的促炎细胞因子上调
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慢性炎症是代谢紊乱的一个关键预测因素。例如,肥胖与细胞因子产生的上调和炎症信号通路的激活有关。
肥胖状态下,脂肪组织中的炎症小体活化会导致促炎细胞因子的过度分泌,如IL-1β和IL-18等。这些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会引发炎症反应,进而影响胰岛素信号传导、葡萄糖代谢和脂质代谢,加剧肥胖相关的代谢紊乱。
▸ 炎症小体分泌IL-1β破坏胰岛素调节
NLRP3炎症小体在2型糖尿病(T2D)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作为代谢应激传感器,在治疗T2D的临床试验中加强了IL-1β受体拮抗作用。
IL-1β升高是发生T2D的危险因素,并通过拮抗胰岛素信号传导导致胰岛素抵抗。IL-1β还介导胰岛中长期高血糖(糖毒性)的毒性作用,导致β细胞破坏并调节葡萄糖诱导的胰岛素分泌。
最近的一项研究描述了慢性高血糖期间小鼠胰岛中IL-1β的分泌情况:高细胞外葡萄糖通过NLRP3炎症小体触发IL-1β分泌。
此外,NLRP3结合蛋白TXNIP作为胰腺β细胞死亡和外周葡萄糖摄取失败的介质,与T2D密切相关。
炎性小体在代谢综合征中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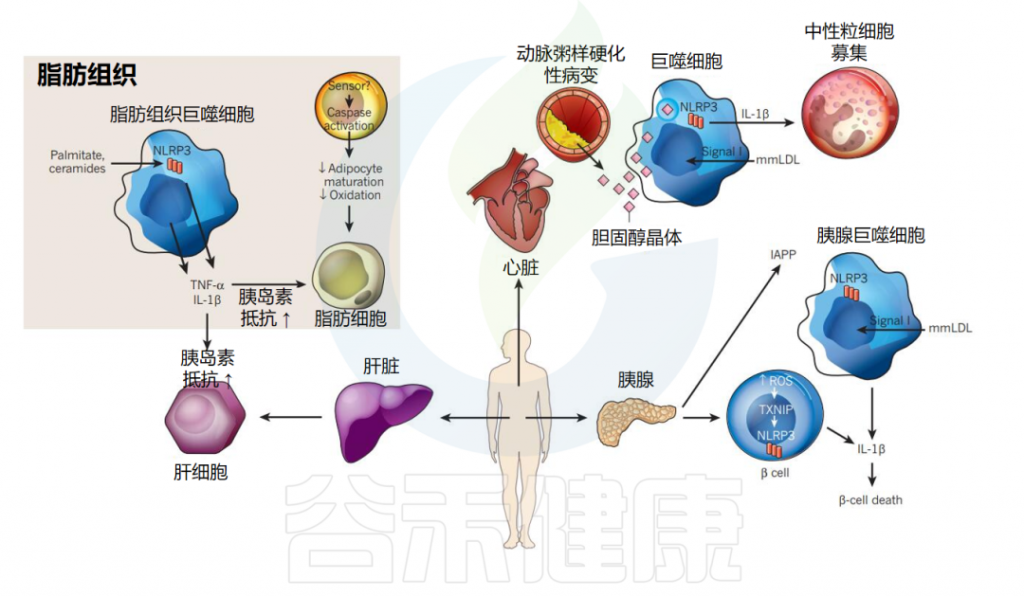
doi: 10.1038/nature10759.
▸ NLRP3炎症小体在动脉粥样硬化中起重要作用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NLRP3炎症小体在动脉粥样硬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其特征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炎性成分的积累和免疫细胞的募集。
观察到在早期饮食引起的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存在微小胆固醇晶体的沉积,这与巨噬细胞的募集有关。体外生成的胆固醇晶体在脂多糖引发的人外周血单核细胞和小鼠巨噬细胞中诱导NLRP3/ASC炎性体激活和caspase-1/IL-1β/IL-18裂解。
此外,使用骨髓嵌合体的体内实验表明,骨髓细胞来源的NLRP3、ASC和IL-1β/β在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活性氧(ROS)还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因此测试ROS在胆固醇晶体诱导的NLRP3炎性体激活中的参与将很有意义。
3
炎症小体和适应性免疫
NLRP3炎性小体除了在先天免疫反应中的促炎作用外,最近的研究强烈表明NLRP3炎性体介导的细胞因子(IL-1β和IL-18)在形成适应性免疫反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IL-1β调节早期TH17细胞分化
据报道,IL-1β信号传导可调节早期Th(辅助性T)17细胞分化,并在实验性变态反应性脑脊髓炎(EAE)诱导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机制上讲,IL-1β信号传导诱导IRF4和RORγt的表达,这是参与Th17分化的两个重要转录因子。IL-1β 还被证明可以与IL-23协同作用,诱导产生IL-17的 γδ T 细胞的发育,从而促进EAE的发展。因此,人类Th17细胞的分化需要IL-1β的存在。
▸ IL-18协同其他细胞因子影响T细胞的反应
与IL-1β相反,IL-18信号在Th细胞分化中的作用取决于其他协同细胞因子。例如,IL-18与IL-12的协同作用诱导产生IFN-γ的Th1细胞,而IL-18与IL-2的组合增强了IL-13(一种Th2细胞因子)的产生。
通过与IL-23协同作用,IL-18扩增极化Th17细胞产生的IL-17。因此,与IL-1β相比,IL-18在形成适应性T细胞反应方面表现出更灵活的功能,这可以解释IL-1β和IL-18在某些疾病模型(如肠道炎症和2型糖尿病)中的不同功能。
基于IL-1β和IL-18在T细胞分化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几个研究了炎症小体在T细胞介导的疾病中的作用。数据表明NLRP3在加剧EAE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由于抗原呈递巨噬细胞和DC需要NLRP3才能最佳地激活初始T细胞形成Th1和Th17效应细胞。
总之,NLRP3炎症小体介导IL-1β和IL-18的产生,IL-1β和IL-18与其他炎症细胞因子配合调节T效应细胞的产生并影响疾病进展。这些研究将炎症小体的作用扩展到适应性免疫的调节。
4
炎症小体和痛风
痛风是一种自身炎症性疾病,其特征是严重的关节炎症,导致关节病和相当大的疼痛。痛风与代谢紊乱密切相关,导致血尿酸水平升高(高尿酸血症)和 尿酸盐(MSU)晶体在关节中沉积。
▸ 尿酸盐是NLRP3炎症小体的有效激活剂
最近的研究阐明了尿酸盐(MSU)依赖性关节炎症的潜在机制。MSU在体外是NLRP3炎症小体的有效激活剂,并且MSU依赖性中性粒细胞募集在体内依赖于ASC衔接子、caspase-1和IL-1R。
IL-1β拮抗剂在临床试验中的成功支持了炎症小体调节的IL-1β在人类痛风和密切相关的假痛风中的致病作用。
5
炎症小体和肝损伤
尽管NLRP3炎性体在DSS诱导的结肠炎期间的组织损伤中发挥保护作用,但对乙酰氨基酚(APAP)诱导的肝损伤动物模型的研究表明,NLRP3炎性体会放大免疫反应并加剧肝损伤。
▸ NLRP3可能是造成肝损伤的关键介质
APAP治疗通过有毒代谢中间产物诱导肝毒性,导致肝细胞死亡。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TLR9和NLRP3炎症小体是APAP诱导的肝损伤和炎症的关键介质。TLR9检测APAP诱导的肝细胞死亡后释放的内源DNA,并上调pro-IL-1β和pro-IL-18的产生,这些物质进一步被NLRP3炎性小体裂解。
因此,TLR9和NLRP3炎症小体在APAP诱导的肝损伤和炎症过程中发挥着作用。然而,NLRP3炎症小体的刺激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基于APAP治疗诱导的急性和强烈的细胞死亡,从死亡细胞释放的尿酸、ATP、线粒体或透明质酸可能会激活TLR9或激活巨噬细胞中的NLRP3炎症小体。
此外,AIM2最近被鉴定为介导caspase-1激活和IL-1β/IL-18加工的胞质DNA传感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测试AIM2在肝损伤和其他涉及广泛细胞死亡的疾病模型(如脓毒症)中的作用。
▸ 拓展:其他炎症小体可能影响的疾病
NLRP3以外的NLRP突变与人类疾病相关。NLRP12突变与一种名为FACS2的类似FCAS的发热综合征有关。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患者的NLRP12突变可能破坏了该蛋白的NF-κB抑制活性。然而,考虑到NLRP12和NLRP3之间的高度同源性以及FCAS和FCAS2患者症状的相似性,这些患者的炎症小体活性可能存在失调。
NLRP1的突变与白癜风等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最近,NLRP2突变被发现与一例家族性Beckwith-Wiedmann综合征有关,这是一种导致胎儿过度生长和印记障碍的疾病。
此外,NLRP7突变与家族性和复发性葡萄胎有关,这是一种异常妊娠状态,胎盘绒毛退化,受精卵无法存活。这些基因突变参与的疾病机制以及炎症小体途径的潜在参与仍有待进一步阐明。
检测炎症小体激活的方法
激活炎症小体具有多个重要特征,包括ASC斑点的形成、促炎性细胞死亡、具有生物活性IL-1β/IL-18细胞因子的分泌以及HMGB1的表达。一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检测:
1.使用RT-qPCR检测NF-κB诱导的pro-IL-1β和NLRP3是否上调;
2.使用荧光显微镜或流式细胞术监测细胞系中ASC斑点的形成;
3.使用Western blot检测caspase-1的裂解或pro-IL-1β/IL-18的成熟;
4.使用ELISA测定IL-1β、IL-18或HMGB1的释放;
5.使用乳酸脱氢酶(LDH)测定或碘化丙啶(PI)染色法检测细胞焦亡;
6.使用检测IL-1β、IL-18分泌的报告基因功能细胞系。
以上方法各有利弊,可以适当的结合这些方法来检测炎症小体的激活。
✦
越来越清楚的是,炎症小体激活caspase-1以多种方式有助于保护宿主免受入侵微生物的反应。例如通过分泌IL-1β和IL-18诱导炎症,介导HMGB1等“警报素”的释放,并触发受感染宿主细胞的焦亡以消除微生物病原体。
炎症小体与肠道微生物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维持肠道稳态和调节免疫反应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炎症小体的功能具有两面性(有害与有益)。这种相互作用的失调可能导致各种胃肠道疾病的发生。因此,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监管,以限制异常激活和对宿主细胞的损害。
NLRP6炎性小体缺乏被证明与促进自身炎症的微生物群的扩张有关,如普氏菌科(Prevotellaceae)。炎症小体可以感知微生物群成员或群落,调节组织修复和再生,以及在稳态和炎症状态下协调粘膜免疫反应。
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炎症小体缺乏和肠道菌群的改变都与人类代谢综合征(如肥胖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倾向有关。炎症小体对肠道菌群的调节是否会影响体重、代谢和炎症,预计将成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Manshouri S, Seif F, Kamali M, Bahar MA, Mashayekh A, Molatefi R. The interaction of inflammasomes and gut microbiota: novel therapeutic insights. Cell Commun Signal. 2024 Apr 2;22(1):209.
Liang Z, Damianou A, Di Daniel E, Kessler BM.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controlled by the interplay between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emerging drug target opportunities. Cell Commun Signal. 2021;19:1–12.
Sim J, Park J, Moon J-S, Lim J. Dysregulation of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in glioma. Cell Commun Signal. 2023;21(1):239.
Pellegrini C, Antonioli L, Lopez-Castejon G, Blandizzi C, Fornai M. Canonical and non-canonical activation of NLRP3 inflammasome at the crossroad between immune tolerance and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Front Immunol. 2017;8:36.
Davis BK, Wen H, Ting JP. The inflammasome NLRs in immunity, inflammation, and associated diseases. Annu Rev Immunol. 2011;29:707-35.
Carriere J, Dorfleutner A, Stehlik C. NLRP7: From inflammasome regulation to human disease. Immunology. 2021 Aug;163(4):363-376.
Lamkanfi M, Dixit VM. Modulation of inflammasome pathways by bacterial and viral pathogens. J Immunol. 2011 Jul 15;187(2):597-602.
Strowig T, Henao-Mejia J, Elinav E, Flavell R. Inflammasomes in health and disease. Nature. 2012 Jan 18;481(7381):278-86.
Próchnicki T, Latz E. Inflammasomes on the Crossroads of Innate Immune Recognition and Metabolic Control. Cell Metab. 2017 Jul 5;26(1):71-93. doi: 10.1016/j.cmet.2017.06.018. PMID: 28683296.